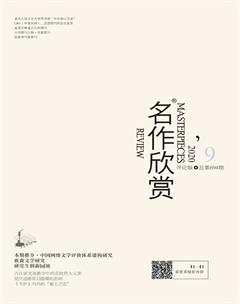解析后現代主義小說《惡棍來訪》主題的不確定性
摘 要: 2011年,美國當代女作家珍妮弗·伊根憑借小說《惡棍來訪》一舉斬獲普利策文學獎,作為一部典型的后現代主義小說,伊根通過極具實驗性的手法呈現了美國從20世紀80年代到現在四十年跨越間,人們在時間流逝中遭遇的青春消逝、夢想幻滅與自我崩潰。本文試在后現代主義小說理論基礎之上,再加以借鑒伊哈布·哈桑在不確定性特征的理論貢獻,分析《惡棍來訪》主題的不確定性,一方面揭示后現代主義社會的混亂與無序,另一方面也表達作者對科技背景下內心焦慮人們的深刻關懷。
關鍵詞:珍妮弗·伊根 《惡棍來訪》 后現代主義 伊哈布·哈桑 不確定性
一、引言
美國當代女作家珍妮弗·伊根(Jennifer Egan ,1962—)的長篇小說《惡棍來訪》(A Visit from Goon Squad)一經出版便引起讀者和媒體的關注,并斬獲包括普利策獎在內的多個重要文學獎項。普利策獎委員會評價該書:“創造性地發掘數字時代下人類的成長、老化,展現出對急速變化的社會文化強烈的好奇。”a小說以美國人狂熱追求的搖滾樂興衰為背景,從十三個不同視角出發,展現了一群熱愛朋克樂的音樂人近五十年起伏曲折的故事。伊根不僅關注音樂與文化,還關注社會及身處其中的美國X一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書寫他們的迷惘、叛逆、追求自我,給予美國X一代深刻的人文關懷,展望美國當代科技影響下的未來生活。
目前國外對《惡棍來訪》的研究分析還比較少,現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對伊根的訪談及書評、音樂內涵、意象研究等方面,國內的研究主要涉及小說的敘事技巧、空間視域、創傷主題、主人公精神焦慮的分析等。作為一部典型的后現代主義小說,伊根在其中加入了大量極具實驗性的元素,如游戲化的語言、電子媒介及超文本的使用、敘事的反情節化等,充斥著不確定性與隨意性,故本文試在后現代主義小說理論基礎之上,再加以借鑒伊哈布·哈桑不確定性特征的理論貢獻,從主題這一大方面來分析《惡棍來訪》彌漫的不確定性這一特征,為解讀作品提供一個新穎的角度。
二、后現代主義文學與伊哈布·哈桑
20世紀中葉,后現代主義在西方社會中出現并引領了文化潮流,涉及哲學、語言學、社會學、文學藝術等領域。“他們懷疑任何一種連續性,認為現代主義的那種意義的連貫、人物行動的連貫、情節的連貫是一種‘封閉體(closed form)寫作,必須打破,以形成一種充滿錯位式的‘開放體(opened form)寫作,即竭力打破它的連續性,使現實時間與歷史時間隨意顛倒,使現實空間不斷分割切斷。”b后現代主義文學呈現出“解體”的趨勢,充斥著含混、異端、不連續、實驗性、隨意性的特點。
在對后現代主義文學這一領域的探索之中,伊哈布·哈桑是美國最早從事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的學者,并且也是頗受爭議的多產的評論家之一。 哈桑在文學 “無以言表”和“自我質疑”的特性中找到了所謂的 “不確定性 ”(Indeterminacy) 和“內向性” (Immanence),從而獨創了“不確定的內向性”(Indetermanence)一詞,并認為不確定性特征是后現代主義文學的本質特征。具體地說:“‘不確定性是指模棱兩可、無連續性、替代、差異性、多元性、去形式化、去合法性和反叛。這些概念又集中體現為‘破壞或‘破壞意志,即要質疑西方的整個話語體系。”c通過不確定性,后現代主義文學對傳統文學權威的挑戰與批評可見一斑。下文將著重討論分析不確定性在《惡棍來訪》主題上的體現。
三、《惡棍來訪》主題的不確定性特征
傳統小說的創作通常揭示了作者確定的目的,想要傳達給讀者確切的消息,其強調的是通過某種話語或元素起到對世人教誨的作用。然而,在后現代主義文學作品中,讀者通常找不到作品某種確切的意圖,從而瓦解了作品主題的“中心化”。在后現代主義作品中,讀者不再受作者的控制,可以通過自己的理解對作品產生獨特的見解。《惡棍來訪》是一部典型的后現代主義小說,在閱讀完這部小說后,會產生以下疑問:“小說是想講述家庭關系的問題嗎?”“是在寫科技對現代社會產生的影響嗎?”“還是在說人與人之間交際的現狀?”顯然答案不止一種,主題不止一個,作者給讀者造成了不確定的閱讀體驗,接下來本文會進一步闡釋對主題的兩種不確定性分析。
(一) “時間”角色的不確定性——時間是“惡棍”嗎?
有學者認為這部小說被廣泛鑒賞的原因之一就是作者對時間、科技以及人性的描寫和處理,其中,關于“時間”是否就是題目中的“惡棍”的主題引起了廣泛的討論——作為惡棍的時間,既是使人遭遇曲折變故的幕后推手,也是治愈傷痛的良藥。
惡棍,指的是胡作非為、作惡多端的人,這個詞語在這部小說中共出現了兩次,第一次出現在第17章,過去赫赫有名、如今卻身材走形且默默無聞的吉他手博斯科說道:“你再也不是二十年前的那個自己了,時間是個惡棍,不是嗎”d,這似乎暗示著時間像個惡棍一樣,掠奪了他的青春、夢想、天真與成功,他抱怨道:“我是怎么從一個搖滾巨星變成如今的無人問津的死胖子呢?”e答案毫無疑問是歲月的流逝。“惡棍”一詞第二次出現是在小說的結尾部分,本尼邀請多年好友也曾是搖滾明星的斯科蒂參加一場音樂演出,可臨到演出前,斯科蒂卻遲遲不敢上臺,本尼問他:“時間是個惡棍,你就這樣被它打敗嗎?”f斯科蒂搖了搖頭,說道:“是時間贏了。”這也意味著斯科蒂接受了現實,承認了時間所帶給他的創傷,在時間的長河緩緩流去之際,也帶走了他的青春年華與夢想。雖然“惡棍”一詞只出現在小說中兩次,但卻貫穿著整部小說。本尼,是著名音樂制作人,在他成功輝煌的光環下卻靠著金片來維持自己的性欲望。作為一個正值壯年的男人在異化的社會與時間無情的摧殘下,他喪失了性沖動,靠著物品來維持。盧,是小說中早年間搖滾樂領域里一個成功的音樂人,他雖有六個孩子,卻與不同女性保持著情人關系,他總是反復強調自己不會變老,可當他再次出現在小說的第五章時,他年事已高,躺在病床上無法自理。小說沒有采用順敘的手法,而是將時間打亂,前一章在某一時間,下一章又來到了幾十年后,伊根這樣描寫仿佛在向讀者展示著時間的殘酷。
但是,時間也不盡然全是惡棍,它給人帶來的不是掠奪的無情與殘暴,而是自我的救贖,小說中薩沙便是其中的一個例子。薩沙的父親在她很小的時候便拋棄了她,由于不幸的童年經歷,薩沙逐漸變得心理扭曲,長大成人后,她便有了偷竊癖的疾病,靠著心理醫生治療得以維持正常生活。幸運的是,薩沙并沒有放棄自己的夢想與激情,而是選擇迎接生活與時間的挑戰,她結了婚并育有兩個孩子,小說的最后她過上了不再靠整日偷東西來緩解壓力,如同正常人的生活。可見時間在薩沙身上留下的痕跡是溫柔的,時間治愈了薩沙。另一個例子便是多莉,她曾是一位為名人工作的公關,在她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在一次宴會上她犯下了巨大的錯誤導致很多宴客被燒傷,由此被判處十五年監禁,這斷送了她的事業。轉眼十五年過去了,她雖出獄卻不復往日風光,她選擇回歸家庭。常年不與她親近的女兒璐璐卻在她出獄在家待著的這些日子里,慢慢有了接觸與交流,開始理解她過去的不易,在這一章節的最后,母女倆相擁坐在沙發上安靜地聽著廣播,吃著水果,一片祥和。可見時間是治愈兩人心理隔閡的良藥,是連接父母與孩子之間情感流動的橋梁。曾經對婚姻失望的泰德舅舅也走出了婚姻的牢籠,邁向了幸福的晚年……
總而言之,時間在有的人身上留下了創傷,卻給另一部分人帶去了新的生活希望。小說題目“惡棍來訪”,看似是把時間比作了惡棍,但在小說多處地方卻也能看到時間的溫柔與魅力。在后現代主義的世界里處處充滿了悖論與矛盾,它們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無限的遐想與不確定。
(二)“科技”角色的不確定性——先進的科技是否有利?
除了對“時間是否為惡棍”不確定性的探討之外,小說中對發達的科學技術帶給人怎樣的影響也體現了不確定性特征。隨著社會快速的發展,科技的發展也呈現出蓬勃迅猛之勢,隨之而來的各種電子多媒體技術滲透進每個人的生活中,而這些信息技術也正是后現代主義社會的標簽之一。對于迅速發展的先進科技給人類帶來的影響是有利還是不利,也是這部小說中主題的不確定性表現之一。
科技的發展給人類的生活帶來了便利,在小說的第五章,在盧快要走到生命的盡頭之時,本尼是他的信徒,他用電腦把昔日的好友(除了斯科蒂)全部召集起來,一起去醫院看望垂危的盧。因為有了強大的互聯網,才沒有讓惺惺相惜的好友錯過生命的最后一程,作者在書中特意提到了“電腦”,因為有了“電腦”才組織到了眾多伙伴,似乎是對先進科技的肯定與贊揚。除此之外,在小說中,作者不僅采用了文字作為敘述手段,更創新地采用了幻燈片、空白頁以及樹形圖、流程圖、關系圖等方式完成了一個章節的敘述,作者大膽地采用了這些后現代主義媒介元素,是對傳統小說創作手法的巨大挑戰。
然而,在《惡棍來訪》中我們也能看到作者對先進科技的擔憂與批評。在音樂制作人本尼的創作過程中,作者表達了數字化對藝術創作影響的擔憂,更新換代的社會潮流使搖滾樂的光環日漸黯淡,對本尼的創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他不再有豐富的靈感,也產生了自我懷疑與否定。在小說的結尾,伊根向我們展示了未來紐約城的生活面貌,一個三個月大的嬰兒也可以通過點擊自己手中的鼠標而下載歌曲,作者夸張的描述無疑諷刺了社會飛速進步的科技。不僅如此,先進的科技對人類的影響是全方位的,科技也潛移默化地影響著語言的使用。比如璐璐與多莉的對話使用的是支離破碎的英語:“Can I just T you”, Lulu asked.“You mean--”“, Now. Can I T you now.” The question was a formality; she was already working her handset. An instant later Alexs own vibrated in his pants pockets; he had to jostle Cara- Ann to remove it. 這種現象在現代社會非常普遍。科技進步了,人類交流的方式卻倒退了,有的人因為長期活在虛擬世界,甚至阻礙了現實中與人相處的能力,外表光鮮亮麗的科技發展之下,是逐漸被異化、迷失自我的人類。
先進科技是一把雙刃劍,關于其和人類的關系,不僅是在這部小說中,更是在當代社會中都蒙著一層不確定性的面紗。
四、總結
后現代主義社會充斥著無序與混亂,美國女作家伊根用她獨特的方式對她眼中的后現代主義文學做出了闡釋。本文通過對《惡棍來訪》主題的不確定性特征的分析,一方面是為加深讀者對后現代主義文學的理解,更是揭示了當代社會的無窮變幻與種種不確定。
a 譚敏:《迷失在時間里的人生—— 評詹妮弗·伊根的新作〈惡棍來訪〉》,《外國文學動態》2011年第4期,第 19—21頁。
b 陳世丹:《論后現代主義不確定性寫作原則》,《河南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2期,第66—68頁。
c 毛娟:《 伊哈布·哈桑的后現代主義文學批評思想評析》,《國外理論動態》2006年第10期,第55—58頁。
def〔美〕詹妮弗·伊根:《惡棍來訪》,張竝譯,重慶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頁,第140頁,第358頁。
作 者: 吉辰,天津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2018級在讀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學、比較文學。
編 輯: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