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寫本《都僧統康賢照和尚邈真贊并序》與石城鎮粟特部落徙居敦煌考論
鄭炳林 黃瑞娜
(蘭州大學 敦煌學研究所,甘肅 蘭州 730020)
《新唐書·地理志》及敦煌文獻《沙州都督府圖經》《壽昌縣地境》《沙州伊州地志》等都記在唐初至武周時期位于羅布泊地區的石城鎮一帶居住著一支粟特人康艷典部落,他們大概于唐朝貞觀年間從中亞遷徙到石城鎮地區,將石城鎮一帶的鄯善人驅趕到伊州納職縣,康艷典部落成為石城鎮的主人,其后代一直擔任唐石城鎮使的職務,主持石城鎮的防務工作。根據敦煌文獻的記載唐開元年間沙州敦煌縣管轄有由粟特人組成的從化鄉,經學術界研究推測,從化鄉的粟特人是由從羅布泊地區的石城鎮遷徙而來的粟特人建立的,我們從敦煌文獻的記載得知,從化鄉最少有兩個里四個村落組成(1)P.3559《唐天寶年間(750)敦煌郡敦煌縣從化鄉差科簿》,錄文參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6年,第229-241頁。,我們從晚唐五代敦煌文獻的記載得知,敦煌文獻記載的康家莊、安家莊、石家莊、曹家莊、羅家莊、石家莊等都是從化鄉管轄下的村落,這些村落分布在敦煌城周邊地區,即城南園、城北園、城東園、城西園和東水池、西水池、北水池或者城南莊、城北莊、城東莊、城西莊等粟特人聚落(2)參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村莊聚落輯考》,收入《2000年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文集:紀念敦煌藏經洞發現暨敦煌學百年(歷史文化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162頁;鄭炳林《晚唐五代敦煌地區的胡姓居民與聚落》,《法國漢學》第十輯《粟特人在中國—歷史、考古、語言的新探索》,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第178-190頁;Zheng Binglin, Non-Han Ethnic Groups and Their Settlements in Dunhuang during the Late Tang and Five Dynasties, Les Sogdiens en Chinse, Paris: école fran?aise d’Extrême-Orient, 2005, pp. 343-362.。這些粟特人是什么時間遷徙敦煌的,遷徙的原因是什么,陳國燦《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曾就從化鄉的出現與石城鎮康艷典部落遷徙敦煌有關,并認為遷徙的時間是唐神龍年間突騎施闕啜忠節帥部進入且末河流域,隨此而引來了吐蕃兵向塔里木盆地東部的進占;粟特人聚落在石城鎮的消失與闕啜在這一地區的劫掠同時發生,推測居住在且末河流域的粟特人在受到闕啜的暴力威脅時迅速逃往敦煌以求得沙州刺史的保護(3)陳國燦《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收入氏著《敦煌學史事新證》,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70-376頁。。但是未能就敦煌粟特人聚落與石城鎮康艷典部落的關系提出直接的資料證據。我們在對《都僧統康賢照和尚邈真贊并序》進行研究發現,康賢照祖上就是石城鎮人,是康艷典部落后裔。因此我們有必要重新對敦煌粟特人聚落來源及其原因進行梳理。
一、《都僧統康賢照和尚邈真贊并序》與石城鎮粟特人康艷典部落
康艷典部落徙居敦煌,直接記載是P.3556《都僧統康賢照和尚邈真贊并序》,P.3556《敦煌名人名僧邈真贊集》第一篇篇首殘缺,篇末亦無撰寫題記。第一行曰:“河西管內佛法主賜紫□□(沙門)”,由本卷《都僧統氾福高和尚邈真贊并序》福高僧官結銜為:“大唐敕授歸義軍應管內外都僧統充佛法主京城內外臨壇供奉大德兼闡揚三教大法師賜紫沙門”,又曰:“洎金山白帝,……遂封內外都僧統之號,兼加河西佛法主之名。”《都僧統陳法嚴和尚邈真贊并序》記載:“爰至吏部尚書秉政蓮府,大扇玄風,封賜內外都僧統之班,兼加河西佛法主之號。”由此看來,“河西管內佛法主”乃都僧統加的號。贊文稱“河西教主,蓮府英賢”,當是敦煌某位都僧統。又按P.3556第二、第三篇乃是繼康賢照出任都僧統的氾福高、陳法嚴,疑此篇乃是康賢照的邈真贊。序文曰:“[石]城名宗,敦煌鼎族。”不記載其姓氏源流,P.4660《瓜州刺史兼左威衛將軍康秀華邈真贊并序》記載“偉哉康公,族氏豪宗”,亦相同。又按序文內容,綿帳上方畫彌勒佛、諸菩薩,下方畫有其形影,可知此篇乃供養像題贊。此篇諸家皆略而不錄。《敦煌遺書總目索引》伯希和劫經錄:“3556集文一卷(兩面抄)。有氾和尚、陳和尚、賈和尚、曹法律尼(曹大王之侄女)、靈修寺尼張戒珠(張議潮之孫女)等邈真贊,又張氏(張淮深之女)墓志銘、清泰三年曹元德轉經疏等。”P.3556是由多篇廢棄文書粘連在一起抄寫邈真贊,其中康賢照、陳法嚴邈真贊背面書寫的是《沙州諸寺尼修習禪定記錄》,這是一篇前后殘缺的文書,中間有“乘:圓戒”字樣,表明這是大乘寺等待出家女性沙彌尼修習記錄,記錄了部分出家尼修習問想甄別兼判的記錄,是道場度僧尼的必要環節,每人一行,前面是問想記錄,后面是甄別兼判成績。1992年我們在輯錄這篇文書時將其定名為“河西管內佛法主賜紫邈真贊并序”,主要是根據第一行殘文“河西管內佛法主賜紫□□”(4)參鄭炳林《敦煌碑銘贊輯釋》,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69-369頁。,而后學術界將其定名為“康賢照邈真贊并序”(5)施萍婷《敦煌遺書總目索引新編》“伯希和劫經錄”:“P.3556a 康賢照邈真贊 按:此依姜伯勤、項楚、榮新江合著《敦煌邈真贊校錄并研究》定名。”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第286頁。饒宗頤主編《敦煌邈真贊校錄并研究》有錄文,并定名為《康賢照邈真贊》,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4年,第213-214頁。吳鋼主編《全唐文補遺》第9輯(西安:三秦出版社,2007年,第317頁)、張志勇《敦煌邈真贊釋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16-317頁)有錄文,沿用饒宗頤定名。上海古籍出版社等編《法藏敦煌西域文獻》第25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48-249頁)有圖版,并定名為《康賢照邈真贊》。參照諸家研究定名,我們將這篇邈真贊定名為《河西管內都僧統康賢照和尚邈真贊并序》。榮新江《敦煌邈真贊年代考》(見《敦煌邈真贊校錄并研究》,第362頁)認為這篇贊文撰寫于902年前后。。康賢照,敦煌大云寺僧,乾符三年至六年接替唐悟真出任都僧錄,根據P.2856V《唐景福二年癸丑歲(893)十月十一日沙州某寺納草歷》、P.2856V《乾寧二年三月十日營葬都僧統榜》、P.4597V《光化三年、四年雜寫書函》、S.2614V《唐年代未詳(895)沙州諸寺僧尼名簿》等記載,景福二年前出任副僧統兼都僧錄,乾寧二年(895)唐悟真圓寂后出任都僧統。又根據S.1604《天復二年(902)四月廿八日沙州節度使帖都僧統等》《天復二年四月廿八日都僧統賢照帖諸僧尼寺綱管徒眾等》《天復二年河西都僧統賢照下諸寺綱管徒眾帖》的記載天復二年康賢照仍然任都僧統,榮新江認為天復二年是康賢照與交替年代(6)榮新江《關于沙州歸義軍都僧統年代的幾個問題》,《敦煌研究》1989年第4期,第70-78頁。。我們根據S.1073《唐光化三年(900)四月徒眾紹浄等請某乙為寺主牒稿》記載:“(前缺)請某乙為寺主。右件僧,戒珠圓浄,才智洪深,善達時機,權謀越群,凡庭葺績,藉此良能。伏望都僧統和尚仁明,神筆判差,希垂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光化三年四月日徒眾紹浄牒。”都僧統指的是康賢照。S.2574《唐天復五年(905)八月靈圖寺徒眾上座義深等大行充寺主狀并都僧統判辭》記載:“靈圖寺徒眾上座義深等狀。眾請大行充寺主。右前件僧,徒中俊德,務眾多能。順上有波驟之勤,訓下存恩恤之義。本性迅速,無羽同飛。邊鄙鴻基,實藉綱要。伏望都僧統和尚仁恩詳察,特賜拔擢。伏請判憑處分。牒件狀如前,謹牒。天復伍年八月日靈圖寺徒眾義深等牒。徒眾靈俊,徒眾,徒眾政信,徒眾惠,徒眾,徒眾靈□,徒眾義深。狀稱多能,無羽能飛者。若闕六翮,豈可接云而高翔也。然來意難違,便可□□。□日。賢照。”(7)鄭炳林、鄭怡楠《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892-899頁。都僧統康賢照與都僧統氾福高的交替年代應當在天復五年八月之后。康賢照擔任敦煌都僧統的時間至少在十年以上。
《都僧統康賢照和尚邈真贊并序》記載敦煌康氏家族的郡望稱:
[和尚俗姓康氏,香號賢照。乃石]城名宗,敦煌鼎族。□□□□□□,□□不戀煩囂。長習捐簪,□□□□□□。遂得鵝珠進戒,皎皎以秋月齊圓。□□□□,□□以春花竟彩。精通萬法,辯□□(若河)決爭流。奯曉千門,談如傾盆競涌。蓮花三座訓迷邪,指中道真如;師子五升化昏愚,悟頓途性相。談空才暇,乃思有相之因;隨眾分身,故表眾生之果。況知色塵號假,色方示有;成生法體號空,應法還為寂滅。(8)鄭炳林、鄭怡楠《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第892頁。
這是敦煌文獻中將敦煌粟特人康氏同石城鎮康氏聯系起的最明確的記載,雖然文獻記載有殘缺,但是“城名宗敦煌鼎族”很清楚,而“城”字最有可能與“域”寫混,無論是西域還是石城,都是對康氏家族族源的追述,我們經過仔細辨認,應當是“城”字而非“域”字,因此城字前面所殘缺的應當是“石”。這里追述的康賢照家族族源是從石城鎮遷徙而來的,因為從康艷典起到石城鎮將康拂耽延,康氏家族最輝煌的時期是在石城鎮擔任鎮將階段,康賢照追述他們這個家族史是為了表明他們家族在唐朝時期的地位不一般,只有是石城名宗,才能成為敦煌鼎族。P.4660《瓜州刺史兼左威衛將軍康秀華邈真贊并序》記載:“偉哉康公,族氏豪宗。”《都知兵馬使康通信贊》記載:“懿哉哲人,與眾不群。”(9)鄭炳林、鄭怡楠《敦煌碑銘贊輯釋(增訂本)》,第375、430頁。P.3258《祈愿文》記載:“康公駿豪迎機,挺用濟時;耿介不群,指揮無滯。”這些記載都表明敦煌粟特人康氏家族出身不同一般,能夠與敦煌的大姓豪宗李氏、索氏、陰氏、氾氏、張氏并駕齊名,號稱敦煌的豪宗鼎族。此后敦煌粟特名人輩出,康氏家族除了康秀華之外還有都知兵馬使康通信“懿哉哲人,與眾不群。剛柔相伴,文質彬彬。盡忠奉上,盡孝安親。葉和眾事,進退俱真。助開河隴,效職轅門。橫戈陣面,驍勇虎賁。番禾鎮將,刪丹治人。先公后私,長在軍門。天庭奏事,薦以高勛。姑臧守職,不行遭窀。”也是敦煌的名人。除了康氏之外,安氏家族也是敦煌的名望家族,最初的歸義軍節度副使安景旻等就是其代表。敦煌的粟特人部落后裔,除了康賢照外都沒有記載其族源,康賢照的這一記載對于我們探究敦煌粟特人部落的源流和從化鄉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義。
敦煌的粟特人聚落是從石城鎮遷徙而來的,而石城鎮的粟特人是何時徙居而來的?有關羅布泊石城鎮粟特人康艷典部落徙居石城鎮的相關記載主要保存在敦煌文獻和《新唐書·地理志》中,通過這些記載我們得知羅布泊地區粟特人康艷典部落是何時遷徙到石城鎮的以及石城鎮康艷典部落在羅布泊地區的活動情況。首先是《壽昌縣地境》和S.367《沙州伊州地志》的記載,他們的成書年代和記載內容基本接近,《壽昌縣地境》記載到石城鎮地區的粟特人康艷典部落:
石城,本漢樓蘭國。《漢書·[西域傳]》云:去長安六千一百里。地多沙鹵,少田出玉。傅介子既殺其王,漢立其弟,更名鄯善。隨(隋)置鄯善鎮。隨(隋)亂,其城乃空。自貞觀中康國大首領康艷典東據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名其城曰興谷城。四面并是沙鹵。上元二年改為石城鎮,屬沙州。東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
新城,康艷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漢名弩支城。東去鄯善三百三十里也。
葡萄城,康艷典筑。在石城北四里。種葡萄于城中,甚美,因號葡萄城也。
薩毗城,在鎮城東南四百八十里。其城康艷典置筑,近薩毗城澤險,恒有土蕃、土谷賊往來。(10)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61頁。
《壽昌縣地境》撰寫時間是后晉天福十年開運二年(945),為州學博士翟奉達為壽昌張縣令撰寫的,記載壽昌縣史事的下限是建中初年。通過這些記載我們得知,康艷典部落于貞觀中東遷鄯善之后,共修筑了石城、新城、葡萄城和薩毗城,其中石城、新城和葡萄城就是指羅布泊三城。S.367《沙州伊州地志》記載除了個別字之外,與《壽昌縣地境》相同:
石城鎮,東去沙州一千五百八十里,去上都六千一百里。本漢樓蘭國。……貞觀中,康國大首領康艷典東來居此城,胡人隨之,因成聚落,亦曰典合城。四面皆是沙磧。上元二年改為石城鎮,隸沙州。
新城,東去石城鎮二百卌里。康艷典之居鄯善,先修此城,因名新城,漢為弩支城。蒲桃城,南去石城鎮四里,康艷典所筑,種蒲桃此城中,因號蒲桃城。
薩毗城,西北去石城鎮四百八十里,康艷典所筑,其城近薩毗澤,山[路]險阻,恒有吐蕃及吐谷渾來往不絕。(11)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第65-66頁。
另外P.5034《西州圖經》殘卷新城、葡萄城、薩毗城也記載東徙的粟特人康艷典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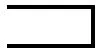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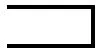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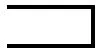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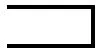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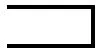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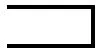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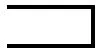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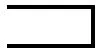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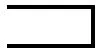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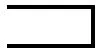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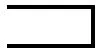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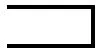
這個記載應當要詳細于《壽昌縣地境》和《沙州伊州地志》的記載,而且比較正確,很遺憾由于文獻的殘缺,留下的內容非常有限,就從這些有限的記載中我們得知,前二者的內容都是抄寫本卷而來的。特別是關于葡萄城的得名,是因康艷典種葡萄于城中而得名,足以體現出來其記載價值之高:“二所葡萄故城,并破壞,無人居止。一城周回二百五十步,高五尺以下。右在山頭,壘石為城,去平川七百步,其山無水草樹木,北去艷典新造城四里。一城周回一百四步,高五尺已下。右在平川,北去艷典新造城四里。”(13)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第49頁。就是說康艷典在原來的兩所破壞故城之外又重新建造葡萄城。我們從這些記載得知,康艷典部遷徙到石城鎮地區之后,主要占據石城鎮、葡萄城和新城等三座城及距離遙遠的薩毗城。葡萄城和新城處于石城鎮通往于闐道路上,薩毗城是經由播仙鎮進入吐蕃境內的交通關隘。
粟特人康艷典部落在石城鎮的活動情況在《新唐書·地理志》也有相應的記載:“又一路自沙州壽昌縣西十里至陽關故城,又西至蒲昌海南岸千里。自蒲昌海南岸,西經七屯城,漢伊修城也。又西八十里至石城鎮,漢樓蘭國也,亦名鄯善,在蒲昌海南三百里,康艷典為鎮使以通西域者。又西二百里至新城,亦謂之弩支城,艷典所筑。”(14)[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43下《地理志七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151頁。康艷典占據石城鎮之后,唐命康艷典為鎮使,大約與播仙鎮同時建鎮,時間為上元中(674-676)。
康艷典部落遷徙石城鎮的時間,我們根據S.367《沙州伊州地志》記載伊州納職縣:“右唐初有土人鄯伏陀,屬東突厥,以征稅繁重,率城人入磧奔鄯善,至并吐渾居住,歷焉耆,又投高昌,不安而歸,胡人呼鄯善為納職,既從鄯善而歸,遂以為號耳。”(15)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第68頁。這里記載鄯伏陀從唐初從鄯善返回,具體時間我們根據伊州部分記載:“貞觀四年首領石高年率七城來降,我唐始置伊州。”(16)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第66-67頁。應當發生于同一個時間,即貞觀四年(630)。這也可以從《元和郡縣圖志》伊州納職縣的記載中得到印證:“其城鄯善人所立,胡謂鄯善為納職,因名縣焉。”(17)[唐]杜佑撰,賀次君點校《元和郡縣圖志》卷40,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第1030頁。《舊唐書·地理志》記載伊州:“納職 貞觀四年,于鄯善胡所筑之城置納職縣。”(18)[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40《地理志三》,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第1644頁。《新唐書·地理志》記載:“納職,下。貞觀四年以鄯善故城置。”(19)[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40《地理志四》,第1046頁。既然鄯伏陀是唐貞觀四年從鄯善遷徙回伊州納職縣,其遷徙出鄯善的原因肯定與康艷典部落東徙石城鎮有直接關系,或者就是康艷典部落將鄯伏陀部落趕出鄯善而投降唐朝建立石城鎮。
石城鎮的設置時間,《新唐書》《舊唐書》都沒有記載,我們只能根據唐朝在西域局勢進行推斷。根據《新唐書·西域傳》焉耆記載:“太宗貞觀六年,其王龍突騎支始遣使來朝。自隋亂,磧路閉,故西域朝貢皆道高昌。突騎支請開大磧道以便行人,帝許之。高昌怒,大掠其邊。……高昌破,歸向所俘及城,遣使者入謝。”(20)[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221上《西域傳上》,第6229頁。直到貞觀十四年侯君集破高昌,西域入朝路線要么經高昌走大海道或者伊吾道,要么經焉耆直達敦煌的大磧路。就是說行經鄯善的道路還沒有重新開啟,因此石城鎮也就沒有設置。后安西都護郭孝恪平焉耆,行軍路線仍然經過西州走銀山道,而不是經鄯善北上進攻焉耆,康艷典部落還沒有歸附唐朝政府。唐朝平定焉耆完全改變西域政局的格局,為控制西域南道創造了條件,從焉耆往南就很容易控制鄯善。唐朝政府平定龜茲,將安西都護府遷徙到其都城,統龜茲、于闐、碎葉、疏勒等四鎮,鄯善就成為唐朝管轄范圍,康艷典部落很可能就是這個時期歸附于唐朝政府。高宗時期,“徙安西都護府于其國,以故安西為西州都督府,即拜左驍衛大將軍兼安西都護麴智湛為都督。西域平。帝遣使者分行諸國風俗物產,詔許敬宗與史官撰《西域圖志》。上元中,素稽獻銀頗羅、名馬。”(21)[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221上《西域傳上》,第6232頁。《壽昌縣地境》及S.367《沙州伊州地志》記載鄯善于“上元二年,改為石城鎮,隸沙州。”(22)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第61、65頁。康艷典就是這個時期出任石城鎮使。
唐朝設置石城鎮很可能與防御吐蕃西進、隔斷吐蕃與西突厥合勢反唐有很大關系。“貞觀九年,詔李靖為西海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積石道,任城王道宗鄯善道,李道彥赤水道,李大亮且末道,高甄生鹽澤道,并為行軍總管,率突厥、契苾兵擊之。”(23)[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221上《西域傳上》,第6225頁。從行軍總管中有鄯善、且末、鹽澤道看,唐朝采取東西合圍。其中“大亮俘名王二十,雜畜五萬,次且末之西。伏允走圖倫磧,將托于闐,萬均督銳騎追亡數百里,又破之。士乏水,刺馬飲血。君集、道宗行空荒二千里,盛夏降霜,乏水草,士糜冰,馬秣雪。閱月,次星宿川,達柏海上,望積石山,覽觀河源。”(24)[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221上《西域傳上》,第6226頁。吐谷渾滅亡之后,吐蕃遂有其地,乾封初年,吐谷渾在吐蕃逼迫之下投降唐朝,唐朝政府準備將其部落徙居涼州之南山。咸亨元年吐蕃入侵羈縻十八州,率于闐取龜茲撥換城,安西四鎮并廢。唐派遣邏娑道行軍大總管征吐蕃,“王師敗大非川,舉吐谷渾地皆陷”,遂徙吐谷渾于靈州,置安樂州。上元二年(675)吐蕃遣大臣論吐渾彌請和,上元三年(676)吐蕃攻打唐鄯、廓、河、芳等州。石城鎮實際上就是為了防御吐蕃進入唐西域地區而設置的軍鎮,同時設置的鎮還有播仙鎮。
唐高宗上元二年之后,粟特人康艷典部落一直擔任石城鎮使,根據P.2005《沙州都督府圖經》廿祥瑞蒲昌海五色記載:
蒲昌海五色。右大周天授二年臘月得石城鎮將康拂耽延弟地舍撥狀稱:“其蒲昌海水舊來濁黑混雜,自從八月已來,清明徹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羅門云:‘中國有圣天子,海水即清無波。’奴身等歡樂,望請奏圣人知者。”刺史李無虧表云:“淮海水五色大瑞,謹檢《瑞應圖·禮升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傔 海夷也。’天應魏國,當涂之兆,明土德之昌。”(25)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第19頁。
相同內容的記載還見載于P.2695《沙州都督府圖經》祥瑞蒲昌海五色:
蒲昌海五色:右大周天授二年臘月,得石城鎮康拂耽延弟地舍撥狀稱:“其蒲昌海舊來濁黑混雜,自從八月已來,水清明徹(澈)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羅門云:‘中國有圣天子,海水即清,無波。奴身等歡樂,望請奏圣人知者。’”刺史李無虧奏云:“淮海水五色,大瑞。謹檢《瑞應圖·禮升威儀》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則河傔[海]夷也。’天應魏國當涂之兆,明土德之昌也。”(26)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第35頁。
從《沙州都督府圖經》歌謠的記載時間是“右唐載初元年四月風俗使于百姓間采得前件歌謠,具件如上訖。”是否證實《沙州都督府圖經》的撰寫時間應當是載初元年(689)之后。另外記載到五色鳥是武周天授二年(691)、日揚光慶云是天授二年冬至日、白狼是大周天授二年,應當說撰寫于天授三年(692)或者更晚。但是文書沒有使用武周所造新字,因此《沙州都督府圖經》應當是武周以后撰寫的作品。這個記載說明武周時期石城鎮的鎮遏使還是由粟特人康艷典部落的后裔所控制,康艷典部落仍然居住在石城鎮一帶。
二、唐中宗唐西突厥在西域的交惡與石城鎮康艷典部落的內遷敦煌
根據《資治通鑒》的記載咸亨四年(673):“十二月,丙子,弓月、疏勒二王來降,西突厥興昔亡可汗之世,諸部離散,弓月及阿悉吉皆叛,蘇定方之西討也,擒阿悉吉以歸。弓月南接吐蕃,北招咽麪,共攻疏勒,降之。上遣鴻臚卿蕭嗣業發兵討之。嗣業兵未至,弓月懼,與疏勒皆入朝;上赦其罪,遣歸國。”(27)[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202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6371-6372頁。不久弓月、疏勒投降唐朝,上元元年(674)年于闐王伏阇雄也來朝。上元二年正月以于闐為毗沙都督府,分其境內為十州,以于闐王尉遲伏阇雄為毗沙都督;同時吐蕃遣使請和。唐朝乘機在故樓蘭設石城鎮,隸屬沙州壽昌縣。次年閏三月吐蕃攻打唐鄯、廓、河、芳四州,“乙酉,以洛州牧周王顯為洮州道行軍元帥,將工部尚書劉審禮等十二總管,并州大都督相王輪為涼州道行軍元帥,將左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等,以討吐蕃。”(28)[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202唐高宗儀鳳元年(676),第6379頁。當年十一月改元儀鳳元年。《新唐書·裴行儉傳》記載:
上元三年,吐蕃叛,出為洮州道左二軍總管,改秦州右軍,并受周王節度。(29)[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108《裴行儉傳》,第4086頁。
播仙鎮就是唐與吐蕃關系惡化后為防御吐蕃而設置的,是唐蕃關系緊張的產物,設立播仙鎮就是為了加強涼州道防區,也可能就是為配合涼州道行軍元帥的抗擊吐蕃的統一行動而進行的行政改置。具體實施這個軍事設置的可能是時任瓜州刺史薛仁貴,《舊唐書·薛仁貴傳》記載:“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開耀元年,復召見,謂曰:‘往九成宮遭水,無卿已為魚矣。卿又北伐九姓,東擊高麗,漠北、遼東咸遵聲教者,并卿之力也。卿雖有過,豈可相忘?有人云卿烏海城下自不擊賊,致使失利,朕所恨者,唯此事耳。今西邊不靜,瓜、沙路絕,卿豈可高枕鄉邑,不為朕指揮耶?’于是起授瓜州刺史,尋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30)[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83《薛仁貴傳》,第2783頁。《新唐書·薛仁貴傳》記載薛仁貴兵敗大非川,被貶象州刺史遇赦回來不久,高宗召見薛仁貴,“今遼西不寧,瓜、沙路絕,卿安得高枕不為朕指麾邪?”(31)[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111《薛仁貴傳》,第4142頁。拜其為瓜州刺史。指的就是經過南道對西域的交通道路,石城鎮和播仙鎮的設置就是這個時間。瓜州刺史兼瓜州都督,兼管沙州,統屬于涼州大都督管轄,石城鎮和播仙鎮設置既可以說是涼州都督所為,也可以說是瓜州都督所為,涼州都督府派兵直接駐守播仙鎮,實際上就是由瓜州都督派遣的沙州兵駐守,而以石城鎮的西域康國人康艷典之后裔為石城鎮鎮遏使,負責管理石城地區。石城鎮和且末鎮的放棄亦與唐蕃在西域的爭奪有很大關系,應當說是唐蕃爭奪產生的直接后果。敦煌寫本P.5034《沙州圖經》記載:
□□□。□□且末國,王都且末城……
□□土地草木畜產與石城□……
□□同。自漢已后,其名不改,隨……
□□□吐谷渾,置且末郡,管……
□□涼州兵士等棄鎮歸敦煌……(32)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第49頁。
石城鎮應當與播仙鎮同時放棄的,就是敦煌文獻記載播仙鎮“涼州兵士等棄鎮歸敦煌”。要得知石城鎮、播仙鎮的廢棄時間,我們只能從唐蕃在西域地區關系、西域政局變化中尋找。陳國燦認為唐神龍年間突騎施闕啜忠節帥部進入且末河流域,隨此而引來了吐蕃兵向塔里木盆地東部的進占,居住在且末河流域的粟特人在受到闕啜的暴力威脅時迅速逃往敦煌以求得沙州刺史的保護(33)陳國燦《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收入氏著《敦煌學史事新證》,第370-376頁。。
武周時期唐與吐蕃在西域的爭奪已經展開,長壽元年(692)九月:“初,新豐王孝杰從劉審禮擊吐蕃為副總管,與審禮皆沒于吐蕃。贊普見孝杰泣曰:‘貌類吾父。’厚禮之,后竟得歸,累遷右鷹揚衛將軍。孝杰久在吐蕃,知其虛實。會西州都督唐休璟請復取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敕以孝杰為武威軍總管,與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忠節將兵擊吐蕃。冬十月,丙戌,大破吐蕃,復取四鎮。置安西都護府于龜茲,發兵戍之。”(34)[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205則天后長壽元年(692),第6487-6488頁。萬歲通天元年(696)吐蕃遣使和親,武則天遣郭元振往察其宜,吐蕃將論欽陵請罷安西四鎮戍兵,并求分十姓突厥之地。吐蕃遣使入請,唐以“四鎮、十姓之地,本無用于中國,所以遣兵戍之,欲以鎮撫西域,分吐蕃之勢力,使不得倂力東侵也。今若果無東侵之志,當歸我吐谷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則無俟斤亦當以歸吐蕃”拒絕吐蕃。吐蕃對西域四鎮、十姓占領,必須經由石城鎮、播仙鎮管轄范圍,或者經由薩毗城繞過石城鎮、播仙鎮。另外就是經由大小勃律進入西域地區。我們經過研究認為石城鎮、播仙鎮的放棄與突騎施闕啜忠節關系不是很大,而是與突騎施娑葛與唐關系惡化有直接關系。
根據《舊唐書·突厥下》記載神龍二年(706)烏質勒卒,“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赍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為娑葛游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使上表以索楚客頭。”(35)[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94下《突厥傳下》,第5190-5191頁。敘述事情經過很簡單,我們從中很難了解事情原委和經過。《新唐書·突厥傳下》也記載這個事件,同樣不是很清楚,神龍二年烏質勒死,長子娑葛代父統兵,“俄與其將闕啜忠節交惡,兵相加暴。娑葛訟忠節罪,請內之京師。忠節以千金賂宰相宗楚客等,愿無入朝,請導吐蕃擊娑葛以報。楚客方專國,即以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經制。嘉賓與忠節書疏反復,娑葛邏得之,遂殺嘉賓,使弟遮弩率兵盜塞。安西都護牛師獎與戰火燒城,師獎敗,死之,表索楚客頭以徇。大都護郭元振表奏娑葛狀直,當見赦,詔許,西土遂定。”(36)[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215下《突厥傳下》,第6066頁。從中我們得知,唐派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到闕啜轄境,馮嘉賓與闕啜往來書疏為娑葛游兵所得,就是說娑葛的勢力也到達了闕啜轄境。娑葛遣其弟遮弩盜塞,這個邊塞城鎮很可能就是指播仙鎮和石城鎮。另外《舊唐書·宗楚客傳》也記載了這個事件:
景龍中,西突厥娑葛與阿史那忠節不和,屢相侵擾,西陲不安。安西都護郭元振奏請徙忠節于內地,楚客與晉卿、處訥等各納忠節重賂,奏請發兵以討娑葛,不納元振奏。娑葛知而大怒,舉兵入寇,甚為邊患。(37)[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92《宗楚客傳》,第2972頁。
顯然宗楚客是娑葛制造邊患的始作俑者,因此監察御史崔琬劾奏宗楚客等稱:“潛通獫狁,納賄不貲,公引頑兇,受賂無限。丑問充斥,穢行昭彰。且境外之交,情狀難測,今娑葛反叛,邊鄙不寧,由此賊臣,取怨中國。”(38)[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92《宗楚客傳》,第2972頁。因此闕啜行賄宗楚客等而制造邊患是朝廷中人盡皆知的事情。《新唐書·宗楚客傳》記載:
景龍二年,詔突厥娑葛為金河郡王,而其部闕啜忠節賂楚客等罷之,娑葛怨,將兵患邊。(39)[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109《宗楚客傳》,第4102頁。
宗楚客受闕啜忠節賄賂而阻止授予娑葛金河郡王而引起兵患。《資治通鑒》唐中宗景龍二年(708)詳細記載事件的經過和原因:
十一月,庚申,突騎施酋長娑葛自立為可汗,殺唐使者御史中丞馮嘉賓,遣其弟遮努等帥眾犯塞。
初,娑葛既代烏質勒統眾,父時故將闕啜忠節不服,數相攻擊。忠節眾弱不能支,金山道行軍總管郭元振奏追忠節入朝宿衛。
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落之眾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保寵祿,死生亦制于人手。方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于入朝,豈可同日語哉!”……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楚客、處訥,請如以悌之策。(40)[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209唐中宗景龍二年(708),第6625-6626頁。
郭元振聞其謀,上疏極力反對,但是宗楚客等不從,建議以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以西兵,兼征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遣使娑臘獻馬在京師,聞其謀,馳還報娑葛。于是娑葛發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疏勒,入寇。元振在疏勒,柵于河口,不敢出。忠節逆嘉賓于計舒河口,娑葛遣兵襲之,生擒忠節,殺嘉賓,擒呂守素于僻城,縛于驛柱,冎而殺之。”(41)[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209唐中宗景龍二年(708),第6627-6628頁。娑葛陷安西,斷四鎮路,唐置軍焉耆以討娑葛,最后唐朝不得已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戰爭以娑葛勝利結束。河口指河流的終端,指河流注入海洋、湖泊或者其他河流的地方。郭元振柵河口是指疏勒河匯入于闐河的地方,而阿史那忠節迎接嘉賓于計舒河口的位置是指塔里木河流入羅布泊的地方,《水經注》河水注:“河水又東逕注賓城南,又東逕樓蘭城南而東注。河水又東注于泑澤。”(42)王國維校《水經注校》卷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9頁。根據敦煌文獻P.5034《沙州圖經》記載蒲昌海:“河有兩源,一出蔥嶺山,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蔥嶺合,東注蒲昌海。”郭元振柵河口在于闐河與蔥嶺河匯合之地,而阿史那忠節迎接馮嘉賓的地點在塔里木匯入羅布泊的地方,而塔里木河流入羅布泊的地方,正好是石城鎮到焉耆交通路線的必經之地:石城鎮“一道北去焉耆一千六百里,有水草,路當蒲昌海。”(43)鄭炳林《敦煌地理文書匯輯校注》第48-49頁。唐朝派遣馮嘉賓等經過石城鎮地區前往安西都護府,闕啜在石城鎮北部的計舒河口迎接馮嘉賓一行,而娑葛就是在計舒河口對闕啜和馮嘉賓等進行伏擊,將他們全部俘虜。因此計舒河口很可能是唐河西節度使和安西節度使管轄范圍的結合部,雙方都屬于防守,娑葛才能襲擊成功。
《舊唐書·郭元振傳》也記載這個事件的詳細經過:
先是,娑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屢相侵掠,闕啜兵眾寡弱,漸不能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入于瓜、沙等州安置,制從之。闕啜行至播仙城,與經略使、右威衛將軍周以悌相遇,以悌謂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眾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資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并專權用事,何不厚貺二公,請留不行。乃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往拔汗那征甲馬以助軍用。既得報讎,又得存其部落。如此,與入朝受制于人,豈復同也!’闕啜然其言,便勒兵攻陷于闐坎城,獲金寶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賂于宗、紀。元振聞其謀,遽上疏曰:……疏奏不省。楚客等既受闕啜之賂,乃建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持璽書便報元振。除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便領甘、涼以西兵募,兼征吐蕃,以討娑葛。娑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客計,馳還報娑葛。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疏勒。時元振在疏勒,于河口柵不敢動。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闕啜,殺嘉賓等。呂守素至僻城,亦見害。又殺牛師獎于火燒城,乃陷安西。四鎮路絕楚客又奏請以周以悌代元振統眾,征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元振奏娑葛狀。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奏其狀,以悌竟得罪,流于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元振奏稱西土未寧,事資安撫,逗留不敢歸京師。(44)[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97《郭元振傳》,第3045-3048頁。
《新唐書·郭元振傳》記載事情的經過,神龍中,“西突厥酋烏質勒部落強盛,款塞愿和,元振即牙帳與計事。會大雨雪,元振立不動,至夕凍冽;烏質勒已老,數伏拜,不勝寒,會罷即死。”子娑葛以為郭元振計殺其父,謀勒兵襲擊,次日郭元振素服往吊,“至其帳哭甚哀,為留數十日助喪事,娑葛感義,更遣使獻馬五千、駝二百、牛羊十余萬。”
烏質勒之將闕啜忠節與娑葛交怨,屢相侵,而闕啜兵弱不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宿衛,徙部落置瓜、沙間。詔許之。闕啜遂行。至播仙城,遇經略使周以悌,以悌說之曰:“國家厚秩待君,以部落有兵故也。今獨行入朝,一羈旅胡人耳,何以自全?”乃教以重寶賂宰相,無入朝;請發安西兵導吐蕃以擊娑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請郭虔瓘使拔汗那蒐其鎧馬以助軍,既得復讎,部落更存。闕啜然之,即勒兵擊于闐坎城,下之。因所獲,遣人間道赍黃金分遣宗楚客、紀處訥,使就其謀。(45)[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122《郭元振傳》,第4363頁。
郭元振知之,上疏反對,但是疏奏不省。
楚客等因建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以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代元振領甘、涼兵,詔吐蕃倂力擊娑葛。娑葛之使娑臘知楚客謀,馳報之。娑葛怒,即發兵出安西、撥換、焉耆,疏勒各五千騎。于是闕啜在計舒河與嘉賓會,娑葛兵奄至,禽闕啜,殺嘉賓,又殺呂守素于僻城、牛師獎于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絕。元振屯疏勒水上,未敢動。楚客復表周以悌代元振,且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且言:“無仇于唐,而楚客等受闕啜金,欲加兵滅我,故懼死而斗。且請斬楚客。”元振奏其狀。楚客大怒,誣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子鴻間道奏乞留定西土,不敢歸京師。以悌乃得罪,流白州,而赦娑葛。(46)[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122《郭元振傳》,第4364-4365頁。
通過這些記載我們得知,烏質勒部將闕啜與娑葛因交怨而屢相侵并勢力不支,郭元振為了緩解雙方矛盾,建議將闕啜部落遷徙到瓜、沙間安置,并追闕啜入宿衛。這本來是很好的策略,因經略使周以悌唆使,闕啜行賄宰相無得入朝,而沒有得到實現。唐朝政府中以宗楚客為代表的主張扶持闕啜聯合吐蕃、拔汗那攻擊娑葛,削弱郭元振在西域的權力,用御史中丞馮嘉賓安撫闕啜、御史呂守素處置四鎮,用牛師獎代替郭元振掌握鎮守四鎮的甘、涼兵士兵權。雙方密謀的地點是羅布泊地區,闕啜計劃與馮嘉賓、呂守素等會合于計舒河口,皆因被俘害而罷,牛師獎死后謀用周以悌代替郭元振也未能實現。
唐朝政府安置西突厥闕啜部落于瓜、沙等州,石城鎮、播仙鎮實際上就是安置闕啜部的主要地區。唐初瓜州沙州屬于涼州都督府管轄,貞觀初年唐玄奘從瓜州偷渡出境,涼州都督李大亮就行文瓜州刺史捉拿。瓜州建都督府,沙州刺史由瓜州的都督調遣,直到沙州建都督府之后地位有所上升。唐神龍年間安置闕啜忠節瓜沙等州,實際上瓜沙都屬于涼州都督管轄。唐將闕啜部安置在西起播仙鎮、石城鎮東到與瓜州毗鄰的莫賀延磧一帶,或者西起且末河東到瓜州南山等地。闕啜忠節部落是游牧民族,將其安置在播仙鎮、石城鎮是唐朝的主動行為,并不構成對唐朝播仙鎮、石城鎮的威脅,闕啜部落到達播仙鎮,經略使周以悌應當還是當地軍鎮的最高統帥,沒有他的默許,闕啜根本不敢攻打于闐坎城。居住在且末河流域的粟特康艷典部落是城居商業農業居民,闕啜不可能也不敢對其形成暴力威脅,而且闕啜不惜率兵攻打坎城掠奪金寶以賄賂唐宰相宗楚客,不敢對近在遲尺的石城鎮、播仙鎮下手,就說明當時石城鎮、播仙鎮等還在,很可能是其強力后盾。闕啜在計舒河口迎接馮嘉賓等,就說明原屬于石城鎮康艷典部落的地域,已經成為闕啜部眾活動的地域。娑葛在計舒河口一帶殺馮嘉賓和呂守素等,俘虜闕啜。根據《資治通鑒》唐中宗景龍二年十一月記載
癸未,牛師獎與突騎施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兵敗沒。娑葛遂陷安西,斷四鎮路,遣使上表,求宗楚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悌代郭元振統眾,征元振入朝;以阿史那獻為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討娑葛。
娑葛遺元振書,稱:“我與唐無惡,但讎闕啜。宗尚書受闕啜金,欲枉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繼而來,奴豈得坐而待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奏言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乞留定西土,不敢歸。周以悌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為十四姓可汗。(47)[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209唐中宗景龍二年,第6629頁。
唐朝置軍焉耆,就是以為焉耆地處南道與中道交匯之地,表明焉耆以南的播仙鎮、石城鎮非唐所有。唐中宗景龍三年:
秋,七月,突騎施娑葛遣使請降,庚辰,拜欽化可汗,賜名守忠。(48)[宋]司馬光編著,[元]胡三省音注《資治通鑒》卷209唐中宗景龍三年,第6636頁。
《舊唐書·中宗紀》記載景龍二年:
冬十一月庚申,突厥首領娑葛叛,自立為可汗,遣弟遮弩率眾犯塞。……癸未,安西都護牛師獎與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敗績,沒于陣。……(三年七月)壬午,遣使冊驍衛大將軍、兼衛尉卿、金河王突騎施守忠為歸化可汗。(49)[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7《中宗紀》,第146-148頁。
《新唐書·中宗紀》景龍二年記載:
十一月庚申,西突厥寇邊,御史中丞馮嘉賓使于突厥,死之。……癸未,安西都護牛師獎及西突厥戰于火燒城,死之。……(三年)七月丙辰,西突厥娑葛降。(50)[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四《中宗紀》,第110-111頁。
至此,唐朝與突騎施娑葛之間紛爭結束,唐朝政府不得不接受既成事實,承認突騎施娑葛的地位。應當說通過這次戰爭,娑葛已經控制了石城鎮、播仙鎮,涼州兵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棄鎮歸敦煌,石城鎮的康艷典部落也是隨著涼州兵士棄鎮歸敦煌而東遷敦煌,唐朝政府為了安置這些從石城鎮遷徙而來粟特人部落,就在敦煌城周邊地區設立了以粟特人為主的從化鄉。我們應當指出的是,經略使周以悌幫闕啜謀劃聯合吐蕃、拔汗那攻打娑葛,因娑葛行動迅速,吐蕃和拔汗那都沒有參與到唐與西突厥娑葛的戰爭中。因此石城鎮粟特人部落的東遷敦煌和播仙鎮涼州兵士棄鎮歸敦煌與吐蕃沒有關系。
三、沙州敦煌縣從化鄉的設置與粟特聚落的形成
敦煌粟特人聚落從化鄉的形成時間,陳國燦根據吐魯番出土來自敦煌又記載從化鄉的大谷文書記載有張令端和曹子節及從化鄉,認為這是從該文書出土于吐魯番阿斯塔那225號張令端的墓葬,根據同期文書墓主人張令端卒后入殮,時間應在唐景龍(707-710)以后,又根據《敦煌縣錄事董文徹牒》認為長安三年(703)三月敦煌尚無從化鄉,認為從化鄉殘文書只能是長安三年三月以后至景龍間的文書,敦煌從化鄉也只能出現這個時期(51)陳國燦《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收入氏著《敦煌學史事新證》,第371-372頁。大谷文書記載:“(前缺)子總張令端……叔牙,從化鄉百姓……之節等(后缺)”。。敦煌文書P.2803《唐天寶九載(750)八月——九月敦煌郡倉納谷牒》記載敦煌十三鄉中有從化鄉:“從化鄉,叁佰玖拾伍碩貳斗壹勝。”(52)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北京:全國圖書館縮微復制中心,1990年,第445頁。直至唐天寶九載從化鄉仍然存在。P.3559《唐天寶年間(750)敦煌郡敦煌縣從化鄉差科簿》記載唐敦煌縣從化鄉最為詳細:
貳佰伍拾柒從化鄉。壹佰壹拾柒人破除。貳拾叁人身死。……叁拾伍人逃走。……貳拾柒人沒落。……叁人虛掛。……叁人廢疾。……貳拾叁人單身土鎮兵。……叁人單身衛士。……壹佰肆拾人見在。壹拾人中下戶。……壹拾人下上戶。……貳拾人下中戶。……壹佰人下下戶。(53)唐耕耦、陸宏基編《敦煌社會經濟文獻真跡釋錄》第1輯,第229-241頁。
差科簿記載下中戶曹大賓服色役為市壁師、下下戶康令欽服色役為里正、羅奉鸞服色役為里正、安突昏服色役為村正、安胡數芬服色役為市壁師、何抱金服色役為村正、羅雙利和羅特勤服色役為村正。根據此紙縫后貼為唐天寶九載敦煌郡倉納谷牒十六件,故確定該卷文書為天寶年間。另外我們根據敦煌地區安城祆祠的出現作為敦煌粟特人聚落建立的標志,《沙州都督府圖經》記載安城祆:“祆神,右在州東一里,立舍畫神主,總有廿龕,其院周回一百步。”祆神,又稱安城大祆,是敦煌的雜神之一。如果說安城的修建與祆神同時,就像敦煌古跡二十詠記載的“板筑安城日,神祠與此興”,即敦煌的粟特人聚落與祆神神祠安置是同時,那么《沙州都督府圖經》的撰修時石城鎮的粟特人聚落已經遷居敦煌,且《沙州都督府圖經》中沒有使用武周新字,表明其撰成武周之后,為開元初增補而成,開元之前敦煌已經修建了祆教神祠,而從化鄉就是這個階段設置的。經陳國燦先生研究,敦煌從化鄉的出現時間正好在唐中宗神龍年間,與突騎施闕啜在這一地區劫掠騷擾遙相呼應(54)陳國燦《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敦煌學史事新證》,第373頁。實際上與突騎施娑葛在羅布泊地區俘虜闕啜忠節、殺馮嘉賓和呂守素等占領該地區有直接關系。
隨著唐朝政府與娑葛關系的改善,唐朝政府在這個地區的軍政機構很快就恢復了。特別是景龍三年娑葛與其弟遮弩關系緊張,“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討娑葛。”(55)[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94下《突厥傳下》,第5191頁。突厥默啜用遮弩討擒娑葛,遂與娑葛俱殺之。突騎施娑葛對唐朝的威脅解除,很可能這個時期石城鎮、播仙鎮的建置得到回復。但是突騎施進入羅布泊地區并生活在這里成為既成事實,并長期生活在這里。敦煌吐蕃文獻Ch.73.xv.4號文書從第45行到末尾記載:
緊接著現在的時間是借貸和征稅時間。當這個三百六十年的時間過去的時候,漢人國家西邊,一個大湖的遙遠岸邊,那里出現一塊陸地,一位黑臉王乘坐一輛戰車,耀武揚威六十載。漢人被其征服,黔首向其效忠。當此王統治六十載過去時,于Bug-chor漢人的沼澤國內出現一小邦的陷落,一名叫大突厥(Drug-chen-po)的人消滅了漢人的黑臉王和Bug-chor的王。漢區和Bug-chor的兩族人為王所征服并交納稅賦。大突厥王統治了七十二年。此七十二年之后,東西突厥開始打仗。首先西突厥……。(56)[英]F.W.托馬斯編著,劉忠、楊銘譯注《敦煌西域古藏文社會歷史文獻》,北京:商務印書館,2020年,第270頁。
文書中記載到的大突厥王,就是指生活在這里的突騎施部落。
直到唐天寶年間,唐與吐蕃為爭奪播仙鎮、石城鎮還進行過戰爭。根據P.5034《沙州圖經》記載有:“□□年,□□都尉即令□且末城。”就是說播仙鎮經過一次廢棄之后,又重新設置,同樣石城鎮可能也在廢棄之后又進行重新設置。這些軍事措施應當說與粟特人康艷典部落沒有任何關系。播仙鎮和石城鎮的重新設置,很可能是天寶初年。《舊唐書·尉遲勝傳》記載:“尉遲勝,本于闐王珪之長子,少嗣位。天寶中來朝,獻名馬、美玉,玄宗嘉之,妻以宗室女,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還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改光祿卿,皆同正。”(57)[后晉]劉昫等撰《舊唐書》卷144《尉遲勝傳》,第3924頁。《新唐書·尉遲勝傳》也有同樣的記載:“尉遲勝本王于闐國。天寶中,入朝,獻名玉、良馬。玄宗以宗室女妻之,授右威衛將軍、毗沙府都督。歸國,與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擊破薩毗、播仙。累進光祿卿。”(58)[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110《尉遲勝傳》,第4127頁。這次戰爭大約發生在天寶八載(749)(59)王小甫《唐、吐蕃、大食政治關系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51、172、179頁。。很快吐蕃再次占領薩毗城、播仙鎮,天寶十三載(754)封常清再次擊敗鎮守播仙的吐蕃守軍(60)岑參《獻封大夫破播仙奏凱歌六章》,[唐]岑參著,陳鐵民、侯忠義校注《岑參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53-154頁。。薩毗即薩毗城,這里經常行經吐蕃,因此薩毗、播仙是吐蕃攻打西域的重要軍事據點。《新唐書·郭虔瓘傳》記載安西副都護郭虔瓘與安撫招慰十姓可汗阿史那獻持異,交訴于朝,玄宗遣左衛中郎將王惠赍詔書諭解:“或云突騎施圍石城,獻所致也;葛邏祿稱兵,虔瓘所沮也。大將不協,小人以逞,何功可圖?”(61)[宋]歐陽修、宋祁撰《新唐書》卷133《郭虔瓘傳》,第4544頁。開元年間突騎施曾出兵圍困石城鎮。這里仍然是唐與突騎施、吐蕃爭奪的重要軍事據點。
我們通過對《都僧統康賢照和尚邈真贊并序》及相關文獻研究得知,唐貞觀四年康艷典率部落遷徙到石城鎮,唐上元二年防御日漸強大的吐蕃對西域威脅,設置了石城鎮、播仙鎮,并將其隸屬沙州,歸涼州都督府管轄。以康艷典為石城鎮使,此后康艷典后裔一直擔任石城鎮使,直到天授年間。唐中宗神龍二年突騎施烏質勒死,長子娑葛代父統眾,烏質勒舊部闕啜不服而發生戰爭,闕啜兵敗部眾被安置在羅布泊地區,闕啜賄賂宗楚客得到唐朝政府支持,豈圖攻擊娑葛,反而被娑葛擊敗被俘虜,唐將馮嘉賓等被殺,娑葛占領羅布泊地區。在突騎施娑葛的軍事打擊之下,石城鎮的粟特人康艷典部落隨著駐守播仙鎮的涼州兵士棄鎮歸敦煌,唐朝政府為了在敦煌安置這些從石城鎮遷徙而來的粟特人,專門在敦煌城周修建了安城祆祠,設立從化鄉。從化鄉規模最少有兩個里四個村落,同時負責敦煌市場的貿易管理。吐蕃占領敦煌后從化鄉被取消,但是粟特人的勢力仍然存在,歸義軍時期敦煌仍然保留很多粟特人聚落,控制敦煌地區的商業貿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