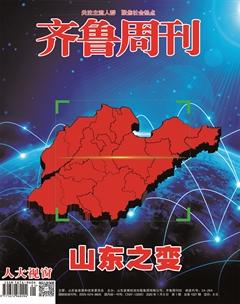“90后立遺囑”與海德格爾
顧玉雪
一代人終將老去,但總有人正年輕。時間是個不懂營私舞弊的家伙,本世紀的第三個十年掀開時代的宏大幕布,呼嘯而至。“20后寶寶”抵達戰場,自嘲“誰還不是個寶寶”的90后們迎來了他們的而立之年。
近日,90后女孩李立(化名)提前立下遺囑。“90后開始立遺囑”沖上微博熱搜,短短時間里,有2億多閱讀量,引起了16000次討論。事實上,李立這樣的年輕人并不是少數。據《2019中華遺囑庫白皮書》統計,立遺囑人年齡趨向年輕化,職業以金融、互聯網、醫療、高科技行業為主,北京生前預囑推廣協會網站上,三分之一注冊預囑者的年齡在35歲以下。
1992年出生的李立是上海某知名醫院ICU病房的護士,見慣太多生命無常的她在遺囑中將房子留給了閨蜜,希望閨蜜可以在她出現意外時照顧她的父母。中華遺囑庫北京第二登記中心的法律專員崔文姬,在自己25歲生日當天立下遺囑。在她看來,立遺囑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情,“因為你不知道意外什么時候來。”
“90后立遺囑”背后有一門我們都應該補的課:死亡教育。我們現在的文化基因里,總是對死亡諱莫如深。“未知生、焉知死”,一個人的死亡觀其實就是他(她)的生命觀。在今天的醫改格局中,醫生往往會用理性的、教科書式的語言談論死亡,不會和病人探討文化語境的死亡,我們的教育也缺乏這樣的語境。
2019年年末,一個急診科醫生的死亡讓我們發現,與惡的距離如此近在咫尺。醫院是最接近天堂也最接近地獄的所在,醫患糾紛引發過經年累月的惡,然而制度設計和人性之惡背后是什么?社會如何面對疾病,面對死亡?
誠如北大醫學人文研究院王一方教授所說:“醫療觀要調整,要把痛苦的接納和對生死的豁達包含進來。”如何面對死亡,是我們終究所要艱難面對的課題。
德國哲學家馬丁·海德格爾在其存在論名著《存在與時間》里對不可避免的死亡給出了一個終極答案:生命意義上的倒計時法—“向死而生”。人的一生就是向死的方向活著。與亡的結果相比較,要解決我們與生命外部所發生的沖突,這個向死的過程更本真,更真實。這種“倒計時”法的死亡哲學概念,讓我們明白每個人的生命在長度之外,還有寬度。這種延長是“內涵性”,是通過內在精神成長的方法自我覺醒。
“90后立遺囑”是時代的產物,它所反映的,是一種流行的集體情緒,這個情緒的關鍵點是焦慮。
在這個曾經被科幻電影設定為“未來”的年代,科學技術和社會文化的前行速度并不同步,對大多數人來說,“焦慮、孤獨和不穩定”成為眾聲喧嘩中的午夜夢回。無論是底層崛起的逆襲夢想還是“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的歸隱情懷,都承載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B站前不久選出的“年度彈幕”awsl(啊我死了)亦道出大時代里的小艱辛和青年癥候。
在社會的金字塔,占據最多人數的“真正的”普通人,對生活的痛感從來就不怎么強烈,除非生活施以重拳。
進入30歲之后,時間便如喪家之犬飛奔而去。海明威在小說《乞力馬扎羅的雪》中,借主人公之口描述死亡:“很奇怪,只要夠疲倦,原來這么容易就能走到這一步。”這種疲倦,也許當我們割斷了連接與自然母親的臍帶之后便一直存在:我們有了獨立的意識,有了對有限性和有死性的覺醒,便意味著終其一生面臨著暫時與永恒、現實與理想、此岸與彼岸之間的激烈沖突。
海德格爾之所以提出“向死而生”這個重大的死亡哲學概念,其實是站在哲學理性思維的高度,用重“死”的概念來激發內在“生”的欲望,就像我們中國人所說的:置之死地而后生。因為海德格爾很清楚地知道,與人貪戀欲望滿足的本能力量相比,不在思想上把人逼進絕路,人在精神上是無法覺醒的。
其實,千百年來人類上天入地、建功立業,正是為了超越自身有限性這一理想,也許迄今為止仍然沒有找到一條通達烏托邦的出路,但亦不可能由于這理想不能實現就放棄追求——
特別想重溫一下小說《乞力馬扎羅的雪》的開頭:“乞力馬扎羅是一座冰雪覆蓋的山峰,海拔19710英尺,據說,是非洲最高峰。它的西峰在馬賽語里被叫作“恩伽耶—恩伽伊”,神之居所。西峰頂附近有一具風干冰凍的花豹尸首。沒人知道,花豹跑到這么高的地方來做什么”——
花豹承載了這樣一種“向死而生”的意象:正是在追求與熱愛的痛苦之中,我們的人生意義得以安放,無論在2020,還是更遠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