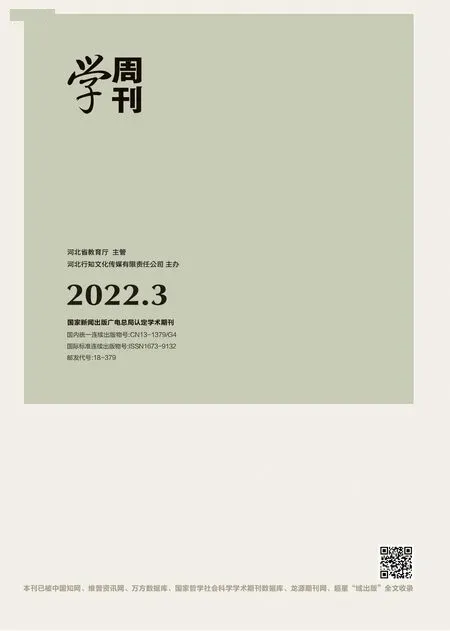評《春山一路鳥鳴啼——王雪濤花鳥畫藝術及影響研究》
摘 要:從中國繪畫發展的歷史縱向來看,20世紀中國美術的發展論爭與風格變遷無疑是最為激烈與多元的時代;若從繪畫史發展的橫向來分析,近現代西方藝術思潮對中國畫壇的影響是顯見的。本文以王雪濤的繪畫學習歷程、花鳥畫風格特征、創作及教育觀念、藝術影響等方面作為案例,結合當時中國美術教育、社會發展、藝術政策等方面分析在“以西潤中”的創作理念指導下,中國畫的風格發展與內涵轉型。
關鍵詞:王雪濤;花鳥畫;藝術風格;影響
中圖分類號:J20? ? ? ? ?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9132(2020)03-0191-02
DOI:10.16657/j.cnki.issn1673-9132.2020.03.186
由劉北一博士撰寫的《春山一路鳥鳴啼——王雪濤花鳥畫藝術及影響研究》已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正式發行。若從20世紀中國美術發展的視角來審視中國畫的傳承和發展問題,“傳統”與“當代”、“東方”與“西方”成為論爭中的兩個焦點。在現代中國畫的發展問題上,美術界大致有三種主要觀點:其一,傳統水墨畫應保持既有的風格,尤其是對文人畫正統性的維護;其二,傳統應融于當代,要充分吸收西方藝術觀念,在題材、內容、材質、風格等方面進行創新;其三,現代水墨要與傳統割裂,應充分發揮畫家的獨創性[1]。總體來說,“中西融合”已經成為一種潮流。歐美學者蘇立文(Michael Sullivan)與李鑄晉在研究20世紀中國繪畫發展與變遷的論著中提出了“新國畫”的學術概念,頗具啟發性[2]。如李鑄晉所著Trends in Modern Chinese Painting與蘇立文的Chinese Ar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比較有代表性。
劉北一的專著以畫家王雪濤為案例,結合20世紀中國畫的發展脈絡分析畫家獨特的藝術風格。通過這項研究,我們看到了一個在恢宏歷史背景中頗具特色的個體發展之路。每一個畫家都不是孤立的個體,他是處在時代之網中的一個結。作者圍繞王雪濤這個“結”,清晰地為我們勾勒出一幅師承和習學的“關系圖”。從師法王夢白、齊白石、陳師曾、陳半丁,到同時代的李苦禪、李可染、顏伯龍、汪慎生,再到學生蕭朗、陳征(衲子)、王培東、陳葆棣,更有外籍西畫教師柯羅多、嶺南高劍父、高奇峰以及明清兩朝陳淳、徐渭、朱耷、華新羅,等等。針對如此縱橫交貫的線索,作者爬羅剔抉,從不同維度剖玄析微,擘肌分理,深入而完整地解釋了王雪濤藝術的成因與動力,這對于理解王雪濤繪畫路徑與風格轉變有重要意義。
對于一個藝術史研究者來說,分期和分類是一項很見功力的重要工作。劉北一通過查閱文獻檔案、走訪有關學者和王雪濤的學生等方式,掌握了很多珍貴的第一手材料。在此基礎之上,他提出了自己的分期觀點,即采取“掐頭去尾”的辦法。他把考察的重點放在20世紀30年代中期以后至70年代中期。他把這30多年的時間分作3期,在此他稱之為“三個過渡期”。根據這“三個過渡期”,他又歸納出了與分期相關聯的“三種風格”:“40年代初期至50年代初期的‘清潤與‘勁挺,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后期的‘鮮麗與‘厚重,70年代初期至中期的‘渾厚與‘蒼勁。”這種歷史分期和風格分類在針對王雪濤的學術研究中具有獨創性,給更多的研究者帶來啟發,為王雪濤研究提供了一個參照系。對于鑒賞和學習者來說,這種縝密的分期和分類更加便于提升理解的精確度。
劉北一還以王雪濤早年于北平藝專的專業變更為線索,窺探了20世紀早期官辦美術教育狀況。北平藝專作為當時中國最重要的官辦藝術院校之一,在引領和踐行20世紀美術思潮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早期的專業及課程設置參照了東京的美術院校,并聘用當時國內頗具影響力的繪畫名家,這些畫家多具有留學背景,甚至包括一些外籍教員[3]。這種教育模式正迎合了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求新精神,在美術界也積極踐行了“以西潤中”的觀念。當時熱衷藝術學習的青年人也受到了這種潮流的影響,如徐悲鴻、林風眠等人赴歐洲學習也是基于這種理想[4]。王雪濤在1922年考入藝專之后,先入西畫科,后于1923年轉入國畫科。對王雪濤而言,西畫觀念與技法的啟蒙對其加強速寫與造型的訓練是有益助的,對其花鳥畫的創新亦有積極影響。在藝專早期的教育實踐過程中,學校內部針對專業及課程設置問題也出現了一些論爭,加之當時的社會氛圍,學校的發展遇到了困境。該研究針對王雪濤在北平藝專的求學情況,通過梳理其與齊白石和王夢白等人的師承脈絡,對于了解王雪濤早期的花鳥畫學習歷程具有重要意義。
傳承與發展是藝術自身演進的規律,正如蕭煥對王雪濤的評價一樣:“王雪濤在繼承與發展傳統寫意花鳥畫技法的基礎上逐漸形成了獨特的個人風格,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王雪濤從齊白石、王夢白及陳半丁等現代畫家那里得到了啟發,并進一步師古人傳統,最終形成了自己的藝術風格,這樣的學習脈絡是留給后人最大的啟發。作為現代花鳥畫壇的杰出畫家,其自身的藝術傳承與發展正是該研究所關注的重點。梳理王雪濤門人及學生的資料對研究其藝術傳承與發展是十分重要的。王雪濤的門人眾多,這些門人或學生來自不同地域。郎紹君曾說:“在現代花鳥畫家中,王雪濤的小寫意獨樹一幟,有廣泛的群眾基礎,眾多的追隨者。如果說存在著一個事實上的雪濤畫派(多在北京、天津、河北及山東等地),并不是夸張之辭。”
如同李鑄晉說的那樣,20世紀的一些國畫家,他們既不因循守舊,又不盲目排斥西方繪畫的觀念,他們的成功在于根植中國文化的土壤,強調畫家的個性并歸結于作品的質量[5]。學界普遍認為1949年之后社會環境的發展與變化對王雪濤花鳥畫風格的轉變造成了決定性的影響,這是一個規律性判斷,而未能全面說明其中的轉變邏輯。王雪濤的繪畫風格轉變主要是兩個方面的原因,一是不斷深入鉆研古人作品;二是技法不斷成熟。王雪濤的花鳥畫從早期的“清潤”風格逐漸轉變為“厚重”與“鮮麗”,這是一種自然的轉變過程。王雪濤的繪畫觀念是一個綜合的體系,包含什么是花鳥畫,如何畫花鳥畫的問題,又涉及花鳥畫的發展歷程、近現代花鳥畫流派、歷代畫家與畫作、畫家與社會、風格與影響等諸多方面。具體到畫面而言,王雪濤主要對筆墨、章法布局、用色、造型、造境等方面提出了觀點,并認為表現自然生機及情境是花鳥畫的核心內容,繼承傳統并能夠推陳出新是畫家的歷史使命。他在教學過程中一方面引導學生借用西方觀察和寫生的觀念,同時注重對古人作品的臨習。在具體實踐過程中,他認為筆墨技法是為造型服務的,這一觀念已經超越了傳統文人花鳥畫的指導原則,并提出了“唯作品論”,即學習畫家作品中的優點,而不是看畫家的名氣。這些觀念的革新具有務實意義和時代性。
學界尚未有專門的文章論述王雪濤繪畫藝術的影響,作為該研究的一個重點,劉北一在談及王雪濤藝術影響的章節,從風格的傳承、風格的發展兩個層級分別論述,將王雪濤具有代表性的學生作品作為案例分析,從宏觀到微觀具體論證王雪濤的藝術影響。在有關王雪濤花鳥畫藝術研究的諸多局限性面前,當代花鳥畫教學中鮮有將王雪濤的作品作為學習的范本,這與范曾所說的“花鳥畫審美觀念”有重要關聯。總體而言,王雪濤繪畫藝術的重要意義在于其可貴的探索,對于一個大的時代背景下,采取了“以西潤中”的方式,而創造了中國花鳥畫的一種新的藝術形式。
從歷史的縱向來看,20世紀無疑是中國繪畫發展觀念最為豐富的一個世紀,中西方藝術觀念的碰撞與融合也使得繪畫作品出現了極多元的趨勢。劉北一將王雪濤作為一個典型案例,通過分析王雪濤的繪畫學習歷程及風格特征,說明了中國水墨畫融合“西法”后重獲新生,王雪濤的這種探索不僅踐行了“西法中用”的觀念,而且用中國畫的趣味表現了大眾喜聞樂見的生活美感。劉北一的研究不僅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而且對于當代花鳥畫的學習和創作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參考文獻:
[1][4]劉曦林.二十世紀中國畫史[M].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2012:57,44.
[2]邱琳婷.“七友畫會”與臺灣畫壇(1950s-1970s)[D].臺灣大學,2011:3.
[3]劉曉路.北平藝專前期若干史實鉤沉[J].美術觀察,1999(11):59.
[5]李鑄晉,萬青力.中國現代繪畫史(第三卷)[M].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32.
[責任編輯 張翼翔]
作者簡介: 杜文婕(1983.6— ),女,漢族,河北廊坊人,編輯,研究方向:魏晉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