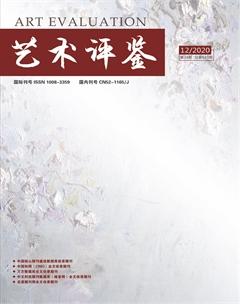關(guān)于青銅制編鐘在音樂考古中的思考
顧君怡
摘要:音樂考古,是一門獨(dú)立又具有兼容性的學(xué)科。編鐘,遠(yuǎn)古而來,既是歷史上不可忽略的禮器,也是我國古代傳統(tǒng)的打擊樂器。青銅制成的編鐘,對(duì)于音樂考古學(xué)來說,是十分寶貴的歷史實(shí)物資料。編鐘作為遠(yuǎn)古之器,有一定的功能性與藝術(shù)性,人文、禮樂都有它的身影,在音樂考古中,是必不可少的存在。
關(guān)鍵詞:編鐘 ?青銅 ?古樂器 ?音樂考古
中圖分類號(hào):J605?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文章編號(hào):1008-3359(2020)24-0021-04
編鐘,作為我國古樂器,一直深受人們的喜愛。音樂考古,是研究古樂器的一個(gè)重要方式。前人在器樂、文物、考古等方面,對(duì)于“編鐘”這一樂器都進(jìn)行了追尋,并且也做了許多關(guān)于編鐘的研究,包括文物出土編鐘的分析、樂律銘文研究等方面,各考古專家都對(duì)編鐘進(jìn)行了詳細(xì)的測量和數(shù)據(jù)分析,一系列的研究蘊(yùn)含著前人對(duì)編鐘這一樂器的喜愛與心血。筆者基于中國音樂歷史文化,將編鐘與音樂考古相聯(lián)系,思考編鐘在音樂考古中的應(yīng)用與意義。
一、編鐘與音樂考古
鐘,是銅制罐體擊奏體鳴樂器。廣義上的鐘,從基本形態(tài)來看,從上至下,整體可以看作一個(gè)類似于扁圓錐體或圓柱體的中空形狀,鐘切面呈圓形或橢圓形,依靠擊打鐘體發(fā)聲。而編鐘,作為各個(gè)種類鐘的一個(gè)集合,青銅制,是大小不同的扁形圓鐘按照音調(diào)高低排列,懸掛在架子上而成,表面帶有銘文裝飾。
音樂考古學(xué),是人們根據(jù)與古代音樂藝術(shù)有關(guān)的實(shí)物史料來研究音樂歷史的科學(xué)。當(dāng)代社會(huì),對(duì)于器樂的研究不僅局限于創(chuàng)新與再次開發(fā),音樂愛好者對(duì)于古樂器的復(fù)原,也越來越重視。古代樂器,包含著一個(gè)時(shí)代的文明,編鐘也不例外。編鐘從古代一步步走來,對(duì)于音樂考古來說,無論從橫向,即不同形態(tài)編鐘之間的聯(lián)系;又或是縱向,即不同時(shí)期編鐘的發(fā)展變化,都能體現(xiàn)出編鐘在不同社會(huì)形態(tài)中所包含的經(jīng)濟(jì)、政治、藝術(shù)等因素,以至于使人們更好的從中得到關(guān)于古代器樂史的研究。
編鐘與音樂考古學(xué)相輔相成。從編鐘的歷史出發(fā),結(jié)合各時(shí)期的社會(huì)發(fā)展實(shí)況,研究編鐘在其中的變化,探討編鐘對(duì)人們藝術(shù)娛樂生活的影響等。以古樂器研究的角度看待編鐘的發(fā)展,逐漸與當(dāng)代音樂考古相銜接,思考其中的應(yīng)用軌跡,從而對(duì)未來的音樂發(fā)展、音樂史研究作出貢獻(xiàn)。
二、從古樂器研究角度看編鐘的發(fā)展
古樂器研究,涉及樂器實(shí)物、樂器文獻(xiàn)等方面。我國古代樂器一般研究的內(nèi)容,含有樂器的斷代分域、形制類型、材料工藝、銘文紋飾、演奏音響等。特別是研究古樂器時(shí),由于出土的文物,并不是一定滿足研究的需要,可能存在時(shí)代之間的斷層,并且不同地域出土的古樂器各不相同。所以,從古樂器研究的角度來說,編鐘在各個(gè)時(shí)代,在形制、材料等方面,都有不同的發(fā)展。
樂器來源于生活,而制作樂器的人們,思維方式受社會(huì)發(fā)展影響。樂器考古一般將石器時(shí)代作為最早的時(shí)間考據(jù),而青銅時(shí)代是石器時(shí)代后的時(shí)代,夏、商、西周、春秋時(shí)期都在這個(gè)時(shí)間劃分范圍之內(nèi),此時(shí)制造業(yè)原料多變,青銅逐漸開始使用,到了戰(zhàn)國與秦漢時(shí)期,青銅制的禮器依然深受人們的喜愛。編鐘也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被人們制作而成。青銅禮器,大致包括食器、酒器、水器和樂器。編鐘是禮器,同時(shí)亦屬于樂器。古時(shí)宮廷娛樂、宗教祭祀、演練等儀式中經(jīng)常出現(xiàn)編鐘的身影,編鐘是這些活動(dòng)中常用的樂器之一。但在古時(shí),編鐘體積龐大,制作需要有一定的人力、物力,一般僅為貴族使用。周王室為了推行雅樂,還專門設(shè)立了大司樂,由此可見皇室對(duì)其的重視程度。
湖北隨縣曾侯乙墓中出土的“曾侯乙編鐘”是戰(zhàn)國早期的大型編鐘,也是目前為止被人們所熟知的編鐘之一。曾侯乙編鐘共有65枚鐘,有三層八組,上層為鈕鐘,中層為甬鐘,下層為大型甬鐘,正中為楚惠王贈(zèng)予曾侯乙的镈鐘。曾侯乙編鐘的表面有許多銘文,大體上為編鐘的編號(hào),記載著當(dāng)時(shí)的音律樂理,配有撞鐘錘和木槌擊打發(fā)聲,曾侯乙編鐘具有“一鐘雙音”的特點(diǎn),即敲擊正鼓部和側(cè)鼓部會(huì)出現(xiàn)兩個(gè)不同的音,兩音之間的頻率為三度關(guān)系,雙音鐘是古代樂器制作者根據(jù)扁體鐘所帶有的共鳴特殊性制成。從整體上看,曾侯乙編鐘是多種類型鐘的一個(gè)集合,編鐘的制作與當(dāng)時(shí)的社會(huì)經(jīng)濟(jì)發(fā)展密不可分。春秋晚期的青銅蟠龍紋鈕鐘,已經(jīng)體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鐘的一個(gè)基本使用形態(tài),外部的蟠龍紋也是青銅器紋飾之一。《工藝美術(shù)辭典》一書中對(duì)于“蟠龍紋”的解釋為,此紋是呈蟠曲于圓形內(nèi)部的一種龍紋,蟠龍是沒有升天的龍,商代以后的青銅器皆有用此紋的情況。漢代時(shí)期,在郡國并行的歷史背景下,地方生產(chǎn)的主動(dòng)性和積極性都有所提升,盱眙大云山出土的一組西漢銅編鐘,蘊(yùn)藏了精美的漢代工藝。到了魏晉南北朝時(shí)期,手工業(yè)重心逐漸向冶鐵業(yè)轉(zhuǎn)移,鍛造工藝發(fā)展迅速,編鐘的制作材料與過程也有了一定的“更新”。
編鐘的制作,首先從材料方面來看,青銅是制作編鐘的常見材料。青銅是銅和錫的合金,銅的延展性好,可以鍛造,也可以熔鑄。青銅的色澤性良好,并且具有一定的抗腐蝕性。青銅制成的禮器表面呈現(xiàn)各式各樣的紋路,一般有饕餮紋、龍紋、鳳紋等。以饕餮紋為例,《呂氏春秋·先識(shí)覽》中曾有“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以言報(bào)更也”的描述,說的就是周代鼎上存在的饕餮紋路,現(xiàn)在的考古文物界以“獸面紋”稱之更廣。編鐘作為青銅禮器,表面同樣也存在這樣的紋路。古代青銅制器時(shí),講究表面花紋的寓意。鳳在古時(shí)是虛構(gòu)出來的鳥,龍與鳳,代表著水與風(fēng),將自然元素放在樂器上,進(jìn)行形象化描繪。而其他紋路,有來自神話,亦有來自民間傳說,例如1977年祥云檢村大石墓出土的編鐘、1978年云南牟定縣福土龍村出土的編鐘等,表面有帶狀飾紋和當(dāng)?shù)氐囊恍﹦?dòng)物圖案,體現(xiàn)了當(dāng)?shù)匚幕瘜?duì)古樂器編鐘表面裝飾的影響。
編鐘的制作,也是樂器與本土文化融合的體現(xiàn),樂器來源于生活,最終成形,就是樂器制作者思維的實(shí)物化呈現(xiàn)。將文化價(jià)值注入編鐘當(dāng)中,是情感的一種抒發(fā),在樂器制作中融合中國傳統(tǒng)文化,古往今來,都值得樂器行業(yè)的愛好者學(xué)習(xí)。
編鐘,在樂器制作者的眼里,可以說具有自身獨(dú)特的魅力。它有著自己的樂律,編鐘上的銘文非常重要,一來銘文記載了編鐘的歷史,二來銘文的出現(xiàn),也為編鐘樂律體系的完備提供了基礎(chǔ)。編鐘,按照排列的結(jié)構(gòu),上層的小鐘是高音區(qū),可以進(jìn)行旋律演奏,而中下層大鐘是低音區(qū),可以用來和聲等。編鐘的調(diào)音,可在編鐘內(nèi)部進(jìn)行銼磨,從而調(diào)整音的高低。古代樂器,與現(xiàn)代樂器一樣,接近制作尾聲時(shí)需要進(jìn)行測音,內(nèi)外部結(jié)構(gòu)的完整度,是達(dá)到樂器標(biāo)準(zhǔn)的關(guān)鍵。
三、青銅制編鐘對(duì)當(dāng)代音樂考古的意義
現(xiàn)代的樂器研究,講究對(duì)樂器的追本溯源。古樂器是樂器文化當(dāng)中必不可少的一環(huán),每一件古樂器的存在都有其價(jià)值。它的背后是音樂文化、樂器文化、社會(huì)發(fā)展歷程的一種集合。當(dāng)代音樂考古,被越來越多的學(xué)者所重視。音樂考古是考古學(xué)里的一個(gè)分支。我國的樂器文化,是一個(gè)巨大的寶庫,特別是對(duì)于古樂器進(jìn)行歷史解析的過程,艱辛但具有不可替代的價(jià)值。古樂器在現(xiàn)代存在的意義是多方位、多角度、多元化的。隨著音樂考古學(xué)的普及,編鐘等遠(yuǎn)古樂器逐漸被發(fā)掘,樂器背后的歷史也被人們所熟知,不僅僅是藝術(shù)學(xué),對(duì)考古學(xué)、歷史學(xué)等其他門類也有一定的影響。學(xué)科之間都是互相聯(lián)系的,音樂考古學(xué)被廣大學(xué)者熱愛,不僅僅是學(xué)科本身的魅力,更重要的是,在進(jìn)行音樂考古的同時(shí),對(duì)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國音樂歷史等都起到了豐富與擴(kuò)充的作用。
編鐘,不是一個(gè)單一的樂器,它從制作材料、樂器形態(tài)、表面修飾、樂律體系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它本身的存在就是古文化的一種再現(xiàn)。中國器樂文化博大精深,每一件古樂器的發(fā)掘,連帶著的是前后文化的重現(xiàn)。對(duì)于音樂考古來說,編鐘的制作工藝,展現(xiàn)的是歷朝歷代繁榮發(fā)展的工業(yè)技術(shù),涉及到當(dāng)時(shí)的音樂與經(jīng)濟(jì)發(fā)展;編鐘的形態(tài),向現(xiàn)代傳達(dá)古時(shí)宮廷等場合獨(dú)樹一幟的演奏方式,體現(xiàn)了當(dāng)時(shí)藝術(shù)的表現(xiàn)形式;編鐘的樂律體系,是古時(shí)樂者科學(xué)地表達(dá)心中旋律的成果;編鐘的表面修飾,則是人們將心中所愿,通過文化寄托的方式,以編鐘為載體,向世人展示。學(xué)術(shù)縱有諸子百家,藝術(shù)也不例外,每一種樂器都攜帶著一系列歷史,古樂器的發(fā)掘?qū)ζ渌囆g(shù)門類的考古也有促進(jìn)作用。編鐘,從來都不是一種“單一”的打擊樂器,所謂“非單一”,并不指其“不純粹”,本身編鐘就是多種類型鐘的一個(gè)小型集合。廣義上的鐘,更是數(shù)不勝數(shù),延伸出來的其他形態(tài)的鐘,也在歷史上留下了各自濃墨重彩的一筆,此時(shí)編鐘的非單一性借各個(gè)種類鐘體現(xiàn)出來。編鐘的發(fā)展,前人無法預(yù)測,后人也無法定性,只是編鐘既然在屬于它的時(shí)代出現(xiàn),就意味著它集經(jīng)濟(jì)、政治、人文、藝術(shù)為一體,作為宮廷樂器為王侯將相所喜愛也好,代表著王權(quán)身份也罷,它都一直以自身的魅力吸引著眾人,被皇室需要、被世人接納,為后人研究古樂器提供時(shí)間、地域等方面的史實(shí)依據(jù)。編鐘對(duì)于音樂考古的意義也由此可見。
現(xiàn)代樂器市場,各類樂器頗為琳瑯,古樂器的復(fù)原對(duì)于樂器愛好者來說,是研究音樂史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復(fù)原的過程,包括重新制作,在這樣的思維里,樂器研究者自然而然地對(duì)編鐘制作所需要的材料、形制、結(jié)構(gòu)、發(fā)音等方面進(jìn)行一個(gè)系統(tǒng)化的了解。不僅僅是編鐘,與編鐘同時(shí)期出土的文物也值得后人深入探討。這樣一來,由編鐘延伸出來多方面的研究,也會(huì)繼續(xù)發(fā)展,其他門類涉及到編鐘的歷史知識(shí)也得到補(bǔ)充,這也是青銅制編鐘在現(xiàn)代對(duì)于音樂考古的意義之一。編鐘,具有時(shí)代性、發(fā)展性,同時(shí)也具有創(chuàng)新性。新式材料與技藝的出現(xiàn),給編鐘在現(xiàn)代的復(fù)原發(fā)展提供了一種新思路。當(dāng)代社會(huì),樂器展覽、博物院展示、器樂論壇、大型音樂表演等,越來越多的平臺(tái)供樂者們使用。以博物館藏的方式為例,南京博物院會(huì)以不同朝代為劃分,向人們展示各朝代經(jīng)濟(jì)、藝術(shù)、文化、政治等方面的人文生活,編鐘也包括其中,博物館等場合講究跨界多元,目的也很明確。既然編鐘的意義,在現(xiàn)代依然存在,那么就值得樂器制作者們繼續(xù)挖掘本源和復(fù)原研究,以滿足樂器研究的要求,竭盡全力,向現(xiàn)代傳遞遠(yuǎn)古之鐘聲,體會(huì)古時(shí)樂器的磅礴,為更多的人開拓眼界,引起樂器愛好者們的思考,這不僅僅是編鐘這一樂器再現(xiàn)它的價(jià)值,更是古今相連,跨越時(shí)空的一種音樂文化融合。
四、結(jié)語
編鐘與音樂考古,相互促進(jìn)。鐘聲跨過幾千年,再次來到人們的心中。樂器與人,不曾分隔。編鐘再現(xiàn)古時(shí)人文情懷。樂器文明,縱觀歷史,長河以往,地域交錯(cuò),文化相融。盛衰更迭,變的是光陰,不變的是編鐘所帶來的文化、歷史和藝術(shù)韻味。編鐘的存在為音樂考古提供了歷史依據(jù),更豐富了鐘這一類樂器的歷史,作為一個(gè)研究載體而體現(xiàn)它的價(jià)值。在未來,編鐘一方面可保持其本源,即遠(yuǎn)古時(shí)期的特點(diǎn),供音樂考古學(xué)者們進(jìn)行研究,另一方面,復(fù)原編鐘是一項(xiàng)值得進(jìn)行的工作,同時(shí)樂器制作講究改良與創(chuàng)新,在考究本源的同時(shí),編鐘能否與現(xiàn)代元素相結(jié)合,從而給人們帶來不一樣的視聽感受,這是樂器愛好者們值得思考的一個(gè)問題。
參考文獻(xiàn):
[1]李純一著.中國上古出土樂器綜論[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177,276-277.
[2]王子初著.中國音樂考古學(xué)[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3:3.
[3]方建軍著.中國古代樂器概論 遠(yuǎn)古-漢代[M].西安:陜西人民出版社,1996:3-7.
[4]李先登著.商周青銅文化[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9:26.
[5]朱立春主編.中國通史[M].北京: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7:30.
[6]崔憲著.曾侯乙編鐘鐘銘校釋及其律學(xué)研究[M].北京:人民音樂出版社,1997:2-3,135-136.
[7]冀昀主編.呂氏春秋[M].北京:線裝書局,2007:344.
[8]馬承源著.中國古代青銅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0,34,150.
[9]中央工藝美術(shù)學(xué)院編著.工藝美術(shù)辭典[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8:58.
[10]謝海元,顧望編著.中國青銅圖典[M].杭州:浙江攝影出版社,2019: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