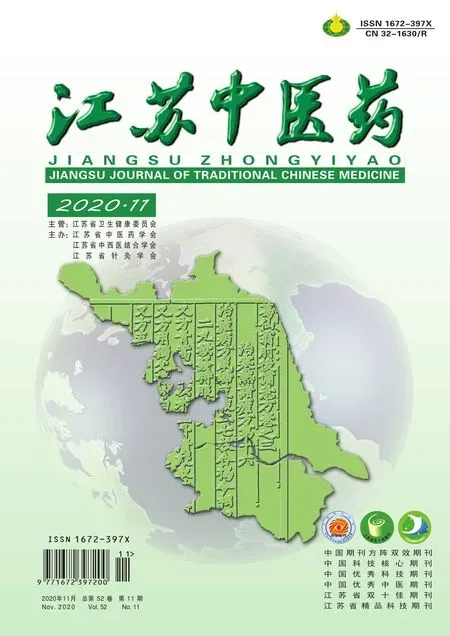顧慶華應用經方治療食管源性胸痛臨證擷要
顧 瑋 陸 榕
(1.江蘇省南通衛生高等職業技術學校,江蘇南通226010;2.南通大學附屬醫院,江蘇南通226001)指導:顧慶華
胃食管反流病等疾病引起的胸痛稱為食管源性胸痛,主要以胃食管反流病、食管動力障礙以及食管超敏為主要潛在機制,也有一部分因食管腫瘤、放療等原因引起的胸痛。研究表明食管源性胸痛患者中,胃食管反流病是其最常見的原因,患病率30%~60%[1-2]。食管源性胸痛典型癥狀為胸骨后或胸骨下發作性疼痛,嚴重時疼痛劇烈,伴泛酸、燒心等,并可導致食管炎及咽喉、氣管等食管外組織損害[3]。目前西醫治療措施主要包括抑制胃酸分泌,降低胃蛋白酶、膽汁等消化酶對食管的損傷,改善胃腸動力,修復食管黏膜屏障及心理干預等[4]。但西藥治療存在易復發、耐藥性等問題。顧慶華教授是第二批全國優秀中醫臨床人才、江蘇省名中醫,從醫三十余載,精于內科,尤擅應用中醫藥治療脾胃病,療效顯著,顧教授認為食管源性胸痛可歸屬“胸痹”證、“結胸”證范疇,提出本病病位在食管與胃、與肺脾肝三臟關系密切;病理因素為寒飲、濕熱、痰瘀等,發病多由肝氣郁結,脾失健運,胃氣上凌于胸所致,同時與肺的宣肅功能失司密切相關,故臨床表現多以胸骨后痹阻、疼痛,咽部如有痰阻,時有反酸或嗆咳為主。本病有虛實寒熱之分,用藥也各有不同,顧教授擅用經方加減治療食管源性胸痛。現將其經驗總結如下,以饗同道。
1 痰熱蘊結——清化痰熱,肅肺和胃,以小陷胸湯加味
《傷寒論》第131條指出:“病發于陽,而反下之,熱入因作結胸;病發于陰,而反下之,因作痞也。所以成結胸者,以下之太早故也。”《諸病源候論·傷寒結胸候》有云:“結胸者,謂熱毒結聚于心胸也,此由病發于陽而早下之,熱氣乘虛而痞結不散也。”由于熱痞結于中焦胸膈,肺氣失于宣通,《素問·經脈別論》云:“飲入于胃,游溢精氣,上輸于脾,脾氣散精,上歸于肺,通調水道,下輸膀胱,水精四布,五經并行”,脾胃與肺共同參與水液代謝。脾主運化水液之作用,有賴于肺氣宣發和肅降功能的協調;肺之通調之職,亦需脾氣運化之力才能正常。脾肺功能失常不能運化水濕,水濕聚而生痰,導致痰熱并結于胸中陽位,從而出現痰熱蘊結證。結胸證有“結甚、結微”之分,顧教授認為本病病證屬于結胸證之輕證,臨床表現除胸悶、胸痛外,還有大便秘結不通、舌苔黃膩、脈弦滑數等癥,遂采用小陷胸湯治療。小陷胸湯原用于傷寒表證誤下、邪熱內陷、痰熱互結的小陷胸證。最早記錄于《傷寒論》第138條“小結胸病,正在心下,按之則痛,脈浮滑者,小陷胸湯主之”及《傷寒論》第141條“寒實結胸,無熱證者,與三物小陷胸湯,白散亦可服”。原方由黃連一兩、半夏半升、瓜蔞實大者一枚組成。全方配伍體現了“辛開苦降”的特點:瓜蔞實寬胸散結、潤腸通便;半夏燥濕化痰、消痞散結;黃連清熱燥濕,故《古今名醫方論》認為本方“以半夏之辛散之,黃連之苦瀉之,栝樓之苦潤滌之”。同時現代藥理研究表明小陷胸湯在消化系統方面主要發揮抗炎、抗菌、止嘔、保肝利膽等功效[5]。
顧教授常配伍紫菀、梔子、淡豆豉,紫菀苦溫而潤,能通肺氣,開泄郁結,梔子、淡豆豉合成梔子豉湯能陳腐解郁熱,疏暢清陽之氣,三藥與小陷胸湯相合共奏清化痰熱、肅肺和胃之功。
2 寒痰痹阻——溫陽散寒,寬胸化痰,以枳實薤白桂枝湯加減
胸居于陽位,《諸病源候論·胸痹候》提出“寒氣客于五臟六腑,因虛而發,上沖胸間,則胸痹”,胸陽一虛,則寒邪易乘陽位,導致胸中宗氣痹而不通,《靈樞·本臟》亦指出“肺大則多飲,善病胸痹喉痹逆氣”。胸中宗氣被郁,肺宣降失職,津液不布,可凝而為痰,痰濁中阻,氣機閉塞,導致痰聚阻氣,肺胃同病。顧教授認為本證胸痹之病勢由胸部擴展到胃脘兩脅之間,而脅下之氣又上沖形成胸胃合病,本證型多表現為:胃脘及兩脅窄隘不舒,心慌氣短,胸部憋悶疼痛,甚則徹及背部,舌質淡紅、苔白膩或滑,脈弦。故采用枳實薤白桂枝湯治療。本方最早記載于《金匱要略·胸痹心痛短氣病脈證并治第九》:“胸痹心中痞,留氣結在胸,胸滿,脅下逆搶心。枳實薤白桂枝湯主之。”原方由枳實四枚、厚樸四兩、薤白半斤、桂枝一兩、瓜蔞實一枚組成。方中重用枳實、厚樸消痞除滿,薤白通陽宣痹散結配伍寬胸理氣化痰之瓜蔞實以通陽開痹、寬胸滌痰,桂枝溫陽能降沖逆之氣。顧教授常配伍芳香化濕之砂仁、豆蔻,二藥與枳實薤白桂枝湯相合共奏溫陽散寒、寬胸化痰之功。
3 中虛氣逆——益氣健脾,降逆和中,以厚樸生姜半夏甘草人參湯出入
小陷胸湯與枳實薤白桂枝湯均用于實證,而在枳實薤白桂枝湯方證后,張仲景提出“人參湯亦主之”,人參湯組成:人參、甘草、干姜、白術各三兩,以藥測證可知,人參湯適用于陽氣虛弱、客氣沖逆的病證,胸痹有虛、實之分,病程有久、暫之別。寒、濕、痰等病理因素長期并存或久用寒涼疏利容易耗氣損陽,人參湯以人參補氣扶正、干姜散寒振奮陽氣、白術健脾益氣、甘草緩中益氣。顧教授認為此方偏于補陽,且無行氣之藥,而在病證中單純陽虛的證型偏少,通常以中虛氣逆證較多,除胸悶胸痛外,還伴有乏力、頭暈、納少、腹脹、便溏、舌質淡、苔薄、脈弦細等,顧教授喜用厚樸生姜半夏甘草人參湯治療,本方見于《傷寒論》第66條“發汗后,腹脹滿者,厚樸生姜半夏甘草人參湯主之”。原方由厚樸半斤、生姜半斤、半夏半升、甘草二兩、人參一兩組成,仲景用于治療太陽病發汗后,陽氣外泄,脾氣虧虛,氣機失調而出現腹脹滿的一張方子[6],《內經·藏氣法時論》:“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用苦泄之。”厚樸生姜半夏甘草人參湯證病機是脾氣不足,氣機阻滯,運化失常,從藥味組成及劑量看本方寓有“治標宜急,治本宜緩”之意。方中以微苦性溫之厚樸為君,行氣消脹,除胃中滯氣而燥脾;生姜性溫而味辛,宣散通陽止嘔,行胃中之滯氣,半夏辛溫、化濕、降逆散結、滌痰,降胃中逆氣,兩者與厚樸為伍,辛開苦降,溫陽行氣;甘草與人參補中益氣、扶中。顧教授常配伍焦山楂、神曲、炒萊菔子,以酸甘性溫之山楂,消一切飲食積滯,甘辛性溫之神曲,消食健胃,辛甘而平之萊菔子,下氣消食除脹,三藥與厚樸生姜半夏甘草人參湯相合,共奏益氣健脾、降逆和中之功。
4 胃虛有熱——益胃養陰,清熱降胃,以橘皮竹茹湯加減
病程日久,出現胸悶,胸痛,呃逆不舒,納差,口中異味,舌苔少、舌質紅,脈細數等表現,顧教授認為此為胃虛有熱,以橘皮竹茹湯加減治療。橘皮竹茹湯出自《金匱要略·嘔吐下利病脈證治第十七》第23條“噦逆者,橘皮竹茹湯主之”。原方由橘皮二升、竹茹二升、生姜半斤、人參一兩、炙甘草五兩、大棗三十枚組成,《景岳全書·古方八陣·和陣》指出:“橘皮竹茹湯,治吐利后胃虛膈熱呃逆者。”方中性微寒之竹茹配伍辛溫之橘皮、生姜理氣和胃降逆,人參、甘草、大棗益氣補中,以復脾胃升降之職。諸藥配伍,補中益氣、和胃降逆。顧教授根據橘皮竹茹湯方證特色結合本證型的特點,常配伍百合、烏藥,百合甘潤微寒,兼能清熱,護衛營陰,再配以烏藥辛溫行氣,一溫一涼,柔剛相濟,潤而不滯。二藥與橘皮竹茹湯相合,共奏益胃養陰、清熱降胃之功效。
5 病案舉隅
張某,男,34歲。2019年7月3日初診。
患者胸悶、胸痛伴反酸反復發作3年,加重1月。經抑酸藥物治療癥狀緩解但未消失。近1月來,胸痛,牽及后背,胃脘嘈雜,伴燒心,大便2~3日一解,干燥臭穢。予心電圖、心肌酶譜、冠脈CT、胸部CT等檢查均未見明顯異常。舌質紅、苔黃膩,脈弦數。胃鏡診斷為:反流性食道炎,淺表性胃炎。中醫辨證為痰熱蘊結。治擬清化痰熱,肅肺和胃。處方:
全瓜蔞20 g,竹瀝半夏9 g,黃連3 g,桔梗6 g,紫菀20 g,焦梔子6 g,淡豆豉10 g,煅花蕊石15 g,煅瓦楞子15 g,甘草3 g。14劑,每日1劑,水煎分2次服。
7月17日二診:服藥后胸悶胸痛明顯改善,大便1~2日一解,質軟通暢,舌質淡紅、苔薄黃膩,脈弦。原方加浙貝母10 g,14劑。服藥后胸痛、反酸等癥已平,大便通暢,守方續進1個月,復查胃鏡:淺表性胃炎。
按語:本案患者以胸悶、胸痛伴反酸為表現,經相關檢查心肺均未見明顯異常,胃鏡示:反流性食管炎,屬于食管源性胸痛,我們認為屬于“結胸”范疇,以清化痰熱、肅肺和胃為法,予小陷胸湯加減治療。方中黃連、半夏、瓜蔞清熱化痰,寬胸散結;梔子、淡豆豉二藥相伍乃“梔子豉湯”意,以祛胸中郁熱;桔梗、紫菀相伍,以宣肅肺氣,體現了臟腑論治,肅肺以降胃;煅花蕊石、煅瓦楞子清胃制酸,護膜生肌;甘草調和諸藥。諸藥合參,共奏其效。
食管源性胸痛為消化內科常見病癥,屬于非心源性胸痛范疇,臨床發病率較高,且易與心源性胸痛相混淆,需要仔細鑒別,不能漏診誤診,食管源性胸痛以胃食管反流病為基礎,因此有些患者常遷延難愈,有時常規疏肝利膽和胃的方法不能達到預期效果。因此,積極地探討經方方證,做到經方與時方并重,拓寬經方的運用范疇,將有助于解決此類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