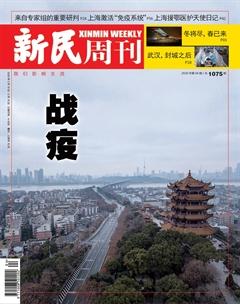火神山雷神山能起到“特種部隊”作用
黃祺

8天時間,一座可容納1000張床位的醫院正式落成。這就是參照2003年非典期間北京小湯山醫院所建的火神山醫院。2月3日,這所醫院開始收治病人。據悉,火神山醫院主要救治確診患者,開設重癥監護病區、重癥病區、普通病區,設置感染控制、檢驗、特診、放射診斷等輔助科室。
近日,《新民周刊》專訪了麻醉專家熊利澤。2003年,熊利澤教授臨危受命,擔任第四軍醫大學赴京醫療隊隊長,帶領醫療隊支援北京小湯山醫院,任小湯山醫院重癥監護室主任。7天時間平地而起的小湯山非典醫院收治了全國七分之一的患者,最終患者治愈率99%,1383名醫護人員零感染,被世衛組織稱為“奇跡”。
臨時醫院將很大程度緩解武漢救治壓力

熊利澤,現任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院長。
《新民周刊》:武漢火神山醫院、雷神山醫院很快就要投入運轉,非典時期您在小湯山醫院擔任要職,從您的經驗看,目前兩個臨時醫院建成后,將在多大程度上緩解救治壓力?
熊利澤:武漢很快就決定建設兩個臨時醫院,被稱為武漢的“小湯山醫院”,說明政府決心很大。我的老領導、小湯山醫院當時的院長張雁靈現在也在現場指導建設工作。
我沒辦法給個確切的數字來預測這兩所醫院能多大程度緩解救治壓力,但根據非典時期的經驗,我可以說將很大程度緩解壓力。
這個結論可以從幾個方面理解:第一,據我了解武漢很多醫院目前壓力非常大,患者太多,存在院內交叉感染的風險。如果這些患者收治到臨時醫院,將很大程度上緩解現有醫院的壓力,否則醫院里一直有交叉感染的話,患者人數會不斷增加。
第二,臨時醫院能夠有一個示范效應。我們從公布的數據可以看出,目前武漢新冠患者出院病人不多。臨時醫院由軍隊派出的醫療隊接管后,他們有檢測能力,可以根據相關指南讓一部分符合出院標準的治愈病人出院。這樣,病人流轉起來,寶貴的醫療資源就能用到最重的病人身上,醫院能收治更多需要治療的病人。
臨時醫院啟用后更重要的作用是減少社會恐慌情緒。根據小湯山醫院的經驗,臨時醫院啟用后治愈率會提高,死亡率減少,那么公眾的恐慌就會緩解。
至少從我個人判斷,我對這兩家臨時醫院寄予厚望。如果光從床位數看,你可能覺得2000多張床位不是很快就住滿嗎?其實不是這樣的。就像打仗,有的特種部隊人數不多,但起到的作用很大。
《新民周刊》:兩個臨時醫院將由軍醫系統接手,我們軍隊醫療力量在這樣的疫情中,有哪些優勢?
熊利澤:軍隊的醫療力量,首先是執行力非常強,醫護人員會按照要求和標準來防護、治療。他們平常就有備戰的訓練,所以磨合的時間會比較短,可以迅速地投入救治。而且軍隊醫療系統本身在災難醫學上,在成體系的救援上具有豐富的經驗,傳染病這樣的公共衛生事件中,比如非典、非洲埃博拉疫情的支援上,軍隊醫療系統培訓了很多專業人才。
軍隊醫療系統還有一個特點,一旦出動,架構會很完整。比如他們會帶自己的檢測人員、檢測設備,彌補目前武漢救治能力的不足。
小湯山經驗:醫護人員個人防護放在第一位
《新民周刊》:小湯山醫院“高治愈率、低死亡率”,醫護人員沒有感染的情況。請您介紹一下當時最重要的經驗是什么?
熊利澤:小湯山醫院最重要的經驗,就是感控做得非常好。一個副院長帶隊,成立了20多人組成的督導團隊,專門管醫護人員的個人防護,對醫院交叉感染的風險進行管控。
在小湯山醫院正式運轉前,我們所有人員做了充分的培訓,并不是說醫院一建好就馬上開始收治病人。我記得有幾天時間,我們做了很多培訓,培訓怎么做防護,要求醫護人員絕對不能感染,如果醫護人員感染那是非常危險的。

2003年非典時期擔任北京小湯山醫院院長的張雁靈。圖片提供/ 熊利澤
當時小湯山醫院把醫護人員的個人防護放到了最重要的位置。比如說我們盡量減少開會,如果開會不允許在室內開會。我記得北京市政府給大家配備了“小靈通”,那時候“小靈通”信號不怎么好。我們有個順口溜:“站在風雨中,手持小靈通,昂著頭挺著胸,就是打不通。”現在通信手段好多了,可以利用這些工具開會。另外那時候后勤保障做得很好。
我們的醫療條件17年進步很大,治療手段比當初好很多,盡管大家對這次疫情控制有批評,但我們也要看到這些進步的地方。
另外,我們成立了一個專家組,我也是專家組的成員。如果出現疑難病例,都是專家組會診解決的,這對于提高治愈率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新民周刊》:臨時醫院條件畢竟不能像正式的醫院一樣完備,您對武漢兩座臨時醫院未來的運轉,有些什么提醒?
熊利澤:盡管現在的臨時醫院肯定比17年前硬件條件好很多,但跟正規醫院還是不能比。比如保溫不知道是不是做得好,因為武漢現在氣溫還是比較低。
還有一個問題,不知道醫護人員宿舍這次放在什么地方。北京小湯山醫院建設時,考慮到傳染風險,工作人員住宿的地方離醫院比較遠,上班必須靠車。現在我們對病毒的傳播能力有了比較多的了解,我們知道宿舍和醫院其實沒有必要距離那么遠。

1月28日,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15名醫護人員加入第二批上海援鄂醫療隊,趕赴武漢。
17年過去,疫情控制能力提高了
《新民周刊》:非典過去17年,您認為這次新冠疫情的控制,哪些方面是有進步的?哪些還需加強?
熊利澤:17年的時間,科學對疾病的認識已經有了很大的進步,對于這次新冠疫情的控制,我們更有信心。我們醫療隊當時出發去小湯山醫院的時候,坐上車大家都在哭。為什么呢?因為非典中死亡的病人中三分之一是醫護人員,大家聽到的消息都是醫護人員在犧牲。那時對病毒完全不了解,疫情到底能不能被控制住,大家沒底,大家都想,去小湯山一年能回來嗎?但這一次,我們已經可以認識到疫情是可以控制住的,我們討論時間的時候是用“月”做單位,這就是最大的進步。
從治療上,因為沒有特效藥,當時給非典病人用了大量的激素,后來導致了嚴重的后遺癥。但這一次的治療,我們從一開始就沒有大量用激素。我們的醫療條件17年進步很大,治療手段比當初好很多,盡管大家對這次疫情控制有批評,但我們也要看到這些進步的地方。

2003年非典期間熊利澤(左二)與同事在小湯山醫院留影。
疫情緩解后,建議迅速關閉能力不足的發熱門診
《新民周刊》:這次疫情與非典相比有什么特別不一樣的地方?您對目前的防控措施有沒有什么建議?
熊利澤:這次新冠肺炎的特點是潛伏期長,趕上春節假期,大家都出發到各地去了。早期這些人員的流動,造成全國都有了病人,大家非常緊張。非典疫情雖然也波及全國,但主要還是在幾個重點區域疫情比較嚴重。防控的建議,我認為應該有更多的流行病學專家參與到政府決策中。現在我們打的是“人民戰爭”,這是我們國家的優勢,這是值得贊賞的。
但我們也要依靠科學的策略,這個就要依靠專業人員,需要流行病學專家出謀劃策。另外我要呼吁防控中不要歧視病人,更不能歧視疾病高發地區的人。如果我們把他們當做“敵人”,他們都躲起來了,或者生病了不去醫院,這可能會造成更多人的感染。應該有一個寬松的環境,讓他們站出來,及時接受治療。
我還有一個建議,在后期的防控中,優質的醫療資源要發揮最主要的作用。綜合性大醫院有正規的傳染科,有一批呼吸科、傳染科人才。但一些區級、縣級的醫療機構,能力不夠,防護的物資可能也不夠,讓他們來應對傳染病,增加了誤診和院內感染的風險。我們要把英雄主義與科學精神結合起來。一開始病人多,必須要這么多醫療機構來應對,但將來病人逐漸減少,就應該盡快地關閉沒有能力的發熱門診,以免造成新的問題。武漢一線的救治,需要盡快從無序狀態轉變到有序狀態,必須要有序管理、有序運轉。新冠肺炎疫情畢竟是一個長期的消耗戰,不是一天兩天能夠勝利的。一開始可能是無序混亂的,但這個階段越短越好。
《新民周刊》:您是湖北人,疫情發生后,是不是特別關注疫情發展?參與了哪些工作?
熊利澤:我從一開始就關注這次新冠疫情,早期的信息顯示情況還是可以的,尤其武漢醫療資源很豐富,我相信能控制得很好。疫情擴散以后,按照上級部署,我作為院長組織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為應對疫情做了人力、物資、場地的準備。大年三十,我們提前把急診二樓全部騰空,作為新冠肺炎疑似肺炎的隔離病房。以前發熱門診沒有專門的CT,我們緊急采購了一臺CT,專門用于發熱病人的檢查,這樣就把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降低。這臺機器是聯影提供的,可以自動調節患者體位,我們工作人員也不需要與患者接觸。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是上海發熱門診定點醫院,我們按照最高的標準來準備,原來整個二樓病房可以收治60多個病人,現在按照傳染病標準,可以收治6人。 1月23號,醫院就發出了組建援鄂醫療隊的號召,醫護人員踴躍報名,很快就組建了15人的隊伍。現在15人參加到第二批上海援鄂醫療隊,已經進駐武漢第三醫院工作。據我所知,第二批醫療隊中,上海市第四人民醫院是派出醫療人員最多的單個醫療機構。
我的專業是麻醉,有很多學生在湖北一線參與救治新冠肺炎病人。這些天我一直在把這些年的經驗分享給一線的這些醫生們。前幾天我寫了一篇文章:《抗擊新型冠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給麻醉科醫護工作者的幾點建議》,我建議大家在救治新冠肺炎病人,做插管操作的時候,要用藥物松弛患者肌肉,減少氣管插管時患者噴射分泌物的出現,降低醫護人員感染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