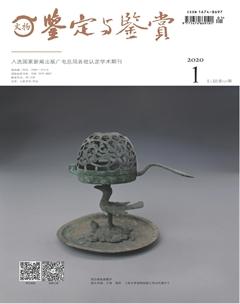由《邦家之政》談出土戰國文獻學派問題
張敏
摘 要:清華簡(捌)《邦家之政》反映的是儒家思想還是墨家思想,學者略有爭議。學派不明,甚至影響到對字句的訓釋。戰國時期的竹簡反映的思想常常蘊含兩個或多個學派的思想,較為復雜,并不適宜以“六家”“十家”分類,反而應回到諸子“百家”,以人物區分,來細化文獻反映的思想。
關鍵詞:《邦家之政》;儒學;墨學
1 《邦家之政》“肥(菲)”字訓釋及其反映的學派思想
清華簡(捌)《邦家之政》“假托孔子與某公對話的形式闡述作者的治國為政的理念”[1],其整理者認為“主要反映儒家的理念,在諸如節儉、薄葬、均分等方面又與墨家思想相合”[2]。王寧認同《邦家之政》為儒家文獻,在其《清華簡八〈邦家之政〉讀札》中,分析簡3“亓(其)豊(禮)肥(菲)”,認為“肥”“當讀為‘配訓‘當、訓‘合,合適、恰當之意”,并非整理者所訓為的“儉樸”。值得一提的是,除整理者、王寧先生兩種訓法外,陳民鎮先生與程浩先生認為“肥(菲)”都應如字讀,得出相反的結論。陳先生認為“肥”字“可如字讀,訓‘薄”[3]。程先生認為“‘肥或可如字讀,理解為禮用豐厚使邦家興盛”[4]。據此,便有三種不同的訓法[陳先生認為“肥(菲)”其義為薄,與儉樸相近]:“儉樸”“適當”“豐厚”。出土文獻中雖有“肥”表示“配”的用法,但王寧先生因其為述及孔子,便將《邦家之政》定為儒家文獻,進而得出“肥”為“合適、適當”之意,或為不妥。前文已提到,《邦家之政》是假托孔子與某公對話,除本篇外,戰國時期,假托孔子的著述還有很多,如《莊子·大宗師》篇講的是孔子與顏回關于“坐忘”的談論,故而并不能簡單以假托某人學說,便得出是某派思想的結論。子居認為“稱及孔子不等于即是儒家……本質上仍是承自子產的尚儉觀”[5]。王寧先生確認為儒家文獻,又因儒家重禮,以其佐證,或有不合。如訓為“豐厚”,似難與節用主旨相符。學者們之所以對“肥(菲)”字做出“儉樸”“適當”“豐厚”三種不同的訓釋,原因有三:一是這些訓釋都可從傳世文獻中找到佐證;二是簡文缺字漏字;三是簡文呈現的思想的復雜性,不僅含有儒家思想,亦含有墨家的節儉、薄葬、均分等,甚至子居認為《邦家之政》為曾受墨家影響、秉承管子學派的子產后學[6]。某家某派的思想并不是涇渭分明的,當某篇文獻反映兩家或兩家以上的思想時,便很難辨別出此篇文獻是哪家的產物。
《邦家之政》“大致可分為三段:前段從正面敘述使國家長治久安的做法,第二段從反面揭示導致國家衰敗破亡的原因;末段倡導從古,慎始扶正,善治人事”[7]。文章第一段闡述“邦家將成”,拋卻眾多學者因“菲”的訓釋產生的不同看法,僅就剩下的任用賢能,宮室低矮,器用素樸,政治平和等思想,很是接近墨家“節儉”的思想,李均明先生的兩篇文章[8][9]都曾提到,“《邦家之政》或為儒墨交融的產物”“《邦家之政》所代表的當為根植于民眾,主張簡樸生活、公平分配乃至社會和諧,與墨家有更多交融的儒者”。文章第二段談及“邦家將毀”,君主不再任用賢能,而是聽信讒言,宮室不再小卑,而是大高,器大禮繁樂淫政苛刑濫等一系列行為與前段對比,邦家衰敗。除《邦家之政》外,新出的上博簡《卉茅之外》亦有“多廟寡情,民故弗敬”的表述。文章第三段則是在前兩段對比后得出結論。
2 儒學思想與墨學部分思想對比
《邦家之政》若不論學派,單看思想劃分,既含有儒家思想的內容,又含有墨家思想的內容,甚至也有學者認為《邦家之政》反映的思想是受墨子影響的、秉承管子學派的子產后學的思想,是儒墨兩學或者說儒墨兩家因“天下同歸而殊涂,一致而百慮”導致兩學派的思想除相異之處外也存在著一定的相似之處。“儒”,“最初是對一種宗教職業人員的稱呼”[10]。孔子整理六經,開辦私學,招收學生,“儒”也逐漸發展成為一種學派。《淮南子·要略》稱:“墨子學儒者之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悅,厚葬財而貧民,久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學的產生則是墨子最初受到孔子思想影響,學習儒家思想,之后因不贊同孔子“復禮”等,發展出另一種學派。
儒學與墨學在一些方面有較為明顯的區別,如墨子提出“兼愛”,孔子認同“親親”。墨子認為,如果每個人都平等地愛眾人,就可以實現政治清明。孔子認為政治清明需要“禮”的維護。墨學主張“節葬”“節用”;儒學重“禮”重“孝”,主張“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在喪葬上、器用上更是有明確的等級制度。再如墨學訴諸的是小生產者的利益,而儒學則相對訴諸的是政治高層的利益。
儒學與墨學亦有相似的一方面,如墨學主張“尚賢”,孔子主張“舉賢才”,雖然方式或有不同,但其根本是推崇賢人的。不僅僅是儒學和墨學,甚至《老子》也多次提出“圣人”治天下。再如皆主張推行仁政,學說相合,是因其當時所處社會所要解決的根本問題是相同的,不同的是解決問題的方式。
《莊子·天下》篇中言“道術將為天下裂”,古之道術分散于百家,《韓非子·顯學》篇中稱“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儒墨兩家的最終政治理想是相似的,儒墨兩家學說相異更多是因為階級立場的不同。
因為要解決問題,便不斷提出一些學說、一些思想。思想的提出者雖受當時時代的限制,但思想提出后,自成一派,便有其后學不斷發展與完善其思想。如關于天人關系的回答,由天人相合到天人相分,因為學說的提出雖受時代的局限,但有意義的學說在提出后會不斷發展,不斷趨于完善。在完善的過程中,“百家”學說互為補充,互相吸收,難免會在某些方面出現趨同,并漸漸形成后世的“九流”“十家”。
3 思想上的“百家”爭鳴
《邦家之政》呈現出不同學派的思想。而在戰國時期,一些學派的思想并不是涇渭分明的。思想的提出是為了解決問題,就如古書成書,并不是單線的,而是許多版本經過不斷整合形成一個傳世本。解決問題的形式不同,就會導致思想的呈現方式不同,并形成了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百家也并不是完全對立的,其思想或許有一部分截然相反,如墨子的“兼愛”與孔子的“親親”;更有一部分是彼此借鑒,彼此吸收,如《邦家之政》所反映的思想。
“百家爭鳴”形成于春秋戰國這個特殊時期,各家的主張或者不盡相同,甚至差異很大,但根本上的目的卻是趨同的,這就使各家各派在尋找著最佳措施的同時產生一定程度的交融。《莊子·天下》篇中將墨翟、禽滑釐視為一派,將宋钘、尹文視為一派,將彭蒙、田駢、慎到視為一派,將關尹、老聃視為一派,莊子自成一派,最后評論惠施、桓團、公孫龍。《荀子·非十二子》中將它囂、魏牟視為一派,將陳仲、史鰍視為一派,將墨翟、宋钘視為一派,將慎到、田駢視為一派,將惠施、鄧析視為一派,將子思、孟軻視為一派。《韓非子·顯學》中稱“世之顯學,儒、墨也”,又說“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呂氏春秋·不二》篇中“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兼,關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后”。除《韓非子·顯學》篇的另外三篇,皆是以人物來區分各自思想上的不同,除儒、墨外,陰陽家、名家等還未徹底形成。至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將諸子百家分為“六家”,即陰陽﹑儒﹑墨﹑名﹑法﹑道德。之后,劉向父子又將其分為“九流”“十家”。儒家、墨家、法家等是漢以后才有的概念,那么,于戰國時的文獻,就難以將其按照儒家、墨家、法家等來論。溯源而上,以人物區分文獻思想則或許比以學派區分文獻思想更為合適。
李銳先生認為“有必要根據當時人的視域來討論什么是學派以及學派劃分的標準。當時人看學派更重視師承淵源和師說,‘百家比‘六家‘九流十家更適合用來稱呼簡帛古書”[11]。關于“百家”,李銳先生亦做出解釋,“戰國時代,論及‘百家時,‘子是‘家的代表,舉一‘子可以賅括一‘家”[12]。由于時代距今太遠,古書體例與今書不同,且又經秦火焚燒,難以辨別某一子所呈現的思想,難以見其全貌,亦難以再現“百家”學說。明確師承并不一定能一錘定音其學派。便如墨子,初學于儒學,之后因反對儒學繁雜而創立墨學。在判別文獻所屬學派時,應當全面地看待這篇文獻所反映的思想,不能僅因為看到文獻部分內容符合某學派,便斷定為某學派的文章。著者所受到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文獻的成型亦可能也較為復雜。
張豈之先生在《中國思想史》中提道:“如果從更加開闊的學術視野出發,不僅看到思想史上學派間的差異,更加重要的是分析‘差異是如何轉化為‘融合‘會通的……找出‘融合的關節點以及‘融合與‘創新的關系,也許這是克服思想史研究中某些概念化、公式化的有效途徑。”[13]很多版本的《中國思想史》雖著述了諸子思想的聯系、發展等,但人在不同時期,面對不同問題、不同對象,會有不同的態度,這就在一定程度上難免割裂諸子思想。
4 結語
如《邦家之政》這類的文獻,包含多種學派的思想,又因其學派本身便有思想相合的現象,“關節點”不好確定,便很難界定屬于哪個學派的文獻。為了方便研究,或許可以退上一步,無法根本上確定文獻學派時,便不具體到某一個學派。先秦有諸子百家,就難免有諸如融合了儒墨學說或者融合了孔子、老子學說等再成一家的,只是因傳世文獻的缺失,我們不能看到。漢朝時定家派,因其文獻所限,如只存在偏向儒學的文獻,缺失了偏向墨學的文獻,那便將其定為儒家,所以,不當簡單地以漢時文獻的家派劃分來界定戰國時文獻的思想。■
參考文獻
[1][2][7]李學勤.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捌)[M].上海:中西書局,2018:121.
[3]陳民鎮.清華簡(捌)讀札[Z].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rp/6831/2018/20181117172306966584873/20181117172306966584873_.html,2018-11-17.
[4]程浩.清華簡第八輯整理報告拾遺[Z].清華大學出土文獻與保護中心,http://www.tsinghua.edu.cn/publish/cerp/6831/2018/20181117171808287933997/20181117171808287933997_.html,2018-11-17.
[5]子居.清華簡八《邦家之政》解析[Z].http://www.xianqin.tk/2019/02/15/707/,2019-02-15.
[6]子居.清華簡八《邦家之政》解析[Z].http://www.xianqin.tk/2019/02/15/707/,2019-02-15.
[8]李均明.清華簡《邦家之政》的為政觀[J].清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8(6):168-172.
[9]李均明.清華簡《邦家之政》所反映的儒墨交融[J].中國哲學史,2019(3):25-29.
[10]張豈之.中國思想史(上)[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2:42.
[11]李銳.對出土簡帛古書學派判定的思索[J].人文雜志,2012(6):101-107
[12]李銳.“六家”“九流十家”與“百家”[J].中國哲學史,2005(3):6-13
[13]張豈之.中國思想史(上)[M].西安:西北大學出版社,201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