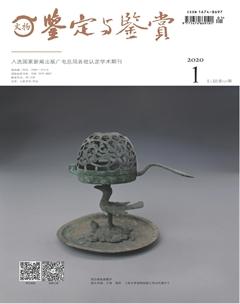對文物保護與修復的認識與思考
郗悅
摘 要:文物保護與修復為考古研究工作提供保障,同時也影響著考古發掘工作的進展。由于其內容的特殊性,且擁有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因此形成一門獨立的專業。但在文物保護與修復過程中仍存在“變舊”還是“變新”等問題的爭議,所以在有關文物修復效果、對文物干預的程度、修復與保護的理念等方面,如何尊重前人為文物賦予的思想內涵、尊重文物承載的精神意義,需要研究者在文物保護與修復的技術上和思想上保持與時俱進、開拓創新、內外兼收,使文物在被保護和修復的同時使其內在的文化意義最大化,從而推動文博事業的不斷發展。
關鍵詞:文物保護與修復;標準;理念;技術
文物保護與修復因其獨特性和擁有相對完整的理論體系而成為一門獨立的專業。文物保護與修復貫穿文物從被發掘至后期保存的整個過程,更是考古發掘中需要提前思考、科學規劃、及時實施的一項必要工作。文物保護與修復為考古工作提供保障,同時也影響著考古發掘工作的進展。近幾年文物保護與修復也因為《我在故宮修文物》等文博節目或紀錄片的播出而進一步走近公眾視野。關注文物保護與修復的相關信息不難發現,時有某地文物被過度修復的報道,因而引發一些爭議,當前有關文物保護與修復度的問題越來越受到重視。
1 影響文物保護與修復措施的因素
現代的考古發掘更注重遺址、遺跡、遺物在發掘過程中及其后的保護,如實驗室考古在海昏侯墓地的運用。而針對文物保護與修復的爭議,主要在于是“變舊”還是“變新”的問題。文物修復后“太舊”,掩蓋了文物本身的魅力,難以窺見文物的真實面貌,如青銅器除去銅銹后實則表面為金色,因而也不難理解古代為何有稱青銅器為“吉金”一說;修復后“太新”,缺少文物原本應有的滄桑感和歲月的沉淀感,沒有了歷史的凝重和肅穆,同時抹去了“污跡”、劃痕本身承載的歷史信息。所以掌握保護和修復的尺度很有必要。不同價值、不同類型側重的文物不應進行統一的規劃,應當有不同的保護和修復方法。
1.1 文物價值的不同側重
《“修舊如原”與“修舊如現”——從傳統書畫修復實踐與現代書畫修復理念兩方面看修復原則問題》一文中,作者提道:“為了達到保護的目的,有些信息必須破壞。現代的一種觀點把修復分為考古修復、展覽修復和商品修復,后面對應的分別是文物的科學價值、藝術價值和商業價值。”[1]作者以修復奚岡《山水》為例,認為:如果不進行全補,這幅山水畫的科學性、藝術性降低到微乎其微了,進而也不具有商業價值;補全后的《山水》還可作為展觀把玩的一件藝術品,這是無法忽視的藝術品修復中存在的個人占有的需求性與商業性。因而文物的修復需要能體現文物本身的意義,如修復秦始皇陵封土西側出土銅車馬的碎片,可更好地了解銅車馬的制作技術以及秦代的工藝水平,這樣的技術了解也為修復其他文物提供經驗和借鑒,同時有助于世人對秦始皇陵陪葬規模的認識。帶有宗教意義(如潼南大佛寺的佛像),或者擁有地域文化特色或特殊價值意義的文物,更應當將恢復其本身的作用價值放在其作為面向社會的文物這一角色之前,在追求作品合乎其對應使用人群需求的基礎之上,達成對公眾需求的呼應。這也是對文物保護的基本目標中真實性原則的反映,修復不僅是盡最大可能的保護,更是在于恢復文物在原對應人群心中的狀態。一味地追求新或者復古都是“一刀切”的標準,是片面的。
1.2 文物的不同類型
陶器、石器、玉器、漆器等質地的文物中,對于形制較小且具有代表性、研究意義、欣賞價值的器物,可以對器物表面進行較為精細的處理,以便更清楚地了解器物在紋飾、裝飾、制作工藝等方面的信息;而對于以大型青銅器為代表的形制較大的器物,則不應過度清理器表,以幫助隨時通過器物表面的化學或者物理分析得到更多與器物出土背景相關的信息,同時為文物保留因歷史而帶來的神秘感。當然,面對文物的保護與修復與否并不能采用過于絕對的劃分標準,仍然需要具體問題具體分析,依實際情況做出合理判斷和科學規劃。
1.3 文物的破損程度
當埋藏環境對有較高價值的文物造成的破壞性損傷如變形、破碎等,影響人們對文物的欣賞和價值認定時,應當采取措施進行修復。例如,殷墟博物館內放置有一件變形的甗,有觀展者對這件器物形態的討論和疑惑。而像銅銹、文物失色等現象,并不會在本質上影響文物的研究和美學價值時,不應當采取“用力過猛”的修復手段,因為這些痕跡體現的是文物“經歷”,是歷史的印記。同時應當明白,修復的過程也會帶來文物信息的損失,如古人在使用這件器物時留下的痕跡,這些痕跡都是考古研究中對過去社會面貌進行了解的依據和參考,這樣的運用尤其體現在對石器時代石器的微痕分析以及陶器、青銅器等的殘留物分析上。
2 對文物保護與修復的思考
2.1 文物保護與修復的不同理念
文物的保護與修復不僅是為了當代,也是為了后世人們能夠有機會在未來以他們的視角看待同一件文物。所以當前的保護與修復需要在極大程度上減少對后世人們的價值判斷的影響,要求保護和修復活動對文物本身的欣賞和研究產生盡量小的影響,這也就提出了“最小干預的度”這個概念,即最小干預的度是在不會對所修復的文物造成二次損傷的前提下,把文物修復盡量完整和完美[2]。
近年來,文物修復工作者在文物的修復理念和技術上也在不斷學習西方先進之處。而關于文物的修復痕跡是否要體現的問題上,西方的觀念較為傾向于修復后不做任何修飾[3],明顯表現出器物的原貌以及修復的狀況。是否體現修復或修飾痕跡應當取決于人們希望通過展出該文物而達成的目的。以后母戊鼎為例,其耳的修復是基于對完整方鼎欣賞的需要而進行的,雖然后母戊鼎有兩個耳,但是二者在細節上仍有差別;故宮博物院中紡織品的展覽,也是為了讓世人更直觀地了解明清時期皇家的生活起居,對于展出的紡織品,文物修復工作者都會定期進行修補、養護,這里的修補則追求的是與文物本身的協調一致。
關于文物的展覽方面,首先不能因為文物修復和保護的難度和成本而因噎廢食,放棄文物的展出,而在博物館內過多采用復制品代替實物,或者用復制品代替關鍵的、有較高價值的但允許進行展出的文物;也不能因為對文物的過度保護而矯枉過正,通過減少對文物的使用而減小對文物的傷害。其次,文物帶給觀展者的感受與其復制品完全不同,這樣情感上的區別源于文物帶給人們的莊重與威嚴感,還源于文物可以使人產生對歷史無法替代的直接參與感,文物給觀展者帶來的體驗是觀展者對歷史的見證。此外,還存在一種修復方式,即展現文物本身較為嚴重的殘缺,僅對細部進行修復,也就是體現文物的殘缺美。典型的例子有盧浮宮鎮館三寶之一的《勝利女神像》、吳哥窟中的“斷壁殘垣”,亦有乾陵的翼馬、羅丹的《巴爾扎克像》等。當修復從審美上無法滿足人們的需要時,保留殘缺的方法則給人們留下了無限的想象空間。
2.2 文物修復技術的不斷進步
文物,首先是對人意識形態、觀念的體現,是意識活動的載體。修復可以視作一次與前人交流的機會,在修復中思考曾經的工匠運用什么樣的技術、想要通過作品表達什么思想內涵。修復具有主觀性,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盡可能地減少修復者的主觀認識對修復過程的支配。當然,對于損毀嚴重、在修復上實在無跡可尋的文物,可以不對文物進行修補、拼接等工作,僅對現有部分進行保護處理,同時可利用計算機輔助設計(CAD)以及快速成型技術(Rapid Prototyping)[4]對文物進行計算機上的模擬修復,針對不同意見可以形成多個修復版本提供參考,同時還可以在允許的情況下或在文物展覽過程中向社會集思廣益。這樣結合計算機的修復早有先例,如1992年西安黑河引水工程工地出土的吳虎鼎,該鼎有一腿斷裂,口沿破裂且整體有變形。由于該鼎銘文很多(斷裂部分也有銘文),且是西周紀年與王年推算的支點之一,因而修復意義較大,采用的方法便是三維計算機輔助建模(CAD),通過有限元進行力學分析,模擬修復過程[5]。而對于向公眾展示多種修復結果也并非偶爾,如1939年在薩頓胡第一墓地出土的頭盔碎片,是目前發現的盎格魯—薩克遜的英格蘭早期僅有的四頂頭盔之一,可能屬于東盎格利亞王國的某位國王,具有較大研究價值。因出土時對頭盔各部分碎片的具體出土位置并沒有做詳細的記錄,所以在頭盔修復中缺少碎片位置的參考,多年的修復中,修復人員對碎片位置給出多個版本的擺放,這些版本在頭盔進行展覽時一同展出供觀展者參考。
3 結語
近百年來文物修復與保護發展的歷程,研究者們一直在文物修復與保護每一個過程上尋求衡量標準,而每一次在理論和技術上的探索,都是在向文物意義最大化的靠攏。文物在本質上是與價值觀相結合的產物,是與一定價值觀相結合的實物遺存。要尊重前人為文物賦予的思想內涵,尊重文物承載的精神意義,也需要通過文物反映當前人們希望向公眾傳達的訊息。畢竟,文物作為博物館的藏品內容之一,同時體現的是博物館作為面向公眾的教育機構所具有的社會價值。■
參考文獻
[1]范勝利.“修舊如原”與“修舊如現”——從傳統書畫修復實踐與現代書畫修復理念兩方面看修復原則問題[D].北京:中央美術學院,2008.
[2]李靜生.文物修復理念探討與實踐應用.中國文物科學研究[J].2012(3):34.
[3]李靜生.文物修復理念探討與實踐應用.中國文物科學研究[J].2012(3):33.
[4]李滌塵,邱志惠,寧軍濤,等.文物計算機輔助修復方法探討.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J].2005(3):12.
[5]李滌塵,邱志惠,寧軍濤,等.文物計算機輔助修復方法探討.文物保護與考古科學[J].2005(3):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