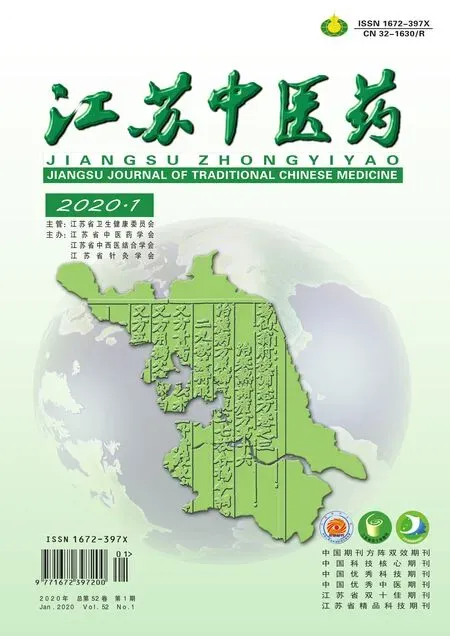繆正來治療難治性皮膚病驗案2則
吳艷秋
(南通市良春中醫藥臨床研究所門診部,江蘇南通226001)
指導:繆正來
難治性皮膚病臨床治療極為棘手,共同特點是皮損嚴重,反復發作,纏綿難愈。繆正來主任醫師,《江蘇中醫藥》編輯部原編審,年逾八旬,行醫60余載,中醫理論基礎扎實,臨床經驗豐富,善治皮膚病之重癥,現擇驗案2則如下,以饗同道。
1 聚合性痤瘡
聚合性痤瘡屬中醫“面皰”范疇,是痤瘡中的一種嚴重類型,具有損容性,可能與免疫相關。此病病情頑固,常遷延多年,愈后往往留有明顯瘢痕。繆老針對面部皮膚病患者“陽熱證”的特質,結合數十年的臨證經驗,自擬“上清方”加減治療。“上清方”由生山梔、川黃連、地膚子、白鮮皮、生熟大黃組成,全方具有清熱解毒、祛濕消疹的功效。
施某某,男,20歲。2018年8月24日初診。
主訴:滿臉痤瘡,膿皰、結節、囊腫反復發作3~4月。患者有痤瘡史4年,近3~4月病情加重,現以滿臉膿皰、結節、囊腫為主,且部分膿皰、囊腫有融合,高凸明顯,顳頰側為甚,有觸痛,易破皮,輕度瘙癢,皮膚泛紅,粗糙不堪,下頜有條狀疤痕疙瘩,質地偏硬。近2周口服異維A酸膠丸,外敷膠原貼,乏效。納可,便干,舌苔黃膩,舌質暗紅邊襯紫,脈弦小數。中醫診斷:面皰。西醫診斷:聚合性痤瘡。辨證:毒熱瘀結,流注肌膚。治宜:清熱解毒,涼血祛瘀。處方:
地膚子30 g,白鮮皮20 g,生山梔10 g,川黃連4 g,生石膏180 g(先煎),知母20 g,寒水石40 g(先煎),生薏苡仁40 g,炙僵蠶30 g,炙烏梢蛇20 g,蟬蛻15 g,生赤芍30 g,蒲公英30 g,菝葜40 g,生大黃6 g(后下),熟大黃6 g,生甘草6 g。14劑。每日1劑,水煎,分早晚溫服。另囑飲食生活宜忌。
二診(9月8日):藥后顳頰側膿皰疹逐漸平退,膚紅較前轉暗,無皮膚瘙癢,結節、囊腫無變化,納可,大便2~3次/日,舌質暗紅,膩苔漸化,脈弦。續予上方加海金沙30 g(包)、皂角刺30 g、玄參20 g。14劑,每日1劑,煎服方法同前。
服藥3月后,額部疹退斑消,皮膚光滑,顳頰側無膿皰,結節、囊腫顯軟化變平,無皮膚瘙癢、疼痛,唯大片瘀斑殘留,下頜條狀疤痕疙瘩質地漸軟,納可,大便2~3次/日,舌質暗襯紫,苔薄膩,脈小弦。續予原方去生石膏、知母、寒水石、炙烏梢蛇、蟬蛻、菝葜,加生水蛭8 g、紫花地丁30 g。14劑,每日1劑,煎服法同前。
2019年1月26日診:無痤瘡新發,瘀斑明顯淡化,膚質軟化,皮膚基本光滑,下頜條狀疤痕疙瘩較前軟化有縮小。改予痤瘡平及化瘀膠囊繼續鞏固療效,并囑飲食可試行開放。治療期間每2月復查1次血常規及肝腎功能,均無異常。
按:本案患者屬典型的聚合性痤瘡,繆老以“上清方”為基礎方,結合聚合性痤瘡特有的“毒、熱、瘀”三者互結的臨床表現,合大劑白虎湯再參入蟲類搜剔祛瘀之品隨證化裁。繆老認為大劑白虎湯與涼血解毒藥并用,可以氣血兩清,對改善皮膚病癥狀,消除皮疹,抑制增生,消腫止癢,均有良效。炙僵蠶、炙烏梢蛇、蟬蛻、生水蛭四種蟲類藥,是繆老治療皮膚紅腫、瘙癢的有效藥組。前三味藥,歷代本草記載為治療風瘡癮疹癬疥的要藥,而水蛭則為治療各種瘀滯的良藥,尤適用于熱瘀交阻型。四味藥共奏息風活絡、捜剔邪毒之效。據現代研究,蟲類藥具有獨特的生物活性,含有蛋白多肽,能改善和提高機體的免疫功能,促進皮膚黏膜修復。故本案患者在經過將近半年的治療后能達到滿意的療效,且安全無毒副作用。
2 慢性蕁麻疹
慢性蕁麻疹屬于難治性皮膚病之一,發病時不適感明顯,長期反復往往影響患者心理及生活質量。此種重癥患者,臨床治療頗為棘手。繆老針對全身性皮膚病患者“陽熱證”的特質,自擬“消疹止癢方”加減治療。消疹止癢方由地膚子、白鮮皮、丹皮、生山梔、炙僵蠶、烏梢蛇、蟬蛻、蛇蛻、土牛膝、生大黃等藥物組成,全方具有清熱涼血解毒、息風消疹止癢之效。
李某,女,56歲。2018年10月12日初診。
主訴:全身不固定瘙癢伴起紅色風團疹反復7~8年。自覺發作與冷熱、情緒等均無關,每日發作頻繁,甚時此起彼伏,入夜尤甚,以大塊或片狀紅色風團為主,局部腫熱明顯,觸之質硬,瘙癢劇烈,影響睡眠,皮膚劃痕(+),風團消退緩慢,不服藥有時2~3日亦無法完全消退,服藥1~2日緩慢消退,發時無胸悶、氣喘、腹痛等不適。既往治療以西藥為主,曾口服過1~2年強的松,多則每日6粒,少則每日1粒,近2年以抗過敏治療為主,各類抗組胺藥混合交替使用,近2周因癥狀嚴重,自行加量,目前非索非那定2粒、鹽酸左西替利嗪片1粒、鹽酸奧洛他定2粒,均1日2次,仍每日局部有紅疹塊或風團發作。皮膚烘熱,瘙癢明顯,半日以上才能消退,曾查過敏源述無異常。納可,大便質干2~3日一行,口干,舌紅襯紫,苔薄黃膩有裂紋,脈弦。檢查:白細胞(WBC)8.5×109/L,中性粒細胞(N)76.8%,血沉(ESR)26 mm/h,谷丙轉氨酶(ALT)112 U/L,谷草轉氨酶(AST)78 U/L,谷氨酰轉肽酶(GGT)85 U/L,空腹血糖(GLU)5.6 mmol/L。中醫診斷:癮疹;西醫診斷:慢性蕁麻疹。辨證:毒熱瘀互結,泛溢肌膚。治宜:清熱解毒,涼血祛瘀,消疹止癢,保肝降酶。處方:
地膚子30 g,白鮮皮30 g,丹皮15 g,生山梔10 g,炙僵蠶20 g,烏梢蛇15 g,蟬蛻12 g,蛇蛻10 g,土牛膝30 g,生石膏180 g(先煎),知母20 g,寒水石40 g(先煎),生薏苡仁40 g,生水蛭10 g,蒲公英30 g,生赤芍30 g,茵陳15 g,田基黃30 g,金錢草30 g,生大黃8 g(后下),生甘草6 g。7劑。每日1劑,水煎,分早中晚溫服。
抗組胺藥逐漸減量,暫時服用:鹽酸左西替利嗪片1片,1日2次;鹽酸奧洛他定1粒,1日2次。另囑飲食生活宜忌。
二診(10月19日):服藥1周,蕁麻疹發作未有加重,以每日局部起數枚紅疹塊或圓形紅色風團為主,瘙癢略減,皮膚烘熱感如前,消退需半日以上,納可,大便日解1~2次,成形,口干減輕,舌暗紅襯紫,苔薄膩中裂紋,脈小弦。續予原法,上方加蘆薈3g,7劑。抗組胺藥減為鹽酸左西替利嗪片早1粒,鹽酸奧洛他定早晚各1粒。
三診、四診蕁麻疹發作呈緩慢減輕趨勢,方藥同前,抗組胺藥繼續以每周減1粒的速度遞減。
五診(11月10日):服藥4周后癥情大為減輕,復查血常規、血沉、肝腎功能均正常,因而繼續遞減抗組胺藥,每晚只服鹽酸奧洛他定1粒。每2~3日腰腹臀部有紅疹塊或圓形紅色風團發作,約4~5枚,伴癢,皮膚烘熱感顯減,消退需2~3 h,但不影響睡眠。納可,大便2~3次/日,不成形,舌暗紅,苔薄白,脈小弦。原方去保肝降酶藥,10劑,減量繼續治療,1劑服1日半,每12小時1服,煎法同前。另鹽酸奧洛他定每周減1/4粒。
六診(2019年2月15日):服藥4月,停服抗組胺藥已有月余,中藥1劑服2日已有20日,1周中有2~3日覺局部膚癢,偶有個別紅斑或紅點發作,半小時內消退,無烘熱感,不影響生活。續予消疹止癢方3劑鞏固治療。
按:繆老根據慢性蕁麻疹病勢纏綿、頑固難愈的特點,結合其多年臨床實踐經驗,總結慢性蕁麻疹的發生與風、濕、熱、瘀有關,而自身免疫功能的低下與紊亂是其發病的重要因素。根據臨床辨證,本病為毒、熱、瘀互結,治宜解毒、涼血、祛瘀并重,且著重自身免疫功能的調節,遂用僵蠶、烏梢蛇、蟬蛻、蛇蛻諸味蟲類藥。研究證實,蟲類藥能改善和提高機體免疫功能,而西藥因為作用單一,往往顧此失彼,難以達到綜合調節的作用,所以療效不佳。而中醫在這方面優勢明顯,利用中藥多靶點、多層面的治療作用,祛除致病因素,達到氣血暢通、陰陽平和,此時外因不能通過內因起作用,疾病就能緩解乃至痊愈。繆老在本案患者的治療中予自擬“消疹止癢方”再合大劑白虎湯及參入活血祛瘀通絡之品,從而達到標本兼治、治病求本的目的。
3 結語
繆老認為皮膚病患者多為陽熱體質,以紅、腫、熱、癢等炎癥表現居多,常為“陽熱證”。無論何種病邪客于腠理,若蘊積不散,則郁久化熱,聚而成毒,阻塞經絡,脈道不利,終致毒、熱、瘀三者互結,肌膚氣血運行不暢,從而形成難治性皮膚病。毒、熱、瘀三者在皮膚病發病演變過程中,互相作用,互為因果。基于上述毒、熱、瘀結病機,根據“久病入絡”的理論以及古人多云“頑疾多屬瘀”的說法,繆老針對難治性皮膚病提出了解毒涼血祛瘀之治療原則,根據發作部位的不同,結合數十年的臨證經驗,自擬方劑,隨機化裁,已形成較成熟且獨特的皮膚病診治思路。繆老喜用生石膏、知母、寒水石、生大黃清熱瀉火;地膚子、白鮮皮、赤芍、山梔清熱涼血解毒;丹皮、生水蛭涼血祛瘀;僵蠶、烏梢蛇、蟬蛻、蛇蛻止癢解毒。治療時從毒、從熱、從瘀論治,且解毒涼血祛瘀并重,使絡脈通暢,藥力隨血暢達病所,并迅速改善癥狀。此外,繆老非常重視飲食忌口,如酒、海鮮、辛辣刺激、牛、羊、雞肉等均在禁忌之列,只有等癥狀緩解后才可試行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