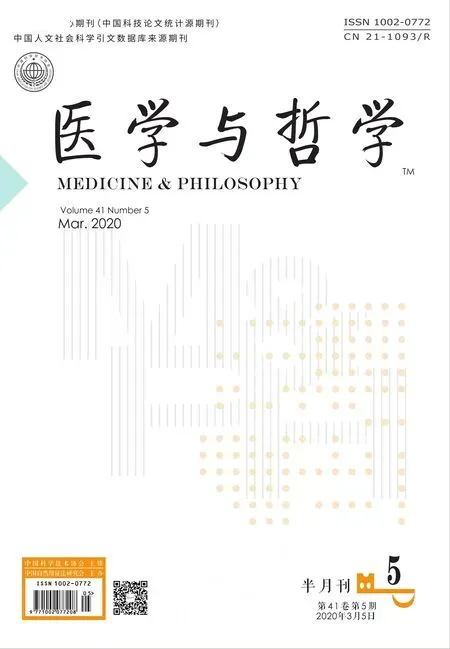讓器物說話
——器物醫學史:一種新的編史學視角
王一方 耿 銘
1 聚焦器物:編史視角的轉換及其理論注腳
一部醫學史,無論是學術史,還是思想史,除了刺眼的“強光帶”之外,還存在著忽明忽暗的“弱光帶”,聚焦器物的醫學技術史(器物醫學史、技術史)就處在這一光譜之中。背后是“耀眼”的精英敘事與“昏暗”的民間敘事之間的落差。因為器物的醫學史常常被視為一種非理論化的歷史研究現象(有人指責碎片化,有人指責隨機化),需要從編史學上給予闡釋,才能賦予這個范式以理論支撐。歷史學家的對象物大多聚焦于文獻與文物(遠古器物),其背后存在著器物(級)與文物(級)之別,蘊含著一種歷史年輪與價值權重的落差,以及厚古薄今的價值選擇。毫無疑問,在正統醫學史研究譜系中,首重文獻(典籍、著作)、觀念、人物,日常醫療、健康器物常常被遺忘,或者歸于民俗研究,除非是歷史久遠的出土文物器具,近現代散落在民間的器物也太過平常,太過雜蕪,它們不過是一些日常健保用品,就是些醫療技術物料,但它卻隱藏著近現代醫學技術演進的密鑰,是觀念的醫學史、人物的醫學史、事件的醫學史之外的別樣風景,也是現代醫學察勢觀風的別樣窗口[1],也就是說,倡導近現代器物為中心的醫學史研究,可望成為主流醫學史的必要補充。
一般來說,歷史學家有三個基本任務,發現與甄別史實,重新書寫,尋找歷史事件之間的邏輯聯系。當然,史學還有更為閎闊的心愿與功用,在于捕捉一個時代的“風標”,那么,在技術史的層面,最易感知風向、風勢、風力或許是器物、圖像。譬如中國古代對馬鐙(器物)的發明與推廣使得騎手在馬上身體的穩定性提升,帶來騎射征戰能力質的提升,繼而影響世界軍事史,由此改寫了歷史的走向與格局。1958年,中國考古學家在湖南長沙南郊金盆嶺一座西晉永寧二年(302年)古墓中發掘出了一組青釉騎士俑(器物),其中一件騎士所騎的馬身左側鞍橋之下,塑出一個由革帶吊系的小馬鐙,鐙呈三角形,外貌簡陋,革帶也很短[2]。1961年,楊泓[3]撰文指出,該騎俑馬鐙,應該是中國乃至全世界現知最早的馬鐙實例。據此,有美國學者稱:“如果沒有從中國引進馬鐙,使騎手能安然地坐在馬上……歐洲就不會有騎士時代。”[4]同樣,列文·虎克處理凸透鏡的技能決定了人類對微觀世界和宇觀世界的觀察、探測潛力,開啟了細胞生物學與微生物學及天文學(星空探測)的新領域。背后是歷史學的理性與物性之辨,因為“歷史不能簡化為抽象的、預言性的描述(原理與法則,范式或模式),而舍棄掉所記錄生活的特征細節……以及所有在特定時間、特定空間存在著的有意義的碎片”[5]7。
無疑,器物醫學史帶來了歷史敘事的變軌:基本路徑是走出觀念史,走向田野,沉入世俗。回歸人-物的二元性,過去歷史敘事常常重視人,而忽視器與物,立體的人物鏡像應該是人與器物的交集、互相映襯。在歷史的記憶深處,物比人長久,人因物而立,人去器物還獨立存在的局面比比皆是,器物雖然不說話,但承載、凝集著人的歷史遺存、風貌與風范。
在研究視野上,醫療、健康器物的解讀呈現出醫學史(明確的專業指向性)與文化史(泛化的/生活化的醫學情境、語境)的交映,無疑,器物史的研究通往文化史的幽谷,吉爾伯特特別指出文化史研究具有四大特征,一是政治光譜(標識),二是跨學科眼光(雜合性),三是建構主義導向,四是歷史境遇的分析意識(情境+語境)[5]478。器物史的拓展必然循著這四個階梯推進醫學科學史與技術史的交融,開啟學術史與思想史的對話,抵達醫學文化史(文化史視域中的醫學)的新邊疆。
方法學拓展上,器物的加入融會了考據(文字)與考證(器物)的境遇,實現文獻學方法與人類學(民族志)方法的交映,有助于時代性格的白描與深描[6]。法國歷史學家雅克·勒高夫指出“記憶是歷史的原材料”[5]493,相對于觀念史來說,具體的器物承載著更樸實的生命故事與生活記憶,在記憶與歷史之間,可望辟出一個創造性的解讀空間(非宏大敘事,非輝格預設)。如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所言:所有的個人記憶都定位于社會情境中,而那些社會情境構造了它們被喚醒的道路……并最終被鐫刻為“社會定式”(social stereotypes)[5]495。而那些被器物“喚醒的道路”,被鐫刻的“社會定式”亦可以被理解為那個時代的健康與醫療的時尚風標。
2 器物醫學史:近代新史學理念的啟迪
1897年,梁啟超首次撰文主張建設以民史為中心的“新史學”,但如何表現“民”的歷史,沒有具體的路徑,人們不知從何下手。王國維[7]在《古史新證》總論中提出“二重證據論”:“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古文獻+文物、器物)……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在這里,王國維所言地下之新材料,包括古(甲骨文、碑銘、簡牘)文字、古器物(陶器、銅器)。但基本上是考古,歷史久遠,留存有限。近現代器物的留存就十分豐富了。1928年前后,顧頡剛為新創立的《中大語史所周刊》(1927年11月始刊)和《民俗周刊》(1928年3月始刊)寫了兩篇《發刊詞》。在顧頡剛看來,要在轉型時期的中國學界開辟學術新路,須對自己所處的時代、學術方向和范圍、材料的狀況和最新治學方法等問題有清醒的認識。針對這些問題,他提出建設新學問須打破學問的功利性,以求真為目標;須打破偶像的權威,以彰顯理性。在此基礎上,他呼吁“承受了現代研究學問的最適當的方法”,“實地搜羅材料,到民眾中尋方言,到古文化的遺址中去發掘,到各種的人間社會去采風俗,建設許多的新學問,要打破以圣賢為中心的歷史,建設全民眾的歷史!”[8]這是顧頡剛到民間去求新史學的重要表述。其要旨是“眼光向下”,走出書齋,拓寬了搜集材料的路徑與范圍。認為“在故紙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沒有什么高下的分別”,主張通過田野調查或者考古,廣泛搜集社會各個角落非文字的材料,諸如民間傳說、歌謠、謎語、諺語、神話、童話、故事,以及被傳統學術研究棄之不顧的檔案、賬本、契約、民俗物品等材料,來拓展研究的范圍。其所謂“眼光向下”,一是單純地依靠從故紙堆中尋找材料的純文獻研究方法已遠遠不能適應新時代學術發展的需求,他們重新估定文獻的價值,開始走出書齋,眼光向下,實地搜羅材料,各種民間文獻、實物、語言、圖像和口述資料進入了史料的搜索范圍。二是告別舊史學的“君史”,“要站在民眾的立場上來認識民眾!探檢各種民眾的生活,民眾的欲求,來認識整個的社會!”[9]
中國近代的巨變,在器物、圖像、技術層面上是最直接、最劇烈的。器物層面的變革,始終貫穿在近代中國醫學史的脈絡之中。雖然大多數技術精英不曾用文字記錄器物的演進歷程,但在他們的從業過程中,仍然會被動地留下一些文字、影像資料。器物醫學史的信念與目標也在于發掘民間敘事的醫學史,從民俗生活來認識醫學與健康。
歷史書寫,并不是隨心所欲地編造,而是立足于證據,主要是物證來復述(再現)某一個歷史事實與場景,刻畫某一個歷史的內核。所謂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然而,證據在哪里?不能只盯著藏有古籍的圖書館,藏有文物的博物館,還要將視點移至民間收藏和民俗生活。新興的人類歷史學將人類學理念和田野調查的方法引入歷史研究領域,賦予器物醫學史全新的權重。那就是歷史邊緣的中心化取向,給予民俗事件、民間收藏的器物以創造性的解釋空間。毫無疑問,器物醫學史作為民間記憶的醫學史,人與物交映互鑒的醫學史,每一件器物背后都有年代感,都有相關人士的情感寄寓。
器物醫學史,關注點有器有物,器側重于醫療活動,物側重于百姓保健活動,器具側重于傳統醫療(如煉丹的器皿、陶器),器械側重于近現代醫療(早期的光學儀器,后來的光電一體化、電磁儀器),器物醫學史的目光主題涵蓋健康(保健)器物、醫療文書(病歷)、醫療器械、醫學科學儀器、醫學教育文書、醫學博物館展品等多個相關領域。器物醫學史就是在歷史中做田野考證,通過醫療保健器物的發現和發掘還原歷史的脈搏、溫度與細節。器物發展的歷史進程中還蘊含著基礎科學研究的大力支撐,體現了二戰以后軍事技術大量轉移到民用領域的歷史軌跡,以及科學與技術的循環加速機制,譬如CT、磁共振成像技術的背后涉及多項物理學的最新發明,其中,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NMR)發明贏得四次諾貝爾獎。1924年,泡利提出假說,原子核中的質子或中子在某種情況下會以角動量運動,即所謂自旋,因此變得具有磁性,他由此獲得1945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937年,前蘇聯物理學家證明液氮中具有磁性。同年,拉比計算出磁動量,獲1944年諾貝爾物理學獎。1946年,潘塞爾與布羅奇分別宣布發現核磁共振方法,用于測量原子核磁場,獲得1952年諾貝爾物理學獎。NMR最先用于化學分析:微量標本測試技術不斷擴大使用對象,后來發展到建構多維人體圖像。2003年,勞特布(發現磁場梯度可以產生二維圖像)與曼斯菲爾德(建立了磁場梯度的信號分析與圖像轉換方法)因這些磁共振成像技術領域里的突破性成果獲得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10]。
3 器物醫學史:研究譜系的展開
當下,器物醫學史的拓展不必追隨文獻醫學史的腳步與節奏,而是要聚焦于歷史潮汐的潮頭與轉折點,尤其是西學東漸的巨大歷史變革。無疑,器物醫學史是近代醫學西學東漸的物證譜系。
其一,光學器物的橫空出世是一個轉折點,400年前,荷蘭人列文·虎克的透鏡加工術帶來顯微鏡、照相術的發明,打開了探索、記錄生命微觀世界的窗口。明末清初,大量西方光學器物通過各種渠道傳入中國,專家分析,歐洲光學器物東傳的幾種不同途徑,如貿易、朝貢和傳教士等。外來的取景暗箱、透視畫、變形鏡、多面透鏡、魔燈等在我國民間都有流傳。照相術的發明與攝影器具的傳入,使得醫學、保健主題的圖像進入醫學史的視野,派生出圖像醫學史的研究分支。
西方光學器物不僅在明清時期的社會生活中扮演了十分有趣的不同文化角色,明清詩歌曾對西來光學器物的文化史進行解讀,清初詩人、戲曲作家孔尚任在《節序同風錄》中,就記載“九月初九:登高山城樓臺……持千里鏡以視遠”。西方舶來光學器物的在地化與工藝史值得深入發掘。明末光學儀器制造家孫云球有一定的西學基礎,著有專著《鏡史》一部,制造各類光學儀器達七十余種。清代著名科學家鄭復光在《鏡鏡冷癡》一書中對各種銅鏡的制造、透光鏡的透光原理等進行了詳細論述,認為應該從最基本的物理原理開始,“此無大用,取備一理”,萬花筒“其制至易,而其理至精”[11]。
清末民初,光學儀器開始明顯地用于醫療目的,觀測生命與疾病指征,始于病原學、病理學探究的設備,如顯微鏡,隨后是1895年倫琴X射線的發現與X光機的發明。在當時,它是現代醫院里第一款大型醫療器具,而且需要與電力設備配套使用,據《點石齋畫報》記載,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美國教會創辦的蘇州博習醫院就引入一寶鏡,“可以照人臟腑……其鏡長尺許,形式長圓,一經鑒照,無論何人心肺腎腸,昭然若揭”,科學技術史界不認可這件寶物就是X光機,一是時間太近,倫琴1895年才發現X光現象,當時不可能在第二年就有普及化的機具生產與出口;二是形態功能也不準確,最初的X光機還無法檢查所有內臟器官,真正可以采信的引進X光機的新聞是1918年浙江寧波慈溪保黎醫院的X光機,據謝振生先生考證,該設備由美國GE公司進口,慎昌洋行代辦,機器、運費、關稅總價4 368.968元(銀元),由于當時慈溪尚不具備電力供應,醫院自建發電機房,延宕到次年才投入使用[12]。隨后的X光器械的發展軌跡不僅有物理當量、檢測功率的不斷加大,設計理念的升級換代(計算機技術的導入),制作工藝的不斷精細,還有醫生防護水平的不斷提升,從無防護到低防護,再到高防護,體現了醫護自我保護意識的增強和廠商設計理念的進步。
第二是外科器具,是近現代形成譜系的醫學器物,歷史上,中醫的外科發展前盛后衰,《周禮·天官志》中就有“瘍醫”之分,歷朝歷代連綿不斷的征戰都需要外科療治,三國時期的華佗就曾經嘗試過外科手術療法,據考古發現,中國最早的手術刀是青銅“砭鐮”,該器物做工精細,形制像一把縮小的“戚”或平頭的“戈”。刃口鋒利,明顯有打磨過的痕跡,三指捏拿,操作方便,如同刀片一般,可精細削割人體器官[13]。但宋以后外科陷于停頓,演變成為以藥物為主的外治之術,西學東漸之后,才脫胎換骨成為以手術為特色的臨床科室,外科醫療器具日漸豐富,隨著精細機械加工、制作工藝的提升,各種手術刀、剪、鉗、夾、皿應運而生,消殺、麻醉、輸血技術的發展也誕生了許多專門器具;現代牙科的興起,更帶動了成套口腔檢查治療器具的繁盛。其背后是醫療器械工業化雛形的凸顯,包括專業醫療器具的臨床動因、研發團隊、模型制作工坊、生產加工的設備、精度、質量控制、臨床測試、定型,以及銷售促進、進出口業務、廣告文書的大量涌現。
此外,第三類是隨著化學藥品逐漸取代原生態的植物、動物藥品,而催生的近代工業化的實驗研發、提純技術、藥業加工、臨床試用、審核準入、市場化的銷售和包裝、藥店陳列、媒體推廣(廣告)而派生的一系列器物。
第四類是近代檢驗、檢測技術與護理技術的萌生而派生的采血、化驗、體溫、血壓檢測、注射給藥、吸痰、給氧、導尿、止血、包扎等癥狀處理的系列器物。
第五類是近代戰爭境遇中急救、轉運、手術、輸血、護理,及臨時救護所組建過程中的器物。如白求恩大夫在冀中根據地發明并設計制作的被稱為“盧溝橋”(加載在馬背上)簡易戰地外科器具箱,以及簡易外傷消毒、固定裝置[14]。
第六類因近代醫療器物是由現代醫學教育的興起,帶來教科書、參考書出版的繁榮,以及考試、考核、培訓、認證卷宗、文憑、文件、教具、掛圖的豐富。
第七類近代器具是伴隨著診所到醫院的轉型,醫療流程的變革,不僅醫療器具越來越系列化,也帶來醫療、財務文書的標準化,醫療過程記錄從無到有,從略到詳,由自由體病案向契約特征的掛號及收費單據、標準化病歷與病志、手術記錄、護理記錄、療養記錄的轉身,其次是醫療賬目由傳統流水轉向復式記賬的現代簿記,以收支平衡、資產負債、現金流量等表單為標志的現代財務制度顯現雛形。
不同于經典與文獻導向的醫學史研究,器物醫學史是某一(類)實物為基礎的研究,必須遵循以下原則和路徑。立足于新近發現的器物,或司空見慣卻寓意不彰的器物,透過實物的細節說話,注重時代性、年代感獨特標志的發掘,以及社會文化心理投射,但200年的近現代化進程腳步實在太快,我們只顧一路高歌猛進,缺乏駐足回味、系統收藏、梳理更新換代器物的集體意識和管理機制,譬如最早一批顯微鏡、X光機被新型機具替換時,沒有被保存下來,而是作為廢物而遺棄或扔進冶煉爐,大型的機具器物尚且如此,小型器物更加離散無蹤,難以成套歸聚,一些重要的器物全憑民間收藏的有限渠道加以回收,珍藏,20世紀六十七年代政治運動對民間收藏的摧殘,更加速了近代歷史遺存的消弭,僅憑分散、隨機聚集的器物如何還原一幅大的近代歷史圖景,仍然是一個懸題。首先必須充分發掘民間收藏的潛力,將家庭隱形收藏品變成半公開的可供學界研究的展品,征集、組織主題、年代特色的醫學技術器物展覽是一個好形式,每一個展覽留下一個藏品目錄,為研究者提供一扇可征集的研究窗口。還可將目光投向公共博物館,從其館藏中發掘醫學器物,豐富學術研究譜系。研究發凡部分著眼于近現代醫療模式(形式、內容)大關節(低倍顯微鏡到高倍顯微鏡,再到電子顯微鏡,從手動X光機到自動X光機,再到CT,增強CT)的變軌、變奏,創新與回歸。
在器物的研究方法上,要高度重視比較研究,開啟古今、中外醫療器物的比較,如日德與歐美、同款器物比較,還有同一國別、同一時期不同地域、不同流派(如中醫與蒙醫、藏醫、苗醫)器物等多元比較譜系,揭示醫學器物發生、發展、傳播演變的歷史層次,破除器物的零星碎片化帶來的困惑和不確定。在器物研究成果的敘事方式上,提倡風格多樣、文體多元、媒體多融,可以是單一器物微小體征、意義的深度發掘,也可以是某一類器物的系統研究、比較研究,還可以是器物的多媒態呈現。
器物醫學史的研究既要動員醫史專家、收藏大師或系統、或分類進行有深度的研究,形成專著或專題文集,也要組織和發動醫生、藥業、醫療器械從業者,醫學生參與征集、研究與寫作,形成各個層級互補的研究格局。最終達到激活全社會、全行業的歷史遺產(舊器物)意識,以器物醫學史的征集、研究推動醫學教育史,院校、醫院等機構史,醫藥行業史、藥業、器械業企業史的升級換代,形成器物醫學史研究和展示的群體、群像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