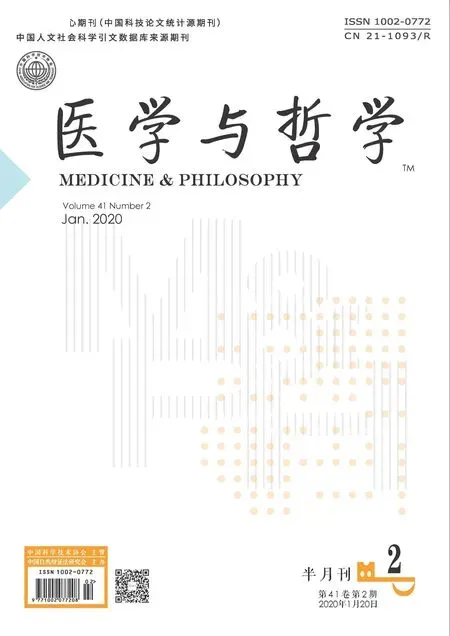歐美生命倫理委員會的機構建設與咨詢服務*
張肖陽 肖 巍
在當今國際世界,生命倫理學已從20世紀60年代問世的新學科發(fā)展成一種國際性的“社會運動”,成為學術界和公眾關注的熱點領域。在歐美社會,生命倫理學不僅作為學科蓬勃發(fā)展,而且在生命倫理委員會機制建設和社會咨詢服務等實踐方面也取得許多成果,這些成果以體制和文化背景為保障有力地推動了生命倫理學的理論發(fā)展和臨床應用。本文將從機構建設、咨詢服務和哲學思維嵌入三個方面探討歐美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建設的經驗,以期為中國生命倫理學學科發(fā)展及生命倫理委員會建設提供有益的參考。
1 機構建設
2005年,聯(lián)合國教科文組織(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出臺了《建設生命倫理委員會指南》,把各種類型的與醫(yī)學、生物學和健康保健相關的倫理委員會統(tǒng)稱為“生命倫理委員會”,較為恰當?shù)匕ú煌瑖液偷貐^(qū)的相關實踐。這一文獻首先強調各國建設“生命倫理委員會”的必要性和緊迫性。隨著生命和健康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和生物技術的不斷創(chuàng)新,個人和社會都愈發(fā)地難以作出與生命相關的道德抉擇,必須以正規(guī)的組織形式來解決與日常健康及政策相關的倫理問題。“生命倫理委員會是一個有組織地、連續(xù)性地強調:(1)健康科學;(2)生命科學;(3)創(chuàng)新性健康政策的倫理維度的委員會。一個典型的生命倫理委員會應當由一定范圍的專家組成,它通常是多學科性的,其成員以不同視角探討解決生命倫理學問題和難題,尤其是道德困境的方案。而且,這些委員會的成員不僅要對倫理困境保持敏感,而且要及時把握更有效的應對這些困境所需要的知識和技能。”生命倫理委員會“強調的不僅是事實,也是深遠的規(guī)范性問題,其決定不僅關乎與某一案例相關的利益紛爭,也超出經驗證據(jù)的事實層面,不僅要求回答‘我應當如何決定和行為’的問題,也要求回答‘我們應當如何決定和行為’的問題,這將把我們從作為哲學傳統(tǒng)分支的倫理學引入到政治學,回答‘政府應當如何行為’的問題”[1]。
目前歐美各國的生命倫理學機構主要包括:(1)臨床倫理委員會(Clinical Ethics Committees,CECs)。它的宗旨在于為本機構的健康保健實踐提供倫理服務,為尋求咨詢的個人(患者、家庭和在這一機構任職的健康保健人士)提供價值觀方面的幫助。在歐美國家,這一委員會具有不同的名稱,例如機構倫理委員會、醫(yī)院倫理委員會以及生命倫理委員會等。(2)醫(yī)療保健倫理委員會(Health Care Ethics Committees,HECs)。它的含義更為廣泛,可以為特定健康保健制度中的所有機構提供倫理服務。與臨床生命倫理委員會相同,其宗旨也在于為患者、家庭、代理人、健康保健人士,或者其他相關人員分析和解決價值觀方面的不確定性和沖突,為之提供咨詢服務。(3)研究倫理委員會(Research Ethics Committees,RECs)。(4)機構倫理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s,IRBs)。與(1)、(2)不同,(3)、(4)的主要任務是對于所提出的關于臨床藥物或者治療研究,研究機構所進行的包括人體受試者的研究等進行倫理審查。
美國生命倫理委員會發(fā)展的歷史可以追溯到20世紀60年代,當時美國開始普遍使用腎臟透析機,但透析機資源遠遠不能滿足腎臟衰竭患者的需求,所以醫(yī)院便成立委員會配置透析機資源,例如1962年,西雅圖建立了“透析委員會”(Dialysis-Committee)。然而,由于其成員多半是白人中產階級男性,所作出的決定總是偏袒自身階層,便引發(fā)全國性的強烈抗議。1973年,政府開始為使用透析機付費,這些透析委員會便終止了功能。然而,這一事件卻引發(fā)了公眾關注“醫(yī)院倫理委員會”問題。事實上,在20世紀60年代,美國便舉行了首個強調臨床實踐技術發(fā)展復雜性的倫理學論壇(Ethics Forums),70年代又建立“流產委員會”(Abortion Committee),80年代美國最高法院受理的幾宗案件導致“健康保健倫理委員會”的建立。有統(tǒng)計數(shù)據(jù)表明,1981年,美國大約有1%的醫(yī)院成立了醫(yī)院倫理委員會。1983年,美國“總統(tǒng)委員會關于醫(yī)學、生物醫(yī)學和行為研究中的倫理問題研究報告”(President’s Commission for the Study of Ethical Problems in Medicine and Biomedical and Behavioural Research)對于“醫(yī)療保健倫理委員會”的職能作出政治陳述。此后“醫(yī)療保健倫理委員會”和“臨床倫理委員會”在美國各個醫(yī)院得到迅速發(fā)展。1984年,“美國醫(yī)院聯(lián)合會”(American Hospital Association)也強調在機構層面探討生命醫(yī)學倫理問題的意義。1998年,“美國生命倫理和人文學會”(American Society for Bioethics and Humanities,ASBH)成立[2]。
相比之下,生命倫理委員會在歐洲社會起步較晚,20世紀80年代才出現(xiàn),而且在不同國家發(fā)展過程和模式各不相同。有的國家采取行政命令方式促進“醫(yī)療倫理委員會”建設,例如2000年挪威議會便要求所有醫(yī)院都應當成立HECs,并要求在5年后基本達成這一目標。根據(jù)德國衛(wèi)生機構2006年的估算,在德國每2 000家醫(yī)院里,只有200家成立了“醫(yī)療保健倫理委員會”。在歐洲其他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也陸續(xù)得以建立,例如意大利帕多瓦大學專門成立了“兒科倫理委員會”等[3]。1997年4月4日,“歐洲理事會”(Council of Europe)在西班牙的奧維耶多市締結了《人權與生物醫(yī)學公約》,這成為歐洲國家在生物醫(yī)學發(fā)展中所奉行的尊重人權原則的綱領性文獻。盡管這一公約分別對臨床醫(yī)學和研究倫理學實踐作出詳細規(guī)定,但卻未提出建立“生命倫理委員會”的要求。
在歐美生命倫理委員會機構建設過程中,也不斷地遇到各種問題和挑戰(zhàn),引發(fā)許多學者思考這一機構的能力和限度問題,發(fā)表了一系列相關論文,例如美國道德神學家理查德·A.麥考密克(Richard A.McCormick)等[4]的“倫理委員會:承諾還是危險?”,R.韋爾(Robert Weir)[5]的“兒科倫理委員會:倫理咨詢者還是法律的看門狗?”,J. 弗利特伍德(Janet Fleetwood)等[6]的 “給出答案還是提出問題:機構倫理委員會有爭議的角色”,D.卡拉漢(Daniel Callahan)[7]的“倫理委員會及社會問題:潛能和陷阱”,D.布萊克(David Blake)[8]的“醫(yī)院倫理委員會:醫(yī)療保健機構的良心還是白象?”。這些爭論主要緣于第一代醫(yī)院生命倫理委員會的局限性,它們最初僅是一個維護個體患者權利和解決棘手案例的咨詢機構。然而,如今這種模式已不足以滿足歐美國家在醫(yī)療保健方面日益增長的復雜性要求。這些爭論也導致一些學者對生命倫理委員會存在的意義提出質疑。有人認為,在官僚機構盛行的背景下,生命倫理委員會似乎成為一種管理機構,而且在醫(yī)學決定過程中,這種機構可能使問題更為復雜。如果把問題都公開出來,專家意見可能不再起作用,同時它的倫理規(guī)范也只是偶爾地產生作用[9]。甚至一些美國醫(yī)生開始抵制生命倫理委員會,認為這種機構干預了醫(yī)患關系,不僅沒有存在的意義,反而具有破壞性和煽動性。盡管如此,美國社會在20世紀六七十年代民權運動的推動下,生命倫理委員會得到迅速的發(fā)展,因為這場運動不僅對政府機構、同時也對社會機構(如醫(yī)院和學校),以及人際關系(如教師與學生的關系和醫(yī)患關系)提出挑戰(zhàn)。美國黑人、婦女、同性戀者、囚犯、學生和消費者、病人都參加進來,目的在于追求個體自主性以及個人作為社會成員所擁有的“生命、自由和幸福權”,例如住房、受教育和工作權,以及掌握自己健康與生命信息的權利和決定權。一些患者和家庭也開始要求拒絕使用維持生命系統(tǒng)的“死亡權利”[10]93-94,在這種背景下,生命倫理委員會便更多地承擔起協(xié)調醫(yī)患沖突,規(guī)范醫(yī)生行為和減少法律訴訟的任務。
21世紀以來,歐美學者也在不斷探索生命倫理委員會的新模式,例如N.溫格(N.Wenger) 認為這種新模式必須具備四個特點:(1)它應當是前瞻性的,而不是消極地等待醫(yī)院把各種困境呈現(xiàn)出來;(2)它在組織上是緊密結合的;(3)需要通過結果,而非良好動機來衡量其功能;(4)它應當受機構價值觀的支配,而不僅僅由患者的合法權利來引導[9]。目前歐美各國生命倫理委員會也都在不斷地調整自己的功能和手段,以期適應生命倫理學本身發(fā)展和實踐產生的新要求。
2 咨詢服務
臨床倫理咨詢是生命倫理委員會的一種重要服務方式。在“美國生命倫理和人文學會”的一份報告中,臨床倫理咨詢被定義為“一種由個人或群體提供的服務,幫助患者、家庭、代理人、醫(yī)療保健提供者,或其他相關方分析在醫(yī)療保健中出現(xiàn)的與價值相關的不確定性或沖突。”這主要集中在兩個倫理領域:(1)針對特有患者案例的臨床倫理學;(2)針對健康保健組織與企業(yè)實踐的組織倫理學[10] 91。在一些歐美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都具有這一臨床倫理咨詢功能。然而,學術界對這一功能也有不同的看法。贊成者認為,臨床倫理咨詢是一種輕便靈活的結構,能夠隨時啟動,尤其是在緊急情況下,其功能直接與醫(yī)療決定相關,這就要求對咨詢員進行倫理學等學科的培訓。反對者則認為,如果鼓勵醫(yī)生成為倫理咨詢專家,他們便可能不再培養(yǎng)自身的倫理意識,不必自己作出倫理選擇,這勢必導致醫(yī)生行為和醫(yī)療實踐與倫理的分離,同時也會削弱醫(yī)生作出醫(yī)療決定的權力。還有人認為,倫理選擇關乎人們對于人生意義的追求和期望,它應當屬于私人性的,不需要倫理專家來指導[3]。
盡管存在上述爭論,但歐美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所做的臨床倫理咨詢工作仍有許多地方值得借鑒:其一,在解決每一種沖突時,咨詢人員要基于一種道德判斷來確定自身的角色,并在咨詢過程中向各方呈現(xiàn)這種角色。咨詢倫理要求解釋案例,與相關者進行交流,預測解決這一問題會產生什么樣的實質影響。然而咨詢者并不是道德真理或者法律的化身,也不需要扮演哲學家和牧師的角色,而只是一個倫理促進者和服務者。他們首先應當明確在道德上可/不可接受的行為界限,負責提醒和幫助人們意識到這些界限。還應保護每個人的權利,使之能夠在社會生活中得到實現(xiàn)。而且,他們不能僅僅是患者權利的代言人,把臨床生命倫理委員會變成患者的維權機構,而是需要在決策過程中充分考慮到生命倫理學基本原則、權利語言方面的沖突,及時向各方呈現(xiàn)這些沖突,并提出解決沖突的建議,而非代表某一方爭取權利。其二,案例研究是臨床倫理咨詢的基本方法。針對具體情境,臨床倫理咨詢者應當意識到自己是案例的作者、行為者和評論者,應當從不同案例中總結出解決問題的方法。意識到有時提供一種解決問題的思路要勝于給出一個“正確的”答案。采用案例方法需要完成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把現(xiàn)成的案例應用于具體的道德困境,解決所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二是根據(jù)臨床實踐自己編輯案例以備日后使用。其三,目前歐美國家的臨床倫理咨詢主要采取三種模式:倫理委員會咨詢、個體咨詢和小組咨詢。這三種模式各有利弊:(1)倫理委員會咨詢模式。倫理委員會傳統(tǒng)上包括在醫(yī)療保健部門工作的各種職業(yè)代表,如醫(yī)生、護士、社會工作者、醫(yī)院的律師、牧師,通常還有一名至兩名行業(yè)外的公眾代表。它的功能類似于一個管理機構,僅僅通過一次例會,聽取臨床主治醫(yī)生說明情況和數(shù)據(jù),經過討論,給出建議。盡管這種形式會讓患者本人或者家屬參與意見,但卻無法讓他們充分表達看法。此外,它的決定大都根據(jù)二手或三手資料,其成員也有一種從眾心理,以便形成大家共同承擔責任的局面。(2)個體咨詢模式。這一模式讓咨詢者感覺到友好氛圍,在緊急情況下可以馬上與相關患者和家屬直接對話。在美國的一些醫(yī)院里,個體咨詢要求成倍地增長。然而這種模式的弊端在于咨詢專家很容易把自己的觀點強加于人,并有可能造成一種幻覺,即一個人,而不是一個機構能夠既有知識,又負責任地作出最佳的倫理決定。(3)小組咨詢模式。這種模式能迅速作出反應,收集數(shù)據(jù),并能清楚地作出決定,因而在許多學者看來,這或許是臨床生命倫理委員會的最佳咨詢模式[3]。
3 嵌入哲學思維模式
在歐美國家,生命倫理學家一直自覺地借鑒和應用當代哲學理論資源來建構生命倫理學理論,實現(xiàn)思維方式的轉變,而這種轉變也會對生命倫理學實踐直接產生重要影響。20世紀后半葉以來,歐美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建設主要嵌入三種哲學思維模式——身體現(xiàn)象學模式、“對話倫理”模式和“問題”模式。
3.1 身體現(xiàn)象學模式
當代哲學現(xiàn)象學發(fā)展重塑了生命倫理學家的角色,例如美國學者德魯·萊德(Drew Leder)試圖通過現(xiàn)象學闡釋人們對于健康與疾病的身體體驗,以及醫(yī)學干預對于人體的改變。他對基于笛卡爾“身心二元論”形成的現(xiàn)代醫(yī)學科學主義提出批評,倡導一種整體主義理論。在《缺席的身體》一書中,萊德闡明了自己的“身體現(xiàn)象學”理論,認為西方文明一直貶低身體,使之總處于缺席和隱蔽狀態(tài)之中,例如身體在表達某種功能時本身就是缺席的——在看的眼睛不會看到自己在看,睡眠狀態(tài)中的身體也無法體驗到自己在睡眠。這種身體存在樣態(tài)和功能方式導致它本身的自我遮蔽,而人們卻尚未意識到身體的這種缺席及其影響,反而由于這種忽視貶低身體的存在。萊德著重研究身體現(xiàn)象而不是關于它的理論,試圖探討身體的來源,以及身體如何成為人們自我意識的組成部分,它如何進行表達,以及人們如何通過身體體驗到健康與疾病、痛苦與疼痛等等。可以說,以萊德等人為代表的“身體現(xiàn)象學”理論對于歐美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建設帶來三點重要啟示:其一,這一理論強調身體不是單純的工具,而是一種自我表達和存在方式,以及一個人的身份。疾病不僅改變了人的軀體,也改變人的存在方式和身份。因此,人類社會一直以來圍繞著健康與疾病以及身體所建構的哲學認識論和社會政治意識形態(tài)都應當重新審視身體的意義和價值。相應地,生命倫理委員會在提供臨床咨詢服務時必須意識到身體的整體性,重視患者的身體體驗以及圍繞身體、疾病和健康所建構的社會文化和體制等方面產生的影響。其二,這一理論看到傳統(tǒng)生命倫理學教科書總是把生命倫理困境描述成“贊成者”與“反對者”之間的戰(zhàn)爭,而“身體現(xiàn)象學”則始于公開的對話,相信每個人在這一建設性對話過程中都能不斷地超越、推翻或者修正自己的看法[11]。其三,這一理論呼喚一種“謙虛”(humility)美德。這一美德亦可被稱為“敘事性謙虛”(narrative humility),它要求生命倫理委員會的專家和醫(yī)生認真傾聽患者的敘事,在任何時候都不應打斷患者說:“你不用再說了,我已經知道故事的結局。”因為即便他們已經知道疾病故事的始末,也不可能把握這位患者完整的自我。從這個意義上說,敘事性謙虛便涉及“如何對待我們不知道的他者之面容——我們無法知道這幅面容——但我們有責任作出反應。”這也需要醫(yī)生具有一種想象力,進入到并非屬于自身的痛苦中去想象患者的痛苦體驗,并依據(jù)這種想象進行診治,把握生命事件中尚未發(fā)現(xiàn)的意義[12]。
3.2 “對話倫理”模式
當代德國著名哲學家尤爾根·哈貝馬斯的“對話倫理”理論也為歐美國家生命倫理委員會建設引入新的哲學思維方式。哈貝馬斯認為,對話倫理的惟一途徑就是在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中實現(xiàn)符合交往理性“話語意志”的平等與自由:不論話語活動參與者的社會政治經濟地位如何,每一個人都應擁有平等的發(fā)言權,不允許有任何來自權力和暴力的威脅。對話原則相信“每一準則的有效性都在于它是一個如果所有相關方參與到實踐對話中來,都能夠同意的準則。”[13]哈貝馬斯的這種對話倫理也在倡導一種“審慎”(deliberation)美德,他借用當代政治哲學家喬舒亞·科恩(Joshua Cohen)的觀點闡釋這種美德,強調它具有三個主要特點:它以爭論形式出現(xiàn),通過信息交流對所提出的方案進行批評審查;它是包容的和開放的,讓受到這一決定影響的所有人都平等地參與進來;它是自由的,沒有任何外在的強制力。參與者依據(jù)準則和交流實現(xiàn)自己的權利,它對于任何參與者來說都不具有使其偏離平等軌道的內在強制力。每一方都有權利平等地傾聽、提出問題和作出貢獻[14]。西班牙醫(yī)學史教授、生命倫理學家迭戈·加西亞(Diego Gracia)也要求把這種“審慎”應用到生命倫理委員會的日常實踐中,認為審慎既是一種方法,也是一個過程,它要求完成下列步驟:(1)由決策人提供案例;(2)針對臨床病例進行全方位討論;(3)識別出倫理問題;(4)為患者選擇出他/她所關心和希望分析的道德問題;(5)確定價值觀上的沖突;(6)提供行為路線圖;(7)分析最佳行為過程;(8)最終決策。“對話倫理”模式要求生命倫理委員會在決策時充分考慮各方觀點之間的交流和對話,讓所有參與案例討論者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和體驗;各方要相互理解和尊重; 作為解釋者,每一位參與討論者都應當清楚他人對事物理解上的偏差,反思那些制約對話的歷史、政治和形而上學結構。正如加西亞所言,每一個最終決策都要被置于三個范圍內進行檢驗:置于法律范圍內檢驗其是否合法?置于公眾關注范圍內檢驗“你是否準備為這一決策進行公開辯護?”置于時間范圍內檢驗“如果再多給你一些時間,你是否還會作出相同的決策?”[15]
3.3 “問題”模式
“問題”一詞來自希臘語problema,是從proballo演變而來,其含義是“向前拋”,意味著問題被擺在或拋到我們面前以求得到答案和解決。然而,“人類思維更傾向于‘非此即彼’的思考而不是同時處理兩個或者更多選擇的復雜思考,而且這通常是人們在無意中犯下的錯誤”。以往生命倫理委員會習慣于這種“非此即彼”思維模式,易于把問題推至極端,陷入一種道德困境,而沒有意識到完全可以通過改變思維方式找到更好的解決問題方案。加西亞建議生命倫理委員會應當以“問題”模式來代替“困境”模式提供生命倫理決策和服務,因為問題本身是開放的,并不要求從兩種或更多的可能性中作出選擇,而是要求創(chuàng)造或者生產出正確答案,只有這種思維模式才符合倫理學的“本性”,這首先因為道德推理不應當依據(jù)“科學”方式來理解,即相信可以獲得一種具有確定性的普遍知識,而應當以“觀念”的方式來理解,即使觀念本身是不確定的,但也不是非理性的。其次由于道德問題并不是數(shù)學演繹,而是與人們的觀念相關,不同的人對于現(xiàn)實的感知不同,因而會產生不同意見。人們需要作出一個不確定的、但合乎情理的道德決定,這就是以“問題”思維作出道德決定的根據(jù)[10]225-226。
4 結語
建設“生命倫理委員會”是中國生命倫理學發(fā)展及其實踐的重要舉措,它不僅具有理論意義,也可以減少和避免許多醫(yī)患關系及臨床醫(yī)療實踐沖突,而且長遠地看來,亦可以通過社會制度結構的一個重要方面——醫(yī)療保健領域來促進社會的民主建設,體現(xiàn)出對人的生命權和自主權的尊重,達到醫(yī)療保健資源的公平配置,實現(xiàn)社會公正與和諧的目標。歐美國家建設生命倫理委員會的經驗和哲學理論思維方式可以為我們帶來許多啟示。從機構建設來說,盡管中國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啟動“醫(yī)院倫理委員會”的建設過程,并于1988年成立中華醫(yī)學會醫(yī)學倫理學專業(yè)委員會。在90年代的綜合醫(yī)院等級評審工作中,衛(wèi)生部和各省陸續(xù)頒布《三級綜合醫(yī)院評審標準》,把醫(yī)療機構設立醫(yī)學倫理委員會列為一個評審條件,并由此促進了全國三級醫(yī)療機構醫(yī)學倫理委員會的建設和發(fā)展。然而在實際作用中,各地各醫(yī)院的生命倫理委員會的發(fā)展并不平衡,總體上尚處于摸索整合階段,相關理論研究也較為薄弱。此外,盡管中國的生命倫理委員會在臨床醫(yī)療實踐中發(fā)揮了一些作用,但功能較為集中在醫(yī)學倫理和研究倫理審查方面,缺乏歐美國家的咨詢服務,尤其是服務于個體患者的功能。而且,中國缺乏對于生命倫理委員會的作用、工作質量與效果的審查和監(jiān)督機制,致使這些機構更多地流于形式,難以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鑒于上述局面,中國生命倫理委員會在建設中應當關注四個重要問題:(1)基于文化基因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生命倫理委員會。生命倫理是一種特殊的意識形態(tài),體現(xiàn)出不同的社會、政治和文化背景,中國特色的生命倫理委員會建設需要服務于“健康中國”的國家戰(zhàn)略,找到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相適應的模式和途徑,例如在理論上需要汲取五千年優(yōu)秀傳統(tǒng)倫理文化,尤其是中醫(yī)藥文化;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在偉大斗爭中構建的革命文化;社會主義先進文化的基因,基于這些文化基因培養(yǎng)民眾的生命倫理意識,使其能夠自覺參與生命倫理選擇、決策與評價,共同建構中國特色的生命倫理文化和有中國特色的生命倫理委員會。(2)加強生命倫理學科體系、學術體系和話語體系建設。生命倫理學也是一門理論學科,生命倫理委員會的建設、作用與完善仰仗于生命倫理學的學科建設與發(fā)展。這里的學科體系主要指以知識結構和科學分工為基礎的學科設置,專業(yè)劃分和學術機構。當代中國生命倫理委員會建設要從根本上解決生命倫理學的學科體系設置問題,借以帶動生命倫理委員會有分有合地協(xié)調統(tǒng)一發(fā)展。學術體系主要指學科內部分析研究問題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體系、學術標準和評價體系。中國生命倫理學研究與生命倫理委員會建設既需要借鑒歐美國家的相關理論并進行雙向的文化汲取和改造,也需要發(fā)展自己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原則。話語體系主要指一個學科的標識性概念、新概念和表述方式,例如歐美生命倫理學中的核心概念有自主性、權利、尊嚴、公正等,這些概念主要基于歐美國家的倫理價值觀形成。相應地,中國生命倫理學發(fā)展和生命倫理委員會建設需要打造出自己的標識性概念、新范疇和表述方式,即便使用與歐美國家相同的術語,也需要賦予它們不同的文化內涵,以便使生命倫理委員會能在中國文化中落地生根,臨床生命倫理咨詢話語更符合中國文化語境,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并能以這些自身特色走上國際交流舞臺。(3)生命倫理委員有必要提供臨床倫理咨詢服務。培養(yǎng)臨床倫理咨詢人員的專業(yè)素質,以及建構問題、提出問題和解決問題的能力是中國生命倫理委員會建設的必要環(huán)節(jié)。生命倫理委員會的作用是否能夠發(fā)揮,以及是否能夠深入人心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臨床倫理咨詢服務的水平,因而臨床倫理咨詢工作者十分有必要接受哲學和倫理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的培訓。(4)生命倫理委員會專家要善于在生命倫理分析中培養(yǎng)和轉變哲學思維模式,與時俱進跟蹤和學習當代哲學和倫理學學科新發(fā)展。在這方面,歐美國家生命倫理學家善于把哲學新思維融入生命倫理學實踐的做法值得借鑒,例如對于身體、精神以及身心關系的現(xiàn)象學理解,對“敘事性謙虛”美德的強調,以及哲學思維方式從“非此即彼”到“創(chuàng)造性”生產答案的轉變等都可以為中國的相關實踐提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