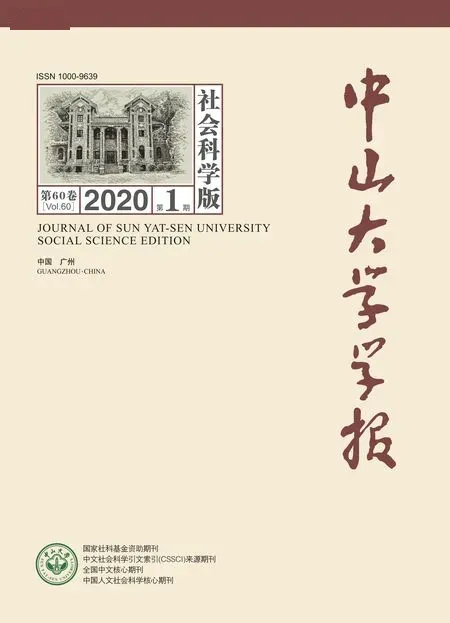行走的秦漢少年*
——教育史視角的考察
王 子 今
秦漢大一統政治文化格局的確定,促成了國家規模的擴張、交通網絡的健全和行旅條件的改善。秦漢時期取得突出進步的交通建設,使得行旅的空間和知識的幅面均得到空前擴展。未成年人也在多種社會文化因素的作用下,通過被動的或主動的行走實踐開創了獲得新鮮見識的學習路徑。他們的人生知識、社會知識、地理知識、自然知識均因交通行為而大為增益。考察秦漢時期的教育史,不能忽視行走的少年們“為學”的交通進程。以求學為目的的行旅生活,更直接與文化繼承相關。
司馬遷在《史記》卷130《太史公自序》中回顧他的學習生活:“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會稽,探禹穴,窺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于是遷仕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還報命。”(1)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3293頁。司馬遷“二十”出游,對于其學力的增長、學識的提煉、學業的成就意義非常重要。秦漢時期,還有許多在成年之前即以遠行實踐體會社會歷史的先例。“行走”,是秦漢少年修養道德、開闊視界、增益識見、提升學力的重要方式之一。相關考察,可以豐富我們對于秦漢時期未成年人生活的知識,深化對教育史的理解,擴展對于交通史研究意義的認識。
孫毓棠曾經指出:“交通的便利,行旅安全的保障,商運的暢通,和驛傳制度的方便,都使得漢代的人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見,他們的見聞比較廣闊,知識易于傳達。漢代的官吏士大夫階級的人多半走過很多的地方,對于‘天下’知道得較清楚,對于統一的信念也較深。這一點不僅影響到當時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夠加強了全國文化的統一性,這些都不能不歸功于漢代交通的發達了。”(2)孫毓棠:《漢代的交通》,《中國社會經濟史集刊》第7卷第2期。秦漢交通是文化統一的條件,也是教育進步的條件。對于社會來說,“交通的便利”使得“知識易于傳達”;對于民眾來說,亦“影響到當時人政治生活心理的健康,而且能夠加強了全國文化的統一性”,致使“人民得以免除固陋的地方之見,他們的見聞比較廣闊”。這些文化作用的實現,往往起始于人們的兒童時代。
一、“小子軍”行跡
明人董說《七國考》卷11分述秦、田齊、楚、趙、魏、韓、燕七國兵制。《秦兵制》題下有“小子軍”條,引“劉子《別錄》云”:“長平之役,國中男子年十五者盡行,號為‘小子軍’。”此雖說戰國史事,卻反映了秦征役制度的傳統。所謂“劉子《別錄》”,繆文遠訂補本作“劉向《別錄》”(3)董說原著,繆文遠訂補:《七國考訂補》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75頁。。張金光論述秦“傅籍與編役”制度引作:“劉向《別錄》說:‘長平之戰,國中十五者盡行,號為小子軍。’”(4)張金光:《秦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213頁。“長平之役”作“長平之戰”,又缺“男子年”三字,然不詳出處。
秦“長平之役”大規模調動兵員事,見《史記》卷73《白起王翦列傳》:“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為上將軍。而王龁為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詳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后,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為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筑壁堅守,以待救至。”秦昭襄王于是有異常舉動:“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王自之河內”句下,張守節《正義》:“時已屬秦,故發其兵。”“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句下,司馬貞《索隱》:“時已屬秦,故發其兵。”(5)司馬遷:《史記》,第2334—2335頁。河內,指今河南省黃河以北地方。有人釋“王自之河內”為“(秦王)親自到韓城、大荔一帶坐鎮”(張衛星:《秦戰爭述略》,西安:三秦出版社,2001年,第106頁),是地理方位理解的錯誤。
長平戰事隨即以秦軍大勝結局。“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為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復。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后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秦昭襄王親自到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對于戰局發展意義重大。然而對于“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七國考》卷11《秦兵制》引劉子《別錄》以為“國中男子年十五者盡行”,按照張守節《正義》和司馬貞《索隱》“時已屬秦,故發其兵”的解說,則以為限于不久前“屬秦”的“河內”地方。
楊寬、吳浩坤主編《戰國會要》卷118《兵六·征兵》“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句后有編者按:“云夢《秦簡》《大事記》載:喜,秦昭王四十五年生,秦始皇元年‘傅’,登記服役。由此可知秦男子服役年齡為十五周歲始,與此印證。”(6)楊寬、吳浩坤主編:《戰國會要》下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141頁。云夢睡虎地秦簡《編年記》的相關文字,據整理小組釋文:
……
今元年,喜傅。
《編年記》紀事自“昭王元年”即秦昭襄王元年(前306)起。整理小組有這樣的說明:“昭王,秦昭王。《韓非子》、《史記·六國年表》作昭王,與簡文同;《史記·秦本紀》作昭襄王。昭王元年為公元前306年。”關于“喜產”,整理小組注釋:“雞鳴時,丑時,見《尚書大傳》。喜,人名。產,誕生,下面‘敢產’、‘速產’等同例。”關于“喜傅”,整理小組注釋:“今,即古書中的今王、今上,指當時在位的帝王,此處指秦王政(始皇)。”“傅,傅籍,男子成年時的登記手續,《漢書·高帝紀》注:‘傅,著也。言著名籍,給公家徭役也。’據簡文,本年喜十七周歲。漢制傅籍在二十或二十三歲。”(7)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年,第5—6、8、11頁;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釋文第5—6、8—9頁。注意到秦制傅籍和“漢制傅籍”年齡不同。
結合睡虎地秦墓竹簡考察秦征役制度,許多學者意見不一。現在看來,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對于“喜”的年齡的計算是有問題的。秦昭王卌五年(前262)“十二月甲午雞鳴時,喜產”,“今元年”(前246)“喜傅”。“喜傅”時如果在“十二月甲午”當日或稍后,只有十六周歲。如果在“十二月甲午”之前,則只有十五周歲,而絕對不是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所說的“十七周歲”。
看來,楊寬等學者“由此可知秦男子服役年齡為十五周歲始,與此印證”的說法,還是有道理的。有了這種“印證”,則可知秦昭襄王親赴河內令“國中男子年十五者盡行”以“國中”為政策空間范圍的說法大體可信,而《史記》卷73《白起王翦列傳》張守節《正義》和司馬貞《索隱》“時已屬秦,故發其兵”說以為“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僅限于“河內”地方的意見,似未可從。
“年十五”,是男性未成年人年齡的高限。《史記》卷47《孔子世家》張守節《正義》:“男八月生齒,八歲毀齒,二八十六陽道通,八八六十四陽道絕。女七月生齒,七歲毀齒,二七十四陰道通,七七四十九陰道絕。”(8)③ 司馬遷:《史記》,第1906,2827頁。以生理條件成熟標志考慮,所謂“二八十六陽道通”,指示了“年十五”的標界性意義。
秦軍中存在少年士兵的情形,可以通過文物資料得以證實。未成年人參與軍事生活情形,在漢代也可以看到相關跡象。《史記》卷59《五宗世家》:“江都易王非,以孝景前二年用皇子為汝南王。吳楚反時,非年十五,有材力,上書愿擊吳。景帝賜非將軍印,擊吳。”劉非15歲從軍,應當不是特例。敵對一方吳楚叛軍中,有吳王劉濞軍事動員以14歲為參戰年齡下限的例證。《史記》卷106《吳王濞列傳》寫道:“七國之發也,吳王悉其士卒,下令國中曰:‘寡人年六十二,身自將。少子年十四,亦為士卒先。諸年上與寡人比,下與少子等者,皆發。’發二十余萬人。”③《漢書》卷48《賈誼傳》記載,賈誼上疏陳政事,說到邊防問題:“今西邊北邊之郡,雖有長爵不輕得復,五尺以上不輕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臥,將吏被介冑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醫能治之,而上不使,可為流涕者此也。”所謂“五尺以上不輕得息”,顏師古注:“如淳曰:‘五尺謂小兒也。言無大小皆當自為戰備。’”(9)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2240頁。按照這樣的理解,則“西邊北邊之郡”在匈奴強大軍事壓力下,雖“小兒”亦參與“戰備”。
白起長平殺降,“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可知趙軍中也有“小者”。上古兵法《孫子兵法·地形》:“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溪;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10)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編:《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附《武經七書》本《孫子》,北京:文物出版社,1976年,第122頁。《孫臏兵法·將德》:“赤子,愛之若狡童。”(11)鄧澤宗:《孫臏兵法注譯》,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第95頁。“嬰兒”“赤子”比喻的使用,或許有軍事生活的現實基礎。
秦始皇陵兵馬俑坑及漢景帝陽陵外藏坑出土少年士兵俑,體現了秦至漢初軍事編制中有未成年軍人存在的事實。未成年人經歷或準備經歷軍事生活,在中國社會史的這一階段,是比較確定的。在戰爭條件下,“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12)司馬遷:《史記》卷7《項羽本紀》,第328頁。,“弱”包括弱小的未成年人。“轉漕”軍需與行軍征戰,都是要經歷遠程交通的。
少年士兵離開鄉土,在與農耕社會完全不同的軍事生活環境中,進入團隊,交識戰友,接受指令,既要學習軍事戰爭技能,也要體會集體主義精神。就文化教育而言,軍隊中也有比較好的條件。《吳子·治兵》:“武侯問曰:‘兵何以為勝?’起對曰:‘以治為勝。’”(13)李碩之、王式金:《吳子淺說》,北京: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第79頁。這里所說的“治”,包括軍法、軍令等各種規范,也都是要通過軍中教育強調其嚴肅性的。
二、“流離系虜”命運
許多未成年人行走實踐的直接因由是被動的。《史記》卷49《外戚世家》記錄了竇皇后弟竇少君的特殊經歷。姐弟離別時的場景與相見時的言辭,通過司馬遷真切的細節描述,足可動人心弦:“竇皇后兄竇長君,弟曰竇廣國,字少君。少君年四五歲時,家貧,為人所略賣,其家不知其處。傳十余家,至宜陽,為其主入山作炭,暮臥岸下百余人,岸崩,盡壓殺臥者(14)《太平御覽》卷871引《史記》:“岸崩,百余人皆壓死。”李昉等:《太平御覽》,北京:中華書局據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1960年2月復制重印版,第3860頁。,少君獨得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為侯,從其家之長安。聞竇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小,識其縣名及姓,又常與其姊采桑墮,用為符信,上書自陳。竇皇后言之于文帝,召見,問之,具言其故,果是。又復問他何以為驗?對曰:‘姊去我西時,與我決于傳舍中,丐沐沐我,請食飯我,乃去。’于是竇后持之而泣,泣涕交橫下。侍御左右皆伏地泣,助皇后悲哀。乃厚賜田宅金錢,封公昆弟,家于長安。”(15)⑤ 司馬遷:《史記》,第1973,3051頁。竇少君“年四五歲時”,“為人所略賣”,“傳十余家”,從事的是“入山作炭”勞作,曾經經歷生死劫難。這種兒童被“略賣”,轉手“十余家”,慘遭奴役的情形,在社會秩序不穩定的時期,可能并不罕見。竇少君從“觀津”至“宜陽”,是經歷了長途交通實踐的。王莽曾經指出西漢末年社會壓迫的殘酷:“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蘭(16)顏師古注:“‘蘭’謂遮蘭之,若牛馬蘭圈也。”,制于民臣,顓斷其命。奸虐之人因緣為利,至略賣人妻子,逆天心,誖人倫,繆于‘天地之性人為貴’之義。”(17)班固:《漢書》卷99中《王莽傳中》,第4110頁。也說明這種社會現象長期普遍存在。
《史記》卷117《司馬相如列傳》載錄司馬相如所著文難蜀父老,則可見“幼孤為奴,系累號泣”的說法⑤。《漢書》卷57下《司馬相如傳下》又寫作“幼孤為奴虜,系絫號泣”。顏師古注:“為人所獲而絫系之,故號泣也。”(18)⑩ 班固:《漢書》,第2586,1068頁。所謂“系累”“系絫”,是以繩索捆綁牽系強制行進的交通形式。“幼孤”的年齡身份指向,是明朗的。《后漢書》卷13《隗囂傳》所謂“幼孤婦女,流離系虜”(19)⑧⑨ 范曄:《后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第517,802,2531頁。,也說到未成年人被迫受到奴役的情形,而所謂“流離”,也指出其“系虜”身份,是通過空間距離的移動而形成的。《后漢書》卷23《竇融傳》載竇融與隗囂書:“而將軍復重于難,是使積痾不得遂瘳,幼孤將復流離,其為悲痛,尤足愍傷,言之可為酸鼻。”⑧也說到“幼孤”“流離”。《后漢書》卷78《宦者傳·呂強》:“室家徙放,老幼流離。”⑨其中所謂“幼流離”字樣也是醒目的。《漢書》卷22《禮樂志》“辟流離,抑不詳”,顏師古注:“流離不得其所者,為開道路,使之安集。”⑩所謂“流離”與“不祥”相關,與“安集”反義的語序組合關系是比較明確的(20)班固:《漢書》卷36《劉向傳》(第1956頁):“因之以饑饉,物故流離以十萬數。”顏師古注“物故,謂死也。流離,謂亡其居處也。”范曄:《后漢書》卷6《質帝紀》(第278頁)“死亡流離”與“物故流離”義近。。史籍記錄中所謂“流離中野”(21)班固:《漢書》卷45《蒯通傳》,第2161頁。、“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于道路”(22)班固:《漢書》卷64下《賈捐之傳》,第2833頁。、“百姓饑饉,父子分散,流離道路”(23)班固:《漢書》卷81《孔光傳》,第3358頁。、“百姓饑饉,流離道路”(24)班固:《漢書》卷83《薛宣傳》,第3393頁。、“百姓困乏,流離道路”(25)班固:《漢書》卷99下《王莽傳下》,第4175頁。、“黎民流離,困于道路”(26)范曄:《后漢書》卷4《和帝紀》,第186頁。、“流離分散,隨道死亡”(27)范曄:《后漢書》卷87《西羌傳》,第2888頁。、“牽掣虜手,流離異域”(28)陳壽:《三國志》卷4《魏書·三少帝紀·高貴鄉公髦》,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第133頁。、“流離迸走,幾至滅亡”(29)陳壽:《三國志》卷7《魏書·張邈傳》裴松之注引《英雄記》,第223頁。、“星散流離,死者甚眾”(30)陳壽:《三國志》卷44《蜀書·姜維傳》,第1064頁。,又“流離遠外”(31)陳壽:《三國志》卷11《魏書·王修傳》裴松之注引王隱《晉書》,第349頁。、“萬里流離”(32)陳壽:《三國志》卷47《吳書·吳主傳》,第1140頁。,也都說明“流離”經行“道路”,往往至于“遠外”,甚至“萬里”以至于“異域”。而“父子分散”,“子”的悲慘境遇,可想而知。
通過底層社會生活以“流離”為形式的艱辛經歷,“幼孤”們承受了人生苦難,見識了社會災變,同時也形成了文化閱歷。受難者通過“困于道路”,“星散”“萬里”,“迸走”“遠外”的經歷,接受了嚴酷的社會教育。前說竇少君故事有“上書自陳”情節,不能排除在“年四五歲時”“為人所略賣”之后習得文字知識的可能(33)參看王子今:《漢代社會的識字率》,《學習時報》2007年9月17日。。
三、未成年人的行進式勞作與交通服務實踐
《史記》卷104《田叔列傳》褚少孫補述說到西漢名臣任安事跡,涉及其少年時代生活于底層社會辛苦勞作的情節:“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司馬貞《索隱》:“將車猶御車也。”(34)司馬遷:《史記》,第2779頁。翦伯贊曾經指出:“這里所謂‘為人將車’就是受人之雇為人趕車。”(35)翦伯贊:《兩漢時期的雇傭勞動》,《北京大學學報》1959年第1期。“將車”雖然技術要求較高,然而也是辛苦的勞作形式。這種勞作的突出特點應是承擔轉輸任務,實現較遙遠空間距離的物資移動。任安“滎陽人”,“為人將車之長安”,現今河南滎陽至陜西西安公路營運線路里程536公里(36)《全國公路營運線路里程示意圖》(第二版),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5年,第四分冊第12頁;第六分冊第2、12頁。,以漢里折合為325米計(37)陳夢家根據對居延地區漢代郵程的考證,以為“以325米折合的漢里,比較合適”,“用400或414米折合則太大”。見氏著《漢簡考述》,《考古學報》1963年第l期;《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第32頁。,相當于1 649里。《九章算術·均輸》:“重車日行五十里。”(38)郭書春匯校:《九章算術》,沈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20、325頁。任安“將車之長安”大致行程多達33天。
漢代畫像資料中可以看到未成年人“為人趕車”的情形。江蘇邳州陸井墓出土漢畫像石,表現主人博戲情景,右側置一解套的牛車,而牛在左側,一未成年人手牽掛系牛鼻的韁繩。有研究者解釋為“屋外左側刻一兒童坐在杌子上逗牛”(39)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湯池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4·江蘇、安徽、浙江漢畫像石》,濟南:山東美術出版社,2000年,第105頁,圖一四三,圖版說明第48頁。。這位兒童,應是來客所乘牛車的御者。山西離石馬茂莊出土墓室門側畫像可見如下畫面:“一人牽牛車行進,牛昂首前行,車為輜車,四人在旁隨之而行。”(40)中國畫像石全集編輯委員會編,湯池主編:《中國畫像石全集5·陜西、山西漢畫像石》,第208頁,圖二八二,圖版說明第77頁。牽牛者身高不及牛背,與隨行“四人”比較,亦小大懸殊,可知應是兒童。山東鄒城郭里鎮羊山村漢畫像石也可見未成年人“將車”畫面。陜西綏德劉家灣出土漢畫像石所見三輛車的“將車”者,都是未成年人。
居延漢簡多見有關“將車”的簡文。例如“里上造史賜年廿五長七尺二寸黑色為蘭少卿將車”(14.12),“將車觻得萬歲里”(77.7),“將車觻得安世里公乘工未央年卅長七尺二寸黑色”(334.13),“將車觻得新都里郝毋傷年卅六歲長七尺二寸黑色”(334.36),“將車河南郡熒陽”(346.39)等(41)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年,第22、136、523、524、539頁。。《候粟君所責寇恩事》簡冊也可見有關寇恩“將車”的文字:“恩從觻得自食為業將車到居延。”(E.P.F22:18)“恩又從觻得自食為業將車莝斬來到居延。”(42)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北京: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476—477頁。(E.P.F22:27)這些“將車”者都是成年人。然而我們又看到如下簡例:
居延亭長平明里不更張廣年廿三長七尺五寸黑色軺車一乘用

以“從者”身份出現的“徐□年十二”,很可能是服務于“居延亭長”“張廣”的“將車”者。所御車輛為“軺車一乘”。
“將車”是行進式勞作。未成年“將車”者如任安“為人將車之長安”,因有一定見識,“之長安,留,求事為小吏”,隨即又選擇至武功,“代人為求盜亭父,后為亭長”。以“有智略”,“后除為三老,舉為親民,出為三百石長”。隨后漢武帝“使任安護北軍”,“立名天下”,“其后用任安為益州刺史”(44)司馬遷:《史記》卷104《田叔列傳》褚少孫補述,第2779—2781頁。。任安交通實踐對于其“智略”之形成,不會完全無關。
《太平御覽》卷403引《任嘏別傳》說:“(任嘏)幼以至性稱,遇見荒亂,家貧賣魚,會官發魚,魚貴數倍,嘏取直如常。”因為官府控制市場,魚價騰升,任嘏依然按照原價銷售。從事商販營生的未成年人也要付出艱辛的勞動。“販”“賣”經營及一些服務型勞作的工作強度可能較許多田間耕作形式為輕,或許比較適合未成年人的體力條件。
據《三國志》卷32《蜀書·先主傳》的明確記載,少年劉備有參與類似勞作的經歷:“先主少孤,與母販履織席為業。”(45)陳壽:《三國志》,第871頁。劉備未成年時的勞動,包括民間日常服用的手工制作和販賣經營。《太平御覽》卷709引《蜀志》則曰:“先主少孤,每販履織席為業。”(46)文淵閣《四庫全書》本。“每販履織席為業”,中華書局用上海涵芬樓影印宋本復制重印本(第3159頁)則作“母販履織席為業”。明確說劉備自己“販履織席為業”,并非只是輔助其母。《太平御覽》卷697引《蜀志》曰:“先主少孤,織履為業。曹公罵云‘賣履舍長’。”亦直說少年劉備自己“織履”“賣履”的經營(47)李昉等:《太平御覽》,第3109頁。《資治通鑒》卷60“漢獻帝初平二年”作:“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司馬光編著,胡三省音注,標點資治通鑒小組校點:《資治通鑒》,北京:中華書局,1956年,第1927頁)《華陽國志》卷6《劉先主志》或作“先主幼孤,其母販履、織席”,則不言劉備參與勞作。任乃強校注《華陽國志校補圖注》指出:“元豐本與廖本作與,他各本并作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355頁)由曹操“賣履舍長”罵語,可知此說不足取。。“販履”,被看作劉備早年行為的一種標志。應當注意到,劉備這種自產自銷的經營,首先是“織席”“織履”的手工生產程序。而“販”字的職業指向也是明確的。“販”,通常是要克服生產處所與銷售處所之間的空間距離的。曹操“賣履舍長”的嘲罵有鄙視其文化資質低下的涵義。但是,“織履”“賣履”的勞作,其實也體驗了另一種學習實踐,可以看作技能教養與經營訓練的形式。
四川新都征集的一件漢畫像磚的畫面主題被定名為“市井”。可見文字標注“北市門”“南市門”。有學者認為,畫面有“酒肆”“雜行”“糧行”及所謂“立傘擺攤販賣者”,以為“生動形象地描繪出漢代市場繁榮景象,為研究漢代社會經濟提供重要資料”。畫面左下方可以看到未成年人形象,但是因為表現內容不很明朗,我們尚不能確定是否可以作為少年從事“販”“賣”活動的文物證明(48)《中國畫像磚全集》編輯委員會編,魏學峰主編:《中國畫像磚全集·四川漢畫像磚》,成都:四川美術出版社,2006年,圖一三一,第98頁,圖版說明第56頁。。
南朝陳徐陵編《玉臺新詠》卷1有“辛延年《羽林郎》詩一首”,宋人郭茂倩編《樂府詩集》卷63《雜曲歌辭三》收入,題《羽林郎》,作者署“后漢辛延年”。詩句講述了霍將軍家奴倚勢“調笑酒家胡”的故事:“昔有霍家奴,姓馮名子都。依倚將軍勢,調笑酒家胡。胡姬年十五,春日獨當壚。長裾連理枝,廣袖合歡襦。頭上藍田玉,耳后大秦珠。兩鬟何窕窕,一世良所無。一鬟五百萬,兩鬟千萬余。不意金吾子,娉婷過我廬。銀鞍何煜爚,翠蓋空踟躕。就我求清酒,絲繩提玉壺。就我求珍肴,金盤鲙鯉魚。貽我青銅鏡,結我紅羅裾。不惜紅羅裂,何論輕賤軀。男兒愛后婦,女子重前夫。人生有新故,貴賤不相踰。多謝金吾子,私愛徒區區。”“辛延年《羽林郎》”被看作漢樂府的名篇。有關“酒家胡”詩句所謂“胡姬年十五”,可以看作未成年人女子從事飲食服務業經營的例證。
上述諸例,都非《史記》卷129《貨殖列傳》“南陽行賈”、“貰貸行賈遍郡國”、“行賈,丈夫賤行也”之所謂“行賈”(49)司馬遷:《史記》,第3278、3279、3282頁。。而確實能夠“行賈遍郡國”者,推想應當也是有未成年人參與的。而“胡姬年十五”輾轉來到中原,是必然經歷長途交通體驗的。
此外,周揚“少孤微,常修逆旅,以供過客,而不受其報”,也是一種服務業經營。李賢注:“杜預注《左傳》曰:‘逆旅,客舍也。’”(50)范曄:《后漢書》卷79上《儒林列傳上》,第2559頁。其接待對象的限定,是行旅的“客”。考察交通史的學術思索,不能忽略周揚“少”時為“逆旅”“過客”的無償付出。
敦煌懸泉置遺址的發掘,出土了可以判斷為“童鞋”的皮鞋(51)甘肅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甘肅省志·文物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甘肅省志·文物志》,北京:文物出版社,2018年,第1687頁。,也獲得了作為蒙學教材的《蒼頡篇》和《急就篇》漢簡(52)駢宇騫:《簡帛文獻概述》,臺北:萬卷樓圖書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第269頁。。這些文物遺存,可以看作未成年人間接參與這處重要驛站接待工作的實證。
上文說到任安“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而后從政,“有智略”,“舉為親民”,“立名天下”。這一情形,是可以說明交通經歷與勞動實踐對于政治知識的獲得與行政能力的提升具有積極的作用。交通經歷與未成年人的見識增益及智能養成有關。
通過苦難生活獲得對社會的真切知識,典型的例證有漢宣帝故事。漢宣帝劉詢出生僅數月就遭遇“巫蠱”大案,在襁褓中就被牽連入獄。這一經歷體驗的苦難,應當是超過“幼孤為奴”的。后來受到有關官員的憐護,被安置由女犯乳養。后逢大赦,釋放出獄,并且恢復了皇族身分:“時掖庭令張賀嘗事戾太子,思顧舊恩,哀曾孫,奉養甚謹,以私錢供給教書。”“(劉詢)受《詩》于東海澓中翁,高材好學”,具有基本的學識基礎,“然亦喜游俠,斗雞走馬,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數上下諸陵,周遍三輔,常困于蓮勺鹵中。尤樂杜、鄠之間,率常在下杜”。所謂“周遍三輔”,顏師古注:“游行皆至其處。”“常困于蓮勺鹵中”,顏師古注:“如淳曰:‘為人所困辱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這種“困”,是另一種低端人口的受迫害經歷。漢宣帝“中興”之治,史稱“信賞必罰,綜核名實”,“吏稱其職,民安其業”(53)⑥ 班固:《漢書》卷8《宣帝紀》,第235—237、275,236頁。,政治成功與其執政資質有密切關系。身居執政集團頂層的這位政治家能夠“具知閭里奸邪,吏治得失”,其社會知識和行政體驗的獲得,是通過底層經歷包括“數上下諸陵,周遍三輔”的交通生活實現的。
這些事跡雖然在“既壯,為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之后⑥,但是“壯”與“取”,并非已經成年的必然標志。雖然《禮記·曲禮下》言“三十曰壯”(54)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據原世界書局縮印本1980年10月影印版,第1232頁。,《釋名·釋長幼》亦言“三十曰壯”(55)任繼昉纂:《釋名匯校》,濟南:齊魯書社,2006年,第150頁。,但是霍去病“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遠在21歲“為票騎將軍擊匈奴”之前(56)班固:《漢書》卷68《霍光傳》(第2931頁):“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既壯大,乃自知父為霍中孺,未及求問。會為票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何東太守郊迎,負弩矢先驅,至平陽傳舍,遣吏迎霍中孺。中孺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自知為大人遺體也。’”。定陶王為傅太后養視,史稱“既壯大”,其實時在少年(57)《漢書》卷97下《外戚傳下·孝元傅昭儀》(第4000頁):“元帝崩,傅昭儀隨王歸國,稱定陶太后。后十年,恭王薨,子代為王。王母曰丁姬。傅太后躬自養視,既壯大,成帝無繼嗣。時中山孝王在。元延四年,孝王及定陶王皆入朝。傅太后多以珍寶賂遺趙昭儀及帝舅票騎將軍王根,陰為王求漢嗣。”。
四、絲路少年足跡
秦始皇直道考古發掘收獲,包括在陜西富縣樺溝口段4個探方和探溝里發現的腳印遺跡。“共揭露出方向雜亂的腳印21個”,腳印應為“成年男子、女子和兒童”行走的遺存。“判斷為兒童的腳印長17厘米,寬7厘米”。考古學者的初步解讀是:“可能是中原方面(漢族)的一兩個家庭成員從這里匆忙行走所遺留。他們走后不久,山體滑坡,泥石流掩蓋了直道。”(58)張在明、王有為、陳蘭、喻鵬濤:《嶺壑無語:秦直道考古紀實》,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總社,2018年,第52—53頁。可能是漢代兒童隨從父兄在前往北邊長城防線的行程中留下了這處珍貴的歷史遺跡。
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出土當時軍人及其家屬的遺物中,有未成年人的生活用品。出土的履,有發掘者認為“為男性成人所用”的“麻布履”1件,也有“似為婦女所用”的“涂漆麻線編織履”1件,另有值得特別關注的兒童穿用的履。發掘報告中寫道:
麻線編織履 一件。標本T2:020。以細麻線編織,口呈橢圓形,底長15厘米,寬5.5厘米,履前部已磨破。為3—4歲小孩所用。
發掘報告中又將被稱作“小孩履”的標本T2:020與另一件成人用履標本T4:018比較(59)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敦煌馬圈灣漢代烽燧遺址發掘報告》,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漢簡》,北京:中華書局,1991年,第54—56頁,圖版壹玖肆。,可以看到尺寸的懸殊。敦煌懸泉置出土可以判斷為“童鞋”的皮鞋。據記述:“皮鞋。漢代。敦煌懸泉置遺址出土。長12.5厘米,寬6厘米,高4.2厘米。皮質。圓口童鞋,鞋幫鞋底均用真皮,以明線縫制,鞋口中后段有系袢。鞋幫一側殘破,另端系帶亦缺失。底有許多蛀孔。是研究漢代物質生活形態與古代服飾發展史的珍貴實物資料。現藏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60)甘肅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甘肅省志·文物志》編纂委員會編纂:《甘肅省志·文物志》,第1687頁。相關實物遺存,也是當時兒童經歷邊塞艱苦生活的見證。
1972年至1976年居延甲渠候官(破城子)遺址的發掘,出土四枚寫有《蒼頡篇》文字的漢簡。1977年玉門花海漢代烽燧遺址的發掘,出土三枚有《蒼頡篇》內容的漢簡。1990年至1992年對敦煌懸泉置遺址的發掘,也獲得了《蒼頡篇》和《急就篇》漢簡(61)駢宇騫:《簡帛文獻概述》,第269頁。。居延漢簡又有簡例“□甲渠河北塞舉二烽燔蒼頡作書”(E.P.T50:134A)。研究者認為:“‘蒼頡作書’四個字是《蒼頡篇》中的內容,它和官文書放到一起,內容互不相屬,所以合理的解釋是,邊塞吏卒利用廢棄的簡牘練習字書上的字。與此相對應的,那些字書的性質只是習字的范本。”(62)沈剛:《居延漢簡中的習字簡述略》,《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6年第1期。
《流沙墜簡》說到列有乘法口訣的簡文,列于“術數類”中,題《九九術》。其內容為:
九九八十一 八八六十四 五七卅五 □□□□ 二三而六 大凡千一百一十
八九七十二 七八五十六 四七廿八 五五廿五 二二而四
七九六十三 六八卌八 三七廿一 四五廿 □□□
五八卌 三五十五
羅振玉、王國維說:“此簡‘二二而四’,今法作‘二二如四’。”參證古代文獻,以為后來“二二如四”的說法形成較晚,“知改‘而’作‘如’,始于宋代也”(63)羅振玉、王國維:《流沙墜簡》,北京:中華書局,1993年,第92—93頁。。駢宇騫對于羅振玉等有關論證中的疏誤有所澄清,指出1987年出土于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的東漢木牘《九九乘法表》文作“二五如十”,可證羅振玉等“改‘而’作‘如’,始于宋代”說不確(64)駢宇騫:《簡帛文獻概述》,第336—337頁。。
居延漢簡中被稱作《九九乘法表》的文字遺存,還有一些值得重視的實例。例如簡75.19:
宣耿
九九八十一 四九卅六 八八六十四
八九七十二 三九廿七 七八五十六
七九六十三 二九十八 六八卌八
六九五十四 五八卌
五九卌五 四八卅二
三八廿四(65)謝桂華、李均明、朱國炤:《居延漢簡釋文合校》,第133頁。
肩水金關簡也有相關內容,例如:
六九五十四(削衣)(73EJT6:193)(66)甘肅簡牘保護研究中心、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編:《肩水金關漢簡》下冊(壹),第76頁。
可以看作蒙學教材的《九九乘法表》近年通過里耶秦簡和張家界漢簡的出土,均有實物發現(67)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南龍山縣里耶戰國秦漢城址及秦代簡牘》,《考古》2007年第7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遺址與出土簡牘概述》,《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2期;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中國文物研究所:《湖南張家界古人堤簡牘釋文及簡注》,《中國歷史文物》2003年第2期。,對于我們認識算學在秦漢基層社會的普及,提供了新的極有價值的資料。
漢代“小學”教材內容的簡牘出土,或當如有的學者所指出的,用于士兵文化學習。但是結合如“鞠”“玩具衣”等兒童玩具的出土,這些文書遺存當年服務于童蒙教育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絲綢之路文化遺存可以看到少數民族“歸義”的交通行跡。河西邊塞出土簡牘資料有反映民族關系的內容,其中亦涉及少數民族未成年人。如敦煌漢簡:
五校吏士妻子議遣烏孫歸義侯疌清子女到大煎都候鄣(90)
涉及“歸義”的“烏孫”貴族“子女”,他們來到河西,“到大煎都候鄣”,是經歷了艱苦的交通實踐的。敦煌漢簡又有:
車師侯伯與妻子人民柒十柒人愿降歸德欽將伯等及烏孫歸義(88)(68)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吳礽驤、李永良、馬建華釋校:《敦煌漢簡釋文》,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9頁。
所謂“妻子人民”中,應當包括未成年人。
額濟納漢簡又有言及“大且居蒲妻子人眾”的簡文:
□大且居蒲妻子人眾凡萬余人皆降余覽喜拜之□□□□□□符蒲等
其□□□□質修待子入余□□入居……伋奏辯詔命宣揚威□安雜□(2000ES9SF4:9)
校尉苞□□度遠郡益壽塞徼召余十亖人當為單乎者苞上書謹□□為單乎者十亖人其一人葆塞稽朝候咸妻子家屬及與同郡虜智之將業(2000ES9SF4:10)(69)孫家洲主編:《額濟納漢簡釋文校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年,第85頁。
外族來降的“妻子人眾”“妻子家屬”中的“子”,應當主要是未成年人。“歸義”,指對漢文化的認同。《史記》卷117《司馬相如列傳》:“皆爭歸義,欲為臣妾,道里遼遠,山川阻深,不能自致。”(70)司馬遷:《史記》,第3044頁。明確說到“歸義”要克服怎樣困難的交通條件。簡2000ES9SF4:9 說“妻子人眾凡萬余人”,數量相當驚人,其中“子”指代的未成年人數量必然相當可觀。簡文“奏辯詔命宣揚威□安雜□”,說到對來“降”的“妻子人眾”進行安置,其中包括“宣揚威□”的政治宣教。
五、“不遠千里”的求學之路
《漢書》卷89《循吏傳·文翁》記載,文翁為蜀郡守,“仁愛好教化”,注意到蜀地文化與中原文化存在距離,欲促成其進步,于是“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予以指導,派遣至京師學習。“蜀生”“成就還歸”者,予以重用。又創立地方官學:
見蜀地辟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余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減省少府用度,買刀布蜀物,赍計吏以遺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文翁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起學官于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為除更繇,高者以補郡縣吏,次為孝弟力田。常選學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出入閨閣。縣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富人至出錢以求之。繇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為之始云。(71)⑧⑨⑩ 班固:《漢書》,第3625—3626,3481,2821,3093頁。
文翁開創的這種少年吏“遣詣京師,受業博士”的異地培訓、異地進修形式,提升了地方教育素養。“招下縣子弟以為學官弟子”,已經激發了諸多學子的游學熱情,而“每出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傳教令”,也是涉及交通文化的特殊政策。所謂“繇是大化,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顯然全面促進了地方文化的發展。
“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很可能是少年吏(72)王子今:《兩漢的少年吏》,《文史》第51輯,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而所謂“學官弟子”“學官僮子”,從四川成都羊子山出土漢畫像磚講經圖的畫面看,應當是包括未成年學子的。
“蜀地學于京師者比齊魯焉”的情形,必然促成了蜀道交通的繁忙。“學官弟子”“學官僮子”及其他“蜀地學于京師者”往返巴蜀山地艱險道路“成就還歸”的事跡,可以看作游學史精彩的一頁,或許也可以看作留學史精彩的一頁。
文翁倡起的往京師求學的路徑,后世仍得繼承。“蜀郡繁人”任末“少習《齊詩》,游京師”(73)范曄:《后漢書》卷79下《儒林列傳下·任末》,第2572頁。,可以看作例證。
《后漢書》卷79下《儒林列傳下》,以“論曰”的形式敘說東漢儒學教育的空前繁榮:“自光武中年以后,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橫塾者,蓋布之于邦域矣。”(74)范曄:《后漢書》,第2588頁。指出了“庠序”“橫塾”的文化吸引力(75)李賢注:“‘橫’又作‘黌’。”,廣布“邦域”,形成了教育史與交通史的神奇交接。
漢武帝初設博士弟子員制度,起初為50人,漢昭帝時增至100人,漢宣帝時增至200人,“元帝好儒”,“更為設員千人”,成帝末,“增弟子員三千人”(76)班固:《漢書》卷88《儒林傳》,第3596頁。。根據王莽的建議,“為學者筑舍萬區”,一時“制度甚盛”(77)班固:《漢書》卷99上《王莽傳上》,第4069頁。。我們可以看到各地學子往長安就讀太學的史例。《漢書》卷86《何武傳》記載,何武,“蜀郡郫縣人也”。“益州刺史王襄使辯士王褒頌漢德,作《中和》、《樂職》、《宣布》詩三篇。武年十四五,與成都楊覆眾等共習歌之”;后來,“武詣博士受業,治《易》”⑧。《漢書》卷64下《王褒傳》又說:“武等學長安,歌太學下,轉而上聞。”⑨《漢書》卷72《鮑宣傳》:“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⑩《后漢書》卷1上《光武帝紀上》說,劉秀曾經在長安太學就學,“王莽天鳳中,乃之長安,受《尚書》,略通大義”。李賢注引《東觀記》:“資用乏,與同舍生韓子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78)⑤ 范曄:《后漢書》,第1—2,2545、2547、2548,2588頁。劉秀“買驢,令從者僦”的故事,體現了太學生經營運輸業以補充“資用”的情形。劉秀與同為“南陽宛人”的朱岑“俱學長安”,朱岑的兒子朱暉則在洛陽“卒業于太學”(79)范曄:《后漢書》卷43《朱暉傳》,第1457頁。。
東漢統治者益祟好儒學經術,于是“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策,云會京師,范升、陳元、鄭興、杜林、衛宏、劉昆、桓榮之徒,繼踵而集”(80)⑥⑧ 范曄:《后漢書》卷79上《儒林傳上》,第2545,2546,2553、2554、2558、2560,2550—2557、2563—2564頁。。“起太學博士舍,內外講堂,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81)范曄:《后漢書》卷48《翟酺傳》,第1606頁。所謂“抱負墳策,云會京師”,“繼踵而集”,“諸生橫巷,為海內所集”,既是文化史的記載,也是交通史的珍聞。《后漢書》卷79上《儒林列傳上》記載,漢明帝曾親自在太學講經,“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于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漢順帝又擴建太學,“凡所造構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漢質帝時,“游學增盛,至三萬余生”,于是有“東京學者猥眾,難以詳載”之說⑤。而“匈奴亦遣子入學”⑥,其行程更為遙遠。太學生及京師學人中多未成年人,如賈逵“自為兒童,常在太學,不通人間事”(82)范曄:《后漢書》卷36《賈逵傳》,第1235頁。,戴憑“年十六,郡舉明經,征試博士,拜郎中”,孫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張馴“少游太學,能誦《春秋左氏傳》”,尹敏“少為諸生,初習《歐陽尚書》,后受《古文》,兼善《毛詩》、《谷梁》”,孔僖“曾祖父子建,少游長安,與崔篆友善”,“僖與崔篆孫骃復相友善,同游太學,習《春秋》”⑧,可能也是少年。而高獲“少游學京師,與光武有舊”(83)范曄:《后漢書》卷82上《方術列傳上·高獲》,第2711頁。,唐檀“少游太學,習《京氏易》、《韓詩》、《顏氏春秋》”(84)范曄:《后漢書》卷82下《方術列傳下·唐檀》,第2729頁。,包咸“少為諸生,受業長安,師事博士右師細君,習《魯詩》、《論語》”,魏應“少好學,建武初,詣博士受業,習《魯詩》”,任末“少習《齊詩》,游京師”,李育“少習《公羊春秋》,沈思專精,博覽書傳,知名太學”,服虔“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85)范曄:《后漢書》卷79下《儒林傳下》,第2570、2571、2572、2582、2583頁。,也是少時有“太學”學歷的史例。
私學之發達,也吸引各地學子不遠千里問師求教。疏廣“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86)班固:《漢書》卷71《疏廣傳》,第3039頁。,申公“歸魯退居家教,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余人”(87)班固:《漢書》卷88《儒林傳·申公》,第3620,3608頁。,都使用了“自遠方至”的說法。班固曾經以“傳業者寖盛,支葉蕃滋”,“大師眾至千余人”來總結西漢學術傳統。所謂“蕃滋”,是得到來自“遠方”的人才支持的。私學的昌盛,史籍記錄有所表現,“若乃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受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專相傳祖,莫或訛雜。至有分爭王庭,樹朋私里,繁其章條,穿求崖穴,以合一家之說”。所謂“經生所處,不遠萬里之路”,李賢注:“經生謂博士也。就之者不以萬里為遠而至也。”“耆名高義開門”所“受”之“徒”,往往來自遠方。“儒者萬里負笈以尋其師”(88)《抱樸子·祛惑》,王明:《抱樸子內篇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第351頁。,成為一時風尚。據《后漢書》卷79《儒林列傳》記載,劉昆曾“教授弟子恒五百余人”,洼丹“徒眾數百人”,任安“還家教授,諸生自遠而至”,楊政“教授數百人”,張興“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孫期“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歐陽歙“教授數百人”,曹曾“門徒三千人”,牟長“諸生講學者常有千余人,著錄前后萬人”,牟紆“門生千人”,宋登“教授數千人”,孔季彥“門徒數百人”,楊倫“講授于大澤中,弟子至千余人”,魏應“教授山澤中,徒眾常數百人”,“弟子自遠方至,著錄數千人”,薛漢“教授常數百人”,杜撫“歸鄉里教授”,“弟子千余人”,董鈞“常教授門生百余人”,丁恭“教授常數百人”,周澤“門徒常數百人”,甄宇“教授常數百人”,甄承“講授常數百人”,諸儒“莫不歸服之”,樓望“諸生著錄九千余人”,程曾“還家講授,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張玄“諸儒皆伏其多通,著錄千余人”,李育“常避地教授,門徒數百”,潁容“聚徒千余人”,謝該“門徒數百千人”,蔡玄“門徒常千人,其著錄者萬六千人”(89)范曄:《后漢書》卷79下《儒林列傳下》,第2571、2573、2577、2578、2580、2581、2582、2584、2588頁。。除前引諸例之外,又如廖扶“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90)范曄:《后漢書》卷82上《方術列傳上·廖扶》,第2719頁。,唐檀“教授常百余人”(91)范曄:《后漢書》卷82下《方術列傳下·唐檀》,第2729頁。,姜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余人”(92)范曄: 《后漢書》卷53《姜肱傳》,第1749頁。,檀敷“立精舍教授,遠方至者常數百人”(93)范曄:《后漢書》卷67《黨錮列傳·檀敷》,第2215頁。,樊英習《易經》,兼明數術,“隱于壺山之陽,受業者四方而至”(94)范曄:《后漢書》卷82上《方術列傳上·樊英》,第2721頁。,公沙穆“隱居東萊山,學者自遠而至”(95)范曄:《后漢書》卷82下《方術列傳下·公沙穆》,第2730頁。,董扶“還家講授,弟子自遠而至”(96)范曄:《后漢書》卷82下《方術列傳下·董扶》,第2734頁。。劉根事跡亦可見“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97)范曄:《后漢書》卷82下《方術列傳下·劉根》,第2746頁。。所謂“遠方至”“自遠而至”“四方而至”“遠來就學”情形體現的與交通史與教育史的交集,特別值得關注。學者向學就學形成的“不遠萬里之路”,負笈游學的風氣,形成了值得重視的交通現象。如《后漢書》卷79下《儒林列傳下·景鸞》:“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98)范曄:《后漢書》,第2572,2073,2735,1263,2689頁。即是“少”時負笈隨師之例。《后漢書》卷63《李固傳》說,李固“少好學,常步行尋師,不遠千里”,李賢注引《謝承書》:“固改易姓名,杖策驅驢,負笈追師三輔,學《五經》,積十余年。”李固“遂究覽墳籍,結交英賢,四方有志之士,多慕其風而來學”。《后漢書》卷82下《方術列傳下·郭玉》說:“弟子程高尋求積年,(涪)翁乃授之。”所謂“尋師”“隨師”“追師”事跡,說明當時學術師承之緒統,受與授,承與傳,多需經過艱苦的交通歷程方能完成。事實上讀書人學業有成的基本條件,首先在于“不遠萬里之路”的磨練。而遠行之見聞,也必然可以增益其學識。
《后漢書》卷37《丁鴻傳》寫道:“鴻年十三,從桓榮受《歐陽尚書》,三年而明章句,善論難,為都講,遂篤志精銳,布衣荷擔,不遠千里。”“年十三”的年齡標記是明確的。在“三年而明章句”之后,也不過16歲。
《后漢書》卷81《獨行傳·范冉》李賢注引《謝承書》曰:“奐字子昌,河內武德人。明《五經》,負笈追業。”《三國志》卷11《魏書·王修傳》裴松之注引王隱《晉書》:“(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身不停家。”(99)陳壽:《三國志》,第349頁。邴原的事跡可以具體說明當時學人行走的經歷。《三國志》卷11《魏書·邴原傳》記載,邴原“北海朱虛人”,“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郁洲山中”。后來,“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原在遼東,一年中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后得歸”。邴原從北海至遼東,越海往返,顯然是難度甚大的海路交通行為,而“將家屬入海”,應當已是成人。然而“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其中當不乏未成年人。裴松之注引《原別傳》說到邴原少年時求學經歷:
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茍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于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齓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針矣;然猶未達仆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仆以鄭為東家丘,君以仆為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兗﹑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師啟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于家而行。(100)②③ 陳壽:《三國志》,第351,352,350—352頁。
“童子”邴原的求學之志令人感動,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欲遠游學”的強烈追求。所謂“登山”“入海”之言,表現了克服交通險阻以“求師啟學”的毅力。甚至在得到孫崧“以書相分”之后,又“藏書于家而行”。《原別傳》還寫道:
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后,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干。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于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②
“藏書于家而行”,又“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似乎“遠游學”“單步負笈,苦身持力”的交通實踐,意義甚至超過了“書”,即基本的經典文獻。由所謂“單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③,可知其“單步負笈”行走的遙遠。
六、“道物故”悲劇與少年學人的行旅犧牲
“道物故”或“行道物故”,指行旅途中死亡。我們討論過行役者途中死亡的情形(101)王子今:《居延漢簡所見“戍卒行道物故”現象》,《史學月刊》2004年第5期。。我們還看到,漢代學人也往往有以這種方式結束人生的情形。
據《后漢書》記載,在“尋師”“隨師”“追師”的路途中結束其學術生命的名儒,可見多例。如《后漢書》卷79上《儒林列傳上·牟長》:
子紆,又以隱居教授,門生千人。肅宗聞而征之,欲以為博士,道物故。(102)⑥⑦⑧⑨ 范曄:《后漢書》,第2557,2557,2572,2583,2751頁。
李賢注:“在路死也。案:魏臺訪議問物故之義,高堂隆答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死者無復所能于事也。’”⑥
又如《后漢書》卷79下《儒林列傳下·任末》記述另一位學者任末的相關事跡: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游京師,教授十余年。友人董奉德于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為郡功曹,辭以病免。后奔師喪,于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于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慚;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⑦
又一位漢末名儒服虔,也去世于道途行程中。《后漢書》卷79下《儒林列傳下·服虔》記載:
服虔字子慎,初名重,又名祇,后改為虔,河南滎陽人也。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有雅才,善著文論,作《春秋左氏傳解》,行之至今。又以《左傳》駁何休之所駁漢事六十條。舉孝廉,稍遷,中平末,拜九江太守。免,遭亂行客,病卒。⑧
所謂“遭亂行客,病卒”也可以讀作“遭亂,行客病卒”。又如《后漢書》卷82下《方術列傳下·王和平》:“北海王和平,性好道術,自以當仙。濟南孫邕少事之,從至京師。會和平病歿,邕因葬之東陶。有書百余卷,藥數囊,悉以送之。后弟子夏榮言其尸解,邕乃恨不取其寶書仙藥焉。”⑨王和平“北海”人,應是自“京師”東行,至“東陶”“病歿”,也是“行客病卒”。《梁史》卷54《諸夷列傳·西北諸戎》記述了絲綢之路上的一則“道物故”故事:“黃武五年,有大秦賈人字秦論來到交趾,交趾太守吳邈遣送詣(孫)權。權問方土謠俗,論具以事對。時諸葛恪討丹陽,獲黝、歙短人,論見之曰:‘大秦希見此人。’權以男女各十人,差吏會稽劉咸送論。咸于道物故。論乃徑還本國。”(103)姚思廉:《梁書》卷54《海南諸國傳·中天竺國傳》,北京:中華書局,1973年,第798頁。這是三國時孫吳政權一位“吏”劉咸“于道物故”事,與前說學者不同。但是其行跡涉及海上絲路交通,也值得注意。又有枚乘應漢武帝召“道死”的故事,顏師古注:“在道病死也。”(104)② 班固:《漢書》卷51《枚乘傳》,第2365,2365頁。
以上牟紆“道物故”,任末“奔師喪,于道物故”,服虔“遭亂行客,病卒”,劉咸“于道物故”諸例,都是成年人遠行,去世于道途中。枚乘故事,《漢書》明確說“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征乘,道死”②。然而任末“少習《齊詩》,游京師”,服虔“少以清苦建志,入太學受業”,他們的求學行旅,都從“少”時開始。但是這些歷史信息提示我們,未成年人經歷行旅艱辛,更容易發生類似“道物故”的悲劇。《漢書》卷64上《主父偃傳》:“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顏師古注:“道死謂死于路也。”(105)④ 班固:《漢書》,第2800,3913頁。《漢書》卷96下《西域傳下·渠犁》:“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④都說“羸”“弱”難以克服行路艱難。蒯通說:“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此言貴能行之也。”(106)班固:《漢書》卷45《蒯通傳》,第2165頁。也強調了“童子”“行之”的不易。
南陽馮良的故事,或許可以提供有意義的參考。《后漢書》卷53《周燮傳》:“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縣吏。年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后乃見草中有敗車死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十許年,乃還鄉里。”(107)⑦ 范曄:《后漢書》,第1743,2575頁。而《后漢書》卷79下《儒林列傳下·趙曄》有情節類似的記述:“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于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杜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撫卒乃歸。”⑦何焯討論《趙曄傳》時寫道:“《周燮傳》載南陽馮良事與此相類,而所從皆杜撫。必一事而傳者互異耳。”(108)范曄:《后漢書》卷109下《考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馮良“少作縣吏”,趙曄“少嘗為縣吏”,只是馮良事跡有“年三十”字樣,而《東觀漢記》卷20《馮良傳》:“馮良,字君郎,南陽人。少作縣吏,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從杜撫學。”(109)清《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本。《北堂書鈔》引《東觀》,輯校者指出各本不同,均無“年三十”字樣(110)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據“《書鈔》卷七七”:“南陽馮良少作縣吏,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主撻之。從杜撫學。妻子見車有死馬,謂為盜賊所害。”(劉珍等撰,吳樹平校注:《東觀漢記》,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723頁)光緒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北堂書鈔》:“馮良恥在廝役。《東觀》云:南陽馮良少作縣吏,恥在廝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主撻之。從杜撫學。妻子見車有死馬,謂為盜賊所害。”孔廣陶、林國賡等續校說明:“今按:《聚珍》本、姚輯本《東觀記·馮良傳》無‘主撻之’字,無‘妻子’四句。陳本脫,因壞以下。俞本與《聚珍》本同。”(虞世南編撰:《北堂書鈔》,北京:中國書店據光緒十四年南海孔氏刊本1989年7月影印版,第283頁)。《后漢紀》卷17《孝安皇帝紀下》的記述,也不言“年三十”(111)范曄:《后漢紀》卷17《孝安皇帝紀下》:“良字君卿,少為縣吏,從尉迎督郵,良恥廝役,因毀其車馬,壞其衣冠,絕跡遠遁。妻子見敗車壞衣,皆以猛獸所是,遂發喪制服。良至犍為,從師受業,十余年還鄉里。”校勘記:“良字君卿。《后漢書·周燮列傳》作‘君郎’。”袁宏撰,張烈點校:《后漢紀》,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第328、338頁。。如果理解馮良、趙曄故事提示了少年求學途中可能遭遇“虎狼盜賊所害”的危險,可能是適宜的。
居延出土漢簡有關于未成年人“病死”的內容:“月十三日送省卒食道上長周育子病死取急歸卒馮同病。”(E.P.F22:492)(112)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肅省博物館、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居延新簡:甲渠候官與第四燧》,第510頁。。這種情形,其實也類同于前述服虔事跡所謂“行客病卒”,可以幫助我們體會求學者“道物故”的悲慘情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