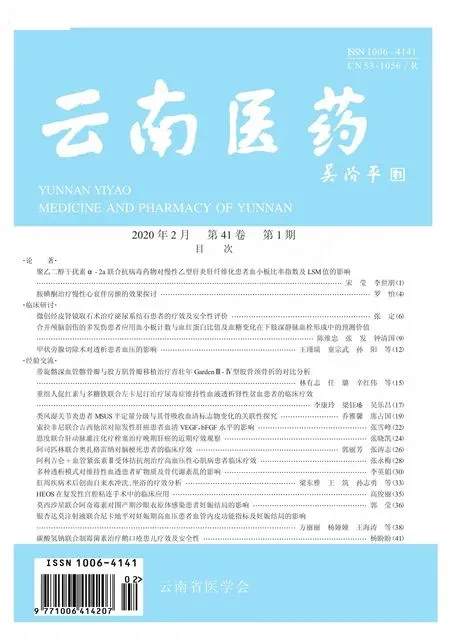社區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的康復現狀調查
楊 婷,張勇輝,王 維,高長青,沈紅梅
(1.昆明市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2.云南省精神病醫院,云南 昆明 650224)
社區康復是指在社區的層面上,利用、依靠社區的人力、物力、技術資料采取的康復措施[1]。當代社區精神醫學的形成與發展主要發源于美國,美國“精神科非住院化運動”的全面開展,尤其以主動式社區治療(assertive community treatment,ACT) 為代表的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的社區照料模式,使其精神病床總數由56 萬張減至14 萬張,且仍在不斷下降,而院外服務由22.6%上升為71.6%;接受社區康復治療的精神病患者,每人的花費僅需900 美元/年,比住院治療每人15 600美元/年下降了94%,社區精神衛生服務取得了良好效果[2,3]。
我國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提出精神疾病社區康復問題,但直到本世紀初我國內地共有嚴重精神障礙患者1 600 萬人,全國各類精神疾病的患病率已達13.47‰,但我國平均12 820 人才有1 張精神科床位,85 552 人才有1 名精神科醫生[4]。人口眾多、精神疾患人數龐大等現狀,加之缺乏適宜的服務規范和服務模式,社區精神衛生服務資源、人力不足等原因,致使我國社區精神衛生服務工作相對滯后,未形成系統的本土理念及實踐模式,患者通過藥物治療病情雖得到控制,但社會功能康復較差,生活質量較低。近年來,雖然住院化的精神康復手段已取得了較大的發展,但是仍然無法達到理想的康復狀態,故覆蓋面廣、成本低、注重心理及社會功能康復的社區精神康復顯得越來越重要。
根據《全國精神衛生工作體系發展規劃綱要(2008-2015年)》、國家《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管理服務規范》要求,對目前昆明市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社區精神衛康復現狀進行全面、系統的了解,分析昆明地區現行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社區康復服務在滿足康復需求方面的優勢與局限,從而有針對性、時效性地提高現行社區康復服務水平,為昆明市社區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社區康復本土化模式提供現實依據。
對象與方法 一、研究對象 本研究于2014年3月-2014年4月期間隨機抽取昆明市主城區100 例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及98 例家屬為研究對象,征得其知情同意的前提下,采用自編患者調查問卷對100 例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及98 例家屬,通過一對一訪談形式進行問卷調查。嚴重精神障礙患者所有量表的評定均由精神科醫師或精神科護士完成通過訪談患者本人或者家屬完成,家屬問卷通過自評形式進行。負責問卷調查的工作人員經過統一的培訓,使用統一的指導語,對被調查者不能理解的語句作必要指導,但不做暗示。共收回100 份患者有效問卷,70 份家屬有效問卷。
二、研究方法 1.研究工具 自編調查問卷包括自編精神疾病患者、家屬調查問卷,問卷內容由基本人口學資料,對社區精神疾病康復情況的了解、建議及意見等內容組成。
2.統計方法 采用SPSS17.0 對數據進行描述性統計分析處理。
結果 1.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家屬對社區康復的了解現狀及要求 本次被調查的70 例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家屬的平均年齡為(61.89±14.03)歲,女性、退休人員居多,大部分家庭月收入在1 000~5 000 之間,監護人以父母為主。有90%(63 人) 的患者家屬對目前的社區康復情況有所了解,其中對藥物治療、精神疾病復發的癥狀及預防、精神疾病的家庭康復有所的了解的家屬分別占60%、43%、34%。康復過程中有77.1% (54人) 的家屬遇到困難,其中分別有17.1%、34.3%、64.3%的家屬在患者服藥依從性、藥物副作用、管理方面等遇到困難。有94.3%(66 人) 的患者家屬想要得到幫助,其中有71.4%的家屬想要得要經濟方便的幫助,78.6%的家屬想要得到精神疾病相關知識方面的幫助,還有小部分家屬希望相關部門為患者提供工作、免費服用新藥好藥,加強人際交往、家務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等方面的康復訓練。調查還顯示患者家屬對目前社區康復管理的滿意度為100%,見表1。
二、社區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的康復現狀 本次被調查的100 例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的平均年齡為(45.67±9.55) 歲,男性、精神分裂癥、漢族、高中或中專文化水平居多,97%患者不能繼續工作,77%患者靠低保和親戚救助生活,79%患者住過精神病專科醫院,97%患者服用過精神科藥物,50%患者病情穩定。100 人中有71 人先后于1999年至2014年期間參加國家免費服藥項目,免費服藥種類有氯氮平、利培酮、氯丙嗪、舒必利、安定等;3 人未服藥、94 人堅持服藥、3 人未堅持服藥;6 人未進行每年體檢、75 人每年體檢1 次、17 人每年體檢2 次、1 人每年體檢3 次、1 人每年體檢4次;有90 人到社區體檢、4 人到綜合醫院體檢、6 人未體檢。有83%的患者對目前的社區康復情況有所了解,其中對藥物治療、精神疾病復發的癥狀及預防、精神疾病的家庭康復有所的了解的分別占83%、53%、43%。康復過程中有64%患者遇到困難,其中分別有24%、27%、26%的患者在藥物費用、藥物副作用、參加社區活動等方面遇到困難。有87%的患者想要得到幫助,其中有66%的患者想要得要經濟方面的幫助,68%的患者想要得到精神疾病相關知識方面的幫助。調查還顯示患者對目前社區康復管理的滿意度為98%,見表2。
討論 本研究顯示,昆明市社區嚴重精神障礙患者多為精神分裂癥患者,以漢族居多,多為初高中文化水平,未婚;絕大部分待在家里處于無業狀態,但人員少部分(3%) 人仍然繼續堅持工作;大部分患者的收入來源于低保或親戚救濟;這些患者的照料者多為其父母,但照料者年齡偏高(61.89±14.03) 歲,多數人已退休在家;患者家庭月收入在1 000~5 000 之間的居多;患者發病年齡從1 歲到65 歲不等,但21%的患者從未住過精神病專科醫院;大部分患者服藥年限長,均在10年以上且均堅持服藥;有71%的患者先后參加國家免費服藥項目;94%的患者每年均會參加體檢,且大部分人是到社區參加每年一次的體檢。目前,大部分患者和家屬對社區康復情況,包括藥物治療、精神疾病復發的癥狀及預防、精神疾病的家庭康復是有所了解的,康復過程中患者遇到的困難從高到底分別是藥物副作用、參加社區活動、藥物費用等方面,家屬遇到的困難主要集中在管理患者方面,一半以上的患者及家屬希望得到精神疾病相關知識及經濟方面的幫助,小部分則希望相關部門為患者提供工作、免費服用新藥好藥,加強人際交往、家務能力、生活自理能力等方面的康復訓練。患者及家屬對目前康復均表達了較高的滿意度。

表1 患者家屬的不同人口學信息頻率統計(n=70)

表2 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的不同人口學信息頻率統計(n=100)
由此可見,目前昆明市社區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生活狀況不容樂觀,大部分患者屬于弱勢群體,需要他人的照顧和監管,但大部分患者的監護人呈老齡化特點,監護人有時也是有心無力,很難有效地監管患者。同時,國內精神康復工作面臨著許多矛盾和困境:首先,精神康復的任務非常艱巨,但社區專業人員匱乏,社區中缺乏精神專科醫生、基層醫生缺乏精神疾病防控的基本知識和服務技能、缺少多學科組成的康復服務隊伍和服務模式,使得很多精神疾病患者在社區和家庭康復期間主要依靠專業機構和藥物治療,得不到綜合性的醫療照顧;其次,社會中一些人對精神疾病患者存在誤解、偏見和歧視,使得患者難以平等地參與社會生活、承擔適當的社會勞動,這些都是精神疾病患者得不到全面康復的重要原因[9]。
因此,為改變我國目前精神疾病患者社區管理和康復的現狀,我們可在借鑒國外精神疾病社區管理先進經驗的同時,根據不同地區的現實條件嘗試一些新的管理模式。當前可引進或借鑒主動式社區治療(ACT) 模式[3,10,11],以個案管理患者模式為切入點,嘗試組建多學科的專兼職服務隊伍,探索隊伍服務與管理機制,研究具有我國或地方特色的社區精神疾病患者全面康復管理模式及驗證其可行性,以推進我國社區精神衛生服務的發展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