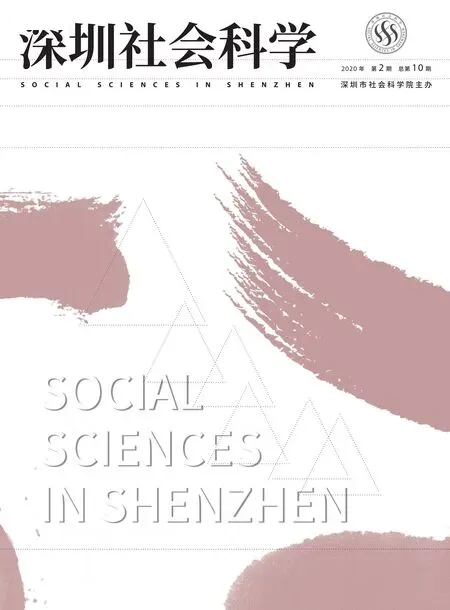道路自信與話語權構建*
王慶林 亢 升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3年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深刻指出:“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的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1頁。總書記對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視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認為中國道路的“中國特色”要做到“四個講清楚”,強調認識中國道路必須從中國自身出發。從近代170多年發展歷程中深刻總結中走出來的中國道路,其歷史敘事必須克服沖擊—回應模式的西方中心論史觀,以中國為中心構建道路話語權,為中國道路自信追本溯源。
海外研究中國近代現代化道路歷史起點缺乏從中國自身出發,而是以西方為中心,提出沖擊—回應模式。這一模式分析做了兩個假設:一、19世紀左右中國歷史進程是與西方的對抗;二、在對抗中,西方積極主動,中國則被迫應對。這種預先的假設顯然對中國近現代史片面認識,不利于客觀認識中國現代化道路的內生發展和樹立道路自信,對中國學界乃至中國社會設置了道路自信的認知障礙。結果是在中國與西方關系中,西方處于主動,中國處于被動,西方不停地提出新概念,中國不停地被動應付。隨著中國的崛起,指出沖擊—回應模式的不實之處,是中國道路自信和話語權構建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沖擊—回應模式及其三種表現形式
最早提出沖擊—回應模式的是費正清。他在1948年第一版《美國與中國》中認為,中國社會具有超強的穩定性,除非有外來的作用,否則中國難以跳出傳統的窠臼,中國現代化是西方刺激后反應的結果。這種分析方式是對19-20世紀中國產生的一種以西方為中心的曲解,其分析框架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國對“西方沖擊”的回應上,把西方的沖擊當成敘事主體,很容易鼓勵人們認為只有有助于說明中國對西方回應的中國近代史才是重要的,凡是與西方侵略沒有明顯聯系的都被認為是不重要的。此后,沖擊—回應模式在美國被廣泛應用到對中國近代現代化的研究。如保羅.H.克萊德(Paul H.Clyde)和伯頓.F.比爾斯(Burton F.Beers)合著的《遠東:西方沖擊與東方回應之歷史》(The Far east: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認為遠東革命運動包括兩個部分:一是西方文化生氣勃勃地向中亞與東亞古老傳統社會全面擴展,從19世紀初持續到20世紀初,幾乎征服了整個亞洲,通常稱為“西方之沖擊”;二是亞洲對西方的回應,一開始軟弱無力,步調參差,方向不明。戰后,這種反應成澎湃之勢,不可阻擋,20世紀中期,出現了一個嶄新東亞①Paul. H. Clyde and Burton. F.Beers:The Far East: A History of the Western Impact and the Eastern. Response (1830-1965), 4th edition. Englewood Cliffs, N. J.: Prentice-Hall, 1966, p6.。上述觀點實質上是西方中心論式的傲慢與偏見。總體來看,沖擊—回應模式集中表現為三種分析框架:沖擊—回應框架、傳統—近代框架、帝國主義框架。
第一,西方沖擊—中國回應框架。該模式認為19世紀中國歷史發展中起主導作用的因素或者主要線索是西方入侵,19世紀到20世紀中國所經歷的一切有歷史意義的變化只能是西方式的變化,堵塞了從中國內部探索現代化道路的可能,把中國近代史研究引入了死胡同。戰后美國對中國近代史研究的主流在70年代前受費正清與列文森等人影響,基本上是沖擊—回應的西方中心論模式。令人擔憂的是,與這種分析模式相對應地形成了對中國的另一個偏見,即中國歷史中只有那些符合西方現代化標準的發展道路才值得研究,而且這些研究明顯具有中西自身所最關切的問題,即側重于中國歷史與西方關系最密切的側面。這種典型的西方中心論顯示在近代只有西方從沒有從外界來觀察自己②John E. Schrecker:The West in Outside Perspectiv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tercultural-Historical Method, Ba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uia Press, 1966 p2.,即歐洲人發現了全球,卻從來無人前來發現歐洲。西方人無須認真對待其他民族對自己的看法,也無需像其他偉大文化的人物那樣,為了求得自己文化的生存,被迫對它做出根本的估量,并有意把自己文化的大部分拆散,然后重新組合起來。這一切造成一種似是而非的怪誕現象:和其他民族相比,西方人雖然是創造近代世界貢獻最大的一些民族,但在某些方面卻成了最不理解這個世界的民族。這種優越感也讓西方無須認真對待其他民族文明,這是人類文明史上從來沒有過的現象,這賦予了西方人一種文化深入人心的普遍性,對于這種普遍性并不必從歷史上做出解釋,而看成理所當然,不可避免。
美國學者柯文在其第一部戰后對美國研究中國近代史模式批判性總結的著作《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中認為沖擊—回應觀念已經陳舊,是典型的西方中心論,對美國的中國現代史研究占主導地位的范式—“沖擊—回應”提出了強勁挑戰。柯文在序言中開宗明義:“研究中國歷史,特別是研究西方沖擊之后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最嚴重的問題一直是由于種族中心主義造成的歪曲。”①[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96頁。中國中心觀把史學家的注意力引向中國歷史內部因素并強調對整個中國史境的探索,這對于深入探討中國近現代化道路極為復雜的情況是有利的。
第二,傳統—近代框架。美國的中國史專家把社會演變分為“傳統的”和“近代的”兩個階段。這種兩分法五六十年代在美國中國史專家中間極有市場,他們幾乎都采用“傳統”和“近代”兩個詞來劃分中國漫長的歷史,而且“近代”通常指與近代西方接觸頻繁的時期。孔飛力在《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序言中討論“近代史界限”這一概念時指出,對近代中國發生的轉變有一種流行看法是:在界說“近代”一詞時,隱含著控制中國歷史發展的主要力量來自中國社會和傳統之外。事實上并非如此,在西方對中國展開全面進攻之前,中國社會的性質已經在發生變化:激增的人口(18世紀人口從1億5千萬增加到3億)、高漲的物價(在同期內增加了3倍)、經濟日益貨幣化,以及農村社會經濟競爭加劇等現象。據此,他提出了一個與流行看法不同的假設:“西方所沖擊的并不只是一個正在衰亡的朝代,而是一個正在衰亡的文化:這個文化極可能就要從自身內部生成某種社會與政治組織的新形式。”②Philip Alden Kuhn:Rebellion and Its Enemies in Late Imperal China: Militarization and Social Structure, 1796-1864,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0, pp1~2,5~6.芮瑪麗則在《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后抵抗》中反復提到:“阻礙中國成功地適應近代世界的并不是帝國主義侵略、秦朝的統治、官員的愚昧或者一些歷史的偶然事件,而是儒教體制自身各個組成部分”。③Mary Clabaugh 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 New York: Atheneum,1965, pp9~10。中國傳統的價值觀念和制度幾乎完全成了中國經濟近代化的阻力,是必須克服的障礙,而不是助力的源泉。這種對傳統與近代截然兩分的假設對西方了解中國近現代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排斥傳統特征從而對近代社會產生誤解相類似的錯誤判斷低估了傳統社會中潛在的近代因素,人為地在傳統與近代之間制造了一條分析鴻溝。這些評論中都包含一個偏執陳舊的看法,認為中國是一個靜止不變的社會。18世紀末,法國哲學家孔多塞指出:“在這些土地遼闊的帝國中,人類的思維能力陷入了停滯不前的可恥狀態,這些帝國亙古未斷的存在一直使亞洲長期蒙受羞辱”④[法]孔塞多:《人類精神進步史表綱要》,何兆武、何冰譯,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37頁。。此后,黑格爾也指出:“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最古老的國家,但它卻沒有過去,這個國家今天的情況和我們所知道的古代情況是一樣的。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沒有歷史”⑤[德]黑格爾:《歷史哲學》,張作成、車仁維譯,北京出版社,2008年,第88頁。。耐人尋味的是,關于中國社會不變的說法在19世紀前其實就已經流行很廣了,并被推崇備至,但19世紀卻給與了否定的評價,過去的社會穩定變成了如今的停滯不前,上述思想方式曾一度得到中國人自己的大力支持。近年來,學界對傳統與近代的關系進行了重新思考,摒棄了那種各執一端、相互排斥的偏見。史華慈在批判近代—傳統框架時指出:“人類過去的各方面經驗,不論有益有害,都可能繼續存在于現在之中,中國之過去和近代未必就作為互不滲透的整體彼此對抗”。①Benjamin I. Schwartz:History and Culture in the Thought of Joseph Levens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5, pp108~109.張灝在論述梁啟超時提出一個總的看法,即“晚清中國知識分子,主要是從儒教傳統沿襲了一套人們所關切的和存在的問題,從而對西方沖擊做出回應的。”②Hao Chang: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p3.事實上,許多傳統價值概念,如梁啟超的群體主義、晚清改革家與思想家對大同理想的追求,并不是中國近代化的障礙,而是它的推動力。
第三,帝國主義框架。研究19-20世紀中國歷史的美國學者使用“帝國主義”這個詞系從毛澤東的著名論斷“中國近代史是一部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與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③《毛澤東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89頁。得到啟發。西方這種帝國主義分析框架取向不僅掩蓋了帝國主義的罪行,而且對它在中國過去一百多年的歷史作用未能認真對待。時至今日,我們把1840年鴉片戰爭作為中國近現代史的開始,中國從此開始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原因是中國遇到了“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種近代史起點的界定容易在西方對近現代史的作用和影響上誤導人們。事實上,鴉片戰爭的客觀作用并沒有像我們所想象的那么重大。中國地域寬廣,發展極不平衡,各個地方對西方沖擊感受并不明顯,比如沿海與內地在受到西方沖擊下表現迥異,古老的內地依然在按照其固有規律緩慢地向前。王熙認為,帝國主義不只是中國人的主觀想象,它是真實存在的,其影響至關重要。但是這種影響正如中國中心論所強調的那樣,同時也明顯地受到中國內部因素的制約。對中國近代史要完整、準確地理解,必須把這段歷史看成內外因素相互交織、相互作用的產物。④王熙:《研究中國近代史的取向問題—外因、內因或內外因結合》,《歷史研究》,1993年第5期。今天,幾乎所有人都認為帝國主義是不好的,它歪曲了中國經濟、迫使中國處于不發達狀態,客觀上刺激了中國民族主義的崛起。但在經濟領域,有相當數量的經濟學家認為帝國主義所起的作用—無論是好的還是壞的,都是比較有限的,源于中國整個經濟規模龐大,自給自足程度非常高,外國經濟入侵影響始終有限。帝國主義的沖擊主要還是在政治領域和思想領域,最直接是阻礙了中國的國家統一和民族獨立,破壞了中國國家主權,削弱政府領導全國的能力,使中國長期陷入混亂的社會秩序當中。中國人民深受三座大山壓迫,和世界上其他殖民地民眾相比,得到殖民主義的一切壞處,卻沒有得到它的任何好處。因此,對于帝國主義沖擊模式,我們需要清楚沖擊的性質和目標是什么,情況就一目了然。
19世紀中期控制中國的斗爭是一場內部斗爭,外國入侵只是一種地區性行為,多限于東南沿海港口城市。1870年后中國針對西方入侵的起義往往發生在西方人很少、外國經濟活動不多的地區,比如直隸、山東等地的義和團運動。如果義和團運動完全是反帝愛國,是針對西方經濟侵略的后果,是西方沖擊的反應,那么嚴格來說更應該發生在廣東,而不是山東、甚至偏僻的魯西南,那里并沒有外國經濟活動。顯然中國農村經濟情況的惡化才是根本原因—是農村各種社會、經濟、政治因素的相互作用的結果,而反帝和反對基督教則是矛盾激化的導火索。同樣,晚清中國改革盡管受西方影響很大,但本質上是中國歷史改革傳統的一部分。中國改革志士們早在鴉片戰爭之前就開始對西方做出反應,只是到了19世紀70、80年代,西方問題才最后成了頭等大事。現在越來越多的學者把中國19世紀的改革運動看成國內改革傳統的產物,當然很少人會認為西方是無關緊要的,也不否認它后來對中國改革思想和活動產生的塑造作用,但是對于把改革視為西方激發,按照西方方向進行的說法產生了激烈的反對。從來沒有一個西方國家在政治或軍事上完全控制中國(包括20世紀30、40年代的中國),中國基本上還是按照自己的方式繼續有效運行。只有清楚認識中國不是殖民地,而是半殖民地,才能正確理解帝國主義框架分析近代中國。
上述三種思想框架都帶有濃厚的西方中心色彩,剝奪了中國歷史發展道路的自主性。它們共同的觀點是,19-20世紀的中國發生任何重要變化完全是由西方沖擊,中國回應的變化,排除了以中國為中心,從內部觀察現代化道路的一切可能。
二、沖擊—回應模式對道路話語權構建的歷史影響
盡管作為嚴肅的學術分析框架,沖擊—回應模式的鼎盛時期是在五六十年代,但它對教科書和其他大學教學資料影響至今。特別是在今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提出之后,最大的誤導在于這種話語范式在本質上是西方中心論史觀模式,嚴重影響了從中國社會內部總結現代化道路規律的方法論,這種近現代史分析模式需要重新認識。這一模式有許多歪曲事實:如費正清為了說明中國對西方挑戰回應不力,不得不反復使用中國社會的惰性這一說法來勾畫—甚至歪曲丑化這一時期中國與西方世界沒有關聯的側面,諸如中國的政治架構、社會經濟和思想等方面。中國在崛起的過程中,有個門檻必須面對,就是西方話語權,沒有話語權是無法真正崛起的。西方在“軟實力”上針對中國的一個重要方法就是“話語制衡”,即以西方話語為武器,不斷設置各種瓦解中國人心的議題和話語,使中國思想界陷入混亂,不戰而屈人之兵。中國學者要從僵化和偏見的西方話語中解放出來,中國崛起的偉大實踐早已超出了西方話語的解釋能力,需要構建中國自己的話語體系,而不是在學習西方中迷失自我,做西方話語的“傳聲筒”。因此,沖擊—回應模式對道路自信歷史影響的實質是構建中國話語權的問題。
沖擊—回應模式帶來的直接影響是對中國近代史的歷史敘事和誤導。中國的傳統歷史敘述到清朝就突然斷裂了,而以近現代史的面目出現。這個突然的“斷裂”姑且不論是否恰當,而在于這個前提下討論近代史問題,如何處理與傳統的關系。如果說傳統歷史敘事的主題是以政治事件和制度史為特征的話,那么近現代史的標準是什么?這個歷史節點恰恰是帝國主義入侵的1840年鴉片戰爭。關于近現代史敘事線索,史學界眾說紛紜,“革命”模式和“現代化”模式交替出現,給近代史的敘事帶來困惑。“革命”與“現代化”二元對立在于人們理解的狹隘,我們只是把它們視為對西方帝國主義侵略的一種被動反應,而較少思考中國歷史自身發展的脈絡,割斷了歷史的連續性。研究明清史的學者,一般不怎么關注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的探索。這是因為近代史已經在現行學科體制內單獨劃分出來,從教學到研究成為相對對立的單元。近代史討論的主題似乎與明清史無關,最多零散見于外交關系方面—比如明清之際傳教士來華、乾隆年間馬戛爾尼使團來華,為近代史做些鋪墊,從而證明天朝上國閉關自守的盲目自大,落后必然挨打的歷史邏輯。其結果是明清史長期以來討論的問題都被局限在一個傳統社會的框架之內,明清社會如何衰落,新的因素如何受到舊制度阻礙而夭折,這種思維無意間強化了中國近代面臨“三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靠自己已經無法改變,只能依靠外力推動的認知模式。讓我們感到困惑的是,明清、甚至宋元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線索,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就突然消失了嗎?在這種認知模式下,有關現代化道路探索的歷史線索論證極易陷入“沖擊—回應論”的邏輯困境。
中國近現代史是一種復雜的歷史環境,在這種環境中從中國社會內部結構產生的各種巨大的勢力不斷發生作用,為自己開辟前進的道路,盡管外來的影響在不斷加強。19~20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必然繼承了18世紀和更早時期發展過來的社會結構和發展趨向。中國歷史本身的若干重要力量一直在發揮作用:人口壓力的陡然增長和疆域的擴大,農村經濟的商業發展,社會階級矛盾日益加劇等等—此時西方登場了,它制造了種種新的問題—也制造了一個新的歷史情景。因此,盡管中國社會日益受到西方影響,帝國主義發動的歷次侵華戰爭加速了中國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進程,但其內在歷史發展自始至終是一個自然歷程。1800年到1840年的歷史發展主線并完全沒有中斷,也沒有被西方取代,它依然是貫穿19到20世紀的一條最重要的線索,即中國社會演變的動力來自中國內部。這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關于事物發展內外因的觀點。
史學家們在討論“中國回應”時往往過分抽象化而一言蔽之。中國在地理上疆域廣大,在種族、語言和地區上差異甚大,極為復雜。即使每個特定的地區,上層社會人物與人民群眾之間在世界觀和生活方式上都存在著巨大的差別。在這兩大社會階層內部,影響人們的態度和行為的因素也是多種多樣,包括氣質、性格、年齡、性別以及由個人的社會、宗教、經濟和政治關系所形成的特定情況。因此,“中國回應”這個詞只是一個代表錯綜復雜的歷史情景的籠統概括。當然,在某一層次上說,所有中國本土人—男人、女人,城里人、鄉下人,窮人、富人,廣東人、湖南人—都參與一個共同文化體系,這個體系可以統稱為中國文化體系;但是在另一個層次上,這些人的經歷千差萬別。所以當我們把這些回應統稱為中國回應時,我們實際上是把各種現象加起來,再加以平均。這種做法在最好的情況下,只能使我們對歷史現實有一個均勻、單一的理解;由于我們魯莽草率地從特殊上升到一般,就很可能把現實完全歪曲了。①[美]柯文:《在中國發現歷史—中國中心觀在美國的興起》,林同奇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第121~122頁。即使當中國人主張“全盤西化”時,在他們心目中也有一個本來的中國,并不是用西方文明機械地代替中國的社會與文化,而是經過精心挑選、按照他們心目中的西方形象來改造中國。比如胡適,主張采納西方的民主與科學,卻反對采納西方的基督教。因此,中國對西方挑戰回應只是部分地—在有些情況下主要是對本土力量的回應。
沖擊—回應三種思想框架采取的做法各不相同,但實質上都對中國道路話語權的構建產生了巨大影響。沖擊—回應模式主要通過中國對西方沖擊的回應來描繪中國的現實,觀察的角度側重西方沖擊一方,盡管事實并非如此。有時僅僅因為歷史事件和西方入侵沒有聯系,或者只是很少的聯系,便被完全忽視和省略了。近代—傳統模式基本上是沖擊—回應模式的放大,其取向是把中國描繪成停滯不前的“傳統”社會,有待精力充沛的“近代西方”賦予其生命,把它從永恒的沉睡中喚醒。中國就像一頭睡著的“野獸”,西方就像“美人”,經她一吻,千百年的沉睡被打破,她用魔幻般的力量把本來將永被封閉的發展潛力激發出來。西方入侵被美化成了救世主,凡屬重要的歷史變化都被定義為西方自身經歷的近代社會進程,中國面臨的必然是一場敗局。沒有西方,不可想象中國會發生任何近代化的變化;同樣不可想象的是,除了近代化的變化外,還有任何什么變化稱得上重要的歷史變化。至于帝國主義模式則把工業化的對外擴張描繪成一件完全的好事,并且一樣認為中國社會缺乏必要的歷史先決條件,無法獨立產生工業革命,因此得直接或者間接地依靠西方入侵提供這些條件。“屈辱的世紀”對中國人的心理和脆弱感情造成了深刻影響,然而,如果據此就斷言:中國人曾在其他所有種族面前都感到自卑,那就錯了。我們驚奇地發現,雖然中國人在現代歷史中長期受到各種問題的困擾,但他們仍然認為自己是優秀的民族。的確,中國人在遭受挫折的時候曾自卑過,但這個階段相當短暫,中國人很快就恢復了自信。這種民族自豪感為中國人提供了一個心理機制,用來對抗帝國主義的干涉,并使自己的生活顯得不那么糟糕。
隨著中華民族的優越感在19世紀遭受重創,中國人經歷了漫長而痛苦的自我認知過程。培養一種良好的社會心態需要時間,社會發展階段不同,社會心態自然不同。中國正向現代化邁進,歐美已達到后現代化社會。相比較而言,歐美發達國家沒有趕超別人的動機,也沒有怕別人追上的焦慮。事實上,歐美這種原發式現代化國家,在現代化進程中,從來都沒有過追趕的焦慮心態。社會學家費孝通最早意識到社會心態危機,他在1993年香港中文大學作題為《中國城鄉道路發展》的演講時,首次提出在對生態秩序研究之外,社會學應該研究社會心態秩序。他當時提出,中國人能否做到“安其所,遂其生”,良好的社會心態是一種成熟自信,是對國家未來發展的一種信念。然而,無論是積極還是消極的,中國人始終深處社會急劇的變化場景之中,心態起伏較大,價值觀和社會心理判斷始終處于新奇之中,直到2000年以后,中國人的價值觀和社會心態沒有再出現新中國前50年中出現過的大起大落,社會心理承受力進一步提高,中國社會心態趨于穩健從容。人們不再固執于某一個極端,既不會固守理想而無視現實,也不會屈從現實而放棄理想,他們會在兩者之間尋求某種平衡,道路自信與道路話語權正是建立在這種成熟穩定的社會心態之上。
三、破除沖擊—回應模式,重新認識中國
第一,“重新認識中國”并不是要完全從中國自身出發,更不是要回到過去,而是重新認識西方以及西方與中國的關系。因為,正是我們對西方認識發生了偏差,所以才要重新認識中國。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告訴我們,自身認識主體性的淪喪及話語權的失落,固然有雙方實力的對比,更源自我們自身理解世界方式的改變。這是近代認識中國的一個特征,無論你愿意與否,一直伴隨著我們,我們生活世界的意義與價值似乎只能通過西方的認識框架才能獲得自我表述,西方由外在生成我們的內在組成。當自我變成他人,對自己的認知就需要他人的參考。我們無法跳出世界歷史的語境,以本質主義的方式構建一個自我的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如果無法察覺這個前提,所有的反思只是在西方中心論框架下的重復和糾纏,“重新認識中國”要以一個不亢不卑的姿態認識西方。晚清以來,中國對西方的態度從漠視、抗拒、接納、擁抱、崇拜到自信,這一復雜的心理歷程深刻反映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通往現代化道路上的探索、迷茫到自信。通過自我批判與否定,向西方學習與模仿,在這個過程中,以他人代替本我的悖論式本末倒置,喪失了主體性。因此,“重新認識中國”問題不在于西方,而在于我們自己認識到與西方互動的錯誤。盡管西方現代化道路充滿著全球化擴張,但它就在那里,按照自身的邏輯和規律發展與演變,本身并無對錯好壞之分,關鍵還是我們在學習中喪失了自我。
近代以來,西班牙、葡萄牙、英國、法國等西方國家通過長期海外殖民侵略,建立了外海殖民地。在征服殖民地過程中,西方文化展現出了排他、攻擊、侵略、屠殺、歧視、奴役的殖民特性,客觀地說,“西方中心論”是伴隨著西方國家海外侵略與全球霸權形成的。“西方中心論”的實質是西方通過殖民化全球化以后逐步形成的一種優等心理,是對人類文明、文化和歷史的誤解。在“西方中心論”看來,西方是世界的中心,西方文明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文明,優于非西方文明。人類的歷史圍繞西方文明和文化展開,西方文明和文化特征或價值具有普世意義,代表著非西方國家和民族的未來發展方向,世界各國現代化道路只有一條,西方道路就是世界道路,“現代化等同于西方化”,非西方國家和民族現代化道路只能遵從西方標準。自1978以來,中國幾乎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經濟增長和削減貧困,沒有時間去思考一個現代中國將如何呈現。事實上,非西方世界崛起所涉及的不僅僅是經濟、政治、文化的深刻變化,還需要重塑人們的認知結構。了解現代中國的根本在于真正認識中國,而不是遵循西方的認知結構。西方經驗的狹隘性和由此導致的非代表性,通常容易被人們所忽視,而這正是過去200多年西方國家享有的主導優勢。隨著那些異于西方文化、歷史和文明遺產的國家的現代化啟動,西方經驗的局限性就越來越明顯。中國的崛起將改變這一切,在這個“現代性競爭”時代,中國將引領世界。中國作為“文明型國家”的崛起,具有超強的歷史和文明底蘊,不會跟著別人亦步亦趨,不會照搬西方或者其他模式,它只會沿著自己特有的軌跡和邏輯繼續演變和發展;這種“文明型國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長處而不是失去自我,并對世界文明做出原創性貢獻,因為它本身是不斷產生新坐標的內源性主體文明①張維為:《中國震撼—一個“文明型國家”的崛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第2頁。。
第二,“重新認識中國”還需要處理好與中國傳統的關系。當代中國人缺乏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足夠自信,即現代化進程中道路自信遭遇危機。根本原因在于近代以來中國現代化曲折過程中,道路探索遭遇了一次次挫折,在應對這種危機的過程中,對中國傳統解構有余,建構不足。我們總是批判過去,認為傳統與現代絕對對立。事實上,這是“后發式現代化”國家都會面臨的難題。這需要我們在現代化道路自信構建過程中,正確處理與中國傳統的關系。墨子刻在《擺脫困境》中指出,只要學者們一心只想解釋中國在近代的種種失敗,則對傳統中國社會停滯不前的固有看法勢必會持續下去。隨著中國的成就超過它的失敗,就需要有一種新的解釋,其基礎是對中國傳統做出與過去迥然不同的理解。②Thomas A: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fucianism and China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7, p197.
站在21世紀的第二個十年看近代以來最大的變化,是中國社會,包括中國知識分子和普通民眾對中國傳統文明態度的根本性改變,這在上世紀是不可想象的。中國道路問題的討論,一定要和中華文明的整體性重新認識聯系起來,在這個基礎上,討論中國現代化道路問題。如果不抓住人們心理的這個最大變化、不抓住對中華文明的重新認同,就是沒有抓住當前現代化道路最大的問題,即道路自信問題。對整個中華文明傳統的拒絕是晚清以來最大的潮流,這個思潮一直到現在才開始根本扭轉,這就是自信的恢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思想提出的現實意義。十九大報告文末,習近平總書記講到,“站立在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吮吸著五千多年中華民族漫長奮斗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十三億多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無比廣闊的時代舞臺,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③習近平:《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的講話》,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7頁。自此,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自信思想形成。對中華文明在人類文明史中的歷史地位進行正確的定論,關系到中華民族的精神源動力進而關系到人類文明的根本走向這樣的大問題。我們今天對自己偉大民族和文明的認識仍停留在“四大文明古國”、“四大發明”這一基本定式上,就是這一基本認識也被強大的思想誤流湮滅得有蹤無影,從而形成了一種對中華文明莫大的誤會:是中華傳統文明,特別是2000多年的封建社會阻礙著中國近代的發展、阻礙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幾千年民族輝煌的表層被一百多年來的民族恥辱銹化得斑駁陸離。
近代以來,最大的不自信還不是來自文化,而是對道路的不自信。近代國勢雖已跌入積貧積弱的狀態,但文化狀況并不能與經濟政治簡單比附,而是各有千秋。在道路選擇不停試錯、選擇過程中,中國人的思想經歷了歷史上最為劇烈的變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一個先進外來文明即所謂的西方文明的進入,并構成了對中國傳統的強烈沖擊。因此,在中國討論現代化道路,就必須處理好與西方的關系,不談中西關系,便無法面對中國現代化的選擇。與此同時,不討論傳統與現代的關系,也無法實現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要處理兩個關系,中西關系和傳統與現代的關系。從魏源“師夷長技以制夷”、洋務派的“中體西用”、嚴復的“西學第一”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都是在處理這兩對關系的復雜矛盾中選擇前行,中國的現代化道路融合了西方及傳統的優點。中西文明的融合,絕不是兩種文明的簡單融合,更不是把西方文明照搬到中國來。中華文明的現代化,既是對中國優秀傳統文明的繼承與更新,也是對外來現代化精華的采納與再創造。
綜上所述,在走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我們需要學習近代以來的歷史,正確認識中國與傳統及西方的兩對關系,從思想和理論上徹底走出“西方中心論”史觀的誤區,清醒認識在這種思想觀和歷史觀支配下所形成的長期以來對中華文明的藐視與輕描淡寫,深刻反省我們對自己偉大文明的漫不經心或冷嘲熱諷甚至是歷史虛無主義的錯誤態度,克服沖擊—回應認識論,從中國社會內部發展規律研究現代化道路,這是當代道路自信構建深刻的歷史原因。十九大報告明確提出“四個自信”為我們構建道路話語權提供了理論依據,中國學者要增強學術研究的自覺,在中國發現歷史,構建道路話語權,堅定道路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