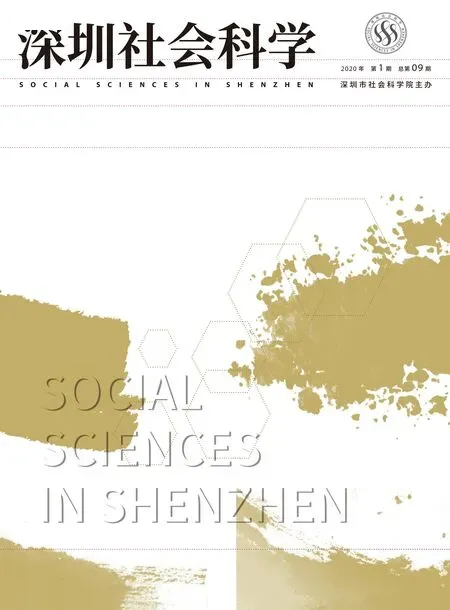保護的責任:演進邏輯、法律性質及中國的立場
堵一楠
引 言
人道主義干預(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是晚近國際法中一個備受爭議的問題。21世紀以來,“保護的責任”概念開始受到世界性的關注,并以罕見的速度完成了從產生到實踐的發展。雖然各國仍然存在較大分歧,但作為全球治理的重要探索,“保護的責任”已然不可避免地被納入了國際法規范的相關論辯之中。本文將大體按照以下順序展開:首先,梳理“保護的責任”生成和沿革的理路,揭示其在言辭和行動層面境遇不同的現實;其次,在與傳統“人道主義干預”理念相比較的基礎上,考察“保護的責任”作為一種正當性話語(discourse)的內在演化邏輯;再次,從國際法淵源的角度切入,嘗試對“保護的責任”的法律性質加以分析,并反思其在聯合國框架下的路徑困境和突破可能;最后,歸納中國對于“保護的責任”的立場,以及在干預規范變革進程中的應對。
一、發展歷程
2001年12月,由加拿大政府提議成立的“干預與國家主權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n Intervention and State Sovereignty,以下稱ICISS)向聯合國提交了《保護的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報告,首次正式提出了這一概念:主權國家有保護本國公民免遭大規模屠殺、強奸、饑餓等災難的責任;在當事國不愿或無力履行,以及其本身為罪犯的情況下,必須由國際社會來承擔這一責任。這是對主權的幫助而非限制。此外,報告還從“預防的責任”、“反應的責任”和“重建的責任”3部分對“保護的責任”的具體內涵進行了闡釋。①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2001, pp.13-17.
“保護的責任”被提出后,很快進入了聯合國的政治議程。②UN General Assembly, A More Secure World: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A/59/565),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 p.56, para.201;In Larger Freedom:Towards Development, Security and Human Rights for All(A/59/2005),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2005年10月,第60屆聯大通過了世界首腦會議《成果文件》,作為“每個國家保護全部人類(populations)的集體國際責任(collectiv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保護的責任”被寫入了其第4部分。這是聯合國第1次以正式文件的形式對“保護的責任”加以框定,標志著該概念獲得了絕大部分國家的接受。文件最終將“保護的責任”的適用范圍嚴格限定在種族滅絕、戰爭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類罪這4項罪行;并強調根據《聯合國憲章》通過安全理事會處理,實際上否定了聯合國框架外的強制性干預行動。③UN General Assembly, 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A/RES/60/1), p.30, paras.138-139.
此后,“保護的責任”得到了聯合國層面的持續推進,并逐漸從政治話語轉向具體實踐。2007年5月,聯合國將“防止滅絕種族”特別顧問的頭銜名稱改為“防止滅絕種族和大規模暴行”,“使其職能范圍更廣”。④UN Security Council, Letter dated 31 August 2007 from the Secretary-General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UN Doc.S/2007/721 (2007).2008年2月,聯合國進而專設“保護的責任”特別顧問一職。⑤UN 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 Secretary-General appoints Edward C.Luck of United States Special Adviser, UN Doc.SG/A/1120 (2008).2009年1月,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Ban Ki-moon)向第63屆聯大提交了《履行保護的責任》(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報告,提出了“保護的責任”的三大支柱:國家的保護責任;國際援助和能力建設;及時果斷的反應。⑥UN General Assembly,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A/63/677),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2.當年9月,聯大通過了有關該概念的第1個專門決議。⑦UN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adopted by the General Assembly on 14 September 2009 (A/ RES/63/308).
然而,2011年發生的利比亞危機成為了“保護的責任”發展的轉折點。安理會在第1970號決議中明確引用“保護的責任”⑧UN Security Council,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6491st meeting on 26 February 2011 (S/RES/1970), p.2.,后又通過第1973號決議授權成員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護利比亞平民”⑨UN Security Council, Adopted by the Security Council at its 6498th meeting on 17 March 2011(S/RES/1973), p.3.。此次實踐的過程和后果都引起了極大爭議—北約據此展開的軍事行動直接造成了利比亞的政權更迭,導致聯合國在敘利亞問題的審議上陷入了僵局。從此,“保護的責任”開始在言辭和行動的維度上呈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面向:
首先,“保護的責任”在國際話語體系中的上升趨勢并未因此被顛覆,反而可以說已經完全收獲了觀念競爭的勝利。2015年9月,在聯大為“保護的責任”舉行的互動對話中,來自89個國家的代表以壓倒性多數向“三大支柱”基本框架的有效性表示了支持。①“Summary of the Seventh Informal InteractiveDialogue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Global Centre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08 September 2015.國際社會已不再爭論“保護的責任”存在與否,而是開始關注其具體的落實過程。這與“人道主義干預”在過去受到的普遍批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然而,“保護的責任”的實施卻遲遲無法取得更大的進展。這一反差在安理會層面表現得尤為突出:截至2019年4月1日,為了應對馬里、南蘇丹和中非共和國等地的情勢,安理會已經在多達81項決議中直接提及了“保護的責任”,而其中只有4次出現在利比亞危機發生之前。但是,后來決議的相關內容幾乎完全以第一支柱為主,更未再授權任何的武力干預。②“R2P References in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s and Presidential Statements”, Global Centre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01 April 2019.可見,對于“保護的責任”在整體意義上的實施,安理會抱有的支持立場無疑是有限的。“保護的責任”目前的處境正表明了建立普遍性人權機制的復雜與艱難。下面,本文將通過考察“保護的責任”的演化動因,探討國際社會為何在話語層面拒絕“人道主義干預”理念卻接受“保護的責任”的緣由。
二、演化動因
人道主義干預對自身正當性的證成困境是“保護的責任”產生與發展的直接動因。通過對思想史譜系的考察我們可以發現,雖然早在17世紀,人權就已經作為干預的理由開始出現在學者的討論之中,但直到冷戰時期,人道主義還未能在國際法層面構成使用武力的重要依據。③H.Lauterpacht,“The Grotian Tradition in International Law”, British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23, 1946;John Stuart Mill,“A Few Words on Non-intervention”, in Gertrude Himmelfarb (ed.), Essays on Politics and Culture, Gloucester:Peter Smith Publisher, 1963, pp.368-384;Hedley Bull,“The State’s Positive Role in World Affairs”, Daedalus, 4, 1979.這一現象在20世紀90年代之后發生了明顯的變化。④Michael Walzer, 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4th edition, New York:Basic Books, 2006, p.108;Gareth Evan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An Idea Whose Time Has Come and Gon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3, 2008.兩極格局的崩塌使得以往為意識形態斗爭所掩蓋的民族問題與宗教矛盾開始凸顯。國際安全形勢的新特征,首先表現為沖突由國與國之間向一國內部轉移。⑤Peter Wallensteen & Margareta Sollenberg,“Armed Conflict, 1989-2000”,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5, 2001.盧旺達和南斯拉夫的大屠殺引發了國際社會的深刻反思:對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不僅限于國際戰爭和武裝沖突,還應包括大規模的人道災難。全面的和平與安全概念(comprehensive concept of peace and security)得到了發展。⑥[奧]諾瓦克:《國際人權制度導論》,柳華文譯,孫世彥校,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39頁。隨著全球化的不斷加深,各國關聯程度的空前加強,放大了全人類的共性—人權的保護開始成為國際社會的重要關切,甚至被稱為“世界范圍內的世俗宗教”⑦Elie Wiesel, “A Tribute to Human Rights”, in Yael Danieli, et al.(eds.), The 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Fifty Years and Beyond, New York:Baywood Publishing, 1999, p.3.。2000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Kofi Annan)在《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s)報告中指出:主權和人權都是必須支持的原則;但如果將人道主義干預視作是一種對主權而言不可接受的攻擊,那么聯合國勢必無法對系統侵犯人權的事件作出處理。①Kofi Annan, We the Peoples:The role of the United N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New York:United NationsDepartment of Public Information,2000, p.48.在此,國家對人權的保護不再僅僅是對公民的義務,而是構成了“國家和國際共同體之間的社會契約”,國家根據此種承諾“換取國際社會對其主權的尊重”。②Anne Peters, “Humanity as the Α and Ω of Sovereignty”, The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 2009.
然而,國際人權法的上空,卻始終盤旋著霸權的陰影。東歐劇變后,以自由主義為核心的公民認同(civic identity)成為了美國主導下當代國際秩序的基石。其強大的觀念力量(the power of ideas),甚至超越了民族國家的意識。③王逸舟:《西方國際政治學:歷史與理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第345~348頁。文森特(R.J.Vincent)指出:人權改變了過去“國家主權的國內正當性與國際正當性無關”的觀點。如果一國的政府未能向其公民提供基本權利,則構成被視為非正當(illegitimate)的理由。④R.J.Vincent, Human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127.在此背景下,人道主義干預成為了西方世界單方面推行其“文明標準”的重要途徑。⑤Jack Donnelly, “Human Rights:A New Standard of Civilization?”, International Affairs, 1, 1998.由此,在以下兩個方面違背了國家主權平等這一國際社會的基礎性事實:首先,傳統的“人道主義干預”理念,在思想淵源上,直接發端于庫什內(Bernard Kouchner)和貝塔蒂(Mario Bettati)于1987 年提出的“干預的權利”(right to intervene)主張。⑥Mario Bettati & Bernard Kouchner (eds.), Le devoir d’ingérence, Paris:Deno?l, 1987, p.300.據此,保護人權的道德被視作是先驗的(a prior),并進而產生了更為強有力的要求:向國際法訴諸一種權利的承認。這一邏輯在本質上僅僅是單向的,目標國的主權在其中只處于從屬的客體地位。其次,傳統的“人道主義干預”理念從未為自身設定包括主體、條件、方式等必要的規范性內容。在實踐中,這導致了人道主義干預往往異化為大國追求自身利益的借口;在理論上,則使得任何通過“人權”對國家概念進行普遍化的主張,必然體現為將己方的政治想象強加給其他歷史傳統,結果只能是對各國的政府形式進行善/惡的劃分。因此,作為控制和偏見的代名詞,“人道主義干預”理念最終止步于一項政治修辭。
然而,國際社會迫切需要共同規范對國家的人權保護加以評價的現實,亟待理論作出回應:于是,“主權作為責任”(Sovereignty as Responsibility)⑦Francis M.Deng, Protecting the Dispossessed: A Challenge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ashington, D.C.: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93, p.14.的思想應運而生,成為了今日“保護的責任”的雛形。在聯合國的積極推動下,這一概念正不斷豐富和清晰。為了彌合人權與主權之間的尖銳對立,從而盡可能獲得更多國家的認同,“保護的責任”在以下兩個方面對傳統的“人道主義干預”理念進行了修正:
(一)主權的定位 不同于傳統的“人道主義干預”理念,“保護的責任”從一開始就從目標國的視角出發,對主權給予了特殊的關注。2001年《保護的責任》報告已經明確指出:主權不僅僅是國際關系的一種功能性原則,還是對(眾多國家和人民)同等價值和尊嚴的承認、獨特身份和自由的保護、塑造和決定自己命運之權利的肯定。⑧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2001, p.7.2009年《履行保護的責任》報告再次強調,即使一國因能力不足或缺乏領土控制無法充分履行保護,而由國際社會提供幫助時,也仍然是“保護的責任”的基本主體。①UN General Assembly,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A/63/677),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10.2014年《履行我們的集體責任》(Fulfilling our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報告重申,“保護的責任”旨在加強(reinforce)而非損抑(undermine)主權。其目的是以《憲章》第2條為基礎,鼓勵各國平等展開合作使人類免遭暴行,無意為國際社會建立等級結構。②UN General Assembly, Fulfilling Our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International Assistance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68/947),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4.相比于人道主義干預,“保護的責任”再次確認了國家主權在全球人權治理中的首要(first and foremost)地位。因為對人民更有效的保護始終只能來源于國家,國際社會的作用只是補充性的,各國之間互相尊重彼此的主權就成為了人權價值的應有之義。
(二)規范的程度 傳統的“人道主義干預”理念十分空泛,而“保護的責任”從被提出之初,設計者就力求使其內容兼具廣度與深度。2001年《保護的責任》報告從預防、反應、重建3個層面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全方位的立體建構,并明確:武力干預只適用于非常嚴峻的情況,必須為其設定苛刻的觸發條件(trigger conditions must be high),從而提出了6條清晰的標準:正確的授權(right authority)、正當的理由(just cause)、正確的意圖(right intention)、最后的手段(last resort)、相稱的方式(proportional means)、合理的預期(reasonable prospects)。其中,至關重要的授權問題,報告更是選擇在第6部分專辟一章進行了討論。③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2001, pp.29-37.而2005年的世界首腦會議進一步對“保護的責任”加以細化,“正當理由”僅限于種族滅絕、戰爭罪、族裔清洗和危害人類罪的發生,并強調了聯合國系統的框定性作用。人道主義干預僅僅關注對已經發生的事件采取行動,而“保護的責任”始終強調,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以預防此類災難,并通過后續的建設確保其不會在未來重演。人道主義干預往往以使用武力作為唯一的手段,而“保護的責任”一再指出,面對預防失敗或必須作出反應的情況,作為優先選擇的,是一系列外交、政治、經濟層面的非軍事性解決辦法。即使涉及武力,也可以通過目標國政府的邀請,以第二支柱的方式進行。④Gareth Evans, “R2P:The Next Ten Years”, in Alex Bellamy & Tim Dunne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923-925.
通過上述變化,“保護的責任”收獲了人道主義干預未能取得的成功:首先,國際社會普遍承認了這一正當性話語的存在;不僅于此,從由非政府組織提出,再到被聯大和安理會頻繁援引,“保護的責任”一直行進在從概念到規則的制度化道路上,所朝向的最終目標,是融入甚至變革現行的國際法體系。早在2004年,“威脅、挑戰和改革問題高級別小組”向時任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提交的《一個更安全的世界》(A More Secure World)報告已經表示,希望“保護的責任”成為一項“新興的規范”(emerging norm)。⑤UN General Assembly, A More Secure World:Our Shared Responsibility(A/59/565), Report of the High-Level Panel on Threats, Challenges and Change, p.57, para.202.“保護的責任”是在人道主義干預無法獲得認可的情況下而形成的。這一概念的提出并不是孤立或偶然的事件,而是20世紀以來國際法人本化現象的邏輯必然和重要反映。在這個意義上,作為人道主義干預的延續,“保護的責任”與前者分享著共同的普世性道德觀念:人權不再僅僅是一個和主權相對應的、或是從外在限制主權的概念,而是構成了主權正當性的內部基礎。⑥陳一峰:《后冷戰時代的不干涉內政原則—西方新于涉主義理論及其批判》,《中國國際法年刊2011》,世界知識出版社,2012年,第107頁。在人類文明日益多元化的今天,主權的解釋進路當然不應如此片面。但必須承認,當前的國際社會,仍然是以西方的秩序想象為原型而展開的,人權作為主流價值依舊會是未來一段時間內的趨勢。對此,有學者指出,在聯合國仍然無法以人道名義超越國家利益的歷史時刻,“保護的責任”卻已經進入了國際規范的萬神殿(Pan-theon)。①Mark B.Taylor, “Humanitarianism or Counter-Insurgency? R2P at the Crossroads”, International Journal, 1, 2005.這固然有其夸大之處,但面對救助國內流離失所者的國際法困境,各國難以對人道主義干預之必要性一概加以否定也是客觀的事實。下面,本文將從國際法淵源的角度,對“保護的責任”的法律性質進行分析。
三、法律性質
目前,學界關于“保護的責任”的法律性質還存在各種觀點。②Carsten Stah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Political Rhetoric or Emerging Legal Nor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2007;Aidan Hehi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 Philip Cunliffe (ed.),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Interrog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Routledge, 2011, pp.84-85.而《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第1款作為權威說明,列舉了彼此之間并無等級次序的條約、習慣和一般法律原則作為國際法的主要淵源,以及司法判例和權威學說作為確定法律原則的補助資料。因此,下文將主要在條約、習慣和一般法律原則三個層面進行討論,并兼采有關司法實踐,嘗試認定“保護的責任”的國際法地位。
(一)條約作為“保護的責任”的國際法淵源 首先,作為迄今為止最重要的國際性條約,《憲章》在序言等多處闡明了保護人權的宗旨和路徑,例如,第4章“大會”第13條第1款規定,聯大“應發動研究,并作成建議”,“助成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實現”;第9章“國際經濟與社會合作”中的第55條與第56條明確規定,聯合國應促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普遍尊重與遵守,不分種族、性別、語言或宗教”,且“各會員國擔允(pledge)采取共同及個別行動與本組織合作”以達成之;第10章“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第62條第2款指出,理事會“為增進全體人類之人權及基本自由之尊重及維護起見,得作成建議案”,等等。但是,在規范性問題上,學界還存在很大的爭議。《憲章》中的人權條款是否對成員國意味著實質性的法律義務,抑或僅僅是政治宣示?聯合國機構是否據此取得了針對成員國采取行動的權利?此種行動的性質和程度為何?對此,各種觀點莫衷一是。凱爾森(Hans Kelsen)認為《憲章》并沒有為成員國確立嚴格的國際法義務,人權條款毋寧是原則性的宣告。③Hans Kelsen, The Law of the United Nations:A Critical Analysis of its Fundamental Problems, New York:Praeger, 1950, pp.29-32.勞特派特(H.Lauterpacht)則認為,一項規則的法律性由于缺乏定義而受到不利影響與因此被消滅是不同的。《憲章》中并未明確規定成員國保護人權確實減損了這些義務的可司法性(juridical character),但并未對其法律本質(legal nature)造成致命的損害。④H.Lauterpacht, “The International Protection of Human Rights”, Recueil des cours, 70, 1949.
在其他專門性的人權條約中,似乎也能尋找到相關的法律依據。例如,《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1條規定,各國應確認滅絕種族行為“系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承允防止并懲治之”。而這正是“保護的責任”概念的一部分。1993年,波黑根據《滅絕種族罪公約》第9條向國際法院遞交了起訴南聯邦的請求書。2007年,國際法院在最終判決時,對該項義務作出了解釋。法院認為,在斯雷布列尼察(Srebrenica)發生的事件符合《滅絕種族罪公約》第2條所設想的滅絕種族罪,雖然無法確定其后果可歸因于南斯拉夫,但《滅絕種族罪公約》設定的義務是:主權國家被要求采取一切合理手段去防止種族滅絕。此義務先于《滅絕種族罪公約》第3條所禁止的行為而存在,并在實際犯罪開始的同時生效。法院甚至指出,這一義務的范圍取決于影響犯罪者行為的能力,這可以通過各國間的地理和政治聯系來衡量。①ICJ, Application of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Bosnia and Herzegovina v.Serbia and Montenegro), Judgment, I.C.J.Reports 2007, pp.215-221, §415,§430,§431,§438.有反對觀點認為,對于特定情形下可能的行動主體,只應形成一種合理的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②Jennifer Welsh & Maria Banda,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Clarifying or Expanding States’Responsibilities?”,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3, 2010.但判決顯然意在說明,即使滅種行為發生在一國管轄地域范圍之外,且本身并未參與實施,其所負有的防止義務卻不因此而消失,而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通常而言,條約僅對締約國具有效力。然而,該解釋還可能產生進一步的影響:聯大在1946年通過決議認為,《滅絕種族罪公約》的理念受到了所有文明國家的承認,因此構成了國際法的基本原則。③The Crime of Genocide, UN Doc.A/RES/96 (I) ,1946.國際法院也確認,《滅絕種族罪公約》區別于一般的多邊條約而具有普遍性,對非締約國和國際組織都有約束力。④Reservations to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evention and Punishment of the Crime of Genocide,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orts 1951, p.29.
此外,“保護的責任”也在國際人道法中得到了體現。二戰后,日內瓦四公約對武裝沖突的國際法規與慣例進行了系統性的編纂,在紐倫堡和東京分別設立的國際軍事法庭則使得審判戰爭罪行成為了現實。此前,相對于有關國際性武裝沖突的大量文件,只有日內瓦四公約的共同第3條及第2附加議定書對非國際性武裝沖突作出了規定。隨著國際法的價值重心進一步從國家轉移到個人,《前南國際法庭規約》在第2條明確指出其“有權起訴犯下或命令他人犯下嚴重違反1949年各項《日內瓦公約》的情事”,之后法庭在“塔迪奇案”(The Tadic case)中確認,武裝沖突的性質不對管轄權產生影響。⑤ICTY, Decision on the Defence Motion for Interlocutory Appeal on Jurisdiction, UN Doc.IT-94-1-A R72, para.70.1998年,《國際刑事法院羅馬規約》正式確定了戰爭罪等4項國際罪行,其中第7條將“危害人類罪”的前提設立為“針對任何平民人口進行的攻擊”,說明具體的反人道行為可以不必發生在國際性武裝沖突中,甚至連和平狀態下的事件也被包括在內。雖仍有爭議,但這標志著國際社會的最低共識在緩慢地形成。正如國際法院所說,人道主義法的許多規則……所有國家都必須遵守,而無論其是否批準了載有這些規則的公約。⑥Legality of Use or Threat of Nuclear Weapons,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orts 1996, p.257,§79.不可忽視的是,國際法委員會(ILC)的《國家對國際不法行為的責任條款》草案在第2部分的第3章引入了“嚴重違反依一般國際法強制性規范所承擔的義務”,其中第41條強調各國應通過合作制止此類行為。可以看到,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在某種程度上,國際人道法的規范已經逐漸獲得了強行法(jus cogens)的地位。在此,或許的確有理由從中推斷出一國對國際罪行作出反應的義務。當然,此處的討論仍失于空洞,我們依然需要從習慣國際法的角度去探討各國對“保護的責任”的具體態度。
(二)習慣國際法作為“保護的責任”的國際法淵源 習慣國際法主要由國家實踐和法律確信2個因素組成。傳統方法側重對國家實踐的考察。《國際法院規約》第38條對習慣國際法的定義是:國際習慣,作為通例之證明而經接受為法律者。顯然,從字面意思來看,二者之間應存在先后關系。然而在“尼加拉瓜案”(The Nicaragua Case)中,國際法院在證明不干涉原則的習慣國際法性質之時,雖然申明“自己的任務是判斷法律確信中存在的規則是否得到了實踐的確認”,①Military and Paramilitary Activities in and against Nicaragua (Nicaragua v.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Merits, Judgment, I.C.J Reports 1986, p.98, para.184.但在先通過國際文件論證了國際社會對不干涉原則的法律確信之后,卻沒有考察正面的國家實踐,而是指出相反的實踐無法體現行為國的法律確信,因此未具備造法效力,不可作為例外。這一做法發展了習慣國際法的方法和理論。此外,隨著現代世界的交往日益便捷,在海洋、外空等領域,由于許多國家的迅速承認,某些習慣國際法在短時間內得以形成。鄭斌(Bin Cheng)稱之為“即時習慣國際法”,認為其產生側重于“法律確信”而非“常例”(usus)。②Bin Cheng, “United Nations Resolutions on Outer Space:‘Instant’ International Customary Law?”, Ind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5, 1965.因為“保護的責任”少有實踐,下文也將主要討論聯合國議程中各國的立場。
2005年,“保護的責任”明文載入了有190多名國家和政府領導人參加的世界首腦會議《成果文件》。有論者據此認為,“保護的責任”享有了“即時習慣國際法”的地位。③Christopher Verlag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Tübingen:Mohr Siebeck, 2009, p.115.然而,一致通過本身并不能證明任何法律事實:首先,《憲章》賦予聯大的僅僅是建議權,其決議不具備約束力;其次,并無任何正式的國際法律文件規定國家間的合意能夠直接成為國際法的淵源。《成果文件》的語詞相當模糊,未能進一步確定采取軍事措施的標準,而只是提及應交由安理會逐案決定。同時,相比于2001年的報告,“保護的責任”的適用范圍被顯著縮小了,繞過安理會的嘗試也被刪去。雖然上述種種可以表明國際社會正產生“法律確信”的萌芽,但是,《成果文件》的出臺僅應被視為一項政治宣言:各國有意向接受“保護的責任”,與接受相關國際法的規制,毫無疑問是兩回事。在此期間,美國的態度較為典型。會議前,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作為時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始終呼吁對擬通過的《成果文件》進行重新起草。他強調,《憲章》從未被解釋為創設了安理會成員在國際和平遭受嚴重破壞的情況下強制采取行動的法律義務—在本國主權之外,國際社會和安理會在法律上沒有義務去保護危險中的平民。最終,他成功要求修改了文件第139段的措辭,用更具道德感的“責任”(responsibility)取代了法律意味濃重的“義務”(obligation)。④Letter from John R.Bolton,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o the United Nations, to President Ping, President of the UN General Assembly, 30 August 2005.
此后,國際社會對這一概念如何履行的問題進行了激烈的公開辯論。2009年7月,第63屆聯大召開了關于《履行保護的責任》報告的辯論會,代表180個會員國和2個觀察員代表團的94名發言人闡述了本方的意見和關切。懷疑仍然是存在的,大會主席德斯科托·布羅克曼(Miguel d’Escoto Brockmann)在開幕致辭中告誡,在確立干預的一般國際責任之前,必須先解決其他問題,特別是欠發達地區人民的生活狀況,以及安理會機制的內在缺陷。⑤UN General Assembly, Sixty-third Session Official Records, 97th Plenary Meeting (A/63/PV.97), p.3.也有部分國家擔憂“保護的責任”在實施中會出現雙重標準,從而導致其被大國濫用,成為霸權的工具。但總體而言,大會對“保護的責任”概念表現出積極的反應,絕大多數與會國家贊同秘書長的報告,非盟尤其表示了歡迎。此外,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國也抱支持的立場,美、中、俄等大部分國家都以相對溫和的姿態有保留地接受了“保護的責任”概念。只有古巴、委內瑞拉、蘇丹和尼加拉瓜四國完全拒絕此前的《成果文件》。三類立場表明,各國在聯合國框架下對“保護的責任”進行的首次正式專題討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然而,這一趨勢在利比亞危機后不復存在。各國的態度都十分復雜,并不可以簡單地視之為“南北分歧”。①Ramesh Thakur, “Emerging Power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fter Libya”, Norwegia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 Policy Brief, 15, 2012, p.2.雖然國際話語的變化或許的確有利于解讀“保護的責任”的法律確信,但事實上,安理會決議對援引這一概念的淺嘗輒止再次證明了使用武力領域的高度敏感性—僅就當前而言,“保護的責任”的習慣國際法地位是不足的。
(三)一般法律原則作為“保護的責任”的國際法淵源 馬爾科姆·肖(Malcolm N.Shaw)指出,關于一般法律原則的含義,大致有三類見解。第一種觀點認為,自然法是檢驗實證國際規則有效性的依據,因此一般法律原則是對自然法概念的引申。第二種觀點則認為,一般法律原則重申了國際法基本原則,必須以國家的同意為基礎,視其為條約和習慣的副標題(sub-heading),應在二者中已有所規定。童金(Tunkin)等蘇聯學者多持此說。第三種觀點贊同一般法律原則確實是單獨的國際法淵源,但范圍相當有限,內容也十分模糊,或許稱之為“適用于國際關系的國內法原則”比較恰當,是貫穿各國法律秩序中的共同主題。②Malcolm N.Shaw, International Law, 8th edition,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p.370-371.王鐵崖贊同最后一種主張,認為一般法律原則是各國法律體系所共有的原則。③王鐵崖主編:《國際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第11~12頁。一般而言,此種價值判斷首先應為各國的法律所當然蘊含,但本身并不在國際層面具有拘束力,而需要國際法的立法機制將其接受為法律規范。這為一般法律原則的確認設立了遞進式的兩個條件。
從國內法的角度來看,當今世界,絕大部分國家都在本國憲法和法律中規定或暗含了對人權的保障。但其中,規定對他國的人權事件作出反應的內容,無疑十分罕見。有學者提出,一般法律原則的形成不再局限于國內法律(foro domestico),只需國家作出意思表示即可。在此,國內法的實踐不再是構成性的。④Bruno Simma & Philip Alston, “The Sources of Human Rights Law:Custom, Jus Cogens, And General Principles”, Australian Yearbook of International Law, 12, 1992.也有觀點認為,通過外交代表的聲明、聯大或安理會的決議、甚至是國際法院的判決,都可從中辨識出國際社會的共識,以此提煉一般法律原則。⑤Nadja Kunadt,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s a General Principle of International Law”, Anuario Mexicano de Derecho Internacional, XI, 2011.在這個意義上,國際人道法的地位將得到提升—國際法院在“科孚海峽案”(Corfu Channel Case)和“威脅或使用核武器的合法性”(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s)咨詢意見等場合中多次強調將人道主義的基本觀念納入國際法的一般原則,甚至逐漸將其作為對世義務(erga omnes)的重要組成部分。⑥Corfu Channel Cas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v.Albania), Judgment of April 9th, 1949, I.C.J Reports 1949, p.22;Legality of the Threat or Use of Nuclear Weapon, Advisory Opinion, I.C.J Reports 1996, p.226;Barcelona Traction, Light and Power Company, Limited (Belgium v.Spain), I.C.J Reports 1970, p.32,§34.但是,目前而言,人權的國際保護還很難被嚴格地認為是一般法律原則。
(四)小結 如果我們將“保護的責任”從內部作區分,差異就一覽無余了。“保護的責任”可被拆解為兩個維度:(1)國家的首要責任:保護本國人民;(2)國際社會中其他成員的補充責任:(a)尊重他國的主權,以協助其履行,以及(b)在當事國未提供此種保護時,由國際社會采取措施代行之。2009年秘書長報告中提及的三項支柱可據此被歸入其中:第一支柱“國家的保護責任”屬于前者,第二支柱“國際援助和能力建設”和第三支柱“及時果斷的反應”正是后者的范疇。施特勞斯(Ekkehard Strauss)認為2005年世界首腦會議并未創造新的法律,應將“保護的責任”理解為根據道德信仰采取共同行動的承諾。①Ekkehard Strauss, “A Bird in the Hand is Worth Two in the Bush - on the Assumed Legal Nature of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1, 2009.誠然,試圖確認“保護的責任”的國際法地位還為時尚早,稱其為一項框架的說法是恰當的,但需注意的是,“保護的責任”并非毫無法律內容。
如上所述,“保護的責任”的第一支柱已深深根植于現有的國際人權與人道法,甚至有很大部分被視為了“強行法”。其中,“保護的責任”所包含的4種國際犯罪通過條約、司法意見等許多形式得到了禁止—但我們也要看到,這里國際法對不同罪行的規制有失平衡:在行為的性質、國家的責任范圍等各方面,有關滅種罪和戰爭罪的法律規則較之族裔清洗和危害人類罪顯然更為明確和細化。其次,秘書長報告根據《成果文件》第138段和第139段認為“保護的責任”的第二支柱主要包括4項內容:(1)鼓勵各國履行第一支柱下的責任;(2)幫助他們履行這一責任;(3)支持他們建設保護的能力;(4)對處于沖突爆發的壓力之下的國家進行援助。②UN General Assembly,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63/677),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15.國際法院2007年在解釋《滅絕種族罪公約》時表達的態度是,各國至少有義務利用自身的影響力,去阻止事件的發生或持續。相比之下,國際人道法在戰爭罪方面確定的國家責任范圍更廣:日內瓦四公約的共同第1條不僅為締約國設定了“尊重本公約”的基本義務,還增添了“保證本公約之被尊重”的衍生義務—這或許可以被認為足夠賦予第二支柱的所有內容以法律意義。類似的措辭還出現在《憲章》第2條第6款:“本組織在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之必要范圍內,應保證非聯合國會員國遵行上述(主權平等、善意履行義務、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等—筆者注)原則”。顯然,國際法對第二支柱中義務的規定遠比上述的第一支柱更為模糊。
那么,此種“確保尊重”(ensure respect)的范圍究竟為何,是否可以延伸至作為第三支柱的“及時、果斷的行動”?這就成為了根本矛盾所在。2009年辯論大會以及2011年利比亞危機之后國際社會的態度都表明了這一點:大部分國家的態度普遍傾向于認可前兩項支柱,對第三支柱卻強調通過外交談判和政治途徑與當事國政府進行溝通,對選擇性適用以及采取武力抱有明顯的顧慮。“保護的責任”的案文本身未賦予任何國家單獨使用武力的權利應無異議,但是安理會是否因此獲得了某種法律義務卻存在爭議。“保護的責任”在2個維度上所包含的內容,其性質完全相同嗎?在本國未履行責任之后,其他國家組成的國際社會能完全對其加以繼承和行使嗎?這些都還有待更進一步的討論。
可以看到,“保護的責任”的法律性質主要體現在第一支柱的規定中,而第二和第三支柱還缺乏足夠的法律依據:其中,最為顯而易見的一點是,即使各主權國家拒絕履行作為國際社會一員所承擔的上述責任,也不會因違反而引起制裁或救濟。③Carsten Stahn,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Political Rhetoric or Emerging Legal Norm?”,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1, 2007.概言之,“保護的責任”距離積極的國際規范地位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在法律與道德之間,國際社會對全體人類的責任或許暫時仍然偏向后者。未來,國際法委員會對“國家責任制度”的編纂與發展,國際法理論中對“國際組織負有法律責任”這一觀點的辨析,都會對“保護的責任”的命運產生關鍵性的影響。
四、路徑困境與突破可能
“保護的責任”從理論到實踐的飛速進展表明,聯合國的機構或成員國,都認為國際社會應當避免在面臨人道主義災難時再次束手無策。然而,各方能夠達成的,僅僅是對這一目的本身的擁護。上文已經指出,“保護的責任”的法律性質仍然不足,國際社會此前形成的共識均屬意向性的說明。因此,在利比亞危機發生后,這一概念的發展逐漸放緩。其中,最大的阻力來源于各國對于第三支柱的紛爭。
首先,歸根結底,“保護的責任”建立在人道主義干預的基礎之上。近20年來,雖然全球化的種種表現對主權形成了挑戰,但國家的核心意義并未因此消除。《憲章》在宗旨部分提及了人權,卻并未將其納入第2條所列舉的各項基本原則中—主權平等卻在其列。隱含之意,是否達成人權目標的手段必須遵循主權平等的原則?目前,履行第三支柱所涉及的主要議題,無論是非國家武裝團體的地位,還是國際刑事法院對國家元首的指控,在實踐中都極可能影響到一國的根本利益—政治獨立。在這種情況下,試圖認定其已經成為一項國際法原則顯然過分荒誕,更不可能以之為基礎進而發展相應的具體規則。不在少數的國家提出,限制否決權是落實“保護的責任”的先決條件。這種呼聲主要來自以下2點原因:一,安理會常常議而不決,無法對災難作出有效的回應;二,大國為維護自身利益,在實踐中存在選擇性適用。2001年《保護的責任》報告指出:當重要的國家利益沒有被涉及時,安理會常任理事國(P5)應在授權使用武力預防或結束人道主義災難的決議中放棄行使否決權。①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2001, p.51.這一建議雖然未能被納入2005年《成果文件》,但后經瑞士、新加坡等國的推動,還是在秘書長2009年的報告中得到了體現,甚至出現了“不否決的責任”(The Responsibility Not to Veto)概念。②Nadia Banteka, “Dangerous Liaisons: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a Reform of the U.N.Security Council”, Columbia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2, 2016.更有國家要求,在安理會陷入僵局時,必須明確聯大和安理會的關系。如此種種,盡管或許會提高大國行使否決權的成本,但在國際關系的現實下,很可能只是勞而無功:改革安理會的提議始終沒有得到中、美等國的回應就是明證。其次,如上所述,以原則為起點發展規則的道路已經被否定,那么“保護的責任”若要繼續深化,防止惡意被操縱和解釋,則必須賦予其明確的法律內容,規定各國的權利義務關系,其中最重要的是將“保護的責任”在執行維度的標準徹底清晰化。包括尼日利亞在內的許多非洲國家都對此表達了支持,并要求將關注點轉向更務實的問題。③Paul D.William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Norm Localisation, and African International Society”,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3, 2009.在此,規則缺失已經成為“保護的責任”從道德信條向國際法推進的關鍵障礙。其中,第三支柱—及時果斷的反應,因其包含了使用武力的內容,成為了履行“保護的責任”無可避免的難題。此種自下而上的進路,意味著各國需要在細節上對使用武力的構成要件達成一致。然而,現實情況的復雜,又如何能夠被文字所窮盡?在科學技術日新月異的今天,隨著法律愈發凸顯其滯后的一面,為“保護的責任”設定具體的觸發機制和操作程序無異于埋下自身安全的致命隱患,是不可能被各國所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對于將“保護的責任”規范化這一目標本身,國際社會也存在許多不同的意見。例如,美國始終反對將“保護的責任”上升為明確的法律規則,因為這必然將限制其單邊行動的自由。①Theresa Reinold,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Impediment, Bystander, or Norm Leader?”, Global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1, 2011.而德國、荷蘭等又擔心過度的限制會遲滯反應的能力,導致災難情勢的升級。②Remarks of Ambassador Dr.Peter Wittig,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Germany to the UN, Informal discussion on“Responsibility while Protecting” with FM.Patriota and Prof.Ed Luck;Statement by Ambassador Herman Schaper,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Permanent Mission of the Kingdom of the Netherlands to the UN, Informal debate on Brazilian concept note on “Responsibility while Protecting”.更普遍的憂慮是,一旦參與了此類討論,等于在官方層面直接承認了以武力解決人道主義問題的正當性,這一步是許多國家不愿邁出的。
各國的猶疑不定,從側面反映了二戰后西方學界希望將“個體性”與“社會性”同時囊括進國際法規范體系所導致的悖論。有學者認為,矛盾無法從根本上被消解,“保護的責任”制度化的進程事實上已經夭折。③徐崇利:《“保護的責任”制度化進程之夭折》,《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類似的批評往往指出:紐倫堡審判以來相關的宣言、條約、決議等已經對國家保護其人民的義務作出了規定。目前所需要的,是推進國際機制以有效應對災難。但是,2005年世界首腦會議及其后的活動表明,“保護的責任”仍然受困于人道主義干預的核心問題:利己動機與意愿缺失。在此,將二者相區分的嘗試是不成功的。所以,“保護的責任”只是對現存的規范與實踐進行了編纂和重述。④Stephen P.Marks & Nicholas Coope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Watershed or Old Wine in a New Bottle?”, Jindal Global Law Review, 1, 2010, pp.105-126;Petra Peri?i?, “Implications of the Conflicts in Libya and Syria for the R2P Doctrine”, Zbornik Pravnog Fakulteta u Zagrebu, 5, 2017.上述觀點所隱含的前提,是將“保護的責任”的成敗完全歸結于第三支柱。然而,正如摩根索(Hans Morgenthau)所指出,意識形態并不能改變以下基本事實:國家利益而非抽象原則將仍然是所有國家決定干預和選擇手段的首要因素。⑤Hans J.Morgenthau, “To Intervene or Not to Intervene”, Foreign Affairs, 3, 1967.國際干預的結構性問題,來源于道德與現實的永恒張力。⑥Roland Paris, “The‘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and the Structural Problems of Preventive 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5, 2014.其徹底的出路,也只能有待于在未來長時段的歷史語境下,發生漸進的倫理涵化或激進的秩序變革。⑦金新:《國際保護責任的倫理困境》,《倫理學研究》,2016年第5期。在這個意義上,強調對第三支柱的實施要素加以明確和細化,收效可能是相當有限的。因此,有必要認識到,盡管第三支柱的進展有所放緩,但自2011年以來,在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層面,“保護的責任”通過對既有零散規則的整合與解釋,正越來越深入地內嵌于國際實踐,逐漸形成了包括聯合國、區域組織、主權國家等不同主體的全方位、多層次結構,正邁向全球人權治理的系統性戰略框架:
首先,聯合國設立了防止種族滅絕與“保護的責任”辦公室(UN Office on Genocide Prevention and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以及建設和平委員會(Peacebuilding Commission)。前者的職能是通過各種渠道收集信息,對特定情況進行評估,并向秘書長、聯合國系統以及國際社會提出預警和建議。后者作為政府間的咨詢機構,主要負責為受沖突影響的國家提供重建支持,由聯大、安理會和經濟及社會理事會選舉產生的31個成員國組成。其次,2011年,時任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在報告中指出,“保護的責任”的履行應考慮到不同地區的差異。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區域和次區域組織做出貢獻。①UN General Assembly & Security Council, The Role of Regional and Sub-Regional Arrangements in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65/877-S/2011/393),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可見,國際人權保護并不排斥區域層面的自主安排。目前,非洲和東南亞地區已經開始著手推進與“保護的責任”相適應的預警體系、援助機制等規范架構。②羅建波:《非洲一體化進程中的國家主權問題:困境與出路》,《西亞非洲》,2007年第6期;李伯軍:《論東盟對不干涉原則的突破與發展》,《求索》,2007年第12期。雖然評判其效果還為時尚早,但這無疑象征著良好的趨勢。第三,2010年,丹麥、加納以及“保護的責任”全球中心聯合發起在國家層面設立專職主管(Focal Point)的倡議,以協調和改善政府間在多邊外交、信息共享等領域的合作,創造承諾共同體,提高主權國家作為首要責任主體的保護能力,并為落實“保護的責任”的組織討論、設計政策。目前,世界上已經有61個國家和地區響應了這一呼吁。③“Members of the Global Network of R2P Focal Points:Prevent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Global Centre for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6 Aug, 2018.
的確,從概念產生的背景來看,“保護的責任”被寄托的厚望,是盡快促使國際社會在第三支柱相關問題上達成共識。有學者指出,實現聯合國采取決定性行動的法律義務是“保護的責任”的真正價值。④蔡從燕:《聯合國履行R2P的責任性質:從政治責任邁向法律義務》,《法學家》,2011年第4期。在可預見的將來,這一任務的前景誠然難言樂觀。但是,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共同屬于“國際社會的補充責任”,在強調刑事追訴以及軍事干預等強制措施以外,更不應漠視人權問題深層次的社會、經濟根源。這要求國際社會尤其是發達國家,對作為第二支柱的“國際援助與能力建設”付出更多努力。2009年《履行保護的責任》報告指出,“三大支柱”同樣重要,沒有主次、先后之分,也不可被割裂。⑤UN General Assembly, Implementing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63/677),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p.2, 15.由于第三支柱的困境而完全否認“保護的責任”的意義是不恰當的。事實是,圍繞第三支柱所產生的局部爭議,并未影響各國對“保護的責任”的整體支持。對于這樣一個包含著不同系統的復雜規范而言,內部構造的發展存在動態性差異是非常自然的現象。因此,必須協調彼此之間的關系,在繼續討論第三支柱的同時,加強對于第一支柱和第二支柱的建設。唯有如此,才有可能通過三者之間的互相促進,保證“保護的責任”的真正落實—這其實也反映了中國的一貫觀點。
五、中國的立場與展望
對于中國政府在“保護的責任”發展過程中的前后態度,國內外學者多有研究。⑥Sarah Teitt,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and China’s Peacekeeping Policy”, International Peacekeeping, 3, 2011;羅艷華:《“保護的責任”的發展歷程與中國的立場》,《國際政治研究》,2014年第3期。具體細節不再贅述。眾所周知,對干預近乎絕對的否定,構成了當代中國外交的核心特征。一般認為,中國政府在利比亞危機中的妥協只是面對具體事態采取的針對性反應,不能據此判斷其政策發生了原則性改動。⑦UN Security Council Sixty-sixth year 6498th Meeting, 17 March 2011, New York, p.10.但這并非表明中國的立場是一成不變的。從拒絕正面回應到積極參加聯合國層面的討論,中國至少從未明確反對這一概念,而是謹慎地呼吁聯大在各國看法不同的情況下,根據2005年《成果文件》深化討論,以促進就具體的規則形成普遍共識。①ICIS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Research, Bibliography, Background--Supplementary Volume to the Report of the ICISS, Ottawa: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re, 2001, pp.391-394;《劉振民大使在聯大關于“保護的責任”問題全會上的發言》,2009-07-24,
正如埃文斯(Gareth Evans)所指出的,集體安全體制的有效,同時取決于國際社會對干預行為在正當性(legitimate)和合法性(legality)雙重維度的認可。⑥Gareth Evans,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Ending Mass Atrocity Crimes Once and for All, 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08, p.139.過去,有關人道主義干預的辯論主要圍繞意圖、授權、手段與后果四個方面展開。⑦陳拯:《框定競爭與“保護的責任”的演進》,《世界經濟與政治》,2014年第2期。“保護的責任”的倡導者從義務的角度為“主權”重新構建了地基,并通過聯合國的多邊體制,最大限度地論證了這一概念的意圖正當與授權合法;對此,心存疑慮的國家只得退而針對“如何進行保護”的問題,突出干預行動在手段與結果方面存在的問題,并提出“保護過程中的責任”、“負責任的保護”等替代框架。⑧General Assembly Sixty-sixth Session, Annex to the letter dated 9 November 2011 from the Permanent Representative of Brazil to the United Nations addressed to the Secretary-General (A/66/551-S/2011/701);阮宗澤:《負責任的保護:建立更安全的世界》,《國際問題研究》,2012年第3期。在主權國家依然是國際社會基本單元的今天,任何政府首先考慮的義務,是對本國人民的承諾。“保護的責任”并不會使這一認知發生實質性變化。⑨Tomasz A.Lewandowski,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Balancing National Interests and International Obligations through Multilateralism”, International Comparative Jurisprudence, 1, 2017.因此,“保護的責任”的履行面臨著不可控的道德風險,貿然付諸實踐使之極易背離最初的愿望。2018年末,科斯肯涅米(MarttiKoskenniemi)在海牙接受采訪時提醒人們:正義的生活仍然需要在國家一類更小的共同體之內創造。⑩“Interview:Martti Koskenniemi on International Law and the Rise of the Far-Right”,
中國有限接受“保護的責任”的背后,是國際格局的變遷所帶來的全新機遇和挑戰。本國經濟的發展,世界安全的保障,乃至全球治理的變革,都意味著中國必須對與“保護的責任”相關的干預規范作出自己的回應。這不僅是中國在未來發展中無法回避的現實問題,更是落實國際法治、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前提性任務。21世紀以來,“中國和平融入國際社會”已是學界研究的一個核心話題。①秦亞青:《國際關系理論的核心問題與中國學派的生成》,《中國社會科學》,2005年第3期。隨著“對國內法的影響”越來越成為“國際法的一項重要特征”②Richard K.Gardiner, International Law, London:Longman, 2003, p.9.,論者多從“國際規范傳播”的視角出發,探討中國對國際法規則的接受情況。然而,中國崛起與全球治理之間的互動,不應僅僅被視作“國家社會化”的進路。我們要看到,這一過程遠不是單向的。中國同時也在追求成為規則的設定者,將自身的價值認知與當時的利益側重反饋于國際體系,試圖影響全球規范的演化。③Melinda Negrón-Gonzales & Michael Contarino, “Local Norms Matter:Understanding National Responses to the 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Global Governance, 2, 2014.2014年5月,中國外交部與中國國際法學會主辦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國際法的發展”國際研討會,中方在總結文件中明確指出:“國家或國際組織經安理會依據《憲章》授權或經他國同意介入該國事務,不違反不干涉內政原則。”④《“和平共處五項原則與國際法的發展”國際研討會總結文件》,2014-05-27,
無論如何,在今后相當長的時間內,干預現象仍然會是國際社會爭論的焦點。對中國學界而言,這一主題的脫敏化也將是一個必然的過程。來自非洲的聲音或許能夠對我們產生一定的啟發:今后最重要的辯論不是使干預非法化(delegitimise intervention),而是以尊重條約中現有規則的方式保護平民,堅持反對單邊行為,并將此視為對國家主權和國際法的侵犯。⑦Saadatu Salisu Matori & Abubakar Bukar Kagu, “Cloaking Neo-Imperialism in the Shadows of Human Rights and Liberal Peacebuilding”, Journal of Law, Policy and Globalization, 88, 2019.最后,還有必要指出,任何大國外交的本質都是內政。美國外交的轉向與其國內的產業結構失衡、社會階層固化、中產群體減少是分不開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未來,在根本上也取決于中國政府能否以實現民主法治的現代化目標為本位,弘揚40年前的歷史勇氣。正如章百家所言,中國影響世界的主要力量來源是改造自己。⑧章百家:《改變自己 影響世界—20世紀中國外交基本線索芻議》,《中國社會科學》,2002年第1期。今天國際社會所面臨的變革可能遠超過世人想象。我們唯有不斷深入思考干預規范的發展變化,才能為未來做好知識上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