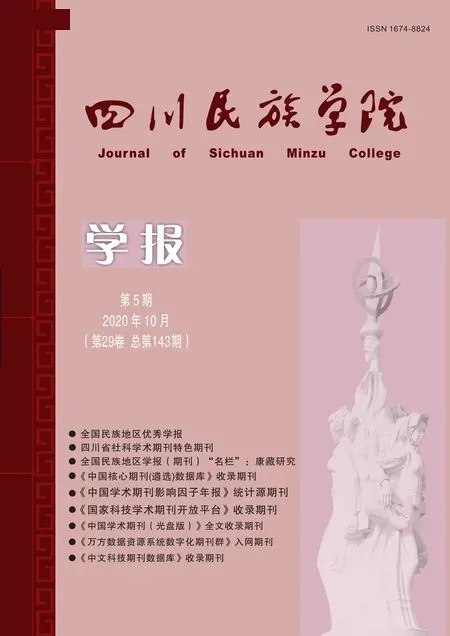生態人類學視閾下阿來“山珍三部曲”的生態關懷
高琳佳
(四川民族學院,四川 康定 626001)
從二十世紀開始,生態危機就以全球性態勢爆發,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日益凸顯,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人口劇增與資源利用的矛盾日益尖銳,人們對生態問題的認識水平得到不斷提升,從而促進了生態人類學的進一步發展。生態人類學是專注于研究人類群體與自然環境的關系的學科,主要以生態系統為研究對象,以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協調發展為研究目的。蘇聯的著名生態學家卡茲納切耶夫把生態人類學分為兩個基本研究層次,社會研究層次和醫學研究層次。他認為:“社會研究層次致力于探討資源問題、人口問題、人類對環境的作用問題、環境管理問題、環境政策問題、環境保護問題”[1]。藏族作家阿來的中篇小說“山珍三部曲”恰好反映出了生活在青藏高原的康巴藏族人在歷史演進中與身邊自然生態環境之間形成的復雜關系,這也就構成了生態人類學研究的基本問題。
“山珍三部曲”是藏族作家阿來近年來出版的中篇小說,包括《河上柏影》《三只蟲草》《蘑菇圈》,其中《蘑菇圈》榮獲2018年第七屆魯迅文學獎。“山珍三部曲”以青藏高原特有的自然物種資源-蟲草、松茸、岷江柏為創作對象,一方面生動形象地描繪出了川西藏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美好畫面,另一方面深入透徹地審視和反思了現代文明過度張揚的消費主義文化對生態的破壞,充分體現出了阿來鮮明的人文關懷和濃郁的生態憂思。
一、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
首先,原始自然的和諧呈現。在小說《蘑菇圈》的開篇,阿來詩意地刻畫了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原始圖景。在圖景中,人、植物、動物以及一切生物是平等共生的,流動著自然的生機,透出淳樸、自然、清新、原始的味道,充分體現出人只是存在于生態系統的一部分,而非高高在上、唯我獨尊地凌駕于其他生物之上。每年春耕大忙之時,山林里便會傳來清麗悠長的布谷鳥鳴聲,在地里辛勤勞作的藏族同胞們都不約而同地停下手里的活計,直起腰來,凝神諦聽這顯示季節好轉的聲音。此時此刻,日月星辰,河流山川,花草樹木,木瓦石板也都會為這美妙而短暫的鳴叫聲停頓,從機村到機村周邊的村莊再到機村周邊的周邊的村莊,乃至整個康巴藏區也都會為這美妙而莊嚴的鳥鳴聲停頓。從一個個特寫畫面逐漸拉遠至全景的勾勒,阿來由近及遠、由小到大地將康巴藏區的自然生態圖景記錄下來,別有一番從靜止到流動的交錯之美。更是別具洞天地將人與自然萬物有機地結合起來,呈現出一幅人與大自然和諧共生的原始畫面。不僅如此,阿來還不乏篇幅地對菌類破土而出的場景進行了大量的描繪,反復運用擬人、比喻、排比等修辭手法,使得對自然的書寫更加生動有趣。“羊肚菌用尖頂拱破了黑土,寬大的身子用力拱出了地表,它完整地從黑土和黑土中摻雜的那些枯枝敗葉中拱出了全部身子,完整地立在地面上了。”[2]5阿來連續運用“拱破”“拱出”“用力”“立在”等動詞來描寫羊肚菌破土而出之勢,并將羊肚菌擬人化書寫,將其賦予了人的力量,這是原始生命的最初動力,這是自然呈現的原始力量,這種無比堅定的力量是對生命的欣賞和贊嘆,是對生命的崇拜和敬重。自然萬物的和諧共生,在極具儀式感的原始畫面中得以體現。
其次,人與自然的平等相處。在阿來的“山珍三部曲”中,處處呈現出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好畫面。阿來在《蘑菇圈》中,著力刻畫了以阿媽斯炯為代表的藏族同胞尊重自然,與自然平等相處,嚴格遵守自然發展規律,對自然資源不狂熱也不貪婪。阿媽斯炯發現了山林里的蘑菇圈,并懂得那是蘑菇生生不息的源泉,懂得保護和澆灌蘑菇圈。天旱的時候,阿媽斯炯每天兩次從山下背水澆灌山上的蘑菇圈,讓蘑菇自由生長。她發自內心的喜愛那些“圍在一起開會的”可愛生命[2]5她執著而虔誠地守護著這片自然寶藏,充分體現了以阿媽斯炯為代表的藏族人對大自然的親近與熱愛。不論是對人對獸還是對鳥對草,阿媽斯炯始終心懷悲憫之情。小說中多次出現阿媽斯炯與野生禽類松雞、畫眉、噪鵑輕聲講話。當她去到山林里看到松雞低頭吸食蘑菇傘蓋時,她放慢腳步小聲說道:“慢慢吃,慢慢吃啊,我只是來看看,”[2]64當她背著水桶爬山去給蘑菇圈澆灌,聽到一只鳥在樹枝上叫個不停時,“她抬起頭來,說,你的聲音也是好聽的聲音。”[2]88原來這只畫眉鳥跟她已經非常熟悉了,每天都飛在樹叢上來等她給水喝。每當阿媽斯炯看到鳥兒跳下枝頭,啄食地上蘑菇時,她都會小聲說道:“鳥啊,吃吧,吃吧。”[2]91環境倫理學家霍爾姆斯·羅爾斯頓就曾提出:“人類區別與非人類存在物是因為人類能以廣闊的胸懷去關注所有的生命(人類和非人類存在物),而動物和植物卻只關注自己、后代或同類的生命。”[3]阿媽斯炯這種平等對待其他自然生命的友善態度恰好印證了藏族文化精神中平等對待萬事萬物的生態倫理情懷。
在小說《河上柏影》中,阿來將岷江柏作為植物,人作為動物放在同一個層面進行書寫,“岷江柏是植物,自己不動,風過時動,”“人是動物,有風無風都可以自己行動。”[4]4可見,在阿來看來人類跟動植物及其他生物是平等的,不存在高低貴賤之分,而人類只是生態系統中的普通成員之一。因此,人類與其他物種的交往應該是平等的。在小說末尾的跋語中,阿來再次寫到“樹不需要人,而人卻需要樹。”[4]217是的,在這個世界上樹的歷史比人的歷史更久遠,因為是樹為人類的祖先提供了果實、燃料等基本的生存物質。也正因為對樹的需要,人類才使得這個世界上的樹越來越少。在《三只蟲草》中,阿來同樣刻畫了純真少年桑吉就像小野獸一樣與大自然保持著平等、友愛的交流。在草原上,躺在草地上享受陽光的桑吉,聽到了青草破土的聲音,聽到了大地土層融凍的聲音,還聽到了枯草在陽光照射下失去水分的聲音。桑吉與云雀的互嘲、桑吉對大地的傾心聆聽無不凸顯著其他自然生命的地位等同于人類,這是貼合自然、回歸原始的顯現,這是人與自然平等對話的表現。
二、過度消費的生態困境
“山珍三部曲”以川西為寫作背景,關注的是川西藏地大自然與藏族人在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生態困境。通過生動的描寫,小說嚴厲地批判了過度張揚的消費主義文化帶給川西藏地災難性的生態破壞,人們為了追求經濟效益而對大自然進行過度開發、無度索取。這一切都歸因于人類對欲望的追求。欲望是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和人類文明的原初動力,沒有了欲望,人類就不可能擁有像飛機、輪船、人工智能這些先進的科技創造發明,人類的物質資源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如此豐富,正如馬克思·韋伯所說的:“對利益、金錢的欲求推動著個人與社會的進步與發展。”[5]然而,當人類無限的欲望需求遇見有限的自然資源時,勢必會造成人類生存環境的污染、資源的匱乏、生態的失衡。盧梭也曾指出:“若欲望無限膨脹,它不僅會吞沒整個自然界,還會成為我們為非作惡的原因。”[6]在“山珍三部曲”中,阿來不同程度地批判了欲望驅動下過度消費帶給大自然的生態困境。
對欲望動力的批判。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物質條件的過度欲求導致欲望的不斷膨脹從而抹殺了人的天性,使得人類漸漸丟失了內心的本真和心靈的善良。藏族人民一直以來對物欲要求淡泊,大多以藏傳佛教宗教信仰為精神依托,可是當物質主義思想及消費主義文化被帶到藏地以后,其濃郁的宗教氛圍被慢慢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猖獗的物質欲求的盛行。在《蘑菇圈》和《河上柏影》中就有深刻的體現。《蘑菇圈》中,當藏族人們知道松茸具有超高營養且價格不菲時,人心就變得急功近利、物欲至上了。在蘑菇還未長大成熟時,人們就提著鐵齒釘耙去到山上,扒開泥土,掏走長在泥土下面的小蘑菇,而這些小蘑菇的菌柄和菌傘都未分開,阿媽斯炯為此潸然淚下。貪欲使人瘋狂地掠奪自然資源,貪欲使人背離自然的發展規律,這樣的例證在《河上柏影》里也有體現。人們為了賺錢,開發旅游,在老柏樹生長地修建混凝土看臺,砍掉了大部分樹根,曾經蒼翠濃郁的柏樹,在被禁錮了樹根的自由生長之后,慢慢地窒息而死了。聽城里人說崖柏木非常稀缺,其價值斐然,在拜物的熱潮中受到人們的追捧,當地的藏族人們就開始瘋狂的采挖,甚至有些人冒死攀上懸崖去砍伐。為了獲得更多的物質財富,人們變得極度的瘋狂,就連石頭都不放過。聽說有種石頭可以做成硯臺,村人們就拿起鋤頭拿起鋼釬開始了近似瘋狂的采挖,有人把功能強大的挖掘機、裝載機都開進了現場。最后,曾經郁郁蔥蔥長滿樹木的河岸和山坡被挖得千瘡百孔,極大地破壞了當地的生態環境。阿來在“山珍三部曲”中,不同程度地揭示和批判了,原本天真善良的藏族同胞在巨大金錢利益的驅使下,變得貪婪無度,打著物盡所用和不能浪費資源的口號,蘑菇被過度采摘、岷江柏遭受瘋狂砍伐、石頭被猖狂采挖,最后導致物種滅絕、生態環境遭到嚴重破壞、大自然變得支離破碎。杜寧曾經指出:“過度消費的價值體系終將是異常的、短暫的,因為它破壞了我們的生態依托。”[7]物欲繁華的現代社會必須摒棄消費主義觀念的誤導才有望重建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關系。
除了對欲望膨脹的批判,阿來在“山珍三部曲”中還體現出對人類中心主義思想的嚴厲抨擊。人類中心主義是造成生態危機的罪魁禍首,人類把自己視為世界萬物的主人,地球上的一切生物都是為人類服務的,因此,人類便開始了竭澤而漁的開發和利用大自然。正如《蘑菇圈》中工作組提出的人定勝天的思想,工作組為了提高糧食產量,給莊稼多上肥料,農家肥被用完之后便去大工廠購買化學肥料,然而莊稼分外茁壯地拼命生長,卻不肯熟黃,最后導致最茁壯的莊稼幾乎顆粒無收。正是以社長為代表的人們,急于求成地破壞自然,違背莊稼成長的自然規律而導致莊稼顆粒無收、釀造出社長上吊自殺的悲劇。
結 語
在“山珍三部曲”中,阿來運用溫柔細膩的筆觸一方面詩意地描繪了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圖景,展現了藏族文化精神中善待自然、與大自然和諧相處、平等對待萬事萬物的生態倫理情懷。出于對大自然的敬畏,藏族人民在日常生活中時刻銘記順應自然、善待自然、遵循自然客觀發展規律的思想觀念,從而形成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生態思想。而阿來恰到好處地在其作品中展示了藏族人與大自然相依為命、和睦共處的美好景象。小說《蘑菇圈》中的阿媽斯炯、《三只蟲草》中的純真少年桑吉、《河山柏影》中的王澤周都是最具代表性的生態代言人,他們的言行舉止充分體現了藏族文化主張天人合一、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態理念。另一方面,通過對青藏高原特有自然物種蟲草、松茸和珍貴樹種的描寫,阿來嚴厲地批判了現代文明過度張揚的消費主義文化帶給川西藏地災難性的生態破壞。阿來不僅給讀者呈現了遠離城市喧囂的青藏高原在現代化大潮中也無一幸免的遭遇了滄桑命運,而且更加關注現代消費主義觀念的誤導將會造成川西藏地遭受到前所未有的生態破壞,從而催生出當地藏族人過度旺盛的物欲渴求,充分體現了阿來鮮明的人文關懷和濃郁的生態憂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