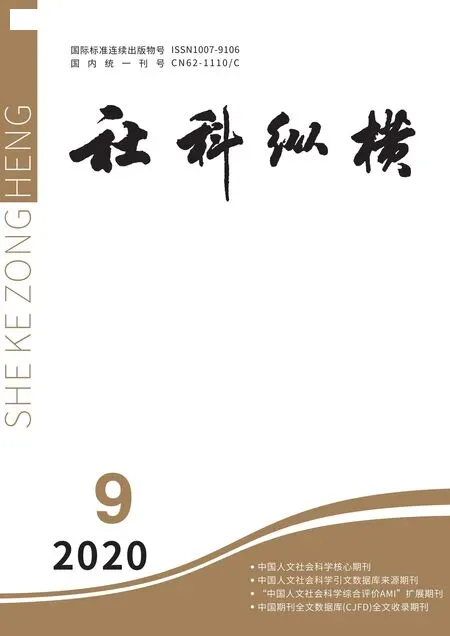齊梁聲律論爭及其新變意蘊
石 蝶 段宗社
(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 陜西 西安 710119)
梁永明年間,由王融、沈約、謝眺倡導聲律論大盛。齊梁時期是一個注重追求文學形式和新變的時代,聲律論的出現代表著古人對文學聲音問題的自覺追求。沈約提出聲律主張認為從屈騷以下“此秘未睹”,自詡是發現聲律的第一人,正是因為對聲律問題有著自覺的認識,這種自覺不僅是在意識上有意打破傳統自然聲韻進行人工聲律的探索,而且還體現在以明確的詩、樂區分意識,從理論建構上突破傳統“借音樂論聲”的模式,以“四聲”字調取代傳統“五聲”模式,以及對誦詩的聲韻和需外在聲樂配合的歌詩的聲韻有意區分。這些均屬于聲律論的新變內涵,而產生這種新變的原因和心態主要有兩個方面:一是在當時佛經轉讀的影響下,從理論形式上有意對傳統“論聲模式”進行新變;二是在民間吳聲歌曲外在聲樂的刺激下自覺地思考“脫樂”的五言誦詩的聲律問題。聲律論的形成是中國古代對文學作品聲韻的認識從“外聽”轉向“內聽”(詩歌誦讀的聲律),并將“內聽”外在形式化的過程,也是聲律探索從自發走向自覺的體現。
針對新出現的聲律,齊梁時期的文人展開了一場關于聲律問題的爭論,爭論的核心焦點在于聲律的來歷以及聲律論的價值。甄琛、陸厥、鍾嶸的觀點一脈相承,一致用前人論音韻的慣例批駁沈約自矜獨得的姿態,由此引發了一場關于聲律探索的古今之爭,這場論爭進一步明晰了聲律論的新變內涵。關于聲律論的價值問題,鍾嶸與劉勰形成了相反的態度,鍾嶸割裂了聲律與“諷讀”的聯系,以自然的“諷讀”主張否定聲律論的限制,試圖消解聲律存在的必要性;劉勰在這場論爭中從發生論的高度系統地梳理了“聲律論”的形成歷史和原因,通過區分“外聽”與“內聽”兩種聲音表現方式,貫通誦讀與聲律,為“聲律論”完善了理論依據。本文通過綜合梳理齊梁文人對聲律論的評價和論述,旨在從當時各家論爭中探索聲律論的形成路徑及其新變內涵。
一、聲律意識的自覺
中國古代有關永明聲律論的記載多在史書中,如《宋書·謝靈運傳》《梁書·庾肩吾傳》《南史·陸厥傳》等均有提及。沈約對聲律問題進行了細致闡述,《宋書·謝靈運傳》中記載:
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后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1](P1778-1779)。
沈約詳細闡述了五言詩的聲韻問題,“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后須切響”,講的是文字的聲調問題,四聲的交錯搭配形成文字本身的聲韻美。“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講的是一聯詩歌的整體聲韻。聲律論在提出之后引起了一些誤解和爭論,爭論的焦點主要在于兩個方面,一是對聲律論的主觀排斥,二是針對聲律論的發明權問題,即關于聲律認識的古今之爭。因不理解聲律論的一系列主張而造成對聲律論的主觀排斥,在當時就有所表露。以梁武帝為代表,《南史·沈約傳》記載:“沈約撰四聲譜,自謂入神之作。武帝雅不好焉,嘗問周捨曰‘何謂四聲?’捨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甚遵用約也。”[2](P1414)徐寶余先生在《梁武帝“不知四聲”辨》一文中結合史料細致梳理,指出梁武帝并非不知四聲,而是主觀上排抑四聲[3],可見四聲理論在當時不被接受的遭遇。而沈約“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的觀點提出之后更引起了不少反對的意見,以甄琛、陸厥、鍾嶸為代表,這就涉及到聲律論的來由問題和如何評價古今對聲律認識的差異問題。
甄琛對沈約的四聲論發問,見遍照金剛《文鏡秘府論》四聲論,其中記載“魏定州刺史甄思伯,一代偉人,以為沈氏四聲譜,不依古論,妄自穿鑿,乃取沈君少時文詠犯聲處詰難之”[4](P31)。雖然甄琛主觀上排斥這種新的聲律理論,但他已經注意到沈約的聲律主張與古人所論之聲韻不同,這從側面表明當時人們已經意識到沈約的理論有不同于古論的“新變”之處,但這種聲律新變多停留在理論層面,還沒有自覺地運用于創作。
陸厥對沈約的批評主要針對其“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的觀點,這一點也影響了鍾嶸。陸厥在《與沈約書》中提出:“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為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岨峿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與玄黃律呂,比五色之相宣,茍此秘為睹,茲論為何所指耶?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2](P1195-1196)陸厥以曹丕、劉楨、陸機等的宮商律呂說為材料反駁沈約“自騷人以來,此秘未睹”的觀點,將中國傳統聲論中所用的宮商律呂、清濁等概念與沈約自矜獨得的聲律主張看作是同類的理論。在《與沈約書》的末尾部分,陸厥舉出大量前人切合聲律的作品,從理論和創作兩個方面批駁沈約自矜獨得的立場。鍾嶸與陸厥生活年代大致相近,鍾嶸在《詩品·下品》中評價陸厥“具識文之情狀”,可見他對陸厥的文學主張是有所了解并且心許贊同的,因而,鍾嶸在評價聲律論時與陸厥的觀點及所用的論據高度相似。鍾嶸在《詩品下·序》中提出:“昔曹、劉殆文章之圣,陸、謝為體貳之才。銳精研思,千百年中,而不聞宮商之辨,四聲之論。或謂前達偶然不見,豈其然乎?”[5](P438)陸厥和鍾嶸都是針對聲律論的發明權問題,用魏晉詩人的聲論觀點和作品質疑沈約,但僅僅舉出前人對音律論述的材料或作品來反駁沈約“此秘未睹”的觀點還不能成立。沈約提出其觀點的時候,對前人的論述也是有所認識的,并認為前人的創作“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暗與理合,匪由思至”(《宋書·謝靈運傳》)。相反,論者應該反過來問問沈約到底發現了什么前人沒有洞見的秘密,由此才能判斷聲律論的價值,而這就與聲律論的新變內涵密切相關。
實則陸厥、鍾嶸雖然都舉出了古人論音的例子反對沈約自詡為聲律論發現的第一人,但他們也注意到了古今論述聲韻的區別。陸厥認為:“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也就是說他承認沈約提出的聲律主張在表述方式上不同于傳統的聲論方式。鍾嶸也注意到了前人對“音韻”的理解與當今的宮商四聲是不同的兩個事物,在批評了沈約自矜獨得的姿態之后,又舉三祖之詞為例論說傳統音韻與今世之所言宮商的區別,認為“三祖之詞,文或不工,而韻入歌唱。此重音韻之義也,與世之所言宮商異矣”[5](P438)。他們都察覺到了今人所論之聲律與古人“論聲”存在區別,但他們依舊用前人的觀點反駁沈約,將沈約的聲律主張歸入到古代“論聲傳統”中,盡力消解聲律論的“新變”成分,這其實也反映出當時文人厚古薄今的思想傾向。
“今論”與“古論”的不同意味著什么?這一問題卻被反對者忽略了。陸厥雖沒有明說“今論”究竟在哪里不同于前論,但他已經指出二者在表述方式上存在差異,沈約極力宣稱“此秘未睹”,實則就是從這里出發的。沈約在《答陸厥書》中指出:“十字之文,顛倒相配;字不過十,巧歷已不能盡,何況復過于此者乎……自古辭人,豈不知宮羽之殊,商徵之別?雖知五音之異,而其中參差變動,所昧實多。”[2](P1196-1197)沈約已經自覺地意識到在傳統五聲與新起的聲律論之間存在一個天然與人為的區別。沈約認為傳統五聲不是一種自覺聲韻認識的理論,其中對聲音變動規律的認識還處在暗合的階段,不足以規定“十字之文,顛倒相配”五言詩的聲律。目前學界大多認為傳統五聲所論的聲韻是一種自然的聲律,沈約在此基礎上提出了一種有意為之的人工聲律,這正是當時聲律新變的體現,也是古人對聲律認識的一次意識上的自覺。如陳僅《竹林答問》訴述:“大凡天地間有聲必有韻,故音韻對偶之學,非強而成也。所異者,古人無心,今人有意耳。”[6](P2230)但僅僅就此即宣稱前人“此秘未睹”,似乎還不能完全體現聲律論在“古論”基礎上的新變之處。
二、理論建構的自覺
除了有意而為的意識自覺的因素外,沈約認為聲律論與傳統五聲還在所屬范圍上有別,這體現了聲律論的另一新變內涵:新的理論建構。《文鏡秘府論》記載沈約答甄琛:
五聲者,宮商角徵羽,上下相應,則樂聲和矣;君臣民事物,五者相得,則國家治矣。作五言詩者,善用四聲,則諷詠而流靡;能達八體,則陸離而華潔。明各有所施,不相妨廢[4](P32)。
沈約指出五聲與四聲各有所施,不相妨廢。四聲和五聲之所以能并行不悖,就是因為二者所屬之領域不同。沈約在辯論中明確指出宮商角徵羽五聲所論是樂聲,而四聲所述是五言詩的聲韻,這種對樂聲與詩歌誦讀之聲的區分意識也體現出聲律論的新變意識。四聲是對文字聲調的新的劃分方式,擺脫了傳統的音韻學的理論框架(五聲)。
陳寅恪先生在《四聲三問》中提到:“中國自古論聲,皆以宮商角徵羽為言,此學人論聲理所不能外者也。”[7]自古以來有關文學作品韻律的論述是在中國古代文學創作經驗積累的基礎上形成的,尤其以駢文、詩賦等有韻文學的創作為代表。傳統上對聲韻的理論性闡釋多是借助宮商樂論,通過外在的樂聲來類比語言的聲韻,這其實還處在對聲韻認識的自發階段。中國古代有關文學作品聲韻的論述一開始就與音樂理論糾纏在一起,并形成了“借音樂論聲”的傳統。先秦詩樂舞不分,最初有關文學作品的聲韻特征的論述,多借用了樂論思想,并在文學的論述中保留了大量音樂術語。宮商角徵羽五音本是中國古代的樂律術語,用來指幾種音樂聲音的高低,后來才逐漸被引入文學作品音韻的分析。《樂記》已經出現了宮商角徵羽五聲,這時的五聲是實指音樂領域的五種樂調,其中提出的“聲成文,謂之音”這一規律為后來以音樂論文開辟了道路。《毛詩序》中的“情發于聲,聲成文,謂之音”便直接引用了《樂記》的樂論思想來論詩。《西京雜記》記載司馬相如作賦的方法時稱:“合纂組以成文,列錦繡以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8](P12)借用外在的宮商樂論的音調來論述賦的聲韻,音樂漸漸被引入對語言文字聲韻的論述,陸機《文賦》對文學作品聲韻的論述:
暨音聲之迭代,若五色之相宣。雖逝止之無常,故崎錡而難便。茍達變而識次,猶開流以納泉;如失機而后會,恒操末以續顛。謬玄黃之秩敘,故淟涊而不鮮[9](P172)。
陸機認為創作作品的聲音應當交替變換,就像五種顏色的相互錯雜,由此來說明作品語言音節上的抑揚頓挫。“音聲之迭代”本義是指音樂演奏時聲音的高低起伏,而在文中是用來說明文學語言上的自然的音調。可見“聲律論”形成之前對聲韻的論述多習慣以音樂設喻,將樂理與詩論相通,其意在通過外在的樂聲來言說文學語言聲韻的變動。此外,封演《聞見記》記載:“魏時有李登,撰《聲類》十卷,凡一萬一千五百二十字,以五聲命字,不立諸部。”[10](P7)魏晉時期對語言音韻的理論建構也以傳統的宮商角微羽五音為基礎,并以五聲分韻部,可見傳統音韻學的五聲概念依舊依附于宮商樂論術語。
聲律論在傳統聲韻學五聲的基礎上另辟蹊徑,提出了一個全新概念——四聲。平上去入四聲不論在聲韻理論建構上還是聲音類別上,都徹底脫離了音樂。永明聲律論也從傳統“音樂論聲”中脫離出來,進行新的理論建設以探求文字本身的聲律。“聲律論”形成之前古人對音韻的論述是借用宮商角徵羽等音樂概念的,并形成了“借音樂論聲”的慣例,闡述的也是結合音樂的外聽之聲。新起的“聲律論”則突破了五聲,形成了“四聲”,不僅在理論的建構上擺脫了音樂宮商,而且以“四聲八病”的理論形式建立語言文字的聲調模式。由此看來,“今論”是要在古論的基礎上完成對文字聲律理論的自覺建構,這種自覺不僅是意識上的有意為之,而且還體現在對聲音類別(樂聲與字音)的區分上。“聲律論”突破外在音樂歌聲來建立文字誦讀本身的聲韻,這正顯示出聲律論的新變意義。由此,中國古代對語言音韻的探究也從自發走向了自覺。
三、新變原因及心態
自覺地將語言文字本身的聲音固定下來,并將其形式化是聲律論的理論貢獻。聲律論代表了中國詩歌發展史上首次自覺地對詩歌語言本身的關注,這種關注是在齊梁時期追求文學形式美的大環境影響下偶然形成的。聲律論的出現并非一朝一夕之事,從歷史的觀點來看,漢魏以來駢文的發展及其形式的追求為聲律論積累了條件,文人誦讀、清談對聲韻的講究也為聲律論奠定了基礎。在沈約正式提出聲律主張之前,前人對聲律問題已有所察覺。《宋書·范曄傳》載范曄《自序》云:“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1](P1830)周颙的《四聲切韻》表示了對聲調的關注,《南史·周颙傳》記載:“(周颙)始著《四聲切韻》行于時。”[2](P985)遺憾的是這部文獻沒有保存下來,今人無法窺探究竟。可見齊代以前,文士已經開始了對音律的探究,南朝時期對聲律問題的重視離不開當時文化環境的誘導。齊梁時期佛學盛行,統治階層自上而下形成了一種崇佛的潮流,佛經的翻譯和梵唄新聲的出現刺激了永明聲律的產生。四聲的形成就受到佛經轉讀的刺激和影響,陳寅恪《四聲三問》一文認為,聲律論在永明時期出現與當時“竟陵王子良大集善聲沙門于京邸,造經唄新聲有關”[7]。
聲律論的形成也與當時的文學生態有關。在詩與樂已然分離的背景下,民間吳聲西曲的興盛影響著宮廷貴族的審美趣味,在音樂歌聲的刺激下出現了一種力求突破外在聲樂而探究詩歌文字本身聲韻的自覺追求。相比于魏晉時期的詩歌創作,南朝詩壇存在兩個顯著的特點:一是詩壇宮廷貴游文學逐漸盛行,另一個是民間吳歌西曲的繁榮。聲律論的形成時間正值民間吳歌西曲盛行之時,《南齊書·良政傳序》記載:“永明之世,十許年中,百姓無雞鳴犬吠之警,都邑之盛,士女富逸,歌聲舞節,校服華妝,桃花綠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蓋以百數。”[11](P913)江南富庶的城市生活,帶來了吳聲西曲的繁榮。曹道衡先生認為沈約所處的劉宋時期正是音樂方面發生變化的時期,卻也是文人們注意詩文音律的時代,已注意到音樂與詩文音律產生的時代關系[12](P77)。商偉在其論文中追溯了宮廷貴族接受并模擬市井文學的過程,認為民間的歌舞引起了宮廷貴族對它們的喜愛和模擬[13],可見,民間的吳聲西曲已經影響了宮廷貴族的審美趣味。劉躍進先生進一步提出齊梁時期永明作家大量擬作具有江南民歌風味的樂府小詩,他們在“歌者之抑揚高下”之間很可能會注意到“四聲可以并用”這一規律,并進一步認為四聲的發明不僅肇始于佛經的轉讀,江南新聲雜曲的影響也是不能低估的[14](P78)。從當時的文學生態來看,吳聲歌曲至少在外部環境上刺激著人的感官,而它對聲律論的影響暫且只能說存在外部的誘導,還沒有深入到內在形式的借鑒①。在江南民歌小調抑揚頓挫的音樂審美刺激下,追求新變的齊梁詩人很自然會想到已“脫樂”的五言詩本身的聲調問題。
《梁書·庾肩吾傳》記載:“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脁、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15](P690)可見四聲論的形成有新變的自覺意識,這種新變并不是完全針對傳統的音韻學(五聲)的新變,還有對以江南民歌為代表的外在聲樂的新變。自西漢班固《漢書·藝文志》于“詩”之外別立“歌詩”,到劉勰“詩與歌別”(《文心雕龍·樂府》)思想的明確提出,漢魏以來對誦詩和歌詩的區分是有明確意識的。在漢代五言古詩影響下成長起來的五言詩是誦詩,而非歌詩,歌詩與誦詩在音律上的不同應是南朝人共知的常識。歌詩需要音樂伴奏,而誦詩則依靠誦讀檢驗。因此,詩樂分離之后誦讀的聲韻問題才是聲律論探討的對象,而這種探求是在當時的歌詩(吳聲西曲)刺激下產生的。聲律論在聲樂之外對五言詩聲韻的刻意探求意味著古人對語言聲音的直正自覺,也顯示出聲律論的新變動機。其新變的核心是在聲樂之外對語言文字本身聲韻的有意探求,并將這種誦讀的聲律要求以“四聲八病”的方式形式化。
四、聲律論的價值爭論
聲律論形成之后,關于如何評價聲律論的價值問題又引起了一次論爭,這場論爭不像沈約與甄琛、陸厥的論爭那樣以文人之間書信對答的方式正面展開,而是存在于論爭雙方各自的論著之中,以鍾嶸、劉勰為代表。鍾嶸以其詩歌“直美”理想否定聲律論的價值,而劉勰則肯定了聲律論的意義。他們產生分歧的原因在于雙方對誦讀與聲韻關系認識的角度不同,鍾嶸割斷了誦讀與音律的關系,劉勰則從發生論的高度梳理了聲律的來歷,通過區分“外聽”與“內聽”兩種表現方式,貫通誦讀與聲律,直正為“聲律論”建立了理論基礎。
鍾嶸對聲律論的批評見《詩品下·序》:
王元長創其首,謝眺、沈約揚其波。三賢咸貴公子孫,幼有文辨。于是士流景慕,務為精密。擗積細微,專相凌架。故使文多拘忌,傷其真美。余謂文制本須諷讀,不可蹇礙,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至平上去入,則余病未能;蜂腰鶴膝,閭里已甚[5](P452)。
綜合來看,鍾嶸的批評主要基于三點原因:一是今既不備管弦,何取聲律;二是清濁通流,口吻調利的“諷讀”要求;三是詩歌直美的理想。以上三點論據都不是從語言形式的角度批評聲律論,而是以詩歌的情感內容來否定聲律論對詩歌語言形式的自覺追求。鍾嶸認為聲律論的刻意講求會妨礙詩歌情感的自然抒發,因而有傷“直美”。針對詩歌的外在聲音問題,鍾嶸在不傷“詩歌直美”的前提下提出了一個最低限制,即他所說的“但令清濁通流,口吻調利,斯為足矣”。鍾嶸“諷讀”原則提出的初衷是為了消解聲律論“四聲八病”的限制,想在自然的維度上取消聲律的人工限制。鍾嶸對詩歌誦讀的基本要求是“不可蹇礙,清濁通流,口吻調利”,也就是說達到誦讀順口聲音和諧即可。但如上文所述,聲律論要解決的正是五言詩的誦讀聲韻問題,聲律論的要求并非就不利于“諷讀”。鍾嶸“諷讀”的詩歌要求與沈約的聲律主張并無本質上的沖突。王瑤先生已經指出:“鍾嶸提出的‘清濁通流,口吻調利’的要求其實也是指‘吟’說;與四聲八病所講原則并無根本不同,只不過程度上有差別。”[16](P302)鍾嶸以“諷讀”否定聲律論暴露了他聲律認識中的問題,即割裂誦讀與聲律。第一,他以不備管弦為由否定“聲律論”表明他混淆了聲律與音樂,將聲律的主張認為是一種外在的聲音,即一種強加在詩歌上的聲韻,因此他認為不能用這種聲律論來規定五言詩的誦讀聲韻。第二,他忽略了詩歌文字的誦讀本身就是含有聲韻,即劉勰所說的“聲含宮商”。綜合整本《詩品》來看,鍾嶸幾乎也沒有表現出對五言詩的聲韻的特別關注(除了上品對張協、謝靈運的評價)。鍾嶸割裂了誦讀與聲律的關系,認為誦讀之詩不必講求聲律,由此他希望在聲律之外,建立一個“清濁通流、口吻調利”的“諷讀”要求,卻忽略了“清濁通流、口吻調利”的要求本身就是有聲律可循的。
劉勰《文心雕龍·聲律》則從發生論的角度解釋了聲律的由來,提出“夫音律所始,本于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17](P301)。將音律、人聲、樂歌三者串聯起來,三者貫穿的根本原因在于“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即人的聲音本身就含有音韻。劉勰進一步提出兩種不同的聲音表現模式:“人聲—樂歌”“人聲—音律”,由此區分出“外聽”與“內聽”兩種聲音,而兩種聲音的認知方式有很大差別。劉勰認為:“今操琴不調,必知改張,摘文乖張,而不識所調。響在彼弦,乃得克諧,聲萌我心,更失和律,其故何哉?良由內聽難為聰也。”[17](P301)外聽與內聽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前者訴諸音樂,后者訴諸誦讀。外聽之聲因借助樂器,故其和諧與否很容易察覺,內聽之聲沒有外在依托因而無法辨識。于是,如何確定內聽之聲是否和諧就成了一個難題,在此條件下劉勰認為:“故外聽之易,弦以手定,內聽之難,聲與心紛;可以數求,難以辭逐。”認為對誦讀聲韻的判斷可以通過“數求”(即樂律、聲律等外在形式)的方式驗證,聲律論便由此而生,聲律論要探究的正是內聽之音,這就從理論上解釋了聲律論的由來。聲律論的形成過程正是一個由“外聽”之聲而走向“內聽”之聲的過程,這一過程在某種程度上正是聲音發展的“自然之道”。因而,劉勰具體論述“聲有飛沉,響有雙疊”則進一步回應了永明聲律論,也承認了聲律論的價值。
劉勰與鍾嶸對聲律論的價值認識產生分歧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對誦讀和聲律關系的不同認識。鍾嶸反對四聲論,理由是五言詩是用于誦讀的,而不是用于歌唱,歌唱講音韻,誦讀不用講音韻。劉勰也區分了歌唱與誦讀,而且以為歌唱訴諸“外聽”,而誦讀訴諸“內聽”,從理論上闡明沈約聲律論的必要性,他將歌唱的音律進一步推及誦讀,認為二者都有聲律要求。鍾嶸的“諷讀”要求對詩歌聲韻的檢驗只能訴諸傳統的誦讀方式,而聲律論則從外在形式上規范了五言詩的誦讀聲律,以達到詩歌音韻鏗鏘的目的。聲律論的出現使得誦讀之聲可以“外求”,文章聲韻由基于感覺內心的調適轉向客觀可操作的技術,“內聽”正在轉向“外聽”。劉勰對聲律論的認識揭示了作文調音之術在永明時代趨于客觀化的趨勢,也完善了聲律論的理論基礎。
注釋:
①杜曉勤《吳聲西曲與永明體成立關系的詩律學考察》(《陜西師范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2.02)一文從詩律形式上對比了吳聲西曲與永明體之關系,認為永明體詩律系受晉宋吳聲西曲聲律之啟發而形成的說法,既不符合詩史,也與邏輯相悖。針對劉躍進的觀點,主張永明體的產生和普及與齊梁宴樂風氣之間確實存在一定的關系,不過晉宋流行的吳聲西曲對永明聲病說的形成并沒有產生多少直接影響。本文在此贊同此說,認為吳聲歌曲在外部環境上刺激著當時人的感官,而它對聲律論的影響暫且只能說存在外部的誘導,還沒有深入到內在形式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