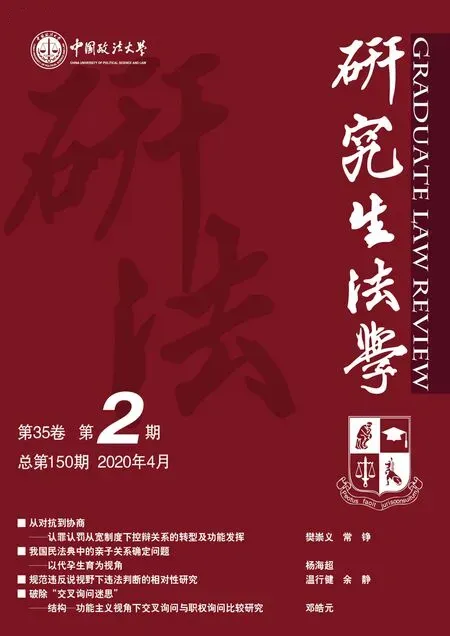規范性文件作為行政行為“依據”的判斷標準
梁 哲
一、問題的提出
201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以下簡稱《行政訴訟法》)規定了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制度,原告在提起行政訴訟時,可以一并請求審查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1]本文的“規范性文件”沒有特殊說明,指的是行政規范性文件,即行政機關制定的除行政法規和規章之外的決定、命令等普遍性行為規則;《行政訴訟法》第53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行為所依據的國務院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對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時,可以一并請求對該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前款規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含規章。可以被附帶審查的規范性文件必須是行政行為的“依據”,如果沒有“依據”關系,即使是規范性文件法院也可以拒絕審查。實踐中很多法院以行政行為不是依據原告主張的規范性文件作出為由,拒絕從實體上審查該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例如在“李達與訴湘潭市雨湖區人民政府確認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決定違法及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案”[2]參見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湘03行初183號行政判決書。中,法院認為因原告所訴行政行為為被告區政府作出的9號征收決定,征收決定上載明的潭政發2013[2]號文件《湘潭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實施辦法》是被征收人在補償程序中將適用的依據,而非被告作出被訴9號征收決定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故對原告提出的9號文件的合法性不予審查。有學者通過大數據的研究方法,發現在原告提出附帶審查規范性文件的案件中,有三分之一左右因為不是行政行為的依據而被拒絕進行合法性審查,占比非常之大。[3]參見王春業:“論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中‘依據’的司法認定”,載《行政法學研究》2019年第3期,第52頁。
那么如何判斷一規范性文件是否是被訴行政行為的“依據”呢?實踐中不同法院對“依據”關系的判斷差距較大,法律、司法解釋也沒有給出相關判斷標準。“依據”關系是決定規范性文件能否進入法院實體審查的關鍵因素,本文擬結合相關司法案例,構建規范性文件和被訴行政行為“依據”關系的判斷標準。
二、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的請求權基礎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3條和第64條,我國規范性文件只能間接審查不能直接審查,法院也不能撤銷不合法的規范性文件。[4]《行政訴訟法》第64條:人民法院在審理行政案件中,經審查認為本法第五十三條規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的,不作為認定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并向制定機關提出處理建議。原告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從而間接地與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具有利害關系。要想對規范性文件進行附帶審查,必須有具體行政行為作為紐帶,也就是行政行為必須是依據規范性文件作出的,只有滿足“依據”關系的文件才能被審查。
(一)規范性文件只能附帶審查
從世界范圍內來看,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模式有直接審查(抽象審查)和間接審查(附帶審查)兩種。直接審查指的是無須依托行政行為,原告直接可以請求法院審查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間接審查則必須依托具體的行政爭議。《行政訴訟法》規定,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只能在對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時,作為一項訴訟請求一并提出,而不能脫離開行政行為直接對規范性文件提出審查,因此我國的規范性文件審查屬于間接審查。
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是一項訴訟請求而不是一個獨立的訴訟,《行政訴訟法》第13條規定法院不受理“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的案件。[5]《行政訴訟法》第13條:人民法院不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下列事項提起的訴訟: (一)國防、外交等國家行為; (二)行政法規、規章或者行政機關制定、發布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決定、命令; (三)行政機關對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獎懲、任免等決定; (四)法律規定由行政機關最終裁決的行政行為。原告對規范性文件只有請求權而沒有訴權,判決的效力只及于當事雙方之間,而不是存在于規范制定者和整個社會共同體之間。立法者無意于通過司法途徑直接糾正規范性文件的違法性,但現實中規范性文件數量龐大且質量不高,立法者又無法忽視來自各方的壓力,因此設計出附帶審查的模式,在審理被訴行政行為是否合法時“順帶”檢視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6]參見中國人大網:“關于《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修正案(草案)》的說明——2013年12月23日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上”,http://www.npc.gov.cn/wxzl/gongbao/2014-12/23/content_1892443.htm,最后訪問日期:2020年1月12日。根據《行政訴訟法》和《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適用解釋》),法院只能對規范性文件的效力進行判斷,而不能對其效力進行處理。但是法院可以對行政行為的效力進行判斷并處理,且我國行政訴訟的審理中心就是判斷并處理行政行為的效力。如此一來,對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審查就變成了尋找行政行為合法性依據的前置程序。[7]參見李稷民:“論我國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的構造——解讀2018年《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帶來的變革”,載《學習與探索》2019年第1期,第72頁。對規范性文件效力判斷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是為行政行為的效力服務。附帶審查不具有處理規范性文件效力的獨立意義,其主要價值在于判斷是否和行政行為構成一般規范和個別規范的涵攝關系。[8]參見李稷民:“論我國行政規范性文件司法審查的構造——解讀2018年《行政訴訟法》司法解釋帶來的變革”,載《學習與探索》2019年第1期,第73頁。而且這種合法性判斷效力只及于個案,一法院認定某一規范性文件違法,該文件在判決生效后可能仍然有效存在。
(二)行政行為是連接規范性文件與審查的紐帶
我國行政訴訟法將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視為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延伸,[9]參見李成:“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進路的司法建構”,載《法學家》2018年第2期,第65頁。附帶審查的主要目的是為了解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根據《行政訴訟法》第25條和相關司法解釋的規定,只有相對人和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人才有資格提起行政訴訟。[10]《行政訴訟法》第25條:行政行為的相對人以及其他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有權提起訴訟。學界對利害關系的界定分歧較大,有學者梳理過我國目前有“實際影響說”“因果關系說”“不利影響說”等利害關系的判斷標準,通說認為只要存在成熟的具體行政行為對于起訴人的合法權益產生了實際影響或者不利影響,或者只要具有因果關系,就能認定“利害關系”的存在。[11]參見王克穩:“行政訴訟中利害關系人的原告資格——以兩案為例”,載《行政法學研究》2013年第1期,第40頁。江必新認為:“如果一個被訴行政行為存在與否,影響到某一個人或者組織的權利義務的增減得失,則可以說存在利害關系。”[12]江必新:“行政審判中的立案問題研究”,載《法律適用》2018年第3期,第5頁。一規范性文件不會對相對人的權利義務產生任何影響,因此與原告之間也不存在利害關系。但是當規范性文件的抽象條文通過行政行為的實施而具體化,行政行為直接影響相對人的權利義務,被實施的條文也就間接地與相對人產生利害關系。
在法律禁止直接審查的情況下,原告基于與行政行為的利害關系,對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提出審查請求,原告與規范性文件的聯系是依靠行政行為來傳遞的,只有與行政行為有關聯性的規范性文件才與原告有間接的利害關系。這里的關聯性表現為“依據”,規范性文件和行政行為構成一般規范與特別規范的涵攝關系,“相對人因與行政行為有利害關系,因此間接與行政行為的依據有利害關系,從而具有請求權基礎。”[13]李成:“行政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進路的司法建構”載《法學家》2018年第2期,第65頁。
如果作為媒介的行政行為不存在,那么原告對行政依據的規范性文件也不具有請求權。例如在吳桂林訴泰州市海陵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案中,原告起訴認為泰州市海陵區住房和城鄉建設局作出“不再受理告知書”違法,并請求一并審查該告知書依據的《建筑工程建筑面積計算規范》和《關于房屋建筑面積計算與房屋權屬登記有關問題的通知》兩份規范性文件。該被訴告知書屬于行政機關對信訪事項的處理,不具有強制力,也不影響相對人的實體權利義務,因此該訴求不屬于行政訴訟受案范圍。連接規范性文件和附帶審審查的紐帶已經斷裂,起訴人所訴不屬于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故一并提起對規范性文件審查也無根據,法院不予受理。[14]參見泰州醫藥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人民法院(2017)蘇1291行初359號行政裁定書。
三、“依據”的范圍——相關條款還是整個文件
作為被訴行政行為“依據”的是規范性文件整體,還是文件中的相關條款?法院在實踐過程中一般認為審查范圍僅是依據的相關條款,從附帶審查的效果和審查效率上來講,“依據”的范圍也應當被限定在相關條款之中。
(一)法律及相關司法解釋確立的標準
《行政訴訟法》第53條規定“……認為行政行為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可以一并請求對該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15]《行政訴訟法》第53條: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行為所依據的國務院部門和地方人民政府及其部門制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在對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時,可以一并請求對該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前款規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含規章。法條原文使用的是“該規范性文件”,從文意解釋的角度來看指的是文件整體,而非規范性文件的相關條款。《適用解釋》第148條規定,法院在審查時“可以”從“規范性文件制定機關是否超越權限或者違反法定程序”和“作出行政行為所依據的條款以及相關條款”等方面進行。[16]《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148條:人民法院對規范性文件進行一并審查時,可以從規范性文件制定機關是否超越權限或者違反法定程序、作出行政行為所依據的條款以及相關條款等方面進行。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行政訴訟法第六十四條規定的“規范性文件不合法”: (一)超越制定機關的法定職權或者超越法律、法規、規章的授權范圍的; (二)與法律、法規、規章等上位法的規定相抵觸的; (三)沒有法律、法規、規章依據,違法增加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義務或者減損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合法權益的; (四)未履行法定批準程序、公開發布程序,嚴重違反制定程序的; (五)其他違反法律、法規以及規章規定的情形。司法解釋將超越權限、違反法定程序、行政行為依據的條款置于并列的地位,審查的范圍不局限于行政行為依據的相關條款。從立法的角度,似乎很難得出法院只審查行政行為依據的相關條款。
(二)法院相關案例確立的標準
然而在實務中,法院認定的“依據”與立法的表述有所偏差,不少法院認定審查范圍僅是依據的相關條款。有地方法院在附帶審查規范性文件時首先要求原告指出請求審查具體的條款,其次才會判斷依據關系是否成立。如在“趙芙蓉訴天津市紅橋區房產總公司、天津市紅橋區邵公莊房管站不履行職責案”[17]參見天津市紅橋區人民法院(2015)紅行初字第0043號行政判決書、天津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6)津01行終130號行政判決書。中,原告提起行政訴訟,同時提出對《天津市公有住房變更承租人管理辦法》第9條一并審查。庭審過程中,被告表示天津市紅橋區邵公莊房管站拒絕給原告辦理過戶的理由不成立,應當依據《天津市公有住房變更承租人管理辦法》第10條第(七)項的規定。由此,原告將申請審查的條款變更為《天津市公有住房變更承租人管理辦法》第10條第(七)項。法院在原告明確相關條款之后才開始審查被訴行為與待審查條款之間的依據關系。2018年10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九例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的典型案例,在新聞發布會上,最高院行政審判庭副庭長王振宇指出:可審查的規范性文件的范圍是作為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的相關條款。[18]參見中國法院網:“行政訴訟附帶審查規范性文件典型案例新聞發布會”,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 cle/subjectdetail/id/MzAwNMgygAMA.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19年12月24日。最高院的態度非常鮮明,只有依據的條款可以附帶審查,這批典型案中的第九號“毛愛梅等訴賀村鎮人民政府案”[19]參見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區人民法院(2016)浙0802行初19號行政判決書。,也體現了最高院的立場。原告訴訟請求中提出對江山市人民政府《關于深入推進生豬養殖污染整治和規范管理的通知》(江政辦發[2014]29號)進行審查,法官在判斷該文件是否構成依據之前,要求原告明確對文件中的哪一條款進行審查,原告在庭審過程中確認是該文件的第3條第3款不合法,法院此后才判斷第3條第3款是否構成被訴行政行為的依據。最高院將此案例作為典型案例公布,其認為“依據”只能是個別條款,原告在請求附帶審查規范性文件時,應當明確具體條款,法院不審查文件整體。
(三)以相關條款為審查核心
學界對于規范性文件的審查范圍存在爭議,有學者認為“附帶審查只是強調啟動程序上不能脫離被訴行政行為而單獨起訴,一旦程序開始后,法院應當對規范性文件進行全面審查。”[20]黃學賢:“行政訴訟中行政規范性文件的審查范圍探討”,載《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5期,第104頁。筆者不贊同上述觀點,關聯性的審查應當以規范性文件的相關條款為核心,而非規范性文件整體。首先,我國的附帶審查制度是一種間接審查,不僅僅在啟動程序上不能脫離被訴行政行為,在審理過程中也應當以被訴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為中心。筆者上文已述,行政行為是連接規范性文件和附帶審查的紐帶,一旦行政行為這一紐帶不存在,規范性文件也就不能獨立被法院審查。規范性文件中與被訴行政行為無關的條款無此連接紐帶,后續法院的審理行為也與此類條款無關,如果法院對此類無關的條款進行附帶審查,就脫離了行政審判的中心。其次,原告對除依據的相關條款之外的規范性文件沒有訴的利益,如果法院對此類條款進行審查,那么“附帶性”就無從談起,與被訴行為無利害關系的條款被法院直接審查,與我國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制度設計的方向相背離。此外,司法資源的有限性也決定了法院不可能對整個文件進行審查。從2016年1月到2018年10月,全國一審行政案件收案中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約為3880件。[21]參見中國法院網:“行政訴訟附帶審查規范性文件典型案例新聞發布會”,https://www.chinacourt.org/arti cle/subjectdetail/id/MzAwNMgygAMA.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19年12月24日。如果法院對這每一份規范性文件的每一條款進行合法性審查,工作量十分巨大,實踐中也并不具有可操作性。有限的司法資源應當集中到核心爭議中,集中審查與被訴行為有關聯性的條款。
《行政訴訟法》和《適用解釋》的相關條款未明確附帶審查的是規范性文件整體還是相關條款,但是地方法院在實際審理中只審查相關條款,未對文件整體作出合法性評價。最高法院發布的典型案例也支持了地方法院的觀點,明確表示“依據”是規范性文件的相關條款而非全部文件。從理論上講,對文件整體進行審查也缺乏可操作性。因此,“依據”關系實質上是判斷行政行為與規范性文件相關條款的關聯性,《行政訴訟法》第53條“……可以一并請求對該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應當理解為“對規范性文件的相關條款進行審查”。
四、“依據”判斷的形式標準
“依據”判斷的形式標準指的是法院根據行政機關的行為或者意思表示判斷一規范性文件是否是被訴行政行為的依據,此標準不涉及規范性文件相關條款的具體內容,僅以行政機關的表示行為為判斷基礎。形式標準因其簡便易行而備受法院青睞,那么該標準是否能識別所有的“依據”關系呢?
(一)形式標準的界定
我國行政訴訟構造要求被告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承擔舉證責任,被告應當提交證明被訴行政行為合法的全部證據和規范性文件。一旦被告無法提供相關證據或依據的規范性文件,將承擔敗訴的風險。為避免承擔敗訴風險,行政機關一般在行政程序中注重證據的搜集和法律依據的援引,在行政決定書中列明行政行為的相關依據,或者在法庭上提交行政行為依據的法律規范。形式上“依據”關系就是行政機關在行政決定書中援引的規范性文件或者行政機關在訴訟過程中提交的證明自身行為合法的規范性文件。法院通過判斷行政機關在行政決定書中是否援引,或者在訴訟中是否提交來判斷行政行為與規范性文件之間是否存在關聯關系,而不需要對規范性文件相關條款的具體內容進行進一步審查。
部分法院將形式標準作為判斷關聯關系是否存在的主要標準。如在“周悟權訴北京市石景山區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不履行法定職責案”[22]參見北京市石景山區人民法院(2015)石行初字第117號行政判決書。中,原告請求法院對《北京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受理違法案件舉報實施辦法(試行)》(以下簡稱《舉報實施辦法》)第15條、第17條、第18條以及《北京市食品藥品監督行政處罰程序規定實施細則》第13條第5款的合法性進行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石景山區法院經過審理,在裁判理由中認為:由于被告已經明確表示其在執法中并未適用《舉報實施辦法》第17條,故在本案中對此條的合法性不進行審查。在此案件中,法院直接以形式標準作為判斷依據,只要行政機關的意思表示表明沒有適用的條款就不存在關聯性,即不可能構成被訴行政行為的依據。還有法院認定,行政機關在行政決定書中沒有載明的規范性文件不構成依據。例如在“吳毅訴長沙市望城區國土資源局限期騰地決定案”[23]參見望城縣人民法院(2016)湘0112行初40號行政判決書。中,原告申請對《長沙市征地補償監督暫行辦法》第2條第5款第一句、長沙市國土資源局《關于實施〈長沙市征地補償實施辦法〉有關問題的意見》第1條第1款第3項關于“自然戶”的認定、《〈望城縣征地補償安置辦法〉實施細則》第17條、第19條“農嫁非”進行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法院認為:“本案審查的是被告作出的被訴《限期騰地決定書》的合法性,被告作出的被訴限期騰地決定書并未載明適用了上述三個規范性文件,因此對上述三個規范性文件的合法性本院不予審查。”望城縣法院在類似案件中都采取此種觀點,同樣以被告行政決定書未載明原告請求審查的規范性文件為由拒絕附帶審查。[24]參見望城縣人民法院(2016)湘0112行初38號行政判決書。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于2016年10月8日討論通過典型案例“朱某訴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總隊要求履行法定職責及請求規范性文件一并審查案”,確立了《行政訴訟法》第53條“依據”關系的判斷標準:若該被申請審查的規范性文件未在被訴行政行為的載體中明確載明,或被告在答辯或應訴中明確表示被申請審查的文件不是被訴行政行為的法律適用依據,法院應當告知申請人其請求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53條的規定,并在裁判文書釋明不予準許的理由。[25]參見上海法院網:“朱某訴上海市公安局交通警察總隊要求履行法定職責及請求規范性文件一并審查案”,http://shfy.chinacourt.gov.cn/article/detail/2017/08/id/2948806.shtml,最后訪問日期:2019年9月3日。
(二)形式標準的特殊問題:經復議行為的依據
形式標準下,未經復議的行政訴訟案件可以通過被告的行政決定書和答辯應訴情況判斷規范性文件是否構成依據,但經過行政復議的案件情況稍加復雜。根據《適用解釋》第22條,只要復議機關未改變原行為的處理結果,改變原行為適用的規范依據也被視為復議維持。[26]《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22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是指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的處理結果。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所認定的主要事實和證據、改變原行政行為所適用的規范依據,但未改變原行政行為處理結果的,視為復議機關維持原行政行為。 復議機關確認原行政行為無效,屬于改變原行政行為。 復議機關確認原行政行為違法,屬于改變原行政行為,但復議機關以違反法定程序為由確認原行政行為違法的除外。復議機關維持原行為處理結果但改變適用依據的情況下,原告在訴訟中如果同時對作出行政行為的機關依據的規范性文件,和復議機關變更后的規范性文件提起附帶審查,應當如何判斷“依據”關系呢?作出原行為的機關在行政決定書中援引甲規范性文件中的A條款,并在應訴過程中提交,而復議機關則在應訴過程中認定適用的是甲規范性文件中的B條款和乙規范性文件中的C條款,法院應當對哪一份規范性文件的哪一條款進行附帶審查呢?在判斷經復議的行政行為與規范性文件的關聯性之前,首先應當明確行政訴訟的審理對象,是復議行為的合法性還是原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確定審理對象之后才能判斷該對象是否與行政機關提交的規范性文件之間具有關聯性。
1.法律、司法解釋的嬗變
最高院2000年發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00年解釋》)認為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的事實、證據、規范依據、處理結果的,都屬于“復議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27]《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現已失效)第7條:復議決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屬于行政訴訟法規定的“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 (一)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所認定的主要事實和證據的; (二)改變原具體行政行為所適用的規范依據且對定性產生影響的; (三)撤銷、部分撤銷或者變更原具體行政行為處理結果的。如此,若復議機關改變原行為規范依據,相對人應當以復議機關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審理對象自然也就是復議行為,關聯性判斷也應當是復議行為與復議機關改變后的規范性文件。此后2015年頒布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2015年解釋》)則改變了對“復議維持”和“復議改變”的規定,“復議改變”僅指復議機關改變原行為的處理結果,而復議機關對事實、證據、規范依據等的改變只要未改變最后的處理決定就屬于“復議維持”。[28]《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現已失效)第6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包括復議機關駁回復議申請或者復議請求的情形,但以復議申請不符合受理條件為由駁回的除外。 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第二款規定的“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是指復議機關改變原行政行為的處理結果。之后2018年的《適用解釋》沿襲了《2015年解釋》對“復議維持”和“復議改變”的規定。針對行政訴訟中經復議行為的審理對象,《2015年解釋》第9條規定:行政訴訟對原行為合法性和復議程序合法性進行審查。[29]《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現已失效)第9條: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在審查原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同時,一并審查復議程序的合法性。行政訴訟只審查復議程序的合法性而非復議決定的合法性,這表明法院應當將改變適用規范后的行為歸入到原行為之中去審查,并不將復議決定的合法性作為一個單獨的審查對象。換言之,法院并非將行政復議決定和原行為視為兩個單獨的審查對象,而是將兩者合并審查,這時審查的“原行政行為”實際上是經過復議修正的“原行政行為2.0版”。[30]參見趙大光、李廣宇、龍非:“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案件中的審查對象問題研究”,載《法律適用》2015年第8期,第79頁。但是2018年《適用解釋》135條第1款將“復議程序”改為“復議決定”,行政訴訟對原行為合法性和復議決定的合法性進行審查。[31]《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135條第1款:復議機關決定維持原行政行為的,人民法院應當在審查原行政行為合法性的同時,一并審查復議決定的合法性。這似乎推翻了將原行為和復議行為合并作為整體審查的結論。但是2018年《適用解釋》第125條又增加了第3款:復議機關在復議程序中收集和補充的證據,可作為認定復議決定和原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32]《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的解釋》第135條第3款:復議機關作共同被告的案件,復議機關在復議程序中依法收集和補充的證據,可以作為人民法院認定復議決定和原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結合2018年《適用解釋》第22條對“復議維持”和“復議改變”的規定來看,復議機關可以根據自己對事實證據的調查和規范適用的理解,對原行政行為進行補強。復議機關補充的理由可以證明原行為合法,此時在訴訟中被審查的原行為也是經過復議修訂的“行政行為2.0版”,復議行為依附于原行政行為。因此,即使行政訴訟審查的對象變更為原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和復議決定的合法性,如果復議改變原行為適用規范,關聯性的判斷也應當是圍繞經復議變更后的適用規范和原行政行為,而非原機關最初適用的規范。
2.原處分主義原則
原處分主義原則指的是“原行政行為之違法僅可以在面向該行為的撤銷訴訟中主張,而不可以在針對復議決定的撤銷訴訟中主張。”[33]梁君瑜:“復議維持‘雙被告制’之再檢討”,載《河北法學》2019年第6期,第77頁。與原處分主義相反,裁決主義主張撤銷訴訟只能針對復議決定。德國、日本、我國臺灣地區在審理對象上均采納原處分主義原則。
德國《行政法院法》第79條規定了撤銷之訴的訴訟標的是“經過復議決定肯定的原本行政行為”。在第三人因復議決定首次受侵害,或者復議決定對原行為構成“補充性的獨立負擔”的,撤銷之訴的訴訟標的才是復議決定。[34]《德國行政法院法》第79條:1、撤銷之訴的標的是:(1)原本行政行為,以其經過復議決定肯定的形式為準;(2)復議決定,如果第三人因該決定首次受到侵害。2、復議決定包含不同于原本行政行為的補充性獨立負擔的,也可單獨成為撤銷之訴的標的。作出復議決定中,對程序規定的嚴重違反,也視為補充性負擔。準用第78條第2款規定。因此,如果復議改變了原行為的事實、理由、適用規范,只要沒有形成“補充性的獨立負擔”,行政訴訟的審查對象仍然是原行政行為,復議只對原行為起到修正作用但是不能替代原行為。
我國臺灣地區在經復議行為的訴訟標的上也采納了原處分主義。臺灣地區的“訴愿”相當于大陸地區的“復議”,“行政處分”相當于“行政行為”。臺灣地區的原處分主義,指的是“原告對于行政處分不服的,應就行政處分提起撤銷訴訟,不得就訴愿決定提起撤銷訴訟;原處分之違法,僅得于原處分之撤銷訴訟中主張,不得于裁決之撤銷訴訟中主張。”[35]徐晃瑞:《行政訴訟法》,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版,第65頁。臺灣地區“行政訴訟法”第24條規定原處分經訴愿決定維持時,以原處分機關為被告,以此推論,應以原處分為訴訟對象。再結合“訴愿法”第79條,訴愿決定可以修改原處分的理由并駁回訴愿申請。因此,訴愿機關可以變更原處分的適用規范但不改變原處分結果,相對人在撤銷訴訟中只能就原處分提出請求。
3.判斷原行為與復議變更后的規范之間的“依據”關系
行政復議程序是對行政行為的一種糾錯機制,屬于行政體系內部的監督。復議機關根據自身對事實、證據、適用規范的把握對原行政行為進行修正,是行政內部監督的應有之義。行政訴訟應當以原行政行為為審理對象,只不過該原行政行為已經經過復議機關修正。回到本小節最初提出的問題,在形式標準下,法院應當認定原行政決定與甲規范性文件中的B條款和乙規范性文件中的C條款存在關聯關系。
(三)形式標準的缺陷
僅以行政機關的表示行為判斷是否構成依據關系對法院來說雖然操作簡單,但隨意性較大,只要行政機關援引,法院就認定為依據,行政機關不援引,法院就不認定為依據,使得法院作為中立裁判者的地位模糊不清。僅以形式標準來判斷依據關系在司法實踐中也引發了一系列混亂。
1.行政機關在行政決定書和應訴過程中表示不一致
在行政機關前后表示行為不一致的情況下,按照形式標準似乎很難判斷依據關系是否存在。例如在“周誠超訴宜興市稅務局稅務行政管理案”[36]參見宜興市人民法院(2018)蘇0282行初53號行政判決、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02行終18號行政判決書。中,被告宜興稅務局在對原告作出的《告知書》中表明《國家稅務總局關于未申報稅款追繳期限問題的批復》(國稅函[2009]326號)(以下簡稱《國稅總局批復》)是作出被訴《告知書》的規范依據,但是在一審開庭時,被告又否認《國稅總局批復》是被訴行政行為的適用規范依據。如果僅依據形式標準,當被告前后表述不一致時,法院應當如何認定?一審宜興市法院摒棄了形式依據,從《國稅總局批復》規定的內容來判斷是否構成依據,最終根據實體內容與行政行為之間的關系判斷存在依據關系,從而對《國稅總局批復》進行附帶審查,二審法院支持了一審法院的觀點。
2.行政機關故意援引或者故意不援引
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行為時,為了增加行為的說服力,使行為“看起來”法律依據充分,可能在行政決定書中列明許多與行政行為無關的規范性文件,如果僅依據形式標準判斷,法院應當對行政機關列明的所有規范性文件進行附帶審查,這一舉措無限擴大了附帶審查的范圍,有違制度初衷。例如在吳錦祥訴蘇州社保中心要求支付社會保險待遇一案[37]參見昆山市人民法院(2017)蘇0583行初136號行政判決書。書中,原告在起訴被告作出的蘇工傷不先支字[2017]第1號工傷保險不予先行支付決定書時,一并請求對社保部《關于印發工傷保險經辦規程的通知》(人社部發[2012]11號)(以下簡稱《工傷保險經辦規程》)第73條附帶審查。被告在作出不予先行支付決定書之前,原告曾向被告申請先行支付,被告也出具了一份答復書,在答復書中載明的依據是《工傷保險經辦規程》的第73、74、76條,但是在最終正式的不予先行支付決定書中,載明的依據為《工傷保險經辦規程》,并未明確相關條款。本文已述,對規范性文件的附帶審查應當具體到相關條款而不是文件整體,綜合蘇州社保局作出的答復書和被訴不予先行支付決定書來看,被告認為的被訴決定書的依據應當是《工傷保險經辦規程》的第73、74、76條。但實際上只有第73條規定的內容可能與本案相關,法院也只判斷73條是否與被訴決定書之間存在依據關系。如果法院對被告列明的所有條款進行審查無疑會造成司法資源的浪費。
此外,實踐中還存在行政機關為了避免法院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而故意不在決定書中列明依據的文件,或者在庭審過程中否認援引規范性文件。例如在“王淑蓉訴漢源縣公安局治安行政處罰案”[38]參見雅安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川18行終6號行政判決書。中,被告向法院提交了《關于依法處理違法上訪行為意見》,但在庭審時強調該文件只是作為參考意見,而且在行政處罰文書中也沒有載明該文件,法院由此拒絕附帶審查該文件。如果法院堅守形式標準,在行政機關故意不列明適用規范、拒絕承認援引的情況下無疑會使當事人認為法院只聽信一面之詞,使得法院的中立性和權威性降低,同時也不正當限縮了附帶審查規范性文件的范圍,有違立法目的。
3.行政機關適用規范性文件錯誤
適用規范性文件錯誤指的是“行政機關在作出行政處理決定時錯誤援引規范性文件或者規范性文件的相關條款,是執法過程中法律選擇的錯誤。其實質在于行政案件事實與行政規范不適當的結合”。[39]關保英:“行政適用法律錯誤若干問題探討”,載《法學》2010年第4期,第39頁。如被告在作出行政決定時援引甲規范性文件,但在法院在審理時發現被告實際上不應當援引甲規范性文件而應當援引乙規范性文件,然而原告一并請求對甲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如果堅持形式審查標準,即應當認為被訴行為與甲規范性文件具有關聯性,但從效力上分析甲規范性文件的處理范圍不能涵蓋被訴行政行為,此時適用形式標準判斷依據關系顯屬不當。
4.小結
依據關系的形式標準是法院通過行政機關的表示行為判斷一規范性文件是否構成被訴行政行為的依據。形式標準簡潔明了,易于判斷,在實踐中也有不少法院采納。但不可忽視的是,形式標準可能造成法院中立性與權威性的喪失,如果行政機關故意援引或者故意不援引規范性文件,或者適用錯誤的規范性文件,使用形式判斷標準無法得出正確的結論。形式標準并非是判斷依據關系的唯一標準,法院在訴訟中需進一步審查規范性文件的實體內容與被訴行為之間的關系,探尋關聯性判斷的實質標準。
五、“依據”判斷的實質標準
形式標準難以識別全部“依據”關系,有法院在實踐過程中拋棄以行政機關的表示行為為基礎的判斷標準,轉而分析規范性文件的具體內容與被訴行政行為之間的關聯關系,以識別“依據”關系是否存在,這就是“依據”關系判斷的實質標準。那么實質標準有何特殊之處?是否能彌補形式標準的缺陷?
(一)規范性文件對行政機關具有拘束力
實質標準的第一步是要判斷規范性文件是否對被訴行為具有拘束力。規范性文件對行政機關的拘束力指的是行政機關遵守規范性文件的相關內容,按照規范性文件的規定作出行為的效力。實質判斷的第一步是界定規范性文件的相關條款是否在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的過程中對行政機關產生必須遵照執行的效力。與形式標準的差異是,這種遵照執行的效力來源于規范性文件規定的內容,而非源自行政機關自身的承認。
1.拘束力的判斷標準
規范性文件對行政機關的拘束力主要表現在規范性文件能夠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提供支持,這種支持可能是任何一個方面的,包括職權、內容、程序、形式等,因此行政機關遵守規范性文件的內容作出相關行政行為。但是這種拘束力只針對行政機關而不針對法院,法院是否認可這種拘束力則需要在具體對涉案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后才能得出結論。王紅衛、廖希飛認為“只要規范性文件對行政機關具有拘束力,就應當認定該規范性文件是行政行為的依據”[40]王紅衛、廖希飛:“行政訴訟中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制度研究”,載《行政法學研究》2015年第6期,第32頁。,但是作者沒有明確拘束力的限定對象是行政機關還是法院。筆者認為拘束力的對象只有行政機關而不包括法院,否則會有邏輯顛倒之嫌。一般而言,首先判斷一規范性文件是否是被訴行為的依據,對于是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才進行附帶審查,審查之后對于合法的規范性文件作為認定行政行為合法的依據,即該規范性文件能夠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提供支持應當是在法院對規范性文件審查之后才能得出結論。王紅衛和廖希飛在“依據認定”這一環節將“規范性文件能夠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提供支持”作為認定規范性文件是行政行為的依據的判斷標準,實際上已經預設前提:該規范性文件合法。因此筆者認為,在對拘束力進行判斷時要限定約束的對象只有行政機關而不包括法院。
拘束力的判斷是否需要唯一性?換句話說,法院認定的、能夠作為被訴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是否必須是行政行為的唯一依據和直接依據?如果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引用的不僅僅是規范性文件,還有該規范性文件的上位法,可否認定為該規范性文件對行政機關具有拘束力?如果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時援引兩項規范性文件,但只根據其中一項規范性文件就能得出行政行為合法的結論,能否否認另一份規范性文件的依據地位?在“崔占英訴北京市延慶區延慶鎮人民政府履行法定職責案”[41]參見北京市延慶區人民法院(2017)京0119行初78號行政判決書、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2018)京01行終717號行政判決書。中,崔占英提出附帶審查《延慶鎮2014-2015年村民住宅抗震節能工程實施辦法》(以下簡稱《2014-2015實施辦法》)的合法性,但是法院判決認為,《2014-2015實施辦法》雖然是延慶鎮政府在信訪事項答復意見書中明確告知崔占英不能享受村民住宅抗震節能補貼結論的依據,可以視為延慶鎮政府對崔占英翻建房屋作出不予初審通過結論的依據。但結合前述分析,崔占英翻建房屋并不符合《北京市抗震節能型農民住宅建設項目管理辦法》(京建發[2010]442號)規定的新農宅項目建設條件,即便延慶鎮政府不援引《2014-2015實施辦法》作為不予初審通過之依據,崔占英仍不符合初審通過之條件,故對《2014-2015實施辦法》已無審查之必要。法院的觀點是,如果還有其他文件能夠認證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那么就無須對原告請求的規范性文件進行附帶審查,即只有行政行為的唯一依據才能被審查。
我國規范性文件審查具有“附帶性”的特點,審查的目的是為行政行為服務,為了檢視該文件是否能證成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如果有其他法律規范能夠證成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那么似乎訴訟目的已經達成,無須對依據的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事實上,立法者創設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制度,不僅僅是單純的解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立法者也希望通過此制度間接地、部分地解決規范性文件的效力問題,從源頭上解決違法行政行為,以此達到維護公法秩序的目的。[42]參見王紅衛、廖希飛:“行政訴訟中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制度研究”,載《行政法學研究》2015年第6期,第32頁;程琥:“新《行政訴訟法》中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制度研究”,載《法律適用》2015年第7期,第91頁。所以當行政行為合法性已經被證成的情況下,主觀目的已然達成,但作為整體的制度目的仍然未能實現。規范性文件的拘束力判斷應該是獨立的,如果因為還有其他規范可以證明被訴行為的合法性而使被請求的規范性文件免于被附帶審查,容易造成附帶審查制度范圍被不當限縮。如果只有唯一依據才能進入審查,那么該制度的適用范圍將十分有限,與設立該制度的初衷相悖。并且從文意解釋的角度來看,《行政訴訟法》第53條“……行政行為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并非行政行為依據的唯一規范性文件,“依據的文件”本就包含復數個的理解。不論是從目的解釋還是從文意解釋的角度均可以得出,法院審查的規范性文件不必須是行政行為的唯一依據。
2.拘束力判斷解決形式標準的缺陷
就行政機關對是否援引規范性文件前后表述不一致,或者故意在行政決定書中援引、故意不援引規范性文件的情況,上文已述,依據形式標準很難做出是否屬于依據的判斷。但是如果運用拘束力的判斷標準,不論行政機關是否在行政決定書中援引,或者在答辯時提交,只要根據規范性文件的相關條款判斷行政行為是否受其拘束即可。如筆者在上文列舉的“周誠超訴宜興市稅務局稅務行政管理案”[43]參見宜興市人民法院(2018)蘇0282行初53號行政判決、無錫市中級人民法院2019蘇02行終18號行政判決書。,被告稅務局在作出被訴《告知書》時援引《國稅總局批復》,但是在一審開庭時,又否認《國稅總局批復》是被訴行政行為的適用規范依據。兩審法院均沒有采納形式標準判斷是否存在依據關系,而是對《國稅總局批復》規定的內容進行了實體審查。根據《國稅總局批復》的規定:“納稅人不進行納稅申報造成不繳或少繳應納稅款的情形不屬于偷稅、抗稅、騙稅,其追征期一般為三年,特殊情況可以延長至五年。”而被訴《告知書》的內容是原告舉報的盧某的個人所得稅已超過法定稅款追征期而不予追征。顯然,被告稅務局遵照執行《國稅總局批復》的相關條款,才做出被舉報人盧某的個人所得稅款已超過法定稅款追征期,不予追征的決定,規范性文件《國稅總局批復》對于被訴行為具有拘束力,應當認為兩者之間具有關聯關系,《國稅稅總局批復》可以作為被訴行政為的依據被附帶審查。對于行政機關故意援引或者故意不援引的規范性文件,同樣是由法院對規范性文件的條款和被訴行為進行對比,判斷規范性文件對行政行為是否具有拘束力。法院以裁判者的身份對是否具有拘束力進行判斷后再判斷是否具有依據關系,避免只通過行政機關的表示行為判斷,有利于保障法院的中立性和權威性。
3.拘束力判斷不能解決的問題
拘束力判斷雖然能解決形式標準中行政機關故意援引或者故意不援引,前后表述不一致的缺陷,但其本身也并非完美,僅依靠拘束力判斷并不能識別所有依據關系。上文提出,只要規范性文件能夠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提供支持,不論是職權、內容、程序、形式等方面均可以視為具有拘束力。如果行政機關在訴訟中將規范性文件作為證據提供,但是在作出行政決定時并未援引為“依據”,此種情況下該規范性文件確實能夠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提供一部分支持,但是其并非行政行為的依據。例如在“戎愛國訴南京市棲霞區住房和建設局(以下簡稱棲霞區住建局)信息公開案”[44]參見南京鐵路運輸法院(2016)蘇8602行初1243號行政判決書、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蘇01行終162號行政判決書。中,戎愛國申請棲霞區住建局公開的信息為本市小市新村139號公有住房承租人的承租信息,棲霞區住建局在一審中當庭向法庭提交寧編字(1986)56號《關于各區建立房產經營公司和人員編制的通知》(以下簡稱《56號通知》)以證明自己不掌握戎愛國申請公開的信息。兩審法院均沒有對作為證據提交的《56號通知》進行附帶審查。行政行為的合法性一般分為事實上的合法性和法律上的合法性,事實上的合法性由行政機關訴訟中提交的證據來證明,法律上的合法性由行政機關提交的法律規范來證明。這兩者都能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提供支持,那么作為證據提交的規范性文件是否同作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一樣可以被附帶審查呢?《行政訴訟法》第34條[45]《行政訴訟法》第34條:被告對作出的行政行為負有舉證責任,應當提供作出該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對證據和作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做了區分處理:被告應當提交作出該行政行為的證據和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法院對證據和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程序也不相同,對行政訴訟的證據,主要審查其證據“三性”,即客觀性、合法性、關聯性;對規范性文件的審查重點則在制定權限、程序、內容等方面。證據是來源于具體行政訴訟案件的,不能脫離于具體案件而單獨談證據。但是規范性文件并非來源于某一具體案件,其獨立于具體案件而存在。且法院在審查證據的合法性時主要針對證據的取得、證據的保存情況,但是規范性文件根本不涉及取得、保存的合法性。無論從立法者原意,還是從兩者的性質、內容、審查方法來看,證據和作為規范依據的規范性文件都應當作出區分處理。然而拘束力無法識別此兩者的不同,不論是作為證據還是作為依據提交的規范性文件都能為被訴行為的合法性提供支持,因此法院通過此標準難以判斷出應該審查哪一類文件。
(二)規范性文件創制的法律關系與被訴行為具有一致性
法律關系是由法律規范形成的兩個或者多個主體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46]參見趙宏:“法律關系取代行政行為的可能與困局”,載《法學家》2015年第3期,第42頁。法律規范創設的權利義務關系如果與行政機關通過行政行為創設的權利義務關系不一致,則該規范和行政行為之間不具有關聯關系。例如在“李達訴湘潭市雨湖區人民政府(以下簡稱雨湖區政府)確認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決定違法及規范性文件附帶審查案”[47]參見湘潭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湘03行初183號行政判決書。中,原告起訴的行為是雨湖區政府的9號征收決定,征收決定上載明的潭政發2013[2]號文件《湘潭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實施辦法》是告知被征收人在補償程序中將適用的依據,而非作出9號征收決定所依據的規范性文件,至于后續的補償程序中是否具體適用該規范性文件,以及是否對原告的合法權益產生實際影響,不是審理9號征收決定合法性時應審查的內容故對潭政發2013[2]號《湘潭市國有土地上房屋征收與補償實施辦法》的合法性本院不予審查。原告請求審查的潭政發2013[2]號文件創制的是有關征收補償的權利義務關系,但是被訴行政行為是征收決定并非征收補償,規范性文件創制的權利義務關系與被訴行為不具有一致性,故該規范性文件不是被訴行為的依據,不得被附帶審查。
通過“法律關系一致性”的判斷能解決拘束力判斷中作為證據的規范性文件的審查問題。如在上文提到的“戎愛國訴棲霞區住建局信息公開案”[48]參見南京鐵路運輸法院(2016)蘇8602行初1243號行政判決書、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2017)蘇01行終162號行政判決書。中,被訴行為是信息公開,而原告請求附帶審查的《56號通知》創制的權利義務關系是有關企業改制之后的人員歸屬關系,與信息公開無關。從拘束力上判斷《56號通知》能夠為信息公開行為的合法性性提供一定的事實上的支持,但是從實體法律關系來看,《56號通知》創制的法律關系無涉信息公開,被訴《不予公開決定書》的規范依據是《政府信息公開條例》。
(三)涵攝與規范性文件的適用
涵攝作為法律適用過程中所運用的法律論證的一種,指的是“將特定案件事實歸屬于法律規范的構成要件之下,以得出特定法律后果的推論過程”。[49]雷磊:“為涵攝模式辯護”,載《中外法學》2016年第5期,第1207頁。涵攝并非是法的發現的重要工具,其主要適用場景是法的證立,相較與法的發現而言,法的論證更加關注的是法的證立即為得出的法學結論提供正當化說理的過程,由此得出涵攝是法的論證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果要主張司法裁判是特定法律的適用結果,則其應當通過特定的邏輯檢測,涵攝就是檢測法律論證正確與否的重要工具。“依據”關系的判斷也就是法的適用過程的判斷,運用涵攝則可以對其邏輯可靠性進行檢驗。
涵攝的模式是將外延較小的概念規劃到外延較寬的概念之下,[50]參見[德]拉倫茨:《法學方法論》,陳愛娥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版,第152頁。將作為小前提的特定案件事實歸化到作為大前提的法律規范之下,最終得出有關法律事實引起后果的判決。運用涵攝可解決行政機關錯誤適用規范性文件的問題。例如在“冼錦光訴中山市海洋與漁業局(以下簡稱海洋與漁業局)、中山市人民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海洋漁業行政登記及行政賠償[51]參見中山市第一人民法院(2015)中一法行初字第246號行政判決書、中山市中級人民法院(2016)粵20行終39號行政判決書。案”中,被告海洋與漁業局援引粵府辦[1990]76號《關于加強沿海摩托艇管理的通知》認為原告的的船舶不符合條件,不予登記。但是被告援引的文件是對“海上摩托艇”的規制,而原告申請登記的是船舶并非摩托艇。本案中的大前提是有關海上摩托艇的法律規范,但船舶并非小前提中的一個示例,因此概念涵攝不能成立,行政機關也就不能適用該規范。
在進行依據關系的實質判斷時,首先應當判斷待審規范性文件是否對行政行為具有拘束力,只要規范性文件能夠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提供支持,這種支持可能是任何一個方面的,包括職權、內容、程序、形式等,就可以判斷具有拘束力。但拘束力判斷不能解決行政機關將規范性文件作為證據提交的問題,在此情況下還需要進行法律關系的判斷,如果與行政機關通過行政行為創設的權利義務關系不一致,則該規范和行政行為之間不具有關聯關系。此外,針對形式標準不能解決的行政機關錯誤適用規范性的問題,如果將不能作為小前提的案件事實歸化到規范性文件之下,則涵攝不成立,依據關系也不存在。
結 論
我國規范性文件只能附帶審查,原告基于與行政行為之間的利害關系,對行政行為依據的規范性文件提出審查請求,原告與規范性文件的聯系是依靠行政行為來傳遞的,只有與行政行為有關聯性的規范性文件才與原告有間接的利害關系,這里的關聯性就表現為“依據”關系。依據關系的判斷有形式和實質標準。形式標準指的是法院根據行政機關的行為或者意思表示判斷一規范性文件是否是行政行為的依據,這一標準簡便易行,實踐中有不少法院采納。但是形式標準無法解決行政機關故意援引或者故意不援引規范性文件,或者適用錯誤的規范性文件的問題,容易造成法院中立性的喪失。實質標準則需要根據規范性文件的具體內容判斷,首先判斷規范性文件對行政機關作出行政行為是否具有拘束力,如果規范行為文件能夠為行政行為的合法性提供一部分支持,則具有拘束力。拘束力判斷可以解決行政機關故意援引或者不援引規范性文件的問題,但也并非完美,如果行政機關將規范性文件作為證據提交,則拘束力標準也無法準確得出結論,因此還要進行法律關系判斷,如果與行政機關通過行政行為創設的權利義務關系不一致,則該規范和行政行為之間不具有關聯關系。此外,涵攝模式可以為行政機關錯誤適用規范性文件的情況提供解決思路,涵攝關系不成立則依據關系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