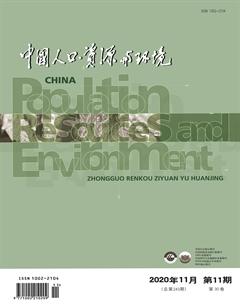多重動機對中國居民親環境行為的交互影響
蘆慧 劉嚴 鄒佳星 陳紅 龍如銀



摘要?實現居民親環境行為自覺是彌補當前親環境行為“高認知度、低踐行度”的“知-行”缺口現象的重要途徑。本研究在梳理國內外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基于規范焦點理論和自我決定理論,對三類親環境行為動機所具備的環保規范情境特征進行理論分析,包含工具性環保動機具備的命令性環保規范情境特征、自利性環保動機具備的描述性環保規范情境特征、規范性環保動機具備的個人環保規范情境特征。結合動機的內外視角,將親環境行為劃分為內、外源親環境行為,構建出“規范-動機”融合視角下的中國居民親環境行為的研究框架,并在中國20個直轄市和地級市進行問卷調查,運用描述性統計分析、層次回歸分析探究動機與居民內、外源親環境行為的三重交互關系。研究發現:①工具性環保動機可以直接正向影響居民的外源親環境行為。②自利性環保動機可以直接正向影響居民的內源親環境行為。③自利性環保動機和內源親環境行為的關系會受到工具性環保動機的負向調節。④工具性環保動機與外源親環境行為的關系并未受到自利性環保動機、規范性環保動機的調節效用影響。⑤自利性環保動機和內源親環境行為的關系會受到規范性環保動機的正向調節。⑥當個體具有高水平規范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工具性環保動機時,能產生最高水平的內源親環境行為。⑦當個體具有低水平規范性環保動機、高水平自利性環保動機和工具性環保動機時,能產生最高水平的外源親環境行為。本研究結論與自我一致性邏輯相符,因此政府可以通過激勵、教育、創辦“模范社區”等措施提升居民親環境行為水平。
關鍵詞?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規范性環保動機;內源親環境行為;外源親環境行為
中圖分類號?X24
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2-2104(2020)11-0160-10?DOI:10.12062/cpre.20200912
親環境行為自覺作為居民在日常生活中主動進行綠色購買[1]、綠色出行[2]、垃圾分類[3]等降低對生態環境負面影響的行為,是我國實現“美麗中國·健康中國”建設目標的重要途徑。然而,2020年發布的《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調查報告》指出,中國公民親環境行為在綠色消費、垃圾分類等行為領域仍存在“高認知度、低踐行度”的“知-行”缺口現象[4],凸顯出中國居民親環境行為自覺尚未達到“知行合一”的理想狀態,同時也折射出在“知-行”缺口形態下所存在的偽裝性、被動性的親環境行為現象。理論上,個體行為的動機作為解釋和理解個體行為的功能性途徑[5],是研究個體行為產生的重要變量[6]。具體到居民親環境行為,由于居民總是嵌入于群體、組織、社會等多重環保規范情境中[7],且親環境行為具有“對他人有利卻需要個體自身付出成本”的利他特征[8-9],意味著不同規范情境下衍生出的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和規范性環保動機皆是影響居民親環境行為自覺與否的決定性因素[8]。那么,嵌入于多重環保規范情境下的中國居民是否會自覺實施親環境行為?以及在此情境下實施的親環境行為又呈現何種特征?
動機是指個體為了實現某一目的而行動的原因,它推動個體投身于某項活動,并朝一個方向努力[10],而居民參與環保行為的動機就是居民以何種目的而實施親環境行為。現有研究已經驗證了個體動機與親環境行為的聯系,主要聚焦于自身需求相關的利益導向動機、自身環保價值觀導向動機等不同動機類型來探究其對個體親環境行為的影響。比如,Afsar等[11]實證檢驗了員工企業社會責任動機對于感知的企業社會責任和自覺環保行為之間的調節作用,蔡建政和胡建績[12]基于元分析探究了環保內部動機與員工環保行為的正向關系。涉及針對公眾環境行為的研究,現有研究大都從不同動機對環境行為的獨立性影響方面展開研究。比如,Jagers等[13]認為公眾出于經濟利益、健康需求以及環保主義動機而實施私人領域親環境行為;Gkargkavouzi等[14]利用目標框架理論研究了三類激勵類型對于公眾親環境行為的影響,分別是利益動機、享樂動機和規范動機。可以看出,雖然學者已經考慮到多重動機對于主體親環境行為的影響,但這些動機僅是從主體的內在需求出發,不僅未考慮到主體所面臨的外部環境因素的干預,比如居民所嵌入的多重環保規范情境[7],也未能考慮到多重動機之間的交互作用對親環境行為的影響特征。此外,內源親環境行為和外源親環境行為的提出有效說明了親環境行為的主動和被動特征[9]。其中,內源親環境行為是指個體受到內在動機的驅動,出于自愿、自覺或積極響應主流價值觀等目的而主動實施親環境行為。外源親環境行為是指個體基于外在動機的驅動,出于規章制度的要求、群體壓力、他人評價等目的而實施親環境行為。故而,為探究居民多種環保動機的情境規范特征,并在此基礎上揭開多種環保動機共同作用于居民實施主動或被動親環境行為過程的“黑匣子”,本研究聚焦于居民的內、外源親環境行為,結合規范焦點理論和自我決定理論,通過理論剖析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規范性環保動機等三種動機的環保規范情境特征,構建出“規范-動機”融合視角下中國居民親環境行為的研究框架,為提升居民親環境行為自覺提供理論與實踐基礎。
研究試圖在以下方面有所創新:首先,從“規范-動機”融合視角出發,結合規范焦點理論,探索三種動機的環保規范情境特征,以系統呈現不同環境規范情境下居民實施親環境行為所經歷的心理過程,為理論剖析三類動機如何影響居民親環境行為自覺提供思辨基礎;其次,納入自我決定理論,聚焦居民親環境行為的自覺與被動特征,從內部與外部動機視角下劃分內源和外源等兩類親環境行為,為有效識別影響親環境行為的內外部因素以及全方位探索如何提升居民親環境行為自覺提供更加明確的指導;最后,為動態呈現影響居民親環境行為自覺實施與否的動機類型和交互特征,構建三種動機與居民親環境行為的三重交互理論模型,以明晰三類動機在影響居民親環境行為實施中的角色和作用特征,以期為政策或管理措施的精準設計與實施提供理論基礎。
1?理論剖析和研究假設
1.1?理論剖析
Cialdini[15]認為個體嵌入于規范情境中時,該規范所反映出的行為信息會對個體產生干預效用,隨后個體在動機的驅動下展現出遵循規范的行為傾向。基于規范焦點理論,命令性環保規范涉及群體情境中大多數人贊成或反對的環保行為,其本質反映著大多數人的價值取向,因此與其保持一致是個體散發合作意愿的信號。此外,Kavvouris等[16]檢驗了由社會規范所引發的心理反應對可持續行為的影響,結果表明命令性環保規范相比于描述性環保規范具備更高水平的心理反應喚醒能力,從而更能激發個體的行為意愿。這是因為命令性環保規范涉及周圍人的期望和要求,而與大多數人保持一致是群體成員最重要的行為準則,個體如果不遵循這些準則,就很可能受到群體中其他成員的排擠[17]。可見,個體為了獲得外界的許可、獎勵抑或是為了融入群體而實施親環境行為這一工具性環保動機[8]折射出其所具有的命令性環保規范情境特征。也就是說,引發個體親環境行為的工具性環保動機往往具備命令性環保規范情境特征(見圖1-A)。
描述性規范發揮效用也許跟“與大多數人行為一致”的從眾行為有關[18],這是因為在很多情境下與大多數人行為保持一致是最安全、最合理的選擇[19]。Cialdini等[20]認為描述性環保規范展現了大多數人的環保行為選擇,它通過向個體展示選擇環保行為的益處,來發揮激勵作用,從而作為基于自我利益導向的決策依據。而自利性環保動機是指個體為了自我需求或自我成功的實現而產生的行為傾向[28]。可見,個體實施親環境行為的自利性環保動機主要是受到描述性環保規范的激發力量,具備描述性環保規范情境特征(見圖1-B)。
此外,隨著研究者們對個體親環境行為的關注,學者們開始強調個體內在特征對其親環境行為的影響作用。比如,Ebreo等[21]提出規范性環保動機具有鮮明的個人規范特征,在此動機的驅動下,個體實施親環境行為是為了符合自身環保價值觀而做“正確的事情”,這與個人環保規范的道德義務感特征達成一致。而這種自我層面的環保規范是依靠自我制裁予以保障實施,而非外部制裁。因此,個人環保規范往往與個體內在的規范性環保動機聯系在一起(見圖1-C)。
1.2?工具性環保動機與外源親環境行為
工具性環保動機引導個體關注群體準則的存在,而該準則會讓個體感受到群體規范的壓力。個體環保行為若與該準則產生沖突,很有可能難以融入群體生活,甚至受到其他成員的冷落。相反,如果與其保持一致,則是散發“合群”意愿的信號,可能會獲得與該環保行為無關的外部收益,比如良好的人際關系、群體的認可等[22]。因此,基于自我決定理論,個體在認識到自身需要和外界環境后會做出行為選擇,其中,外界環境因素所引發的外在動機會引導個體為了追求活動本身之外的某種結果而從事某項行為[23]。因此,在具備命令性環保規范情境特征的工具性環保動機引導下,個體為了融入群體生活、遵循群體行為準則,抑或為了獲得群體或社會的認可和獎勵,會激活個體實施親環境行為的行為傾向,即外源親環境行為。基于以上描述,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1:工具性環保動機能對個體的外源親環境行為產生正向影響。
1.3?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
自利性環保動機強調個體在考慮自身需求的基礎上通過認知判斷做出對自己有益的親環境行為選擇[8]。而自利性環保動機由于具備描述性環保規范情境特征,當個體注意到周圍大多數人的親環境行為選擇時,這種行為規律被解釋為該親環境行為也許能滿足個人的某些利益。根據自我決定理論,這種規范信息所引發的個體內部動機不需要任何的驅動力量,個體在自利性環保動機的驅動下,為了自身利益獲得滿足和收獲樂趣會主動實施親環境行為[24],即內源親環境行為。基于以上描述,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2:自利性環保動機能對個體的內源親環境行為產生正向影響。
1.4?工具性環保動機與自利性環保動機的調節效應
工具性環保動機和自利性環保動機的目標雖然是相似的,均聚焦于自身利益而非他人,但個體在工具性環保動機的激勵下所追求利益的評審標準是外部人群,比如外界的認可和表揚;而自利性環保動機引導個體將自身利益實現作為審判標準。可見,個體在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的驅動下實施親環境行為能為個體帶來不同的利益滿足感。但是根據自我決定理論,工具性環保動機作為外部動機更多的指向被動實施,而自利性環保動機屬于內部動機則引導個體主動實施[25]。鑒于此,作者認為兩種動機之間的沖突會讓個體感到矛盾從而在面臨親環境行為選擇時出現遲疑的情況,也就是說,個體會陷入追求外部獎勵而被動實施親環境行為抑或出于自身利益的考慮而主動實施親環境行為的矛盾情境。基于自我決定理論,個體由于享受自身對行動的控制感,因此當以前那些讓自己樂在其中的任務變成一種義務而非自主選擇的活動時,動機就會遭到破壞[26]。由于工具性環保動機具有外部因素指向特征,它促使個體過于關注群體行為準則的壓力,使得實施親環境行為變成一種“不得不去做的事情”,因此工具性環保動機可能會削弱個體在自利性動機引導下主動實施親環境行為的意愿,故而工具性環保動機會削弱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的積極關系。相對應的,自利性環保動機更能引發個體實施親環境行為的主動性,因此當個體在工具性環保動機誘導下被動實施親環境行為時,自利性環保動機會引發個體的思考,會讓個體產生反思“我實施親環境行為難道僅僅為了社會的認可和獎勵嗎?”[27],因此自利性環保動機會抑制工具性環保動機與外源親環境行為的積極關系。基于以上描述,作者提出以下假設:
H3a:自利性環保動機對工具性環保動機與外源親環境行為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
H3b:工具性環保動機對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的關系具有負向調節作用;
1.5?規范性環保動機的調節效應
規范性環保動機追求的是一種“至善”的理想境界,指的是個體基于“該環保行為是正確的”的出發點而產生親環境行為選擇[8],這是一種超越現實和有限自我的內在動機[28]。當個體具備較高水平的個人環保規范時,會意識到如果不實施親環境行為將會產生內疚、后悔、自我否定等負面情緒體驗,因此其“做正確事情”的內在道德傾向將會得到提升,而此“道德義務感”會激活個體的規范性環保動機[29]。根據自我決定理論,具備工具性環保動機的個體僅僅是為了從外部獲得利益而實施外源親環境行為,但規范性環保動機強調個體基于自身環保價值觀而主動實施內源親環境行為,在此情境下,兩種環保動機產生沖突。因此,由于規范性環保動機的介入,個體基于工具性環保動機而實施外源親環境行為的意愿受到削弱,也就是說規范性環保動機會削弱工具性環保動機與外源親環境行為的正向關系。此外,由于規范性環保動機具備個人環保規范情境特征,在該動機驅動下實施親環境行為能讓個體產生自豪、自我肯定的積極情緒,因此具備較高水平規范性環保動機的個體為了避免自我制裁、獲得自我肯定會對具有利他特征的親環境行為產生較高的實施意愿[30]。而具備描述性環保規范情境特征的自利性環保動機將會使個體意識到實施親環境行為不僅能滿足自我利益,還能獲得實現價值觀的滿足感、成就感,因此個體會更加自愿實施親環境行為。由此,規范性環保動機可以增強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的正向關系。基于以上描述,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4a:規范性環保動機與工具性環保動機可以產生交互作用,當規范性環保動機較低時,工具性環保動機與外源親環境行為的關系更強;
H4b:規范性環保動機與自利性環保動機可以產生交互作用,當規范性環保動機較高時,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的關系更強。
1.6?三種動機的三重交互
正如前文所描述,目前研究尚未探索三種動機的交互作用對于親環境行為的影響。由此,我們認為規范性環保動機可以起到強有力且長期穩定的“內在驅動”作用[22],而工具性環保動機和自利性環保動機由于其嵌入的命令性、描述性環保規范情境特征,兩者導向一致時則代表群體的正式、非正式行為壓力具有相同內容指向,此時個體將更加確信親環境行為就是一件正確的事情,從而更能提升個體實施內源親環境行為的意愿。因此,當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較高且規范性環保動機也處于較高水平時,個體內源親環境行為水平最高。此外,我們認為當個體的內在環保意識不太強烈時,此時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能發揮更大的作用。個體在具有明確利益指向的動機的引導下會實施更大力度的外源親環境行為。因此,當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較高而規范性環保動機處于較低水平時,個體外源親環境行為水平最高。基于以上描述,我們提出以下假設:
H5a:規范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和工具性環保動機存在三重交互,當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較高且規范性環保動機較低水平時,外源親環境行為水平最高;
H5b:規范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和工具性環保動機存在三重交互,當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較高且規范性動機較高水平時,內源親環境行為水平最高。概念模型見圖2 所示。
2?研究設計
2.1?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中國居民為調研對象,共涉及北京市、上海市、徐州市、蘇州市等20個直轄市和地級市居住地的居民。正式調研從2019年10月至2020年3月,共發放問卷950份,回收932份,對所有問卷進行真實性、合理性刪減后得到821份有效問卷,有效回收率為86.4%。本項研究是通過在線調查和實地調查結合進行的。在線調查是通過網絡平臺比如微信APP發放問卷,并為每個參與者提供了獎金獎勵。實地調查是向各地級市居民發放問卷,并向參與者贈送小禮物。其中男性占比58.6%,已婚人數占比43.2%,26~35歲人數占41.4%,本科以上學歷占63.7%。
2.2?測量
為了確保概念的準確性,本研究邀請了四名中英文流利的雙語教學者將被選取的量表翻譯成中文[31]。隨后邀請五位人力資源管理領域的研究者進行了小組討論,最終根據他們的意見進一步修訂了問卷項目,以確保量表的適宜性。各變量的測量題項均使用李克特5點式,其中1代表“完全不符合”,5代表“完全符合”。
(1)工具性環保動機。本研究選取了Ridings等[32]開發的參與動機量表,修改后共包含3個題項,“我實施親環境行為是因為周圍大多數人對我的環保行為有所關注”“我實施親環境行為是為了獲得周圍大多數人的肯定”等。該量表信度為0.905,信度良好。
(2)自利性環保動機。本研究選取了Carstan等[33]開發的自利動機量表,修改后共包含3個題項,“我實施親環境行為是因為我想滿足自身環保訴求”“我實施親環境行為是因為環保目標和愿望對我來說很重要”等。該量表信度為0.750,信度良好。(3)規范性環保動機。本研究選取了De Dreu等[23]開發的規范環保動機量表,修改后共包含4個題項,如“我實施親環境行為是因為我需要履行自身環保責任義務”“我實施親環境行為是因為我尊重大自然”等。該量表信度為0.83,信度良好。
(4)親環境行為。本研究選取了Lu等[9]開發的員工內外源親環境行為量表,修訂后共包含10個題項,如“實施親環境行為符合我的環保價值觀,因此我實施親環境行為”等。該量表信度為0.752,信度良好。
(5)控制變量。研究在選取研究對象時設計了控制變量,分別是婚姻狀況、性別、年齡、受教育水平,它們在之前的研究中被認為能夠影響個體親環境行為[34]。
3?研究結果
3.1?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鑒于研究量表皆由被測者自己評價填寫,因此為了避免出現共同方法偏差問題,本研究進行了Harman單因素檢驗。結果顯示,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釋百分比為22.288%,小于40%,因此數據結果并未受到共同方法偏差問題的影響,后續的數據結果具有一定的可靠性。
3.2?驗證性因子分析
為了評價關鍵研究變量的結構效度,使用Mplus7.2進行了一系列驗證性因子分析。結果表明,假設的五因子模型與數據吻合較好,包括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規范性環保動機、內源親環境行為、外源親環境行為(χ.2 = 929.004, df = 242, CFI = 0.922, TFI = 0.911, RMSEA = 0.055, SRMR = 0.053)。該模型相比于其他簡潔模型展示出更好的擬合度,見表1。
3.3?描述性統計分析
根據表2的結果顯示,工具性環保動機與外源親環境行為存在顯著正相關(=0.390, P<0.01),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存在正相關(=0.247, P<0.01),由此推斷,工具性環保動機對于個體外源親環境行為有促進作用,而自利性環保動機對于個體內源親環境行為有促進作用。
3.4?回歸結果
本文采用層次回歸分析方法以檢驗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分別與外源、內源親環境行為的直接關系、工具性環保動機對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的調節作用、自利性環保動機對工具性環保動機與外源親環境行為的調節作用、規范性環保動機對工具性環保動機與外源親環境行為以及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的調節作用,同時再考察三種動機對內外源親環境行為的三重交互作用。由于存在交互項,因此將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規范性環保動機進行了去中心化處理。
首先,將控制變量納入模型1;其次,將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和規范性環保動機納入模型2;然后,將所有二階交互項納入模型3;最后,將三階交互項納入模型4。回歸分析結果如表3和表4所示。
由表3和表4的模型2可知,工具性環保動機對于個體外源親環境行為存在正向相關關系(=0.109,P<0.05),自利性環保動機對于個體內源親環境行為存在正向相關關系(=0.087, P<0.01), 因此假設1和2得到驗證。假設H3a認為自利性環保動機可以正向調節工具性環保動機與外源親環境行為的關系,正如表3中的模型3展示;工具性環保動機和自利性環保動機的交互項并不顯著,因此對于外源親環境行為沒有預測作用(=-0.034,P=0.606)。因此,假設H3a未得到驗證。假設H3b認為工具性環保動機可以調節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的關系,正如表4的模型3展示。工具性環保動機和自利性環保動機的交互項是顯著的且負向預測內源親環境行為(=-0.093, P<0.01),因此假設H3b得到驗證。假設H4a、H4b認為規范性環保動機可以分別調節工具性環保動機與外源親環境行為及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的關系。根據表3和表4中的模型3可知,工具性環保動機和規范性環保動機的交互項并不顯著(=0.033, P=0.637),而自利性環保動機和規范性環保動機的交互項顯著且正向預測內源親環境行為(=0.180, P<0.001),因此假設H4a未得到驗證而假設H4b得到驗證。假設H5a、H5b認為三種動機存在三重交互且分別對于外源、內源親環境行為有負向、正向的預測作用。根據表3和表4中的模型4可知,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和規范性環保動機的三重交互項可以有效負向預測個體外源親環境行為(=-0.073, P<0.001),該三重交互作用僅代表當工具性環保動機和外源親環境行為關系達到最大值時,此時具備高自利性環保動機、低規范性環保動機。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和規范性環保動機的三重交互項可以有效正向預測個體內源親環境行為(=0.026, P<0.1),該三重交互作用僅代表當自利性環保動機和內源親環境行為關系達到最大值時,此時具備高工具性環保動機、高規范性環保動機。因此假設5a、5b得到驗證。
為了更好地分析各個調節作用,我們繪制了調節作用圖。根據圖3,可以看出工具性環保動機對于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的負向調節作用,即工具性環保動機可以削弱自利性環保動機和內源親環境行為之間的積極關系。根據圖4,可以發現規范性環保動機對于自利性環保動機和內源親環境行為關系具有促進作用。
此外,圖5的三重交互調節作用圖表明當規范性環保動機達到最小水平、自利性環保動機達到最大水平時,工具性環保動機和個體外源親環境行為的關系達到最理想化狀態(t=-7.471, P<0.001)。而當居民的規范性環保動機處于較高水平,自利性環保動機和工具性環保動機處于較低水平時,居民的外源親環境行為水平最低。這表明,隨著個體的工具性環保動機程度增加,當個體的規范性環保動機處于較低水平但具備較高水平的自利性環保動機時,個體反而會因為工具性環保動機增強而更加實施外源親環境行為。圖6繪制了各個變量分別取高值、低值的不同效應,當居民的規范性環保動機、工具性環保動機都處于較高水平時,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的關系達到最理想化狀態(t=1.036, P<0.05)。而當居民的規范性環保動機、工具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都處于較低水平時,居民的內源親環境水平最低。
4?結論與討論
4.1?研究結論與討論
首先,研究結果證實了工具性環保動機與外源親環境行為、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的積極關系,這與Taylor等[8]提出的動機與環保行為理論邏輯關系相符,并且本研究對其進行了補充性的實證檢驗。同時也恰好符合規范焦點理論所提出的觀點[35],即當個體處于命令性規范和描述性規范的情境下,規范信息可以發揮作用從而有效干預個體的親環境行為[36]。
其次,該研究表明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關系會受到工具性環保動機的負向調節以及規范性環保動機的正向調節。而工具性環保動機與外源親環境行為的關系并未受到自利性環保動機、規范性環保動機的調節影響。可見,相比于內源親環境行為,個體外源親環境行為的產生過程是相對穩定的,也就是說,居民為了融入群親環境行為關系的調節作用圖體生活、獲得認可和獎勵而實施親環境行為的工具性環保動機不易受到其他因素的干擾而產生親環境行為意愿的轉變。因此,對于居民來說,群體壓力、規章制度等外在因素在其進行親環境行為選擇考慮時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此外,工具性環保動機可以負向調節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的積極關系。這一結論說明個體為了滿足自我需求而主動實施親環境行為的過程中,工具性環保動機打破了個體追求自我一致性的心理過程,導致親環境行為主動性意愿受損。也就是說,居民基于自利性環保動機而實施親環境行為是因為該行為與他們的需求達成一致。然而,工具性環保動機的介入使居民聚焦于群體規范的壓力,關注其是否能與群體準則保持一致而避免群體的排斥、冷落等非正式懲罰,這使得親環境行為變成他們不得不做的事,而不是他們想做的事。根據認知評價理論,這種外部條件會降低個體對實施親環境行為的主動性。因此,工具性環保動機越強,居民基于自利性環保動機而主動實施親環境行為的意愿會越低。
相反,規范性環保動機卻正向調節自利性環保動機與環境行為的積極關系。這一結論與自我決定理論的自我一致性邏輯相符。居民通過觀察他人的環保行為而對親環境行為產生一定的認知,并發現自身的環保訴求,在此情境下,所萌發的自利性環保動機將驅動居民主動實施親環境行為。而該環保行為的實施過程使居民獲得了追求自我一致性的滿足感,因為該行為恰好可以實現自身需求。相似的,規范性環保動機強調環保行為與自身環保價值觀的一致性,個體預期實施親環境行為后可以獲得自豪、自我肯定的積極情緒體驗。因此,自利性環保動機與規范性環保動機具有相同的環境行為主動性指向,而兩種動機的交互作用可以增強居民追求自我一致性的意愿,因此規范性環保動機可以正向調節自利性環保動機與內源親環境行為的積極關系。
最后,本研究驗證了內源、外源親環境行為產生的三重交互路徑。當個體的規范性環保動機處于較低水平,而自利性環保動機、工具性環保動機處于較高水平時,此時能產生最高水平的外源親環境行為。鑒于之前的描述,當個體的內在環保意識不太強烈時,此時具有明確利益導向的動機能乘虛而入且發揮推動作用,從而促進外源親環境行為。當個體的規范性環保動機、自利性環保動機、工具性環保動機都處于較高水平時,此時能產生最高水平的內源親環境行為。這與“在一個社會里,如果社會規范和個人規范趨于一致并且被激活的水平都較高,這個社會肯定是秩序良好的社會”[14]的觀點是一致的。當個體的內、外部動機都具有共同指向且具有較高水平時,此時個體的內源親環境行為是達到最大值的。
4.2?建議
基于以上討論,作者提出以下管理建議。
首先,針對親環境行為主動實施意愿已經較高的城市和地區,政府可以考慮緩和命令性環保規范信息的傳達力度,比如降低環保規章制度的懲罰力度,轉而更加重視居民的個人環保規范的持續提升。這是因為,此時如果繼續采取強制性環保政策,可能會造成居民的環保逆反情緒,降低其主動實施親環境行為的意愿。而個人環保規范激活的主要途徑就是環境宣傳教育。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政府應更加注重網絡、在線等現代化手段,比如可以通過綜藝節目的主題宣傳等措施,更近距離滲透于居民的個人生活并且產生潛移默化的作用。
其次,各地政府可以根據各社區居民的親環境行為實施情況創建“模范社區”[8],對該社區給予宣傳和獎勵,并在合理范圍內給予特定權利和優惠措施,以此增強其他社區居民的社會學習能力,提升親環境行為自覺水平。而且由于居民存在多重身份,比如“公民”“員工”等,因此,依靠居民的“身份共享”,該模范社區的居民可以實現親環境行為從生活領域向公共、工作領域的積極溢出。然后,政府可以通過教育、激勵等措施提高居民的外源親環境行為水平,因為即使是外源親環境行為也能對社會環境改善、可持續發展產生推動作用。
最后,如果政府、群體、個體等多主體均能產生親環境行為認可,并共同參與全社會的環境治理任務,這將是最理想化的社會狀態。無論從社會層面,還是從個人層面來看,該理想狀態需要全社會的合作。一方面,目前我國環境立法雖已完善,但執法力度仍有待加強,法律的環境保護功能尚未發揮完全效用。另一方面,居民的生態環境價值觀轉變是基于社會危機和困境的出現,因此政府需要向居民及時提供有關環境危機和困境的信息,以促進居民環保自我反思,樹立環境信念,增強親環境行為認可,提升親環境行為自覺。
4.3?研究局限與展望
本研究存在一些局限性,這為未來的研究提供了潛在的方向。
首先,本研究量表均是基于同一時點居民的反饋進行測量,測量結果可能會受到居民當時情緒和情境的影響,缺乏對被測者長期的動態關注,未來研究可以采取多時點的測量,以驗證結論的長期穩定性。此外,本研究結果僅僅證實了多重動機并存的可能性,但自我決定理論還涉及外在動機向內在動機的轉化,個體基于天生的積極調節能力,會逐漸認可社會規范并將其內化于心。因此,如何在下一步研究中進一步探析在時間的推移下,個體產生內外動機的轉化從而促進外源親環境行為向內源親環境行為的轉變,這有助于提出更加針對性的環保治理措施。
其次,本研究中的被試者皆為中國本土居民,其文化背景也許會影響個人判斷。因此未來的研究可以采取跨文化情境,通過選取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調查對象,以驗證結論的普適性。此外,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居民對于規范情境的反應可能是有差異的,因此相應的親環境行為動機可能也會有所不同。未來研究采用跨文化情境也許能探索出其他親環境行為動機,以豐富現有的結論。
參考文獻
[1]ARVOLA A, VASSALLO M, DEAN M, et al. Predicting intentions to purchase organic food: the role of affective and moral attitudes i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J]. Appetite, 2008, 50(2-3), 443–454.
[2]CARRUS G, PASSAFARO P, BONNES M. Emotions, habits and rational choices in ecological behaviours: the case of recycling and us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8, 28(1), 51–62.
[3]CHAISAMREJA R, ZIMMERMAN R S. A comparative investigation of TPB and altruism frameworks for an empirically based communication approach to enhance paper recycling[J]. Applied environmental education & communication, 2014, 13(1), 28–37.
[4]生態環境部環境與經濟政策研究中心. 公民生態環境行為調查報告(2020年)[R]. 2020.
[5]TAKEUCHI R, BOLINO M C, LIN C C. Too many motives?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multiple motives on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5, 100(4):1239-1248.
[6]王輝,常陽. 組織創新氛圍、工作動機對員工創新行為的影響[J].管理科學, 2017, 30(3):51-62.
[7]SANTOS F P, SANTOS F C, PACHECO J M. Social norm complexity and past reputations in the evolution of cooperation[J]. Nature, 2018, 555:242-245.
[8]TAYLOR D, ERIN P H, LEIGH R. Cultural evolution of normative motivations for sustainable behaviour[J]. Nature sustainability, 2018(1):218-224.
[9]LU H, ZOU J, CHEN H, et al. Promotion or inhibition: moral norms, anticipated emotion and employee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20, 258: 120858.
[10]CHERRIER H, BLACK I R, LEE M. Intentional non-consumption for sustainability: consumer resistance and/or anti-consumption?[J]. European journal of marketing, 2011, 45(11):1757-1767.
[11]AFSAR B, BASHEERM A G, REHMAN Z U, et al.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employe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tive attributions (substantive and symbolic)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perceptions and voluntary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J].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2020, 27(2):769-785.
[12]蔡建政, 胡建績. 如何激發員工環保行為:基于元分析的問卷研究[J].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 2019, 36(2):6-21.
[13]JAGERS S C, LINDE S, MARTINSSON J, et al. Testing the importance of individuals motives for explaining environmentally significant behavior[J].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2017, 98(2): 644-658.
[14]GKARGKAVOUZI A, HALKOS G, MATSIORI S. How do motives and knowledge relate to intention to perform environmental behavior: assessing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nstraints[J]. Ecological economics, 2019, 165:1-11.
[15]CIALDINI R B. Professionally responsible communication with the public: giving psychology a way[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7, 23(7):675-683.
[16]KAVVOURIS C, CHRYSOCHOU P, THGERSEN J. ‘Be careful what you say: the role of psychological reactance on the impact of pro-environmental normative appeal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20, 113:257-265.
[17]PAGLIAROS S, ELLEMERSN N, BARRETO M, et al. Individual vs.collective identity management strategies: the role of group norms and personal gain[J]. Psicologia sociale, 2010( 3): 387-402.
[18]MURRAY G R, MATLAND R E. Mobilization effects using mail: social pressure, descriptive norms, and timing[J].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2013, 67(2):304-319.
[19]FALZER P R, GARMAND M. Contextual decision making and the implementation of clinical guidelines: an example from mental health[J]. Academic medicine journal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Medical Colleges, 2010, 85(3):548-55.
[20]CIALDINI R B, RENO R R, KALLGREN C A. A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recycling the concept of norms to reduce littering in public place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0, 58(6):1015-1026.
[21]EBREO A, VINNING J, CRISTANCHO S. Responsibility for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waste reduction: a test of the norm-activation model[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systems, 2003, 29(3): 219-244.
[22]張福德. 環境治理的社會規范路徑[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 2016, 26(11):10-18.
[23]GKARGKAVOUZI A, HALKOS G, MATSIORI S. 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a scale for measuring multiple motives towar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MEPS)[J].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2019, 58:101971.
[24]RYAN R M, DECI E L. Intrinsic and extrinsic motivations: classic definitions and new directions[J].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sychology, 2000, 25:54-67.
[25]STONE D N, DECI E L, RYAN R M. Beyond talk: creating autonomous motivation through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J]. Journal of general management, 2009, 34(3):75-91.
[26]RYAN R M, DECI E L.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the facilitation of intrinsic motivation, social development, and well-being[J]. American psychologist, 2000, 55 (1):68-78.
[27]LIN C, TSAI Y, CHIU C. Modeling customer loyalty from an integrative perspective of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and expectation-confirmation theory[J]. Journal of business & psychology, 2009, 24(3):315-326.
[28]楊松. 規范判斷、規范動機與VM患者案例[J].自然辯證法通訊, 2019, 41(9):43-51.
[29]BAMBERG S. Social context, personal norms and the use of public transportation: two field studies[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2007, 27(3):190-203.
[30]JUDITH I M, DE G, LINDA S. Moralit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the role of awareness, responsibility, and norms in the norm activation model[J]. The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9, 149(4):425-449.
[31]HOSKISSON R E, EDEN L, LAU C M, et al. Strategy in emerging economies[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3):249-267.
[32]RIDINGS C M, GEFEN D, ARINZE B. Some antecedents and effects of trust in virtual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strategic information systems, 2002, 11:271-295.
[33]DE DREU C,AUKJE N. Self-interest and other-orientation in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implications for job performance, prosocial behavior, and personal initiative[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9, 94(4):913-926.
[34]LU H, LIU X, CHEN H, et al. Who contributed to ‘corporation green in China: a view of public and private-sphere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among employees[J]. Resources Conservation & recycling, 2017, 120:166-175.
[35]韋慶旺, 孫健敏. 對環保行為的心理學解讀:規范焦點理論述評[J].心理科學進展, 2013, 21(4):751-760.
[36]SUN H, BLESS K E, SUN C, et al. Institutional quality, green innova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J]. Energy policy, 2019, 135:111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