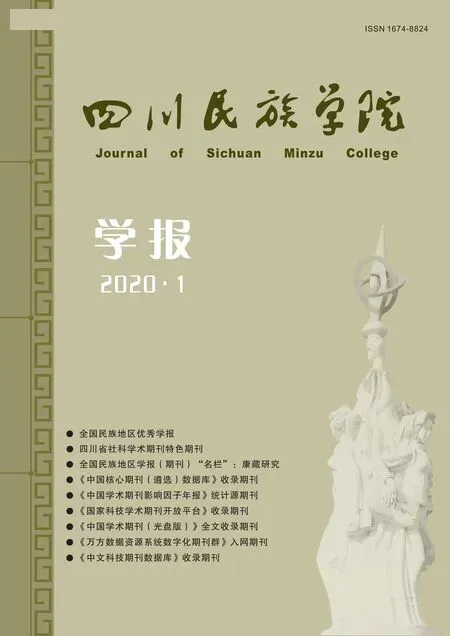基于良性互動的民族史觀教育體系建構略論
黃曉通
中國是一個傳統的多民族國家,各地區少數民族在各自的生存和發展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民族歷史和文化,貢獻和豐富了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價值和內涵。民族史教育擔負著傳承中華民族文化的重大作用,目的在于培育中華民族精神,增進中華民族認同,增強民族凝聚力,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貢獻力量。隨著時代的發展,傳統的民族史教學體系陷于陳舊,以民族間自然良性互動的新民族史視野為核心的體系建構更富于現實深蘊和時代意境,融入中華傳統文化以完成從舊至新的話語體系轉換,使民族史教學回歸本真、更具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之風貌,并提升新時代民族社會治理的效用。
一、 傳統民族史教育體系存在弱點
我國是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根據2010年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少數民族人口占內地總人口8.49%,比2000年增長了0.08%。對一個普通學生來說,歷史教育貫穿其初等教育至高等教育全過程(尤其2009年《中國近現代史綱要》納入大學思想政治課課程以后),政治—歷史教育對于當代大學生的國家觀的形塑具有重大的意義。近代以來,中國國情發生深刻變化,隨著“西方近代民族學說的引入與流傳”[1],在先進知識分子的努力呼吁和中國社會形勢需求下,中華民族史觀開始形成并在不同階段顯現出各自的特點:在西方話語權與“現代性”強勢擴張的情況下,古代的華夏認同受到巨大沖擊,晚清-民國時代的人們,甚至許多知識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產生了自我認同的疑惑;在當今國家富強的時代語境與訴求下,加強民族團結、構筑中華民族命運共同體理念充滿了宏大的國家統一視野和深切的現實關懷,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民族史教育在目標上追求各少數民族達成中華民族共同體之認同,進而自覺維護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傳統的民族史教育體系對于中華民族形成過程的描述忽視了各民族融合的一般建構過程,存在不足。
(一)民族史一體化陳述的斷裂
民族史本身并非單一和孤立的史學學科,而是融合了古代歷史、社會學、政治學、民族學、社會倫理學等的綜合交叉學科。民族間歷史的發展也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其間存在著戰爭、交流、共存等表征。在歷史的進程中,有的民族吸納了其他民族的東西存續和發展下來,有的民族則由于各種內部或外部的原因消逝了,民族與民族間充滿著各種形式內涵豐富的互動和影響,構成整體而一體化的民族史脈絡。將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二元對立的潛在意識主導了民族史教育的性質導向,引致了民族史一體化內在連續性的斷裂,以及民族間文化上的隔閡和誤解。某種程度上說,這是中國古來“華夷”二元對立及“本部”與“藩部”之分思想的延續,是應當批判對待的。
同時,在傳統民族史教育體系中,部分教材的敘述和一些教師的講授亦缺乏整體史觀的視野,難以站在從古至今的人類社會發展高度的視野下對歷史進程進行宏大的敘述和思考,容易忽略重要的發展支脈和局部事件的重要作用,形成對于許多時間性歷史結果在原因解釋上的模糊和概念化,亦消解了許多特定階段少數民族的重要作用,固化了教師知識蘊藏的話語向導,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教育的僵化和停滯。因此,各級課堂的民族史教育陷入矛盾難解的話語困境,也使許多少數民族學生的文化心理產生隔膜。當今信息化時代飛速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進入一個新的時代,傳統民族史的陳述方式和脈絡已難以滿足社會的需求,亟待改革。
(二)民族史教育話語的陳舊落伍
在我國幾十年傳統型歷史教育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套固化的歷史表達的語言模式,長期主導歷史教育話語表達領域。常常為“自古以來”“有史以來”等。如何“有史以來”,往往簡單帶過,中華民族歷史表達更多為了促進民族和諧而選擇表面上“團結”“進步”的歷史,而忽略了表面上不那么“積極”的歷史。其實,從內在的歷史發展邏輯來看,那樣一些看似不那么“積極”的歷史反而在一定程度更深入地促進和推動了中華民族的形成模式。
讓我們以歷史表述中經常出現的“民族融合”為例:民族融合一般意義上多從民族間關系上考慮,講究各民族之間在長期的歷史演進中,在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方面的交流影響,民族間差別縮小乃至消失,因此更強調各民族之間的相對平等性。然而,古代至近代的民族融合交匯僅依托屯墾、戰爭、行商、宦游、逃難、謫戍幾個有限的路徑,尤其是民族之間的征戰,作為民族之間矛盾斗爭最激烈的一種表現形式,給各民族人民帶來的往往是災難和痛苦的民族記憶,我們近年來的歷史教育所存在的一種傾向就是盡可能對此避而不談。我們認為,這是在教育工作中回避矛盾、掩蓋問題、繞著困難走的一種表現。從深層次看,中華民族建構的歷史變遷縱向上時間漫長,橫向上囊括豐富,征戰和民族壓迫在民族關系當中是統治階級的短期行為,和平友好的貿易往來是長期性的,相互依存、相互吸收,進而共同締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是民族關系的主流。所以,只有不回避民族關系中的這些歷史事實,才能真正動態地、多層次地、立體地呈現中華民族史與民族關系史,并豐富民族史話語內涵,使之更具現實性教育意義。
(三)民族史教育內容的匱乏單一
在浩瀚的幾千年的中國歷史進程中,各少數民族在實踐中形成璀璨豐富的文化和風俗習慣。我們縱觀各歷史或者民族史的通用教材,在教材內容的呈現上偏重于主流漢民族的文化發展演變史。在漢民族主政的王朝歷史教材式的表述中,更多地強調和凸顯漢民族的文化人物、文化事件、文化作品,而對同時期少數民族文化卻不太重視。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先生曾在1936年2月“晉南北朝史”課上指出:“每聞人言:中國文化最高,或謂漢族文化最高。漢族文化自為一極高之文化,然遂謂其為世界上最高之文化,則殊不當。如讀藏文之正續《藏》,則可知藏族學問甚高。又如在中古時,阿拉伯人有極高之文化。不能因為自己無知遂謂某民族文化甚低,或文化不足道。”可謂灼見。
據我們的觀察,通用教材的文化史敘述中,許多少數民族的文化往往被流水賬化,表達過于概括式,失之于簡略,似乎只作為主流文化的陪襯,甚至呈現邊緣化的趨勢。各少數民族歷史文化在民族史教育體系中不能得到其應有地位,對于少數民族受眾來說會施加一種不平等的心理影響。例如朝鮮族的農樂舞、滿族刺繡文化、錫伯族民間故事文化等等,雖然很多進入非遺名錄,但是在許多教材的表述中,只用一些簡單的詞語一掠而過,甚至有些并不提及。類似這樣對少數民族文化展示重視的不足,造成民族史教育內容的匱乏和單一,危害較大。
二、 基于自然良性互動的民族史教育體系的重構
“中華民族”概念產生于近代,并在近代歷史發展過程中得到強化。而中華大一統則最早實現于秦漢,此后歷經分裂又歸于一統。中原華夏族與周邊少數民族的融合是一個漫長的過程,而在這個過程中的種種歷史樣態并不應該被刻意隱藏,因為中華五十六個民族的歷史生態進程無法被割裂看待,割裂反而容易被肆意扭曲。在傳統歷史教育的建構中,這條主線的陳述往往過于籠統和簡單,新民族史教育內涵意在形成一統的民族史教育體系,并在此基礎上完成各民族歷史和文化的相互影響和相互作用,建構中華民族統一性,同時切實保護各民族自身文化的傳承。因此,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的形勢下,我們應構建展現良性互動的民族史教育體系,真正體現多元一體,才能真正達成基于各民族內心真實性基礎上的中華民族共識。
(一)完成民族史教育范式的轉換
從自然生態進程來看,中華民族大一統的概念培育立足于對各民族及其生態發展的基本尊重。人類生態發展和沿革呈現出自然性的發展面貌,蘊含內在的規律。馬克思主義者強調“并沒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自特征的總和”,“各自”蘊含相應的平等狀態。追溯中華民族理念的產生,我們可以發現,1905年梁啟超先生在《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闡釋了“中華民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后在時代浪潮的推動下五四運動之后,中華民族和中華民族精神被廣泛應用,被社會主流所倡導”。但我們不難發現,當今主流教育體系仍缺乏對各民族發展原生態的重視。
例如關于藏族先民在青藏高原所建立的吐蕃王朝,共存在兩個多世紀,而我們的歷史教科書對吐蕃的介紹以及學生對這一政權的認識,僅僅停留在“唐蕃會盟”“甥舅之親”幾個基本概念以及松贊干布、祿東贊、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幾個歷史人物而已。對于吐蕃鼎盛時期與周邊各政權的關系,吐蕃在唐代絲綢之路上所起的作用,古吐蕃人的宗教、文化、科學技術的發展則幾乎沒有涉及。其中央王朝對西南少數民族聚居地區的“改土歸流”,其時間跨度之長、涉及民族之多(至少涉及今壯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布依族﹑侗族﹑瑤族﹑水族等民族),使其成為歷史教育中無法回避的大事件。通行歷史教科書對這一事件時間斷限的確定及其與“攤丁入畝”經濟政策的關聯都存有商榷之處。我們認為,在歷史教育中,中華民族各成員發展史、兄弟民族歷史不可以做浮光掠影的介紹,這種教育是舊史書(尤其是被稱為“正史”的紀傳體通史)中“諸蕃傳”“四夷傳”落后思想的殘余。歷史教育中對少數民族史部分的介紹必須以“對多民族國家的統一和經濟文化的發展有無積極意義”為標尺,同時盡可能吸納已被史學界承認的新成果,衡之以黨的民族政策決定去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我國各族人民共同締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都為中華民族形成和發展作出了卓越貢獻”。[2]因此,轉換傳統史教范式,即要淡化漢民族主導的民族融合史,嘗試書寫各民族共同作為、良性互動的歷史長卷,展示參與的各民族同等的行為表達和話語力量。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的塑造,應得益于在中華大地上生活過的各個民族的共同歷史文化的表達和傳承。
(二)提升民族史教育體系的時代輻射力
民族史,不僅僅包含歷史變遷和發展,更應關注當下,聚焦現實,體現時代意境。中國自古形成的多民族歷史文化形態被費孝通先生稱之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這一極具概括性的提法被廣泛傳播和應用。“多元一體”,“一”將“多”容納其中,“多”是“一”囊括中的多種表現形式,“一”是“多”的發展趨勢和目標指向。現代中國“多元一體”民族格局提出三十年來,已成為中國民族學論述和民族史教育的根基,這一根基,是長期的民族田野考察,以及20世紀三四十年代民族問題討論的切磋琢磨中產生的。而當今社會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的形塑,不僅需要完善的民族史理論,更需要在中華大地上生活過的各個民族的歷史文化的共同表達和傳承。而這種傳承和表達,需要如今的民族史教育富含更多的社會意境和時代輻射力,才能肩負起更多的現實擔當,真正成為凝聚中華民族共識的有效途徑。
民族史教育體系時代輻射力的凝聚,需要更密切地關注當今少數民族的生活樣態、文化境遇、心理訴求,讓其成為推動民族間歷史-現實蘊含增長的有效動力。比如遼寧省沈陽市,有西塔朝鮮族聚居區、西關回族聚居區、北郊石佛寺錫伯族等少數民族聚居區。在歷史的變遷中,他們陸續遷往城市居住和生活,如今他們的生存狀態、文化心理、情感趨同,以及當今民族政策對他們有什么影響等等應該得到充分關注,并且融入教材內容中來。即要深刻地根植于民族歷史變遷、民族文化積淀、民族發展狀況、民族現實狀態,并且要貼近民族群體在時代和社會的動態變化,才能讓少數民族感到自己真正是中華民族大家庭的一員,才能在空間-區域-城市-社會多層次記憶中構建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園,這樣的史教體系才能更接近少數民族的心理,發揮更好傳播和教育的效果,才能由內到外增強各民族人民的國家認同感。
(三)加強民族史教育話語的邏輯生成
民族史教育作為以民族分類為特征的教育樣態,成為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途徑。卷帙浩繁的文獻材料成為歷史課程的內容設置的詳盡來源,文獻體現文化烙印和延續,因此編著的課程也必然承擔了民族文化傳承的功能。在學校教育領域中,一方面,課程載體之書本話語展現了民族史教育的意境選擇;另一方面,教師的二度闡釋話語亦反映了民族史教育的色彩偏向。除此兩個主要方面外,課程的目標、課外活動的安排、學生的學習模式、現實媒體的宣傳導向等方面亦影響民族文化的傳播。其中最關鍵的因素之一,是民族史教育話語的內涵和趨向,其直接關系了民族文化傳承的質量和效果。
話語的現實的影響乃至塑造能力是我們不能忽視的。古代統治階級反復宣稱“夷狄,禽獸也,畏威而不懷德”,這本身就是用一種政治權威話語對民族觀進行構造。直至20世紀三四十年代,芮逸夫等學者受政府委托,考察西南各少數民族,訂定“改正西南少數民族命名表”,將帶有污辱性的族名(如“犬”“牛”“羊”偏旁之名目),改為“人”字之偏旁,“以期泯除界線,團結整個中華民族”。新中國成立后,更是對挫傷民族感情有礙民族團結的話語進行了整頓和清理。一個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們所熟知的壯族,它在歷史上被稱為“貍獠(俚僚)、蠻、土人、俍”等等,后來統一改用宋以來常用的“僮”,后來因為“僮”在漢語中有奴婢、低賤之意,六十年代在周恩來總理的建議下改為“壯族”,遂為今名。可見話語問題并不簡單,關于民族的話語,除了要考慮歷史傳統,還要考慮民族所在區位、主要產業、獨有文化等等,而不能以一元化的強勢話語來進行強制命名與觀念塑造。
由此可見,我們在民族歷史的表達和轉述中,尤其要加強話語的邏輯生成,包括文本話語和教學話語,對于因果發展、制約和影響、推動和阻礙等眾多關系的剖析須符合正常思維的結構,避免為了某種結果而構建原因,或模糊產生之條件。尊重民族間自然良性互動的原生態,加強史教話語的邏輯脈絡,可以為受教對象構建清晰可觸的民族文化發展基本概貌,提升民族史教育的成效。
三、 融入中華傳統文化蘊涵創新民族史教育體系
教育和文化相互促進,相互影響。教育讓文化更有效地傳播、延伸和擴展;文化促使教育的內涵和意境獲得提升和豐富。中華傳統文化博大精深,源遠流長,匯聚了各民族共同的歷史記憶和風俗傳承,在聚合過去并力圖解決現實問題中一步步走向未來,并在繼承、傳播和不斷豐富中推陳出新。以中華傳統文化蘊含融入新民族史教育體系,完成民族史教育縱向和橫向的層次創新,推動新時代民族史教育體系整體性質的提升。
(一)融入“中華民族”的歷史性整體視野
“中國以地域遼闊,人口數量龐大、資源豐富、少數民族眾多,區域間發展不平衡,經濟發展水平中等偏下為主要現實,其中不少與教育相關的問題均存在‘安全隱患’”,因此在全球化背景加劇下,要確立“教育安全”的意識,“幫助人們在國家前途和民族利益的高度上審視與各類教育發展相關的問題”。[3]知識界的個別人士把民族看作是給一定人群以情感聯系與歸屬感的“想象的共同體”,是可以被建構甚至被“發明”的。而近年來世界上在“民族自決”口號下各類“獨立”運動的猖獗(如蘇格蘭脫英公投事件、加泰羅尼亞公投事件),其后往往有“想象的共同體”的擁躉者為之背書。足見民族教育關系國家教育安全,未可看輕忽略。國家教育安全關系著國家大局穩定和中華民族的前途命運,應該引起我們的警醒和重視。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形勢下民族史教育體系的對象,包括漢族在內的中華各民族,不再重點針對漢族或者其他少數民族。民族史教育應融入“中華民族”歷史性的整體宏大視野,中華民族的歷史進程,是各個民族互相融合、共同奮斗、開拓進取的歷史。近代以來,中華民族在遭受外侮的情況下歷經磨難,團結一致,勇敢抗擊侵略者,維護了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延續了民族和歷史的血脈傳承。共通互融、血脈相連、難以分割的民族間的歷史和文化記憶構成了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堅實的思想基石。因此,要基于家庭-社會-國家三重維度的整體性考量,這意味著民族間的真正融合的推動需要漢族與少數民族以及少數民族之間真正的尊重和了解,包括從政治、經濟、文化、語言等層次和方面去思考和作為。少數民族要了解漢族,漢族也需要了解少數民族,過去過于強調少數民族要去學習和融合漢族文化、而漢族似乎不用去過多了解少數民族文化、一般也不需要刻苦學習某種少數民族語言的教育趨勢和壓力會造成少數民族難于消除的不平等心理,民族間融合難以達成,反而加大隔閡,損害民族團結大局。因此,融入“中華民族”的整體性視野,才能尊重差異,包容多元,提升民族共識。
(二)以傳統文化滋養民族史教育的動態發展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一個民族長期的共同生產和生活的產物,是維系一個民族生存、延續的靈魂和血脈”[4]。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歷史實踐中所創造的具有本民族歷史特點的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的總和。”[5]中國的傳統文化多元化,是在吸收各周邊各民族地區的文化因素,逐步形成一個動態的體系并在時間的推移中又向周圍傳播的歷程,周而復始的影響和被影響。
中國作為一個傳統的多民族國家,各地區少數民族在各自的生存和發展中貢獻了作為整體的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價值和內涵,充實了中華傳統文化的寶庫,是各民族聯結的紐帶和血脈。比如壯族的壯錦文化、滿族的旗袍文化、傣族的潑水節文化等等,絢麗繽紛,多姿多彩,通過不斷挖掘、書寫、傳播各民族傳統文化,展示中華各民族在歷史進程中繽紛多彩的生活方式、風俗習慣、精神理念、審美趨向,凸顯時代變遷中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升華,滋養民族史教育的動態發展,才能讓民族史教育更貼近人心,獲得情感升華和理念認同。
(三)以“文化自信”引領民族史教育體系創新
文化自信,是一個國家和民族對自身文化的高度肯定和認可,包含強烈的文化歸屬感和價值認定。影響民族意識形成的諸多因素中,歷史/文化根源是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習近平總書記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95周年重要講話中明確提出“堅持不忘初心,繼續前進,就要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闡明“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6]。民族史教育的內在模式創新,依托于強大的中華傳統文化淵源;而完成對中華傳統文化自身的高度肯定,弘揚文化自信,也賦予民族史教育最持久最深厚的創新動力。以中華文化自信為核心,構建民族史傳承體系的創新基點,進而帶動整體民族教育保持長久的生機和活力,前提必須強調各民族文化的平等。
以“文化自信”引領民族史教育創新的重大意義,包含以下三個維度:其一,通過書寫和傳達中華傳統歷史文化的深厚積淀增強中華民族成員的民族自豪感,培育堅定的愛國和愛鄉情愫;其二,通過傳承理性、和諧、客觀、公正的民族歷史觀,形塑中華民族的文化精神和價值觀自信,提升全體民族成員的民族團結理念;其三,通過推動中華傳統文化由國內至世界的展示和傳播,提升全體公民的中華文明全球意識,增強中華民族國家的話語力量。
結 語
“現代中華民族觀念的形成和演變,思想論證和社會接受,凝聚著作為現代國民的中國人之整體認同的政治文化底蘊與時代精神走向。在新時代,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更需要深化和強化這一政治性和文化性蘊含”[7]。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強調:“深化民族團結教育,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加強各民族交往交流,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8]。在中國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民族史書寫和民族史教育是一個重要并且敏感的話題,涉及各少數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接受視閾,更是關系到各民族和諧穩定的大局。要真正促進民族間互動和團結,“其主導力量來自自上而下的國家建構,也源自自下而上的民族社會壘砌”[9]。教育作為最為關鍵的社會意識培育和社會文化傳播途徑,承擔著重大的歷史和現實責任,“教育將面臨如何促進一體化和多樣化協調統一的問題”[10];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念賦予了民族史教育新的使命和職能,我們應該在遵循中華各民族多元一體基本格局上,挖掘民族史教育發展的內在良性互動規律,積極倡導各民族平等的歷史抒寫局面,讓各民族文化同力發光;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民族史教育中真正凝聚民族共識,才能集全民族之力,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中完成中華民族的復興大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