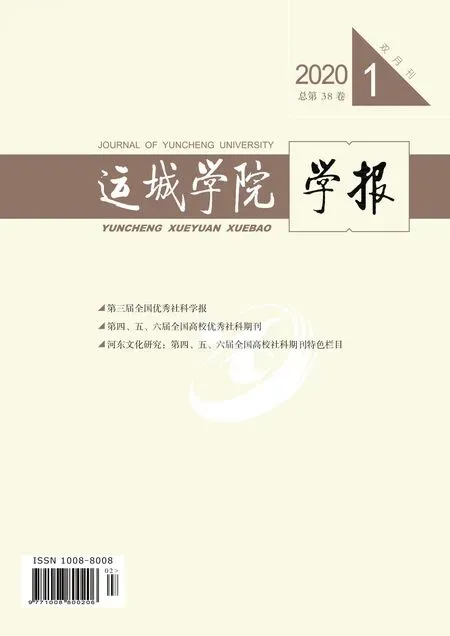破窗理論視角下農村黑惡勢力犯罪防控研究
簡 筱 昊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刑事司法學院,武漢 430073)
2017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辦《文摘》(第160期)《當前農村涉黑問題新動向值得關注》上作出重要批示,“當前農村涉黑問題出現一些新情況……要開展一輪新的掃黑專項斗爭,重點是農村”。2018年1月,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關于開展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明確將掃黑除惡同基層反腐敗和基層“拍蠅”結合起來,指明了依法嚴懲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政治方向。根據《通知》的要求,2018年的任務主要是營造掃黑除惡的高壓態勢,2019年的任務是攻堅克難、提升人民滿意度,2020年的任務則是建立長效機制、取得壓倒性勝利。但是,當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依舊嚴重威脅著農村地區的政治安全、經濟繁榮和社會穩定,并且呈現出一系列新的特征。本文試圖以在美國取得頗豐成效的破窗理論為視角,檢驗農村地區黑惡勢力犯罪的成因,并提出有針對性的防控對策,以期從積極一般預防的角度為長效機制的建設提供些許建議。
一、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典型特征
受社會結構和文化環境的影響,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天然帶有獨特的印記。當前,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時期,農村地區更是處于從傳統“熟人社會”轉向現代“陌生人社會”的關鍵階段。傳統政治、經濟、文化體制的解析和新興體制的未完全建立,給農村社會生活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正是在新舊體制的交替中呈現出全新的面貌。
(一)黑惡勢力官方化,滲透基層政權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首要特征是向政治領域滲透。一方面,黑惡勢力團伙為了增加自己的生存空間和生存能力,不得不尋求“保護傘”等制度力量的庇護。另一方面,新農村建設過程中存在的“釘子戶”以及村民上訪等問題,使得基層政權對黑惡勢力解決問題的能力頗為青睞。基于上述原因,農村黑惡勢力與基層政權之間存在千絲萬縷的聯系。與此相對,黑惡勢力對基層政權的滲透主要通過兩種路徑,一是黑惡勢力通過暴力威脅、拉票賄選等方式操縱選舉,進而把持農村基礎政權,即“黑惡勢力村官化”;另一是基層工作人員主動拉攏黑惡勢力,將制度力量作為交易籌碼,與黑惡勢力形成利益共同體,即“村官黑惡勢力化”。[1]前者如寧夏海原馬正山黑惡勢力團伙(1)參見馬正山、楊生義等尋釁滋事罪一審刑事判決書:寧夏回族自治區海原縣人民法院(2018)寧0522刑初109號。,自2010年以來,馬正山、楊生義、楊萬林等通過滋擾選舉、威脅村支書等方式,操縱海原縣白崖村選舉,控制村級政權。后者如河北定州孟玲芬黑惡勢力團伙(2)參見孟玲芬、石永波濫伐林木、職務侵占、詐騙、非法占用農用地、尋釁滋事、敲詐勒索、破壞生產經營一審刑事判決書:河北省定州市人民法院(2016)冀0682刑初106號。,孟玲芬自當選泉邱二村村主任以來,組織丈夫、弟弟等糾結社會閑散人員,以暴力威脅等手段橫行鄉里,逐步形成了以孟玲芬為首的黑惡勢力團伙。
(二)犯罪主體多元化,增加矯正難度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主體多元化主要表現為主體成分復雜,既可能是當地經濟能人,也可能是社會閑散人員;既可能是德高望重之輩,也可能是聲名狼藉之徒;既可能是鄉紳名士,也可能是土豪劣紳。例如,有司法工作人員統計,廣西貴港港南2013至2018年黑惡勢力犯罪案件中,有65.4%的被告人是刑滿釋放人員。[2]此外,2007年的一份數據顯示,湖南某市50%的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案件存在基層領導干部的參與。[3]但是,大致上可以分為基層領導干部、暴發戶、地痞流氓、刑滿釋放人員和社會閑散人員。其中,前四種人員通常是團伙的組織者、領導者和積極參加者,閑散人員構成團伙的成員。如此復雜的成員結構,導致的最直接后果是,難以對犯罪分子進行有效甄別和矯正。首先,主體的分散性和復雜性使得偵查機關的力量被分散,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查處需要投入更多的力量;其次,團伙成員之間往往形成互相照應的關系,一旦存在風吹草動,容易引起成員流竄后果;最后,盡管有2019年《社區矯正法》的引領,但是對這些犯罪分子區分矯正依舊存在制度保障上的困難。
(三)犯罪手段軟暴力化,增強隱蔽性
當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手段依舊以暴力和暴力相威脅為主,并有軟暴力化的趨勢。同樣見于上述司法工作人員的統計,當地黑惡勢力犯罪中的暴力因素出現概率高達86.2%。[2]并且暴力犯罪的實施往往伴有隨意性和突發性。但是,隨著法治建設和掃黑除惡的縱深推進,黑惡勢力犯罪手段開始軟暴力化,以借助軟暴力與一般違法行為和輕微犯罪之間的模糊界限遮蔽犯罪的涉黑惡性質。此外,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往往披著解決民間糾紛和社會矛盾的外衣,以光鮮形象和正當訴求掩飾非法目的。[4]一方面,黑惡勢力借助惡名,插手民間糾紛,包攬訴訟,以幫助鄉里解決矛盾的名義謀取利益、魚肉百姓;另一方面,黑惡勢力瞄準拆遷補償、環境污染等問題,以虛假事實欺騙民眾,對存在的問題夸大其詞,擾亂群眾認知,影響地區穩定。犯罪手段的軟暴力化以及與民間糾紛和社會矛盾的結合均增強了黑惡勢力犯罪的隱蔽性,提高了公安機關的查處難度。
(四)犯罪動機單一化,追逐經濟利益
農村黑惡勢力復發早期,犯罪動機較為多元,或是好勇斗狠以彰顯英雄氣概,或是占據山頭以圈定勢力范圍,亦或是壟斷行業以謀取經濟利益。既可能是無傷大雅的自我聊慰,也可能是影響深遠的精心算計。但是,更多的是為了打破改革開放前期條條框框的束縛,宣泄內心壓抑的情緒。[5]然而,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推進,金錢至上的價值觀念在我國生根發芽,財富的多少更是直接與人生的成敗相勾連。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動機也隨之向單一的追逐經濟利益轉變,他們開始參與市場經濟、壟斷行業、插手民間糾紛甚至剝削百姓愚弄政府,只為獲取巨額經濟利益。例如,上文提及的馬正山黑惡勢力團伙和孟玲芬黑惡勢力團伙均依賴暴力或者軟暴力手段謀取了巨額非法經濟利益。與此相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分子內心打破枷鎖的向往以至于略顯單純的執著,為市場經濟下“理性經濟人”利弊得失的精心衡量所替代。農村黑惡勢力中盲目的情緒宣泄者和做夢者已然消失不見,只剩下整齊劃一的利益追逐者。
二、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破窗效應”
蘇力教授認為,知識總是帶有地方特性,總是脫胎于特定的制度空間和社會空間。[6]125破窗理論脫胎于第三次工業革命中后期社會失范背景之下,有效地應對了轉型時期人類社會的精神焦慮,取得了良好的犯罪防控成效。盡管破窗理論不是解決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問題的唯一理論依據,事實上也難以堪此重任,只是處于社會轉型導致的類似社會問題之下,破窗理論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防控的借鑒意義亦不可小覷。所以,有必要對其進行單獨檢視,以期對我國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防治有所啟示。
(一)破窗理論的核心內容
破窗理論由美國犯罪學家威爾遜和凱琳于1982年提出。破窗理論的形象表達是,“如果一扇窗戶壞了,而不加以修理,那么其余的窗戶很快就會被打破”。[7]如果不夠關注和警惕最為輕微的違法行為或者越軌行為,那么更為嚴重的違法犯罪行為就會發生。破窗理論認為社會混亂和嚴重犯罪之間存在一種間接的關系:“由混亂造成的公民恐懼導致社會控制的削弱,從而創造了犯罪的條件。”[8]換言之,破窗理論認為犯罪發生機制主要包括四個階段,即無序環境——恐懼心理——控制失效——犯罪發生。對犯罪的恐懼以及防范意識的低下會削弱社會控制的作用,進而誘發犯罪。因此,社區應該警惕最小的違法行為。一個精心照料的社區會關心輕微的犯罪,并建立起一種社會秩序的紐帶,阻止嚴重的犯罪行為的發生。
破窗理論的社會心理基礎是從眾心理和模仿心理,即個體傾向于使自己的行為符合公眾的輿論和選擇,具有一定程度的盲目性和擴散性。[9]破窗理論的中心焦點不是預防犯罪,而是對犯罪的心理恐懼。[10]社會環境無序的印象在破窗效應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社會秩序的真實狀況為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映射至民眾心目中的具體印象如何。換言之,對社會秩序的印象會影響公眾對犯罪行為的心理態度,即便社會秩序較為混亂,但是如果公眾的印象是有序的,依舊可以擺脫對犯罪的恐懼心理進而增強社會控制對犯罪的遏制作用。因此,決策者可以有針對性地調整此種印象以促進民眾自覺遵守法律。但是,精明的犯罪者往往能夠擺脫從眾心理、模仿心理以及印象管理的束縛,根據利弊得失的衡量作出是否實施犯罪的理性選擇。破窗理論在應對此類違法犯罪分子時略顯捉襟見肘。
(二)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基本成因
1. 合法社會控制虛化
農村黑惡勢力產生、發展乃至壯大的關鍵因素是合法社會控制的虛化。合法社會控制弱化的地方,黑惡勢力、恐怖勢力等非法社會控制就會滋生。合法社會控制包括正式社會控制和非正式社會控制,正式社會控制是指以國家強制力作為保障的制度控制,非正式社會控制即不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且與社會發展需求相適應的控制。“早期以熟人社會為典型特征的農村地區,主要以村規民約、風俗習慣、人情往來等非正式社會控制作為社會運作的紐帶。但是,一方面,現代法治國家的建設要求國家正式社會控制在農村地區創立權威和支配性權力關系,正式社會控制在農村地區帶有天然的侵略性;另一方面,非正式社會控制作用的發揮更多地依賴美好品性和善良道德的內心約束,缺乏國家機器強制力的保障。”[11]正式社會控制的侵蝕和非正式社會控制的弱化,為黑惡勢力、恐怖勢力等非法社會控制在合法社會控制缺位或者虛化的農村地區的滋生創造了空間。陳柏峰教授通過對兩湖平原鄉村混混現狀進行實證研究發現,湖南鄉村集體意識強,村規民約、風俗習慣等非正式社會控制強勁,混混社會地位低下;而江漢平原農村正式社會控制尚未完全建立且農村集體意識不強,混混問題較為嚴重。[12]該發現證實了農村黑惡勢力與合法社會控制之間的關聯。
2. 非法經濟利益刺激
當前,農村黑惡勢力主要存在于或者服務于礦產、建筑、拆遷、交通等利益巨大的行業。[13]非法經濟利益的刺激是農村黑惡勢力得以滋生的外部條件。當代中國農村社會已經擺脫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而向市場經濟轉變,在此過程中,存在著資源市場化、資源重新分配、市場主體定位以及由此衍生出來的上層建筑建設問題。而且這些問題都與經濟利益的生產和分配存在密切關聯,驅使農村閑散人員糾結以獲取非法經濟利益。具體來說,一方面,農村地區存在著豐富的土地、林地、草地、河流等自然資源,農村經濟的發展需要對上述資源進行市場化開發。而市場開發決定了需要重新確定市場主體和利益歸屬等問題。另一方面,新農村建設過程中,拆遷補償、土地征用、環境保護等直接關涉利益的再次分配。面對經濟利益的快速流動,農村不法分子按捺不住追逐經濟利益的沖動,糾結勢力形成利益團體,既使用暴力、脅迫等手段壟斷資源的開發,抑制行業的良性競爭;又隨意插手民間糾紛,充當執法者和中間人,活躍于政府和民眾之間,侵吞亟待重新分配的利益,攫取巨額經濟利潤。[14]
3. 僥幸心理錯誤誘導
僥幸逃脫的心理是促進黑惡勢力犯罪實施的內在因素。精明的利己者總是能夠在收益與成本對比分析之中作出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選擇。如前所述,農村地區黑惡勢力中執著的理想者已消失殆盡,剩下的都是工于算計的逐利者,他們總是能夠妥當處置非法利益與違法犯罪成本之間的關系。根據我國《刑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犯罪所得以及涉案財物或是返還被害人或是收歸國有,犯罪的結果終將是竹籃打水一場空,但是依舊存有不少人爭先恐后地鋌而走險。原因在于行為人貪圖一時的享樂和錯誤地估計了刑罰與犯罪的常態關聯,對刑罰的降臨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認為刑罰與自己的距離還十分遙遠。此種僥幸逃脫的心理在我國農村地區表現得更為明顯,首先,正式社會控制尚未建立支配性權力關系,黑惡勢力憑借惡名或者小聰明即可對抗淳樸的非正式社會控制;其次,知識信息的不對等導致農村黑惡勢力對我國正式社會控制懲治犯罪的決心和力量缺乏清晰的認識;最后,市井小民的短識使得農村黑惡勢力錯誤地估計了自己逃避偵查、逮捕和懲罰的能力。對國家懲治犯能力的低估和對自我逃避懲處能力的高估使農村黑惡勢力的僥幸心理膨脹。
(三)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破窗”表現
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破窗”表現解決的是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惡化的起點問題,即“第一扇破窗”。在威爾遜和凱琳看來,違法犯罪的起點是肆意涂鴉、環境臟亂、管理松散、尋釁滋事等處于微觀層面的無序現象,[15]但是如上所述,宏觀層面的社會控制的虛化、介觀層面的非法經濟利益的刺激同樣在農村黑惡勢力的滋生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只是,從示范效應的角度來說,“第一扇破窗”應當是一種外化的可以為后來者模仿學習的社會現象而不是現象背后的原因本身。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破窗”表現大抵可以分為兩個向度,一是外來向度,即他人的違法犯罪行為的參考借鑒作用,如新舊觀念更迭之際,“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時代悄然離去,偷雞摸狗、欺行霸市成為人們日夜提防的對象。當輕微違法犯罪行為無法得到有效矯治時,其他人就會模仿學習失范行為。二是自我向度,即自己的輕微違法犯罪行為的試探作用,如幼時的小偷小摸演變成成年時期的江洋大盜,先前的小打小鬧演變成后來的作奸犯科。
改革開放以后,市場經濟的觀念沖擊著封閉的農村,帶來眾多不安定的因素,尤其是金錢至上的價值觀直接打破了農村以熟人關系作為紐帶的生活。在種種爭名奪利的違法犯罪之中,為了攫取更為巨大的經濟利益,農村黑惡勢力應運而生。因此,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產生的“第一扇破窗”可以追溯至改革開放以來農村地區的各種失范現象。正是因為這些失范現象未能得到有效的治理,誘發了更為重大的違法犯罪行為,這與津巴多的“偷車實驗“高度吻合——津巴多將一輛沒有牌照的汽車停放在布朗克斯區街道上,隨后的24小時內,不斷有人襲擊車輛并拿走了車上所有值錢的東西,襲擊者大多穿著講究且包括“受人尊敬的白人”,[7]也解釋了破窗理論對預防“第一扇破窗”的重視。只是以從眾心理和模仿心理作為心理學基礎的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破窗”現象帶有一定的盲目性的解讀并不總是合適,農村黑惡勢力已經發展到一個比較高級的階段,能夠對犯罪的利弊作出符合理性人的判斷。
三、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防控”對策
有學者認為,破窗理論對犯罪防控的啟示包括事前預防和事后修補兩個方面。[16]但是從破窗理論在美國實踐中的具體運用來看,其主要是通過對無序現象的整治來實現犯罪預防的目的。正如有學者認為的“破窗理論以零容忍政策為犯罪控制的基本策略,要求對違法犯罪對抗力弱的弱勢環境的主動補強,以有效預防和阻卻犯罪”、“強化積極預防乃是破窗理論作用于刑法理念的產物”。[17]對弱勢環境的主動補強,形成了犯罪情景預防理論,即可以通過適當的環境設計來減少對犯罪的恐懼和犯罪率。通過采取積極的預防舉措,也可以建立針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的長效應對機制,鞏固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勝利果實。以下從積極預防的角度展開。
(一)強化合法社會控制,擠壓黑惡勢力生存空間
1. 加強基層組織建設
合法社會控制的虛化是農村黑惡勢力有機可乘的先決條件,防范農村黑惡勢力的首要措施就是加強體現正式社會控制的基層組織建設,擠壓黑惡勢力的生存空間。首先,要加強基層黨組織的建設,充分發揮基層黨組織的領導作用,積極宣傳黨的方針政策,樹立黨的光輝形象;其次,要加強基層黨組織對基層自治組織、基層政權組織對基層自治組織、上級政權組織對基層政權組織的領導和監督;再次,規范國家公共權力行使,完善責任追究制度,暢通群眾舉報路徑,形成上下級機關之間以及政權組織與民眾的常態聯動,以防范基層組織中的“保護傘”存在;最后,要規范基層自治組織的運作程序和方式以防范黑惡勢力對基層自治組織的滲透,提升基層組織的社會治理能力。
2. 建立農村警察巡邏機制
犯罪情景預防理論對犯罪控制的一個重要貢獻是建立社區警察巡邏制度。[18]社區警察制度的初衷是培養民眾的地盤意識和主人翁意識,調動民眾參與犯罪的防范以克服對犯罪的恐懼心理,進而切斷無序現象與違法犯罪之間的關聯。在我國農村地區,雖然已經存在民兵制度,但是其存在組織落實空、人員名單虛、應急能力弱等缺陷,[19]不足以在農村地區形成常態聯動機制。黑惡勢力的防控需要國家正式社會控制的組織和引導,有效的做法是,由轄區派出所組建一支由專職警察領導和維護、由志愿者參與的巡邏隊伍,不定時地在農村開展警務巡查工作。此外,可以增派電子警察,在農村公共地區增加設置攝像頭,使違法犯罪行為暴露在陽光之下。
3. 堅持“零容忍”的高壓打擊態勢
掃黑除惡專項斗爭已進入攻堅克難關鍵階段,要始終保持對黑惡勢力犯罪的“零容忍”高壓打擊態勢。破窗理論對犯罪的預防就是通過對無序現象的綜合治理實現的,與我國對黑惡勢力堅持“打早打小”的基本政策相一致。在貫徹“零容忍“的政策中,要始終把握住農村黑惡勢力犯罪主體多元化的特征,一方面,密切關注地痞流氓、社會閑散人員和刑滿釋放人員等違法犯罪高發群體,對其越軌行動傾向進行及時糾察,另一方面,積極開展村“兩委”人員摸底工作,將基層組織人員可能參與的違法犯罪行為扼殺于搖籃之中。“零容忍”不僅是三年掃黑除惡專項斗爭的基本態度,也是鞏固斗爭勝利果實的長效機制,更是提升農村社會治理能力的重要方針。
(二)優化市場資源配置,弱化非法經濟利益刺激
1. 發揮市場配置資源主體地位的同時加強政府監管
農村市場化過程中資源配置不均衡導致的非法利益的刺激是黑惡勢力(犯罪)滋生的介觀因素,由此推演的防控對策是優化市場資源的配置,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地位,保持各方主體能夠在公平競爭的情況下進入農村市場,提高黑惡勢力的準入成本,合理分配農村資源利益。此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理論表明,政府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必須改變消極的“守夜人”角色成為積極的“服務者”,農村地區資源的配置也離不開政府的監管,尤其是需要及時糾偏不法分子壟斷市場、惡意競爭的行為,使利益在符合市場規律的情況下良性分配,以弱化巨額非法利益的刺激。
2. 完善農村財務制度,發揮村內外監督作用
不管是“黑惡勢力村官化”還是“村官黑惡勢力化”,在逐利動機驅逐下,均會對農村集體財產產生不法念頭。為了抑制此種不法念頭,需要完善農村財務制度,建立現代會計制度和財務管理制度,加強內部監督和外部監督。監督措施主要包括規范集體財產的使用和村級賬目的公開,妥善做法是由基層政權組織具體落實農村財務公開,細化財務公開內容,規范財務公開程序,基層紀委監察組織進行監督。[20]即使不法分子難以直接接觸財產,又增加侵財行為暴露風險,提升犯罪成本降低相對犯罪收益,以抑制不法分子的趨利性動機。
3. 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提升農村過剩勞動力就業能力
從黑惡勢力團伙成員構成來看,閑散人員在量上占據相當比例,政府以及社會各方既需要通過再教育增強農村閑散人員的就業能力,也有必要通過筑路治河、開疆培林、屯墾畜牧等工程吸收農村閑散人員,提升農村人口就業率,使得人人能夠通過勞動獲得有保障的生活,降低閑散人員的絕對數量。從犯罪動機來看,黑惡勢力糾結成伙的主要目的是謀取經濟利益,當通過勤懇勞動可以獲得豐富報酬時,違法犯罪的相對成本就提高了,非法經濟利益的刺激在理性人看來也就弱化了。通過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技能培訓,至少可以有效控制黑惡勢力團伙的規模,減少因為生存困境而導致的違法犯罪行為。
(三)建立社區支持體系,糾偏僥幸錯誤心理誘導
理性經濟人的“理性”是一種有限理性,指稱的是行為人能夠根據自己所獲取的信息作出利益最大化的選擇,但是囿于自我控制能力的低下、獲取信息的不對稱等,行為人作出的選擇在一般人看來可能并不理性。所以,有必要克服片面性因素對選擇的不利影響。
1.發揮家庭教育對未成年人品行的塑造作用
以孟玲芬案為例所體現出的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分子的偏執性格和低自我控制能力的預防需要從幼年或兒童時期著手。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師,培養孩子良好的品行和較高的自我控制能力離不開父母的陪伴和以身作則。但是,經濟落后使得農村地區青壯年勞動力流失,造成嚴重的空心化和留守兒童問題。因此,一方面,要幫助父母樹立正確的家庭觀和教育觀,以溫暖的家庭氛圍和正確的教育方法培養孩子健全的人格;另一方面,既要發展農村地區經濟,以召回年輕勞動力,又要建立社區支持體系和經費保障制度,以提高家庭教育的效能、減輕父母教養的成本。[21]
2.加強基礎教育對核心素養的養成作用
教育是一項公益性事業,國家應當發揮主導性作用。學校作為國家教育事業的主體,理當肩負起核心素養的培養任務。但是,經濟發展的不平衡,導致農村地區的教育資源相對匱乏。為了使農村地區學生的核心素養能夠得到有效提升,首先,需要國家對農村地區的教育給予政策扶持,尤其是師資引進政策優惠和待遇優惠;其次,完善農村地區教育配套基礎設施,使學生能夠有教室待以穩定學習環境、有書看以開發智識、有器材玩以鍛煉身體;最后,提供城鄉學生交流機會,糾偏農村地區“分數至上”的教育觀念,促進學生核心素養的全面發展。
3.提升普法宣傳教育對矇昧心智的去除作用
黑惡勢力(犯罪)產生的一個重要因素是錯誤估計了犯罪與刑罰之間的關聯,低估了國家懲治違法犯罪分子的決心和能力。因此,需要加強農村地區的普法宣傳教育和法治建設,引導村民積極使用法治方式解決糾紛、維護合法權益,提升農村地區的法治水平。[22]法治建設的矇昧去除作用體現在三個方面:一是使不法分子認識到刑罰與犯罪的必然性關聯,破除僥幸心理的誘導,繼而作出抑制犯罪動機的選擇;二是使糾紛能夠以合法方式解決,降低對非法途徑的迷信,避免受害者轉變為犯罪人;三是使普羅大眾認識到我國法治建設的成就,認識到國家打擊違法犯罪行為的決心和能力,樹立對國家治理能力和治理體系的信任和依賴。
四、結語
現階段,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呈現出黑惡勢力官方化、犯罪主體多元化、犯罪手段軟暴力化和犯罪動機單一化等新的特征,防治農村黑惡勢力犯罪必須牢牢把握上述特征,并準確針對合法社會控制虛化、非法經濟利益刺激、僥幸心理錯誤誘導的犯罪原因采取措施。破窗理論以積極的一般預防作為理論視角,要求我們重視對農村無序現象和輕微違法犯罪行為的治理,從而抑制黑惡勢力犯罪的爆發。由此得到的啟示是,強化合法社會控制,斷絕黑惡勢力官方化或者尋求“保護傘”的渠道;堅持“零容忍”政策,使軟暴力手段無處遁形;優化市場資源配置,使利益在市場規律下合理配置,降低非法巨額利益的刺激;矯正低自我控制能力、暢通信息獲取途徑,糾偏僥幸心理誘導。但是,破窗理論對于黑惡勢力犯罪的事后治理的關注略顯薄弱,并且以從眾心理和模仿心理作為其理論基礎,無法解釋犯罪分子根據利弊得失作出的理性選擇。而上個世紀中下葉發展并流行起來的控制理論和理性選擇理論,對農村黑惡勢力犯罪成因和對策的解釋起到了很強的補足作用。因此,破窗理論只是研究農村黑惡勢力犯罪防控對策的一個視角,長效機制的建設還需要更為開闊的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