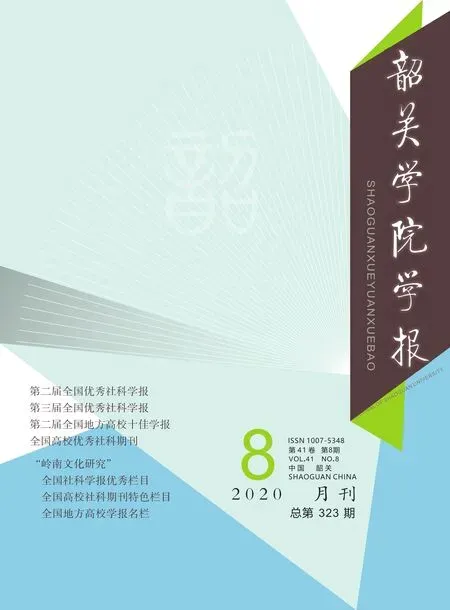抗戰(zhàn)時期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的歷史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
廖 益,童順平,張玉龍
(1.韶關(guān)學院 院長辦公室;2.韶關(guān)學院 教師教育學院;3.韶關(guān)學院 馬克思主義學院,廣東 韶關(guān) 512005)
廣州淪陷前夕,廣東省政府及所屬部門北遷韶關(guān)。國立中山大學、私立嶺南大學等10多所大專院校隨之先后輾轉(zhuǎn)來到粵北。內(nèi)遷粵北的華南高校作為隱性的華南“聯(lián)大”,是抗日戰(zhàn)爭時期與西南聯(lián)大、西北聯(lián)大并存且產(chǎn)生巨大影響的三大高校群落之一,在近現(xiàn)代中國高等教育史和華南地區(qū)抗戰(zhàn)史上都有著十分重要的歷史地位,對其進行全面與系統(tǒng)的考察,有著重要的歷史價值與現(xiàn)實意義。
一、輾轉(zhuǎn)遷徙:保存、賡續(xù)華南高等教育
抗日戰(zhàn)爭爆發(fā)后,中國高校迅速成為日本侵略者打擊的重點目標。隨著平、津、滬、寧等地相繼淪陷,中國高校大多陷入了生死存亡的困境。為保存民族文脈,“使優(yōu)良教授得以繼續(xù)服務,并使學生完成學業(yè),且隱為內(nèi)地高等教育擴大規(guī)模起見”[1],中國高校開始了史無前例的戰(zhàn)略大遷徙。廣州淪陷前后,以國立中山大學、私立嶺南大學為代表的華南高校也被迫卷入遷移行列。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先后內(nèi)遷到粵北的學校有30多所,其中大專院校10多所,分別為國立中山大學——1938年10月遷廣東羅定,1939年1月遷云南澄江,1940年4月遷廣東坪石,設校本部、文學院、理學院、工學院、醫(yī)學院、法學院、師范學院,校本部和先修班設在坪石鎮(zhèn),文學院設在坪石鎮(zhèn)鐵嶺,理學院設在坪石鎮(zhèn)塘口,工學院設在坪石鎮(zhèn)三星坪,醫(yī)學院設在樂昌縣城外河南水,法學院設在樂昌縣武田司,師范學院設在乳源縣管埠,1944年秋分三部分遷徙,一部分遷廣東連縣,一部分遷廣東仁化,一部分遷廣東興寧、梅縣。私立嶺南大學——1941年冬香港淪陷后,校本部遷曲江仙人廟大村,設文學院、理工學院、農(nóng)學院和醫(yī)學院,文學院、理工學院在大村,農(nóng)學院在樂昌縣水牛灣,醫(yī)學院在江西中正醫(yī)院借讀,1945年春遷廣東梅縣。私立東吳大學——1942年9月遷曲江仙人廟,設文學院、理學院,文學院設政治學系、經(jīng)濟學系、中國文學系、社會學系,理學院設生物系,1944年5月遷往桂林。廣東省立教育學院——1938年遷廣西梧州、騰縣、融縣,1939年8月遷廣東乳源,廣東體育專科學校由云浮遷來乳源,并入廣東省立教育學院,易名為廣東省立文理學院,設文史系、社會教育系、生物系、理化系和體育專修科,1939年底遷連縣,1942年春遷廣東曲江,1944年夏遷廣東連縣,1945年1月遷廣東羅定。私立廣州大學——1938年分三部分遷徙,一部分遷廣東開平,一部分遷香港九龍,一部分遷廣東中山,1940年秋校本部由廣東開平遷廣東臺山,1941年冬遷廣東曲江,停辦教育學系和社會學系,合并文、法兩學院為文法學院,增設商學院,內(nèi)設會計學系、銀行學系和工商管理學系,1944年冬,部分師生疏散到廣東羅定,1945年1月,全體師生疏散到和平、興寧。私立廣東國民大學——1938年分兩部分遷徙,一部分由廣州遷廣東開平,一部分遷香港,1941年香港淪陷后大學部由香港遷廣東曲江,設文學院、法學院、工學院,1944年遷廣東羅定。廣州協(xié)和神學院——1938年遷香港,1939年遷云南大理,1942年由云南遷韶關(guān)大村,設神科。廣東省立法商學院(前身是省立勷勤大學商學院)——1938年遷廣西融縣,繼遷廣東遂溪,再遷廣東信宜,1941年秋由廣東信宜遷廣東曲江,設立會計、銀行、工商管理等學系,增設統(tǒng)計學系,1945年1月遷廣東信宜。這就是當時廣東乃至華南高等教育的全部“家底”。
這些內(nèi)遷到粵北的高等學校,不僅延續(xù)了華南高等教育的血脈,更在粵北催生了幾所新的高等院校,如1940年春,在韶關(guān)西北郊創(chuàng)辦了廣東省立藝術(shù)專科學校,也稱廣東省立戰(zhàn)時藝術(shù)館,設戲劇、美術(shù)、音樂三個部,1940年底遷連縣,1941年初遷回韶關(guān)北郊,易名為廣東藝術(shù)院,學制兩年,1944年底遷連縣,1945年1月遷往連山、羅定。1942年秋在樂昌縣坪石鎮(zhèn)創(chuàng)辦了私立中華文化學院國文專科學校,1944年秋增設大學部,設中國文學系、史地學系、新聞學系,并設置了文哲學部、史地學部、生物學部三個研究部,1945年初遷梅縣,戰(zhàn)后遷廣州。1944年1月在韶關(guān)北郊創(chuàng)辦了南方商業(yè)學校,設財務、會計、銀行三科,1944年夏遷往連縣,1945年1月,遷往梅縣。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因為戰(zhàn)事的不斷變化,無論是內(nèi)遷到粵北的華南高校,還是在粵北新創(chuàng)辦的高校,為了延續(xù)華南高等教育的血脈,他們不得不一遷再遷,甚至數(shù)遷。其中,中山大學先后遷徙3次,省立勷勤商學院先后遷徙4次,私立嶺南大學先后遷徙3次,而廣東省立文理學院則先后遷徙10次,時任教育部長陳立夫曾說其是抗戰(zhàn)中高校“遷校次數(shù)最多的”[2]。整個遷徙過程,堪謂艱難竭蹶、困難重重。如中山大學在遷移羅定、云南澄江和坪石、梅縣等地過程中,廣大師生“迢迢遠道,越懸崖,過山峽,經(jīng)歷了幾千里的長征”[3],但是遷徙的師生卻是“強健勝前”,“風雨不能侵蝕,憾擊不能動搖”[4]。
即便如此,本著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即使赤手空拳,也要維護母校的存在”[5]的堅韌毅力,內(nèi)遷粵北的華南高校不負使命地完成了保存高等教育和文化的大遷徙,對后來的華南高等教育發(fā)展產(chǎn)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當下華南的諸多名校,如華南理工大學、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華南師范大學直接孕生于內(nèi)遷粵北的國立中山大學,北京大學、武漢大學、中南財經(jīng)政法大學等也嘉惠于內(nèi)遷粵北的國立中山大學。誠如廣東省副省長許瑞生所言:“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山大學的老師和同學從粵北西京古道旁的韶關(guān)坪石三星坪碼頭上岸,并在坪石度過了可歌可泣的近五年時光,讓‘火種’保存至今。這既延續(xù)了中山大學的文脈,又讓華南理工大學、華南農(nóng)業(yè)大學、華南師范大學找到了昔年在硝煙中頑強生長的根脈。”[6]
二、焚膏繼晷:創(chuàng)新、豐富華南的學術(shù)成果
抗日戰(zhàn)爭時期,內(nèi)遷粵北各高校的先師們,秉承“立言”的學術(shù)傳統(tǒng),拿起手中的筆,以筆抗戰(zhàn)、以教學抗戰(zhàn)、以學術(shù)抗戰(zhàn),克服環(huán)境惡劣、圖書缺乏、實驗儀器匱乏的困難,以頑強的毅力,積極從事科學研究和創(chuàng)作活動,短短幾年時間里,提出了很多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學術(shù)理論,出版發(fā)表了大量的科研論著,有些理論和論著甚至成為了一些學科的標志性成果,從而構(gòu)筑起了華南高校的學術(shù)研究高地。
潛心學問是內(nèi)遷粵北各高校先師們共同的自覺行為、自覺使命,教師們在教學之余,積極根據(jù)自己的學科方向,開展各種學科研究,取得了豐碩的學術(shù)成果,現(xiàn)茲按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對他們1940-1944年間發(fā)表出版的具有代表性的學術(shù)成果進行大致的臚列,借此以窺知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的學術(shù)聲音、學術(shù)形象、學術(shù)地位。
(一)自然科學領域的代表性成果
從事自然科學教學的先師們,積極開展各自領域的相關(guān)研究,呈現(xiàn)出各領風騷的學術(shù)風采。數(shù)學:如中山大學數(shù)學天文系胡世華先生,1943年發(fā)表《論人造的語言》,仔細介紹了一階謂次演算,在國內(nèi)引起了較大的關(guān)注。天文學:中山大學理學院鄒儀新女士,1942年發(fā)表《國立中山大學天文臺第二次日食觀察報告》,詳細報告了日食的相關(guān)情況。物理學:中山大學理學院盧鶴紱先生,1944年發(fā)表了《重原子核內(nèi)之潛能及其應用》,全面闡述了核裂變的實驗發(fā)現(xiàn)及有關(guān)理論,并預言人類將有大規(guī)模利用原子能的可能性。農(nóng)學:中山大學農(nóng)學院蔣英先生,1941年發(fā)表《中國紫金牛科植物研究紀略》,詳細報道了紫金植物的研究結(jié)果;嶺南大學農(nóng)學院李沛文先生,1942年發(fā)表《柑橘儲藏實驗(下篇)》,是我國較早關(guān)于水果儲藏的研究報告;中山大學農(nóng)學院丁穎先生,1944年發(fā)表《水稻純系育種法的探討》,較早提出育種理論和辦法;中山大學農(nóng)學院鄧植儀先生,1944年發(fā)表《湖南之土壤問題》,較早提出對湖南土壤的利用問題。醫(yī)學:中山大學醫(yī)學院楊簡與梁伯強先生,1943年發(fā)表《在粵北日本住血蟲之傳染》,較早研究了粵北此病的傳染途徑。地理學:中山大學地理系吳時尚先生,1941年出版《廣東省之地形》,確立“珠江三角洲”地理學說,提出“廣花平原”的地理概念;1943年與何大章合撰出版《廣東省之氣候》,是中國第一部大區(qū)域氣候?qū)V荤娧芡?943年發(fā)表《武江流域的上游聚落地理》,是人文地理學聚落研究的開山之作。
(二)社會科學領域的代表性成果
從事社會科學教學的先師們,教學之余,或進行學科研究,或進行文藝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熠熠生輝的享譽后世的學術(shù)成果。文學:中山大學文學院詹安泰先生,1944年發(fā)表《中國文學上之倚聲問題》,詳實地區(qū)分了中西文學與文體的不同;中山大學師范學院黃錫凌先生,1941年出版《粵音韻匯》,是學粵語的經(jīng)典之書;中山大學文學院岑麒祥先生,1942年發(fā)表《入聲非聲說》,提出了自己的新看法。歷史學:中山大學歷史系陳安仁先生,1941年出版《中國民族抗戰(zhàn)史》,條舉而概述中華民族從先秦到清末的對外抵抗史;中山大學歷史系鄭師許先生,1943年發(fā)表《香港問題》《澳門問題》,1944年發(fā)表《臺灣與丘逢甲》,1945年發(fā)表《劉銘傳與臺灣》,以種種史實說明臺、港、澳是中國的領土。政治學:中山大學法學院王亞南先生,1944年為回應李約瑟的提問,連續(xù)寫作17篇文章,1948年結(jié)集以《中國官僚政治研究》為名出版,是我國第一部運用馬克思主義科學方法研究傳統(tǒng)官僚政治的著作。經(jīng)濟學:中山大學法學院王亞南先生,1942年開始撰寫“高等經(jīng)濟學”講稿,1946年以《中國經(jīng)濟原論》為名出版,是“中國最早一部嘗試把政治經(jīng)濟學中國化的成功之作”[7],提出了“中國經(jīng)濟學”概念。法學:中山大學法學院呂復先生,1943年出版《比較地方自治論》,是當時具有重要影響的憲法學著作。社會學:中山大學社會學系董家遵先生,1941年發(fā)表《廣東風俗志》,是研究廣東民間風俗的第一手資料;中山大學文學院朱謙之先生,1943年發(fā)表《文化社會學之發(fā)端》,論證并建構(gòu)了文化社會學的理論體系。人類學:中山大學師范學院的楊成志先生,1943年出版《廣東人民與文化》,詳細考證廣東人的不同形成歷史與地理分布及因此而衍生的不同文化。心理學:廣東省立文理學院的阮鏡清先生,1942年出版《學習心理學》,1944年出版《性格類型學概觀》,《學習心理學》,自覺地運用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對西方學習心理學諸派別進行剖析和評判,內(nèi)容新穎、觀點進步,建國初期由教育部定為全國第一本心理學參考書;《性格類型學概觀》倡導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來研究人格。圖書館學:中山大學圖書館杜定友先生1943年發(fā)表《圖書分類原理》,詳細論述了分類的理論依據(jù)。還有很多當時已開始研究或完成了的初稿,在粵北期間還沒有來得及發(fā)表與出版,如中山大學文學院詹安泰先生,1940年開始寫作《詞學研究》;廣東省立文理學院郭大力先生,1941年開始翻譯《剩余價值學說》。
藝術(shù)家們在教學之余,也積極進行文藝創(chuàng)作,中山大學師范學院黃友棣先生,1943年為中文系學生萬蕪軍創(chuàng)作的《杜鵑花》譜曲,是抗戰(zhàn)歌曲中的經(jīng)典之曲;中山大學師范學院馬思聰1944年創(chuàng)作了《F大調(diào)第一小提琴協(xié)奏曲》,是中國人創(chuàng)作的第一部大型小提琴曲。
以上所列,盡管是掛一漏萬,但卻可大致顯示出內(nèi)遷粵北高校先師們的研究實績。
不僅教師們勤奮科研,行政人員在公務之余,也積極從事科研,僅以中山大學、廣東文理學院校長在粵北期間發(fā)表的科研成果,即可得到說明。據(jù)不完全統(tǒng)計,中山大學校長許崇清先生,1941年發(fā)表《民族自由與文化建設》《所謂社會底層教育作用》;1942發(fā)表《學園告訴年輕朋友們》《教育即生長論批判》《社會改造思想機制》等;廣東文理學院校長林礪儒先生,1941年發(fā)表《民族建國與國民教育》,1942年發(fā)表《怎樣做中學校長》《精神剃須論》,等等。
同時,學校領導和教師們還不斷思考學校辦學理念,積累辦學經(jīng)驗,為日后組織、領導中國高等教育打下了思想與理念基礎,有先后成為武漢大學校長的李達,華東師范大學名譽校長的劉佛年,北京師范大學校長的林礪儒,廈門大學校長的王亞南,中央音樂學院院長的馬思聰,華南農(nóng)學院院長的丁穎等。
三、薪火相傳:培養(yǎng)、積蓄服務抗戰(zhàn)和建設的人才
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在整個遷徙辦學過程中,克服重重困難,秉承中華民族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堅持嚴謹、開放的辦學思想,積極投身于教學科研工作,為抗戰(zhàn)和國家建設培養(yǎng)了大批優(yōu)秀人才。“各科畢業(yè)生,大都能學以致用,出路頗佳,……抗戰(zhàn)以來在內(nèi)地服務實際擔任抗戰(zhàn)工作不少;其為求學術(shù)深造,畢業(yè)后再出國深造者亦所在多有。”[8]值得提及的是,內(nèi)遷粵北高校在抗戰(zhàn)時期極其艱難的環(huán)境下培養(yǎng)出了很多優(yōu)秀的畢業(yè)生,據(jù)統(tǒng)計,僅坪石時期的中山大學培養(yǎng)和畢業(yè)的學生就有2萬多人,他們?nèi)蘸笥械某蔀榱烁黝I域的杰出人物。
現(xiàn)擇要簡列如下:
何憲章,1940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研究院,后為廣東省農(nóng)業(yè)機械研究所高級工程師。
黃本立,1940年就讀于坪石培聯(lián)中學,1945年考入嶺南大學物理系,后為廈門大學教授,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著名光譜化學家。
張作梅,1941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工學院,后為中國科學院長春分院副院長,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金屬材料、機械工程學專家。
楊卓成,1941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建筑系,后為臺灣和睦建筑師事務所建筑師,臺灣漢族建筑設計大師。
張保升,1941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地理系,后為西北大學教授,我國著名地貌學家,我國醫(yī)學地理研究先驅(qū)。
鐘功甫,1941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地理學系,后為廣東地理研究所研究員,歐亞科學院院士,農(nóng)業(yè)區(qū)劃和生態(tài)農(nóng)業(yè)地學家,地理學家。
徐中玉,1941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研究院中國文學部,后為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教授,著名文藝理論家,被譽為中國“大學語文之父”。
梁釗韜,1941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人類學部,后為中山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馬壩人”鑒定專家,中國人類學、民族學奠基人之一。
歐明,1942年考入嶺南大學醫(yī)學院,后為廣州中醫(yī)學院副院長,教授。
周鳴錚,1942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研究院土壤部,后為中國科學院林業(yè)土壤研究所研究員,農(nóng)業(yè)分析化學家,我國土壤分析和測土施肥的開拓者之一。
羅來興,1942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地理系,后為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教授,中國著名地貌學家,黃土地貌研究奠基人。
彭澤益,1942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文學院歷史系,后為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著名歷史經(jīng)濟學家。
戴裔煌,1942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文科研究所人類學部,后為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中葡關(guān)系和澳門史研究先驅(qū)。
曾昭璇,1943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地理學系,后為華南師范大學地理系一級教授“當代地學大師”“水土保持研究之父”[9]。
張壽祺,1943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后為中山大學人類學教授,人類學家。
伍沾德,1943年考入嶺南大學,后為美心集團創(chuàng)始人之一,廣東省中山大學教育發(fā)展基金會理事,中山大學嶺南學院董事會名譽主席兼籌募發(fā)展委員會主席。
丘陶常,1944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研究所歷史學部,后為暨南大學教授。
黃翠芬,1944年畢業(yè)于嶺南大學化學系,后為軍事醫(yī)學科學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分子遺傳中心主任、名譽所長,1996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基因工程創(chuàng)始人之一。
涂西疇,1944年畢業(yè)于中山大學經(jīng)濟系,后為湖南財經(jīng)學院教授、院長。
陳香梅,1944年畢業(yè)于嶺南大學,后為中央通訊社第一位戰(zhàn)地女記者,有“中美民間外交大使”的美稱。
葉叔華,1945年畢業(yè)于真光聯(lián)合中學,同年考入中山大學數(shù)學天文系,后任中國科學院上海天文臺臺長、研究員,1980年獲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1980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這些,只是粵北華南高校兩萬多畢業(yè)生中的極少數(shù)代表,更多的畢業(yè)生則在各自的崗位,為民族的解放、國家的富強或者貢獻自己的青春與熱血,或者貢獻自己的知識與智慧,他們或服務于地方經(jīng)濟社會,或服務于戰(zhàn)時國家需要,或直接參軍參戰(zhàn),為民族抗戰(zhàn)及維系戰(zhàn)時生產(chǎn)和發(fā)展后方經(jīng)濟社會做出了應有的貢獻。用自己的行動踐行粵北華南教育精神,詮釋粵北華南教育的價值。
四、責任使命:促進地方經(jīng)濟社會的發(fā)展
從發(fā)展地方經(jīng)濟社會目標出發(fā),抗戰(zhàn)時期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把研究視野聚焦于與國計民生密切關(guān)聯(lián)的實際問題,努力將研究成果轉(zhuǎn)化為現(xiàn)實生產(chǎn)力。為增加戰(zhàn)時廣東糧食生產(chǎn),中山大學農(nóng)學院學人們除稻種純育外,還開展各區(qū)育成種及撿定種的比較試驗、冬作及雜糧的品種比較試驗等,將育成繁殖的稻種提供給廣東省政府,以期增加戰(zhàn)時的糧食生產(chǎn)。嶺南大學學人們則對農(nóng)藝、園藝、茶蔗、蠶桑、肥料、昆蟲、植病、畜牧、農(nóng)具、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與制造等進行研究,并將研究成果提供給地方政府或推廣給社會。此外,他們還與湖南、廣西兩省政府合辦湖南蠶絲改良場和廣西蠶絲改良場,致力于蠶絲品種的改良研究與技術(shù)推廣。農(nóng)學院蔣國慶先生進行家蠶培育,并指導農(nóng)民進行家蠶養(yǎng)殖。這些農(nóng)學研究與推廣收到了較好的效果。為配合戰(zhàn)時需要,學人們加緊對粵北與粵湘邊境一帶的軍事礦產(chǎn)資源進行調(diào)查,不僅對各礦藏的價值進行評估,還在此基礎上撰寫成報告,提供給政府和實業(yè)界參考[10]。這些研究成果對粵北諸地礦產(chǎn)資源的開發(fā)利用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他們除對日本血吸蟲在粵北的傳染、闌尾炎、華南肝硬化、胎兒軟骨營養(yǎng)異常癥、肺炎結(jié)核、華南人鼻炎粘膜慢性變化、多種腫瘤等進行研究,同時還征集各地臨床病理材料以作研究,為粵北各地醫(yī)院檢查病人材料,包括鏡檢、培養(yǎng)法、血清檢查及動物實驗等,為衛(wèi)生機構(gòu)檢查涼品及各種疫苗,制造多種診斷菌液血清及抗原,為粵湘贛各省醫(yī)院義務代驗臨床病理組織物,詳細報告研究結(jié)果,促進了我國南方醫(yī)療的進步[11]。
與之同時,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還通過抗戰(zhàn)宣傳動員、社會服務等多種形式,努力提高民眾的知識水平,改變其思想觀念和行為。為激發(fā)民眾的民族意識和抗戰(zhàn)激情,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先后組建了“下鄉(xiāng)工作隊”、“隨軍服務團”、“抗日先鋒隊”等抗日救亡團體深入縣、鄉(xiāng)從事抗日宣傳與動員工作。他們以群眾喜聞樂見的方式,如戲劇表演、音樂、運動、電影等,宣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意識,鼓勵民眾踴躍為抗戰(zhàn)捐款捐物,踴躍參軍參戰(zhàn)。如嶺南大學戰(zhàn)地服務團在韶關(guān)中山紀念堂舉行戲劇音樂軍民同樂會,就造成了一時無兩的空前社會影響[12]。為改善中等教育師資,中山大學師范學院設立各科教材教法研究委員會,籌辦設置初中教員進修班;設置小學教育通訊研究處,招收通訊研究生,其中招收特別研究生171人,普通研究生145人,按月寄發(fā)研究參考大綱,派教授到粵北各中學巡回輔導,每年巡回一區(qū),選出富有中等學校教學經(jīng)驗及研究興趣的教授為輔導委員,輔導各中學的英文、國文、數(shù)學、歷史、地理等科教學。為改變普通民眾大多數(shù)為文盲,既身無長技,又毫無現(xiàn)代戰(zhàn)爭常識的現(xiàn)狀,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以固定掃盲學校和文化補習班為主,以民眾流動教學為輔,積極開展民眾文化補習以及防空、防毒等國防知識、自然科學科普常識、藝術(shù)與公共衛(wèi)生習慣等教育活動,引導和提倡健康的娛樂活動,以提高民眾素質(zhì)和改良社會風氣。這些活動在當?shù)禺a(chǎn)生了較好的影響。為增加當?shù)孛癖姷纳a(chǎn)生活技能,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還大力推行生產(chǎn)與生計教育,除通過開辦各種培訓班、函授學校傳授民眾生產(chǎn)技藝和技術(shù)外,還開展了形式多樣的技術(shù)推廣和社會教育活動。如利用考察與技術(shù)推廣的機會將農(nóng)業(yè)知識和經(jīng)驗推廣給農(nóng)民[13];通過舉辦農(nóng)產(chǎn)品展覽會和出版街頭壁報(周刊)和《農(nóng)事淺說》的形式,介紹農(nóng)事常識和農(nóng)業(yè)科技知識以及解答農(nóng)民和社會人士關(guān)于農(nóng)事的詢問等[14]。
五、歷史內(nèi)涵:穿越時空的華南高校大學精神
大學精神是大學的靈魂。在外遷、返遷與繁復遷徙的辦學過程中,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逐漸凝結(jié)成了一些帶有共同精神特質(zhì)的優(yōu)秀品格,即大學精神。
一是民族為難之際的家國情懷。毫無疑問,愛國主義是抗戰(zhàn)時期內(nèi)遷高校的精神內(nèi)核。相較于戰(zhàn)時內(nèi)遷西南、西北地區(qū)的國內(nèi)高校,生于華南、長于華南的粵北華南高校群體具有濃郁的愛祖國與愛鄉(xiāng)里愛故土意識,達到了合乎時代與邏輯相統(tǒng)一的獨特家國情懷。“東望故鄉(xiāng),白云水隔,遐想珠海,金波玉液,石牌廣原,胡騎充斥,為何風光,可能如昔?”[13]152這段話反映了外遷游子對國家前途的擔憂,對故土的深深眷戀。由此也就不難理解,抗戰(zhàn)爆發(fā)后中山大學、嶺南大學為代表的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在遷徙過程中為何出現(xiàn)一再遷徙,甚至圍繞粵北反復多次遷徙這一高校內(nèi)遷史上獨特現(xiàn)象的發(fā)生。可見,這一現(xiàn)象與其牽念故土大相關(guān)聯(lián)。也正是這一獨特家國情懷,顯示出身處他鄉(xiāng)的師生,與祖國與內(nèi)地與華南同呼吸共命運。香港淪陷,嶺南大學遷到韶關(guān),時偽廣東大學想聘請陳心陶,陳心陶嚴詞拒絕,不當漢奸,帶著妻兒歷經(jīng)艱辛隨嶺大來到粵北。冼玉清謝絕家人及朋友邀其留在澳門的好意,以“今國家正在為難之時,我應與全民共甘苦,倘因一已有優(yōu)越條件而高枕茍安,非素志也”[15]為由,依然決定冒險到粵北嶺南大學任教;當日軍即將到達坪石前夕,人人爭相逃命,中山大學圖書館主任杜定友抱定“與中大圖書同生死”的決心,力爭要將中山大學的幾十箱圖書隨車撤走,終于感動了鐵路當局。中山大學建筑工程系衛(wèi)梓松教授,因病未來得及隨眾撤退,落入敵手,日軍欲利用他的聲望,威逼利誘他出任坪石鎮(zhèn)維持會會長,衛(wèi)梓松以死明志,于1945年3月3日服用安眠藥自盡。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立足粵北諸地,在保持和延續(xù)中國高等教育的同時,投身抗日救亡運動,或積極響應當局號召參軍,或踴躍服務于國家軍需征調(diào),或積極奔赴前方作戰(zhàn),如嶺南大學的毛錦霞同學參加了共產(chǎn)黨領導的抗日活動,中山大學的200多名師生加入東江縱隊,參加抗日戰(zhàn)爭。在戰(zhàn)火硝煙中踐行“愛國愛家”、“精神同聚責同擔,愛報兩勿忘”[18]的嶺南精神傳統(tǒng),為抗戰(zhàn)奉獻自己的青春熱血和生命。
二是教學科研追求自由的精神。在戰(zhàn)火紛飛的歲月,無論條件多么艱苦,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始終秉持開明、民主與自由之理念。教授治校不同程度地體現(xiàn)在粵北華南高校的大學管理之中。教師聘任的標準是唯才是聘,因而教師中既有基督徒,也有非基督徒,同時還有進步學者和作家;不同的學術(shù)觀點可以在校園公開自由辯論,各類社團組織可自由創(chuàng)建;李濟深演講的“反對獨裁,爭取民主”的內(nèi)容摘要可以在校報發(fā)表,馬克思主義經(jīng)濟學原理以及辯證唯物論等課程或講座可以開設舉行。自由的學術(shù)氛圍,促進了學術(shù)交流的頻繁,也促成了不少研究成果的產(chǎn)生。
三是互助克難辦學的奮斗精神。姑且不論遷徙過程的艱難,粵北、粵東諸地辦學時期,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面臨著時局的動蕩、辦學經(jīng)費的極度短缺以及政治因素的干預和制約等等困難與挑戰(zhàn)。就師生個人言,主要有日軍空襲和臨近戰(zhàn)區(qū)帶來的心理恐慌和生命威脅、戰(zhàn)爭引發(fā)的家庭變故和與家人分離的情感煎熬、衣食住行等方面的生計危機以及圖書資料與儀器設備短缺給研究和學習造成的諸多制約,等等。但內(nèi)遷粵北華南高校師生并沒有因此消極沉淪,反而是苦且益堅。一方面,本著苦斗精神,“日則節(jié)膳忍餓,面多菜色,夜仍焚膏繼晷,目注蕓編……始終不懈。”[16]另一方面,各校則發(fā)揮互助精神,共克難關(guān)。如嶺南大學農(nóng)學院的學生委托中山大學農(nóng)學院予以代培。東吳大學遷至粵北大村之時,面臨校舍困難,嶺南大學則義無反顧地提供暫住校舍,幫其解決燃眉之急。湯擎民在《仰念詹安泰先生》中寫道:“先生于鐵嶺下賃得臨江泥屋數(shù)椽,只有十來平方米的地方,用泥磚隔成前廳后房。前廳的全部陳設是一張小書桌,兩張靠背竹椅和一副‘功夫茶’具。客廳,同時也是書齋。”[17]正是憑著這種艱苦奮斗與互助克難的精神,使得華南的高等教育并未因戰(zhàn)火而間斷。
六、現(xiàn)實呈現(xiàn):歷久彌新的多維度當代意義
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而“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18],今天,我們致力于挖掘研究抗戰(zhàn)時期粵北華南教育史,具有如下之意義:
一是從抗戰(zhàn)時期粵北華南教育歷史中,可尋覓、發(fā)現(xiàn)華南高等教育歷史的脈絡。粵北華南教育史,是華南高等教育史中重要的發(fā)展環(huán)節(jié),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作用。粵北華南高等教育中有關(guān)治校設計、院系調(diào)整、學術(shù)活動、科研成果等目前均關(guān)注不夠、彰顯不夠,研學粵北華南教育史,可以了解華南教育,尤其是華南高等教育的發(fā)展歷史,了解華南高校的發(fā)展脈絡和傳承因緣,明晰華南高校教育先師們?yōu)槿A南教育的延續(xù)發(fā)展所做出的貢獻,更可了解華南高等教育在全國的學科地位。
二是從抗戰(zhàn)時期粵北華南教育歷史中,可傳承、發(fā)現(xiàn)粵北華南教育的精神。抗戰(zhàn)時期內(nèi)遷粵北的華南教育史,是一部不畏困難、迎難而上的奮斗史。從這部歷史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多種華南高等教育精神,或者熱愛祖國的精神,或者追求科學的精神,或者抗戰(zhàn)必勝的精神,或者不怕苦難的精神,或者服務人民的精神。開展粵北華南教育史的研學,就是要從粵北華南教育史中,汲取這些精神的營養(yǎng),滋潤豐富我們的師生乃至民眾,發(fā)揮粵北華南教育史的育人功能。
三是從抗戰(zhàn)時期粵北華南教育歷史中,可找到文化灣區(qū)的共同文化基因。粵北與港澳本就同根同源,人們之間有著千絲萬縷的因緣,抗戰(zhàn)時期內(nèi)遷粵北的華南高校,有的學校是從香港輾轉(zhuǎn)遷徙而來,有的師生是港澳之人,他們或隨學校而來到粵北育人,或為追求知識而來到粵北求學,有的師生后又回到港澳,服務于港澳的社會經(jīng)濟建設,由此更加深了港澳與粵北的聯(lián)系與感情,因此,在粵港澳大灣區(qū)建設中,可以發(fā)掘當年粵北華南教育中共同的教育記憶和共同的情感,動員當年參與華南高校教育的當事者和后裔,來到粵北華南教育研學基地,檢拾當年的教學記憶,同敘當年的家國情懷,發(fā)揮他們在港澳的力量,共同為推進人文灣區(qū)的建設做出貢獻。
四是從抗戰(zhàn)時期粵北華南教育歷史中,可找到鄉(xiāng)村振興的動力。抗戰(zhàn)時期內(nèi)遷粵北的華南高校,在教書育人之余,師生們積極利用知識服務于粵北鄉(xiāng)村的建設與發(fā)展,或是服務于農(nóng)村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如農(nóng)學院蔣國慶先生開展家蠶品種保育,并在粵湘農(nóng)村推廣養(yǎng)殖;或是服務于農(nóng)民身體的健康成長,如中山大學醫(yī)學院黎希干先生從事粵北僑肥血型的研究;或是服務于農(nóng)民文化生活的提高,如開辦夜校,開放圖書館。研學抗戰(zhàn)時期粵北華南教育歷史,就是學習、汲取他們服務于鄉(xiāng)村建設的精神,以新時代社會經(jīng)濟發(fā)展的要求,將自己的知識服務于鄉(xiāng)村振興建設,多方面參與鄉(xiāng)村建設,為促進粵北鄉(xiāng)村和廣大農(nóng)村地區(qū)的農(nóng)民致富和鄉(xiāng)村的振興,貢獻知識與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