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辭筆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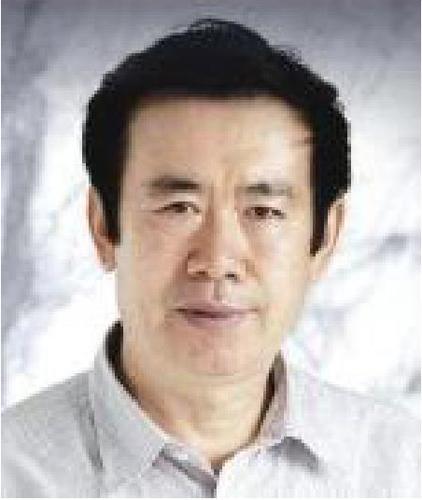
張煒
超越怪力亂神
隨著向南,歌聲中的神巫氣息愈發濃重,南國如此,東方亦如此。魯國東面的齊國,素有談仙論道的傳統,那里的人追求長生不老。在浩淼的大海深處,在繚繞的海霧之間,云開日出之時,一些迷離的島嶼隱約可辨,它們被稱之為“蓬萊”。杜牧《偶題》詩云:“今來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萊不是仙。”白居易《新樂府·海漫漫》中描繪:“云濤煙浪最深處,人傳中有三神山。山上多生不死藥,服之羽化為天仙。秦皇漢武信此語,方士年年采藥去。蓬萊今古但聞名,煙水茫茫無覓處。海漫漫,風浩浩,眼穿不見蓬萊島。”那里有“蓬萊”“方丈”“瀛洲”三座仙山,有仙人騰云駕霧而去,上達靈霄,據說不僅僅停留在傳說之中,而是時有發生。這一切具有多么大的誘惑力,曾經使一個個炙手可熱的權勢人物,如秦始皇等,一次次奔向那里,做著永生之夢。那個地方雖與儒家傳統思維多有忤逆,可是孔子所推崇的周公等人,對于傳說中的宗族先人和山川諸神,都充滿了敬畏,經常祭祀祝禱。
這一切仍然與“怪力亂神”脫不了干系,盡管它們中間還有一些嚴密的界限,但無論如何還是超越了現世人生。至于詩人屈原所生活的楚地,人神交集、穿梭往來之頻繁深入,思緒之飄逸、飛揚和爛漫,又遠遠超過齊國。神巫之聲震耳欲聾,它們在生活的許多角落里滋生茂長,在一些固定的祭祀場合里,簡直成為最隆重的旋律。這一切是傳統,是風俗,是現實生活之需,它在人類生存的許多方面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神巫之事業,廟堂不可以超越,權臣不可以超越,禮法、政事、體制,都充斥著它們的色彩。
我們深受儒家文化熏染,對于“怪力亂神”有一種隱隱的不安,甚至會產生拒斥心理。然而,儒家之“不語怪力亂神”,并不表明一概否認和無視,只是“不語”而已。那些儒家的代表性人物,其知悟力和思辨力還不至于一概否定某些未知領域,他們沒有這樣武斷。他們的“不語”之中就包含了某種敬畏,為復雜難言的神秘事物保留了一個空間,置留了一個余地,仿佛留下了未來言說的可能。比如在孔子“不語”之時,我們會聽到他的另一種聲音,感受到他對于上天的肅穆神色。他不回避蒼穹中的那種力量,而且相信夢境、宿命,相信冥冥中那些不可忽略、具有決定力的元素,也談到了“知天命”。而在東方齊國,在煙濤迷茫的沿海地帶,更有南方楚國,在長江淮河流域迷蒙的山霧之中,這一切卻逼到了眼前。一方水土培育一種認知,楚人不僅要言說,而且還要放聲歌唱,旋律之中滿是“怪力亂神”,這種傳統比齊國更為盛大和持久。
楚地可以找到許多“靈媒”,這一特別的角色在人世與神鬼之間打開了一條通道,以便自由來往,互通有無,互為借助。在人類虔誠的祈禱中,在豐盛的筵席間,神鬼領受和享用了尊榮與美味,它們常常是攜著人間犒賞,甚至是賄賂滿意而去。人與神鬼之間達成了諒解,各取所需,是一次美好無間的合作,這個過程大致是愉快的,并且是有效的。人類生活的苦難,被來自另一個世界的力量給平衡、消解和驅除了,盡管還不是全部,但已經是至為寶貴的援助了。
生活在這種環境中,深受神巫文化傳統熏染的詩人屈原,當然相信這一切。他是一個參與者,實踐者。他在《離騷》《天問》《九章》和《九歌》中,都毫不隱諱地表達了這些意緒,而且沉浸其中;在這些詩篇里,他作為一個杰出的呈現者,比民間那種濃烈的色調更增添了一份堅信、確鑿和理性。但屈原也深受儒家思想的影響,謹慎而忠誠地事君,他對于社稷的強烈責任,他的拘謹與恭敬,他對于周代禮法與體制的恪守,又說明思想深處仍然是一個儒者。只是他詩篇中所表現的神巫之氣,似乎與儒家意識形態存在著較多差異。
對于“怪力亂神”,屈原不僅是能言,而且還做出了豐沛的表達,這一點多少給我們帶來了一些迷惑。他在形式上不斷吸取和借用南國祭祀之歌,甚至跟隨靈媒的牽引,走入那個時而歡樂、時而陰森、時而怪異的非人世界。他需要神巫的幫助,就像生活在貧窮困境中的勞民一樣,那么無助、惶惑,甚至是恐懼。生活的不可預測性、危險性,一次又一次逼近了他,讓他產生了一種絕望感。在這痛苦的掙扎中,他沒有任何辦法,只好投向那個鬼神的世界。他實在需要尋找,需要詢問,需要這份慰藉和支援。“欲從靈氛之吉占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兮,懷椒糈而要之。”(《離騷》)
屈原離開宮廷,踏上流浪之路,走向了民間。民間生活所依靠和借重的那些“怪力亂神”,使他感到耳目一新,進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他與現實中大多數人一樣,認同了這種精神依托,用他們的音調吟唱,順著他們的途徑前行,在精神的攀援和尋找中,漸漸走向了自己。這個“自己”與民眾還存有不少的距離,看起來相似,實則又有許多區別,有超越性。詩人越過形式和表象,走向了自己的世界觀,靠近了自己的理性主義。他自身的修養和遵循的禮法,使他的歌詠與民間仍然不同,在地域文化以及審美特征上產生了許多差異。總而言之,詩人還是歸入了一種個人的自由表述,這對于神巫之歌是一次突破和創造。
詩人穿行于神巫之間,與其交集往來,但掛念的依然是個人的政治立場,貫徹的仍舊是自己的道德倫理。就這個層面來說,他頑固而執拗,只是求助于它們來驗證自己、說明自己、大聲宣示自己而已。他將這其中獲得的一份自信、純粹而堅定的信念,帶回現實的使用和判斷之中,在與民間相類似的形式里,塞入了個人的內容。這是一個貴族詩人的取向,是一個儒家臣子的訴求。這一切當然是其出身及所屬階層所決定的,是宮廷和民間文化的結合。正是由此,產生了我們所看到的這樣一位詩人。
詩人是一個集大成者,是一個復雜的綜合體,他把自然和鬼神、民間和宮廷,把豐富而繁瑣的巫術祭祀、莊嚴齊整的宮廷禮法,把悲觀絕望、剛直不屈、委婉低沉與山野星空下的求索叩問等,全都囊括一體,完成了復雜糾結而又悲憤莊嚴的一生。直到生命的最后,他仍未放棄那份剛倔與自尊,它們成為他吟唱中最為驚心的部分,就是這個部分,讓后來的傾聽者變得心情肅穆,淚水潸潸。
在鐵與綢之間
屈原的一生是政治的一生。他是一個政治詩人,一個廟堂里誕生的抒情者。我們可以設想,如果他沒有走入逆境,就可能成為西方的那種“桂冠詩人”,詠廟堂之趣,歌廟堂之德,而且不乏強大、絕美和華麗。他將領受一切王權的光榮和恩惠,獲得崇高的世俗地位。以他的資質、能力和身份,完全諧配那頂桂冠。然而屈原走向了一條完全相反的道路,他是一個政治失意者,一個被排擠和傾軋的廟堂忠臣,進而成為一個流放者。記載中至少有過兩次流放,一次比一次悲苦,一次比一次不堪,壓力加大,苦難加重,最后窮途末路,一死了之。
這一切的根源頗為復雜,有政見之爭,有個人恩怨,還有其他種種難言的一切,但政見分歧可能是一個癥結。楚國宮廷內部雖然紛爭繁復,卻有一個基本而重要的選項,它將朝臣分成兩大派別:親秦派與親齊派。秦國與齊國構成了一西一東兩大存在,一個是軍事強國,一個是經濟強國,有著不同的文化結構和生活指向。在七雄競逐的政治版圖上,領土闊大的楚國具有至關重要的地位,它倒向和傾斜于某一方,后果將是致命的。
諸侯割據、四分五裂的戰國時代,催生了一大批“合縱連橫”的搖唇鼓舌者,即所謂的“縱橫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為張儀和蘇秦。這些巧舌如簧之流走馬燈似地穿梭于各諸侯國之間,使整個社會局面更加動蕩。從一段段奇妙的歷史記載中,便能感受那個充滿了戲劇性的特殊時代,那些記錄簡直不像真實的歷史,而更像一出演義和小說,像埋下了伏筆的戲劇設計,像一支掛在墻上必要打響的槍,像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戲劇理論中所規定的格局:既驚心動魄又過于巧設。可是真實的歷史確是如此,張儀和蘇秦之輩屢屢得手,他們以一人之力攪動天下,無論是秦國、齊國,還是其他五個大國,無論多么神圣莊重的盟約,多么足智多謀的臣僚,多么威赫的文武班底,竟然都難敵一人口舌之力。他們時而唇槍舌劍,時而聲情并茂,其巨大的說服力誘惑力簡直令人不可想象,嘆為觀止。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當時的政治、外交、軍事與經濟,甚至影響了一個民族的未來,并且直到幾千年之后的現代社會,都要承受當年的歷史后果。
當時中華民族曾面臨許多選擇,或是將命運指針撥向窮兵黷武的西部強秦,或是撥向繁華富庶的東方齊國。齊地海風吹拂,物質富裕,昌明而奢華,其強勁的物質主義和商業主義在戰國時期最為突出。它與秦國那種嚴苛、凜冽的高原性格相距甚遠,與現代物質主義的揮霍奢糜、與強大娛樂主義的末世情結,倒是頗為接近。當時處于齊國腹地的東夷族已經發明了煉鐵術,從而使冷兵器時代發生了一次飛躍,出現了更加鋒利的刀劍和箭簇,于是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原來銅錫合金為主的金屬兵器,得到大幅度的躍升和改良,殺伐之力大為加強。
在發明者的故鄉齊國,由于財富的巨量積累,科技水平遙遙領先于其他諸侯國,所以齊人擁有非同一般的軍事力量,甲胄閃亮,軍服炫眼,馬匹強壯,戰車堅固,可以說齊國的一切,無不令出使該國的屈原驚嘆。記載中鼎盛時期的齊軍氣象非凡,所向披靡,只是到了后來,齊國的繁華和富裕走向了反面,它的豪奢浮華、物質主義、娛樂至上使國民慵懶頹廢,國家政體變得虛浮無力,精神渙散,心理頹蕩。于是歷史記載中又出現了另一種描述:這些裝備精良的齊國士兵徒有很強的觀賞性,一旦拉到戰場上,戰鼓一響,弓箭一發,他們即扔下武器四散而逃。這都是后話了。除了鐵的發明,齊國人還發明了絲綢和紡織術,柔軟華麗、輕薄到不可思議的絲綢,成為天下最精美、最令人驚嘆的物產。有了絲綢才有后來的“絲綢之路”,讓整個世界為之驚艷。通過那條蜿蜒曲折、悠長遙遠的道路,才有了漢文化的西進傳播。
當年齊國的絲綢會對詩人屈原產生多么大的誘惑,它不同于冰冷的鐵,它不是堅硬的、單調的,而是滑潤的、五彩斑斕的。直到今天,絲綢的代表作仍然存于齊國故地周村,可見這個傳統是多么頑固而深遠。如果說鐵器代表了生硬與殘酷,那么絲綢就代表了享用和安逸,它是日常生活中柔軟的代表,是享受和娛樂的象征。后來人們幾乎可以忽略齊國與鐵的關系,卻牢牢記住了它與綢的關系。
位于長江流域的楚國,面對秦國和齊國伸出的橄欖枝,也就變成了“鐵與綢的選擇”。絲綢的柔軟、起伏如大海之波,與三面環海的齊國氣質更為接近。鐵雖然產生于東方,最大受益者卻不是發明者東夷族,不是齊國,而是西部高地上的秦人。鐵的冷硬鋒利使人想起凌厲嚴酷的西北風。就文化血緣上的親近感而言,屈原自然會選擇齊國,這緣于那種浪漫的文化血脈。齊國松弛開放,神仙文化源遠流長,有迷人的《韶》樂,更有思想的都會稷下學宮。魚鹽氣息代表著富足,屈原向往東方,向往大海,在今天看來,似乎更接近于一種現代思想和審美方向。我們無法想象一個渾身掛滿鮮花的純美詩人會選擇西部強秦;那些海霧迷茫中的仙山與放逸,與沖淡的老莊思想有著某種相似之處。還有齊人鄒衍關于大九州的浪漫想象,顯然都在預示一條自由開放之路。
在齊、秦、楚三國鼎立時期,楚國的任何選擇都舉足輕重。楚國擁有長江淮河流域的廣大土地,物產豐富,氣候濕潤,景致優美。楚人倔犟、強悍,具有非同一般的心智和力量。楚國有一句傳播很遠的民謠:“楚雖三戶,亡秦必楚。”其意是,即便楚國只剩下三支氏族,也能滅亡秦國。這是多么雄壯的豪志,令人恐懼,與陶醉在物質享受和消遣娛樂中的齊國是多么不同。后者擁有最先進的技術和巨量財富,有著令人迷戀的音樂藝術,甚至還發明了足球。記載中,齊國都城臨淄的居民,生活優越閑適,趾高氣昂,這在戰亂頻仍、爭奪慘烈的冷兵器時代,這是多么危險的一種生存狀態。實際上這種繁華與優越最不堪一擊。正是在這樣一種歷史情勢之下,楚齊聯合多么明智和重要,那將是財力與強悍的結合,并體現了倫理的優越性。相對于冷酷、粗蠻和血腥的強秦,這種聯合將是中華民族的理想選擇,是楚人獲取最大利益、擁有美好未來的一個決定性步驟。
作為外交大臣,詩人屈原幾次出訪齊國,并且有過長長的滯留期。在那個舒緩富裕的國度里,他感受了人性的舒暢與自由,其情感的靠攏是自然而然的。一個明晰洞察的詩人,對于齊國當然也不可能毫無保留,只是在記載中我們沒有看到留下來的相關文字。總之,以詩人為代表的親齊派一度占了上風,最終卻由于各種原因失敗了,楚國竟然選擇了秦國。其結局就是楚懷王被強秦囚禁,楚國慘敗,國破家亡,楚國都城被迫遷移,群臣潰逃。
這段歷史不堪回首,與國家共存亡的詩人也走向了自己的末路,投向了大江。水波像絲綢一樣起伏抖動,撫摸、纏裹著詩人,一起奔向那個遙遠的所在。冰冷堅硬的鐵割裂了綢,戰勝了綢,從此,一個民族不幸的未來便依次展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