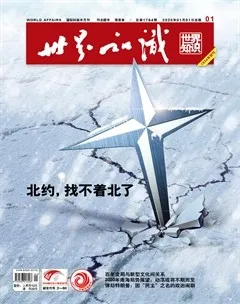日本“印太戰略”的幾個維度
薛力
日本的綜合國力被中國超越,并且差距越來越大。這對日本來說,正是“百余年未有之大變局”。日本為此全面調整對內政策與對外戰略。構想與推動日本版“印太戰略”就是其中的一環。
在內政方面,日本采取的措施有:在政治與軍事上,成為“正常國家”,例如把防衛廳升格為防衛省、通過憲法解釋實現海外派兵、致力于修改憲法第九條;在經濟上調整結構、加快產業升級與中低端產業的海外轉移;調整政府開發援助(ODA)適用標準與對象國;推動觀光立國以培育經濟新增長點;在教育與科技上強化投入,鼓勵基礎科學創新,并且效果明顯。新世紀以來日本獲得諾貝爾獎者達18人,僅比美國少一人,遠遠多于英德法等。
在外交方面,日本的戰略思維很清晰:靠自身無法與中國競爭與抗衡,有必要采取多方面的綜合措施,包括政治上保持距離、經濟上有限接觸、文化上展開競爭、安全上強化防范。
在政治上,日本不認同中國的政治制度與政治價值觀,無意與中國進一步強化政治關系,認為自己“西方一員”身份在處理對華關系上是個優勢,為此倡導構建一個環繞中國東部、南部、西南部的“自由與繁榮之弧”。
在經濟上,先是以經濟伙伴關系協定(EPA)為抓手,強化與一些國家的經濟關系,繼而力倡“10+6”以對沖中國主張的“10+3”。當發現10+6在一些方面不足以平衡中國、甚至可能也被中國主導后,轉而先后采取加入TPP、主導CPTPP等措施。對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先是疑慮與反對,但經過幾年觀察后,認識到其對日本的一些潛在價值,加上應對特朗普“美國優先”的需要,因而轉而采取有限度支持的立場,并將第三方市場合作確定為重點,但迄今進展有限。
對于剛剛結束的除印度以外的15個國家的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文本談判,日本認為,沒有印度的加入,日本不會簽署RCEP。個中原因,還是擔心自己在RCEP框架內難以制衡中國。
在文化上,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例如在2015年提出、實際效果超出預期的“觀光立國”政策;通過一些非政府機構,以日本文化節等方式在全球推廣“魅力日本”的做法;在政府機構與非政府機構的扶持下日本料理店在全球樹立“中高檔餐館”形象;東京都把動畫產業作為地方特色產業進行扶植和推廣等。從國家形象構建的角度看,日本的文化外交取得了成功,對日免簽國家已達到189個,排名世界第一;而國際游客的滿意度平均達到80%,中國游客對日本旅游的滿意度更是高達90%。
安全問題是日本印太戰略的核心領域。日本擔心中國的“威脅”,認同“亞太再平衡不足以平衡中國,需要擴展為印太再平衡”的觀念,因此安倍2016年提出日本版“印太戰略”:從太平洋到印度洋的廣大地區,擁有“相同價值觀”的國家進行合作,日美澳印將起主導作用。日本對構建“四國同盟”的熱情超過了其他三個國家。
但以“四國同盟”為標志的印太再平衡進展有限。雖然美國建制派、民主黨與軍方對此有興趣,但強調美國第一、注重實利的特朗普則興趣有限;奉行“不結盟”,強調外交上的“戰略自主性”的印度不愿成為他國對抗中國的工具;澳大利亞擔心影響與最大貿易伙伴中國的經濟關系。而東盟國家希望在印太地區保持其中心地位,不希望在中美之間選邊站,對日本力推“印太戰略”持保留態度。考慮到東盟國家是“海外日本”的重點組成部分,以及中日政治關系的改善,日本于2018年11月開始用“印太構想”取代“印太戰略”。
日本也不反對與美韓組成亞洲版小北約,與韓國簽署《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就是典型表現。但由于歷史問題與國民情感的對立,這在可以預期的未來難以實現。文在寅政府甚至一度決定不再續簽上述協定。
總之,無論是“印太戰略”還是“印太構想”,日本在印太地區外交方略的主要目標都是中國,其主要措施是:遠交近守、平衡中國、保持影響、獲取實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