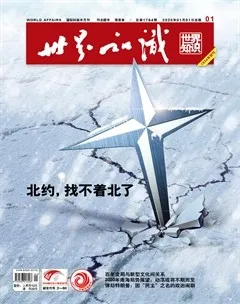第二次中亞峰會:由凝聚共識到協商共治
許濤
2019年11月29日,被稱作“中亞峰會”的中亞五國領導人會晤在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舉行。這是2018年3月15日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今改稱“努爾蘇丹”)舉行的首屆中亞五國領導人會晤的后續進程。本屆中亞峰會不僅豐富和發展了上次會晤的議題,而且各國領導人還通過《聯合聲明》和各自講話提出了一系列旨在加強地區內安全、經貿、交通、人文等領域合作的具體倡議,完成了一些理念上的重要升級,預示中亞各國協作關系將進一步深化。
首先,各國參與協商解決地區問題的熱情明顯增高。由于歷史和地緣的原因,目前中亞國家在眾多方面面臨共性問題,如安全、水資源、生態、交通等。在2018年3月的首次峰會上,中亞各國領導人對搭建一個合力面對共同問題的協商對話平臺均抱參與態度。但這畢竟是中亞國家獨立解決自身問題的首次嘗試,各國參與熱情不一。例如,2018年土庫曼斯坦是由議長努爾別爾德耶娃作為總統特使出席會議。而2019年土總統別爾德穆哈梅多夫不僅親自出席,還提出建立中亞商務委員會等具體倡議。除烏茲別克斯坦、哈薩克斯坦兩個致力于建立長期的中亞國家元首工作會晤機制的中亞大國外,吉爾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等中亞小國也表現出明顯的熱情,提出諸如借助中亞峰會平臺與美國、俄羅斯等大國加強合作的倡議,不再像過去那樣只是被動跟進和謹慎觀望。
其次,由倡導共同民族精神轉向務實合作。2018年在阿斯塔納的會議是蘇聯解體后首次沒有設置域外席位的中亞五國領導人會晤,所發表的《聯合聲明》重點強調了“凝聚地區共識、推動合作、相互支持、共同解決所面臨問題”。雖然也提到“利用水資源、糧食安全、發展工業、高新技術、數字經濟”等領域,但基本沒能提出具體的措施和方案。本屆峰會上,各國元首分別提出了各種具體建議,大致可歸到三個層面:一是關于峰會機制建設,如哈薩克斯坦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倡議商簽《21世紀中亞發展睦鄰合作條約》和舉行中亞各國國家安全會議秘書會議;二是關于地區經濟發展,如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提議簽署《關于中亞運輸系統共同發展的協定》和建立“中亞國家投資論壇”“中亞工商協會”;三是關于加強地區文化聯系,各國領導人提出了設立“中亞日”“中亞科技文化獎”、舉辦“中亞旅游大會”和“中亞運動會”等倡議。這些提議不僅反映出中亞各國當前對地區事務的主要關切,也預示著五國領導人會晤機制今后的發展方向。
第三,維護共同利益的意識進一步強化。從醞釀首屆峰會時開始,主導國就巧妙選擇了五國在民族文化方面的共性作為切入點,回避了各國在民族、語言和宗教派別等方面存在的差異。如納吾魯孜節是流傳于許多歐亞民族的重要節日,被中亞峰會選作共同的民族文化符號。本屆峰會上,五國領導人除了提出設置一系列冠以“中亞”之名的獎項、基金、紀念日、共同機構、國際論壇外,還通過《共同聲明》表示,“在政策方面加強區域合作,維護地區安全與穩定,實現可持續發展符合中亞國家人民的根本利益,有利于進一步加強兄弟般的關系,用強大的中亞文明潛力促進地區經濟和人文事業共同發展”,并表示希望通過“兄弟般的”團結協作“促使中亞成為一個穩定、開放和充滿活力的發展中地區,成為國際社會的可靠成員”。
第四,烏茲別克斯坦發揮主場優勢推動峰會升級。中亞峰會的啟動源于米爾濟約耶夫接任烏茲別克斯坦總統以來對烏內政外交的改革,而烏茲別克斯坦對外政策的重大調整之一就是改善與中亞鄰國關系。在此背景下,米爾濟約耶夫在2017年9月的聯合國第72屆大會上首先提出定期舉辦中亞國家元首工作會議的建議。同年11月,米爾濟約耶夫在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舉行的一次國際研討會上再次提出來年舉行首屆中亞峰會,并建議成立“中亞國家領導人協會”。哈薩克斯坦首任總統納扎爾巴耶夫一周后宣布2018年3月在阿斯塔納舉行首屆中亞峰會,并向各國領導人發出邀請。烏茲別克斯坦雖未爭取首屆峰會主辦權,但一直是有關倡議公認的發起者。盡管第二屆峰會由于種種原因延至2019年底舉行(上屆峰會確定2019年3月納吾魯孜節期間在塔什干舉行第二屆峰會),但烏方仍為本屆會議做了細致安排,米爾濟約耶夫親自到機場迎送所有領導人,安排各國元首向烏前總統卡里莫夫紀念碑獻花,在烏總統官邸舉行“象征五國兄弟之情與合作的友誼樹”種植活動,推選納扎爾巴耶夫為“中亞五國領導人會晤名譽主席”等,在形式上將中亞峰會推上新臺階。

2018年3月,首屆中亞峰會在哈薩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納(今改稱“努爾蘇丹”)召開。
第五,地區領導人會晤模式的定位更加清晰。本屆峰會《聯合聲明》提出,“中亞國家為把握可持續發展的新機遇,信任、協商、互動的需求不斷增加”;“中亞國家通過定期領導人會晤和中亞國家外長會晤形式開展政治協商與合作對話,并逐步推動這一形式的機制化”;“中亞國家間的政治協商和對話進程是開放性和建設性的,并不針對第三方的利益”。同時,對地區安全威脅除強調阿富汗局勢仍是重點外,在水資源分配、人口增長、沙漠化威脅、咸海生態災難等非傳統安全問題上也達成共識,并提出要在聯合國相關決議框架下繼續采取聯合行動的倡議。回避地區“一體化”概念,以中亞地區集體身份參與當今國際進程的倡議,也成為本屆峰會引人注目的新理念。在全球政治、經濟形勢充滿不確定性帶來風險的情況下,協調中亞各國政策、整合地區資源有利于增強中亞地區國家獨立抵御各種威脅的能力。《聯合聲明》還表示將促成中亞各國在參與聯合國、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等國際機制時達成初步的政策協調,以提高本地區在全球事務中的獨立地位。
第二屆中亞五國領導人會晤召開后,俄羅斯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國際研究所主任研究員安德烈·卡贊采夫在《生意人》報上發表題為《不加也不減的五國》文章,評稱,中亞各國獨立后曾經長期探尋一種與全球性力量互動的最佳模式,用“5+1”的方式為自身發展“外掛火車頭”,如“5+美國”“5+歐盟”“5+日本”等,當然也包括“5+俄羅斯”。“中亞國家最終選擇了自己創造的一個新框架”,“從長遠來看,這將是加強該地區穩定與合作的更有效方式”。作者也指出,中亞國家要成為真正意義上具有獨立性的“中亞5”,還有很多問題要解決。的確,由于歷史的原因,中亞各國之間仍然遺留著錯綜復雜的問題。但更應看到的是,中亞國家間也存在著大量的共同利益和必需共享的資源。兩屆中亞領導人會晤標志著整合地區發展要素的進程已經啟動,而且其動力就發自于中亞五國自身。這一進程有利于中亞各國的穩定與發展,地區的整體繁榮自然也有利于“絲綢之路經濟帶”框架下的中國與中亞各國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