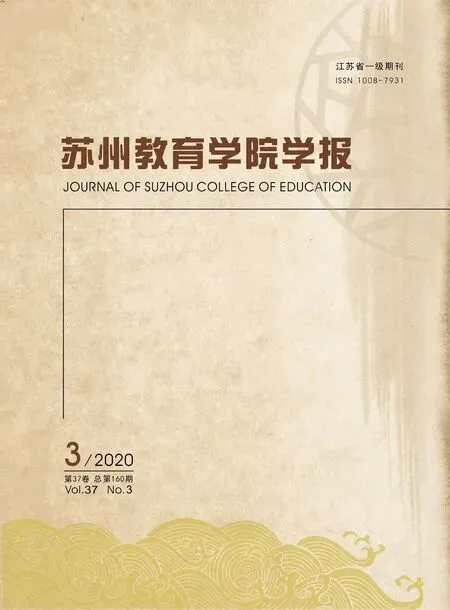略論《讀〈山海經(jīng)〉》與隆安之亂
吳國富
(九江學(xué)院 學(xué)報(bào)編輯部,江西 九江 332000)
一、關(guān)于《讀〈山海經(jīng)〉》意蘊(yùn)的學(xué)術(shù)觀點(diǎn)辨議
陶淵明因讀《穆天子傳》及《山海經(jīng)》而作《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很多人認(rèn)為這組詩的寓意類似于屈原的《遠(yuǎn)游》。清代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卷四借用吳兢《樂府古題要解》的說法,說《讀〈山海經(jīng)〉》類似于曹植等人所作的游仙詩,均源自楚辭《遠(yuǎn)游》篇,也都有“傷人世不永,俗情險(xiǎn)艱,當(dāng)求神仙,翱翔六合之外”[1]的特點(diǎn)。又如李光地《榕村續(xù)語錄》卷二:“《讀〈山海經(jīng)〉》數(shù)章,頗言天外事,蓋托意寓言,屈原《天問》、《遠(yuǎn)游》之類也。”[2]292虞集《胡師遠(yuǎn)詩集序》云:“《離騷》出于幽憤之極,而《遠(yuǎn)游》一篇,欲超乎日月之上,與泰初以為鄰。陶淵明明乎物理,感乎世變,《讀〈山海經(jīng)〉》諸作,略不道人世間事。”[3]128認(rèn)為《讀〈山海經(jīng)〉》與《遠(yuǎn)游》一樣,“頗言天外事”而“略不道人世間事”。既然如此,也就談不上有什么寓意。劉履《選詩補(bǔ)注》卷五:“詞雖幽異離奇,似無深旨耳。”“愚意淵明偶讀《山海經(jīng)》,意以古今志林多載異說,往往不衷于道,聊為詠之,以明存而不論之意,如求其解,則鑿矣。”[4]袁行霈以為劉履此說“最為通達(dá)”[5]398,同時(shí)認(rèn)為“自湯漢解釋《述酒》以來,或以為陶詩多有寓意,《讀〈山海經(jīng)〉》內(nèi)容荒渺,尤易作種種猜測(cè),恐失之穿鑿”[5]398。
細(xì)究之,按湯漢解釋《述酒》的思路去理解《讀〈山海經(jīng)〉》是有問題的,然而說這組詩毫無現(xiàn)實(shí)寓意,也未免過于武斷。就隱喻時(shí)事而言,論者多以為《讀〈山海經(jīng)〉》暗指劉裕篡晉之事。吳崧《論陶》:“此數(shù)首,皆寓篡弒之事。”[2]310蕭統(tǒng)曾說陶詩“語時(shí)事則指而可想”[3]9,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認(rèn)為《讀〈山海經(jīng)〉》頗能體現(xiàn)這一特點(diǎn),如其中“巨猾肆威暴”一首,“蓋比劉裕篡弒之惡也,終亦必亡而已矣”[2]308。王瑤注《陶淵明集》也認(rèn)為這組詩因劉裕弒逆而作,“帝者慎用才”之語就是慨嘆于晉室的滅亡[6]451。
然而與此相左的觀點(diǎn)也很多。逯欽立認(rèn)為《讀〈山海經(jīng)〉》作于義熙四年(408),是年六月,詩人遭遇火災(zāi),旋即徙居南村,《移居》云:“敝廬何必廣,取足蔽床席。”[7]114可知南村居民稠密,房屋狹窄,與《讀〈山海經(jīng)〉》所云“繞屋樹扶疏”“摘我園中蔬”[7]334-335的景象不合,因此可知為義熙四年遇火之前所作。此說頗能反映這組詩創(chuàng)作較早,與劉裕篡晉無關(guān)。袁行霈指出,“巨猾肆威暴”一首,敘述“鼓”與“欽?”因殺“葆江”、“貳負(fù)”與“危”因殺“窫窳”,均遭到了帝王的懲罰,但這兩件事并不涉及篡位,與劉裕篡晉不倫不類[5]397。邱嘉穗《東山草堂陶詩箋》認(rèn)為:“‘夸父’、‘精衛(wèi)’、‘巨猾’、‘放士’四首,皆指切時(shí)事,尤隱然可想。惟末篇辭義未詳,姑闕焉以質(zhì)知者。”[2]292這反過來表明《讀〈山海經(jīng)〉》暗喻劉裕篡晉的觀點(diǎn)難以成立。馬墣《陶詩本義》卷四曰:“此《讀〈山海經(jīng)〉》十三首……慨慷后世之事,而晉、宋之事在其中,并不專言晉、宋也。”[2]310也認(rèn)為《讀〈山海經(jīng)〉》雖有“指切時(shí)事”的特點(diǎn),卻很難用劉裕篡晉來一一坐實(shí)。
論者往往因“忠晉憤宋”的誤導(dǎo)而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境地。如黃文煥《陶詩析義》卷四云:
擔(dān)當(dāng)世事,矢志社稷,有如夸父其人者,功縱不就于生前,亦留于身后矣。精衛(wèi)也,刑天也,是皆有其志者也。嗟夫!世人之不及久矣,但有作惡違帝之欽?而已。……佐惡之奸臣愈多,賢者愈無所容,鴸且日見,而士日放,云如之何!此元亮讀書之血淚次第也。再拈重華之佐堯,賢得舉而惡得退,桓公于仲父臨卒之言,賢不聽舉,惡不聽退,自貽蟲尸之慘,蓋從晉室所由式微之故寄恨于此。[2]288-289
黃文煥對(duì)《讀〈山海經(jīng)〉》后五首主旨的闡述非常準(zhǔn)確,這組詩重點(diǎn)在于揭示“晉室所由式微之故”。然而,黃文煥又說:“愴然于易代之后,有不堪措足之悲焉。”[2]296這等于把前述的分析全部推翻,又落入了“忠晉憤宋”的窠臼。因?yàn)闁|晉的“式微”與東晉的“易代”是兩個(gè)完全不同的概念。“式微”之時(shí),雖然忠奸不分、賢愚顛倒,但皇權(quán)猶在,猶有掌控天下的可能性。“易代”之后,皇權(quán)和東晉的臣子都不存在了。
陶澍注《陶淵明全集》卷四:“晉自王敦、桓溫以至劉裕,共鯀相尋,不聞黜退,魁柄既失,篡弒遂成。此先生所為托言荒渺,姑寄物外之心,而終推本禍原,以致其隱痛也。”[8]125陶澍說《讀〈山海經(jīng)〉》在于“推本禍原”,追溯東晉衰亡的緣由,這是對(duì)的。但他將劉裕與王敦、桓溫并列,同歸于東晉衰亡的緣由,這又是錯(cuò)誤的。因?yàn)橥醵亍⒒笢嘏涯嬷畷r(shí),乃是晉室“魁柄未失”之時(shí),而劉裕篡弒,則發(fā)生于晉室“魁柄既失”之后。王敦、桓溫可以稱為“亂臣賊子”,但劉裕卻只能稱為“竊國大盜”。
總之,黃文煥所論之“愴然于易代之后”、陶澍所論之“劉裕”“篡弒”,乃是受“忠晉憤宋”說誤導(dǎo)的結(jié)果,難以信從。而兩者所論之“晉室所由式微之故”及“推本禍原”則頗為合理,并可以用來闡述《讀〈山海經(jīng)〉》后五首的含義。
二、《讀〈山海經(jīng)〉》后五首的意蘊(yùn)
依據(jù)黃文煥的說法,第九首“夸父誕宏志”[7]346、第十首“精衛(wèi)銜微木”[7]347,重點(diǎn)在于歌詠擔(dān)當(dāng)世事、矢志社稷之人。黃文煥又說:“天下忠臣義士,及身之時(shí),事或有所不能濟(jì),而其志其功足留萬古者,皆夸父之類,非俗人目論所能知也。胸中饒有幽憤。”[2]301又論“精衛(wèi)銜微木”一首云:“被溺而化為飛鳥,仍思填海;被斷而化為無首,仍思爭(zhēng)舞。……死后無裨生前,虛愿難當(dāng)實(shí)事,時(shí)與志相違。……志士之為精衛(wèi)、刑天者,何可勝嘆;懦夫之不知有精衛(wèi)、刑天者,何可勝嗤!想當(dāng)日讀《經(jīng)》時(shí),開卷掩卷,牢騷極矣!”[2]302說這兩首旨在為社稷擔(dān)當(dāng)?shù)闹臼咳嗜锁Q不平,牢騷已極,堪稱精當(dāng)之論。
黃文煥認(rèn)為第十一首“巨猾肆威暴”[7]350旨在指斥“作惡”及“佐惡”之人。這是正確的,但落實(shí)到具體的解釋之時(shí),則未免有曲解之嫌。
據(jù)《山海經(jīng)·西山經(jīng)·鐘山》所敘,鐘山山神之子“曰鼓,其狀如人面而龍身,是與欽?殺葆江于昆侖之陽,帝乃戮之……欽?化為大鶚……見則有大兵;鼓亦化為鵔鳥……見即其邑大旱”[9]37。“欽?”相傳為昆侖山神,一作“欽駓”。黃文煥借助這個(gè)故事把“帝戮之”的意思帶進(jìn)來,與詩中“違帝旨”之語形成對(duì)照,無形中強(qiáng)化了“帝王懲罰惡人”的色彩。《山海經(jīng)·西山經(jīng)》又記載“貳負(fù)”與其臣“危”殺“窫窳”,帝乃“梏之于疏屬之山”[2]307。黃文煥認(rèn)為詩句“窫窳強(qiáng)能變”[7]350所指就是這個(gè)故事,“長(zhǎng)枯固已劇”[7]350即“長(zhǎng)梏固已劇”之意。黃文煥認(rèn)為“窫窳”與“祖江”都是帝王垂憐的對(duì)象,“是欽?、貳負(fù)等均違帝旨,窫窳、祖江均荷帝憐者也”[2]307。基于此,黃文煥說本詩的主旨就是“違帝旨者終為帝所牿戮,庶幾足昭為惡之報(bào)”[2]307。而詩歌最后兩句,又進(jìn)一步強(qiáng)化了“為惡者不可長(zhǎng)久”的主旨—“使被帝戮而長(zhǎng)枯不得復(fù)生,固為罰之劇,即化鵕、鶚,亦豈堪恃乎?”[2]307
事實(shí)上,黃文煥這種解釋是很有問題的。“窫窳”在《山海經(jīng)》中多次出現(xiàn),如《山海經(jīng)·北山經(jīng)》說“窫窳”是一種“其狀如牛,而赤身,人面,馬足”[9]64的食人怪物,而《山海經(jīng)·海內(nèi)南經(jīng)》載:“窫窳”“居弱水中……其狀如龍首,食人。”[9]236郭璞注云:“窫窳,本蛇身人面,為貳負(fù)臣所殺,復(fù)化而成此物也。”[9]239意指“窫窳”原為蛇身人面之天神,被殺之后,復(fù)化而成此“龍首”而“食人”的怪物。黃文煥將“貳負(fù)”與“危”因殺“窫窳”而被“梏之于疏屬之山”當(dāng)作陶詩中“窫窳”的唯一出處,已經(jīng)很不妥當(dāng)。而把這個(gè)食人怪物說成是一個(gè)被冤屈而死的人物,則更是不妥。另外,將“長(zhǎng)枯固已劇”解釋成“長(zhǎng)梏固已劇”,借此突出帝王對(duì)“貳負(fù)”與“危”的懲罰,也近乎于臆斷。因?yàn)樵娭胁]有提到“貳負(fù)”與“危”,而“窫窳”與“長(zhǎng)枯”句又是分開的,把兩者糅合到一個(gè)故事中,并沒有什么根據(jù)。
玩味原詩,“巨猾肆威暴”是詩人重點(diǎn)揭示的問題,“違帝旨”的“欽?”以及“強(qiáng)能變”的“窫窳”應(yīng)當(dāng)都屬于詩人所說的“巨猾”,亦即狡詐多變、大奸大惡之人。“窫窳強(qiáng)能變”應(yīng)當(dāng)綜合了《山海經(jīng)》的幾處記載,意指“窫窳”一會(huì)兒蛇身人面,一會(huì)兒人面馬足,一會(huì)兒又變成龍首,但本質(zhì)上還是個(gè)吃人、害人的怪物。
在此詩中,“祖江”應(yīng)該是唯一一個(gè)用來與“巨猾”對(duì)比的“善人”。張衡《思玄賦》“速燭龍令執(zhí)炬兮,過鐘山而中休。瞰瑤溪之赤岸兮,吊祖江之見劉”[10]可為佐證。但黃文煥反復(fù)強(qiáng)調(diào)帝王對(duì)“巨猾”的懲罰,把“祖江”解釋為帝王垂憐的對(duì)象也是不妥的。原詩之所以要強(qiáng)調(diào)“祖江遂獨(dú)死”,表明“祖江”算是白死了。而“明明上天鑒”[7]350又反映帝王對(duì)“巨猾”無能為力,所以需要借助上天之手來懲罰惡人。最后兩句“長(zhǎng)枯固已劇,鵕鶚豈足恃”[7]350,其意為:善人死了就永遠(yuǎn)枯朽了,實(shí)在值得傷悲!然而那些死后妖魂不散、成精作怪的鵕鶚,也不過逞兇一時(shí)罷了!老天有眼,不會(huì)讓他們長(zhǎng)存的。這兩句更能暗示帝王處于“缺位”狀態(tài),不能懲惡揚(yáng)善。這一點(diǎn)又恰好可以和下一首對(duì)君王用人不當(dāng)?shù)闹赋饴?lián)系起來。
第十二首“鸼鵝見城邑”[7]352,指君王為小人所惑,賢士遭到放逐。寄希望于青鳥,讓它給君王指點(diǎn)迷津,然而這只是一種幻想罷了。論者對(duì)這首詩的意見比較統(tǒng)一,如黃文煥《陶詩析義》卷四:“放士之主,必其迷惑者耳……青鳥不可得,而舉世益多迷人。”[2]308又如陶澍注《靖節(jié)先生集》卷四云:“詩意蓋言屈原被放,由懷王之迷;青丘奇鳥,本為迷者而生。何但見鴟鴸,不見此鳥,遂終迷不悟乎!寄慨無窮。”[8]124
第十三首“巖巖顯朝市”[7]352順接第十二首,旨在提醒帝王應(yīng)當(dāng)區(qū)分賢愚,慎用人才,不可繼續(xù)為小人所惑,否則到了敗亡之際,就噬臍莫及了。陳沆《詩比興箋》卷二云:“末二章,賢士放棄,小人用事,追溯致亂之本也。”[11]這種解說是合理的,與黃文煥所說的“晉室所由式微之故”以及陶澍所說的“推本禍原”一致,揭示了《讀〈山海經(jīng)〉》后五首一以貫之的主題。
總之,《讀〈山海經(jīng)〉》后五首意在感慨仁人志士功敗垂成,大奸大惡橫行一時(shí),君王不分賢愚,導(dǎo)致國事日非,無可救藥。顯而易見,這樣的陳述具有很強(qiáng)的現(xiàn)實(shí)隱喻意義,但用于劉裕篡晉則十分不妥。劉裕掌權(quán)之后,誅殺異己,廣植黨羽,真正忠誠于東晉的臣子已近乎絕跡,哪里還有為東晉而奮發(fā)的仁人志士?復(fù)辟之后的晉安帝以及劉裕所立的晉恭帝,連掌握朝政都已成為一種奢想,哪里還談得上區(qū)分賢愚、黜退小人而提拔賢人?
《讀〈山海經(jīng)〉》后五首影射的只能是晉孝武帝一朝的歷史。淝水之戰(zhàn)以后,東晉王朝本來很有希望蕩平北方敵寇,重新一統(tǒng)天下,但事實(shí)上卻功敗垂成。究其原委,就是君王賢愚不分,任意猜忌排擠賢才英杰,任由大奸大惡在朝中橫行。君王為小人所迷,不但導(dǎo)致國事日非,而且釀成了動(dòng)搖根本的內(nèi)亂,東晉王朝也就病入膏肓、無可救藥了。具體說來,《讀〈山海經(jīng)〉》后五首影射的人物故事,都可以在晉孝武帝時(shí)期找到相應(yīng)的史實(shí)。
1.“巖巖顯朝市”一首,是感慨晉孝武帝一朝的政事。這首詩引用了齊桓公的典故,而晉孝武帝與齊桓公的相似之處很多。齊桓公位列春秋五霸之一,在列國紛爭(zhēng)的情況下表現(xiàn)較為出色。而在五胡十六國與東晉并峙的亂局中,晉孝武帝也算是一位尚可稱道的君主。齊桓公前期任用管仲為相,內(nèi)強(qiáng)國力,外伐諸侯,稱霸天下。管仲去世之后,齊桓公任用易牙、豎刁等小人,變成了一個(gè)昏君,因此引發(fā)內(nèi)亂,自己也饑渴而死。與齊桓公相似,晉孝武帝也是個(gè)明暗參半的君主。在位前期,他重用謝安等賢人,安定內(nèi)部,抵御敵寇,取得了淝水之戰(zhàn)的勝利,收復(fù)了大片失地。然而后來又重用司馬道子等奸佞,排擠功臣,朝政因而敗壞,國勢(shì)一落千丈。在他死后不久,大規(guī)模的內(nèi)亂就爆發(fā)了。
第十三首中的“何以廢共鯀,重華為之來”[7]353,也很像是對(duì)謝安的評(píng)判。東晉前期,內(nèi)有王敦、桓溫之流威逼皇權(quán),外有敵寇不斷侵犯,遍地都是共、鯀之徒。到謝安執(zhí)政時(shí)期,擺脫了內(nèi)憂外患的狀況。這一點(diǎn)類似于舜代堯攝政之后,“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尚書·舜典》)[12]。詩中的“仲父獻(xiàn)誠言,姜公乃見猜”[7]353,也與晉孝武帝猜忌謝安、桓伊一事有關(guān)。《晉書·桓伊傳》記載:謝安因受猜忌而引退,令桓伊深感不平,為此對(duì)孝武帝唱《怨歌》云:“為君既不易,為臣良獨(dú)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反流言。”[13]2119
2.“夸父”“精衛(wèi)”等神話故事,可用于比喻謝安、謝玄、桓沖、朱序這一班名賢。他們都有志于平定敵寇、一統(tǒng)天下,也都建立了赫赫功勛,然而在晉孝武帝的牽掣下,他們最終都沒有實(shí)現(xiàn)自己的遠(yuǎn)大志向,只能赍志以歿,懷恨而終,令人悲嘆,卻也可歌可泣。
3.詩中所云的“巨猾”,包括“欽?”“窫窳”,可認(rèn)為是在影射司馬道子、司馬元顯父子等奸佞。司馬道子起初深得晉孝武帝信任,但他任用王國寶等寵臣,一味專恣弄權(quán),又令晉孝武帝十分不平。中書郎范寧以儒雅方直著稱,力勸晉孝武帝廢黜奸臣王國寶,遭到司馬道子、王國寶的打擊報(bào)復(fù)。晉孝武帝迫于無奈,“流涕出寧為豫章太守”[13]1734。此事即可以用“欽?違帝旨”來形容。司馬道子“既為皇太妃所愛,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shí)失禮敬”[13]1734,令晉孝武帝十分不平。又因博平令聞人奭上疏揭露司馬道子的罪惡,晉孝武帝對(duì)他便益發(fā)厭恨了。但因“逼于太妃,無所廢黜”,“乃出王恭為兗州,殷仲堪為荊州,王珣為仆射,王雅為太子少傅,以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13]1735。晉安帝即位以后,司馬道子“稽首歸政”,卻又把權(quán)柄轉(zhuǎn)移到自己兒子司馬元顯的手上。這父子兩人頗似陰魂不散,被殺之后化為“鵕鶚”的“欽?”,也類似死后“強(qiáng)能變”的“窫窳”,他們相繼弄權(quán),導(dǎo)致朝政徹底朽爛,終于葬送了司馬氏的天下。與此同時(shí),鎮(zhèn)守京口的兗州刺史王恭于隆安元年(397)起兵討伐權(quán)奸,司馬道子為了息事寧人,便將所有責(zé)任推給王國寶,派人將他逮捕賜死。之后司馬道子父子實(shí)施反撲,出兵征討王恭。隆安二年(398),王恭因部下劉牢之倒戈而兵敗,被捕之后處斬于建康。“窫窳強(qiáng)能變”與“祖江遂獨(dú)死”對(duì)舉,應(yīng)該就是隱喻這一事件,前者指司馬道子逃脫了懲罰,后者指王恭因討伐奸佞而死。
三、《感士不遇賦》為《讀〈山海經(jīng)〉》提供的旁證
《讀〈山海經(jīng)〉》與《感士不遇賦》存在很多共同點(diǎn),又有一些細(xì)微的差異。將二者進(jìn)行比較,可以進(jìn)一步確定《讀〈山海經(jīng)〉》所影射的時(shí)事。
1.二者都為仁人志士功敗垂成而悲慟。《感士不遇賦》云:“廣結(jié)發(fā)以從政,不愧賞于萬邑;屈雄志于戚豎,竟尺土之莫及。留誠信于身后,慟眾人之悲泣。”[7]366據(jù)《史記·李將軍列傳》,漢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大將軍衛(wèi)青率兵出征匈奴,李廣為前將軍,本來應(yīng)該作為前鋒,但因衛(wèi)青“陰受上誡,以為李廣老,數(shù)奇,毋令當(dāng)單于”[14]2874,李廣帶領(lǐng)偏師繞行東道。因中途迷路而未及時(shí)到達(dá)。“大將軍與單于接戰(zhàn),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14]2875匈奴遁走,衛(wèi)青勞而無功,便追究李廣延誤軍機(jī)之責(zé),李廣因此憤而自殺。“屈雄志于戚豎”就是指這件事情。然而李廣死后,“天下知與不知,皆為盡哀。彼其忠實(shí)心誠信于士大夫也”[14]2876。“留誠信于身后,慟眾人之悲泣”即指此。《讀〈山海經(jīng)〉》歌詠夸父“余跡寄鄧林,功竟在身后”[7]346,與《感士不遇賦》對(duì)李廣“留誠信于身后”的詠嘆是一致的。
2.二者都認(rèn)為當(dāng)權(quán)者錯(cuò)失良機(jī),導(dǎo)致仁人志士勞而無功。《感士不遇賦》云:“庶進(jìn)德以及時(shí),時(shí)既至而不惠……奚良辰之易傾,胡害勝其乃急。”[7]366《讀〈山海經(jīng)〉》則說:“徒設(shè)在昔心,良辰詎可待。”[7]347仁人志士徒有精衛(wèi)、刑天一般的雄心壯志,卻再等不到“良辰”,亦即錯(cuò)失良機(jī)、“時(shí)既至而不惠”之意。
3.二者都提到宰輔受猜忌的現(xiàn)象。《感士不遇賦》:“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悼賈傅之秀朗,紆遠(yuǎn)轡于促界。悲董相之淵致,屢乘危而幸濟(jì)。感哲人之無偶,淚淋浪以灑袂。”[7]366《讀〈山海經(jīng)〉》則云:“仲父獻(xiàn)誠言,姜公乃見猜。”[7]353很顯然,賈傅、董相、仲父等語都是在影射宰相一類人物受譏謗、受猜忌、受排擠的情況。
4.二者對(duì)奸佞、昏君的描繪也較相似,但有輕重之分。《感士不遇賦》云:“密網(wǎng)裁而魚駭,宏羅制而鳥驚……雷同毀異,物惡其上。妙算者謂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無猜,卒蒙恥以受謗。”[7]366說奸佞對(duì)賢人的讒言太多、迫害太急,但他們尚未達(dá)到大奸大惡、動(dòng)搖國本的程度。到《讀〈山海經(jīng)〉》之中,奸佞就被形容為無惡不作的“巨猾”或顛覆政權(quán)的“共鯀”之徒,直接對(duì)亡國負(fù)責(zé),語意就要重得多。《感士不遇賦》說:“無爰生之晤言,念張季之終蔽。”[7]366君王受小人蒙蔽,不得下情,但還不算特別昏庸。《讀〈山海經(jīng)〉》以迷于奸佞、放縱邪惡以致國亂身死的楚懷王、齊桓公來比喻君王,語意就要重得多。
5.二者都相信天道會(huì)懲惡揚(yáng)善。《感士不遇賦》云:“承前王之清誨,曰天道之無親;澄得一以作鑒,恒輔善而佑仁。”[7]366“澄”為“清”之意,指天。《老子·三十九章》云:“天得一以清。”[15]“鑒”同“監(jiān)”,指老天在監(jiān)視著人世。《詩經(jīng)·大雅·烝民》云:“天監(jiān)有周。”[16]《讀〈山海經(jīng)〉》則云:“明明上天鑒,為惡不可履。”[7]350這與“澄得一以作鑒”意義相同。
綜合起來,《感士不遇賦》與《讀〈山海經(jīng)〉》均有“指切時(shí)事”的特點(diǎn),都抒發(fā)了對(duì)朝政的不滿之情,表達(dá)了士之不遇的感慨。二者的共同點(diǎn)反映它們指向同一朝政,而不同點(diǎn)又反映它們指向同一朝政的不同階段。創(chuàng)作《感士不遇賦》時(shí),建功立業(yè)的時(shí)機(jī)已經(jīng)錯(cuò)失,賢人已被排擠,朝廷已被小人把持,已經(jīng)亂象叢生,但君王尚能維持大局,足以顛覆國家的共、鯀之徒尚未出現(xiàn),讓人感覺到希望尚存。而至《讀〈山海經(jīng)〉》之時(shí),“士之不遇”已變?yōu)椤笆恐^望”,“小人”已成為“肆威暴”的“巨猾”,政權(quán)已在他們的恣意妄為中搖搖欲墜。將這兩個(gè)階段聯(lián)系起來考察,就大大增加了它的確定性。淝水之戰(zhàn)以后不久,謝安等賢人因受猜忌而被排擠,司馬道子開始亂政,東晉名將如桓沖、謝玄、朱序等人的北伐志向遭到挫敗,以致錯(cuò)失良機(jī)、功敗垂成,而禍亂的因素則在不斷積累之中。但此時(shí)晉孝武帝在位,尚能維持大局,還沒有走到極端的地步,這就是《感士不遇賦》的創(chuàng)作背景。到了《讀〈山海經(jīng)〉》之時(shí),晉孝武帝已死,失去制約的司馬道子開始恣意妄為,變成了“巨猾”,而王恭等人屢次發(fā)動(dòng)清君側(cè)的軍事行動(dòng),則又將東晉推向了藩鎮(zhèn)與奸臣大火并的深淵。在《讀〈山海經(jīng)〉》中,“懷王”與“放士”連用,就應(yīng)當(dāng)指楚懷王之死。因?yàn)榍鞣沤现眨簿褪浅淹跎硭绹鴣y之時(shí)。而“臨沒告饑渴”[7]353一句,則明確指齊桓公死于內(nèi)亂。之所以反復(fù)引用君王身死國亂的典故,應(yīng)當(dāng)就是在隱喻晉孝武帝,因?yàn)闀x孝武帝暴崩之日,也就是國家開始大亂之時(shí)。
四、《讀〈山海經(jīng)〉》與歷史事實(shí)的關(guān)聯(lián)
《讀〈山海經(jīng)〉》頗有“感慨時(shí)事”的特點(diǎn)。綜合歷代學(xué)者所論以及上述辨析,這組詩旨在揭示國君昏庸、奸佞當(dāng)?shù)馈⒅伊蓟捋E的政治現(xiàn)象,體現(xiàn)了特別關(guān)注東晉朝政的情懷。為此可以進(jìn)一步考察它與特定史實(shí)的關(guān)聯(lián)性,從另一個(gè)角度來判斷其創(chuàng)作時(shí)間。
1.桓玄敗亡之后,晉安帝反正,劉裕等人掌握了朝政,偶有起兵反叛之人,也很快就被翦滅。站在東晉的立場(chǎng)來看,這一時(shí)期的劉裕功大于過,以“巨猾”形容之并不妥當(dāng),其罪在于誅殺異己,與共、鯀之流的罪行很不相同。此時(shí)政出劉裕等人,晉安帝不過是一個(gè)符號(hào),“欽駓違帝旨”“帝者慎用才”之類的議論也沒有事實(shí)的依托。因此,說這組詩作于彭澤辭官之初或義熙四年前后,是不夠合理、缺乏依據(jù)的。在此之后,劉裕的地位日益穩(wěn)固,篡位之心日益彰顯,東晉名存實(shí)亡,詩人也就不可能站在東晉的角度去感慨士之不遇、抨擊奸邪橫行、提醒帝王慎用人才了,因此《讀〈山海經(jīng)〉》也不會(huì)作于這一時(shí)期。
2.桓玄當(dāng)政之時(shí),不乏正義之舉。他不但誅殺了司馬道子父子,也一度刷新了朝政。若說《讀〈山海經(jīng)〉》作于此時(shí),則“巨猾肆威暴”等語也就失去了所指。桓玄篡位之后,晉祚一度斷絕,站在東晉的角度感慨士之不遇、抨擊奸邪橫行、提醒帝王慎用人才,同樣毫無意義。因此,《讀〈山海經(jīng)〉》不大可能作于桓玄當(dāng)政及篡位時(shí)期。
3.據(jù)《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fēng)于規(guī)林》及《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涂口》等詩,隆安四年(400)、隆安五年(401)陶淵明均在仕途中奔走,生活不夠安定,與《讀〈山海經(jīng)〉》第一首所描述的家居景象不符。尤其是庚子歲(隆安四年)五月中他從京城還家,四月份在家的可能性極小。而《讀〈山海經(jīng)〉》作于孟夏,明顯與庚子歲的情況不符。
根據(jù)上述推斷,《讀〈山海經(jīng)〉》應(yīng)當(dāng)作于隆安四年之前。前面已經(jīng)指出“巨猾肆威暴”暗喻司馬道子父子,“祖江遂獨(dú)死”暗喻王恭之死,因此《讀〈山海經(jīng)〉》應(yīng)當(dāng)作于王恭被殺之后,亦即隆安二年九月以后。《晉書·安帝紀(jì)》:“(隆安二年九月)輔國將軍劉牢之次新亭,使子敬宣擊敗恭,恭奔曲阿長(zhǎng)塘湖,湖尉收送京師,斬之。”[13]251這兩種推斷指向了一個(gè)共同的時(shí)間,亦即隆安三年。因此,《讀〈山海經(jīng)〉》說“孟夏草木長(zhǎng)”,這個(gè)孟夏就應(yīng)當(dāng)是隆安三年四月,也就是這組詩的創(chuàng)作時(shí)間。此時(shí)司馬道子父子因挫敗了王恭等人的“清君側(cè)”并殺了王恭,氣焰更加囂張,而桓玄等人則正在醞釀更大的軍事行動(dòng),矛頭直指司馬道子父子。就在第二年,詩人創(chuàng)作了《庚子歲五月中從都還阻風(fēng)于規(guī)林》,一般認(rèn)為他此時(shí)已經(jīng)作了桓玄的僚佐[6]388。后人對(duì)于陶淵明追隨桓玄的心理動(dòng)機(jī),頗有些不同的看法。
通過上述分析,《讀〈山海經(jīng)〉》反映了詩人對(duì)時(shí)政的鮮明態(tài)度。在詩人看來,當(dāng)時(shí)的執(zhí)政者妄逞“威暴”,殘殺大臣,必將陷國家于危亡之中,為此桓玄在王恭死后繼續(xù)“清君側(cè)”,乃是安定時(shí)局的必要舉措。若有機(jī)會(huì),他還是很樂意為此效力的。然而這種水火不相容的“君子小人之爭(zhēng)”,實(shí)質(zhì)上已經(jīng)將復(fù)雜的派系之爭(zhēng)、權(quán)力之爭(zhēng)裹挾進(jìn)來,從而變成了東晉王朝內(nèi)部的大火并,直接導(dǎo)致了司馬氏政權(quán)的覆滅。從《讀〈山海經(jīng)〉》來看,詩人并沒有清醒地意識(shí)到這一點(diǎn),反映他當(dāng)時(shí)對(duì)王朝政治的認(rèn)識(shí)還不很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