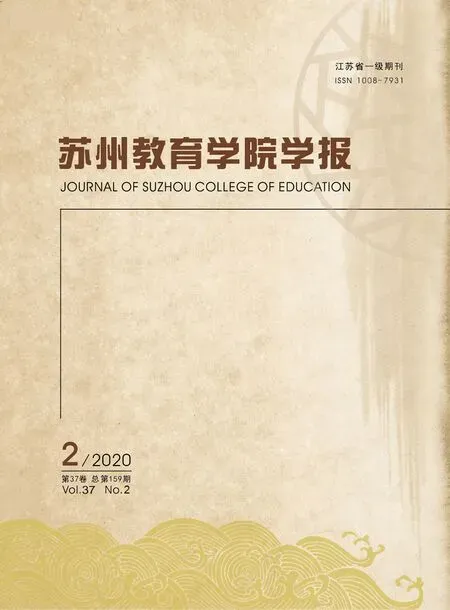明清文人結社的吳江現象
袁美勤,馮月根
(1.蘇州農業職業技術學院 園藝科技學院,江蘇 蘇州 215008;2.蘇州市吳江區政協,江蘇 蘇州 215200)
文人結社是一種特殊的社會組織形式。最早結社的是東晉的“白蓮社”,其社事活動主要與佛教相關。唐宋以降,文人結社漸成交友集會的主要方式,其負載了政治、文化、文學諸種意義。明清是江南文人結社活動最為活躍的時期,地域性的文人結社蔚然成風,文有文社,詩有詩社,遍布江、浙、閩、贛、粵等省的文人社團不可殫數,社盟活動動輒千人,少者數十人,白下、吳中、松陵、淮揚等都是集會之地。結社文人制定社約、聚會創作、編輯刊物、結集出版。而吳江結社之風尤盛,結社之多、參與者之眾、作品之豐、社會影響之大實屬罕見,成為江南社團活動高地,形成了“吳江現象”。
一、明清吳江文人結社的成因與特點
吳江地處太湖之濱、三江之始、江浙滬咽喉之地。境內湖泊水網密布,大運河南北貫穿,所謂“跬步皆溪,非舟莫渡”①倪師孟、沈彤纂:乾隆《吳江縣志》,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地理位置優越,水陸交通便捷,物產豐饒,風物清嘉。明清時期,吳江的農業、手工業、商業尤其是絲綢業發達,商賈云集,是近代資本主義經濟萌芽的地區之一,社會安定富庶、民風淳樸,客觀上為文人結社提供了物質條件和生存土壤。自東晉衣冠南渡,又北宋南遷臨安后,江南人文素養累積深厚,吳江地處蘇杭之間,自古以來即是鐘靈毓秀之地,有范蠡、張翰、顧野王、張志和、陸龜蒙、袁黃等名人賢士,尚文重教之風濃郁。“畸人碩士,彬彬蔚起”②陳去病輯:《笠澤詞征序》,1915年國光書局鉛印本。,到明清之時更是文社密集,文獻繁富,文學發達。尤其是號稱吳江“七大鎮”的松陵、同里、黎里、汾湖、平望、盛澤、震澤,在明清之際,出現了大量世家,如周、徐、袁、葉、沈、朱、蒯、汝、柳、吳、金、潘等大姓望族。這些大家族有著詩禮傳家的傳統,家學淵源深厚,代代熟讀經書,通曉義理,才俊輩出。典型代表如葉葉交輝的汾湖北厙葉家,一門風雅;延續四百多年被譽為“門才之盛”甲于平江的松陵望族沈氏家族等。薛鳳昌《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序》中說:“吾吳江地鐘具區之秀,大雅之才,前后相望,振藻揚芬,已非一日。下逮明清,人文尤富……風雅相繼,著書滿家,紛紛乎蓋極一時之盛。”①薛鳳昌:《吳江文獻保存會書目序》,民國油印本。明清江南文化繁榮,吳江及周邊地區藏書、印刷、出版業的發達也直接推動了文化的興盛與發展。彈丸之地的吳江與江南諸地一樣書香風雅、群星璀璨、大家輩出,成為文人結社唱酬交流的中心,形成一種獨特的文學現象。此外,明清之際“市隱”之風仍然盛行,文人們普遍以隱居讀書自娛為樂,吸引了不少文人雅士歸隱于吳江,不但本地學人仿效,而且游學者眾,如經常往來旅居吳江的袁枚,僅吳江的女弟子就招收13位之多。加上吳根越角的太湖之濱自然風光旖旎秀麗,是文人學子“偃仰嘯歌”的理想居所。明中葉后,文人們一方面圍繞科舉考試切磋學問,研磨時文;另一方面普遍追求自覺、自主的思潮及言論的自由,尤其深受王陽明“學貴得之心”[1]的影響,主張以心得來判斷是非,欲掙脫傳統思想的枷鎖,獲得自由自主的個人思想。再加上繁榮的江南經濟,促進社會各階層頻繁流動,為文人交流唱和、切磋結社提供了機會,成為風雅時尚,各種社團猶如雨后春筍紛紛出現,其社事活躍且輻射江南各府州縣,蔚為壯觀。僅陳去病一人就先后成立了雪恥會、中國教育會、徽州會、杭州秋會、上海神交會、安徽黃社、紹興匡社、蘇州南社、浙江越社等。據不完全統計,明清時期僅吳江地區就有社盟組織23個之多,且風行百數十年。文人學士們不僅結社會友,有的還積極參與政治活動,抨擊時弊,關注民生,甚至議政監督。如復社、慎交社、驚隱詩社、南社等眾多社團,其中皆有吳江人氏為中堅主將或結社領袖,他們帶領正義之士向上抗爭,尋求生存與發展,在全國頗具影響力。明清吳江結社數量、參與者、作品之多,社會影響之大,使其成為江南社團活動的典型,形成了吳江現象。
二、明清吳江文人結社概述與盛況
陳去病在《松陵詩派行》中對吳江文人詩社、文學群體進行了梳理和記述。他在《五石脂》中說到:“據父老傳說,第就松陵下邑論,則垂虹橋畔,歌臺舞榭相望焉,郡城則山塘尤極其盛。畫船燈舫,必于虎丘是萃,而松陵水鄉,士大夫家咸置一舟,每值嘉會,輒鼓棹赴之,瞬息百里,不以風波為苦也。聞復社大集時,四方士子之舟相赴者,動以千計,山塘上下,途為之塞。迨經散會,社中眉目,往往招邀俊侶,經過趙李,或泛扁舟,張樂歡飲。則野芳濱外,斟酌橋邊,酒樽花氣,月色波光,相為掩映,倚闌騁望,儼然驪龍出水晶宮中,吞吐照乘之珠。而飛瓊、王喬,吹瑤笙,擊云傲,憑虛凌云以下集也。”[2]927可見文人結社社事活動盛況。
社友中,有志同道合的,有父子叔侄一門家族的,有夫妻共同參與的,有閨閣士女,還有地方官員,甚至有僧人結盟的,結社蔚然成風。
早在明萬歷年間,盛澤鎮卜夢熊就曾創設綠曉齋社,后由其子舜年(字孟碩,號野水)繼之,“偶相飄聚,動聲四海”②卜舜年:《綠曉齋集》,清道光庚寅年(1830)寶教齋刻本。。
吳江閨閣仕女們也紛紛結社立盟,以“清溪吟社”詩社為典型。《乾嘉吳中女性詩人群體研究》中提到吳江:“十位多才多藝的閨閣女子聚在一起組成詩社,開展了豐富多彩的雅集活動,她們有時以詩相聚,舉行詩酒雅集,有時以歌相聚,相攜彈唱,風雅至極。”[3]
文人結社具有傳承性,竹溪草堂詩社創立人袁景輅,字質中,號樸村,居同里鎮,少有詩才,精于制舉文,屢試不第,詩學源流秉承沈德潛,與顧汝敬、王元文、沈芥舟、陳毓升、沈夢祥、沈培生等共結詩社,后其子袁棠(字甘林,號湘媚)接力竹溪草堂詩社。
還有僧人文士共同結社的,清初吳江僧大持結社,就是一例。乾隆《吳江縣志》卷三十七載:“大持,字圓印,姓沈氏,吳江人。云棲染,受具工詩,又有實印(字慧持)、接待寺僧妙嚴(字端友)、際瞻(字師星)、源際(字曠兼)皆吳江少年僧,結詩社以清新之句相尚。”①倪師孟、沈彤纂:乾隆《吳江縣志》卷三十七《人物十四》,清乾隆十二年(1747)刻本。
學吟社是家庭結社,成立于清嘉慶十六年(1811)秋,同里鎮章家浜金氏家族弟兄父子,此唱彼和。金銳在《其恕齋詩集》中這樣記載:“人生幾何,對酒當歌。不堪卒讀,愁緒頗多。憶昔辛未,一門結社。略識詩書,不盲不啞。弟兄父子,即友即師。此唱彼和,析疑賞奇。佳話韻事,喜能得雨。徹夜長吟,興高鼓掌……”②金銳:《其恕齋詩集》,清乾隆二十二年(1757)刻本。
明清時期,吳江有以下重要的社盟組織及相關人物:
1.復社
復社最早成立于崇禎元年(1628)至崇禎二年(1629)間,地點就在吳江松陵鎮北鄰的尹山土山,由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江南應社等十多個社團聯合組成,乃明末清初全國讀書人集結而成的規模最大的文人集團,其成員多達3000多人。
復社是明末規模最大的政治性文人社團,人員之多、影響之大,為世所罕見。復社創立以興復絕學、切磋學問為旨,發展到后來開始裁量公卿、訾議朝政,社事活動逐漸與時局、政局等發生了聯系。陸世儀《復社紀略》中云:“吳江令楚人熊魚山開元,以文章經術為治,知人下士,慕天如(張溥)名,迎至邑館,巨室吳氏、沈氏諸弟子,俱從之游學。”③陸世儀:《復社紀略》,清光緒戊申年(1908)國學保存會刻本。
復社發起者為吳江孫孟樸、吳扶九以及時任吳江縣令的熊開元等人。當時確立的宗旨是“剝窮而復”④楊鳳苞:《秋室集》卷五,清光緒間湖城義塾刻本。,希望在文風乃至政見上否極泰來。復社不僅僅是一個切磋藝文的文人組織,更是一個學術組織,甚至是一個政黨化組織,他們經常參與社會活動。直至南明弘光政權滅亡,復社才停止活動。眾多學者認為,復社是我國近代政黨的雛形,其歷史地位非同一般。
2.慎交社
清順治六年(1649)吳郡成立“慎交社”。創立者為吳江俊杰吳兆騫(漢槎),及其長兄吳兆寬、次兄吳兆夏。同邑入社者有計東、顧有孝、趙澐等人。當時江南才俊,多有參與,如狀元孫承恩,亦是慎交社人。沈彤、倪師孟纂《震澤縣志》有云:順治十年(1653)在虎丘,組織了盛況空前的結社活動。在虎丘大會上吳兆騫與詩人吳梅村(吳偉業)即席唱和,吳梅村嗟嘆,以為弗及。一時吳下英俊,都以結識吳兆騫為榮。吳梅村更與賓客言:“江左三鳳凰,陽羨有陳生,云間有彭郎,松陵吳兆騫,才若云錦翔。”⑤沈彤、倪師孟纂:《震澤縣志》卷三十八《舊事》,清乾隆十一年(1746)刻本。沈彤《震澤志》云:“慎交社創于郡中,宋既庭實穎主之。而吾邑之在社者,則吳弘人兄弟為之冠也。”⑥同⑤。
陳去病《五石脂》云:“漢槎(吳兆騫)長兄弘人名兆寬,次兄聞夏名兆夏,才望尤夙著,嘗結慎交社于里中。四方名士咸翕然應之。而吳門宋既庭實穎、汪苕文琬,練水侯研德玄泓、記原玄汸、武功檠,西陵陸麗京圻,同邑計改亭東、顧茂倫有孝、趙山子澐,尤為一時之選。”[2]864
3.驚隱詩社
清順治七年(1650),葉繼武、吳宗潛、吳炎、潘檉章等情牽故明,恥事新朝,在吳江唐湖北渚古風莊創立驚隱詩社。該詩社“以故國遺民,絕意仕進,相與遁跡林泉,優游文酒,芒鞋箬笠,時往來于五湖三泖之間”。①凌淦:《松陵文錄》卷十,清同治十三年(1874)刻本。
驚隱詩社又名“逃社”“逃之盟”,成立初始有入社成員48人,來自蘇州、無錫、嘉興、杭州、吳江、湖州、昆山等地,其中吳江就有34人,人數最為集中。顧炎武、歸莊等參加過該社活動。謝國禎在《明末清初的學風》一書中專門論述了顧炎武與驚隱詩社的關系[4]。主盟者為汾湖葉繼武和銅羅嚴墓的吳宗潛。袁景輅《國朝松陵詩征》云:“散人(葉繼武,號帶五散人)當鼎革后,隱居唐湖之古風莊,與吳東籬昆仲結驚隱詩社,社中人皆江浙之高蹈而能文者。”②袁景輅:《國朝松陵詩征》,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愛吟齋刻本。驚隱詩社不是一般意義上的詩社,入社者皆為明朝遺民,他們不單吟詩作賦,更維系著漢家正統文化,激勵后人愛國愛家。
清楊鳳苞《秋室集》述之頗詳:“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為詩社,以抒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其最盛者,東越則甬上,三吳則松陵……松陵為東南舟車之都會,四方雄俊君子之走集,故尤盛于越中。而驚隱詩社又為吳社之冠,汾湖葉桓奏,社中之領袖也。”③楊鳳苞:《秋室集》卷一《書南山草堂遺集后》,清光緒間湖城義塾刻本。
費善慶纂修《垂虹識小錄》記載:“晚明結社之風甚盛,吾邑有驚隱詩社出,四方高蹈能文之士,一時云集。如顧、歸、潘、吳、顧、戴、王、錢等,均以故國遺民,絕意進取,遁跡林泉,優游文酒。社集在唐湖北渚古風莊,頗有煙水竹木之勝,不啻避秦之桃花源也。其后莊史事發,社遂輟。”[5]
驚隱詩社的主要發起人和領袖人物是葉繼武(人皆以“孟嘗君”稱之)和戴笠(字耘野)。沈彤、倪師孟纂《震澤縣志》卷三十八載:太湖葉桓奏,鼎革后隱居唐湖北渚古風莊,與嚴墓東籬兄弟并為驚隱詩社領袖。④沈彤、倪師孟纂:《震澤縣志》卷三十八《舊事》,清乾隆十一年刻本。
驚隱詩社有姓名可考者有48人。除葉繼武、吳宗潛外,還有顧炎武、歸莊、陳濟生(字皇士。顧炎武的二姐夫)、潘檉章(1626—1663,字圣木,一字力田)、吳炎(?—1663,字赤溟)、錢肅潤(字季霖)、戴笠、王錫闡(1628—1682,號曉庵)、王礽(字云頑)、朱明德(字不遠)、朱鶴齡(1608—1683,字長孺)、顧有孝(字茂倫)等人。
因受湖州南潯鎮莊廷鑨《明史》案牽連,骨干潘檉章、吳炎被清廷當局所殺。順治十七年(1660)清廷下令嚴禁士子立盟結社。
吳宗潛也因與閔聲批選唐詩編《嶺云集》牽連下獄,驚隱詩社遭此變故,遂逐漸解散,直至康熙三年(1663),前后長達十五個年頭,江南士人結社之余風由此而絕。極盛百年的吳門人文在康熙年間出現斷裂現象,或者說進入了另一種組合結構,吳、潘之死及“驚隱”解體,實為轉折點。
4.紅梨詩社
清道光十年(1830)春,陳希恕等在盛澤圓明寺附近的西庵創立紅梨詩社,推薦周夢臺(字叔斗)為社長,社員有周夢臺、唐壽萼、馮泰、陳希恕、張寶璇、張沅、仲湘、沈彤、賈敦臨、張寶鐘、史致充、金鐘秀、沈漢金、沈曰壽、沈曰富、沈曰康、陳應元、楊秉桂、翁雒、金作霖、沈煥、楊解、張開福、趙懿、張銜、張鈞、吳山嘉、葉樹枚、蔣寶齡、吳鳴鏘等。當年共舉行雅集14次,并將唱和之作結集《紅梨社詩鈔》一卷,九月刊刻部分,全部詩鈔刊成于道光十一年(1831)初。《靈蘭精舍詩選(合刊)》①陳希恕:《靈蘭精舍詩選(合刊)·卷首》, 民國十一年(1922)鉛印本。卷首記述了蘆墟名流士人如儒醫陳希恕(1790—1850)常趕赴盛澤紅梨社以詩相切磋。陳希恕編輯唱和詩集有多種,如《古鯨琴館倡和集》一卷、《玉臺倡和集》一卷、《木香倡和集》一卷、《餞春倡和集》二卷、《黠夏倡和集》一卷、《詠物倡和集》二卷等。
5.南社
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漸起,在科學與民主思想沖擊下,一批進步青年學子結社團,出刊物,傳播先進思潮,各種社團如雨后春筍般涌現。
南社社名取“操南音,不忘其舊”之意。南社之“南”與陳去病有直接關系。1903年陳去病自日本回國后加入教育會,他的思想發生了一次大轉變,便以文學家的敏感與“南”字結下了親緣,改其字為“巢南”,名其集為《巢南集》。“巢南”本于《古詩十九首·行行重行行》“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之名句,“胡”“越”對峙,與排滿革命的思潮吻合。當時,在中國政治腐敗、列強包圍的危難之下,許多志士仁人為探求救國救亡之路,以提倡民族氣節和推翻封建帝制為使命。繼承明清社盟組織余緒,創設文學社團。宣統元年(1909),同盟會會員陳去病、高旭、柳亞子等在蘇州虎丘張公祠(即張國維祠)發起成立南社。南社以研究文學、提倡氣節為宗旨,弘揚愛國熱情,光大中華民族傳統文化。時有“文有南社,武有黃埔”之盛譽。南社會員遍及大江南北,社員總數達1180余人,是近代中國人數最多、影響力最大的文學社團和文化社團。
必須指出的是,從南社的醞釀、發展、高潮,直至余緒,都有吳江人參與。南社發起者陳去病、柳亞子和高旭三人,吳江人占了二席。吳江籍南社社員冠全國各縣。陳去病是南社成立的主要奠基人,柳亞子是南社的主帥、實際領導者,曾有“沒有柳亞子就沒有南社”的說法。當時吳江的南社社員人數在全國也居第一,達139人之多。
此外,吳江各地還有不少“結社”組織,如光緒二十二年(1896)被稱為“吳江三杰”之一的金松岑在同里鎮創辦自治學社、理化音樂傳習社,以傳授新文化;光緒二十八年(1902),金松岑在家鄉同里鎮創辦同川學堂,翌年應蔡元培之邀赴滬參加中國教育會;光緒三十七年(1911)初,范煙橋與友人在同里鎮結盟的“同南社”,范煙橋在《茶煙歇》里說:“里中(吳江同里鎮)少年負笈四方者,咸賦歸來,乃有讀書之會,其地為袁東籬復齋遺址,雅有林木之勝,在同里之南,故號同南社。主其事者,余與徐稚稚也。自余遷吳下,乃告散歇。”②范煙橋:《茶煙歇》,中孚書局民國二十三年(1934)版。社員有范煙橋、徐稚稚、張錫佩、徐麟、薛元琪、金祖榮、嚴琳、沈雷漁等。
如火如荼的江南社事,使清廷預感到可能對其政局安全帶來潛在隱患。順治九年(1652)、順治十七年,清政府兩次下令禁社。順治十七年正月,給事中楊雍建上疏:“今之妄立社名,糾集盟誓者,所在多有。而江南之蘇、江、浙之杭、嘉、湖為尤甚。其始由于好名其后因之植黨。”并建議:“不得妄立社名,其投刺往來,亦不許用同社、同盟字樣,違者治罪。”①陳希恕:《靈蘭精舍詩選(合刊)·卷首》, 民國十一年(1922)鉛印本。朝廷采納疏言,嚴行禁止。順治十八年(1661),又有奏銷案,使各地社事活動大受影響。
三、明清吳江文人結社的作用與影響
明清吳江文人結社遺風一直延續至民國時期,如“吳江求是學社”“新南社”“星社”等眾多社團。當然也有諸多吳江士子積極參與嘉興、湖州(南潯)、松江、吳中等周邊地區的社團組織,還客游外省各地,與當地社團交友論文,如計東在河南中州與雪苑社徐作肅、陳宗石、侯輔之等研討詩文,陳去病在上海組織神交社等。
縱觀明清文人結社的吳江現象,其結社之盛,聲名之大,影響之深廣,絕不是偶然的。如火如荼的結社形象地折射出當時的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自然生態和人文環境狀況。一方面明清吳江世運升平,物力豐裕,優渥的自然環境和雄厚的經濟基礎、相對穩定的社會環境和良好的文化生態,催生文人結社茁壯成長;另一方面,吳江文社興盛、文化發達也反映了地方的政治地位、經濟發展和文化風尚。聲望人士結社招集,參與者競文采風流,繪就文人結社圖,并出版社約、社刊、社圖。上至士大夫下至“田野小民,皆知以教子孫讀書為事”[6]62,以至于有“民生期間,多秀而敏”之說、“布藝韋帶之士,皆能摛章染墨”[6]63之譽。在文化上,文人結社活躍了吳江的文壇,擴大了文化交流,促進了文化教育發展,推動文人結社向外拓展,提高了吳江文人的影響力、知名度。文人們以各種社團為活動平臺,走出書齋,結社為盟,熏陶漸染,文章振動,創作大量文學作品。他們精研詩、詞、書、畫、曲、律等,風雅相繼,極大地促進了詩、詞、歌、賦甚至曲、律、志、史等創作的繁榮,給后世留下了豐富多彩的文化產品和寶貴的精神文化遺產,至今仍然滋養著后生后學。明清吳江文人結社活動,由詩酒唱和、怡然自娛,到憂國憂民、干預朝政,表明了文人志士的政治抱負和鮮明的政治傾向。他們飽讀詩書,經世致用,躬行實踐,重視文學的社會作用,抵制專制統治,伸張社會正義,反抗民族壓迫以及倡導政治改革的主張,他們普遍要求通過文學闡揚“國魂”,激發群眾的愛種保國之念,反對清朝政府的專制統治,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服務。總之,明清吳江文人結社,“欲一洗前代結社之弊,作海內文學之導師”②高旭:《南社啟》,《民吁報》1909 年10 月17 日。,吸引了眾多有識之士,“誠欲考往哲之遺風,續枌榆之盛業”[7],他們跌宕于詞場酒海間,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為后人留下了豐富的精神遺產,在我國文學史、文化史、社會史乃至革命史上都作出了貢獻,也是吳江的驕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