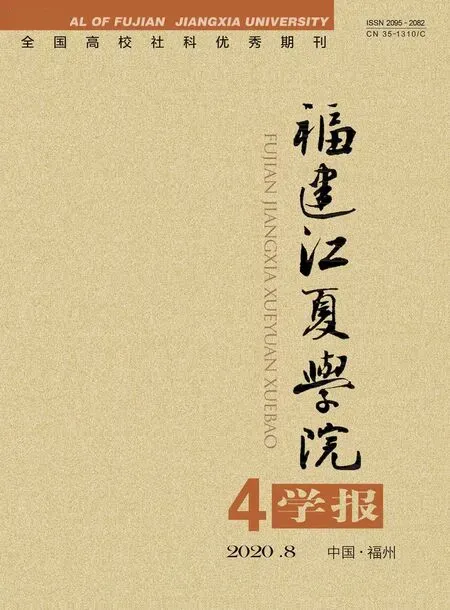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與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學”
龔曰心
(龐培·法布拉大學,西班牙巴塞羅那,08005)
1827年,已過古稀之年的德國文豪歌德(Johann Wolfgang Goethe)首次前瞻性地預見了世界文學的興起:“民族文學在現代算不了很大的一回事,世界文學的時代已快來臨了。現在每個人都應該出力促使它早日來臨。”[1]a歌德并非第一個提出“世界文學”這一概念的人。在他之前,August Ludwig von Schl?zer 于1773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用了這一術語,Christoph Martin Wieland也在他翻譯的賀拉斯的信件的過程中,用“世界文學”來形容這位古羅馬著名詩人所處時代的文學。歌德盡管多次提及“世界文學”,但并沒有給出一個明確的定義,只是促進了比較文學作為一門學科的發展。當時世界文學只是比較文學中的一個分支。直到20世紀末、21世紀初,才真正出現了關于世界文學的理論發展,比如本文提及的兩位學者及其專著。現在,隨著經濟全球化和政治全球化的推進,歌德這一神奇的想法已成現實,但學界對“世界文學”的定義一直都存在爭論。
漢學家蘇源熙(Haun Saussy)曾說:“由于存在許多種民族或者地方的角度,就有許多種世界文學”。[2]隨著人類文學意識的不斷覺醒,越來越多的學者開始全面地考慮何謂“世界文學”,在下定義時將歷史語境和文學語境都納入它的所指之中。其中,法國學者帕斯卡爾·卡薩諾瓦(Pascale Casanova)的《文學世界共和國》(The World Republic of Letters)和美國學者大衛·丹穆若什(David Damrosch)的《什么是世界文學?》(What Is World Literature?)自問世起就掀起了一陣又一陣的討論熱潮,彰顯了歐美兩塊大陸對于世界文學的共同關注。
一、研究綜述
一直以來,圍繞世界文學這一概念,外國學者有許多有意義的討論。以“世界文學”這個概念為整體,西班牙皇家語言學院院士、哈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克勞迪奧·紀廉(Claudio Guillén)在他1983年的著作《在一個與另一個之間:比較文學導論》(Entre lo uno y lo diverso: introducción a la literatura comparada)中,總結了學界內普遍存在的三種理解:指世界各國的文學作品的總集,指各國跨越國境線而在世界范圍內有一定影響的文學作品,或者是指經過國際化的標準選擇后的一流作家和作品。[3]
本文比較的兩本理論專著,引起了各國學者的激烈討論,自其出版起,至今綿延不絕。此處梳理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和批評。
在西方學界,比利時魯汶大學的西奧·德漢教授(Theo D′haen)的專著《世界文學簡史》(The Routledge Concise History of World Literature),總結了“世界文學”這一概念生成與發展的歷史。其中第五章將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共和國”與弗朗哥·莫萊蒂(Franco Moretti)關于世界文學的理論并置,將二者劃歸為把世界文學作為一種系統的理論典范,但在其著作中,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學”只是一種對歌德理想化期許的回應,認為其著眼點回到了文學作品的閱讀與流通,故尚不成為一種被單獨討論的文學理論,此種態度或可稱其為對丹穆若什理論的一種批評。[4]同樣的,卡薩諾瓦的主張也受到世界各國學者的批評。華盛頓大學圣路易斯分校的伊格納西奧·桑切斯·普拉多(Ignacio Sánchez Prado)編纂的論文集《“世界文學”中的拉丁美洲》(América Latina en la “literatura mundial”),圍繞著卡薩諾瓦與莫雷蒂的文學理論,收集了許多相關的批評與討論。其中對卡薩諾瓦的批評,集中于她在論證過程中對市場因素的忽略,也即不贊成她對文學世界共和國的獨立性的過分強調,同時其以巴黎為中心的單一視野,也遭到了其他學者的批評。[5]
在國內學界,對于相關理論的討論略顯匱乏,盡管早在20世紀80年代,我國學者就已經引入了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的概念,但圍繞本文重點關注的兩部著作,相關討論的產生卻有一些延遲。李滟波對丹穆若什著作的內容進行了概括,肯定其在全球化語境下,對“世界文學”做了詳實而有理有據的論述,但認為其不足之處在于將所有跨文化流通的作品視為世界文學,此概念過于寬泛。[6]周啟超對卡薩諾瓦的理論和其他各種世界文學理論作簡要的分析與比對。[7]劉巖闡釋了文學世界共和國的建構因素,著重展示文學場域、文學資本、語言、翻譯和神圣化資助人在構建此文學空間中的作用,同時指出卡薩諾瓦的缺點是忽略中國文學的獨特生命力,將其置于次要位置。[8]高方在厘清該文學空間的生發機制后,將卡薩諾瓦對于翻譯的論述延伸到中法文學空間中,認為依靠翻譯活動完成的兩國文化交流其實是不平等的,應從中受到啟迪,思考如何解決交流過程中的誤解與無知。[9]
因此,從現有文獻來看,國內外學者對世界文學的討論中,鮮有將卡薩諾瓦與丹穆若什的理論相對比的研究。雖然在中文翻譯中,“文學世界”與“世界文學”表面看來只是語序的差異,但是這兩部專著在討論世界文學時,有著完全不同的切入點,由此也形成了不同的所指。因此,本文將對這兩種對于世界文學的生成及發展機制的理論進行比較,尋找兩者的共同點和差異性,探討兩種理論中值得商榷的地方,尋求對理論的深入理解與合理借鑒,幫助我們完善對于“世界文學”這一概念的認知。
二、《文學世界共和國》:從文學社會學角度建立的獨立文學空間
帕斯卡爾·卡薩諾瓦師從法國著名社會學家、批評家皮埃爾·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布迪厄的場域理論,特別是文學場理論,在各民族文學研究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而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共和國》實際上對國際文學場進行了細致的考察,是場域理論在世界文學理論方面的成功應用。卡薩諾瓦在1997年的博士論文《國際文學場域》的基礎上完成了專著《文學世界共和國》于1999年出版,一經問世就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討論,被翻譯為包括英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在內的多種語言,為作者帶來了國際性聲譽。
卡薩諾瓦嘗試厘清世界文學的概念,認為全世界范圍內的文學作品共同構成一個動態的整體。其中各個環節相互影響,這個動態的整體即為“文學世界共和國”。即,從文學社會學角度建立的一個獨立文學空間。依據布迪厄的的場域理論,每個文化場都有其相對獨立性,但也受到來自權利場(國家政治)和其他場域的影響。國際文學場也同民族文學場一樣,受到權利場影響的同時,保持著相對的自治與獨立運作。各民族文學在這個國際文學場域內有其一席之地,占據著文學共和國的“中心”和“邊緣”,或者說“首都”和“外省”。
獨立的文學空間,其文學世界的“地圖”不會與經濟或政治版圖相吻合,經濟上的強大并不一定導致文學上的領先。我們可以通過英、法、美三國文學的互相角力來驗證。從宏觀上來說,法語自17世紀起,長時間地被認為是一種優越的文學語言,巴黎也自然而然地長期占據著文學共和國“首都”的位置,但18世紀末起,隨著英國的經濟發展,英國文學嘗試挑戰法國文學的絕對主導地位,但沒有成功;19世紀末、20世紀初,經濟強盛的紐約也加入到這場競爭中來,當紐約已經被賦予世界經濟中心的榮光時,世界范圍內的人民卻并不贊同它在文學世界的中心地位。[10]135-136
文學世界的相對獨立性表現為各民族文學間的競爭,成為文學世界共和國發展的動力。文學世界的等級地位并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時間的變化而發展,原先在邊緣位置的民族文學,可以通過斗爭和努力,獲取地位的提升,從而改變文學世界共和國內的格局。顯然,被統治的民族文學通常企圖突破現狀得到認可,而處在統治地位的民族文學則試圖繼續鞏固其施行祝圣的權利。換言之,文學世界共和國并非一個完全自由的空間;雖然世界文學空間已經一定程度上擺脫了意識形態、民族主義等非文學因素的干預,但它仍舊不是一個絕對公平的場域。[11]
可見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建立在各民族文學間的不平等之上,而這種不平等源于語言本身的不平等,以及由此導致的文學史的不平等。文學相對于民族的依附性是原初文學世界不平等的原因。與歌德將世界文學理解為各民族文學的平等對話不同,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其實是一個帶有較強殖民色彩的概念。雖然語言學和文學是不同的學科,但實際上文學的問題直接關系到語言的問題。由于某些民族語言擁有更多的經典性作品,這些語言會自然而然地被公認為是更具有文學性的語言,由此從語言世界跳躍至文學世界,產生了民族文學間的不平等結構。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源于歐洲,在歐洲語言中,法語最早實現了它的反抗與解放,跳脫成一種具有文學性的語言。如,16世紀時,在杜貝萊《保衛和發揚法蘭西語言》的帶動下,法語克服了“語言奴隸制”,代替拉丁語成為了重要的文學語言,巴黎也由此成為文學世界之都。可以說,語言本身的不平等導致了民族文學的不平等,而文學世界的不平等結構形成了一種誕生出階層和暴力的文學經濟,這種“精神經濟”表現為文學信仰以不平等的方式在國際文學空間流通,由此推動著“共和國”的發展與流變。也就是說,在這個不平等、充滿競爭和博弈的空間內,各個文學通過不同的策略,企圖躋身世界文學之列,獲得文學的正當性。
不過,在解釋民族文學獲得正當性的途徑之前,卡薩諾瓦先論證了巴黎作為世界文學之都的正當性。卡薩諾瓦認為杜貝萊保衛本國語言的倡議一方面奠定了世界文學空間的基礎,另一方面奠定了巴黎的中心地位。“他引起的國際競爭標志著全球文學空間統一進程的開啟”。[10]58在法語之后,其他歐洲通俗語言也開始了推翻拉丁語壟斷的進程。16世紀起,文學成為一種斗爭的工具,民族文學的輪廓逐漸清晰,各民族文學參與到國際文學空間的競爭中去,在這一聚合過程的推動下,文學世界共和國誕生了。在七星詩社和法國國王等大力推廣下,法語在歐洲推翻了拉丁語的統治,引領了民族文學的碰撞與交流,卡薩諾瓦也提到各國文人對巴黎的膜拜,企圖證明巴黎影響了許多世界性作家的創作,是“文學首都”。
事實上,卡薩諾瓦很強調這一點。其專著的第一部分解釋了文學世界的運行機制后,第二部分致力于總結民族文學由“邊緣”走向“中心”、獲得正當性的策略。大致可以分為兩種:同化,通過淡化或否定原初差異,這是對不擁有任何民族自由的人而言的首選之路,即“背叛”民族文學事業;異化,譴責模仿,制造差異,進而獲得其他民族的肯定。[10]241雖然前者相對后者而言,是捷徑一般的選擇,但如果異化得到大面積肯定,其在世界范圍內造成的影響力將超過簡單的抹殺原初差異。比如,拉丁美洲文學,直到19世紀40年代前,都以模仿歐洲文學為主,而60年代興起的“魔幻現實主義”打上了只屬于拉丁美洲的烙印,這種區別于歐美主流作家作品的藝術風格,為這塊原本遠離中心的大陸,積累了特殊的文學資本。當我們今天提到拉美文學時,不會再有人把它當作世界文學空間里的“第三世界”,盡管它在經濟、政治世界中仍然不處于中心位置。
可見,對卡薩諾瓦來說,文學世界除了相對獨立性和內部的持續競爭的特點之外,另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源于歐洲,且巴黎占據絕對中心位置。這一點恰恰令人質疑:為什么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源于歐洲?為什么沒有論證將歐洲作為文學世界起源的合理性?換言之,卡薩諾瓦的視野是單一的,她構建的文學世界是一個以歐洲文學為基點的文學空間,東方文學被出于慣性般地置于次要位置。因此,《文學世界共和國》不可避免地帶上了殖民色彩,畢竟當歐洲各民族文學競爭、文學世界生發之際,歐洲之外的民族文學也在不斷發展,其他歷史悠久的民族文學也擁有廣泛的輻射范圍和強大的影響力,比如中國文學。但由于卡薩諾瓦的身份背景,這些文學在歐洲中心論的文學世界中,成為了后來者。
卡薩諾瓦的理論的不足是顯而易見的。后來者多批評卡薩諾瓦的理論帶有明顯的殖民主義色彩,雖然她本人也注意到了文學世界的形成與殖民關系的緊密聯系。在她的設想中,世界文學空間的起源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形成初期,也即上文提到的《保衛和發揚法蘭西語言》的誕生時期;第二階段是版圖的擴大階段,從18世紀末持續到19世紀初,伴隨著“詞典學革命”;最后是去殖民化階段,“標志著世界競爭中出現了一直被排除在文學概念本身之外的主角們”,比如來自第三世界的拉丁美洲文學。[10]49-50但這不能為他的殖民化正名。這里還可以拉美文學的發展作一管窺。歷史上,拉美文學曾經兩次撼動西方,第一次是20世紀初魯本·達里奧(Rubén Darío)引領的現代主義詩歌潮流,第二次則是60世紀60年代著名的“文學爆炸”。如果說,前者還有“借助于引進巴黎輸出的文學現代性方式”[10]107,后者的輝煌卻實在不能證明巴黎的“首都”地位。“文學爆炸”的代表作家,如加西亞·馬爾克斯(García Márquez)、巴爾加斯·略薩 (Vargas Llosa)等,主要是受到英語文學,特別是北美文學的啟迪[12],福克納和海明威是他們的創作老師。要說來自歐洲的影響,首先也來自德語作家卡夫卡。另一方面,“文學爆炸”的產生,很大程度上要感謝巴塞羅那的中轉作用。這座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城市,由于天然的語言優勢,在拉美文學走向世界的過程中占據了重要地位。巴爾加斯·略薩的處女作《城市與狗》(La ciudad y los perros),在被歐洲眾多出版社拒絕后,最終被巴塞羅那的編輯卡洛斯·巴拉爾(Carlos Barral)發現,由此開始,他那尚且名不見經傳的出版社Seix Barral,成了拉美文學的大本營。而文學代理人卡門·巴爾塞斯(Carmen Barcells)則為加西亞·馬爾克斯打開了巴塞羅那之門。[12]不止一位文學評論家認為,如果一部秘魯的文學作品,想要傳播到布宜諾斯艾利斯,通過巴塞羅那要比通過秘魯首都利馬來得快。[13-14]總之,在拉美文學20世紀60年代創造的這次成功的異化中,我們看不到巴黎的身影,取而代之的則是巴塞羅那。因此Constanza Ternicier批評卡薩諾瓦,認為她看似承認國際文學場內的競爭與變化,但她的論證實際上是由巴黎中心論出發的,由是構造了一個看似穩定的文學世界,視野不可避免地顯得狹隘了。[12]
三、《什么是世界文學?》:全球化語境下的一種流通和閱讀的模式
美國比較文學協會主席、哈佛大學教授大衛·丹穆若什是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領域的另一位明星人物,他2003年出版的《什么是世界文學?》試圖在全球化語境下對世界文學做一個全面、全新的闡釋。這部著作在學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與《文學世界共和國》一樣,該書于201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翻譯成中文。
丹穆若什從“世界文學”廣為人知的起源講起——歌德的預言,開宗明義地表示:“世界文學不是一個無邊無際、讓人無從把握的經典系列,而是一種流通和閱讀的模式,這個模式既適用于單獨的作品,也適用于物質實體,可同樣服務于經典名著與新發現的作品的閱讀”。[15]6接下來,本書從流通、翻譯、生產三個方面論證了這一模式,最后總結:世界文學是民族文學間的橢圓形折射;世界文學是從翻譯中獲益的文學;與我們自身空間不同的世界的形式。[16]
世界文學應當是包含一切在其原本文化之外流傳的文學作品。它們或者通過翻譯、或者通過原語言,跨越國境線,進入民族文學范圍之外的流通,獲得作為世界文學的生命力,且通常表現為三種基本模式:經典的作品、杰出的作品、觀察世界的窗口。[15]18
在此情況下,該書第一部分討論了作為一種“流通”模式的世界文學。成為世界文學需要滿足兩個基本條件:被當作文學作品閱讀,進入跨文化的語境中。[15]7第一章中,《吉爾伽美什》從廢墟中的歷史遺產變為古巴比倫民族史詩,展示了語言文字變成文學作品的過程:由于它包含的史料可以確認《圣經》中許多事件的背景,在流通的過程中其文學價值漸漸得到肯定。[15]45-86再比如,第三章考察了世界文學選集的變遷,揭示了“跨文化”內涵的不斷擴充與完善。作者認為在過去的半個世紀中,世界文學約等于約定俗成的歐美文學經典,于是他指出了幾種通用的世界文學選集存在的缺陷:或缺少女性作家,或缺少非歐美地區的作家,它們已經不能適應全球化的趨勢。[15]146新的世界文學選集具備了更全面的視野,將亞非作家、女性作家都囊括其中。這說明在文學流通十分發達的今天,世界文學是一個對各民族文學開放的總集合。
對丹穆若什來說,跨民族流通是當前世界文學最基本的特質,但有必要指出的是,強調文學作品的流通并不會限定世界文學本身的多樣性。本書的最后一章題為“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就證明作者意識到,有限的論述不可能在無限時間和空間內一直有效,也就是說,丹穆若什和卡薩諾瓦一樣,都肯定世界文學是一個動態的概念,其所指隨著時間的流變而發展,但是前者強調文學作品的跨文化傳播,后者強調文學空間內中心與邊緣之間的持續競爭。
接下來在第二部分中,丹穆若什討論了翻譯為世界文學帶來的收益。他認為,翻譯是民族文學成為世界文學的有效途徑之一,有效地幫助文學作品跨越種族界限。如果作品能從翻譯中獲益,則能成為世界文學,這種獲益是宏觀的,不同于文本層面信息傳遞的成功與缺失。比如,麥赫蒂爾德·馮·馬格德堡(Mechthild von Magdeburg)13世紀用地方德語創作的散文《一縷上帝的流動之光》(The Flowing Light of Divinity),把對基督的熱切渴望比作是炙熱的、對肉體的愛。在被翻譯為拉丁語時,過去的譯者(同時是一位神父)弱化了其中的情色成分。直到20世紀,當代譯者才敢直面這種熱烈的文字,但由于原作不易考證,當代譯者也只能在被改動過的版本基礎上,反過來推敲馬格德堡的語言。[15]190-208從翻譯學角度看,這樣的譯作會與原文有明顯的出入,但宏觀來看,在文化交流中更可貴的品質是對譯者特有文學風格的恢復,因為它豐富了世界文學的殿堂。再比如卡夫卡(Franz Kafka)的《城堡》(The Castle)。1926年卡夫卡友人整理出版的《城堡》與作者手稿有較大出入;1982年,德國菲舍爾出版社推出的版本才努力保留了作者特有的書寫方式。[15]209-230卡夫卡本身的語言與傳統美學大相徑庭,如果翻譯時注重優美、流暢,反會產生與原文不相符的審美效果。對卡夫卡作品譯本的修訂,使他擺脫簡單地被規劃到他國文化的命運。同時,這也說明即使是獲得經典地位的作家,有時在世界文學中也需要重新定位,更何況那些初露鋒芒的新興作家。
丹穆若什的著作第三部分分析了作品進入世界文學的途徑以及文本在生產過程中涉及的復雜因素,以麗格伯塔·門楚(Rigoberta Menchú)的個人自述《我,麗格伯塔·門楚》(I, Rigoberta Menchú)和米洛拉德·帕維奇(Milorad Pavi?)的《哈扎爾辭典》(Dictionary of the Khazars: A Lexicon Novel)為考察對象。比如,前者常常被粗暴地理解為是當事人的自傳,是為了提醒門楚爭取印第安人權利與和平的努力。但實際上在出版、傳播和翻譯的過程中,它已經成為了多人“創作”的結晶,出版商和書商的各種努力為的是吸引注意,而非闡述事實。[15]256-286這是文學作品被跨國團隊操縱的結果之一——受到市場閱讀興趣的影響,作品內容發生了變異。這說明丹穆若什也注意到非文學因素也在深刻影響著世界文學的構建,國際化的文學世界與政治、經濟世界相交織,但由于缺少文學社會學的方法論,其討論傾向于“見微知著”,明顯有別于卡薩諾瓦宏觀的歸納與總結。
對丹穆若什來說,當前世界文學指的是作品傳播到其他民族文化中并被閱讀的一系列過程,因此它的關鍵是需要一種有效的閱讀方式。由于文學作品源自不同的國家和民族,為了盡可能地理解這些作品,讀者應該去了解它們本來的歷史、文化語境,這樣才能促成跨語言、跨民族的文化交流。反之,如果閱讀之前缺少對原語文化的了解,而把本國文化或已知的他國文化強加于作品之上,這將大大影響閱讀的有效性,曲解作品的內涵。一般來說,有兩種途徑形成適應世界文學的閱讀能力:通過對大量作品的泛讀,或對部分作品的精讀。這一論述可用一個案例來反向論證:張巖、梁耀丹和何珊考察了5位獲得國際文學獎的中國作家在海外傳播與接受的情況,通過海外讀者對這些作品的評價,發現“獲得國際大獎對中國作家提升國際影響力起到重要的作用,但外國讀者仍然對中國文學作品有相當程度上的閱讀和理解困境”。[17]換言之,有意義的世界文學的形成,最終還是仰賴合理的閱讀方式,依靠足夠的跨文化素養,而最表面、最不文學的國際文學獎項,只能暫時地推動文學作品完成跨越國界線的傳播,無法真正打破文化壁壘。
丹穆若什的一系列論證彰顯了全球化語境下,在作品、作者和讀者的互動關系中,人類文學意識的全面覺醒,一定程度上消除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學者因為研究對象的無限性和不著邊際性而引發的焦慮。[6]他為我們厘清了“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關系。通常,比較文學被看作是世界文學的有機組成部分,這種觀點顯然又一次把世界文學作為了一個總集合。比較文學應該是世界文學的方法論,旨在研究世界文學中的共同現象和復雜關系,尋找一種普遍的規律,這樣比較文學才不會流于表面,而能確保其研究具有真正的價值。
不過,這部專著也有明顯的不足。區別于卡薩諾瓦的殖民色彩,《什么是世界文學?》有著嚴重的“為世界而世界”的傾向,為了避免傳統的歐美為中心,丹穆若什特地用了很多不廣為人知的案例作為研究對象,甚至在其中完全找不到美國文學的蹤跡,這與卡薩諾瓦對巴黎以及法國的無上推崇形成了有趣的對比。由于企圖擴大世界文學的版圖,本書涉及的作品、作者、時間和地域跨度都讓人驚嘆:上至巴比倫的楔形文字殘片、阿茲特克人的傳統歌謠,下及危地馬拉婦女的自述、帶毒之書的跨文化閱讀。雖然可以肯定,他的研究對象都是一定語境下的“世界文學”(換言之,未必一定是中文語境下的世界文學),但這增加了閱讀的難度,也含有一定的刻意性。當然,這部作品總體來說瑕不掩瑜,仍舊是世界文學領域富有啟迪性的里程碑之作。
四、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的碰撞與對比
本文選取的兩部作品,代表兩種比較文學研究風格的大陸:法國的卡薩諾瓦與美國的丹穆若什,構成了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的對照。雖然嚴格說來,二位學者意欲辯明的是世界文學,但作為一對“孿生姐妹”,或者說,比較文學作為世界文學的方法論,我們有理由就此追溯兩個學派的歷史,來看這兩派由對立到融合的歷史與現在。
在我國,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的對立與分歧并非比較文學領域的新話題。早在1981年,王堅良與徐振遠就撰文《比較文學: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梳理了該學科在國外的歷史淵源和當前發展。作為傳統世界的中心、比較文學的誕生地法國似乎自然而然地孕育出一種學究氣的研究風格,主張實證和考據,研究范圍局限在文學內部的互相影響,這種“影響研究”(influence study)不把其他文化活動納入考察比較的范疇。[18]法國學者們嚴謹治學的態度,為比較文學奠定了穩固的基礎,使之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但與此同時,法國學派狹隘的研究對象和嚴苛的研究方法,遭到了大洋彼岸美國學者的鄙夷。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展,美國學派發展出一套自己的理論,與法國學派分庭抗禮,用“平行研究”(parallel study)開拓了比較文學的疆域。他們“強調比較文學應該關注沒有事實聯系的不同國家或民族的文學之間的美學價值關系”。[19]換言之,美國學派認為藝術是一個整體,而文學是其中一種形式,它應當被放置于更大的文化環境中,唯有如此,才能保留藝術的完整性,獲得比較文學研究真正的意義。
有必要指出一個“中國特色”的歷史遺留問題:“平行研究”概念的起源。如前所述,“平行研究”一般被視作是美國學派的標志性方法,指對沒有事實聯系的文學現象的比較研究(比如將《紅樓夢》與《百年孤獨》相對比),以及新興的跨學科研究。然而,目前有據可考的“平行研究”的最早出處,是古添洪和陳慧樺(陳鵬翔)的《比較文學的墾拓在臺灣·序》(東大圖書公司,1976),其中說道:“(美國派)提倡諸國間文學的平行研究,探索其類同與相異”。[20]這個20世紀70年代出現在臺灣的一家之言,在比較文學蓬勃生長的時期,被拿來作為簡化這門學科的工具,把美國學派塑造成法國學派的對立面,并用“平行研究”來概括美國學派的方法論。1980年,大陸首次引入這個臺灣制造的概念,在《是該設立比較文學學科的時候了》中,趙毅衡說“美國學派認為在任何有可比性的問題上都可展開研究,所以強調無影響接觸實證的‘平行研究’(parallel study)”。[21]漸漸地,大陸學界在20世紀80年代初“比較文學大家談”運動中,復刻了70年代中期臺灣建立比較文學學科時的那種概念簡化,“平行研究”一詞逐漸被傳播和接受,成為一種共同的認知,一種學科常識。很難相信,這個用來概括美國學派方法論的概念,并非源自雷馬克或者其他任何美國學者,而是一個比較文學中國化的產物。
讓我們回到法國學派與美國學派的對立關系上來。事實上,這兩個學派雖有分野,但并非水火不容。對峙之初,兩派都贊同的是“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是跨越國境線的文學”[18]。隨著學科的發展,每一派都很難故步自封,為了維持學科的活躍性,必須選擇“走出去”。于是,20世紀80年代,兩派的針鋒相對基本結束:法國學派開始把美學議題納入比較文學范疇,甚至提出比較文學向東方的轉向;美國學派則意識到實證的重要性,在其研究中重視有嚴謹考據的文學史。[18]
《文學世界共和國》和《什么是世界文學?》出版之時,兩塊大陸的比較文學學者早已冰釋前嫌,共同邁進世界文學這一“似舊而新”的領域。但我們仍舊可以在他們身上找到兩個學派留下的不同印記。
正如法國學派和美國學派的共識是研究跨國文學,卡薩諾瓦與丹穆若什也都是從民族文學起步來構建他們的世界文學理論,但是,這一同樣的起點,除了指向了不同的理論本身,還展現出二人在思維方式上與生俱來的差異。卡薩諾瓦所在的歐洲大陸是起源、是正統,雖然她將社會學理論移植到文學研究中,發展出一套大膽創新的文學世界理論,但其論述仍舊隱隱遵循著法國學派對“影響研究”的推崇,因為所謂國際文學場內的“競爭”,就是各民族文學之間的互相影響,只不過卡薩諾瓦不再著眼于某一小處具體存在的影響,而是站在一個更高的視角,宏觀檢視文學世界內的種種相互作用。而當丹穆若什把世界文學定義為一種閱讀和流通的方式時,他已經拓寬了此處“文學”的定義,把文學與其他的社會文化活動連結在了一起。換言之,丹穆若什的理論中,并沒有嚴格定義各種概念,而是留下了足夠的適應空間,最后一章“足夠的時間和空間”就是明證。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更系統,因此也更封閉;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學”更開放,因此也更松散。
進一步說,如果法國學派代表的是保守,美國學派展示的是開明,那卡薩諾瓦與丹穆若什又將形成一組有趣的對照。如前所述,對卡薩諾瓦的批評大部分來自她難以擺脫的“歐洲中心論”和強烈的殖民色彩。法國巴黎成為她文學世界中雷打不動的“首都”,顯然與她的法國人身份不無關聯。如果是歐洲或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作者,運用布迪厄的場域理論去研究國際文學場,大概會注意到上世紀下半葉巴黎的衰落,但在卡薩諾瓦身上,卻是發生多次提及拉美文,而忽視巴塞羅那對拉美文學的祝圣作用的情況。與此同時,北美經歷了經濟發展后,學術方面廣納賢才,思路開放。如果說《吉爾伽美什》至少已經經歷過時間檢驗,從歷史文物變成了公認的英雄史詩,那么對于《我,麗格伯塔·門楚》的文學性似乎還有爭議,它通常會被歸類為紀事作品,而丹穆若什卻因其跨越國境的傳播,把它納入對世界文學的討論中,這無形中擴展了文學的概念。丹穆若什“過度的”兼收并蓄,造成了可疑的“為世界而世界”的傾向,這種開放到極致而引來的批判之聲,與卡薩諾瓦深層的保守再次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結語
雖然對兩位大家的批評之聲不絕于耳,但這些持續的爭論,也證明了兩部著作長久的生命力和影響力。合理的批評可以讓這兩套理論漸趨完善,但為批評而批評,倒不如腳踏實地,學習歐美大陸這兩種理論中的科學性。
正如現代主義理論和后殖民理論被照搬到東方來遇到的不適應性,我們也應反思,從歐美直接拿來的“世界文學”概念,是否也會在此地遭遇一些“水土不服”。今天,我們的工作是比照卡薩諾瓦的“文學世界”與丹穆若什的“世界文學”,但明天,對于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的發展,更重要的是有適合東方語境的理論的創新。盡管站在中國學者角度書寫的世界文學,大概會遭到西方學者的強烈批評,但我們也不該因難畏懼、因噎廢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