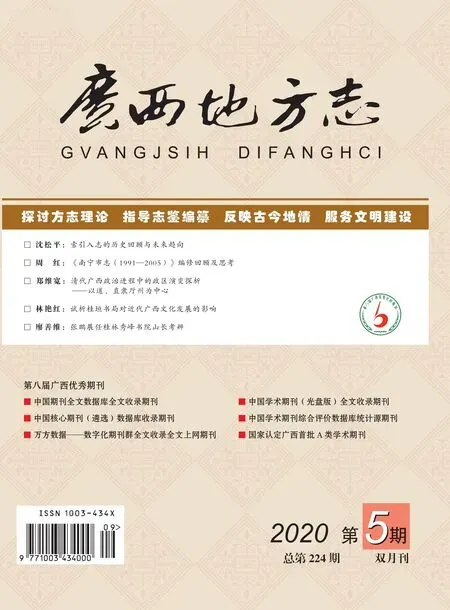清末桂林舊照片“立憲萬歲”的考述
呂立忠
(廣西桂林圖書館,廣西 桂林 541199)
有兩張清末桂林拍攝的老照片,在2011年辛亥革命100年紀念之際,在國內廣為流傳。其時,《南方周末》出版的《辛亥革命百年紀念特刊》,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影像辛亥·晚清社會》,北京衛視播出的大型歷史記錄片《辛亥》,等等,都載錄、引用了該照片。各報刊、著作及影視作品在載錄、引用時,或說照片記錄的是1905年“桂林一次官方集會”,或說照片記錄的是1905年“廣西桂林公立學堂舉行運動會”。
有研究者認為,“這組老照片定格住了史上一個重要瞬間,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晚清場景,彌足珍貴。”[1]有學者在提及這兩張照片時寫道:“在廣西桂林的一次官方集會上,會臺上方高懸著‘立憲萬歲’的匾額,會場上不同的服裝就是一個新舊交替時代的風景,一邊是穿清朝官服的大小官員,一邊是穿著新式校服的小學和師范學堂學生。這一切都意味著中國開始從古代向近代轉型。”[2]應該說,該組照片備受關注,為眾多報刊及專著載錄、引用,正是由于它生動、直觀地再現了“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晚清場景”。
其實,這組照片在2005年時已出現在國內——當年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沈嘉蔚編撰《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國·目擊變革》一書中,收錄了這兩張照片。一張照片的介紹文字是:“1905年廣西桂林的一個官方集會。這是主席臺,最矚目的是橫額上的‘立憲萬歲’幾個大字……當年7月16日,清廷頒旨派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在此前后,張之洞、袁世凱等重臣奏請清廷實行憲政改革。這張照片說明‘立憲’已是官方公開話題,并深入人心。”另一張的介紹是:“這是與上頁同一集會的會場……”[3]各報刊、著作及影視作品等,在載錄、引用兩張照片時,將照片拍攝的時間認定(標注)為1905年,或來源于此①注1:筆者所見《影像辛亥·晚清社會·上》(福建教育出版社,2011.03),《清末制憲》(陜西人民出版社,2011.08),《家國春秋·150年中國社會生活場景》(南方日報出版社,2011.10),《有圖有真相:20世紀中國史1900-1910》(海峽書局,2014.04),《壹玖壹壹·從鴉片戰爭到軍閥混戰的百年影像史》(湖南美術出版社,2017.09)等多部圖書,收錄有該照片,并標注照片攝于1905年。注2: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州立圖書館網站發布照片,其說明文字及拍攝時間的標注,亦是根據沈嘉蔚之說(見山東畫報出版社2012年出版《老照片·第81輯》一書中沈嘉蔚撰《清末舊照〈立憲萬歲〉》一文)。。
照片原件原來由喬治·莫理循收藏。喬治·厄內斯特·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1862-1920),澳大利亞出生的蘇格蘭人,于1894年來到中國,從上海出發,沿長江溯游而上,開始了他第一次在中國的旅行,一年后,他將旅途見聞撰輯成《一個澳大利亞人在中國》一書在倫敦出版,頗受好評。《泰語士報》賞識其才能,于1897年2月正式聘其為常駐北京記者,從此開始了他長達20余年的中國生涯。其去世后,所遺留文獻包括照片由其遺孀捐贈給悉尼的米歇爾圖書館——今為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州立圖書館(The State Library of New South Wales ,Sydney,Australia)的善本部保存。沈嘉蔚編撰之書(《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國——目擊變革》)收錄的這兩張桂林老照片,即來源于此。
對沈嘉蔚一書介紹的兩張桂林舊照的資料性價值,讀者是十分認可的。但是,對其書中介紹的兩張照片拍攝的時間,讀者頗有質疑。有人評曰:“作者顯然沒仔細讀歷史,需知五大臣歸國,引發清帝國‘立憲潮’,已經是第二年,即1906年以后的事了。1906年7月24日,考察歸來的載澤在向慈禧匯報考察結果時,首次明確提出‘立憲效法日本’的建議。9月1日,清廷才正式發表‘仿行憲政’。廣西官員有膽量在1905年公開打出“立憲萬歲”的橫幅標語嗎?”[4]
一些讀者、網民則提出,照片拍攝于1907年,記錄的是一次集會——廣西學界第一次游藝會。此次游藝會,被認為是“廣西歷史上最早的省級運動會”[5]。據今廣西桂林圖書館藏《廣西學界第一次游藝會全案》(廣西官報處編輯,清末鉛印本),可知:該運動會由廣西巡撫衙門籌辦,于1907年11月29至30日在桂林舉行,39所學校參加比賽。2012年出版的《百年光影:桂林城市記憶》[6]及2015年出版的《半壁民國一碗粉》[7]二書,均收載這兩張桂林舊照片,并疑照片或拍攝于1907年舉行的廣西學界第一次游藝會。
針對讀者、網民關于照片拍攝時間的質疑,沈嘉蔚于2012年2月在《老照片·第81輯》一書中發表《清末舊照〈立憲萬歲〉》一文[8],予以回應,并提出他對照片拍攝時間的新的看法。他從照片本身提供的一個細節,推斷有人提出的照片拍攝于“1907年廣西學界第一次游藝會”的說法是錯誤的:照片畫面主席臺右側有張日程表,顯示集會只有一天(日程表顯示的大會流程安排是:升旗,開會,奏軍樂,宣詔,呼萬歲三,祝詞,演說,奏軍樂,停會;下午開會奏軍樂,各學堂運動,閉會奏軍樂,鳴炮三聲),而“廣西學界第一次游藝會”日程為兩日。沈先生據其掌握的資料提出:“比較可能的,這個集會應是在1906年9月份召開的,專門為了‘宣’清廷決定預備立憲的‘詔’而開的,宣詔后又有演說,然后輔以運動、唱歌等助興節目。”
應該說,沈嘉蔚先生的推斷,是極有可能接近事實的:
1898年秋天,慈禧太后的屠刀砍下譚嗣同等“戊戌六君子”的頭顱,絞殺維新運動,清帝國在一片肅殺之氣中,徐徐落下19世紀的帷幕。未曾料想,1900年,紀元更始,八國聯軍侵占北京,慈禧攜光緒皇帝等倉皇西逃,飽受流離之苦。于是,有了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緒帝名義頒發的“變法”諭旨,20世紀出現第一線微弱之光——歷史上有名的“清末新政”開始了。至1905年7月9日,清廷決定派大臣出洋考察政體。當年9月24日,五大臣欲出國時,遭遇革命黨人吳樾炸彈襲擊(五大臣有驚無險,吳樾則當場取義成仁),延至12月初始離京出國。分兩路先后考察、游歷美、德、俄、英、法、日等國。大約半年后,五大臣考察歸來,面奏考察觀感,均“詳言立憲利國利民,可造國祚之靈長,無損君上之權柄”[9]。慈禧太后心中有了底,于1906年9月1日(農歷七月十三日)以光緒皇帝名義頒布“仿行立憲”上諭。決定預備行憲政,本著“大權統于朝廷,庶政公諸輿論”,改官制、修法律、興教育、理財政、整武備、設巡警等,根據預備情況,數年后再“妥議立憲實行期限”。
“預備立憲”的消息傳來,朝野上下、商學各界一片叫好聲,以為這是千古未有的盛舉,人們奔走相告,甚至有喜極而泣者。全國上下一片歡騰,各地張燈結彩,敲鑼打鼓,熱烈祝賀這道破天荒的上諭。9月5日的北京街頭,掛出龍旗慶賀,各個學堂都舉行了慶祝活動。最熱烈的當數上海:9月9日開會慶祝,上街游行;16日,上海各大報——《申報》《時報》《中外日報》等又聯合舉辦慶祝會。到會的上千人,馬相伯(著名教育家,震旦大學首任校長、復旦大學創始人)等人發表演講。馬相伯的演講詞登載在《申報》等報刊上,我們現在還能讀出他當年的激動和興奮:“我中國以四五千年破壞舊船,當此過渡時代,列強之島石縱橫,外交之風波險惡,天昏地暗,民智未開,莫辨東西,不見口岸。何幸一道光明從海而生,立憲上諭從天而降,試問凡我同舟,何等慶幸! ”[10]全國許多省的情況也都差不多,先后集會慶祝。并且,此時已出現了“立憲萬歲”的口號。例如,在直隸省省會保定(今屬河北),“省城學界商界”舉行“立憲慶祝大會”,“臺上演說立憲宗旨,演畢,臺上發號,全體歡呼立憲萬歲”[11];在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嘉定學會”于9月23日開會慶祝,大門外高搭彩棚一座,額曰“立憲萬歲”[12]。于此看來,清朝廷頒布預備立憲詔之后,廣西開會慶祝“立憲”,打出“立憲萬歲”的橫額,是極有可能的。
筆者最近翻閱到的文獻,可證實照片確實是桂林慶祝“立憲”時拍攝的——在《北洋官報》1906年第1225期(冊)“各省近事”欄有這樣的記載:標題是“桂林開慶祝立憲大會”,內容為:“自七月十三日明詔宣布立憲,各省埠學商兩界爭先慶祝,獨桂林僻處南徼,數月來無人提議及此。現學務處司道特諭飭學界于皇太后萬壽日舉行慶祝立憲盛典,開特別大會,以文昌門外簡易師范學堂為會所。是日,林大軍機、張護院率領司道文武各官蒞臨登臺演說。此外,學生及男女賓到會者約三千余人,合拍一照。散會后各學堂教員學生整隊游行。城鄉內外各街,晝執龍旗、夜持燈籠,游行三日三夜,沿途唱歌,此誠桂林第一次文明大會也!”[13]
據此記載可知:地處偏遠的廣西,慶祝立憲的活動晚了一些——1906年9月1日(農歷七月十三日)“立憲”上諭頒布,之后兩月有余,廣西學務處飭令學界舉行慶祝立憲大會,時間定在1906年11月25日(農歷十月十日),即慈禧太后“萬壽日”。當天,桂林各學堂師生3000余人集會于文昌門外簡易師范學堂,林大軍機、張護院——巡撫林紹年及護理巡撫、布政使張鳴岐率文武各官蒞臨慶祝會會場,林、張等人還登臺演說。據《清德宗實錄》卷564,1906年11月6日(光緒三十二年丙午九月二十日甲寅),清廷令:廣西巡撫林紹年“開缺,以侍郎用”,“在軍機大臣上學習行走”;次日(九月二十一日乙卯),清廷又令:以柯逢時為廣西巡撫,未到任前,由署廣西布政使張鳴岐暫行護理。故《北洋官報》的報道中,稱林氏為“林大軍機”,稱張氏為“張護院”①諭令下后,林紹年因故并未能立即卸任——見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奏折檔案:(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初四日)廣西巡撫林紹年奏報交卸撫篆日期事(檔號03-5469-069),(光緒三十二年十月初四日)護理廣西巡撫張鳴岐奏報接護撫篆日期并謝恩事(檔號03-5469-072);林紹年實于光緒三十二十一月入直軍機處——貴州省博物館1986年編印《貴州省墓志選》之《林紹年墓志》中云“:三十一年授廣西巡撫……且嘗疏請立憲,朝廷既更定官制,嘉公治績,內召以侍郞充軍機大臣。三十二年十一月入直,權郵傳部尚書。”據此以及《北洋官報》的記載,可知:廣西學界舉行“慶祝立憲大會”時,林紹年仍在桂林,尚未入京赴任。。很明顯,清末“立憲萬歲”組照,記錄的是:在廣西省城桂林,學界舉行的“慶祝立憲大會”。并非是桂林的運動會。雖然照片拍攝到的集會日程表顯示出此次集會上有“各學堂運動”,但集會的主旨是慶祝立憲。與“宣詔”“祝詞”“演說”一樣,“運動”是大會的流程之一。
慈禧太后生日當天,桂林學界開慶祝立憲大會,在主席臺掛上“立憲萬歲”的匾額,會后,三千余師生游行三日三夜慶賀,可謂歡喜之極。翻閱當時上海的《申報》等報紙,知慈禧太后生日這一天,其他許多地方也舉行了慶祝活動。北京的《京話實報》1906年第53號報道說:“從此要實行立憲,這次圣壽就是實行立憲的紀念。這等的好日子,拍著巴掌,跳著腳兒,要喜喜歡歡的慶賀大典。”善良的國人,以為真的要走上憲政的軌道了。但后來的事實證明,“立憲”只是空頭的許諾,不過是水中月、鏡中花而已!
關于兩張照片相關的情況,筆者還介紹如下:
其一,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州立圖書館,兩張照片分藏于莫理循文獻不同的類別之中(也就是說兩張照片不在一起)[14],因此,有研究者對兩張照片是否拍攝于同一場合提出疑問,認為兩張照片可能并非涉及同一事件(或說不是一套照片)。沈嘉蔚在新南威爾士州州立圖書館查閱到這兩張照片后,將其復原為一套,認定它們是“同一集會”的一組照片,其理由是:“全部莫理循收藏中,僅此二照為相同紙質,相同規格,相同裝幀,均由‘桂林學院街容芳齋照相館’拍攝。此外無此照相館拍的其他照片。此照也非常明顯地是一套:先從司令臺下拍司令臺,再從司令臺上拍操場全景(司令臺上的菊花亦留在了此照前景)。”[15]現據《北洋官報》1906年第1225期(冊)“各省近事”欄“桂林開慶祝立憲大會”一條的記載(可以說,此記載將當時照片拍攝涉及的時間、地點、人物、事件等一一載明),可知:兩張桂林舊照片,確實是同一場合下的一組照片,拍攝的是“桂林學界慶祝立憲大會”的會場,主席臺、臺下集會的官員與各學堂師生,各拍一張。
其二,目前,各文獻在引用、載錄照片時,有標注攝影者為喬治·莫理循的,也有標注喬治·莫理循為收藏者的。據查,喬治·莫理循到訪過桂林——1906年12月,他開啟了一次由北往南的考察旅程,經開封、漢口、長沙、桂林至越南的河內,直至次年3月初,才返回北京。1907年3月4日,他在《泰晤士報》發表有《從北京到越南北部邊境》。其文章中寫道:“……在具有出色的初等、中等、高等學校的桂林,我看到一名法國人在風琴伴奏下教唱英國歌曲。學英語的熱情到處可見……”[16]但是,在此次經過桂林的考察旅程中,莫理循并未曾拍攝照片——其二子阿拉斯戴厄·莫理循曾言:“據我所知,先父在1910年以前自已沒有拍過照片。”[17]并且,1906年11月25日,桂林舉行慶祝立憲大會時,莫理循還沒有開始此次涉及中國南方地區的考察。因此,莫理循不可能是“立憲萬歲”組照的拍攝者,而只是收藏者——很可能是在他到訪桂林時獲得了這兩張照片。又據《北洋官報》所載“桂林開慶祝立憲大會”的消息,大會舉行時,“學生及男女賓到會者約三千余人,合拍一照”,說明這么大場面的照片拍攝,是按預定的計劃進行的,那么,照片的拍攝,理應預先準備好,在當地找好攝影師,因此,最為可能的是,攝影師來自“桂林學院街容芳齋照相館”。
其三,有研究者在介紹兩張照片內容稱:這是“桂林公學”的一次集會,并介紹說:公學,指晚清時由官方出資興辦的新型學校,當時桂林公學計有廣西大學堂、桂林府中學堂……[18]如照此說,則照片中出現的“桂林公學”的旗幡,即是官辦學校的總旗幡(其他旗幡則是各學校的校旗)。其實,并非如此。“桂林公學”是一所學校。光緒《臨桂縣志》卷十四之“建置·書院”中有“榕湖經舍”條記載:光緒三十一年(1905),于“榕湖經舍”原址借地設“桂林公學”。另外,《新聞報》1905年1月5日“各省新聞”欄,亦載有“桂林公學”籌設的消息。據此,“桂林公學”與照片中的“廣西簡易師范學堂”“啟明兩等公小學”“附屬高等小學堂”等學堂一樣,是眾多新式學堂中的一所。將照片標注為“桂林公學的集會”顯然有誤。再有,需要指出的是,將照片標注為“清末桂林公立學堂(學校)集會”①筆者另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州立圖書館網站關于照片的說明里,即標注為“1905年廣西桂林公立學校體育運動會”——其英文說明中寫有:The sports meet of Guilin public schools in Guangxi Province,1905.也是不正確的。原因如下:光緒二十七年(1901),清廷諭令,將各省、府、廳、州、縣現有大小書院一律改為兼學中學、西學的學堂。此后數年間,各地根據《欽定學堂章程》(即“壬寅學制”)、《奏定學堂章程》(即“癸卯學制”),陸續創辦、設立不同類型的學堂。這些學堂,依其資金來源可分為三種:官立(官費)、公立(地方集資)和私立(個人出資)。照片中的“廣西簡易師范學堂”即是一所“官立”學堂(光緒三十二年,即1906年,廣西巡撫林紹年奏請,將廣西高等學堂改為簡易師范學堂[19])。很明顯,當時參加集會的,有“官立”學堂的師生,而不是限于“公立”學堂的師生了。因此,常被各專著單獨載錄、引用的那張清末桂林舊照——各學堂學生舉校旗集會的照片,可標注為:1906年桂林學界舉行集會慶祝立憲;或可以標注為:1906年,桂林各學堂集會慶祝立憲。

注:照片來源于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州立圖書館網站(https://www.sl.nsw.gov.au/)數字資源
以上即是筆者對備受關注的清末“立憲萬歲”舊照片相關問題的考證與介紹。應該說,1906年在桂林拍攝的這兩張老照片,是清末一個新舊交替時代的生動、直觀的記錄,是珍貴的歷史證物,它證明了“立憲”曾成為清末中國朝野上下的政治口號與追求。正是因為這個原因,這兩張老照片屢屢被人引用,被載錄于各種媒體及報刊、專著等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