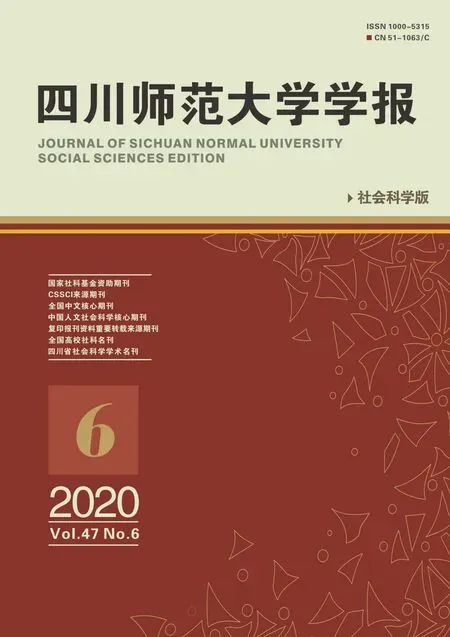《芝加哥格式手冊》(第17版)注釋和參考文獻的變化及其意義
羅 銀 科
(四川師范大學 a.社科學報編輯部,b.教育科學學院,成都 610066)
《芝加哥格式手冊》(TheChicagoManualofStyle)在出版社和編輯中的地位毋庸置疑,其影響力早已超出了美國,超越了英語國家,具有廣泛的世界影響力。從1906年初版問世,到2017年第17版出版,集眾多資深編輯百余年的深耕細作,其每一版的變化都值得我們認真學習和研究。本文即關注該手冊(1)本文主要參考《芝加哥格式手冊》第16版英文版和中文版,第17版英文版。具體版本信息如下: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The Essential Guide for Writers, Editors and Publishers, 16th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美國芝加哥大學編著《芝加哥手冊:寫作、編輯和出版指南(第16版)》,吳波等譯,高等教育出版社2014年版;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The Chicago Manual of Style, 17th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為方便引用,第16版英文版和中文版在文中統稱“舊版”,第17版稱“新版”。筆者對新版的翻譯參照了第16版中文譯本的一些譯法。與學術論文寫作規范休戚相關的注釋和參考文獻章節在最新版中的變化,并分析其變化原因,探討其價值。
一 對于細節的不斷完善,讓手冊更周全更易于理解
因為是過于細節的東西,所以該部分內容難免讓人覺得瑣碎和跳躍。但又不得不說,且要放到第一部分來說。因為在學術規范上,規則的形成,經年累月,所以大的改動幾乎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能被接受的,而能夠改動的多半就只是細節。規范的改變一定是循序漸進的過程,所以我們可以看到新版《芝加哥格式手冊》充斥著對于細節的縫縫補補,如不經意,你甚至都不會察覺到這種變化。可正是這樣的細節修改成就了它的經典。
(一)增內容
1.讓讀起來比較費解的內容簡單易懂
舊版“簡短引用的目的”一節有這樣的表述:“為了避免那些使用腳注或尾注的學術作品的文獻部分占用過多版面,對于已經提供過完整信息的資料來源,只要有可能,就應該對其后續引用采用簡短形式。”(舊版14.24)如果不聯系前后文,此處“已經提供過完整信息的資料來源”是很難理解周全的,所以新版在此插入了一句解釋,即“無論是在以前的注釋中還是在提供完整參考文獻數據的參考文獻中”都算作是“已經提供過完整信息的資料來源”(新版14.29)。同時指出了需要重新提供完整信息的“例外”情況,“在沒有參考文獻的著作中,最好在每一章第一次出現時就重復完整的引文”(新版14.29)。
新版關于注釋編號,增加了是符號而不是數字的情況說明(新版14.24)。如果注釋編號是符號,在正文中和數字編號一樣,設為上標。在注釋中,符號編號不后跟句點(這點有別于數字編號),但可以后跟空格,只要前后一致即可。舊版指出注釋編號應位于句末或從句末尾,但只給出了位于句末時的示例(舊版14.21),位于從句末尾的情況并沒有提供相應的示例。新版覺得有必要提供,所以增加了相應的示例(新版14.26)。這樣的補充,無疑是形象的。
新版在談到腳注和尾注的選擇時,在分析了一般情況后指出:“把注釋放在哪里的決定通常是由出版社做出的。”(新版14.43)這個提示對于作者很重要,提醒他們需要提前了解不同出版社的風格。
舊版指出,如果匿名作品的作者身份能夠猜到,在書名頁中卻被省略了,列為注釋或參考文獻時要在方括號中包含名字;然而在隨后的一個示例中,在名字后卻緊跟了一個問號(舊版14.80)。新版對這個問號做了解釋,即“不確定的情況下用問號表示”(新版14.79)。雖然舊版在其他地方對同樣的情況有過解釋,但作為工具書,這樣的重復是必要的。
在談到版本信息時,舊版指出卷號都要置于版本序號之后(舊版14.118)。新版在此處增加了對應示例的交叉引用(新版14.113)。同樣的做法還有“卷號和頁碼”一節(新版14.116)。新版其實是在有意減少交叉引用的。后文將要討論到的將“作者姓名”和“標題”從參考文獻各要素中抽離出來放到“圖書”版塊之前進行講解,就有這個目的。但與增加示例相比,他們更傾向于交叉引用。
在參考文獻中引用跨越多年出版的多卷本作品的某一卷,提供的日期(或日期范圍)“通常應該和最后提及的標題對應”(舊版14.124),即多卷本的出版日期。關于日期范圍,舊版涉及到了這種情況,但并未提供相應的示例,所以理解起來是比較困難的。新版在相同小節增加系列編輯與其中一卷編輯不同時,如果引用這一卷,則系列編輯與該卷編輯都應列出的情況。在列舉該情況的示例中一舉多得地顧及了舊版不曾列舉的提供日期范圍的示例(新版14.119)。最妙之處是竟然選取了尚未完全出版的多卷本作品。
2.讓例外越來越少
作為一本百科全書式的編輯手冊,《芝加哥格式手冊》總是試圖囊括編輯和作者可能遇到的各種問題,力爭讓例外越來越少。
新版增加了“每一章節后面可以有簡短的參考文獻”的一種具體情況,即“以獨立章節的形式出版的書”(新版14.62)。
舊版指出:“三重長破折號(3-em dash)可以代表之前條目中的相同兩位或更多作者(或編者、譯者等),只要他們都按照相同順序列出。”(舊版14.65)但在實際中有一個特例滿足這樣的條件,卻不能使用三重長破折號,即:
Author 1, Author 2, Author 3. Title . . .
______, Author 4, ______. Title . . .
所以,新版在“只要他們都按照相同順序列出”后補充說明“并且沒有作者出現在一個資料來源而不出現在另一個”(新版14.69)。
要用冒號把主標題和副標題分開,新版對可能出現的情況進行了補充說明,即主標題和副標題之間并沒有冒號,也需要用冒號將主副標題分開(新版14.89)。實踐中,這樣的情況不在少數。
標題中的日期,沒有介詞引導時,要用逗號與前面的內容隔開。舊版指出書名頁上僅用不同字體來表示的日期也要用逗號分開(舊版14.101);新版增加了書名頁上或在作品標題處“另起一行”來表示的日期也要用逗號隔開(新版14.93)。
隨著時間的推移,并不是如舊版所說的較古老的作品才可能沒有出版地(舊版14.138),通過商業自助出版平臺出版的新書通常也不會列出出版地。在這種情況下,出版地通常可以省略(新版14.132)。
在談到出版社名稱中的“and”和“&”標記時,舊版認為兩者是等同的,只要保持一致即可(舊版14.141)。但它卻忽略了一種情況,即在構成系列的出版社名稱中使用“and”和“&”是有區別的。在構成系列的出版社名稱中,系列逗號通常在&之前省略,但在and之前卻不省略;然而也有例外,如Farrar,Straus and Giroux一般是這樣寫的(即用and,不是用系列逗號)(新版14.135)。
對于“共同出版”舊版只解釋為“不同國家的兩家出版社同時(或幾乎同時)出版”(舊版14.147),新版補充道:“一些共同出版發生在出版社和另一個機構(如博物館)之間。”(新版14.140)
學術期刊文章的后續引用一般采用縮寫形式。其中一種縮寫形式就是作者的姓氏、期刊名稱、卷號和頁碼的組合(舊版14.196)。舊版在此舉了一個例子:Cotler and Woodruff,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56:840.新版“半替換”了此示例:Rosenblum,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63:225.但補充說明道:“EconomicDevelopmentandCulturalChange的頁碼在一卷書中是連續不斷的。如果不是這樣,除了卷號,縮寫應包括期號(即‘63 (2): 225’)。”(新版14.185)這樣的補充是必要的。如果加個交叉引用(即:“見14.177”),把冒號后的空格交代一下就更周全了。
如果報紙(2)舊版此處為“美國報紙”,見舊版14.210。名稱中不含有城市名稱,應該把它添加上,并和報紙的正式名稱一起用斜體字表示,但對于有疑問的地名,比如Guardian(Manchester)(3)此處的“有疑問”與舊版的“特別情況可以特殊處理”(舊版14.210)一樣,交代得不夠清楚。但舊版在緊接著的小節中,對Manchester用正體的原因作了說明,明確指出是因為Guardian屬于國外報紙(非美國)(舊版14.211),而新版在緊接著的小節將用正體的條件從“國外”變成了“非英語標題”(新版14.194),Guardian顯然不符合。,卻不需要用斜體(新版14.193)。一些全美知名的報紙不用添加城市名,但還有一些,因為有不同的版本,卻需要添加國別加以區分,如Times(UK)等。
3.提供一種更可行的解決策略
對于作者身份未知的匿名作品,舊版主張注釋和參考文獻應該以書名開頭(舊版14.79);新版卻增加了一種特殊情況,即如果某一作品明確寫著“匿名”(Anonymous),那么在將該作品列為注釋和參考文獻時,作者姓名處就應寫“匿名”二字(新版14.79)。因為有作者的作品,在注釋和參考文獻中處理起來要比沒有作者的作品容易些,盡管作者名叫“匿名”。
標題或副標題中出現的長破折號通常被認為是標題或副標題的一部分(新版14.98)。這樣引導,就能很好地協調標題中同時出現長破折號和冒號的情況。這一點是有別于中文語境的,需要注意。
如果作者和編輯對所涉及語言的用法不熟悉,則不應該在沒有專家幫助的情況下去嘗試改變非英語標題的大小寫(舊版14.107);新版認為:“必要時,圖書館目錄條目可能會有幫助。”(新版14.98)因為圖書館目錄條目雖然可能沒有專家那么專業,但也經過專業人員之手。
新版增加了頁面無明顯計數標記的圖書或圖書某部分的處理方式,那就是自行計算頁數,就像對待推測出的出版地那樣,將結果置于方括號中(新版14.155)。這樣做雖算不上精確,但比什么都不提供強很多。
在線查閱的學術期刊文章、雜志文章或報紙,提供相應的URL將有助于讀者做進一步閱讀。但有些URL只對訂閱者或訪問特定庫的用戶有效,在這種情況下,列出商業數據庫的名稱即可(新版14.175,14.189,14.191)。這一點很重要,但問題的關鍵在于查閱者經常意識不到查閱的是商業數據庫,就像我們的國標《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中所列舉的示例一樣(4)羅銀科、黃晶《國標〈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示例中電子資源存在的問題及其糾正》,《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5期,第167-169頁。。
(二)改措詞
1.讓規則更具操作性
參考文獻都按照作者姓氏的字母順序放在一個單獨列表中,但參考文獻如果沒有提供作者或編者的名字,舊版的做法是“按照標題或者讀者最有可能查找的關鍵詞”的字母順序(舊版14.57),而新版則將之改為“按照標題,如果沒有,則用描述性短語”(新版14.62)。這在規則上更明確,層級遞進關系更明顯。
2.讓含義更豐富
舊版在談到作者姓名的形式時,對于只要知道中間姓名的首字母,就要列出來的原因,說是“為了便于按字母順序排列”(舊版14.72),而新版中改為了“為了幫助區分相似的名字”(新版14.73)。后者明顯包含前者。
3.讓內容更易于理解
舊版在談到對開本的頁碼標注時,是這樣描述的:“在一些早期的圖書中,印張由對開頁組成——即把一大張紙折疊一次。因此每個對開有2張紙,即4頁。這些紙張只在正面的邊緣進行編號。”(舊版14.162)這樣的解釋顯然是不夠清楚與準確的。所以,新版進行了改寫:“一些早期的書用紙張編號而不是頁碼。這樣的紙張通常只在正面或背面編號……這種紙張有時被稱為對開。”(新版14.155)這就去掉了繁瑣解釋,簡單明了。
二 善于洞察作者和讀者的習慣,并將其融入規范體系中
何為規范,習慣使然。《芝加哥格式手冊》深諳此道理,所以不會固執己見,善于從作者和讀者的習慣中汲取營養,可以從反對到推薦,也可以從不反對到接受,還可以“將錯就錯”,但也可以暫不表態,只是陳述。
(一)從反對到推薦
舊版中對于各種格式軟件是很不屑的,從版面安排就能明顯看出(5)舊版將“資料來源引用軟件”一節放到了第14章“概述”版塊的最后(舊版14.13),而新版提到了靠前的位置(新版14.5)。。舊版指出:“許多軟件程序聲稱能自動對資料來源引用格式進行統一。這些軟件中,最好的那些程序能夠幫助作者節省用于抄寫和組織所引用資料的時間。此外,越來越多的在線文檔會含有預先統一格式的引用,有時候這是為了和資料來源引用軟件配套使用。但是,學術作品通常引用的資料來源的種類幾乎總是會超出軟件可以接受的范圍。”(舊版14.13)新版的語氣顯然緩和了很多,表述為:“很少有必要從頭開始創建源引用;甚至大多數印刷資源都會被圖書館目錄或其他在線資源列出。從那里,復制和粘貼相關數據或使用許多可用的工具提取數據就足夠容易了。”(新版14.5)除了推薦一些相關軟件,更加肯定其優勢,“引文管理工具最適合引用最近出版的書籍和期刊文章以及其他常見的出版物格式”(新版14.5),還對之前太過武斷的措詞進行了修改,將“學術作品通常引用的資料來源的種類幾乎總是會超出軟件可以接受的范圍”中的“幾乎總是”改為“通常”(6)新版“只有多字的作者”小節(新版14.83)對待只有名字的作者的做法也在舊版(舊版14.74)基礎上加了“通常”,因為總有例外發生。,并較之前更細化了保證引用的一致性、精確性和完整性的注意事項(新版14.5):
仔細檢查你的數據。在構建資料來源數據庫時,在獲取實際資料來源的數據后,請立即對照實際資料來源檢查每個字段。確保作者的姓名、作品標題、日期等準確無誤,并將其輸入到適當的字段中。還要檢查是否有丟失或冗余數據。(但是,可以收集比引用中使用到的更多的數據。)無論是您自己輸入數據還是從庫目錄或其他資源導出引用,都需要這樣做。
仔細檢查你的引文。一旦你的原稿中插入了一個資料來源引用,確保它符合本章或第15章中的建議。需要檢查的內容包括錯誤的標點或大寫,以及丟失或多余的數據。在引文管理應用程序中輸入更正(或根據需要調整其設置),并在原稿中重復檢查結果。
確保你的引文有備份。一些應用程序將允許您自動備份數據。保存本地副本通常也是一個好主意。這樣的備份不僅對正在進行的研究很有幫助,而且在你的原稿因為任何原因必須重新提交的情況下也很有幫助。
對于引文及其引用格式正確性有著嚴格要求的編輯和作者,讀完這段話,一定會拍手叫好。它們都是實際經驗的總結,值得我們的編輯和作者認真學習。
網絡資源具有極大的不穩定性,即隨時都有可能變化或者消失,所以有些出版社會要求作者提供訪問日期,以便核實。舊版推薦的做法是在引用資料副本上標注日期來存檔(舊版14.7);新版承前推薦引文管理工具的做法,直接改為“引用管理軟件將自動做到這一點”(新版14.12)。但是,僅僅保存訪問日期是不夠的,新版本專門用一小節指出哪些網絡文獻需要保存永久記錄以及如何保存(新版14.15),強烈建議作者備份的網絡資源包括:社交網站或應用程序上的推文,金融機構的網頁,或者新聞網站報道正在發生的危機的新聞版本——任何日后難以最初訪問形式回溯的資料來源(不受此條約束的資料來源的例子包括期刊、雜志或任何已在國會圖書館或其他國家注冊機關登記在冊書籍中的文章)。保存這樣的副本可以打印輸出或以數字文件(如PDF或屏幕截圖)的形式保存,也可以通過永久鏈接創建服務(如Perma.cc)的方式保存。
《芝加哥格式手冊》試圖引領某種習慣,當發現固有的習慣根深蒂固時,也會順勢而為。舊版在對待完整引用的交叉引用時,是這樣一種態度:“過去,學術作品的普遍做法是在每一個新章節里完整地重復細節,不過如今已經很少有這個必要。”(舊版14.26)而新版卻話鋒突變:“簡單地在每一章的注釋中重復一個資料來源的全部細節可能更好,這是本手冊對于沒有參考文獻表的作品推薦的方法。”(新版14.31)
(二)從不反對到接受
“章節和文章標題以及小標題上的注釋編號”這一節最能體現出《芝加哥格式手冊》對于某種格式規范從“不反對”“可以接受”,到融入自己的規范體系中(新版14.27)。舊版對于一些學術期刊、出版社喜歡給標題和對應的注釋添加一條注釋參考號(或符號)的做法的態度是“本手冊如今不再反對期刊文章標題采取這種做法”(舊版14.22),對于在圖書章節或一篇文章中偶爾有注釋參考號和小標題一起出現的情況,變得“也可以接受”;而新版中,直接刪去了這些“不情愿”的修飾語,讓一切變得順理成章。
(三)“將錯就錯”
有一些規則本身并沒有問題,遵循了某些原則或延續了某些傳統,但人們在遇到同樣問題時偏偏忘記了這么做或有意那樣做。《芝加哥格式手冊》看到了這些跡象,并從自身找問題。
對于學術期刊文章,舊版曾這樣規定:“如果一整卷期刊的頁碼是連續的,或者如果月份或季度和年份一起出現,則期號可以省略。”(舊版14.18)這樣做的目的是避免信息重復,盡量做到簡捷。但新版卻改為:“作者應該記錄期刊的全部信息,包括期刊期號,即使一整卷期刊的頁碼是連續的,或者如果月份或季度和年份一起出現。”(新版14.23)這樣做的目的確實可以部分節省讀者查閱的時間、提高效率,可誰又能確定這不是《芝加哥格式手冊》對于經常記不住去省略的作法的一種妥協呢?
對于前一條注釋中所引用的單個作品,在后一條出現時,是使用縮短引文還是“出處同上”(“ibid.”)這一問題上,舊版只提供了“出處同上”一種做法(舊版14.29);新版基于“出處同上”并不比縮短引文節省空間,也容易引起混淆等原因,提出“不鼓勵使用ibid.”的建議(新版14.34)。
當遇到雙重標題時,舊版認為在or前面加逗號是“不太傳統但卻更簡單的做法”(舊版14.99),但事實上可能作者更喜歡用這種“不太傳統”的做法;新版直接刪除了“不太傳統”這樣的字眼,并解釋“與早期版本的不同之處在于,它認識到了平衡編輯權宜與忠實于原始資料的重要性”(新版14.91)。
(四)不表態
《芝加哥格式手冊》有時也只是陳述事實,并不表態。舊版在多次引用和多次參考如何使用注釋編號時指出:“許多醫學出版物采用一種有編號的參考文獻體系,要求作者使用這種多重參考編號。”(舊版14.23)新版則將之前的“許多醫學出版物采用一種”中的“醫學”改為“科學”、“一種”改為“一些”(新版14.28)。
社交媒體(social media,或social networking)的內容越來越多地被作為資料來源進行引用,《芝加哥格式手冊》在新版中也將這一內容納入進來,并就像之前很多次出現過的一樣,試圖去引導這種習慣,而且給出了簡單的定義:“社交媒體(或社交網絡)是指通過專用平臺或服務共享的任何基于互聯網的公共交流論壇。一個網站可以承載或包含博客或社交媒體內容,博客與社交媒體(更不用說社交網絡)重疊,模糊了術語之間的區別。這三種都可以包括多媒體內容。社交媒體也可以包括私人共享的內容,通常與其他形式的個人交流一樣被引用。”(新版14.205)社交媒體的內容很多是沒有標題的,新版規定:“如果要引用,文章本身的文本(部分或整體)可以作為標題”(新版14.206),“引用前160個字符,包括空格”(新版14.209),同時也給出了引用社交媒體內容的基本引文格式(新版14.209)。
三 電子格式出版物本身在資料引用方面的變化及其帶來的資料引用格式的改變
電子格式(electronic format)出版物日益繁榮,給資料來源引用帶來了新變化。這在舊版《芝加哥格式手冊》中已經體現得很明顯,新版延續著這一變化。這些變化當然可以是細節的,也可以是根據作者習慣來的,但更重要的是電子格式帶來的。
(一)電子格式出版物本身在資料引用方面的變化
在電子格式出版物中,注釋通常與正文鏈接,腳注和尾注之間的區別可能不適用(新版14.43;14.49)。同樣的,在沒有固定頁數的電子格式出版物中,帶有頁碼的尾注的頁眉標題也不適用,也可以采取將注釋鏈接到文本的方式幫助導航(新版14.47)。在電子格式出版物不支持腳注的情況下,未編號的腳注可能立即出現在其所屬的要素之后,或與之鏈接(新版14.52)。已經出版的材料的來源說明,可能需要與章節標題鏈接,或緊隨其后出現(新版14.54)。在電子格式出版物中,對于省略了注釋編號的圖書,帶注釋的單詞或短語可以直接鏈接到其在正文中出現的地方(新版14.53)。電子格式的作品有時也將未編號的傳記性注釋和致謝放在文章或章節的末尾(新版14.55)。
總之,在電子格式出版物中,很多注釋都可以通過鏈接的方式實現關聯,從而擺脫繁瑣的注釋規則。
(二)電子格式出版物帶來的資料引用的改變
1.摒棄網絡文獻單純只提供DOI作為引用要素的做法
舊版對于引用在線參考資料,建議用URL或DOI作為引用的最末要素(舊版14.4),而新版中摒棄了單純提供DOI這種做法,提倡將DOI附加到https://DOI.org/以形成URL(新版14.8)。這樣做的原因,是“作者應該更喜歡”(新版14.8)。道理很簡單:因為如果還是按照舊版規則,要驗證某個提供了DOI的參考資料的正確性,首先需要打開國際DOI基金會網站或Crossref所提供的DOI解析器(或支持DOI的搜索引擎),然后輸入或粘貼DOI,又或者在網絡瀏覽器的地址欄中的http://dx.doi.org/后加上一個DOI,比較繁瑣、麻煩;而新版則簡單得多,只需要把帶有DOI的URL復制粘貼到網絡瀏覽器的地址欄即可。新版同時還推薦使用Handle System提供的以https://hdl.Handle.net/開頭的URL,因為其功能與基于DOI的URL基本相同(新版14.8)。
2.電子出版物獲取方式的表述多樣化、簡單化
舊版的出版時間是2010年,新版已經到了2017年,這段時間內,電子書的呈現方式發生了一些變化,人們的閱讀習慣也隨之改變。人們的資料引用途徑除了一些介質,如DVD、CD-ROM等,越來越多地傾向于應用程序(application)、格式(format)、設備(device)等(新版14.100)。應用程序如iBooks,格式如EPUB,設備如Kindle(新版14.137)。如果注釋或參考文獻參閱的是電子圖書,作為完整引用的最后部分,在表述上,新版也較舊版更為簡捷,比如“Kindle edition”(舊版14.166)變為“Kindle”(新版14.137)、“EPUB e-book”(舊版14.166)變為“EPUB”(新版14.137)。越來越多的圖書會以在線的方式增加一些補充性的內容,對于這樣一類引用,舊版是沒有涉及的,新版則增加了“僅供在線閱讀的一本書的補充”這樣的內容(新版14.112)。
3.將自行出版、預出版納入體系
舊版并未涉及作者自行出版(self-published)的書籍,但隨著商業自助出版平臺的興起,這樣的行為變得日益普遍,對此的引用也隨之而來,所以有必要進行相應的規范。新版提出:“除非作品是以出版社或印刷者的名義出版的(在這種情況下,可以按本節其他地方的描述引用),如‘self-published’(在注釋中縮寫為‘self pub.’,但不在參考文獻中)或‘printed by the author’(作者印刷)等語言通常是合適的。”(新版14.137)通過商業自助出版平臺出版的新書通常不會列出出版地點。在這種情況下,出版地點通常可以省略(新版14.132),除非被引作品本身已經列出或以其他方式知道某個地點(新版14.137)。可以添加平臺或發行商的名稱。對于電子書,添加閱讀圖書所需的應用程序或設備的名稱或文件格式的名稱,或兩者兼而有之(新版14.137),但“通常指定用于閱讀或獲取圖書的應用程序(在某些情況下)或設備的名稱比命名特定的文件格式更有幫助”(新版14.159)。
隨著預出版的推廣,一些期刊為了解決預出版與印刷版之間可能產生的頁碼沖突,采用了一種連續出版模式,即每一篇文章都被分配一個唯一的ID,并且在網上發表時即被視為最終版本。任何后續的印刷版本都不作任何更改地復制。并且,包含PDF版本的文章都是從1開始分頁的,可以在相應的注釋中引用(新版14.174)。新版想必也看到了這一趨勢,因此做了這樣的引導:在注釋中,引用的頁碼位于文章ID之前;在參考文獻中,不要包括以這種方式發表的文章的頁數范圍(新版14.174),因為意義不大。
此外,新版將舊版中介紹電子格式如何標注頁碼的一小段話(舊版14.166)擴充為一節詳細介紹,分列種種特殊情況(新版14.160)。這是廣泛使用電子圖書的結果。很多雜志開發了適用于不同設備的app,便于讀者隨時下載。而通過這樣的方式下載的雜志,很多屬于流媒體性質,在頁碼甚至是內容上與紙質的版本都有所區別。所以,新版指出使用特定應用程序下載的雜志文章,應注明用于獲取或閱讀文章的應用程序或設備的名稱(新版14.189)。
四 示例大量更新,適當增加或刪除,并且遵循一定的原則
新版相對于舊版,僅第14章,對大量的示例進行了更新。其中一部分是出于去DOI化的更新,即改變舊版中對于網絡資源,單純提供DOI的做法的更新,如新版14.8小節中對應舊版14.6小節進行的示例替換;還有一部分示例的替換似乎遵循“兩年前”原則,即2017年選取了2015年的示例(如新版14.8),2010年選取了2008年的示例(如舊版14.6)。這一選取示例的原則有時變為“至少過去兩年”,如新版14.19小節將舊版對應小節(舊版14.14)2008年的示例改為2014年的(7)唯一的例外出現在“當作者是機構”這一節(新版14.84),該節的示例用到了新版《芝加哥格式手冊》自身。這在時間上完全不符合“至少過去兩年”原則,甚至可以說是超前使用。因為從邏輯上講,在使用這個示例的時候,新版《芝加哥格式手冊》還未出版。這個例外傳遞的信息是對于自身質量的自信。舊版相對應部分(舊版14.92)也是同樣的做法。。對于一些增加的內容,有的也相應地增加了示例說明。如對于URL換行原則補充了一種情況,當特別長的要素必須被打斷,以避免一個非常松散或緊密的行時,可以根據該手冊之前提供的單詞劃分指南在單詞或音節之間打斷它,隨后增加了相關示例(新版14.18)。還有一些示例的增加,是為了讓已有內容更加形象,更易于理解,比如書名中如果出現了問號或感嘆號時,怎么處理它們與其他標點符號的關系一小節,在內容并未增加的情況下,只是增加了舊版不曾列舉的示例(新版14.96)。刪除的示例,一部分是為了去DOI化,如新版14.18小節相對于舊版14.12小節,只是單純對提供DOI示例的刪除。
當然,也有一些比較棘手的示例,新版選擇了沿用舊版的辦法。比如新版14.90小節中有兩個副標題的示例就是沿用舊版14.98小節的;再如新版14.92小節中標題中帶有“以及其他故事”的示例,也沿用了舊版14.100小節的。因為這樣的示例確實不多見,替換起來相對麻煩一些。
反觀國內的一些標準,示例的更新率很低,有的示例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使用,而且在二次三次使用同一示例時還出現轉錄錯誤(8)羅銀科《國標〈信息與文獻 參考文獻著錄規則〉示例的編校失誤及其歸因》,《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7年第2期,第128-132頁。。研究《芝加哥格式手冊》的示例,我們可以發現,在遵循一定的原則的情況下,示例的大量更新不難做到。比如至少過去兩年,再比如用經典替換經典,用暢銷替換暢銷(新版14.127)。
可以看到,新版在示例上力求完善,但不可否認,總有例外,無法窮盡。最典型的例子恐怕就是書名頁上的“其他貢獻者”,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次要責任者。由于對于次要責任者的表述方式實在太多,為防止掛一漏萬,新版加上了這樣一句話:“對于其他貢獻,描述應該準確地傳達書名頁上的信息。”(新版14.105)
五 改變規則
這樣的例子不會、也不能太多,其中一部分又是為了順應作者的習慣(前文已述)。
對于很長的標題,《芝加哥格式手冊》主張在參考文獻和注釋中可以縮短。舊版的做法是標題內用3個省略號點來表示省略部分,如果省略的是標題末尾部分,則用4個點表示(舊版14.106)。這樣做的問題在于,省略號是作品本身自帶的還是引用者后加的并不明確。所以新版主張在省略號外加上方括號,以示省略號是引用者后加的,不是原標題的一部分(新版14.97)。這樣一來,舊版省略標題末尾用4個點表示的做法,自然就變成了用方括號括起來的省略號加句號。這樣理解起來就容易多了。并且,這樣的做法與出版地未知但能判斷出來的處理方式(新版14.132)一致。
對于由集團及其成員聯合出版,或者是一些學術出版社通過一個特別的出版部門或在一個特別的品牌下發布的圖書,在列為參考文獻時,舊版的做法是集團名稱后可以列出成員名稱,學術出版社后面列出品牌名稱,都用斜線隔開(舊版14.145-146)。但這樣做的問題在于,斜線無法清楚交代被分割在兩邊的出版者之間的關系。所以新版舍棄了這樣的做法,直接改為文字表述的方式交代兩者之間的關系(新版14.139)。
關于網站和博客的名稱,舊版曾嘗試引導類似書名或其他類出版物標題的那些名稱可以采用相應的格式(舊版14.244)。新版時卻明確指出:“與上一版的建議不同,類似于傳統印刷品但沒有(也從來沒有)印刷品的網站的標題可以像其他網站的標題一樣對待,這取決于編輯的自由裁量權。維基百科可以被視為一個網站而不是傳統的百科全書,標題用正體而不是斜體。”(新版14.206)因為“類似書名或其他類出版物標題”的名稱太難權衡了。
六 優化結構,化繁為簡
新版《芝加哥格式手冊》在結構上最大的調整是將原本置于“圖書”一節中的“作者姓名”和“標題”兩個次級項目上升到與“圖書”同級,并先于“圖書”進行講解。為什么將作者姓名和標題從參考文獻各要素中抽離出來放在圖書和定期出版物之前予以講解?其實舊版中就能找到答案:“圖書作為正式出版物有著悠久的歷史,確保了它們在作者姓名和標題上的各種形式能作為模板,為其他許多類型的資料來源生成文獻式注釋和參考文獻條目提供參照。”(舊版14.68)與其在講解其他類型的資料時交叉引用此處內容,不如將其提取出來先行講解,以避免交叉引用帶來的繁瑣感。這一點在新版“引用作品的標題的斜體與引號”小節(新版14.86),體現得尤為明顯。該小節用一段話,將舊版中原本分布于若干小節的標題到底用斜體還是引號,抑或都不用,做了整體概括,使人一目了然。
新版對舊版的“匿名作品——作者身份未知的情況”(舊版14.79)和“匿名作品——作者身份已知的情況”(舊版14.80)兩個條目進行了合并,統稱“未列出作者(匿名作品)”(新版14.79)。同樣的做法,將舊版的“筆名——作者身份未知的情況”(舊版14.81)、“筆名——作者身份已知的情況”(舊版14.82)、“很少使用的筆名”(舊版14.83)和“‘作者’的描述性短語”(舊版14.85)四個條目整合為“筆名”(新版14.80)。這樣做的好處,除了減少條目外,使得舊版14.81中提到的“在正文引用中則省略pseud.”與14.85既可以共用一個示例,又顯得清楚明白。
新版將舊版“編者和作者”(舊版14.90)一小節的內容放入“除了作者之外還有編者或譯者的情況”(新版14.104)一小節中,可能是看到了舊版該小節標題的不合理性。舊版該小節的內容實際上談的是編者或譯者與作者之間的關系問題,僅僅只是示例舉了編者的而已,所以從標題來看,是不恰當的。但如果再加入“譯者”的示例,新版的改動就順理成章了。
新版將舊版“系列叢書主編”小節(舊版14.129)合并到“系列叢書的標題、編號和主編”小節(新版14.123)。作者可能認為本身就處于被包含情況的分列過于繁瑣。同樣的情況還有,將舊版“沒有卷號或僅有日期的情況”小節(舊版14.181)合并到“學術期刊的卷、期和日期”小節(新版14.171)。
可以看出,新版在章節結構上,秉持的原則是能合到一起的絕不再單列,目的只有一個:精簡條目。新版在結構上的很多調整與舊版一樣,是根據當下現實中出現和使用頻率來安排的。比如用很長的一節介紹社交媒體內容的引用(新版14.209);再如新版將“較古老作品的免費電子版”與“存儲在CD-ROM和其他固定介質上的圖書”兩小節對調(舊版14.168-169,新版14.162-163)應該就是出于這樣的考慮;還有將“網站、博客和社交媒體”類資料來源往前提了很多(新版14.205-210)。為了減少交叉引用帶來的繁瑣感,新版將很多內容進行了整合。這種在結構上的調整和優化,帶來的結果就是,新版第14章在新增了不少內容的情況下,條目數卻減少了12條。這樣的調整和優化,從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無疑是成功的。
七 結論
綜上所述,只是厚厚的《芝加哥格式手冊》的一個版塊(9)限于篇幅,即便是“注釋和參考文獻”部分,筆者也放棄了對“法律和公共文件”變化的介紹和探討。的變化,更確切地說,只是筆者現有認識水平下體會到的一些變化。這些變化,有的引領當下,有的迎合當下,有的記錄當下,大都值得我們去學習和研究。
當然,《芝加哥格式手冊》并非盡善盡美,新版相對于舊版的很多變化足以說明。當然,并不是新版的所有變化都值得我們去學習的。因為對于變化,《芝加哥格式手冊》有時也是只是試探性的,因此需要我們辯證來看待。正如新版將舊版的很多小節進行合并處理,優點前文已經談到,但作為一本工具書,條目越清晰、越詳細無疑越便于讀者查閱,所以,如若從時間成本去考量這種變化(如新版14.99),其意義就不大了。再如將“電子郵件列表”小節內容(舊版14.223)從私人通信版塊放到了“網站、博客和社交媒體”版塊(新版14.210),誠然在格式上更接近于后者,但其在內容上似乎放在前者更容易查詢和理解。很多示例,不知是否出于版權考慮,并未配有相應書籍的書名頁或版權頁,但如果加上,理解起來就容易許多。比如14.90小節中帶有兩個副標題的示例,如果附上該示例的書名頁和版權頁,例子豈不是更形象?舊版將碩士、博士學位論文放到了“未出版作品和非正式出版物”板塊,在談到具體引用時,也作“未出版作品”處理,只是加了句“在其他情況下引用它們的格式與引用圖書相同”(舊版14.224);至于什么是“其他情況”,則沒有解釋。新版雖去掉了“未出版作品和非正式出版物”這樣的版塊名(新版14.215),但實際上還是延續了舊版的做法,同樣對“其他情況”沒有解釋。
學術規范一定是延續性的,沒有終點的,因為人們的習慣一直在改變。所以,我們可以在《芝加哥格式手冊》新舊版的對比中看到“正在被淘汰”(舊版14.31)改為了“已經被淘汰”(新版14.36)。
早在2003年就有人疾呼“盡快出臺一部適合我國國情的有利于學術健康發展的中國的《芝加哥手冊》”(10)肖力華《學術規范期待〈芝加哥手冊〉》,《編輯學報》2003年第5期,第358頁。,到了2012年還有人在呼喊“中國需要自己的《芝加哥格式手冊》”,并稱可喜地看到了一些苗頭(11)劉彬《中國需要自己的〈芝加哥手冊〉》,《光明日報》2012年9月11日,第14版。。可光是這樣的大處著眼是不夠的,更需要的是小處著手。正如《芝加哥格式手冊》所說的那樣:“寫作、編輯和出版,精確性和對細節的關注,再加上清晰易懂的文字,似乎永遠不會過時。”(新版“前言”)對比新舊版本最深切的體會就是,細微處足見其功力深厚。中國要想推出自己的《芝加哥手冊》不難,找個僻靜的角落坐下來,讀讀它。你會發現,其間并無晦澀的字眼,有的只是編輯們的日積月累。我們所缺的只是細心揣摩,錙銖必較,點滴積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