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長的頭皮
編譯 思羽
在信息互聯和大數據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帶來極大便利的同時,對于隱私的擔憂也令人不由地擔心。假若更進一步,記錄我們信息的裝置從手機和電腦變成大腦植入物,會發生什么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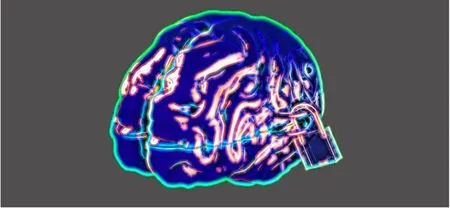
在我被囚禁的第289天,他們過來見我。
我的腦袋不斷悸動,感覺像塞滿了金屬纖維,但是當哈格里夫船長和博莎拘留官為我的牢房開鎖時,我還是在臉上擠出微笑。我的手臂、雙腳、手腕、腰部、胸部、大腿和脖子都被綁在支架上,一套厚厚的囚犯綁縛衣緊緊捆住我的軀干,靠磁力吸附在支架后部。在那之后,他們又將我封禁在外骨骼囚服里。
總的來說,我將這視為一種恭維。
博莎在全息影像儀上檢查我的狀態。當她瞥向哈格里夫,說了句“沒有進展”時,我笑得更歡。
哈格里夫用指節敲打了埋入我的太陽穴的接線。“哦,他遲早會崩潰的。或者,你可以干脆地告訴我們。我們最終會把秘密挖掘出來,哈魯斯。”
“唉,”我透過固定在我臉上的鋼網口絡用刺耳的聲音說道,“你們到目前為止都干得不錯。”
博莎的拳頭擊向我的腦袋一側。我因為這次拳擊而搖擺,吐出一口帶血的唾沫。我在太空船塢的酒吧里挨過更狠的拳頭。
“我得要說,一邊腦袋連著‘接線’,一邊當走私犯是相當愚蠢的職業轉向。”
哈格里夫這一次說到點子上。當名叫“接線”的大腦植入物出現時,每個人都認為只有富人會購買它們。結果相反的事成為真實。“接線”的制造成本變得如此低廉,任何一個希望與現代生活保持同步的人都得要買一臺。他們將記憶和信息即刻儲存、備份在數據圈里,隨時都能訪問。在一些星球,安裝“接線”是強制性的。富人們負擔得起通過內部濕體(wetware)訪問的遠程存儲,那種存儲空間是黑客也無法駭入的,也不會把他們的記憶、去過的地點、做過的事情登記在半公開數據庫中。實際上,你負擔得起不安裝“接線”的代價。
這是我轉向走私的部分原因。各星系的人會支付可觀的信用點,只為獲得一些他們不想在海關登記的物品。麻醉劑、烈酒、數據庫、文物、軍用級武器、遠古遺物。任何東西都可以。我和船員們的走私事業干了差不多九個標準年。我犯了一次差錯,但一次閃失就足以讓我陷身囹圄。我被星系安全部隊抓獲,丟進這個位于星系深處的拘留中心,接受審訊。
哈格里夫靠在像鏡子一樣光滑的墻上。“如果你放棄你的船員,一切都可以結束。”
我打了個響鼻。“你們不經常做這種事,對吧?”
“嘿,我們有的是時間。你沒有。”
我將近在這兒坐了300天,抵抗著他們從我的“接線”輸入進來的“剝頭皮”軟件,忍受它在我頭腦的“服務器機柜”間聞來聞去。它從我的腦子里搜羅出我干過的買賣、服務過的主顧、走私過的有趣物品。最重要的一項是:我的船員去了哪里。我對抗“剝頭皮”軟件時,腦袋悸動,伴隨著滯鈍的疼痛。我往腦海里填入分心的念頭、錯誤的記憶和隨機的統計數據,假裝它們是真實的,以此來迷惑軟件。我殺滅研究模式,用心智的方式埋葬數據。這是一場名副其實的意志大戰。人工智能無法判斷哪段記憶是真實的,哪段記憶是虛構的,除非它們想把我的大腦變成一堆冒煙的神經元。但軟件在適應新情況,識別出新模式,漸漸知道我是如何思考的。如果我身上的外骨骼囚服沒有將我的睡眠限制在一晚四小時,并將我的食物和飲用水攝入量降到最低的話,或許我能夠抵抗它。他們一邊用持續不斷的白噪音對我進行狂轟濫炸,一邊將我包裹在桑拿一般的酷熱或者邊境永凍土一般的寒冷中。這是“文明”的酷刑,勉強合乎星系際法律。我的身體麻木了。我幾乎無法保持醒覺,更不用說進行心理戰。
但我每抵抗一天,我手下的船員們就能多搶先一天。我們就是這樣對付出問題的掮客交易。我們不會關注如何在下周、下個月幸存下來。我們只關心明天。我們能在事實上將難題永遠推遲下去,只要我們能堅持到第二天。現在,我在為船員們做那種事,痛苦地熬過一天接著一天。任何一位優秀的船長都會這么做,而我自豪地認為自己是最出色的。當我們成為走私者時,我們發誓要對彼此絕對忠誠。一言既出,駟馬難追。我不會讓別人說出阿利斯泰爾·哈魯斯沒能硬撐到確鑿的崩潰點。
“我希望他沒有松口。”我回頭瞅去,看見博莎在撥弄我的外骨骼囚服的約束帶,用能壓裂骨骼的力氣收緊約束帶。“那樣更有意思。”
哈格里夫傾身靠近我,近得足以親吻到我,再用紋身的手指輕彈我的“接線”裝置。“哈魯斯,你是個生意人。那么讓咱們做筆生意吧。你現在開口交代,我會將你從外骨骼囚服里放出來,拔掉‘剝頭皮’軟件。給你一間頭等艙房間。該死的,只要告發指認你手下的船員,我會給你安排一件鈷等級的金屬基板,不是那種非法制造的便宜垃圾。你有什么想法?”
我使出全力,用腦袋去撞她,讓她知道我的回答。骨骼嘎吱嘎吱響,鮮血四濺。她趔趄后退,手摸著被撞傷的鼻子。盡管我很疲憊,可我還是在口絡后面用力咧嘴笑,幾乎要把臉龐撕裂,“那真的是你能秀出的最好一招?”
博莎正要將我的下顎碎裂成糖玻璃一樣的碎片,哈格里夫阻止了她。“不,將剝頭皮軟件提升到下一級。實際上,提升三級吧!讓它去深挖,讓永久性傷害見鬼去吧。看看再過幾個月后他有多反叛。哈魯斯,等你亂流口水、通過管子來喂食時,你會希望你接受我提出的條件。”
博莎超馳控制了系統,調整設定,讓它低于法定最低值。機器運轉起來。我咧嘴看著她們離開,去為下一場即將到來的心理戰做準備。隨著剝頭皮軟件野蠻地挖洞進入我的大腦,我的頭痛變得令人戰栗,悸動不已。當我在心智的結構里擦除我的船員們的名字,我的被牢牢束縛的拳頭晃動起來。我準備好再抵抗一天。以及它之后的一天。還有它之后的另一天。
那是我所需要的一切。只要再抵抗一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