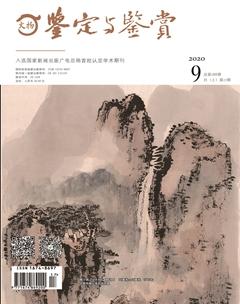淺談重構美術史
劉倩茹
摘 要:文章主要借墓葬藝術這一案例來講述目前重構美術史的必要性。無論是古代還是現代,不同的歷史時期會有一些超越時間的共同的歷史邏輯。作者針對當下中國美術史研究的視角、美術史學習的缺漏以及目前美術史研究的現狀等進行探討,認為中國美術史的重構既可以是循序漸進的、長遠的、有邏輯的發展,也可以是不同時代潮流的橫向對比。
關鍵詞:美術史;墓葬藝術;重構
最近閱讀巫鴻博士的《美術史十議》,巫鴻博士在《“墓葬”:美術史學科更新的一個案例》一章中,提出重構美術史的基本局限在于這些學者并不是從對不同文化和藝術傳統的實際案例中分析研究總結的,而是沿用以往的一些概念和分析方法,從而讓研究成果具有很大的文化片面性。目前我們更應該運用歷史的眼光去研究重構美術史。雖然我們研究的是歷史問題個別案例,但是我們所得出的結論卻是不局限于研究對象本身的,相反我們更希望借助于對個例的研究去反思重構美術史的概念和方法。嘗試運用自下而上的思考方式去層層挖掘美術史中的不同現象和邏輯結構,以此來逐漸拓寬美術史研究的深度與廣度,這才是更有意義的。因此,筆者就上述這一點,從“墓葬”這一具體問題入手,討論重構美術史的問題。
墓葬作為世界獨一無二的文化藝術,在中國已有數千年的發展歷史,是我們所知的最源遠流長的一種綜合性建筑和藝術傳統。①古人不僅重視生前的榮華富貴,死后也要竭盡全力通過各種手段、方式去維護和體現自己的身份地位。這種現象并不僅僅出現在中國古代,埃及著名建筑古跡金字塔也同樣體現了這一特點。中國的墓葬藝術絕大部分是以墓葬主人為主體,帶有陪葬奴隸和各種各樣的陪葬品,且注重墓葬整體空間的建筑與裝飾等。這種墓葬傳統經過漫長的發展歷程,通常有一套獨特的視覺語匯和形象思維方式,它與中國本土宗教、倫理,特別是和中國人的生死觀及孝道思想息息相關的。①從另一種角度來說,古人是希望通過這種極其隆重的墓葬讓自己的靈魂得以升華、得以安息。
但是當現代人了解研究這項獨特藝術時,卻出現了本末倒置的現象。他們往往非常重視從考古遺址中發掘出來的一些壁畫、明器或墓俑等,對于完整的、具有內在邏輯的墓葬通常不夠重視甚至是忽略的。墓葬藝術通常包括墓葬和它的內部陳設、明器等,如果將目光僅僅盯在所出土的文物,挖掘它們的各種潛在價值,研究它們的來龍去脈,那對于墓葬本身來說是極其不公平的。作為承載這些文物的載體,墓葬本身和各種文物應該被擺在同等重要的位置,正因為有了這個載體,這些文物才有了賴以生存的文化、禮儀和視覺環境,才得以被保存流傳下來。而不是僅僅把它當作一種獨特的地下建筑,放到建筑史中去進行研究。以馬王堆一號墓為例,該墓發掘報告正文共分為四章,包括《墓葬位置與發掘經過》(2頁)、《墓葬形制》(34頁)、《隨葬器物》(120頁)和《年代與死者》(3頁)①,其中《隨葬器物》一章占大篇幅,總共歸納為十大類,按照帛畫、紡織品、漆器、木俑、樂器、竹筒、其他竹木器、陶器、金屬器、竹簡的次序一一著錄。在參加國外展覽時,這些展品也基本上是按照報告中的器物排序分類來陳設的。但是當我們結合《隨葬器物分布圖》時,才知道這些器物的擺放位置和作用都是有各自意義的,才知道古人是在給死者的靈魂營造一種怎樣的藝術空間,表達了他們怎樣的思想情感,是它們共同構成了這一墓葬空間的禮儀和象征意義。而這份挖掘報告井井有條的分類并不代表墓葬設計者的意圖,更沒有體現漢代文化和藝術的特性。
從重構美術史的角度來說,這種對中國古代墓葬的整體性研究也將引導我們重新思考美術史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研究方法。目前我們所接觸到的藝術基本上是我們能直接或間接觀賞感受的,大到陳列在各大博物館里的文物或者展覽上多姿多彩的藝術品,小到路邊隨處可見的廣告招牌和宣傳畫,我們也是基于這一點去研究藝術。但是墓葬藝術通常是通過環境和器物的擺設,給人們營造一個想象的空間,各自體會創造者的意圖。比如馬王堆一號墓中,墓葬設計者通過各種物件的擺放和空間的精心布置,給后人營造出一個約3米長、1米寬、1.5米深的舞臺劇場景。①不論是張掛的絲帷、竹席、屏風等,還是各種栩栩如生的舞蹈俑和奏樂俑,甚至有很多女性的化妝品和假發等這些私人物品,都說明墓葬設計者在用這種“非再現”的手法為墓主人營造一個優雅而華麗的靈魂居所。這就與現代藝術有很大區別:一個是直接擺在眼前供觀賞、供討論研究,我們可以非常直觀地去感受、去品鑒;一個是通過想象來挖掘內在價值,我們需要結合具體事物去想象那究竟是怎樣的一個場景,這就好比二維空間和三維空間的區別。似乎傳統的美術史研究方法就不適用于研究類似于墓葬藝術這種比較特殊的藝術門類了,也不能直截了當地將以往的理論知識拿來解釋墓葬藝術了。
因此,筆者非常贊同巫鴻博士提出的重構美術史觀點,運用整體性眼光去看待和研究這類特殊性質的藝術。哲學上說“存在即合理”,既然墓葬藝術是明器與墓葬的結合體,我們為什么只著眼于出土文物,而忽略其所處環境呢?墓葬的存在難道就僅僅是裝文物?筆者不認為是這樣。在筆者看來,這兩者是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的。這對于大多數人來說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離開了墓葬整體環境的器物就沒有了歷史背景,離開了器物的單個墓葬環境就會空洞無味。因此,只有在研究中將兩者有機結合,整體看待、整體研究,才能方便我們更加深入了解造墓者的意圖和意義,才能盡可能做到不遺漏一些我們可能會忽略的重要方面,做到全面客觀公正地去研究這類帶有特殊性質的藝術門類。相反,如果我們僅僅研究墓葬中的器物,忽略它們所處的環境空間,忽視墓葬的價值,我們就可能會陷入一葉障目、只見樹葉不見森林的思維模式中。
當我們意識到研究美術史需要有整體性眼光時,我們就會面臨如何進行整體性研究這一新問題。這種研究方法具體應該如何操作,它的可行性又如何?還是以墓葬藝術為例,當我們已知墓葬藝術包括器物與墓葬,我們可以通過器物的擺放位置、種類或顏色等,去思考它們對墓葬環境會產生怎樣的影響,可能寄托了墓葬主人一種什么樣的情感;反之通過對墓葬整體空間的考證,從而去探究它給其中的器物提供了怎樣的生存環境,與這些器物共同構成一個什么樣的空間效果。這兩種相反思考問題的角度有利于我們更加全面、更加辯證地去研究墓葬藝術,深入了解中國古人在那個時代的一些想法與觀念。因此,通過這個案例我們便得知這種運用整體性眼光研究美術史的辦法是切實有效的,它能幫助我們在把握大方向的同時不遺漏細節之處,能一方面豐富我們對從前不熟悉歷史的深入了解,另一方面也拓展了我們對美術史理論研究的思考深度。實際上當我們運用整體性眼光去看待和研究這類特殊性質的藝術時,也同樣是在對它們進行一種全新的定位。這種定位可以有效地幫助我們去發現以往我們曾忽略的、曾不以為然的一些重要資料,一定程度上發揮這類藝術作為某一種文化的實物證據的意義。因此,今后我們在研究美術史中的問題時,需要用更加整體全面的、聯系與發展的眼光去尋找適用于研究如墓葬藝術這種傳統美術史研究方法無法精確解釋研究的藝術種類,讓這類藝術在中國美術史的研究和教學中逐漸形成一個系統的專門領域,而不是一直被人忽略或是作為附屬品被注意。我們要盡可能去掌握處理和解釋這類藝術的一套系統的理論方法,以豐富我們對于此類藝術的理解與深入。
參考文獻
[1]巫鴻.美術史十議[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6.
[2]尚剛.中國工藝美術史新編[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3]郭軍營.21世紀中國美術史研究的回顧和展望[J].參花:下半月,2016(6):134.
[4]馮鳴陽.圖像學方法與美術史研究[J].數位時尚:新視覺藝術,2009(3):17-20.
[5]樊昌生.新世紀新輝煌—江西省文化廳舉辦"新世紀江西考古成果展"[J].南方文物,2009(4):1-6.
[6]鄭曉慧.為了永恒的"文化記憶"—談墓葬文化遺產的數字化[J].蘭州學刊,2009(2):124-126.
[7]楊嫣.論死生信仰中的古代墓葬藝術[J].美術大觀,2015(4):84-85.
[8]劉玉環.馬王堆漢墓遣策名物考[J].西南學刊,2012(1):248-255.
[9]倪潤安.北魏平城地區墓葬文化來源略論[J].西部考古,2011(00):291-309.
[10]盧蓉.關于閩南墓葬文化和墓碑考察—田野調查法的介入及意義[J].美與時代:中旬刊,2011(7):58-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