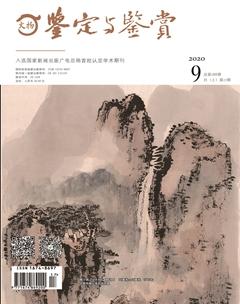海昏侯劉賀墓主棺實驗室考古發現細節公布
近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專家李存信發布了相關論文,進一步揭曉了海昏侯墓實驗室考古的各種不為人知的細節。據李存信介紹,外棺內遺存主要集中于外棺頭箱位置。在頭箱長約70厘米(橫向)、寬近50厘米的范圍內,上層出土一件制作工藝精良的漆木盒。漆木盒表面和側面均嵌有不同動物形狀的金箔飾片,受上方棺蓋重壓的影響,漆木盒被壓成平鋪狀,已完全破損變形。漆木盒下方出土了兩件玉璧,直徑分別為29厘米、20厘米,后者盛裝于上下可以扣合的木盒之中。底層出土有不同規格、數量各異的黃金制品,包括麟趾金、馬蹄金、金餅、金板等。
由于槨室倒塌形成的巨大壓力,內棺側板和端板被擠壓成破碎狀,散落于棺外周邊,且外形變化嚴重。棺內所有遺存被壓縮至厚約5厘米的空間內,多數遺存呈扁平狀,形狀出現扭曲,并且互相疊壓。由于埋藏環境及水土內含有較高的酸性物質,墓主人遺骸除牙齒外完全朽蝕。墓主腰間至腳端上方表層似保留著已經泥化的紡織物品。內棺棺蓋至底板的空間距離只有約5厘米,棺內遺存多數呈斷裂破碎狀。內棺南端頭箱部位出土有11件規格不一、大小不同且存在疊壓關系的漆木盒和一件青銅質長方形盒,均被內棺蓋板壓成扁平狀。
考古人員把內棺遺存分為四層進行提取。第一層遺存在內棺頭箱北側,為墓主人頭部,頭部上方覆蓋一層夾纻髹漆覆面(也稱溫明),覆面表層放置有兩件直徑各異、厚度不一的玉璧。墓主頸、胸、腰等部位出土規格各異的玉璧15件。第二層遺存在內棺南端,為墓主頭部范圍,將覆蓋于臉部的玉璧取出后,發現下方有墓主人的上下頜牙齒,牙齒保存狀況大體良好,具備一定的牢固程度。墓主頭部下方為一木枕,木枕已被壓成平板狀,表面髹褐色漆。木枕表面和側面鑲嵌有8枚素面玉飾,分別位于墓主頭部下方、前側面和左右兩端。在木枕兩端相互對稱的位置上,側立放置8件規格不一的乳丁紋玉璧和透雕玉環,但多數已斷裂破碎,并有部分缺失。墓主身體中部左側出土一件較完整的青銅質帶劍鞘玉具劍,右側出土一件鐵質帶劍鞘玉具劍,后者存在斷裂情況,劍鞘為木質夾纻髹漆,玉質的劍首、劍格、劍璏、劍珌雖有部分斷裂破碎,但基本保持完整形態。墓主腰間、腹部下端及身體兩側出土有多件玉質、瑪瑙質、琥珀質和角質的小型飾件。其腰間右側出土有一組串飾,包括玉質印章、鐵質書刀、韘形玉佩及兩件水晶飾件。第三層遺存為金縷編綴的琉璃席,四周有包邊,長198厘米、寬54厘米、厚約3厘米。其中包邊寬約3厘米,原厚度應與內側琉璃席片相近,部分已腐蝕,現存厚度約0.1厘米。包邊底層為植物纖維組成,中間層由不規則與無規律的金箔片和紅色彩繪互為鑲嵌點綴,表面則覆蓋一層云母片。云母片材質十分脆弱,多數已呈破碎狀,并有一定程度的缺失。琉璃席由縱向32片、橫向12片組成,每片長約6厘米、寬約4厘米。內棺第四層遺存為金餅。琉璃席片揭取后,其下是相對距離一致、規格相同的一組金餅。此層遺存由縱向20、橫向5合計為100枚的金餅組成,每枚金餅的直徑約6厘米,厚約1厘米,重量約250克,其重量差在1克之內。從金餅的外表觀察,其邊緣和底端部分非常光潔,底端中部區域向上略有凹陷,上部表層呈蜂窩形態。這種情況的存在與鑄造金餅的模具有關,主要原因應是模具與鑄造金屬液態之間的溫差及排氣不順暢。百枚金餅多數為素面,只有數枚于底端出現十分規律的“V”形符號,這是在模具加工時留下的印跡。另外,也有數枚金餅于鑄造完成后在底端光潔處刻有數量不一的文字。(來源:節選自中國考古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