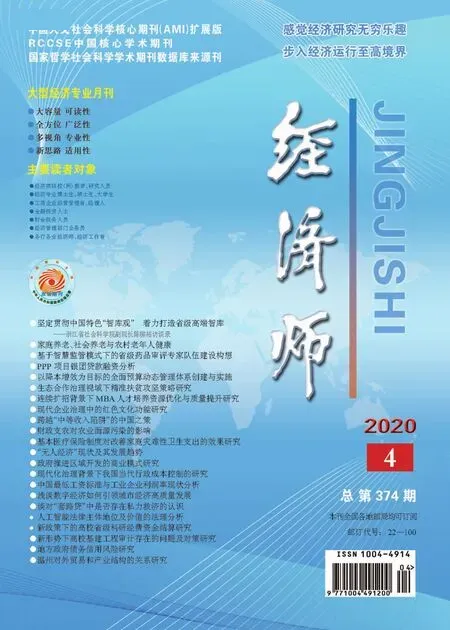共享經濟下勞動關系的認定
●陳雅宜
一、案件導入與裁判分析
(一)案例一
1.案件基本事實。原告張琦與被告上海樂快信息技術有限公司勞動爭議案,該案被稱作共享經濟第一案。樂快公司開發了一個名為“好廚師”的軟件,用戶下載該APP 后就可以在平臺預定廚師上門服務。張琦于2015年5月入職樂快公司,并成功注冊為“好廚師”APP 的廚師。樂快公司于2015年改為網上派單,每月不設底薪,按接單數量計薪,張琦不同意,公司于同年10月突然違法開除了張琦。
張琦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法院確認雙方存在勞動關系;樂快公司支付其解除勞工關系經濟補償金、未簽訂勞動合同雙倍工資并為其補繳社會保險等。樂快公司辯稱:根據廚師入職簽訂的《合作協議》,可以直接認定雙方僅為對等合作關系。
2.案件分析。本案最大的爭議焦點為: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勞動關系是否成立屬法定范疇,盡管樂快公司辯稱《合作協議》規定雙方為商務合作,但法官應當根據本案實際情況對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予以認定。
勞動保障部《關于確立勞動關系有關事項的通知》中規定勞動關系成立需符合以下三個標準:(1)用人單位和勞動者符合法律、法規規定的主體資格;(2)用人單位依法制定的各項勞動規章制度適用于勞動者,勞動者受用人單位的勞動管理,從事用人單位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3)勞動者提供的勞動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
根據“三標準”說,勞動關系的成立包含用人單位主體資格、勞動行為給付義務和勞動者業務組成三個要素。本案中,首先,樂快公司和張琦都符合法律規定的勞務主體資格;其次,張琦由公司指派工作,說明其在平臺的控制下進行勞動,報酬由“好廚師”平臺給付而非直接由APP 用戶支付,這屬于有報酬的勞務行為;最后,張琦提供的廚藝技能服務又是“好廚師”平臺的主營業務,是用人單位業務的組成部分。因此,張琦與樂快公司實質上建立勞動關系,雙方所簽《合作協議》實際亦系履行勞動關系的協議。
(二)案例二
1.案件基本事實。原告劉慧于2014年10月入職五八到家公司,擔任美甲師,雙方未簽訂勞動合同,而是簽訂了《五八到家信息服務協議》。2015年8月,劉慧向五八到家公司郵寄送達了解除勞動關系通知書,以五八到家公司未依法繳納社會保險、未足額支付勞動報酬為由,提出解除雙方勞動關系。
劉慧向一審法院起訴:請求法院確認雙方存在勞動關系,五八到家公司支付未簽訂勞動合同雙倍工資差額及解除勞動關系經濟補償金。五八到家公司辯稱:根據雙方簽訂的《五八到家信息服務協議》,五八到家公司不是一家提供美甲服務的美甲網店,作為平臺,公司的業務范圍決定了與原告劉慧只能是合作關系;勞務費由客戶直接支付給劉慧,因此劉慧的勞務行為不屬于從事五八到家公司安排的有報酬的勞動。
2.案件分析。本案最大的爭議焦點為:雙方是否存在勞動關系。盡管原被告雙方已經簽訂《58 信息服務合同》,但雙方是否構成勞動關系法院仍需根據“三標準”進行實質審查。
本案中,第一,雙方簽訂了《58 到家服務協議》中,平臺沒有規定服務的方式和流程,劉慧提供的證據無法確定其受到五八到家公司的勞動管理;第二,五八到家公司只向劉慧提供客戶信息并收取一定的信息服務費用,也沒有指派她特定的工作并支付其報酬;第三,五八到家公司員工主要從事移動互聯網平臺的運營和技術支持,它起到的僅僅是作為一個平臺溝通需求和供給的作用,劉慧提供的美甲服務并不屬于五八到家公司的經營范疇。因此,劉慧于五八到家公司之間并未構成勞務關系,雙方沒有任何人身或組織上的從屬性。
對比“樂快公司”和“五八到家公司”兩個案例,同樣是平臺與服務者的勞動關系認定問題,同樣是按照勞動關系認定“三標準”來判斷,結果卻截然不同。“實質審查”的運用看似涵蓋了各類勞動關系的認定,但在司法實踐中,案件事實不同,互聯網技術發展快,當事人提交證據不全等因素都將影響到“三標準”的合理判斷,法院在面對新案件時往往需要重新權衡雙方權益。共享經濟之下,賣家和平臺之間是一種超越現有勞動法所設的新型勞動關系,如何認定勞動關系將是今后司法審判中一個重要任務。
二、共享經濟下勞動關系的認定
(一)要素評價認定標準
在互聯網迅猛發展趨勢下,共享經濟繼續保持高速增長,平臺和服務者之間的勞動關系發生變化,主要是兩種趨勢:一是傳統企業的勞動關系轉向新型合作關系。勞動力市場正轉向人力資本市場,勞動合同將來也可能不復存在或減少。二是互聯網經濟并未改變勞動關系,用工關系仍是勞動關系或者雇傭關系。①共享經濟下,無論是合作關系還是雇傭關系都擁有相應的存在空間,與新興的合作關系相比,雇傭關系顯然更為普遍。在美國,加州法院判決的Uber 案引發了關于共享經濟下員工法律地位問題的討論。根據加州法院為認定是否構成勞動關系所創設的“要素評價”體系,法官對該案法律問題詳細分析后認為雙方之間勞動關系成立。如果說我國勞動關系的標準是抽象概括式,美國法院更傾向于通過具體列舉式來規范勞動關系的邊界。如從用人單位對勞動者的控制程度、主體雙方資本技術及勞務投資的比例、單位對員工工資福利的掌控水平、工作的可持續性、工人技能施展路徑、工人工作是否為單位主營業務范圍等來進行判斷。②“三標準”說具備普適性優勢,而在我國共享經濟浪潮中,強實用性的“要素評價”體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現有勞動關系認定方式的不足。
平臺與服務者之間是否形成勞動關系,首先就應當確定平臺性質。平臺一般分為三種類型:一是交易輔助方,不承擔任何責任;二是間接運營方,與賣家一同對買家承擔責任;三是直接運營方,可單獨對買家承擔責任。依據平臺對交易的強弱控制差異,以判斷該平臺是直接運營方還是交易輔助方。根據“要素評價”體系,平臺對交易的控制大致如下:
1.平臺對交易達成的控制。共享經濟下的數字平臺,破除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獨特的運行方式賦予它獨有的功能。一是展示功能。好的平臺吸引大量買家用戶和賣家用戶,賣方發布商品或者服務的相關介紹,買方可以預先獲知對方的大概情況;二是供需功能。平臺提供豐富的信息資源,需方通過詳情簡介可以快速匹配最合適的供方;三是評價功能。接受服務后用戶可以自行評論,成功的交易大部分通過良好的商品評論達成,良性的平臺也注重服務方和被服務方的自主選擇權,與此同時平臺也可以根據用戶反饋構建大數據結構。
2.平臺對交易價格的控制。目前,我們常見的一些平臺或多或少控制著定價權,比如滴滴打車。而一些輔助性的平臺,比如58 到家,咸魚等,則預留了買賣雙方協商價格的空間,只提供或者甚至不提供價格模板。如果平臺對員工的工資福利等的掌控水平過高,那么雙方可能被認為已經構成了勞動關系。
3.平臺對交易履行的控制。規范雙方履行行為是平臺本身的信譽功能。一方面,平臺作為雙方交易的中介,創造可信的交易環境十分重要,實際上這是為交易者的錢貨提供擔保,使得交易安全進行;另一方面,一個輔助經營的平臺,如果服務者提供的服務覆蓋平臺的主營業務,工作的內容、程序和給付方式都受到平臺指派,那么雙方實際上則構成了勞動雇傭關系。
4.平臺對違約責任的控制。為了規制買賣雙方,使其不能隨意取消訂單或者惡意影響交易,平臺設立違約責任是一種對三方都有利的行為。平臺對賣家有違約處罰權,平臺可在賣家違約時扣除其信用值。平臺對買家也有違約處罰權,如司機接單后乘客取消訂單,平臺可以扣除買家一定的費用。但是平臺本身不具有對服務者的任意解雇權,平臺對供求雙方的違約處罰權應當控制在合理、適當的范圍之內。
(二)設立新型勞動關系
目前,共享經濟下的勞動關系是一種超越勞動法規制范圍內的新型關系,這種新型勞動關系正逐漸趨于彈性化、多元化和虛擬化。我們討論它是勞動關系還是合作關系之外,還可以認為它是一種類勞動關系。類勞動關系概念首次出現在國際勞動組織出臺的《雇傭關系報告》中。這種用工形式在人格從屬性上要弱于勞動關系,而在經濟從屬性上又要強于合作關系,政府若依舊采取傳統的勞動關系思維,有時無法處理共享經濟中的各種問題。這類群體雖然在表面上看起來比較像是自雇型勞動者,時間自由,工作場地也不受限,但實質上在經濟來源方面比較依賴于平臺以及平臺提供的客戶群體。③或許勞動法可以構建該新型勞動關系,從新對勞動者權益和平臺利益進行平衡式的保護。
三、結語
國家支持并鼓勵共享經濟的蓬勃發展,但平臺與勞動者的矛盾逐漸暴露出來。如果法院在處理與以上兩個案例相似的案件中,多傾向于認定平臺與服務者存在正式的勞動關系,勢必會對整個共享經濟產生影響。正如五八到家公司案中被告辯稱的那樣:“本案法律關系的認定將對移動互聯網預約上門服務平臺,乃至O2O 商業模式具有深遠而重大影響。”因此,法院的判決不能僅僅只看到判決當下的勞動者保護效用,適應國家共享經濟政策方向對社會經濟整體的發展則更為有利。與之對應的,我們看到美國加州Uber 案件,討論至今,原被告雙方仍然在圍繞程序性問題進行博弈,法院尚未對法律關系類型等實體性問題作出判決。主審法官用極強的邏輯和技巧充分論證了Uber 與司機之間可能存在勞動關系,但又直接說明認定勞動關系屬于實質性事項,應該由陪審團負責。這正說明了共享經濟下的勞動關系的認定目前仍處于灰色地帶,法官的判決可能直接對共享經濟今后的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勞動關系與否的認定在今后將面臨更多利益平衡的選擇。
注釋:
①常凱.雇傭還是合作,共享經濟依賴何種用工關系[J].人力資源,2016(11):38- 39
②袁文全,徐新鵬.共享經濟視閾下隱蔽雇傭關系的法律規制[J]. 政法論壇,2018(1):119- 130
③蓋建華.共享經濟下“類勞動者”法律主體的制度設計.改革,2018(4):102- 1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