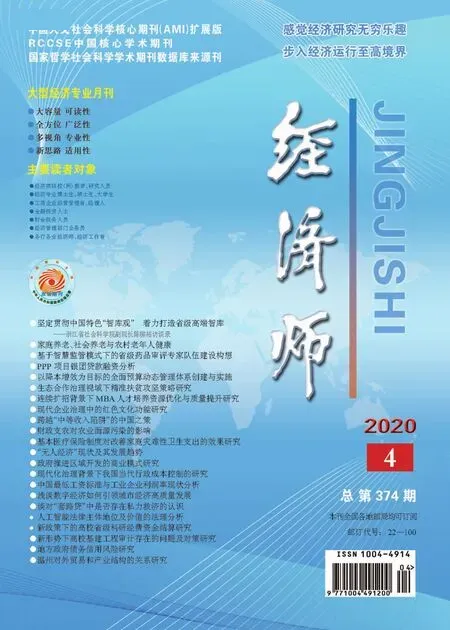大學治理中存在的問題及根源分析
●高明燁
20 世紀90年代以來,我國高等教育事業(yè)迅猛發(fā)展,國家對于高等教育給予各方面的支持。但是高校教育質量沒有顯著提升、公共資源使用效率低下,受到社會輿論的關注和質疑。同時,從科研到學術、從基建到招生,高校學術腐敗、經(jīng)濟腐敗案件頻見報端,牽涉的人員范圍涉及學校方方面面,腐敗行為形形色色。高校會發(fā)生這些問題,說到底是大學治理存在著比較嚴重的問題。
一、大學治理概念及內涵
1995年,全球治理委員會中研究報告《我們的全球伙伴關系》將“治理”的定義為: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物的諸多方法的總和,是使相互沖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調和并且采取聯(lián)合行動的持續(xù)的過程。而大學治理可以表述為:一整套相互協(xié)調的、正式或非正式的動態(tài)的機制,用來協(xié)調現(xiàn)代大學各個利益相關者包括政府、學校、教師、學生等之間的關系,使得現(xiàn)代大學價值最大化,以有效地為社會培養(yǎng)所需要的人才。其本質上是對于大學因存在多種利益關系而形成的組織特性,以及其相互作用機理的研究。按照大學各個利益相關者與大學本身的關系特征,可將大學治理結構分為大學外部治理結構和大學內部治理結構,而內部治理結構對于協(xié)調大學內部利益相關者進行決策權行使以及利益分配方面,更能直接、完整地影響高校治理效能和辦學效益,是高校提高治理能力的重點。
二、我國大學治理推進進程
我國的大學治理可以追溯到民國時期,20 世紀20~30年代,以蔡元培為代表的大學校長們對中國大學制度進行了積極的探索,并試圖建立起教授治校等現(xiàn)代的大學治理體系,但在當時的歷史背景下,有關理論探討和實踐探索未能進一步向前邁進。1917年,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在此之前,北京大學具有典型的科層化組織結構,衙門作風和官僚積習嚴重,學問研究之風低迷。蔡元培對此進行大力整頓,打破原有的集權管理,將校長權力逐步分化,教授共享“治校權力”。這種民主管理思想,有力地調動了教師的工作積極性,使北京大學轉變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爆發(fā)了“五四”運動后成為中國馬克思主義的傳播陣地。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大學治理大致經(jīng)歷了以下幾個進程:
(一) 新中國成立后30 多年間(1949- 1977年)
新中國成立后的30 多年間,我國大學治理是以政府為主導,在特殊的歷史時期,更多強調的是完成政治使命、滿足國家需要,中央和地方對大學治理權力關系分配是集權與分權交替進行,大學在制定政策、配置資源、規(guī)劃建設、人事制度等方面都由政府制定。新中國成立初期,對民國時期遺留的高等院校先接管、接收、接辦再逐步改造,形成由國家支配的大學治理管理體系。宏觀管理體制上,大部分高校歸地方管理,權力下放卻造成了教育質量下降、教育秩序也比較混亂,后于1963年中央重新收回高等教育的管理權。
(二) 改革開放后30 多年間(1978- 2009年)
這30 多年是我國大學治理恢復重建和改革發(fā)展時期,圍繞著大學辦學的自主權限以及高校治理架構來開展,積極探索“校長負責制”以及簡政放權、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等,199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從法律上規(guī)定了高校的領導體制及行為主體權責,肯定了高校部分辦學自主權。分為兩個階段:
1978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我國高等教育事業(yè)開始恢復,大學治理結構再次回到“中央統(tǒng)一領導、地方分級管理”的集權狀態(tài)。此后,上海部分高校領導集體呼吁給予高校一點自主權,這成為相當長時間內大學治理變革的關鍵點,同時逐步實行校長負責制的嘗試,后定為“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
黨的十四大后,我國正式進入改革開放新階段。1993年《中國教育改革與發(fā)展綱要》中提出擴大高校辦學自權,使高校成為面向社會自主辦學的法人實體,政府對學校轉為宏觀管理。但未能落實辦學自主權。直到199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高等教育法》的頒布為我國的大學治理變革引入“法制因素”,保障了“法人治理”。
(三)全面深化改革時期(2010年至今)
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建立以及社會主義法制體系的逐步形成,我國大學治理變革中有了“市場因素”和“法制因素”,但長期形成的弊端難以使大學治理短時間內達到目標。《國家中長期教育改革和發(fā)展規(guī)劃綱要(2010- 2020年)》中提出要建設“依法辦學、自主管理、民主監(jiān)督、社會參與的現(xiàn)代學校制度,構建政府、學校、社會之間新型關系”“完善中國特色現(xiàn)代大學制度”“落實和擴大學校辦學自主權”“完善治理結構”等內容。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大學治理改革是國家治理改革的重要部分之一,這將成為我國大學治理變革的關鍵時期,高等教育理念、體制機制將進一步發(fā)展完善。
三、我國大學治理存在問題及根源分析
探索建立現(xiàn)代大學制度是當前高等教育改革的難點,其中推進大學治理是關鍵,尤其是大學內部治理的變革,更加有力地推動大學由內到外、自下向上發(fā)展和前進。但當前,大學治理還存在很多問題,本文著重從內部治理角度進行分析。
(一)行政權力官僚化傾向嚴重
一方面,政府對大學采取的是行政化的治理方式,高校主要由政府興辦,高校的運行管理受到政府部門的直接領導,高校領導由政府任命,招生規(guī)模及專業(yè)設置、教師編制及教學評估等受制于政府教育管理部門,經(jīng)費也靠政府撥款,造成了高校人、財、物等相關權力都掌握在政府手中,高校被政府行政力量牢牢控制;另一方面,中國大學的管理機制也造成了大學本身管理的類政府化和官僚化的特性,本應是教育、科研機構的高校,卻按照行政機關模式設置機構,以及相關人員給予相應的行政級別,相應的薪資、待遇也按相應行政級別配給,行政權力占有和支配資源,本應作為學術召集人的院長、系主任等,成為行政體系中的領導干部,其手中掌握著教學成果評價、科研項目評審甚至是教師職稱評定等,不可避免地看到行政權力干預教學、科研、學術的影子,學術權威依附于行政權威,使得大學權力觀念畸形發(fā)展,行政權力過分強化,學術問題也用慣用的行政化思維去解決和治理。
(二)內部組織體系結構不合理
大學的組織結構就是“大學組織內部的結構要素在外部環(huán)境諸要素的作用下組成的具有一定關系的組織形式。”我國大學都是采取校、院、系直線職能式組織結構,這種行政系統(tǒng)科層式體制不合適用來管理大學,難以科學劃分三個管理層次的責、權、利;大學內部組織體系結構幾乎照搬行政機構,龐大臃腫、人員冗余,容易造成人浮于事、效率低下;大學組織體系缺乏系統(tǒng)規(guī)劃和頂層設計,機構各自為政,內部規(guī)章制度不夠統(tǒng)一及系統(tǒng),“碎片化”現(xiàn)象嚴重;行政機構與學術組織之間權責不明確、層次不清晰,學術組織常常被泛化為行政機構。
(三)決策權力分配不科學
大學決策權力主要包括政治權力、行政權力、學術權力、民主權力。政治的導向指引教育的方向,政治權力保障黨的教育方針的貫徹落實;行政權力與學術權力是一對基本矛盾,兩者之間要平衡協(xié)調;民主權力是是高校師生員工表達利益訴求、參與學校民主管理的權力,也是保證政治權力、行政權力、學術權力平衡運行的基礎。目前,大學決策權力分配主要存在的問題是:政治權力異化,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但往往過分強調政治權力,政治權力統(tǒng)領行政權力、學術權力及民主權力;行政權力泛化,過于集中于行政系統(tǒng),各級“領導”以學術權威、學科帶頭人、學術骨干、“雙肩挑”教授等雙重身份參與學術事務,以行政思維處理學術決策,甚至行政手段干涉學術資源分配;學術權力虛化,學校權力機構往往作為行政的代言或直接學術機構行政化,學術權力被嚴重淡化;民主權力弱化,教代會選舉的代表其參與民主管理及監(jiān)督的選舉權及投票權常常在現(xiàn)實中被形式化和過程化,沒有真正發(fā)其民主權力的作用。
(四)大學運行監(jiān)督機制缺位
對大學運行的監(jiān)督按來源可以分為外部監(jiān)督和內部監(jiān)督,外部監(jiān)督主要有上級教育主管部門監(jiān)督、上級紀檢監(jiān)察審計部門監(jiān)督、外部輿論監(jiān)督等,內部監(jiān)督主要有學校黨委監(jiān)督、學校紀委監(jiān)督、內部審計監(jiān)督、教職工代表大會及師生員工監(jiān)督等。目前,對高校運行的監(jiān)督機制不足以滿足現(xiàn)代大學制度下的制約及監(jiān)督要求,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外部監(jiān)督的缺位,教育主管部門、上級紀檢監(jiān)察審計部門等管轄單位多,監(jiān)督范圍廣,監(jiān)督手段和力量受限,難以對所有高校有面面俱到的監(jiān)督,多是以下發(fā)文件、召集會議等方式布置自檢,部分抽查;另一方面,大學內部監(jiān)督的缺失,缺乏主動出擊的動力機制,內部審計監(jiān)督不受重視,且人員力量不足難以滿足工作需要,員工的制約和監(jiān)督機制缺失,沒有參與監(jiān)督的平臺,監(jiān)督手段匱乏。
四、高校治理存在問題的根源分析
大學治理不是一個抽象的理論,我國的高校治理也是特定的歷史和時代的產(chǎn)物。上述高校治理存在的問題的根源:一是受我國傳統(tǒng)文化影響,形成政府包辦一切的觀念,且高校領導任用方式的影響,由政府任命,并很大程度上是作為官員的概念來任命,甚至不懂教育的黨政機關領導被提拔任命為校長,這就容易導致高校過度行政化;二是政府對大學實行以行政權力為主的管理,權力占有和支配資源;三是新中國成立后,大學與科學院分離,大學的學術力量被嚴重削弱,學術權力在大學內部被邊緣化;四是大學章程建設滯后,未能理順大學的基本治理結構,未能構建和平衡好行政權力、學術權力與民主權力的關系,大學運行規(guī)章制度不健全,且外部監(jiān)督不得力、內部監(jiān)督不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