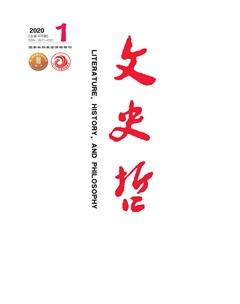論中國古代文獻傳統的歷史獨特性
趙益
摘要:中西文獻傳統沒有高下之分,只有特色不同。基于中西比較的視野考察中國古代文獻,可以發現其歷史特色主要體現在相互關聯的三個方面:第一是具有獨特的連續性內涵,其中最重要的是書寫系統獨一無二,文獻書面語一以貫之,從而使文獻成為文化連續的核心因素;第二是文獻整體在各個方面保持穩定,始終遵循著其內在規律發展演化,反映出中國思想原則對文獻發展的決定性影響;第三是“印刷資本主義”晚至近代方才出現,中國古代文獻主要是以精英文獻為主,通俗文獻僅扮演溝通大小傳統的角色,二者合力,加強了古代中國“古典共同體”的持續穩固。
關鍵詞:中國古代文獻;書籍;印刷術;精英文化;中國文明;圖書館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20.01.09
近現代以來吾人重新反思中國歷史上的文化成就,其他方面的看法或不盡相同,但在文獻方面,推重中國為世界范圍內最為杰出的“文獻之邦”,則幾乎眾口一辭。早自20世紀30年代鄭鶴聲、鄭鶴春編撰首部《中國文獻學概要》時即有日:“中國文化之完備,世界各國殆莫之京,此為中國文明之特色,即典籍之完美是也。”此后類似論述,層出不窮。這種總體評價當然并無錯誤,中國古代紙與印刷術的發明,早已被公認為是推動人類文明重大跨越的不朽貢獻;文獻的書寫、載籍、印刷、制作、生產與流通等各個方面的成就,也確實非同凡響。但是,正如不同文化既并非單線進化的階段的不同,更沒有高低貴賤一樣,以中國為代表的東方文明和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文明各自所擁有的文獻傳統,也不應有孰優孰劣的評判。任何一種文獻傳統都有其獨特的歷史成就、文化內涵和社會功能,機械的、簡單的是非比較不僅會導致對“他者”的忽視或誤讀,更重要的是使“自我”失去了反觀自身的合理性基礎。
因此,對中國文獻傳統歷史成就的獨特性必須予以認真的審視。否則,任何推重不僅會因缺乏理據而逐漸流為空泛的贊許,甚至會出現錯誤。徹底弄清中國古代文獻成就的具體表現、復雜內涵特別是個性特點,遠比單純的溢美重要得多。只有這樣,才能使中國作為“文獻之邦”的立論獲得牢固的基石,同時也能使從文獻傳統中探知中國文化的觀照取得真正的收獲。而對任何事物予以認真的審視,最重要的是需要采取比前有研究更加合理的觀照方法。有鑒于此,本文即嘗試從中西比較的角度,就中國文獻傳統的歷史特殊性此一問題作出自己的思考,敬乞海內外方家教正。
問題回顧與反思
毋庸諱言,在對中國古代文獻歷史成就這一問題上,以往的認識或多或少存在著一些誤區,最為主要的就是草率地判定了一些“基本事實”,并以這些實際上是不盡準確的事實推出了兩大結論:第一是中國現存古典文獻數量龐大,放眼世界唯我獨尊;第二是中國古代文獻歷史悠久,水平發達遠邁西方。
這兩大結論都極欠妥當。
首先看現存數量。早先有楊家駱1946年統計為10萬種,胡道靜1961年估計為7萬至8萬種;此后吳楓的估計,認為“不能少于八萬種”(不包括出土文獻和非漢文文獻);吳氏之后,王紹曾得出的數字是9.5萬種,與此前估計相差不遠。比較突出的是曹之的估計,認為整體線裝古籍總數“當不少于十五萬種”,但其所依據的數據重復太多。最近《中國古籍總目》出版,經部序次號共編得15144(含本部叢書177;叢書子目不編號),史部得66502(含本部叢書10),子部得38298(含本部叢書91),集部得54889,叢部得2274(子目不編號),合計為177107。按照《中國古籍總目》的編纂體例,理論上序次號應大于實際著錄種數(但二者相差不會太多)。具體言之,因為《中國古籍總目》的立目原則包含了這樣兩條:“一書經重編后傳抄刊刻,內容有所增損,卷數隨之變化,即不再作相同品種立目”,“一書正文及其傳箋、注釋、音義、考訂等以不同形式合編,即作為不同品種立目”,故存在著重復計算不同版本以及同書異名等情況。另外,《中國古籍總目》也收錄了很多檔案型文獻如地圖、拓片、文書等。綜合來看,盡管《中國古籍總目》遺漏的可以歸入“四部”范疇的書籍固然不多,但各種通俗文獻、民間抄本(特別是民間科儀、寶卷、唱本等)的數量目前仍然很難估量,再加上《中國古籍總目》的重復無法得到精確的統計,因此中國現存各類古籍數量究竟多少仍是一個謎團,20萬種左右只是一個關于傳統意義上的“書冊”文獻數量的推測。
這個數量固然十分龐大,但歐洲古代書籍的遺存種數有過之而無不及。早先據費夫賀(LucienFebvre)、馬爾坦(Henri-Jean Martin)的估計,公元1500年之前問世、如今有案可考的印刷書,版本多達三萬到三萬五千種(版本種數大于書籍種數),總發行量約當一千五百萬到兩千萬冊;僅1450年到1500年出版印制的書籍保存下來的就有一萬到一萬五千種之多;整個16世紀印制的書籍,大約有15萬到20萬種不同的版本,估計約有1.5到2億冊@。最新的一個研究是推算出西歐從6世紀到15世紀每個世紀所產生的抄本分別為13552、10639、43702、201742、135637、212030、768721、1761951、2746951、4999161(件);從1454到1800每五十年的印本書產出量分別為12589、79017、138427、200906、331035、355073、628801(種或版)。盡管這些并非是現有遺存數量,其單位“件”“種或版”也遠遠多于中國所謂“種”,同時其具體測算數字亦有可商之處,但仍然是非常能夠說明問題的。
歐洲18世紀以后印刷出版以及遺存圖書的種數是此前的數倍。19世紀以后更為可觀,1840年以后英國、法國、德國的年平均出版書籍就有萬冊之多,19世紀一百年整個歐洲的書籍如果只保留其中四分之一的數量,也要遠遠超過20萬種。總合各種相關數據可以得出,現存1900年以前歐洲圖書的種數,不會低于50萬種。
其次看歷史悠久的程度和不同歷史時期的發展水平。中國古代文獻在總體數量上既不存在優勢,在文獻歷史的悠久程度和發展水平方面同樣也無法占據絕對上風。
中國的書寫起源甚早,書寫與載籍二位一體,即使夏代“有冊有典”是一種傳說,文獻傳統至少也要從甲骨卜辭記錄算起。西周時期除了青銅銘文之外,應該已經出現了簡牘;降至春秋,可供閱讀的簡冊書籍已經較為豐富。但此類文獻仍多由國家擁有,直至戰國時期,圖書的生產、制作和貿易并不發達。
既然有書籍,就肯定有買賣,這一點并無疑問,但沒有證據表明先秦時代出現了專門書店。西漢時期同樣如此,揚雄《法言·吾子》所謂“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之“書肆”,應是“書籍陳列”之義,并非是指專門出售圖書的市肆。除此以外,古典文獻中沒有任何關于書店的反映。至范曄《后漢書》方有很多關于在市場上買賣圖書的記敘,如《王充傳》“充少孤,鄉里稱孝。后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眾流百家之言”,《荀悅傳》“家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沈靜,美姿容,尤好著述”等,但也很難說就是東漢的真實情況。
而希臘在公元前5世紀后期就出現了圖書業,以尼羅河三角洲紙草為載體的形制雖然所能承載的文字數量較少,但一卷圖書的最低容量也能應乎撰錄、閱讀的需要,同時也并非不夠堅固耐用。西方古典學者研究認為,在蘇格拉底和阿里斯托芬的年代,詩歌、歷史以及其他作品已得到廣泛傳布,若非圖書以商業化的規模生產,則此種傳播斷無可能;羅馬時期的圖書業則較希臘更為發達,至早在西塞羅和卡圖盧斯時代便已有書店的存在。
中國戰國時期的惠子“有書五車”,稷下學宮也有相當的著述和藏書,但總體上除周室及諸侯國宮廷外,先秦時期的私人藏書并不常見,清人阮元認為“古人簡策繁重,以口耳相傳者多,以目相傳者少。……古人簡策,在國有之,私家已少,何況民間?是以一師有竹帛,而百弟子口傳之”,所言甚是。希臘公元前5世紀末顯然也已經存在私人藏書,到前4世紀亞里士多德已經收藏了大量的圖書,呂克昂學園和阿卡德米學園都已具備圖書館形式。中國在秦代經歷了一次焚書,漢代立即有了恢復,在公元前后劉向劉歆整理國家藏書時至少擁有一萬五千卷圖書;而西方肇始于托勒密一世的著名的亞歷山大圖書館在公元前47年一部分館藏毀于戰火以前,有一種說法是全部藏書多達70萬卷。
羅馬的私人圖書館首先發展,圖書館似已成為羅馬名流府邸的必要部分;阿西尼烏斯·波利奧于公元前39年創辦了羅馬第一座公立圖書館。根據公元350年的一個地區普查,羅馬曾有28座公共圖書館。各行省亦有公共藏書,即使小城鎮也不例外。中國古代先秦時期“惟官有書”,這種情況在相當長的時期里沒有較大的改觀。唐以降私人藏書固然較為發達,但真正勃興仍在印刷術發明以后,且多以秘藏性質的藏書樓為主。中國直到封建時代晚期才出現面向大眾的公共圖書館。
綜上可知,4世紀以前中國文獻書籍發展的水平并不高于希臘、羅馬。4世紀以后直至15世紀這近一千年的時間中,中國的書籍編纂生產方具有一定的優勢(據前文所引Eltjo Buringh和Jan Lu-iten van Zanden的研究,11世紀以后的優勢已十分微弱),但這種優勢在歐洲印刷術興起而導致的革命面前一下子就變得無足輕重了。歐洲從15世紀“谷騰堡革命”以后即迎頭趕上,雖然同期中國明代也出現了商業化出版,但歐洲仍然取得了壓倒性的勝利:16世紀歐洲最重要的印刷出版中心威尼斯擁有近500家印刷工廠,共印制書籍近1800萬余冊,僅書商吉奧利多(Gabriel Giolito)一家就出版了約850種書籍。威尼斯的規模遠超明代16世紀幾大出版中心建陽、杭州、南京、蘇州、徽州出版數量的總和;明代任何一個商業書坊、家族、藩府也難望威尼斯書商吉奧利多之項背。明代是中國商業出版真正開始的時代,由于刊刻之易,導致著書之易,黃虞稷《千頃堂書目》著錄明代著作12000余種,其著錄雖不能確證是實見其書,但確實為當時著錄明人著作最多者。即使算上大量的通俗文獻如科舉書、醫書、通俗文學、宗教文獻等,整個明代出版書籍至多也只有2萬種左右,遠遠落后于同時代的西方。
清代圖書出版印刷水平有持續的提高,但雕版仍為主流,數量并不巨大;晚清新技術傳人后,出版印刷數量方開始陡增。總其一代所編纂的圖書,大約在22萬種以上,現存大約在16萬種左右,其中絕大部分為清代晚期出版物。這一數字遠遠無法與18至19世紀的歐洲相提并論,因為從18世紀始特別是已進人工業化的19世紀,歐洲書籍(尚不包括期刊、報紙)的出版種數將是此前數量的數倍,而16世紀到18世紀歐洲書籍的每種平均印刷量已經穩定在千余冊左右,遠遠超過平均每種每版印刷100部的雕版實際印刷數量。以往曾經有過的一種所謂“1750年以前中國生產的書籍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加起來的總數還要多”的說法,已經被證明是一個明顯的錯誤。
歐洲圖書生產的發展、社會的進步再加上悠久的圖書館傳統,圖書館藏書量這一代表圖書出版、知識分享和整體社會發展水平的指數從近代以來即大大超過中國。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總結認為:從大約公元1500年起,中國圖書館在藏書數量上開始被南歐的圖書館趕上,公元1600年后被北歐的圖書館完全超越,到1700年以后,又被北美的圖書館超越;19世紀期間,隨著歐洲和美洲藏書量多達100萬部的大型國家圖書館,以及如羅阿克頓圖書館這樣有將近7萬部藏書的私人圖書館的出現,中西方圖書館藏書量的差距進一步擴大。
上述簡單的舉例分析無疑就使兩大結論的準確性和合理性已經發生了動搖。這種動搖不可避免地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中國文獻傳統的歷史成就究竟體現在哪些方面?或者說,既然中西文獻傳統不存在優劣之分,中國文獻的歷史成就到底有哪些獨特之相?
連續性
中國文明表現出一種非凡的連續性,已經得到當代學術研究的公認。中國文獻傳統同樣如此,連續性亦非常明顯。但文明發展意義上的“連續性”評價標準不可簡單移植至文獻傳統之上,因為文明的連續性主要是指早期文明或未衰落,或未發生嚴重的斷裂和轉變。除中國黃河文明外,其他同時先后發生的原生文明基本都出現了為次生文明所覆蓋的情況,而世界上唯一的兩個文獻傳統——西歐和中國——都沒有出現像早期文明那樣的斷裂、轉變情形。因此,中西比較視野下文獻的連續性,應主要體現在各自不同的“連續性特色”和“連續性程度”之上。
顯然,中國文獻的“連續性”在特色和程度上都具有獨特的內涵。
首先,中國文獻在發展階段上沒有明顯的中輟和低潮期,即使歷經災荒、戰爭、改朝換代的政治動蕩以及外族的入侵,文獻傳統不僅沒有絲毫中斷,而且在歷經摧毀下一次又一次地得到恢復。
盡管文獻存佚并不主要取決于外部因素,但天災人禍對文獻物質因素的影響也不可忽視。中國自古戰亂頻仍,古人常常感慨文獻時遭厄運,漢以后批判暴秦燔書已史不絕書,隋牛弘又有“五厄”之論,明胡應麟接續而成“十厄”之說,可謂最詳總結。問題在于,十厄之后,實亦伴隨十次恢復,考諸史記,斑斑可證。胡應麟亦同時指出雖有“大厄之會”,亦有“盛聚之時”:“春秋也、西漢也、蕭梁也、隋文也、開元也、太和也、慶歷也、淳熙也,皆盛聚之時也”,確是非常睿智的見解,我們不能只注意到了文獻遭遇天災人禍的不幸,而忽略災厄之后必有恢復的事實。近人陳登原撰《古今典籍聚散考》有日:“綜計是卷所記,其最明顯之現象,即在承平之時,公家私人均致力于搜羅巖穴,博藏深弆;及其亂世,則又倉皇棄之于兵匪之手。如潮汐然,忽高忽低,而終于散失消沉。”陳氏所謂“如潮汐然,忽高忽低”無疑是恰當的總結,而“終于散失消沉”的結論則并不正確,中國古代文獻雖然不免散亡,但總體上仍保持一種強大的連續性。
在西方,羅馬帝國的覆滅和宗教的籠罩使6至14世紀明顯成為文獻發展的低潮。“無數珍貴的藏書直到公元5世紀仍有存留,而后消失得無影無蹤。日耳曼部落的入侵將它們埋葬,猝死的古代文化成了它們的墳場。”所剩的書籍生產幾乎都與宗教有關,而且書籍稀少,甚至連教士也很少能有閱讀的機會。這一情況直至10到12世紀才略有好轉,至16世紀谷騰堡印刷革命后才出現高潮并延續至今日。毫無疑問,中國文獻傳統中顯然不存在這種幾乎貫穿整個中世紀的極其漫長的文獻衰微,當然也沒有類似于歐洲文藝復興那樣性質的文獻重振。
其次,中國文獻書面語言一以貫之,自金文記錄、《尚書》《春秋》《左傳》《國語》及先秦諸子等經典奠定的極為成熟的書面語作為唯一的“文獻語言”傳承至今,三千年來連續未斷。此一特殊之處尤為顯明,其根源肇自于中國書寫的發明并發展成語素或語標文字(Morphemic or logographic writing)后,出于發明這種書寫系統的文明所擁有的獨一無二性和強大影響力,使這種已經非常成熟的文字(甲骨文)就已經成為“書面語”的書寫而非“日常言語”的書寫。書面語就是借助日常言語創立一種文字(語素)組合格式,把文字與意義庫的對應規范起來。如果書面語極早發生于一個文明程度較高的區域且這個區域文化最終能夠征服其他區域文化并連續發展下來,那么這種書面語就不會像日常語言一樣被文化融合所影響,而是保持它的獨立性。在文化高度強勢而未中斷的情況下,區域語言差異越復雜、語言融合越頻繁,書面語的傳統就越能得到保持,并會漸漸脫離日常言語,形成“言文不一”的局面。總之,中國書寫系統和古代書面語可以認為是世界范圍內獨一無二的現象,它成為中國的“第二語言”,主要以規范化的語詞系統而不是用對應于日常言語語音的符號來指代意義。通過這種書面語言,人口眾多的中國人得到了一門全民族語,從而得以承載知識、思想、信仰傳統,并能擺脫方言歧異、言語變遷的困擾而實現跨越時空的傳達。
西方在這一方面完全不同。由于埃及和兩河文明的衰落和被覆蓋,“神圣書寫”不可避免地讓位于不同方言的書寫,因此文字作為語言特別是語音的外殼,必然走向拼音文字,拼音文字又必然導致民族書寫。另外,統一王朝的衰亡使“雅語”逐漸失去統治地位,從而使文獻書寫形成分化。這對文獻傳統連續性的影響是相當嚴重的,“到公元6世紀,希臘語在西方已經成為死語言,教皇大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約公元590-606)便完全不懂了,羅馬帝國已完全控制在蠻族移民手上,東西方文學教養和對圖書的照管與收藏完全衰落了。希臘語在羅馬已經完全沒人說了,而拉丁語在君士坦丁堡已被禁止。不可設想羅馬的圖書館會在這個時候繼續增加它們的希臘語藏書,或希臘語圖書館致力于拉丁語書籍收藏”。至17世紀,拉丁語又全面式微。從15世紀60年代至16世紀初約五十年間,歐洲出現了第一本德語、捷克語、意大利語、加泰羅尼亞語、法語、佛蘭德語、西班牙語、葡萄牙語、丹麥語、瑞典語、普羅旺斯語、波蘭語等主要地方語言印刷書籍,此后這一地方語言印刷書籍名單持續增加,“至此,各地的民族文學皆建立起基礎,并令泛歐書市開始分裂;各國執政者基于政治與宗教理由,推展各種成效顯著的圖書審查,亦助長這種分化。到頭來,歐洲的不同國家,終以文化差異為界,將彼此的出版市場永久區隔開來”。
方言出版促成西歐民族國家的形成,而長久不變的書面語卻使中國王朝始終存在。代表著國家權力、教會權力和文化權力的拉丁語被地方語言取代,這種情況在古代中國從未發生。在歐洲,印刷術可能反過來促進了民族語言的格式化和固定化,并強化了民族與民族之間的“語言壁壘”,這一情況在中國同樣也未出現:書面語言的格式化和固定化早在先秦時代就完成了,書面語經典長久垂范,并不待印刷術的發明而進一步加強;同時,明以來通俗文獻特別是通俗文學所帶有的方言、俗語,也未能因為印刷品的普及而形成對標準書面語的顛覆。錢存訓所指出的印刷術對中西社會所發生的不同作用——“印刷術促進文化發展,擴大讀書范圍,普及教育,推廣識字,豐富各科學術,這些效果雖是一樣,但程度不同。不過在西方,印刷術同時激發理智思潮,促進民族語言和文字的發展以及在文學上的應用,并鼓勵了民族主義和建立新興民族國家的行動。相反的,在中國印刷術幫助了書寫文字的連續性和普遍性,成為保持文化傳統的重要工具。儒家典籍與科舉考試用書的印刷,更可證明。所以,印刷術是中國文化和社會的相對穩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實際上也正是說明了中國文獻傳統連續性所具有的特殊的社會文化意義。
第三,經典及經典闡釋傳統同樣連續不斷,并沒有因為宗教、政治和族群異見而形成斷裂。
經典闡釋的連續性是中國古代主流思想——儒家思想賴以發展壯大的重要基礎,也是整個文化核心得以延續的關鍵所在。因為儒家思想不斷提倡的倫理道德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宗教,所以不會別宗教所左右,反而改造宗教為其所用。同時,緣于儒家思想成為統治哲學,除了少數暴政時期外,王朝政治一貫維護著經典傳統而不使之有絲毫的斷裂。古代中國并不乏各種次生族群,也常因游牧族群的入侵而導致異族入主,但異族的華化始終是歷史主流。在“來中國則中國之”的過程中,文化可能稍有損傷,但不久即恢復原狀。經典闡釋的情況同樣如此,無論是北朝、金、元以及清,可能在某個時期稍有頓挫,但經學傳統從未斷絕,這在書籍史上可以從六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的編纂刊刻上得到具體證明。最典型的是,與歐洲基督教、東正教分裂以及后來民族語言不同所形成的不同印刷書籍完全相反,自元以后,中國、日本、朝鮮、琉球、越南則形成了一個“漢字書籍共同體”,并且這一共同體并非是單向的傳播模式,而是往復交流意義上的“書籍環流”,成為9世紀以來東亞文化圈賴以存在的根本性保障。
穩定性
文獻傳統既未中斷,照理而言,文獻的發展就勢必會隨著社會文化經濟的進步而形成一個持續發展上升的趨勢。但事實上中國古代的情況卻并非如此,整體文獻明顯呈現出一種螺旋式發展的模式;至少在清中期以前千余年的文獻歷史過程中,每一個大的螺旋以后并沒有出現顯著的躍升。前文所討論的現存古籍數量可以為證:若現存1911年以前的古籍約為20萬種,則明代以前古籍現存至多1萬種,明代大約1到2萬種,清順治至嘉、道大約4到6萬種,而整個晚清可以達到10-12萬種,從這些數字可以推出從《七略》以來至17世紀近1600年的文獻種數的增長率,極其有限。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經籍會通一》日:“古今書籍,統計一代前后之藏往往無過十萬(卷),統計一朝公私之蓄往往不能十萬,所謂天之生財止有此數也。”盡管胡氏總結的原因不完全正確,但他所揭示的現象卻是歷史事實。也就是說,整體文獻保持著一種穩定性的存在。
中國古典文獻的穩定性的主要內涵之一是文獻傳統具備一種歷時性的內在規律,積聚、散佚有常,生產、保存、淘汰亦有常,也就是在數千年的歷史中,文獻整體是一個按自身規律保持運作的有機系統。
前文已論,不能完全用文獻頗遭人為摧殘來解釋文獻未能實現突破進展的事實。固然,中國自古天災人禍不斷,文獻時遭水火,散佚確為嚴重:至清代,史志所載及藏奔家著錄所載宋以前書,已百無一二;即宋以來目錄所載,十亦不存四五。但透過現象看本質我們可以明顯發現:文獻的散亡,主觀原因大于客觀原因,內部因素大于外部因素,亦即文獻的散亡并非主要是天災人禍所造成,而根本上是社會歷史環境下主觀取舍和文獻內部規律作用的后果。個人認為這是一條最重要的中國古典文獻基本規律之一,它所揭示的意義是:中國古典文獻之所以呈現出一種低增長的螺旋式發展,保持著某種穩定性,并不是一種偶然而是一種必然結果。
文獻內部的規律,主要體現在文本內容特質和文獻作為知識載體的形式內涵方面。比如技術性知識存在著明顯的階段性,一旦舊有知識被新知識淘汰,則原有相關文獻必然漸次散亡。《漢志》“兵書略”凡五十三家,七百九十篇,圖四十三卷,除上升為軍事哲學之《孫子兵法》外,一無所存;秦火燔《詩》《書》、百家語,不去種樹卜筮之書,前者十九有傳,而后者百不存一,均為此理。再比如刪繁就簡、融匯眾說、取精用宏之新冊,往往能夠代替所據之舊典,《漢志》存而《七略》《別錄》亡,鄭玄《毛詩箋》出而三家詩浸佚,即乃此屬。
主觀取舍當然更為關鍵。如果說在文獻內部規律方面中西傳統還存在某種共同性,主觀取舍方面則迥乎不同,最后的選擇去取皆是其各自文化內核規定性的產物。兩漢以后中國正統思想以較為成熟的實用理性為準則,主觀選擇性極為明確,整體精英階層重視歷史經驗,強調倫理道德,都排斥百家極端、怪奇、忤逆之談,罷黜術數、讖緯及宗教異端,同時忽視技術知識。精英階層主導社會自上而下的教化,始終以儒家思想為指導原則,不為政治、宗教、經濟甚至外來文化傳人所左右。在文獻散亡方面,此一主觀法則的作用從某種意義上說就是一種“無形的摧毀”,較諸兵燹和焚禁這一類“有形的摧毀”,所造成的古代文獻的危害尤烈。
綜合而言,可以這樣認為,中古以后無論經歷何種天災人禍,也無論獨裁統治實施怎樣的禁絕方針,文獻的總體格局已基本定型:注定散佚的,終歸漸趨無形;必然存留的,往往不絕如縷。總量則是緩慢增加,從中古到17世紀一千多年來至多也就五到六倍的增長。很明顯,這與西方5世紀以前的情況或許有一定相似之處,但和6世紀以后的情況完全不同。據前引Eltjo Buringh和Jan Luitenvan Zanden的研究估算,西歐自公元500年至公元1800年這1300年來書籍生產的平均年增長率為1%,也就是公元1000年的生產量是公元500年的約144倍,公元1500年達到約兩萬倍,而公元1800年則達到約四十幾萬倍。這一長時段的增長結果是極其驚人的,中國的增長率和增長結果遠遠不及。
中國古典文獻的穩定性的主要內涵之二是從兩漢以來直至18世紀,中國持續的文獻傳統固然不乏新創,但總體上以繼承為主、新創為輔。形成此一內在機制的根本原因是經典形成甚早,作用時間極長,經驗主義和復古主義的力量極為強大,儒家思想的核心是整頓衰弊的現實世界并恢復遠古黃金世界的輝煌,因此闡釋經典以發現前往“大同”的道路,成為思想文化最根本的建設手段,“述而不作”進而變成一種思想和方法原則。《四庫全書總目》“經部序”所謂“經稟圣裁,垂型萬世,刪定之旨,如日中天,無所容其贊述。所論次者,詁經之說而已”云云,雖系就“經”而言,但實際上也是古人所以著述的基本心態的寫照。
事實可證,從《隋書·經籍志》確立四部系統后直至清乾隆時期,整體文獻雖不能說完全走向封閉,但至少是沒有發生劇烈的體系變化。《隋志》分經、史、子、集四部共四十個二級類目,《四庫全書總目》分四部共四十四個二級類目(含六十七個三級類目)。新增、改易者并不多。收書內涵上除了集部和子部雜家類有較大擴張外,其他類目的增大幅度都是有限的。“四部”固不能返“七略”,但“四部”并未完全邁越或顛覆唐宋舊觀,知識更新沒有實現質的提高。也就是在知識創造方面,保守的、內斂的思想觀念發揮著顯著的規范作用。這個特點,當然與前文所述之“連續性”和后文將述之“精英性”密切相關并構成一種整體性。
相比之下,歐洲文藝復興運動所突破的是中世紀以來宗教保守思想的束縛,以“發現”古典為名而行創造之實,實用知識得到重視,新的學科不斷涌現,知識系統得以更新。緊接而來的知識產權自覺意識的產生和印刷資本主義的出現,使書籍生產不僅完全擺脫了舊時代的政治、文化禁錮,而且更重要的是促成“知識”變為銷售商品這一現代性因素的出現。而在中國,這一切直到20世紀初帝制結束以后方才真正發生。
精英性
出于教育普及程度極差、農業人口居多及地區文化水平差別較大等原因,中國古代的識字率(具有閱讀能力的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較低,直至20世紀初葉,整體社會的識字率不會超過20%,明代以前則更不堪言。早先國外漢學家如羅友枝(Evelyn Sakakida Rawski)研究認為,19世紀中期到晚期,男性約為30%到45%,女性有2%到10%具有讀寫能力(如此,低限平均為16.6%至20.5%;高限為24%至28%),這個結論顯然過于樂觀。以歐洲的情況作比較: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一個總結是遲至1840年,即使在歐洲最進步的兩個國家——英國和法國——也有近半數的人口是文盲,而在落后的俄羅斯則幾乎98%是文盲。
識字率的低下,導致古代中國閱讀人口的階層和范圍均極有限,與歐洲相比更為遜色:歐洲“閱讀階級”除了貴族和地主士紳、廷臣與教士等舊統治階級外,還包括平民出身的下層官吏、專業人士以及商業和工業資產階級等新興的中間階層。中國明清時代的能文之人,除了精英分子以外,中間階層非常有限,只有如生員、吏員、部分僧道師巫、代筆者、書會先生、算卜等專門職業者、商人特別是書商及其雇傭寫手和極少數的城鎮市民。
正是由于這一原因,使古典文獻無論是曾經編纂、出版、流通者,還是現存者,均以精英文獻為主。從發生上來看,汪德邁(Leon Vandermeersch)最新的研究甚至得出了一個釜底抽薪式的結論:中國書寫一開始就不是語言的記錄而是一種意義——理性的、前科學占卜的記錄,從而直接生成書面語;而音節文字所形成的書面語,是識字率低下的根本原因之一。從早期觀念上來看,《墨子》“書于竹帛,鏤于金石,琢于盤盂”已數數言之,按照墨子的理論,最需要傳達和保存的認知和記憶,是對天的意志和鬼神(二者實即最初的宗教)的敬崇,“又恐后世子孫不能知也,故書之竹帛,傳遺后世子孫。咸恐其腐蠹絕滅,后世子孫不得而記,故琢之盤盂,鏤之金石,以重之”@。這其中當然有不少理想化的猜想,但實際上就出土文獻中的早期書寫而言,甲骨文是卜辭,屬于墨子理論的第一個方面“宗教”;青銅銘文主要是紀功、誥命,屬于墨子理論的第二個方面“政治”——理性的和現實的行為。發展到印刷時代情形依舊,與西方更是大不相同,如錢存訓所指出的:“印刷在西方社會中,主要是一種營利事業,跟隨工業革命而發展成為一種龐大的出版工業,是大眾傳播的主要媒體。而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印刷術的主要功能并非謀利,卻含有一種強烈的道德觀念。刻書對知識的傳播和文化保存,認為是人生的一種美德,所謂‘傳先哲之精蘊,啟后學之困蒙,亦利濟之先務,積善之美談。尊重古代典籍是儒家思想的主要成分。”所有這一切都使書寫和載籍文獻從最初到最后,必然都只能是屬于精英分子而不是其他階層。
隨著社會的進步,民俗文獻當然亦漸次而生,但一直居于極低的地位。即使是商業化出版的時代,國家和士人階級也表現出強大的主宰力量。徹底顛覆這一主宰力量的“印刷資本主義”,要晚至19世紀末方在某些地區發展起來。在此之前,精英文獻出版雖然在有些時候也呈現出商品狀態(特別是帶有文物性質的宋元舊本),但從未像歐洲的《百科全書》出版一樣,既是一個啟蒙運動行為,又是一個典型的“生意”。而作為商品的通俗文獻如蒙書、科舉應試書、日用型書、宗教書、通俗文學書等一方面畢竟仍為中等文化水平之人所閱讀,一方面還是無法撼動精英文獻的主導地位。
一直到近代以前,中國書籍印刷的復本量都是比較小的。雕版印刷術為主流,活字印刷始終沒有得到規模化應用,也能說明這個事實。因為精英文獻的出版并不需要龐大的一次性產量,而是需要可以長久的保存印版以便將來修訂,或者垂諸久遠。雕版印刷恰恰可以符合這種需求。利瑪竇最早就指出了這一點:雕版印刷并非不可以大量印制復本,因為技術的成熟其成本也低于活字,但其最明確的優點是“一旦制成了木版,就可以保存起來并可以用于隨時隨意改動正文。也可以增刪,因為木版很容易修補。而且用這種方法,印刷者和文章作者都無需此時此地一版印出極大量的書,而能夠視當時的需要決定印量的多少”。當代研究者普遍認為雕版印刷有利于分散于各地且每版印量不大,有待重印的書籍生產模式。也就是說,雕版是適應精英文獻生產的模式,與西方完全不同。通俗文獻雖然出自于商業生產,但因其閱讀者至少是識字之人的緣故,高數額的一次生產量并不是市場需要,故而也同樣一直采用雕版印刷。盡管理論上雕版印刷的復本量可以達到成千上萬,有研究表明,除了宮廷或政府以外,無論是何種類型的書籍,個人印刷和商業出版中每一版次的實際印刷量至多也就在100-200部之間。這證明中國雕版印刷術從技術到模式都是為精英文獻而不是商品化通俗文獻服務的。
另外一個典型的例證是報紙,書史研究者都指出,報紙是整個后工業化時代印刷史中最重要的內容,“尤其是受歐洲影響或控制的海外殖民地的印刷發展史上,印刷文化最初是通過報紙的出版而發展起來的,報紙在當地社區被用作一種發布信息和維系凝聚力的手段。報紙的大規模機器印刷,在萌芽階段影響和促進了民族凝聚力的形成、語言的塑造和羅伯特·埃斯卡皮所稱的‘獨立的民族文學的產生”,當然也就是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謂印刷資本主義(print capitalism)的根本性要素,只有在相同的時間段內被千萬人消費的日報,才可以讓人感到被同一種語言連接在一起。然而在中國,即使算上傳教士創辦的報紙,也要遲至19世紀中葉以后才較多出現,而直至19世紀末20世紀初才真正開始在社會上發生顯著作用。
因此,16世紀開始興盛的書籍商品化,既然未能形成“印刷資本主義”,當然也就不可能像歐洲一樣,創造出一個“從根本上腐蝕了歷史悠久的王朝原則,并且煽動了每一個力有所及的王朝去進行自我歸化的”“群眾性的、以方言為基礎的民族主義”。中國古代文獻主要是以精英文獻為主,通俗文獻則扮演溝通上下的角色,二者合力延續、加強的是“古典共同體”,而不是現代的“想象的共同體”。19世紀末以降主要在上海出現的“印刷資本主義”所帶來的通俗文學作品、知識讀物、日用書籍以及報紙、雜志等媒介出版物,方才促進了后者的誕生。
中國并不是世界上文獻傳統唯一悠久、發達的地區;中西文獻傳統沒有高下之分,只有特色不同。中國文獻傳統的連續性、穩定性、精英性,絕非是一般意義上的文獻傳統皆能具有的共性,而是在中西比較視野下所得出的中國載籍發展演變的歷史獨特性。文獻傳統的特色在根本上是由文化特性決定的,但它同時又以其非凡的能量反過來影響和建構文化特性。
[責任編輯:孫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