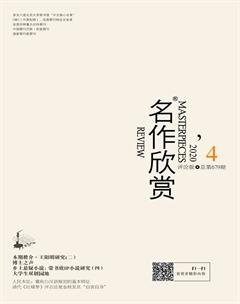道是無晴卻有“情”
摘 要: 新海誠最新的動畫電影《天氣之子》自上映以來便備受關(guān)注,除了延續(xù)以往的對“天空”的細致刻畫、“天空”是“自由”“理想”的象征之外, 《天氣之子》中“天氣”之“晴”隱含了新海誠對“情”的象征意義。連綿的陰雨,讓人對“晴”充滿向往,“晴”在故事中是各種情緒與情感的表達;“情”是一個人孤獨的“心情”,是兩個人真摯的“愛情”,是主人公缺失的“親情”。
關(guān)鍵詞 : 新海誠 《天氣之子》 無晴 有“情”
新海誠是繼宮崎駿之后日本最成功的動畫電影導演,自2016年《你的名字》 在國內(nèi)上映以來,一直備受追捧和關(guān)注。《你的名字》 創(chuàng)造了200億日元和5億人民幣的票房奇跡,《你的名字》 的成功無疑讓受眾們對新海誠2019年的新作《天氣之子》 充滿期待。2019年11月被稱為《你的名字》 姊妹篇的動畫電影《天氣之子》 在國內(nèi)上映,但其反響卻不如《你的名字》。雖然《天氣之子》在故事情節(jié)、邏輯架構(gòu)上不如《你的名字》,但是其“天空”還是延續(xù)了以往的“理想”“自由”的意象,其中對“陰雨”天氣的渲染,表達了人們對“晴”的向往,暗含了人們各種“情”的情緒書寫和情感表達,值得回味。
一、一片“自由”的理想“天空”
新海誠的動漫作品最常出現(xiàn)的畫面就是用絢麗的光影來表現(xiàn)天空的奇異之景。天空總讓人感到神圣、崇高、敬畏。風和日麗、風輕云淡總讓人心情愉悅,陰雨連綿、雷霆萬鈞卻讓人充滿愁緒、心生畏懼。“天空”在新海誠的作品中都是具有神秘力量的所在,就像“幾乎所有早期的宗教在構(gòu)想無所不能的超越、至高無上的神靈等概念時,令人驚奇的是,他們都會聯(lián)系到天空或太空。天空是神靈的家,雷電和暴雨是它力量的展現(xiàn)。這是因為天空凌駕于一切存在、特性和明確的形體之上。” a新海誠的天空是絢麗的、神奇的,也是讓人充滿敬畏的。雨天的水珠像七色光的小魚,御風飛揚,晴天的天淡云閑,讓人仿佛置身夢境。
“天空”是新海誠動畫的背景,是體現(xiàn)導演理想的“自由”空間。“天空”是自由,是理想,是開闊、唯美、自由的象征,蘊含著治愈的力量。正如諺語“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那樣,天空是超越日常平凡的社會生活的,是代表“自由”和“理想”的。此外,《天氣之子》中的天氣之“晴”有著特別的意義,是現(xiàn)實中人類的各種情緒的表達。
二、一個人的孤獨“心情”
《天氣之子》中“晴”天的第一個意象是和人的“心情”密切相關(guān)的。人們的心情容易受天氣的影響,好天氣總是會帶來好心情,陰雨連綿的天氣很容易影響人們的心情,讓心情壓抑沉悶,陰雨天讓人的心情仿佛也潮濕得可以擰出水來。《天氣之子》中的“天氣”是不正常的,就像其中反復出現(xiàn)的那句“這個世界本來就是瘋狂的”。東京連綿不絕的陰雨,數(shù)月不開,讓人感覺壓抑、寂寞和郁悶。陽光燦爛的晴空,成了很多人向往之物,所以“晴天”才成為了“100%晴女”陽菜謀生的手段和工具。
《天氣之子》中的“晴”是心情的象征,晴天固然是令人愉快的心情,是積極的符號表達,而相對而言,雨天就是令人壓抑的心情,是消極的符號表達。影片對“孤獨”氣氛的渲染很到位。《天氣之子》中反復出現(xiàn)的各種雨天的畫面,表達的雨總是和離愁別緒、一個人的孤獨糾結(jié)在一起,“一聲聲。一更更。窗外芭蕉窗里燈。此時無限情。夢難成。恨難平。”特別是“為賦新詞強說愁”“百憂如草雨中生”的少男少女們,總會沉浸在這種“孤獨”的情緒中。晴天的時候,看到燦爛的陽光,人就會心情舒暢。而電影中多次出現(xiàn)男主帆高關(guān)于家鄉(xiāng)的回憶,他騎著單車追逐著島上的一束光芒,希望能站到那束陽光的下面,他嘴里念叨著:“我要離開這個島。”在這里帆高對陽光的追逐也是孤獨和缺乏安全感的表現(xiàn)。就在帆高來到東京之后,新海誠選擇了東京的新宿作為主場地,而新宿是東京最繁華、人口密度最大的區(qū)域。帆高在新宿骯臟的角落——情人旅館的垃圾桶旁避雨,夜晚的黑暗再加上一直下著的雨,這些都映襯了帆高在東京浪跡的困境和不安,這些場景都表現(xiàn)了主人公強烈的“孤獨”情緒。
少年的“孤獨”不僅是個人的,而是有共性的,是社會化過程中必然遭遇的狀況。越成長越需要獨自面對繽紛而廣闊的世界,但少男少女們時常感覺自己是那么的渺小而無力,如何消解這種深刻的孤獨感是他們自我探索的成長過程中思考的問題。作為現(xiàn)代都市的東京,人口眾多,所以少年剛開始找工作只能住在擁擠的網(wǎng)吧里。窗戶上的雨順著玻璃流下,看上去像人臉上流過的淚痕。帆高在網(wǎng)吧用來蓋泡面的那本書是美國作家杰羅姆·大衛(wèi)·塞林格的《麥田里的守望者》。書里描述了十六歲中學生霍爾頓被學校開除后,因為不想回家而在紐約流浪的經(jīng)歷。電影中男主角帆高的設(shè)定和霍爾頓十分相似,都是十六歲離家出走、在城市中漂泊的少年,身上帶著種憂郁的氣質(zhì),對世界懷抱著各種不滿的情緒。無論是影片里的帆高,還是《麥田里的守望者》的主人公都是 “孤獨”的。
影片表達的“孤獨感”讓很多城市人都能找到共鳴。“孤獨”是現(xiàn)代人的通病,時代越發(fā)展,人們的交流更便捷了,交流方式更多樣了,反而更封閉了。“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人們總是借各種自然的變化來表達、宣泄自己的情感,并很容易就沉溺于自己想象的“孤獨”世界中,感到極度無助、苦悶。正因為雨一直下,人們才更向往晴天;也正因為這種滲入脊背的孤獨,人們才更向往和他人有一段感情的交流,這正是《天氣之子》用“無晴”的天氣,表達的孤獨“心情”。
三、兩個人純真的“愛情”
“晴”除了“心情”,還容易讓人聯(lián)想到“感情”,在《天氣之子》中,“晴”是“感情”的符號,象征著兩個人純真的“愛情”。《天氣之子》中少年遇到愛情的怦然心動,讓他從一個人的孤獨中逃離,仿佛生命一下子充滿了活力和意義。影片中陽菜的出現(xiàn),讓帆高仿佛找到了屬于自己的陽光——而具有超能力的陽菜,的確是一個具有讓天空放晴的超能力的女孩。帆高在關(guān)于家鄉(xiāng)的夢中,追逐的陽光也代表著可以掃去心中孤獨和陰霾的自由和未來。和陽菜相識相知后,兩個人共同經(jīng)營著“放晴”的業(yè)務(wù),不僅解決了兩個人的生計問題,而且讓帆高心中一直以來的壓抑和孤獨的心情也一點點放晴了。但是當陽菜因為過度使用自己的超能力,在帆高身邊消失時,整個東京即使“晴空萬里”也改變不了帆高心中的不安,他的整個內(nèi)心世界仿佛再次遭遇瓢潑大雨,再次變得陰暗不堪。
人是社會化的動物,需要釋放情感,需要向他人傾訴,希望有人能理解自己。即使渴望逃離現(xiàn)實的人們還是希望能得到他人的關(guān)心,希望通過友情或者愛情來證明自己的存在價值。故事用兩次偶遇,讓少年和少女相識、相知。第一次是少年帆高,離家出走到東京闖蕩,在東京找工作并不順利,最后只能到麥當勞每餐都吃著最便宜的玉米羹,這樣遇到了在店里打工的少女陽菜。陽菜送給帆高一個漢堡,成了帆高吃過最好的一頓飯,而少女也在這一刻成了照亮少年內(nèi)心的“陽光”。正如一首歌里唱的“只因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沒有忘掉你容顏,夢想著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見”。第二次是某日街頭,陽菜正要被人拉去做特殊成人工作,被偶然路過的帆高看到。關(guān)鍵時刻,在看到陽菜被黑社會的人拉拉扯扯的時候,少年通過偶然拾到的“槍”表達了自己的勇氣和力量——達到了“英雄救美”的目的。愛情是沒有理由的,有很多偶然性的因素。雖然現(xiàn)代社會凡事都講求效率,但是現(xiàn)代人還是會向往輕松、浪漫的戀愛,向往沒有功利的兒女情長。
雖然很多觀眾對為何少年手中有“槍”,覺得不太合理,但正是因為偶然出現(xiàn)的“槍”鞏固了兩個人的愛情。因為看不見的黑暗總在夜幕下出現(xiàn)——剛到東京的時候帆高被黑社會的人踢倒在地上,垃圾堆里正好滾落出的手槍被帆高偷偷藏了起來。影片中出現(xiàn)的“槍”是武器,也是權(quán)力的象征,之所以沒有上繳警察,是因為少年覺得自己要掌握自己的命運。“槍”在整個故事中一共出現(xiàn)了三次:第一次是偶然拿到槍、藏槍;第二次是在看到陽菜被黑社會的人拉拉扯扯的時候“英雄救美”;第三次則是為了去救神隱的陽菜,和警察對抗。可以說,少年手中的“槍”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幫助少年實現(xiàn)了自己的“自由”選擇,達到了兩次通過自己的力量去“救”少女的目的,證明自己和少女的“情感”聯(lián)系。
在故事的結(jié)尾,由于祭祀給上天的少女被少年從天上救下來,東京的天氣開始變得更加瘋狂,整整下了三年的雨,大半個東京都被淹沒在雨水中。少男少女的愛情如此純真、執(zhí)著,是寧愿毀滅全世界,也要成全的感情。少年帆高拯救少女陽菜時說的那句“天氣什么的就讓它瘋狂下去也無所謂,我只要你!”其實就是在表達兩個人純粹、純真而堅定的感情。你我都是渺小的,是廣闊天地間的匆匆過客,但兩個人可以不計后果去拯救對方,天氣怎么樣,世界今后會如何,都無所謂。懵懂的戀情因其青澀、內(nèi)斂而神圣、美好,新海誠的“青春”故事中的戀情沒有性的表達,因為那不夠神圣;也沒有家庭的瑣粹,所有的“權(quán)威”——家長都要“神隱”,因為家庭生活的瑣碎讓人無法浪漫。對愛情的向往是青春期的重大主題,看同齡人的戀愛,受眾特別容易產(chǎn)生代入感。新海誠的故事是完全虛構(gòu)的,但是“肯定存在與他們存在類似經(jīng)歷、類似情愫的人”b。 兩個人“不孤單”,不需要為世界放棄自己的真愛,才是各自心中的“晴天”。
四、主人公欠缺的“親情”
“晴”在《天氣之子》中還是“親情”的表達。親情,是人們應(yīng)對社會生活中種種不幸的“雨傘”,是霧霾天里讓人珍惜的“晴朗”,是應(yīng)對社會風雨的必需品。雖然在東方世界的傳統(tǒng)家庭關(guān)系中,父母是很重要的存在,承擔著對子女的教育責任和義務(wù)。但在《天氣之子》中,母親的形象是一種缺失狀態(tài)。陽菜知道自己是“晴女”是在母親生病即將去世的時候,陽菜祈禱雨不要一直下,能讓自己和母親一起去散步。母親去世了,世界還是陰雨綿綿。正如我們渴望晴天,渴望“親情”,但是我們?nèi)魏稳藷o法阻止親人的離世一樣,我們很難改變天氣的陰晴。
影片《天氣之子》中父輩是缺席的“,親情”是欠缺的。通過父輩的“缺席”設(shè)定,實際上弱化了權(quán)威的影響,強化了與權(quán)威對抗的自我存在感。其實日本動漫吸引年輕人的秘訣就在于它具有“青春”屬性,它認為“權(quán)威和紀律正是成人世界強加給孩子的東西”c。正因為直面青春的沖動和苦惱,連青春的錯誤、與成人世界的對抗也是充滿魅力的。十五歲的少女陽菜的母親一出場就病逝了,母親的去世,讓陽菜成了代替母親的角色,成了弟弟的守護者。她無力地維持著和弟弟兩個人的沒有父母的“家庭”,還擔心弟弟被警察送到兒童管護中心。十六歲的少年帆高第一次出場就是一個人在甲板上迎接著風雨的到來,臉上的傷口似乎言說著自己的不幸。濕濕的雨胡亂地怕打在帆高的臉上,仿佛淚水一般。故事沒有交代他離家出走的原因和目的,只是用雨天渲染著他的感傷情緒,用不正常的暴風雨暗示他在現(xiàn)實生活中的不如意。這個留白也給人無限遐想的空間,他到底是遭遇了家庭暴力還是遭遇了學校的霸凌?父母不在身邊的少年,眼里寫著對東京的向往,臉上掛著曾經(jīng)經(jīng)歷的傷痛。兩個看似無父無母的年輕人,要面對陰雨連綿的東京,象征性地表達了“親情”的缺失。兩個人唯有通過售賣“晴天”維持生計,確立自我的價值和自我的存在感。
在故事的結(jié)尾,當帆高救出陽菜,東京開始遭遇三年大雨,但社會并沒有因此停止運行,東京的人們依舊如往常一樣工作、生活,沒了陸地,船成了主要的交通工具。帆高原先的上司須賀對他說:“別以為你們改變了世界,世界本來就是瘋狂的。”同樣,婆婆富美也安慰帆高:“如今被淹沒的東京,只是回到了幾百年前本來的樣子罷了。”然而,當帆高看到在路邊祈禱的陽菜,他的內(nèi)心獨白卻是:“不對。世界并不是最初開始就瘋狂了。是我們改變了世界。”少年在內(nèi)心里還是很想證明自己的價值,找到自己的存在感——盡管這種想法很“中二”,這種內(nèi)心獨白很無力,主人公缺乏了“親情”,很想通過能改變世界的“愛”來證明自己,但是事實上東京的雨還是一直下個不停。
五、總結(jié)
《天空之子》中有很多讓人動容的有關(guān)“情”的表達——雖然天空多數(shù)時候是陰雨不斷,但是“天氣”是一種符號,道是無晴卻有“情”。《天氣之子》中用讓人期盼的“晴”暗示了各種“情”。“晴”的意蘊和表達,可以說使新海誠的青春動漫帶給受眾更多夢想,有和受眾進行“夢”的交流的潛質(zhì)。新海誠的動畫都是很唯美的,有人說他的每一幀畫都可以成為桌面,美的像人類最美好的青春“真情”一樣,像“夢”一樣。人類天生就喜歡做夢,正如尼采所說:“夢是白天失去的快樂和美感的補償。” d新海誠動漫用藝術(shù)豐富的表現(xiàn)力、唯美的畫面、悠揚的音樂、聲優(yōu)充滿感情的演繹突出表現(xiàn)各種“夢”。“動漫的表現(xiàn)手法不受現(xiàn)實規(guī)則的限制,這種悖離產(chǎn)生的張力則是比任何一種影視形式更具有視覺沖擊力”e,給欣賞者一個多彩的“夢想”空間。可以說,《天氣之子》是最具有新海誠風格的作品之一,這部作品中的“天氣”有著特別的含義, “晴”(“情”)是“心情”,是一個人的“孤獨”,也是“感情”——兩個人純真的“愛情”,還是“親情”,新海誠動漫主人公特有的“親情”的缺失。
a Ronald W .Hepburn:The Aesthetics of Sky and Space,Environmental Value,2010 (3)。
b 〔日〕新海誠:《你的名字》,枯山水譯,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6年版,第204頁。
c 媒體與未成年人發(fā)展論壇組委會編:《媒體與未成年人發(fā)展論文集》,中共黨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3頁。
d 田兆耀:《“電影如夢”解析》, 《東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4期。
e 易欣欣,生喜:《影視動畫經(jīng)典作品剖析》,海洋出版社2004年版,第76頁。
參考文獻:
[1] 山口康男.日本動畫全史[M].于素秋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技術(shù)出版社,2008.
[2] 瑞澤爾.后現(xiàn)代社會理論[M].謝立中譯.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
基金項目: 本文系江蘇省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后現(xiàn)代語境下的日本青春動漫研究”(15WWB007)系列成果之一
作 者: 吳新蘭,法學博士,南京郵電大學副教授,研究方向:日本文化、中日文化比較研究。
編 輯: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