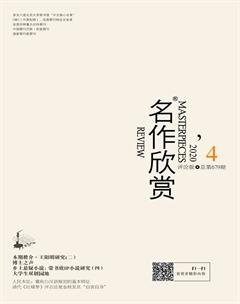無本回譯視角下的僑民文學翻譯
摘 要: 本文試對林語堂經典之作《吾國與吾民》 的無本回譯進行研究,通過譯本對比,以無本回譯的三個評價標準為主線,解析譯者針對文本所做出的不同闡釋及所采用的翻譯策略和方法。筆者通過對比分析得出如下結論:1.譯文的產生是語言、文體和文化標準多維度觀照下的結果,因而無本回譯的終極性范本并不存在。盡管譯本各有偏向,但它們為《吾國與吾民》 在文學舞臺上大放異彩、確立其翻譯文學的地位做出了巨大貢獻;2.以《吾國與吾民》漢譯本個案為例,不僅深化了對無本回譯這一普遍翻譯理論的闡釋,同時通過剖析語言、文體和文化在無本回譯中的具體操作,可用來指導僑民文學的漢譯實踐;3.《吾國與吾民》 作為異語創作的文學作品,多方面刻畫了中國形象,推動了中華文化在海外的傳播。而無本回譯回應了漢語及中國文化的價值,促進了文化反哺進程。
關鍵詞: 僑民文學 無本回譯 《吾國與吾民》
一、無本回譯概念流變
(一) 回譯
早在唐朝,玄奘就與回譯結緣,他進行的是將中文回譯為梵文的工作。賀顯斌(2002)認為“對譯文進行再次翻譯, 把自己或別人的譯文翻回原文, 這種翻譯方法在英語里被稱之為back translation” 。他不僅從語言層面解釋了回譯對于譯文的檢驗作用和對翻譯研究的輔助作用,更認識到“回譯就是文化還原”。
然而有一種特殊的回譯并無原文可依。吳玲玲和李丹(2004)基于對林語堂英文作品翻譯的認識指出:“盡管沒有一個完整的中文本在前, 林語堂的英語作品中很大一部分帶了翻譯的性質。那么再把他的文章翻譯成中文時,就涉及有回譯的問題了”,因此雖然與回譯的定義稍顯不同,但仍將它視為一種“特殊的回譯”。王正良(2007)指出,翻譯之前一定要分清文本的性質,回譯的對象必須是譯語文本。他將原語文本稱為譯底,回譯譯文稱為譯心,按照回譯目的將回譯分為已知譯底回譯和未知譯底回譯。在這一系列分析中將回譯對象限定在譯語文本中,作者卻將譯底分為已知和未知,既然已經明確譯語文本,證明一定是有原文本可以依照的,又何以探討已知譯底和未知譯底?筆者認為這種分類本身就存在一定矛盾,而對于“無本回譯”的發現已經呼之欲出。
除了通過探討在回譯概念下這一特殊翻譯現象在語言層面的轉化,也有學者將文化層面的討論納入研究,并試圖通過豐富回譯概念的內涵來解釋這一特殊翻譯現象。陳志杰和潘華凌(2008)立足于文化本土化和全球化交界處,通過將“復譯”和“古本復原”兩個概念納入回譯的范疇,將回譯定義為“通過回溯擬譯文本與目的語文本間內在的語言和文化聯系, 把擬譯文本中源自目的語的語言文化素材或文本重新譯回源語的翻譯活動”。其中,關于林語堂《風聲鶴唳》 翻譯的個案探討已經指出此類回譯過程具有特殊性,即在源文本隱而不發的情況下,這種單向的僅從B文本回歸到A文本的過程也是一種隱含式的回譯活動。這一個案雖已意識到回譯不單涉及語言層面,還需考慮到擬譯文本和譯入語之間的親緣性文化關系,然而對它的定義還停留于“復譯”和“隱含式回譯”上。
周紅民和程敏(2016)更是直接將回譯定義為“將A 國語言書寫的B 國文化翻譯成B國語言的過程”。這一定義中已經包含了原文本語言能指和文化所指的不對應性,同時也突破了翻譯的語言轉換層面而直指文化層面。通過分析美國作者所寫的中國北魏時期史學文獻,指明了回譯的“不可逆轉性”,借助譯者對四字格、古語和長句的處理表明對待此類型的歷史文獻翻譯時應盡量貼近目標讀者的取向,使語言與文化達到高度融合。但即使作者的分析已經接近“無根回譯”或“無本回譯”的概念性認識,最終還是落腳到要關注回譯對于文化回歸的程度,受敘述角度、篇幅和術語概括的限制,并未實現理論化的認識和表述。
從以上學者對于回譯的研究可以看出,學界一開始對于回譯的概念理解和定義過于寬泛,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開始引入其他翻譯概念或重新定義來將其細化,雖然對其的認識已經不止局限于文字間的相互轉換和將其應用于譯文質量檢驗和語言對比上,但對于文學翻譯這一大領域卻少有涉及。
(二) 從無根回譯到無本回譯
國內最先對這一翻譯現象進行定義的是王宏印教授。他在著作《文學翻譯批評概論》中將“在語言上不存在以原作為根據的回譯”現象定義為“無根回譯”(rootlessback translation):如果我們把用一種語言描寫本族文化內容的書寫稱為“原語書寫”,那么用另一種外語描寫本族文學場景的則可稱為“異語書寫”,由此產生翻譯上的回譯,就是“異語回譯”。如果把朝向原文的回譯稱為“有根回譯”,那么我們把這種非典型的并無同一語言原本的回譯姑且稱為“無根回譯”。其典型作品便是林語堂用英文創作的小說Moment in Peking(常譯為《京華煙云》)及其漢語翻譯。隨后基于該個案的分析,王宏印和江慧敏(2012)進一步給出解釋:“ 《京華煙云》的漢語翻譯屬于‘無根回譯,即運用外文進行中國文化題材的文學創作,但又用漢語翻譯回來,呈現為漢語文學形態,返銷給中國讀者或漢語讀者。這種翻譯成漢語的返回只是文化上的返回,而不是語言的返回,所以稱為‘無根回譯,即在語言上不存在以原文為根據的回譯。”隨后,王宏印深化了對這一概念的認識并將其修改為“無本回譯”。王宏印(2015)認為,“所謂‘無本回譯,充其量是缺乏文本根據的回譯,但仍然有文化之根( 這里是中國文化,而不是泛泛的人類文化) 作為根基,而不是完全失去其根”。至此,無本回譯有了其確切的定義,即“以原文本的原始缺失為基礎,也即以異語創作為基礎,作為不得已的第二位的文本依據,即翻譯的始發文本進行有文化依據或依歸的翻譯或回譯; 在這里,本土或本體文化作為潛在的基質,或假設的參照架構,始終在起著重要的作用”。作者還隨之討論了無本回譯中有關原文復現和文本刪節與合并處理問題。然而要想使無本回譯朝向一種普遍翻譯理論發展,離不開對理想譯者和評價標準的討論。王宏印(2016)將研究目光從《京華煙云》部分轉向《大唐狄公案》,試圖通過這兩例個案的討論將研究拓展到更廣闊的領域。文中指出,無本回譯的譯者“需要特殊的對中國文化的深入認識,和對于西方文化的深入了解”,而評價標準需從語言、文體和文化三方面入手。通過論述其概括的對象和理論論述范疇證實了無本回譯是一個普遍性理論,它不止立足于中國文化本位,還適用于其他文化中的人用異語寫作并返回到本族語和本族文化。
二、林語堂及《吾國與吾民》
林語堂以“兩腳踏中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為座右銘。《吾國與吾民》是他第一部在美國引起巨大反響的英文著作,實乃向西方世界客觀全面介紹中國及中國人民的佳作。因其是由林氏在異國英文寫成,因而可以算得上僑民文學。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賽珍珠稱其“實事求是,不為真實而羞愧。它寫得驕傲,寫得幽默,寫得美妙,既嚴肅又歡快,對古今中國都能給予正確的理解和評價”。該書英文原版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寫成于1935年,現有兩版在市場上流傳甚廣,其一為1936年黃嘉德首譯版本,譯名為《吾國與吾民》,其二為1988年郝志東、沈益洪合譯版本,又稱全譯本,譯為《中國人》。
三、無本回譯評價標準的具體運用
王宏印指出,無本回譯的評價標準需從語言、文體、文化三方面入手。本文將以無本回譯為基礎,以《吾國與吾民》的兩個漢譯本為例,擬從上述三方面來闡述兩位譯者在無本回譯時對于各種翻譯技巧的運用及翻譯難點的處理,比較不同譯本的精彩譯筆與美中不足。
(一) 語言標準
1.四字格 中文表達中最具特點的當屬四字格。無本回譯不僅要將用異語創作所展現的文化回歸本源,也應貼合目標讀者,使屬于同一語境的文本和讀者高度融合,因此在翻譯時,對于四字格的處理顯得尤為重要。而譯者在目錄處理的方式上可清晰體現這一點。原著中用八個詞語作為小標題串聯起第二章The Chinese Character, 分別是mellowness, patience, indifference, old rough, pacifism, contentment, humor和conservatism.黃譯本處理為圓熟、忍耐、無可無不可、老猾俏皮、和平、知足、幽默及保守性。筆者認為,這一翻譯非但沒有觀照到原文用一到兩詞的精煉,更沒有兼顧譯入語在格式和表達上實現風格統一。反觀郝沈譯本,譯者將這八個單詞處理為老成溫厚、遇事忍耐、消極避世、超脫老猾、和平主義、知足常樂、幽默滑稽和因循守舊,不僅展現譯者深諳母語之道,同時長于語言轉換,具有在忠實于原文的基礎下按照翻譯標準指導操作的能力。
2.信息增刪 考慮到無本回譯語言能指和文化所指的不一致性,翻譯時信息的增刪應以讀者接受為導向,避免添加冗余信息。請看下列翻譯:
例1:The fundamental dualistic outlook, with the differentiation of the yang(male) and the yin(female)principles, went back to the Book of Changes, which was later formulated by Confucius.
黃譯:陰陽二元的基本觀念,始出于《易經》,此書為中國上古典籍之一,后經孔子為之潤飾而流傳于后世者。
合譯:中國人由陰陽構成的二元世界觀,可以追溯到《易經》。孔子曾經對此書作過詳細的闡述。
黃譯本補充了關于《易經》 性質的信息,而對于無本回譯來說,其面向的是了解熟知中國本土文化的讀者群,這一信息補充略顯冗余拖沓。合譯本與原文保持了較高的一致性,言簡意賅地傳達了原文信息。
然而并非所有的增加信息的翻譯都會起到反作用,英文是簡約化的語言,而漢語常常要通過重復來保持句子的平衡性,在回譯時就需要將必要的成分補充出來,以消除讀者在閱讀時感受到的語言使用差異。
例2:Whether ordinary people drink ale or Liptons tea is entirely a matter of social accident, and can make no difference because they are ordinary men.
黃譯:不論普通人喝燒酒也好,呷立頓茶也好,都只算是社會上無足輕重之偶發事件,毫無特色可言,因為他們是普通人。
合譯:普通人是喝淡色啤酒還是喝李普頓茶,這僅僅是一個不同的社會行為方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區別,因為他們是平凡的人。
原文中drink作為動詞只出現了一次,但兩版本的譯者不約而同都補充了動詞,且黃譯本中的“呷”字尤為傳神,作為動詞與茶及茶文化匹配度高,是更為地道的中式表達。而合譯版本也將動詞補充出來使得句子工整,雖少一分神韻,但也不影響閱讀效果。由于前文林氏立足的是約翰遜時代的倫敦人,再加上ale一詞本身也是麥芽酒的意思,因此淡色啤酒要比燒酒貼切些。從這個例子足見翻譯時不僅要考慮譯入本族語文化是否恰當,還應將上下文一致連貫納入考察范疇,不可只照顧譯入語文化而忽視了原文本表述。因而筆者認為,合譯本譯者既有補充信息的意識,又尊重原文本傳達的信息,更勝一籌。
3.被動句 漢語和英語在使用被動句的頻率上有所差別,漢語使用頻率低,且側重使用無標志被動句,在語義方面多包含消極意義,而與之相比英語的使用頻率高,表義也更為寬泛和客觀。但并非所有英譯漢都要試圖將被動轉換為主動,因為翻譯離不開具體語境的考察。
例3:Even as late as the Manchu times chaste widowhood was expected of the wife of a scholar with official titles.
黃譯:直至清朝時代,守節的婦德蓋尤為僅所期望于紳士之家。
合譯:甚至到清代,也僅僅是有官職的文人死后,妻子才會被認為應該守寡。
例4:Worship of chastity, which they so highly prized..., and women were henceforth to be responsible for social morals.
黃譯:婦女因此須負社會道德上的責任。
合譯:婦女被認為要為社會道德負起責任。
第一例原文表述即是被動語態,黃譯本將其轉換成了有標志的被動句,即N1+被(為、叫、給、讓)+N2+所(給)+Vp的形式,這也是被動句的一種固定形式,也就是婦德為紳士之家所期望,后經過句式調整增加了“于”這一被動句標志詞,完成了最終的翻譯。而合譯本采取了更為直接的被動句N1+被(為、叫、給、讓)+N2+Vp形式。兩個版本無一例外選擇將翻譯處理為被動句,不僅將婦女的地位放在主語位置凸顯,同時也帶有作者和譯者共同的情感傾向,認為男性信仰者崇尚恭順忠誠的女性品德,倡導三從四德是一種自私的印證。而第4例原句是主動語態,雖然黃譯本翻譯中規中矩,但合譯本則更體現了被動句在表達消極情感色彩上的功能,因為這里仍舊討論的是社會對于婦女貞潔的重視即地位忽視的對比,這一轉換不僅體現了譯者靈活處理句式的能力,更承接了上文的情感,展現了譯者作為原本的第一讀者所必要的理解能力。
4.段落分合 譯文段落的調整并非不“信”,相反,如果譯者可以充分破解句子結構,明晰句子之間的邏輯關系的話,便可跳出原文框架,通過段落調整的方式進行積極的改動,這是具有開放性的文本所賦予每位譯者自由地詮釋文本的權利。第一章中林氏指出,分析研究一個國家時不能也不應忽視普通人,并舉了索福克勒斯的兒子和阿里斯托芬戲劇中的人物來說明普通人對于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影響。之后作者用一句話將目光轉回對中國人的分析上:But who is the common man, and what is he? The Chinaman exists only as a general abstraction in our minds. 該句在原文中作為新一段的開始,而合譯本并未分段。也許是句首的But一詞使人用慣性判斷這句話與前文粘連性較強,但筆者認為該句引導的后文意在對比中西方發展軌跡的不同,通過解釋中國人獨有的歷史傳統和相同的文化來證明中國特色的社會文明,兩段論述重心存在較大差異。且作者以兩個問句開頭,意在引發讀者的思考和興趣,突出下文論述的重點,此時順應原文的格式和邏輯處理更佳,合譯本段落合并的方式既模糊了論述重點,使得前后兩部分內容差異無從體現,也讓原本簡明清晰的段落變得冗長。然而并非所有用轉折詞、連接詞開啟新段落的部分都不可在翻譯時更改,當新一段與前文關系密切時,譯者可以通過合并段落強調遞進或轉折的關系。如原文Home and Marriage一節中,作者提出一個問題:Have women really been suppressed in China, I often wonder? 然后通過論述盡管女性受到不公平待遇,仍有權管理家庭,且官吏的小妾們也能控制老爺。隨后作者用一個連接詞and+評述性狀語開啟下一段: And what is still more important, women have been deprived of every right, but they have been deprived of the right to marry. 這既是對作者提出問題的回答,又是對前文論述的補充,因而與前文在邏輯上都緊密相連。據此,兩版本譯文均合并為一段,黃譯本處理為“更需注意者 ……”,合譯本譯為“更重要的是……”,充分說明了后文的遞進關系。
至此,筆者以語言風格標準入手,從四字格、信息增刪、被動句及段落分合對兩個譯本進行對比。黃譯本存在語言形式不統一、增添冗余信息、忽視原本文化語境和情感色彩的缺點,但也考慮到增補動詞、合理處理被動句、重視語篇銜接的問題。相比而言合譯本雖有功有過,但整體暴露的語言問題較少。
(二) 文體標準
關于文體標準,王宏印(2016)曾提出翻譯中的文類或文體處理的基本原則:“一個是保留原文本的文體類型和品位并與之對應,一個是改變原文本的文體類型,或者使其上升,以提高品位,但又增加了翻譯的難度,或者使其下降以助普及,并可減少翻譯的難度。當然,這里的文本類型變異是相對的,其依據是詩劇高于詩,詩高于散文,散文高于小說,在這個意義上,無本回譯的文體標準,也可以參照執行。”My Country and My People作為一部僑民所著的向西方世界介紹古今中國的小說,其中含有大量反映中國文學、藝術和政治生活的詩歌及古文,這類型的回譯屬于一定程度上的“有本回譯”,只需回溯其原文,將其原封不動呈現給對本族文化耳熟能詳的讀者即可。兩版本都充分尊重本族文化之根,做到了對文本準確充分的還原。其次,黃譯本在翻譯時多采用四字詞語,夾有部分生僻字或由富有文化底蘊的表達,如描述雅典人時,稱其:“終日狂飲饕餮,唯以醉飽為務,爭辯紛紜,譎辯狡猾,唯利是圖”,指出愛護女性的特性在中國早期歷史上“付之闕如”,且多用銜接詞遂、蓋、雖、仍等。與之相比,合譯本對這兩處的處理分別是“喝醉酒,貪吃,愛吵架,貪污受賄,喜怒無常”以及“在中國的早期歷史上,卻看不到這種對婦女的感情”,而連接詞也采用更通俗的表達,包括于是,所以,因此等。可以看出,黃譯本對文字的處理在復古中夾在著一些晦澀,多用銜接詞使得句子短小凝練,這是由于其所處時代雖已發起白話文運動,但也免不了文白夾雜的使用。而合譯本時期已處于20世紀后半期,其行文簡潔流暢,易于理解,對句子的銜接和整合處理拿捏到位,因而也更適合當代讀者掌握原文全貌。合譯本也曾在譯后記中說道:“為了適應當代讀者的需要,譯文采用現今通用的語體文,力求明白曉暢而又生動活潑。”作者精準定位目標讀者的能力及謹慎選擇語言風格的態度也由此可見一斑。
通過分析,筆者認為在文體方面兩版本譯者都較好地保留了原文本的類型和品味,只是限于時代特征,黃譯本偏向于文白夾雜,而合譯本更為通俗,易為大眾所接受。
(三) 文化標準
僑民文學作品涵蓋了中國歷史文化的方方面面,回譯時要做到本土文化的落腳與回歸。
例5:Starting out with the dualistic notion of yin(female)and yang(male) principles, already current in the period of the Warring Kingdoms…
黃譯:道家的陰陽二元意識,在戰國時代已流行。
合譯:陰陽二元說早在戰國時期就很流行。
作者為了這一概念更好地為西方讀者所接受,在括號中用female和male作為補充,深入淺出地向讀者展示了其基本內涵。而考慮到陰陽概念早已融入中國人的日常生活及表達中,兩版本譯者都沒有處理原文括號中的內容。原文與譯文差異的展現既迎合了讀者的審美和閱讀需求,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的不同,強調僑民文學中文化回歸的必要性。
四、結語
僑民文學的無本回譯是依托語言、文體及文化標準指導下所進行的翻譯活動,要求譯者在觀照語言文化差異的前提下統籌好各個翻譯要素。《吾國與吾民》的漢譯作為個案,有助于人們在認識無本回譯這一理論的基礎上進一步了解僑民文學漢譯的過程,完善理論應用的框架。通過兩個譯本對比,筆者認為譯者們都緊緊圍繞原作向西方世界構建中國形象的初衷,力圖還原原作風貌。由于所處時代不同,不同譯者對譯文的處理方式也各有千秋。黃譯本文白夾雜,語言復古凝練,行文邏輯嚴謹,但在細節的處理如語言結構平衡及對中西文化差異的關注度上不夠。合譯本兼顧原文風貌和當代人的閱讀習慣,使得讀者基于這一文本得以審視自我,這對于文本本身創作意義和譯本帶來的文化反哺價值都是一次積極的印證。兩版譯本各有得失,因而沒有絕對意義上的終極范本之說。自原作1935年寫成至今,廣為流傳的翻譯版本只有黃嘉德譯本和合譯本,二者相隔時間較久,說明學界對《吾國與吾民》翻譯的關注度相對較低。原作在文學史上的地位無可非議,而譯作作為翻譯文學的地位須得在比較之中確立。盡管翻譯很難做到十全十美,但筆者認為若有更多的學者汲取前人的經驗參與這一經典作品的翻譯當中,既可豐富無本回譯理論的應用,又可在學術性、藝術性和可讀性上更上一個新臺階,敦促當代讀者以嶄新的眼光解讀文本,使其在當代社會煥發新的生機。
參考文獻:
[1] 陳志杰,潘華凌. 回譯——文化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交匯處[J]. 上海翻譯,2008(3).
[2] 黃嘉德. 吾國與吾民[M]. 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8.
[3] 賀顯斌. 回譯的類型、特點與運用方法[J]. 中國科技翻譯, 2002(4).
[4] 郝志東,沈益洪. 中國人[M]. 上海:學林出版社,2007.
[5] 林語堂.M y Country and My People. 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0.
[6] 王晨爽. 讀者接受理論關照下的華裔美國文學翻譯——以《喜福會》的無根回譯為例[N]. 東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2).
[7]王 宏印,江慧敏. 京華舊事,譯壇煙云——Moment in Peking 的異語創作與無根回譯[J]. 外語與外語教學,2012(2).
[8] 王宏印. 從“異語寫作”到“無本回譯”——關于創作與翻譯的理論思考[J]. 上海翻譯, 2015(3).
[9]王 宏印. 朝向一種普遍翻譯理論的“無本回譯”再論——以《大唐狄公案》等為例[J].上海翻譯, 2016(1).
[10]吳 玲玲,李丹. 林語堂英文作品翻譯之特點[N].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學報, 2004(2).
[11] 王正良. 回譯研究[D].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論文 ,2006.
[12]曉 禪. 無本回譯視角下《花鼓歌》漢譯研究[D]. 江南大學碩士論文,2018.
[13]周 紅民,程敏. 回譯: 語言回歸亦是真—— 一篇歷史文獻回譯中的漢語體驗[J].上海翻譯,2016(5).
作 者: 王宇凡,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外國語學院文學在讀碩士,研究方向:翻譯理論與實踐。
編 輯: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