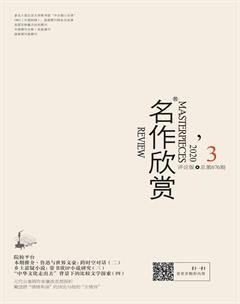21世紀新詩砥礪前行:光之旋律,美之哲思
摘 要: 當代青年詩人納蘭集詩歌創作、詩歌教學與詩歌評論于一身,可謂是“為詩而詩”之新人。納蘭的詩集《紙上音階》以美學之問、信仰之求、哲學之思引領中國當代詩壇。在文化全球化視域下,文壇新秀奠定了當代詩歌的主體性、文化創意與哲理風格。納蘭以詩之作顛覆歷史的霸權,建構時空的話語權。讀者欣賞此類作品終會收獲青春的反思、自由的理念與思想的火花;從中迸發生存力量,感悟生活意義,建構生命深度,賦予生態關懷,進而誘使讀者創作及反思,為中國當下的創意寫作教學夯實根基,推動中國詩歌的傳承、傳播與發展。
關鍵詞:21世紀新詩 光 美 納蘭 《紙上音階》
中國當代詩壇的青年才俊納蘭本名周金平,1985年生于河南開封,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詩刊社第35屆“青春詩會”代表。黑龍江省牡丹江師范學院2018級文藝學專業研究生及牡丹江師范學院“乃寅寫作班”特聘教師,主講詩歌類創意寫作課程。2018年6月,參加第18屆全國散文詩筆會、第11屆星星夏令營。2009年在《詩選刊》第12期首次發表詩歌之后,其詩歌及詩歌評論相繼發表于《詩刊》 《文藝報》 《星星》 《野草》《長江叢刊》《詩潮》等。 2016年獲25屆“東麗杯”全國魯藜詩歌獎優秀獎;2018年獲第三屆“延安文學獎·詩歌獎”; 2019年獲第四屆“詩探索·中國詩歌發現獎”。此外,文學評論著作《批評之道》被評為2019年度河南省作家協會重點扶持項目。
一、傳承與超越
青年詩人納蘭的詩集主要有《水帶恩光》《執念》《紙上音階》等,其中,《紙上音階》于2019年8月由南方出版社公開出版。我捧讀這位學生兼同事雙重身份之詩人的作品,不由地懷念青春年少的輕狂、精神豐腴的歲月及20世紀80年代詩歌的縱橫天下,更有人認為當代詩壇最重要的詩人依然是20世紀80年代的詩人。然而,我雖然相信舊人的坐標與偉大,卻堅信新人的開拓與唯美。20世紀80年代無疑是現代詩歌的黃金時代,中國詩壇群星閃爍,除北島、顧城、舒婷、海子這“四大詩王”以外,還有西川、流沙河、島子、殷實、雁北、簡寧、潞潞、韓東、于斯、牛漢、關鍵、馬麗華、馬學功、劉益善、劉立云、劉小放、梅紹靜、章德益、郁笛、江河、沙鷗、綠地等,尚有遍布全國的“大學生詩人”創作群體。海子就曾說過,80年代既不寫詩,又不讀詩的人都有病。80年代詩歌的輝煌映襯著當下詩壇的寂寞與冷落。
21世紀以來,各地詩壇也算是明星高懸,如雷平陽、韓博、莫非、馬麗華、黃斌、沈浩波、魯西西、楊鍵、朱朱、王小妮、王家新、于堅、綠原、屠岸、柏樺、田禾、周濤、菜耳、藩維、桑克、龐培、余怒、葉輝、宇向、伊沙等,詩人似乎化身為區域文化爭霸的代言者,詩歌創作群體的“地域化”昭示中國詩歌“大一統”時代的漸行漸遠。納蘭在《從思想的堅果里剝出詩歌的果仁》嘆道:“我站在光的相對論的另一側/明亮只在作為詞的時候,才值得信任。//還沒有用溪水更新體內的溪水/還沒有使星辰墜落為紙上的供詞。//灰燼的寂靜是我們的本質而童年的布老虎/已穿著大頭鞋走失。//哦,牧羊人,愿你的話語/變為拯救。”a納蘭志在探尋從詩學、美學及哲學到詩之路徑,“果仁”象征精神、純凈與種子,一如他在《隱秘之美》中所言:“我在所有的路上,渴慕‘道和‘美。” b文化全球化下,納蘭執著于詩歌的個體性與普遍性,他以語言與詞語為脈,借用光、黑暗、影子、風、雨、雪、淚水、琥珀、母親、身體、稻草人、薄暮、星空、大地、山、石、草原、沙漠、河流、小溪、水、樹、雛菊、落葉、接骨木、蒲公英、青松、青橙、石榴、草莓、麥子、荷、藕、米、螞蟻、羊、蛇、鳥、蝴蝶、蜜蜂、白鷺、蟬、草船、釘子、卷尺等審美意象編織空、無、靈魂、天堂、解放、消逝、自由、秩序、非相、隱喻、隱秘、凈化之美的哲思。
二、詩與美學
柏拉圖美學的千古之問在于求解而不得的感嘆:美是難的;《理想國》充斥著對待詩與詩人的矛盾。納蘭則認為詩是美的桂冠,詩亦是難的。詩之難難于創作、目標、作用與價值的維度。他在《詩難》中如此解析:“寫一首詩是難的/要經歷一次產難和受難/又要遭受非難。罹難。說難。/你想著也擁有一雙釘痕手/一頂荊棘王冠/擁有把水變為酒的技藝。/一個傳遞佳音的信使/有鴿子落在他的肩頭。/你在塵世經歷鞭笞、羞辱、責難、非議,/你在水邊如一棵垂柳/俯身傾聽蛙鳴、蟬鳴、喜鵲的嘰喳/一切聲音里的啟示。/詩是避難所,/詩是難的/你想將身體邀約到一首詩里/但沒有通道。” c在納蘭看來,審美主體注定在劫難逃,唯獨詩不是苦難,卻難以找到歸途。詩人將自身的苦難孕育為靈與美,唯有經歷磨難的詩人方能驗證“詩藝無藝”“詩人不幸詩家幸”的境界與傳說。
現代詩的本真在于以字詞聯盟的外在形式,表達形而上學的含義與意義,呈現犧牲之美與理趣之味。納蘭在《詞語的肉身》中將詩歸結為以語言的變體傳遞不變之理的火炬,由是,詩人高居啟蒙者與圣者的位置,坦然面對悲劇及悲劇之美:“節節草每一節都有自己的意愿/倘若一心建造通天塔,就要把己意順服于天意。//一條繩子的一生,/繩結即劫難。//安禪之人,/他把松散的光陰搓成了捆縛毒龍的繩。//一生都輸給了光陰。/一生都在尋找詞語的守恒定律,/把生命之光傾倒給詞語的肉身。//一生也當知足于/幾個單詞里釋放的不竭的光/酷愛光的人,/早已成了‘夸父。” d詩人同樣是英雄,以“不可為而為之”的擔當和孤寂播散藝術的火種。天才詩人的凄涼與創造性皆源于此,他們在命中注定的苦難之旅中鑄就向上的追求、抒發向善的情感、安撫向美的靈魂。同時,弘揚生命的內涵與真諦,承繼中華民族的文化內核與精神要素,演繹東方美學的極致。
三、詩意地棲居
21世紀新詩構建生態審美文化之維,回應自然之殤與時代之痛。納蘭慮及“我們能到哪兒去?”之類的終極問題,《砍伐》辯證地重新審視人與自然之間的依存關系:“輪到森林去砍伐人,成為自己的主人。/有的樹木成為斧子的把柄。/有的樹木咬住了斧頭,/成為消解暴力的美學。//你的魔術之手從樹木的身體里,/掏出椅子、梯子和柜子。/直至將樹換成一個樹洞,/你對著樹洞訴說自己的虛空。//你想將椅子、梯子和柜子放回去,/但已無安放它們的身體,/魔術已經失手”e。詩人以生態審美意識貫穿整個作品,森林是生命的容器、時間的秩序和歷史的見證,生態環境的存在就是人類生活的起點與終點。作者在不露聲色中無可奈何地惋惜人類的幼稚無知,竟然世世代代以宇宙的主人自居,當眾神在破壞力中退隱而去,留下赤裸裸的蒼涼與沉寂時,后悔莫及的人類甚至缺乏面對這滿目瘡痍的頓悟和勇氣。
新世紀詩人用青春為生命吶喊,用藝術之美化真理為信仰。納蘭在《詩的功效》中寓詩人及詩以生生不息、永不屈服、至死不渝之崇高的力量與形象,“一條光的繩索。/他背著/看不見的五行山,宛若西西里弗推著自己的石頭”f。西方美學史上,雖然黑格爾力圖除掉藝術為哲學開道,但藝術絕不會終結,不僅因為藝術伴隨人類誕生而來,更因為偉大的藝術家已在、尚在且將在。鮮活的讀者有責任本著摒棄厚古薄今之態度,在跨文化認同及審美記憶中,學習且傳承新世紀的詩之歌及詩人的創新精神,促進中國當代詩歌的創作、欣賞與研究。
abcdef納蘭:《紙上音階》,南方出版社 2019年版,第20頁,第28頁,第 13頁,第 40頁,第50頁,第122頁。
基金項目: 教育部地方高校第一批本科專業(漢語言文學)綜合改革試點項目(項目編號:ZG0143);黑龍江省優勢特色學科建設項目“地方語言文學”(項目編號:DF-2017-10233);牡丹江師范學院教育教學改革工程項目“地方高校創意寫作人才培養的研究與實踐(項目編號17-XJW19023);牡丹江師范學院博士科研啟動基金項目“牡丹江民俗文化產業發展研究”(項目編號:MNUB201606)的階段成果
作 者: 王丙珍,哲學博士,牡丹江師范學院教授,碩士生導師,黑龍江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博士后流動站在站博士后,研究方向為當代審美文化、北方少數民族文學研究及創意寫作教學研究與實踐。
編 輯:趙紅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