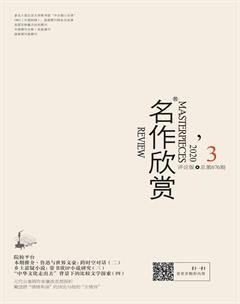論布萊希特《三毛錢小說》
摘 要: 撒旦(惡)本應潛藏于黑暗中,停留在人的無意識領域,但它卻走到了陽光下面,呈現在讀者面前,這種令人陌生而又熟悉的事物令人感到恐懼。恐懼是對某種本應隱蔽起來卻顯露出來的東西的心理反應,從創作理念上說,這正是布萊希特倡導的“陌生化效果”。他把《三毛錢小說》寫成一部散文形式的《惡之花》,因為布萊希特意識到,比起善來說,破壞性的惡更是歷史發展的重要動力。
關鍵詞:撒旦 本我 恐懼 陌生化
作為20世紀德國最具震撼力的劇作家、詩人、導演和戲劇理論家,布萊希特創立和發展的“史詩戲劇”以及“陌生化效果”,不僅給現代劇壇注入了蓬勃生機,也是對西方傳統戲劇的一次顛覆性突破,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布萊希特置小說創作于次要地位。
早在 20世紀 20年代,布萊希特就考慮過創作長篇小說,1920年7月1日他在日記中這樣寫道:“我有很多想法……還有很多關于如何寫小說的認識,這些認識之所以引人入勝,因為它足以置因為(所有其他)小說而早已存在的傳統以死地。”a應該說《三毛錢小說》 就是一部充分體現布萊希特對小說想法的作品,同時也是布萊希特計劃創作的數部長篇小說中唯一完成的一部,在世界文壇上有“德國最重要的流亡作品”和“德國文學史上最重要、最淵博的諷刺小說” 之稱。
《三毛錢小說》 是布萊希特在1933年至1934年流亡丹麥期間完成的,這是一部 “反向改編” 的作品。b1928年,布萊希特把英國劇作家約翰·蓋伊的《乞丐歌劇》改編成《三毛錢歌劇》,這個劇作給他帶來國際聲譽,也是他史詩戲劇的第一次成功實踐,而《三毛錢小說》又改編自《三毛錢歌劇》,這樣說來, 《三毛錢小說》不僅是一次“反向改編”的作品,而且也是一部“雙重改編”之作。
《三毛錢小說》雖然改編自《三毛錢歌劇》,借用了后者的主要人物與情節,與后者存在著一種堅定的互文關系,但這并不意味著在讀《三毛錢小說》之前讀者要先去劇院看《三毛錢歌劇》,或者要先去讀《三毛錢歌劇》的劇本。實際上《三毛錢小說》就是一部地地道道、如假包換的小說,它與其他小說并無二致,如果說有的話,那是因為布萊希特是一位善于與魔鬼打交道的人,加上他對小說的獨到思考,使《三毛錢小說》展現了一個異彩紛呈的奇妙惡世界,讓人感到既驚心動魄卻又魅力無窮。
布萊希特把《三毛錢小說》的背景放在19世紀末到20世紀初的英國倫敦,主人公皮丘姆表面上是一家出售舊樂器的商店老板,實則是倫敦丐幫的幫主。他像任何一位資本家一樣進行剝削,只不過他剝削的對象是乞丐,他是倫敦行乞行業的壟斷資本家;與他產生交集的是一位綽號“尖刀” 的麥奇思先生,他是一系列廉價品商店的老板,這種商店以大甩賣的價格拋售商品,商品價格十分低廉,因為它們全部都是偷來的,麥奇思可以說是盜竊行業的壟斷者,他把倫敦的全部盜賊都變成了他手下的雇員。麥奇思偷娶皮丘姆的女兒波莉,婚宴上警察總督布朗竟然前來道喜,原來麥奇思和布朗是鐵哥們,強盜和警察是一家。丐幫和強盜本來就不和,于是皮丘姆去告發麥奇思,緊要關頭警察頭目布朗幫助麥奇思,使他搖身一變成為“銀行家”,隨后麥奇思又同皮丘姆沆瀣一氣,合伙對倫敦民眾為非作歹。小說的結尾是受剝削壓迫最重的退伍傷殘士兵費康比被判處死刑并被絞死。行刑時,一大堆小業主、縫紉女工、傷兵和乞丐在場,大家無不拍手稱快。讀者讀到這里不禁毛骨悚然,正如評論家所言:“很難想象還有什么更凄慘、更無指望的結局了。”c
德國文藝理論家施勒格爾認為:“如果在一部長篇小說里,以一種有趣的方式塑造并闡明了一個全新的性格,那么即便依照最尋常的看法,也足以使這部小說出名。”d應該說,布萊希特在《三毛錢小說》中就塑造了一種全新的性格——撒旦式性格,而這種撒旦式性格卻又散發著奇妙的惡的魅力。比如丐幫幫主皮丘姆,他不應被看成是通常模式的吝嗇鬼,他是個惡棍,這毫無疑問,他的罪行在于他的世界觀;“變壞是根本沒有止境的。這是皮丘姆深信不疑的,也是他唯一的信念”e。既然他有這樣的信念,他做起事情來完全沒有底線,為所欲為。他把自己的女兒波莉當作資本,把她推到一個令人作嘔的色鬼的床上,因為在他看來,自己的女兒也如同《圣經》一樣,只不過是給他提供幫助的渠道罷了;他在把女婿麥奇思送上絞刑架之前,把他當作空氣,從不看他一眼,因為皮丘姆想象不出有任何一種個人的價值能吸引他對這個奪走他女兒的人采取另外一種態度。“尖刀”麥奇思及其罪行之所以使他感興趣,是因為他可以假借這些罪行殺人。而書中另一位撒旦式人物威廉·科克斯,他作為一名經紀人,卻勾結政府要員弄虛作假,絞盡腦汁地把貨真價實的“水上棺材” 偽裝成舒適豪華的游艇,把幾艘破爛不堪的舊船賣給國家充當運兵船,結果使滿船官兵全都命喪海底,因為作為把賺錢當作自己生活內容的科克斯與其商業伙伴都深深意識到:“這種盯人的競爭真可怕!不管什么卑鄙的生意,只要你不干,馬上就會有其他人來干。一個人不得不忍受很多事。你如果感情沖動,即使只有一秒鐘,那你就全完了。只有鐵的紀律和自我克制才能成功。”f《三毛錢小說》中充斥著各種各樣、形形色色的撒旦式人物,充滿著畸形、暴戾、黑暗,令人觸目驚心、脊背發涼,讀者讀后“與其說感到厭惡,還不如說感到悚懼”g。
但這又有什么新奇之處呢?在此之前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里就充滿著長長的一大串窮兇極惡、光怪陸離、滿身血污的大資產階級身影,把人嚇得膽戰心驚,《人間喜劇》的主導方面不是肯定與頌揚,而是批判與否定,在巴爾扎克的作品中,丑惡得到了痛快淋漓的表現。馬克思就曾經說巴爾扎克寫的是“殺人、通奸、詐騙和侵占遺產”的人的歷史,盡管如此,巴爾扎克畢竟還對《人間喜劇》中的貴族寄予深深的同情,為他們唱了一曲無盡的挽歌。這一方面說明了巴爾扎克頭腦中殘留著貴族觀念;另一方面,從深層象征意義上看,巴爾扎克筆下的貴族形象,又是人欲橫流時代人的理性與善的象征,寄予了巴爾扎克對人性復歸的希望。布萊希特與巴爾扎克的不同在于《三毛錢小說》中沒有正面人物形象,當然更談不上通過正面人物形象寄托作家對人性復歸的希望。布萊希特筆下的世界是鬼魅的世界;在這里,人脫去了虛假的道德外衣,赤裸裸地走向讀者,他們不再高貴,不再優雅,而變得自私、兇殘、專橫,一切人性之惡都表現出來,就是人們最心儀的男歡女愛,也變成了金錢魔鬼式的愛情;愛情不再是人類精神的一種最深沉的沖動,而是暴露他們身上的惡的化學試劑。 “尖刀” 麥奇思認為“女人委身于一個男人,責任自負,風險自負。他完全反對給女人規定條條框框。愛情不是養老保險”h。他在心里是這樣反思自己對波莉的感情的:“同一個姑娘結婚,是看中她的錢還是看中她的人,這樣自問是完全錯誤的。兩者常常兼而有之。一個姑娘家很少有什么東西能像一筆財產那樣激發一個男人的熱情。她沒有財產,我當然也會想要得到她,但是或許不會這樣熱烈。”i而當波莉奉父親之命來誘惑科克斯,在科克斯的寫字桌上看到一枚她估價大約為二十英鎊的胸針時,在她的想象中這枚胸針便與科克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內心進行著對各種親密接觸行為的價格計算:“超過接吻是完全不可能的,至多他可以摟抱我。這對那枚胸針來說并不多。”j
在《三毛錢小說》中,不僅愛情喪失了使人們的生活充滿溫柔和芳香的能力,就連懸壺濟世的醫生也道貌岸然起來,暗地里“大刀闊斧”地為人非法墮胎,表面上卻冠冕堂皇地大談宗教和道德的神圣、官方禁令、職業良心等,他對前來找他做墮胎的波莉這樣說道:“您向我提出的是何種非分要求?一切生命都是神圣的,且不說這方面有公安條例。醫生要是做您想的那種事,就會失去自己的診所,而且還要進班房……這畢竟是非法手術,即使為了患者的利益而不用麻醉藥,也得要十五英鎊,而且要先付,免得事后翻臉不認人……親愛的小姐,腹中的胎兒就像其他生命一樣神圣……星期六下午我有門診……還有,您把錢帶來,不然您就根本不必再來了……”k正如評論家所言:“對混亂不堪的世界中那種混亂不堪的人際關系進行如此冷酷刻畫的,除了布萊希特外,恐怕很難找到第二個人了。”l
本杰明·富蘭克林是18世紀美國最偉大的文學家,他的《自傳》被譽為美國文學史上第一部經典文學作品,他用自己的經歷回答“人如何生活”這個大難題,自傳中最吸引人的部分,是他為自己制定的達到完美品德的十三種德行計劃。可以說,道德的自我完善是富蘭克林在《自傳》中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布萊希特在《三毛錢小說》中從另一個角度回答了“人如何生活”這個天字號第一大難題,書中這樣寫道:“人究竟靠什么活?靠每時每刻折磨、掠奪、襲擊、扼殺、吞噬人!只有完全忘掉自己是人,人才能活。先生們,休要自作聰明,人只有靠作惡才能活!”m德國哲學家叔本華認為:和動物一樣,人類主要的和根本的推動力是自私的,也就是對自己生存和舒適的追求。但不要忽略的一個事實是,人類同所有其他動物有一個本質的不同,那就是人類建立了道德的體系,試圖以此約束其自私的天性,因此,如果以盜竊、搶劫或殺人來作為獲得資源的手段就會受到道德規則的約束,他能夠憑良心覺得自己所做的違背道德的事很不好,產生負疚感。吃掉了羚羊以后,獅子就已經滿足了,事情僅止于此。人也需要美餐,但對人來說僅有美餐是遠遠不夠的。畢竟,人類生活中確實存在一種無論如何也要捍衛的超越一切的價值,雖然,一旦涉及細節問題,涉及具體的情況,人們的思想和道德情感就開始發生分裂。但是另一方面,惡也與我們息息相關,惡與我們如影隨形,魔鬼、女巫、吸血鬼,等等,等等,他們雖是文化虛構出來的產物,但人們正是用它們形象地對惡進行描繪,這一類惡形惡狀的事物教育我應該感到害怕,同時也召喚我們與之交鋒。
從某種角度上說,基督教完全清楚來自惡的這一方面的長期誘惑,甚至耶穌都受到過魔鬼的誘惑,魔鬼將世上的萬國與萬國的榮華都指給耶穌看,并對耶穌說,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這一切都賜給你(具體參見《馬太福音》第4章第8節)。耶穌拒絕了,但誘惑始終都非常巨大,畢竟,大多數人都不像耶穌那樣堅若磐石,毫不動搖。其實,我們根本沒有必要借助惡魔來對惡進行具體的想象,因為,“惡真實地存在著,它就存在于人類的形象之中,潛伏在我們每一個人身上”n。格奧爾格·西美爾在他的《社會學》一書中是這樣說的:“惡與秘密有一種直接的內在聯系。”o是的,按照現代精神分析學家弗洛伊德的觀點,撒旦不是什么外在之物,它來自于人類的潛意識,是本我,是受到壓抑、排斥的欲望,是本能的形象化表達。本我“沒有價值觀念,沒有倫理和道德準則。它只受一種考慮的驅使,即根據唯樂原則去滿足本能的需要”p。撒旦對上帝的反叛,正是欲望、本能以其強大的生命力對道德律令的挑戰與撻伐。畢竟,道德是建筑在群體的彼此約束上的,而本能是活生生的生命之根,具有冒險精神和反抗性,使生命呈現出豐富性與生動性。從某種角度上說,對于本能的扼殺就是文明對生命的禁錮,就是上帝對撒旦的懲罰,就是超我對本我的壓抑。人不能長久地囿于知覺狀態,他必須重新闖入無意識存在中,因為那里存在著他的根。
歌德的《浮士德》就是這種“根”的產物,是歌德擺脫自我知覺狀態而進入無意識存在的本我產物。如果說生命之花的開放需要根的話,那么這花一定是艷麗誘人而又邪惡的“惡之花”,是那心理潛意識哺育了它。所以榮格說:“《浮士德》并非是歌德創作的,而是《浮士德》創作了歌德。”q
應該說,布萊希特的《三毛錢小說》就是一部散文體的“惡之花”,給讀者帶來一種驚懼的恐怖美,而恐怖又是與人類自我保護的機能相聯系,所以恐怖有一種更加深刻的審美效果。弗洛伊德認為,在常人的理解中,害怕的東西之所以嚇人那是因為它不為人所熟悉或了解,實際上這種觀點是錯誤的。他認為恐懼是對“某種本應隱蔽起來卻顯露出來的東西”的心理反應,因為“令人害怕” 的事物是腦子里早就有的,只是由于約束的作用,它才被人從腦子里離間開來。“這種同約束因素的聯系使我們進一步懂得謝林對‘令人害怕的所下的定義,某種本應隱蔽起卻顯露出來的東西”! 8。在弗洛伊德看來,害怕的感受來自于本應受到約束的熟悉的東西,這種東西就是本能,人類的本能應該深藏于潛意識領域,如果它被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就會遭到道德的懲罰。這種對道德戒律的畏懼就是恐怖。撒旦(惡)本應潛藏于黑暗中,停留在人的無意識領域,但它卻走到了陽光下面,呈現在讀者面前,這種令人陌生而又熟悉的東西又怎能不令人感到恐怖?從創作理念上說,這也正是布萊希特倡導的“陌生化效果”。他認為“陌生化的反映是這樣一種反映:對象是眾所周知的,但同時又把它表現為陌生的……毫無疑問,這種陌生化效果會阻止發生共鳴”s。共鳴訴諸人的情感,造成喪失主觀能動性的負面效應,會讓人喪失改造現實世界的沖動,“每一種旨在完全共鳴的技巧,都會阻礙觀眾的批判能力。只有不發生共鳴或放棄共鳴的時候,才會出現批判”t。畢竟“藝術之成為藝術,是因為它具有使人精神獲得解放、震動、奮起及其他種種力量。倘使藝術無能力為此,它就不是藝術了”@ 1。這樣看來,布萊希特把《三毛錢小說》 寫成一部散文形式的《惡之花》,是因為他意識到,比起善來說,破壞性的惡更是歷史發展的重要動力。它表現為一種原始的力量,表現為對一個舊時代的否定,還表現為對某種既定價值的顛覆,因為布萊希特堅信:“這個可怕而又偉大的世紀的人是可以改變的,他也能夠改變這個世界。”@ 2
a 〔德〕布萊希特:《三毛錢小說》,高年生、黃明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譯本序,第1頁。
b 關于布萊希特把《三毛錢歌劇》改編成《三毛錢小說》的問題,本人已有專文論述,具體參見:《論布萊希特的反向改編——從〈三毛錢歌劇〉到〈三毛錢小說〉》,《戲劇文學》2012年第7期。
cl〔德〕瑪麗安娜·凱斯廷:《布萊希特》,羅悌倫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2年版,第132頁,第112頁。
d 〔德〕施勒格爾:《雅典娜神殿斷片集》,李伯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96年版,第135頁。
efhijkm〔德〕布萊希特:《三毛錢小說》,高年生 黃明嘉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7頁,第35頁,第122頁,第24頁,第101頁,第58頁,第40頁。
g 〔德〕沃爾夫岡·耶斯克:《三毛錢小說的影響》,轉引自布萊希特:《三毛錢小說》,高年生、黃明嘉譯,附錄二,上海譯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369頁。
n 〔奧〕弗朗茨·M·烏克提茨: 《惡為什么這么吸引我們?》萬怡 王鶯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4頁。
o 轉引自〔德〕彼得-安德雷·阿爾特: 《惡的美學歷程——一種浪漫主義解讀》,寧瑛等譯,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版,第315頁。
p 〔美〕卡爾文·斯·霍爾等: 《弗洛伊德心理學與西方文學》,包華富等譯,湖南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27頁。
q 〔瑞士〕榮格:《現代靈魂的自我拯救》,黃奇銘譯,工人出版社1987年版,第249頁。
q 〔奧〕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論創造力與無意識》,孫愷祥譯,中國展望出版社1987年版,第149頁。
st@ 1 @ 2〔德〕布萊希特:《布萊希特論戲劇》,丁揚忠等譯,中國戲劇出版社1990年版,第22頁,第240頁,第6頁,第66頁。
基金項目: 本文系2019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拔尖研究項目“布萊希特研究”階段性成果
作 者: 何玉蔚,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世界文學博士,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與闡釋學研究中心副教授,研究方向:西方文學與文化。
編 輯: 張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