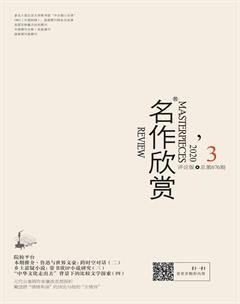不忘故國的梅下僧人
摘 要:方以智《梅花詩》 中的遺民情結經歷了覺醒、勃發、堅定三個階段,體現了他明亡之后由傷懷、落寞再到固守忠節的心路變化:在山河破碎、憂愁憔悴之際見梅花盛開,欲借賞梅以銷亡國之愁,是遺民情結的覺醒階段;梅開易謝,雖自然之理而人生難免有情,感物之余,生歸隱之思,托心志于佛理,此為遺民意識的勃發階段;自幼受到忠節思想影響的方以智難忘故國,他以出家為僧的方式對抗清廷的逼仕,最終借“詠梅” 堅定了自己遺民情結。
關鍵詞:方以智 梅花詩 遺民情結
方以智詩集中共有三十八首梅花詩,分為三組,分別是《梅花十首》 《和白門梅花韻十六首》 《又梅花十二首》,均見于其《浮山后集》。《梅花十首》題下自注:“仙回西溪,梅花十里,嚴伯玉引愚于此,不覺呻吟。”a此詩作于廣西,據任道斌《方以智年譜》:順治七年十一月,清兵陷桂林,平樂等相繼告陷,方以智匿入仙回山南洞。清兵于平樂搜以智不得。追至仙回,拷逼嚴瑋以求以智。閏十一月,以智剃發僧服出,以免嚴瑋。b則 《梅花十首》作于方以智順治七年十一月至閏十一月間,此詩作后不久,方以智為保友人無恙,出家為僧。《和白門梅花韻十六首》《又梅花十二首》作于順治九年,方以智隨施閏章北歸桐城后,為避清廷征召,受戒于南京天界寺。《和白門梅花韻十六首》題下自注:“本和之,不知是梅下僧不耶?”c陳垣先生說:“明季遺民逃禪,示不仕決心也。”d方以智之逃禪,最直接的原因即在于此,其梅花詩中深厚的遺民情結乃是“言為心聲”的反映。
一、觀梅:遺民情結的覺醒
(一)渲染梅花香色:色在空中驕白日,香從冷處傲紅爐 亡國后飄零困苦、閉關苦節的方以智在觀梅時遺民情結漸漸覺醒,但“梅花之美” 似乎阻礙了這一進程,他仍然回歸詠物詩本身,不吝用層層渲染之詞去描摹梅花的外在品質,他自嘲:“逢場眼見繁華盡,翻笑雕蟲興未闌。”(《和白門梅花韻十六首·一》) 詩中隨處可見對梅花香氣和姿色的夸贊:
眼開便見千秋白,蕊破先傳五葉丹。黍谷吹成香道路,蘆笙解唱玉闌干。(《梅花十首·一》)
步障銀鉤罩曲阿,四天螺黛散兜羅。衣飛小白門前像,雪涌空青海里波。(《梅花十首·三》)
霧縠輕盈護素沙,珊珊玉立薄帷斜。誰留南國當初種,剪破東風第一花。(《和白門梅花韻十六首·三》)
色在空中驕白日,香從冷處傲紅爐。(《又梅花十二首·四》)
中國古人有一個傳統,“凡言花卉,必須附會以婦人女子,如玉蕊花則言有仙女來游,杜鵑花則言有女子司之” e,“梅”作為美人的形象在古代詠梅詩中數見不鮮。南朝艷體詩流行,借梅花以寫美人之風很盛。唐人筆下梅花美人詩則較為清麗,“以塑形,顯貌為主,比之六朝詠梅詩更本真,更具有文學性,還原了文學的面貌”f。方以智詩中的梅花形象既有“霧縠輕盈,珊珊玉立” 這種大家閨秀的嬌羞之美,又不乏驕白日的艷麗之美與傲紅爐的冰冷之美,可以說眾美的合體,足見其對梅花的癡迷之深。
(二) 借賞梅以銷愁:癡坐竟拋班草杖,飽看懶唱采薇歌 方以智如此癡迷梅花香色,一是他作為詩人兼畫家對美感的回應,不自覺地形于歌詠,方以智在組詩中還提及畫梅之舉,如“紗縠朦朧難說喻,珠璣咳唾更迷人。此回拜見真高士,面目當前寫得真。”(《又梅花十二首·八》)丹青詩文,形式不同,內在多相通,尤其是“詠物詩” 和“寫生畫”。“詩畫本一物,天工與清新”,身兼數藝的蘇軾正是看到了詩畫的相通之處。二是身心沉浸在梅花之美的方以智暫時忘記了山河破碎的黍離之悲、親友隔絕的別離之痛,他在梅花詩中也不諱言此點:
癡坐竟拋班草杖,飽看懶唱采薇歌。不勞帝釋珠宮雨,埋怨空生漏洩多。(《梅花十首·三》)
舊家手跡白描新,想象羅浮見不親。 雙鬢久忘江南信,一枝空憶嶺南春。(《和白門梅花韻十六首·六》)
方以智賞梅進入一種癡迷的狀態,一旦脫離這種狀態,他的“家國之情” 又涌上心頭”,《梅花十首》 作于嶺南,如果說尚在漂泊之中的方以智尚能借賞花以銷愁,那么痛定思痛,他北歸后回憶多年的流離歲月,難免觸物生情,故而順治九年的這兩組梅花詩較少渲染梅花的外在美,多詠其內在品質,且不乏傷時之句。
二、惜梅:遺民情結的勃發
(一)落梅之感:美人面目終黃土,禪客衣囊盡白云 甲申農民軍攻陷北京,方以智守節不屈,拋妻棄子,逃到南都。當時弘光朝由阮大鋮主政,混淆是非,阮與方以智為同郡世仇,遂遭誣陷,他不得不按照好友陳子龍的指示流離嶺南。家學使他養成了根深蒂固的忠節思想,山河破碎、身名俱辱對他的精神創傷較一般士子更甚,而梅花正如一劑強麻醉藥,使他的身心進入一種絕對麻木的狀態。但人們一旦依戀于某物,其遽然離去必在心理上形成很大的落差,如果說觀梅阻礙了方以智遺民意識的覺醒,那么落梅則使得方以智的遺民情結徹底勃發。故詩句中難掩惜花凋零、百無聊賴的傷感:
憶遠忽同千里色,參天能隔幾重云。玻璃嚼碎敲空問,鐵笛橫吹總不聞。(《梅花十首·四》)
天上招魂非筆墨,空中埋玉免塵埃。和根擲向蓬萊外,枉費深山瘠土載。(《梅花十首·九》)
萬代皆傷此日寒,枯腸冰冷墨痕干。人間屬和千篇易,世外傳真一筆難。(《和白門梅花韻十六首·一》)
片片都歸玉塵分,冷風一陣更紛紜。美人面目終黃土,禪客衣囊盡白云。(《和白門梅花韻十六首·九》)
對“落梅”的吟詠可以溯源到《詩經·摽有梅》 一詩,毛詩說:“ 《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g意在歌詠文王之德。我們也可以將其看成一首愛情詩,反映的是作者老大無偶的急切之情,后代的文人或借以表達懷才不遇之情,而落梅詩主題也有變化,但感情基調多偏于消極,偶有一二作家出奇立論,欲與古人爭勝,似不能改變“悲涼” 的落花意象。花開花謝,本是自然規律,又何足悲?然詩人賦予“物” 以情感,“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h。方以智的這些落梅詩風格傷感而悲壯,遭遇國變,蒙受冤屈,流離萬里,兵火中原,故而有“枯腸冰冷墨痕干”的心境,欲借文字來舒緩這些堆積起來的復雜情緒。“腥風匝地”“哀寄江南”皆直道時事。“萬代皆傷此日寒”,斯復何時,不自我先,不自我后,這種仰天長嘆大有生不逢時的意味,《詩經》 中也不乏此類純粹哀嘆的作品,古人將其定義為“變風變雅”,《毛詩》 說:“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i青年方以智詩風慷慨悲壯,他從不諱言這種“變風變雅” 的亂世之音:“今之歌,實不敢自欺,歌而悲,實不敢自欺。既已無病而呻吟矣,又謝而不受,是自欺也,必曰吾求所為溫柔敦厚者以自諱,必曰吾以無所諱而溫柔敦厚,是愈文過而自欺矣。”j可貴的是中年方以智仍然保持著以往詩風,是真名士自風流,不妨將負面情感直接表達出來,故直言傷心、哀慚,皆觸目時事而發。傷心人別有懷抱,此時見落梅,借以銷愁忘憂之物遽爾失去,本就傷懷的方以智表現出不舍的情感,但“天上招魂”“人間吹笛”,總難免“美人面目終黃土”的現實。
(二)逃禪之思:琉璃殿上燈明滅,瓔珞光中幔有無 隨著意志的進一步消沉,方以智生出避世隱居的念頭。梅花已謝,則聊以銷愁之物亦不復存,除眷戀親友外,萬念俱灰,唯托心佛法而已,文字亦可以棄絕不作:
編蒲羞學路仲舒,無柿無蕉棄蔽廬。信手拈為千載案,逢春聊當一行書。青牛望去成何氣,白馬奔來夢久疏。卻問看花聞道者,瑯函玉軸可如如。(《和白門梅花韻十六首·二》)
翻身親跳出冰壺,春在吾家壁不枯。雪竇閑時拋碎玉,灰堆何事羨真珠。琉璃殿上燈明滅,瓔珞光中幔有無。一瓣從旁疑此漢,和根拔問赤須胡。(《又梅花十二首·九》)
這種枯槁木石的狀態一與政治形勢有關,當時清兵由華北向嶺南擴張,永歷皇帝逃亡緬甸,如果說方以智在南明時期尚存恢復失地、還于舊都之望,此時的他祝法南京,不得不面對慘淡的形勢;二與個人心境有關,方以智飽嘗世情風波,少年時的濟世之志已漸漸淡去,唯望隱居讀書,參研易理,繼承家學,方以智說:“讀書之士,生當亂世,可謂至苦。然當亂世而舍讀書,則尤苦矣。”k其逃禪為避清廷征召,在思想上并非純粹的佛教徒,晚年的他倡導“三教歸易” 的學說,這種思想正是在逃禪中醞釀而成。方以智梅花詩中有部分關于逃禪的場景描寫:
甘露可知仙掌折,繁星落向玉樓明。叮呤末后巖頭句,彈指相逢日不輕。(《和白門梅花韻十六首·十六》)
生意須知出世殘,冰心死愛寶林寒。雖無南畝深耕苦,欲保東皇護法難。佛恨門庭傳粉本,天教風雨弄泥團,藥欄歲歲堆成浪,便倩花梢作探干。(《又梅花十二首·十一》)
梅花已謝,萬念俱灰,取枯梅之枝入室,托懷于青燈佛法,然生性通脫的方以智很快從消極頹廢的心境中脫離出來,他仿佛從逃禪中得悟大道。梅花雖謝,梅樹雖枯,然明年尚可再會,彈指相逢,且雖知出世之殘痛亦安之若素,盛衰有時,如花開花落,寒日盛開,春來自謝,知梅格仍在足矣。由于心境的轉變,方以智筆下的梅花形象從“美人”變成了“高士”,梅花的“高士”形象在宋代時盛行,林逋《梅花二首》:“孤根何事在柴荊,村色仍將臘候并。橫隔片煙爭向靜,半粘殘雪不勝清。”l 陸游以調侃的語氣說道:“梅花宜雪復宜陰,摩挲拄杖過溪尋。幽香著人索管領,不信如今鐵石心。”(《看梅絕句五首·一》) m明初高啟詠梅名句:“雪滿山中高士臥,月明林下美人來。”(《梅花九首·一》) n將梅花的“美人”與“高士”兩種形象并稱。方以智梅花形象的轉變是在遺民情結勃發后的冷靜思索,也是歷經困苦后自身精神層面的升華。
三、詠梅:遺民意識的堅定
(一)“愛寒”之梅格:生意須知出世殘,冰心死愛寶林寒 梅花凌寒而開、春暖即謝的花期特征在歷代文學中被人格化,并且賦予了它不畏困苦、不慕繁華的內在品質。方以智著重突出梅花以“愛寒”為中心的梅格:
第一天心只愛寒,東風珍重寫來難。眼開便見千秋白,蕊破先傳五葉丹。(《梅花十首·一》)
巉巖石骨倚香林,零雨連旬滿地陰。忽掛神州天盡月,安傳盤古歲寒心。(《梅花十首·六》)
歲寒蘅杜總荒蕪,結爻青蒼自托孤。色在空中驕白日,香從冷處傲紅爐。(《又梅花十二首·四》)
生意須知出世殘,冰心死愛寶林寒。雖無南畝深耕苦,欲保東皇護法難。(《又梅花十二首·十一》)
梅花的開放環境是寒冷的,而梅花似乎也很“享受”這種惡劣環境,在“蘅杜荒蕪”之際,獨立天地之間,與松柏皆有歲寒后凋之心,故謂之“愛寒”。東風春暖,百花盛開,則早已凋謝,無意與桃杏爭春,故“東風珍重寫來難”“欲保東皇護法難”。因梅花之性“愛寒”,故方以智又謂之“鐵骨”:“久知鐵是前生骨,偶爾風傳蠻地香。”這里的梅花又含有“苦節之士”的形象,蘇軾貶謫在嶺南時作《西江月》:“玉骨那愁瘴霧,冰肌自有仙風。高情已逐曉云空,不與梨花同夢。”! 5正是做到“節士”與“美人”梅花形象的融合;方以智詠梅“瘴癘未聞花變色,風霜直以句投人”,可以說繼承了蘇軾的手法,這里的“義士”形象也是流離于蠻風瘴雨的方以智的自我寫照。
(二)安貧之士節:三更月照虛空骨,一字幡招淡泊魂 方以智采用“物我為一”的手法將“梅格”與“士節”達到了統一。首先,梅花所處的寒冷環境正如士人生逢亂世,“萬代皆傷此日寒”“雪窖彌天特地寒”,國家淪喪、社稷滅亡使天下士子心靈無所皈依,于流離漂泊之際百感叢生,悲觀甚至絕望,這種心境皆可以由一“寒”字概括。其次,現實既已如此,士人亦須安之,以梅花“愛寒”之品格自勵,堅定遺民情結,安貧樂道,淡泊名利,不仕新朝:
寒路繁枝砍莫嗟,種成環堵舊生涯。酸心已解行人渴,冷眼休防醉客嘩。(《又梅花十六首·十》)
可許倉黃修白社,翻愁紅紫吊青門。從今珍重東皇意,桃李無言莫負恩。(《和白門梅花韻十六首·十一》)
難言佛國無兵火,早乞樵夫借斧斤。省得嶺頭張網者,攢花簇錦亂紛紛。(《和白門梅花韻十二首·十》)
“敗竹那能藏隱士,孤松未免作秦官”,此句隱喻仕宦清廷者,一反以往“惜梅” 常態,感激東風吹落梅花,正因為梅花如不凋謝,與桃李爭春,氣節頓失,故而說“珍重東皇意”“繁枝砍莫嗟”。“嶺頭張網”,隱喻清廷逼仕者,“酸心”“冷眼”,皆勘破之語,行人之渴,醉客之嘩皆流連世間榮辱得失者。方以智苦節,身入佛門,本避清廷征召,然當時尚不乏仕宦清廷者,而己身獨愿守寒冷之道,借梅以反復道之。
方以智曾于亡國之前思索亂世中士人的自處之道,并以東漢末年的管寧和孔融為例,二人出處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管寧隱居不仕,安于淡泊;孔融情難自禁,逐名亡身。故“文人才士,正當以懷曠達之意,可引之淡然于利祿,淡然于利祿,圣人許之矣”! 6。方以智借詠梅花之節,表現出淡泊的生活態度和流連故國的情態:
明珠覿面休輕撒,敗絮沖寒枉送窮。數點臨池香一炷,幾人不負此窗中。(《和白門梅花韻十六首·十三》)
三更月照虛空骨,一字旛招淡泊魂。凍慣白衣揮鐵筆,玲瓏粉碎總無痕。(《又梅花十二首·六》)
甘隨野牧歸春雨,痛入胡笳散曉風。漫道江城騎鶴去,影隨華表落長空。(《又梅花十二首·十二》)
方以智在萬念俱灰之際堅定了遺民情結,并安于“敗絮沖寒”“窗前畫梅”的淡泊生活,“甘隨野牧”“痛入胡笳”,正不仕清廷之意,又以傳說中的丁令威自比,騎鶴歸來,影隨華表,無不見其眷戀故國的情態,真忠臣節士之詩也。
四、結語
隨著遺民情結階段性的變化,方以智的詩中梅花形象也發生了從“美人”到“高士”再到“節士”的轉變和融合,因此方以智筆下的梅花形象是多樣而統一的,我們不妨說這三種形象都是方以智自身的寫照。少年時以“美人” 自期,博學多能,“年九歲能賦詩屬文,十二誦《六經》。長益博學,遍覽史傳,負笈從師,下帷山中,通陰陽象數、天官望氣之學,窮律呂之源,講兵法之要”! 7,卻懷才不遇;中年出家為僧,安于淡泊,是高士,更是堅定遺民情結的義士。余英時先生說:“密之垂剃近二十年,且于佛教思想亦深有所契悟,然統觀其晚年行跡與夫最后之抉擇,則密之終不失為明末一遺民,而非清初一禪師。”! 8方以智曾倡導“即事而隱”,這是古人對待暴力權威的一種虛與委蛇的方式,如東漢的禰衡裸身擊鼓,曹操倍感屈辱;東晉的戴安道碎琴,以示不愿出仕。方以智說禰衡“隱于鼓”、戴安道“隱于琴”,他閉關高座寺,以拒清廷征召,并作梅花詩以表明氣節,我們也可以稱其“隱于梅”吧!
ac〔清〕方以智:《浮山后集》,黃山書社2019年版,第237頁,第299頁。
b 任道斌:《方以智年譜》,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69頁。
d 陳垣:《明季滇黔佛教考》,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119—120頁。
e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72—1480頁。
f 孔英明:《梅花意蘊流變探微》,《南寧師范高等專科學報》2005年第2期。
gi〔唐〕孔穎達疏:《毛詩正義》,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90頁,第8頁。
h 彭玉平:《人間詞話疏證》,中華書局2011年版,第408頁。
jkpq〔清〕方以智:《浮山文集前編》,黃山書社2019年版,第312—313頁,第531頁,第394—395頁,第339頁。
l 〔宋〕林逋著,沈幼征校注:《林和靖詩集》,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96頁。
m 〔宋〕陸游:《宋本新刊劍南詩稿》,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7年版,第14 頁。
n 〔清〕金植輯注:《高青丘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651頁。
o 鄒同慶、王宗堂注:《蘇軾詞編年校注》,中華書局2002年版,第785頁。
! 8 余英時:《方以智晚節考》,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2年版,第153頁。
作 者: 陳璐,閩南師范大學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明清文學。
編 輯: 張晴 E-mail: zqmz060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