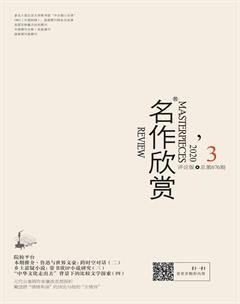《陸犯焉識》:“家”的內涵及流變
摘 要:小說《陸犯焉識》 中共有四次半以“家”為中心的“離去—歸來”結構,“家”的內涵在主人公一次次的離去歸來中發生了數次轉變,從原先的“禁錮之家”轉向了“自由之家”,最后轉變為“破碎之家”。本文從小說主人公在上海、美國、重慶、西寧的數次輾轉中入手,分析不同時空下的“家”的內涵,以探求其轉變的原因及主人公陸焉識的理想之家的樣貌。
關鍵詞:《陸犯焉識》 家 離去 歸來
小說《陸犯焉識》 的時間跨度長達七十年,陸焉識的“家”在其中經歷了恩娘離世、焉識被捕和被迫搬遷等一系列事件,“家”的內涵也隨之發生了數次轉變。一開始,家之于陸焉識是一座牢籠,在恩娘當家的時代,他在家中沒有自由。后來,恩娘離世,陸焉識被捕入獄,家成為他日思夜想的地方,是自由之所。最后,陸焉識被特赦回到家中,兒女們長大成人,各自組成家庭,家卻因為他的回歸變得別扭不堪。小說的結尾耐人尋味,馮婉喻去世,陸焉識帶著她的骨灰離家,回到曾經禁錮他的草原。對于一直割舍不下的家,他最終選擇了離開。
嚴歌苓打亂了故事中原有的時間接續順序,這一安排使得故事發生的場所在敘事中的順序也被打亂,因為“無論是作為一種存在,還是作為一種意識,時間和空間都是不可分割的統一體”a,時間的改變也必然導致空間的改變。
上海→美國→上海→重慶→上海→……→西寧→上海→西寧→上海→西寧……①
上海 =美國② 上海 = 重慶③ 上海→西寧→上海→西寧→上海→西寧④
上海→西寧→上海→西寧→上海→西寧⑤
被捕 出逃 自首 釋放 離家 禁錮之家→監獄→自由之家→監獄→破碎之家→自由?⑥
序列①是按照時序列出的故事發生的場所。上海是陸焉識的家,離家又回家,陸焉識的人生軌跡是由多次的以家起點的“離去—歸來”組成的。“‘場所是非常具體的空間,只有當某一個空間和具體的人物、事件以及時間結合在一起的時候,才能成為真正的場所,而此一場所則構成了一個‘敘事空間。”b盡管數次輾轉分別與不同的事件掛鉤,但每個場所構成的敘事空間都指向家的逃離或回歸。
一、禁錮之家
序列②和③中場所的轉變可以解讀為陸焉識對“家”的逃離,此時的家是以恩娘為權力中心的家,陸焉識身在其中,沒有自由,只能被迫履行自己的職責與義務,接受被安排好的人生。自由是陸焉識一生執著的追求,因此在這個時期他的目標就是逃離這個禁錮之家。1928年他前往美國留學,一方面是逃離被恩娘安排的婚姻,另一方面則是尋找家之外的自由。“太平洋上的游輪是他監禁的開始。五年的自由結束了。放浪形骸到頭了……他眼睛一次次的潮濕,不是哭他的望達,是哭他的自由。他跟誰都沒有說過,他多么愛自由。從小到大,像所有中國人家的長子長孫一樣,像所有中國讀書人家的男孩子一樣,他從來就沒有過足夠的自由。”c陸焉識深知五年的留學時光是一生中僅有的自由時間,所以他極盡所能讓自己不被束縛。與望達發生婚外戀,設立紅粉預備隊,絕不加入任何一個團體,因為“他所剩的自由不多,絕不能輕易地再交一部分給某個組織”d。離家又歸家,是初品自由滋味又失去自由的過程,這是陸焉識第一次對禁錮之家的逃離。
序列③是陸焉識離家前往重慶又歸家。盡管戰爭是促成這一次出走的關鍵因素,但他拋開家庭成員獨自離開就是對家的逃離。陸焉識在重慶出軌韓念痕,先后兩次的出軌不僅是對婚姻的反叛,更是對家的逃離。馮婉喻是恩娘安排的妻子,安排的背后是家的權威迫使陸焉識履行長子的職責與義務。家,讓他失去了自由的權利。他貪戀自由,盡管有勇氣選擇暫時逃離家庭的束縛,卻又無法狠下心與束縛自己的家庭徹底斬斷聯系。“焉識的信說明了他對妻子、繼母、孩子的責任心有多重。他在意他們,對他們守時,守信用。這樣的男人是不會跟他的家庭分開的……戰爭讓他混賬了一場,戰爭打完,最終他還要言歸正傳地生活,去和妻子、孩子、繼母把命定的日子過下去。”e雖然陸焉識厭倦禁錮之家,但是責任心使得他沒有辦法為了個人的自由放棄整個家庭,歸家是他必然的選擇。
無論美國還是重慶,都是陸焉識暫時的避風港。在他的價值體系里,自由處在最高的位置,但道德感和責任感會束縛他,壓制他不去追求自由,并要求他去做“正確”的事情,而每當被壓抑一段時間,他會選擇暫時地離家出走。回到上海過上正常家庭生活的陸焉識不得不為家中的瑣事所困,為了盡可能少與妻子、恩娘糾纏于家務事中,他不斷縮短在家的時間。“這不是公文包,是一件行李。為了躲到各個咖啡館、圖書館去辦公,他每天必須提著行李出門進門。”f“離去—歸來”的模式在上海的家與家外面的世界中每日演習。但不論如何,陸焉識最終都會選擇歸家。
二、自由之家
家在陸焉識的價值體系中處在非常高的位置。加斯東·巴什拉在《空間的詩學》中對家這一空間的總結是:“家宅是一種強大的力量,把人的思想、回憶和夢融合在一起。在這一融合中,聯系的原則是夢想。過去、現在和未來給家宅不同的活力,這些活力常常相互干涉,有時互相對抗,有時互相刺激。在人的一生中,家宅總是排除偶然性,增加連續性。沒有家宅,人就成了流離失所的存在。”g“家”始終是精神家園的堅實后盾,是陸焉識在外追尋人生理想失敗后仍可回歸的地方。雖然回家意味著失去絕大部分的自由,但是家與自由之間并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陸焉識之所以不認為在家中可以擁有自由,是因為家不是他親手組成的,是恩娘的權力組成了他的小家。因此,在他自覺對馮婉喻的感情以前,不可能認為家中存在自由。
1954年春,陸焉識在小女兒丹玨的注視下被押上囚車,在幾個監獄之間短暫停留后,最終被轉移到了青海西寧,在西寧度過了幾乎整個后半生。
序列④和序列⑤體現了陸焉識在上海和西寧之間的多次往返。因為政治原因被流放西寧,此時的西寧可以和不自由畫上等號。“我祖父在大荒漠的監獄里,也比別的犯人平心靜氣,因為他對自由不足的日子比較過得慣。”h相較于西寧的監獄,曾經被陸焉識視為不自由的家現在顯然是個自由的所在。于是當他在場部禮堂的科教片里看到自己的三女兒丹玨,就萌生了回家與家人團聚的念頭并采取了行動。這時恩娘已死,陸焉識本人也意識到了對妻子馮婉喻的感情。家的內涵發生了第一次轉變:恩娘的去世代表著束縛的力量消失,家中所有令陸焉識不快或厭惡的因素也沒有了,禁錮之家轉變為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是陸焉識理想的家庭狀態,他對于久未回歸的家充滿了美好的幻想,對妻子馮婉喻也充滿期待。組成自由之家的成分確與禁錮之家的不同,但是否與他理想的自由之家完全一致,仍有待驗證。當他越獄回到上海,暗中探視家人后,發覺家中的一切與從前大有不同,卻又都比想象中更好,陸家三代人在諸多風波之后依然和美地生活在一起。一窺自由之家的狀況后,陸焉識甚至覺得此生已經圓滿,決定回西寧自首,不拖累家人。這是他為家庭做的最后的貢獻,也是對自由之家的報答。
三、破碎之家
隨著運動的結束,陸焉識被特赦得以回到上海的家中,他終于可以回到日思夜想的自由之家。但是,歷史的傷痛難以撫平,兒女們都難以完全接受陸焉識的回歸,錯愛一生的馮婉喻又患上了阿爾茲海默癥。在物理空間上,他確實從西寧返歸上海,回到了他曾經看到的自由之家,但他的回歸,卻打亂了原有的家庭秩序。兒女們對這位曾經的政治犯父親不敢放松警惕,“都怕老阿爺那不太漂亮的政治面貌經不住鄰居的橫看斜瞅”i。街坊鄰居對陸焉識也是有所防范。家人們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約束他,在這個家中,陸焉識再次失去了自由,關于自由之家的所有幻想也隨之破滅。但是,為了陪伴幾乎錯愛了一生的妻子馮婉喻,對于種種束縛與不自由,他選擇了忍耐。但好景不長,馮婉喻在陸焉識歸家不久后就病逝了,陸焉識對于自由之家的種種設想都是圍繞馮婉喻建立起來的,她的去世意味著自由之家的破碎。因此,馮婉喻之死代表著自由之家再無實現的可能,家成了破碎之家。于是,陸焉識沒有向任何人告別,獨自帶著馮婉喻的骨灰回到西寧,這個曾經剝奪了他半生自由的地方,最后卻成為了自由之地。
序列①中一共有四次半的“離去—歸來”結構。如果作者按照故事時間的自然順序進行敘事,那么四次半的“離去—歸來”會非常直觀地呈現出來,但是,嚴歌苓采取了大幅調整敘事時間的方式,讓故事時間的原有順序支離破碎,使得這些“離去—歸來”模糊在敘事技巧之后,淡化了自由之家幻滅的傷感。“家”的內涵發生了兩次較大的轉變,陸焉識一直有回歸自由之家的執念,但“家”的內涵卻是決定他離去或者歸來的關鍵因素。不自由或者婉喻失憶的家不會令陸焉識留戀,當家已破碎,大可選擇以自由為家。
四、結論
“家”是《陸犯焉識》中人物活動的主要場所之一。對于家,陸焉識希望它既是精神家園也是自由所在。關于家的書寫中,作者在空間上建構了四次半的“離去—歸來”結構,家的含義在陸焉識一次次的離去又歸來中不斷改變,先從“禁錮之家”轉向“自由之家”,最后轉向“破碎之家”。其中,“自由之家”是陸焉識認為的家的理想狀態。最后,當他確信家已經不可能成為“自由之家”后,果斷選擇了離開。“離去—歸來”結構在跳躍的敘事時間下分離破碎,使得“自由之家”破滅的傷感隱去不少。小說中場所的多次轉換,時間的頻繁跳躍,都是嚴歌苓賦予“家”不同內涵的重要手段,體現了作者對于時間與空間的獨到認識。
ab龍迪勇:《空間敘事學》,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年版,第7頁,第203頁。
cdefhi嚴歌苓:《陸犯焉識》,作家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頁,第39頁,第178頁,第140頁,第45頁,第414頁。
g 〔法〕加斯東·巴什拉:《空間的詩學》,張逸婧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年版,第5頁。
作 者: 伍一荻,湖北大學文學院在讀本科生。
編 輯: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