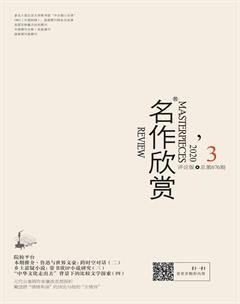拉康精神分析下的《白輪船》
摘 要: 吉爾吉斯民族作家艾特瑪托夫于20世紀70年代發表的小說《白輪船》,從奧羅茲庫爾姨父、莫蒙爺爺、小男孩這三個主要人物焦灼的關系和以長角鹿媽媽為焦點的矛盾沖突中,展現了一個關于精神價值的追求與毀滅的故事。而最后,長角鹿媽媽被射殺,族人卻大擺鹿肉宴,則預示著信仰破滅后,人們最終的失落和毀滅。
關鍵詞:拉康 缺失與尋找 父親的隱喻 毀滅
小說的副標題是“仿童話”,而讀到最后長角母鹿被射殺,孩子在絕望中投水,才不禁恍然,這實際上是一個“反童話”的故事。而在童話世界里過去、現在、未來可以同時涌現,三個主要人物呼應著時間橫斷面的三個切點,即不貞的過去、無后的現在、已死的將來。信仰破滅后的布古族面臨著巨大的精神危機,當他們逐漸意識到尋找的徒勞之后,誰又能肯定穿過漫漫長夜的狂歡所迎來的“將來”是靈魂的救贖,還是肉體的自戕?
一、鏡像階段: 老人與孩子的心理關系
根據拉康的鏡像階段論,主體的自我確證是從鏡像開始的,而鏡像也就是一切想象認同的開始。通過鏡像,主體與外界逐漸建立起一種聯系,卻將我們導入一種自己與他者的不可思議的關系中,即“我”在成為自己本身之際認同的對象其實并非自己,而是他者,“我”為了成為真正的自己而必須舍棄自己本身,穿上他者的衣裳。人想要在象征界里擁有一個自我的前提在于將自己想象地投射到鏡像中,即鏡子中的他者,從而加入到和他人的某種契約關系之中,納入到他人的支配之下,這樣的關系模式使主體內在產生矛盾和對立,也就是說主體通過這種方式建立起來的自我本身就是分裂的,而主體尋求自我認證的初衷本就在于確定自己的同一性,這種分裂也影響著我們對他者向外的情感投射。
《白輪船》中男孩的外祖父莫蒙是一個被社會秩序排斥在外的人,在已經被世俗的文化秩序侵蝕后的林區,人們已經深諳金錢或者權力的威力,而他卻妄圖守住民族傳統的精神價值,守住布古族民族的根,他依然秉持著所有的布古族兒女都是兄弟姐妹的信念,而別人只是把他當作給“年輕媳婦”跑腿的差使。他身為三個兒女的父親,身為部落族人的長輩,被總是被自己的女婿呼來喝去,隨意折辱。這也僅僅是因為女婿奧羅茲庫爾是護林所的頭頭,而世俗權力已經壓倒部族傳統信仰的力量,成為這個閉塞之地的價值指標了。他的精神世界和他尷尬的現實處境之間的矛盾讓他成為一個在象征界秩序夾縫中生存的人,要靠社會(象征界)來認同自我顯然是不可能的,因而只能返回童年中尋求自我認證,老人終于發現了存在于身外的自我——孩子。這時孩子起了作為老人鏡像的作用,因而老人不再是自己了,孩子“以主體之名占據主體位置”,開始就是一個“替身”,這個作為替身的偽自我在場時,本我被謀殺了,確切地說,是“我”的自殺。老人把孩子看成理想的自我,即“大它”,對孩子的愛也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自發的愛,也就是一種“自戀”。 因此,他把“長角鹿媽媽”的故事教給孩子,讓其成為他心目中幸福的源泉和象征,使他們的欲望具有同一性;他送孩子去上學,甚至不惜第一次忤逆奧羅茲庫爾,他希望孩子讀了書之后有出息就不會像自己一樣一輩子待在山里了,這些,似乎都是老人講將自己的理想投向孩子的表現。
而就孩子的角度而言,他無父無母,沒名沒姓,甚至從小就沒有見過他們。 因此在其嬰兒時期的鏡像階段,母親始終都是處于缺席的狀態,而唯一陪伴他長大,關心他、愛護他的就是外祖父莫蒙。在此意義上,老人已經成為男孩心理意義上的母親了,也成為嬰兒進入鏡像階段最開端時的“他者”。據拉康的理論,孩子總存在有在想象中認同母親的欲望對象的傾向,于是在老人一心想守護“長角鹿媽媽”的美麗傳說的影響下,“長角鹿媽媽”也成為孩子的欲望對象。男孩心中的長角鹿媽媽是他內心所有美好的象征,她是吉爾吉斯民族的恩人和母親,對老人和孩子而言,長角鹿母鹿能帶來彌補母親缺失的心理慰藉。老人和小孩對長角鹿媽媽共同的希冀與向往,也體現了老人將自我投射到孩子身上之后,其欲望共同指向母親(嬰兒對母親的欲望)的隱喻意義。
二、父親的隱喻:缺失引發的尋找
《白輪船》里的人物或多或少都面臨著一些缺失。小男孩無父無母,從小與外祖父相依為命;外祖父唯一的兒子死了,兩個女兒中大女兒不會生育,常被女婿虐待;外祖母是后來才到外祖父家里來的,她原來的丈夫和五個兒子都死了,她不滿意現在的生活,經常抱怨和責罵外祖父;別蓋伊姨媽不能生育,她的母親身份被剝奪了,而奧羅茲庫爾姨父也不能成為父親。
這些人物自身所伴隨的缺失狀態都無意識地引發了他們的尋找行為。拉康認為,無意識的產生來源于進入語言符號系統一瞬間形成的心理結構,因此它具有語言式的結構。語言符號的實在是能指,能指在追索所指,無意識同樣也具有一種與能指相同的對于被壓抑的內容的追憶。無意識中希望、欲求和意象等都構成了能指,其發生作用的兩個機制也與語言結構有相似性——凝結(隱喻)和移置(轉喻),而無意識的顯現則體現了詞語的游戲——雙關、聯想等。人在進入象征界時,只有進入語言結構內部才能成為言說的主體,又因為語言符號系統是先于個人存在的社會系統,個人的意志與行為只能被社會符號體系所左右,意即被迫認同先在的社會文化秩序。
在《白輪船》的那個偏僻閉塞的護林所里,那片被奧羅茲庫爾這個土皇帝般的世俗權力的代表所籠罩下的林區里,人們所接受的文化秩序依然還是父權中心的,準確來說,他們都是同一個“父親”的“孩子”,“父親”并不指向現實中的父親,而是成為一個隱喻,一個符號,拉康稱之為“父親的名字”。于是,在這樣的心理(語言)結構下,每個人的欲望或被壓抑的欲望都構成了他們的無意識,驅使著他們的行動。小男孩一心想要變成魚去尋找在白輪船上做水手的父親,他的主要的心理線索以及最后的悲劇指向的都是白輪船,從某種角度上來看,白輪船就成為小男孩父親的象征。莫蒙外祖父對小男孩的深厚的關愛以及對布古族古老習俗的守舊和捍衛都是在傳遞一種對于父親身份的尋找,他的兒子死了,女兒無法生育,他在女婿面前畏畏縮縮,所有的這一切都暗示了他父親身份的喪失,他送小男孩去上學,希望將他培養成一個人才,以后走出山林,也是在建立自己的父親身份。而根據拉康的觀點,“父親的名字”成為一種能指的符號,他所代表的就是在嬰兒進入象征界時對他產生影響的語言結構,也是這個社會先在的社會秩序,在這種程度上,老人和小孩尋找的東西其實是同質的,他們都在尋找進入這個社會文化秩序的途徑。因此小說中莫蒙沒被邀請去布古族人的葬禮時非常生氣,因為這表明他被排斥在了社會秩序之外。
但值得一提的是,盡管小男孩一心都想去尋找自己的父親,但卻非常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父親已經組建了新的家庭,有了新的孩子,所以他不可能去找自己的父親,因為他在父親那里沒有自己的“身份”,我們又回到了自我認證的問題上了。所以他把欲望放在了長角鹿上,也是拉康的“大它”,即自己成為社會秩序的中心,他和外祖父都希望回到長角鹿媽媽庇護著吉爾吉斯人的時代,然而外祖父最后卻在世俗權力面前親手毀掉了他們共同欲望的維系,于是小男孩最終跨進河里,以自戕的方式進入了“父親”的文化秩序——真正去尋找白輪船了。
三、欲望和主體:走向自我毀滅
《白輪船》整個故事就可以看作是小男孩尋找父親最終走向毀滅的心路歷程,造成悲劇的必然性在于拉康所述的現代人自身所具有的本源性裂痕。這種裂痕存在于每個人身上,而且幾乎是從它進入鏡像階段的開端,第一次在鏡子前看到自己的鏡像,把自己想象地投身到鏡子中的他者,從而將自己與外在世界分隔開的那一瞬間就形成了。拉康認為人在鏡子里看到自我的鏡像,從而完成自己認證,但這種認證并不能幫助他找到關于自我的完整性,因為他看到的只是一個幻想,并不能真正地和主體合二為一,因此它并不能消除主體的缺失感和分裂感,而這種體驗會伴隨一個人終身。
小男孩無父無母,甚至沒有名字。這說明他既沒有母親在鏡像階段幫助他完成自我確證,也沒有父親以實現進入象征界的欲望,他甚至沒有名字,沒有一個可以幫助他和其他人(其他孩子)區分開來的能指符號,于是他也就是一個孩子,所有孩子中的一個。這種多維度的缺失狀態也內源性地產生了他的欲望,甚至是被壓抑的欲望。他夢想著去白輪船上尋找父親,可是父親已經有了新的家庭,于是他不能去了;他的望遠鏡藏在牛棚里不敢讓外祖母發現,白輪船的故事他誰也沒告訴。由欲望引發的多方面的尋找行為,其實也就是他的欲望客體轉移的過程,他把母親的欲望轉移到長角鹿媽媽身上,而把對父親的欲望轉移到白輪船上。而根據拉康的觀點,父親是第一個進入母嬰關系結構的人,所以最終是父親所代表的先在的社會文化秩序將孩子與母親之間的美好聯系切斷了,長角鹿媽媽被殺害了,孩子的欲望也被殺死了,他沒有進入社會文化秩序的欲望了,他最終也就進入社會文化秩序了。
參考文獻:
[1] 艾特瑪托夫.白輪船[M].力岡譯.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9.
[2] 福原泰平.拉康:鏡像階段[M].王小峰等譯.石家莊: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3] 方漢文.后現代主義文化心理:拉康研究[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0.
[4] Lois Tyson.當代批評理論實用指南[M].趙國新等譯.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14.
[5] 趙毅衡等編著.現代西方批評理論[M].重慶:重慶大學出版社,2010.
[6] 馬愛忠.重構的鏡像[D].西北師范大學,2011.
[7] 宋治蘭.尋找父母——試析《白輪船》中小男孩走向毀滅的心路歷程[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1999(4).
作 者: 黃倩,西南交通大學人文學院在讀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國現當代文學。
編 輯:趙紅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