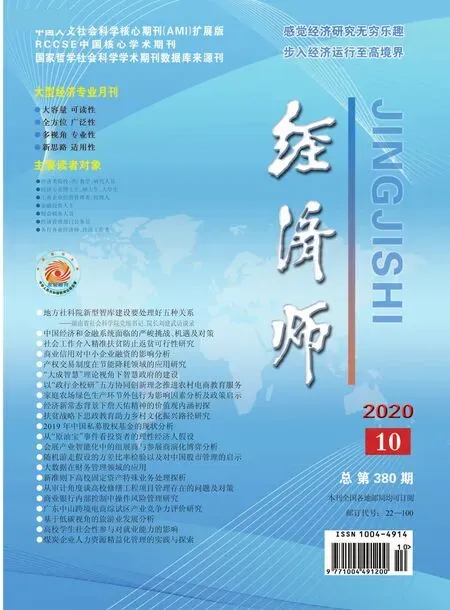《啟蒙辯證法》對技術理性與大眾文化的批判
●王子奇
《啟蒙辯證法》一書詳細地分析了自啟蒙以來人們所處的一般生存困境,對啟蒙帶來的技術理性至上的價值觀念進行了深層的文化批判,它揭露出以往被認為是解放與自由的啟蒙和理性不是真正的解放與自由,相反它最終走向了與之對立的一面。在理性之光的照耀下,人與自然成為了統治與被統治的關系,人的主體性高度膨脹,在技術理性的支配下,人一方面奴役自然,另一方面也在奴役著人自身,最終導致了人與人、人與自然之間的異化。啟蒙返回神話,啟蒙帶來的理性最終變成了單向度的技術理性。
著眼于此,霍克海默和阿多諾對西方工業文明所包含的技術理性和大眾文化進行了深刻的文化批判,使普照在啟蒙之光下的人們認識到“被理性啟蒙的世界不是一個人性得到真正發展,自由得到全面實現的世界,而是一個普遍異化的世界。”①
一、啟蒙對技術理性的呼喚
在《啟蒙辯證法》中,霍克海默、阿多諾首先對啟蒙與神話進行了詳盡的論述,指出啟蒙源于神話,而神話則是西方文化的淵源。維柯認為,神話最初是歷史的真實表達,霍克海默、阿多諾也正是在神話的歷史敘事中找到了“以統治權的建立”為標志的啟蒙理性的確立,換言之,神話是理性的產物。當人們將眾神與元素區分開、眾神由元素本身變為元素的管理者時,世界已由混沌不分的狀態轉向了秩序井然。也就是說,神話就是人試圖給世界以秩序,通過神來表達自身的感情意愿;啟蒙則是通過理性來樹立起人的主體性。
啟蒙最初的目的是使人擺脫迷魅,戰勝對自然的恐懼,用理性喚醒人的主體性,從而確立人的主體地位、實現人的自由與解放。可以說,近代以來的世界是理性支配下的世界,在霍克海默、阿多諾看來,啟蒙用形式邏輯對世界加以衡量與計算,使整個世界統一于抽象的理性同一性。啟蒙自身就存在著否定自身的內在邏輯,抽象的理性同一性將理性精神推至極點,理性由此獲得了上帝的屬性,人類由對神的崇拜轉向了對理性的崇拜。被理性引領著的啟蒙高度弘揚人的主體性,使人與自然相分離,自然成為了被征服和占有的對象,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變成了統治與被統治、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然而人對自然的統治卻并未使人變為自然的主人,結果恰恰相反,技術理性使人與自然發生異化。一方面,人單方面地征服自然,使得自然生態環境愈加惡化,造成了自然對人的報復和懲罰,人與自然的關系遭到破壞;另一方面,技術理性導致物對人的奴役,人類迷醉于對物質的追求中,被自己的無法滿足的欲望和大機器所支配,從而迷失了自我、喪失了思考的能力。由此,自然和人皆成為了被技術理性、工具理性所奴役的對象。
綜上所述,啟蒙最初是為了粉碎神話,然而啟蒙在確立人的主體性的過程中又吸收了神話的因素,進入了新的理性神話之中。理性代替神成為了世界秩序的締造者與管理者,理性成為了衡量一切的尺度,世界在理性的魔尺下被量化、數字化了。這一魔尺用以衡量世界的工具就是數學邏輯和科學理性,近代以來,由于實驗科學的進步,數學邏輯和科學理性所弘揚的科學方法成為了人們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唯一方法。而科學方法正如霍克海默、阿多諾所述:“科學家熟悉萬物,因此他才能制造萬物。”②科學家要想熟悉萬物,并試圖找出隱藏在萬物中的一般原理與規律時,就必須層層推進直達研究對象內部,進而獲得萬物的本質屬性和一般規律。然而這個接近本質的過程卻使主體與客體漸行漸遠,因為這個過程就是破壞甚至毀滅客體的過程。
在霍克海默、阿多諾看來,啟蒙之所以重返神話,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啟蒙理性被抽象的理性同一性所支配,抽象的理性同一性使啟蒙理性最終異化為技術理性。技術理性要求將一切合理化、統一化、標準化,將整個世界納入可計算的范疇,高揚人的主體價值,進而把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思維方式推至頂峰,技術理性終于成為了新時代的“上帝”。
二、理性的異化
霍克海默、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指出,人類破除迷魅的過程實際上也是確證自我的過程,隨著人類主體性的確立,理性被技術理性取代,人與自然走向了對立面。自弗蘭西斯·培根提出“知識就是力量”的口號以來,人類加強了對自然的探索,理性成為了人們用以統治自然的工具。霍克海默、阿多諾認為,啟蒙的真正的本質就在于欲將知識與統治人和自然的權力相等同。“歷來啟蒙的目的都是使人們擺脫恐懼,成為主人。但是完全受到啟蒙的世界卻充滿著巨大的不幸。”②人類在啟蒙之光的指引下開始改造自然,企圖讓自然匍匐在人類的腳下,然而在人類肆無忌憚地破壞之下,生態環境迅速惡化、自然資源日益枯竭、災害頻發,自然已經走向了人類的對立面。
技術理性在導致人與自然對立的同時,也帶來了人自身的物化,技術理性不僅是人類進行統治的工具,也是人類被統治的工具。
一方面,啟蒙理性最初想要實現的人的自由與解放非但沒有得以實現,反而更加禁錮了人的自覺意識,人類成為了迷失自我的“機器”,人及人的活動變得標準化、合理化、同一化。在抽象的理性同一性的支配下,啟蒙以后的世界是一個“合理化”了的世界,而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個“合理化世界”的典型代表。資本主義對合理化的追求使人們統一于同一的標準之下,理性成為了統治人、控制人的異化力量,這時理性變成了統治人的技術理性,技術理性使人們陷入理性的神話中而忘卻了自身,只剩下一副冰冷的軀殼。也就是說,理性變成技術理性之后所造成的直接惡果,便是使原本自由自覺的人失去自我主體的意識、喪失反抗精神,人成了技術理性的同一化的產品。霍克海默、阿多諾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正是由于包括工人階級在內的多數人喪失了具有反抗精神的自我意識以及精神上的麻木,才會被少數的資產階級所統治與奴役。由此我們得出這樣一個結論:技術理性與個人發展之間產生了這樣一個悖論,即當獨立的個人想要實現自我發展時就需要發展技術理性,而技術理性愈是得到發展,就會愈發得到限制個體意識發展的力量,人的自我意識便被不斷削弱。③于是理性成了統治人的工具,人則變成受理技術性操控的機器,技術理性要求用數理邏輯和數學計算的形式衡量世界上的一切事物,而處于這種形式下的人們則不會對本質問題進行深入地探究,人的自我意識也在無時無刻地計算下日益弱化。
另一方面,技術理性統治下的人類不僅自我意識日益弱化,其能力也在逐漸弱化。隨著社會分工的發展,社會生產被分解成了若干獨立的部門,受理性同一性支配的人們成為了社會鏈條中的一個環節,人的思維與實踐皆受到技術理性的奴役,人成了“原子化”的個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人們的能力更多地是為了服務更高效、合理的組織與管理機制,換言之,這時人的行為只服從于其所在鏈條的支配,人們不再做其想做,而只做其該做,個人的能力隨著思想的枯竭而逐步弱化。從表面上看,被奴役的人們實現了個人的主體化,然而實際上他們從未擺脫奴役著他們的技術理性的無形之手,看似通往康莊大道的合理化的理性才是阻礙個體自由全面發展的最大淵蔽。對合理化的追求使人們沉迷于科學技術,迷失了自我的人們看不到幸福背后的深淵。
技術理性帶來的科學技術的發展逐步成為了代替神話的意識形態,從而倒向了非理性。自近代啟蒙以來,技術無論在內容抑或形式上都蘊含著豐富的政治、倫理以及文化內涵,技術不再是中性的手段與方法,而是體現著特定價值取向的載體。科學技術成為意識形態的思想由霍克海默首次提出,日后在哈貝馬斯那里得到完善。技術理性更多地是通過政治、倫理和文化控制人的精神世界,進而達到統治世界的目的。也就是說技術理性成為了意識形態,成為了人們普遍認同且社會普遍遵循的文化模式。誠如《啟蒙辯證法》所書的那般,此時的大眾文化已然同符合契,“例如西方的、電影院常客了如指掌的那些東西的標準化,是擴散技術的理性化,而不是嚴格地指哪種生產過程。與藝術品中的技術不同,文化工業的技術從一開始就是擴散的技術,機械復制的技術”②。生活在社會系統中的人們無時無刻不在接受著文化工業所生產出的文化產品,在大眾傳媒高速發展的時代人們只需動動手指便可瀏覽成百上千條信息,就連原本超越現實、批判現實的藝術創作也墮落為粉飾現實、服務現實的工具。小說、影視的創作為了迎合大眾口味、獲取更多利益而千篇一律。高度發達的技術理性不僅摧毀著外在的自然,同時也在破壞著人自身的力量,人的一切都在邏輯規則中運行,人的主體思維的過程稱為了工具化、技術化的機器運轉的過程,這樣機器取代了人,思維也沒有了意義。“所以說啟蒙理性作為工具理性實際上是以非理性而告終”。④追求合理化的理性不僅促進了工業和社會的發展,也極大地提高了人的主體地位,使人成為了自然的統治者。理性的異化一方面導致了人與自然的尖銳對立,另一方面也導致了人本身的物化,技術理性終于走向了非理性。
三、文化工業——啟蒙意識形態的倒退
大眾文化本質上是一種滿足大眾的文化需要、滋潤精神沃土的文化形式,其本身便有著意識形態特征。但在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只有擁有著交換價值的商品才能夠在市場上流通,文化也是如此,在這種情況下流通于市場中的大眾文化實際上已經變質為具有反文化性質的文化商品。文化創作完全受理性同一性的支配、服從于利益最大化的原則,本應蘊含于文化作品的超越性和創造性也已不在,文化淪為工業化的產品,即文化工業。
霍克海默、阿多諾在《啟蒙辯證法》中對文化工業使大眾文化向意識形態領域倒退從而使文化倒向非文化這一根本性問題進行了揭露與批判,開辟了大眾文化批判的思路。隨著啟蒙帶來的理性精神日益深入人心、工業化進程的持續推進,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倫理以及科技等領域正籠罩在技術理性的無形大手之下。其中,資本和技術走向聯合,這個新的“盟軍”以種種技術手段滲透入文化領域,大批量地復制與傳播文化產品,這樣就誕生了工業化的文化生產體系,即文化工業。《啟蒙辯證法》中并未給文化工業以明確解釋,但其大意如下:在資本主義社會中,通過大眾傳媒等手段對民眾的意識形態加以控制,從而使大眾文化成為獲取利潤的手段。
換言之,由于理性異化為技術理性,資本主義的文化領域也成為被技術理性奴役的工具,文化受到技術理性的滲透,最終淪為以利益遵循為導向、受標準化與齊一化支配的大規模生產與復制文化產品的商品文化。啟蒙理性籌劃并計算著文化商品的生產、傳播及其后果,符合技術理性要求而生產出來的文化商品整齊劃一,進一步滲透在文化商品的使用者——廣大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普遍遵循和社會運行的內在機制,逐漸消除人們自覺思維的能力,使大眾文化成為控制人們的意識形態工具。這時,本應蘊含著人類主體性及主體精神的文化創造墮落為被動生產文化商品的商品化的文化生產。文化工業生產出的大眾文化具有控制人的意識的意識形態功能,也就是說,人們所選擇與接受的文化實際上都是被文化工業生產出來的,符合標準化、合理化的要求,缺乏主體性的文化商品,因而技術理性帶來的文化工業使得大眾文化和人相異化,人們被隱藏在大眾文化背后的文化模式支配。通過以上分析可以斷言,文化工業的根本目的并非是為了提高人們的精神文化修養與滿足人們的精神文化需要,而是和其他生產部門相同,最終目的是使資本增值、獲取利潤。也就是說,文化工業從本質上看是一種反文化。因而,商業是他們的意識形態,利潤是他們的生命,消費者即是商品拜物教的信徒。⑤
霍克海默、阿多諾將對技術理性的批判伸展至文化消費領域,為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開辟了道路。他們試圖呼喚文化創作的主體精神,打破技術理性的桎梏,啟發人的心智,真正實現啟蒙的最初歸旨——人的全面自由與解放。
注釋:
①衣俊卿.20 世紀的文化批判[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局,2003
②[德]馬克斯·霍克海默,西奧多·阿多諾著.洪佩,郁藺月峰譯.啟蒙辯證法[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
③郭倩.《啟蒙辯證法》中的批判理論研究[D].黑龍江大學,2018
④王鳳才.批判與重建[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4
⑤包桂芹.霍克海默、阿多諾《啟蒙辯證法》研究[D].吉林大學,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