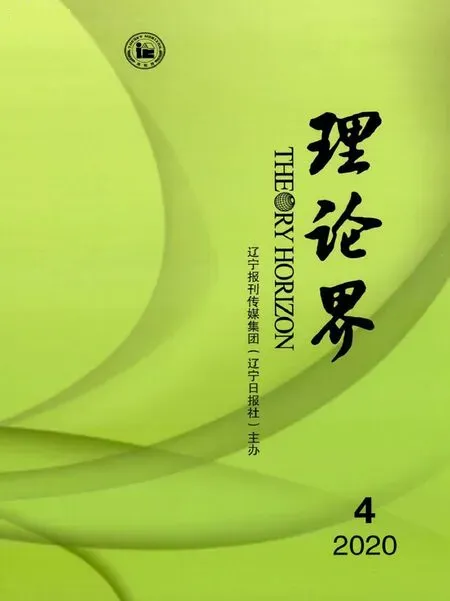聚焦中的經濟學方法論問題域分析
程曉東
經濟學方法論是一門新興的分支學科,雖然其早期思想伴隨經濟學的誕生早已存在,但作為學科形態出現不過幾十年時間。關于其誕生的標志性事件,主要存在三種看法:一是1980年馬克·布勞格著作《經濟學方法論》〔1〕發表;二是1953年弗里德曼發表“實證經濟學方法論”〔2〕一文;三是1994年《經濟學方法論》專門期刊的創立。作為學科形態意味著,圍繞經濟學方法論的研究者和文獻顯著增加,尤其是專業刊物和課程設置達到一定規模。尚處于蓬勃發展中的經濟學方法論,問題域具有明顯的發散性,學科界限彈性較大,面臨失焦的風險。本文著眼于經濟學方法論問題梳理,以探究經濟學方法論研究可聚焦的問題域,從而作為批判思考現狀和未來方法論研究的平臺。
一、經濟學方法論“傳統”問題
給“傳統”一詞加上引號,主要有兩點考慮:一是經濟學方法論存在的時間的確不長,似乎很難稱得上“傳統”;二是即使存在歷史悠久的傳統,我們也很難識別某種單一的傳統。這里既因奠定經濟學方法論的“科學哲學的貨架(shelf of scientific philosophy)”之諸多傳統,〔3〕也因諸多經濟學家本就是多元方法論者,無論在經濟學家抑或方法論者的著作中,我們不難發現多個“傳統”的并存,有時甚至是對立“傳統”的并存。這種情況加劇了我們探尋“傳統”問題的難度,但不妨對其作出一定的分類梳理。
1.波普爾傳統
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興起,比較常見的說法是以布勞格的著作《經濟學方法論》的發表作為標志。布勞格的著作,正如他自己所聲稱的,堅持波普爾傳統。他認為,經濟學研究要回答的終極問題,“是波普爾提出的眾所熟知的問題:什么事件,如果它們具體化的話,會導致我們反對那個框架?”〔4〕與此相應的經濟學方法論研究,在他看來,是提供對于經濟學理論是否(至少潛在地) 能用經驗的證據來檢驗的規范判斷,做一個“不悔的波普爾主義者”。〔5〕
布勞格的問題可以看作是對一個長期困擾經濟學的問題的集中表述,即科學的“劃界問題”。在布勞格的著作發表之前,經濟學家和方法論者已對劃界問題作了諸多探索,既有從庫恩、拉卡托斯、邏輯經驗主義等哲學“范式”探討經濟學“結構”的嘗試,也有從經濟學實踐出發對新古典綜合的失敗等問題的反思。在布勞格以波普爾主義作為經濟學方法論終極“貨架”之后,作為反彈的“復興實踐”動向實際上是另一種范式的延續。
從波普爾傳統在上世紀80年代成為經濟學方法論爭論焦點的前后發展來看,相關問題幾乎都圍繞以上兩者而展開,即在一般和具體兩個層面展開對:①經濟學遵循的范式和綱領②及其具體問題,以及③理解經濟學實踐④及其具體問題的探討。當然,這里區分出的四個問題存在一定的交叉關系。例如,體現范式和綱領的實證經濟學和規范經濟學之劃分又必然是理解經濟學實踐的內容。
2.羅賓遜問題域
相比于波普爾傳統帶來的爭論和引人注目問題,瓊·羅賓遜于1977年提出的問題則顯得更加不可調和和充滿批判。這些問題不見得為主流方法論者所接受,但對于我們梳理方法論問題仍具有借鑒意義,至少可以作為檢驗方法論問題的參照。
羅賓遜在文章《問題是什么》中提出的問題包括:①正統經濟學在多大程度上受意識形態錯誤地驅使?這種狀況為什么能夠一直持續下去?②是否因為經濟學研究對象的變化太過頻繁,以至于其一般的“法則”才一直沒有獲得承認?③為什么新古典經濟學不能在社會生活中的歷史性時刻起到適當的作用?④經濟增長的目的是什么或作為一個富足的社會我們希望實現什么?⑤為什么那么多的經濟學家認為民族國家的組織原則是理所當然的?⑥經濟學解釋的發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為是對(不) 適當的方法的“選擇”,例如選擇數學而不是參與者的行為學?〔6〕
可以看出,羅賓遜的六個問題主要針對經濟學的科學地位、形式主義方法、社會原子主義等的批判而展開,代表了主流經濟學方法論之外的另一種思考,盡管其中個別問題可以納入以上四個問題之中。
3.米洛斯基問題域
在同名文章《問題是什么》中,米洛斯基也提出了主流經濟學方法論問題之外的思考,但他自認為提供的是一些“更大的問題”:①標準是什么?②社會科學的“社會”指什么?③我們是由我們的研究對象構成的嗎?④我們是如此純粹嗎?⑤為什么如此多的經濟學家看起來像蹩腳的應用數學家?⑥經濟學確實不可能進行實驗嗎?⑦究竟什么是新古典經濟學?〔7〕
盡管米洛斯基提出的棘手問題偏離主流經濟學方法論者討論的主題,但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反映了“復興實踐”的主題。尤其是問題⑥對經濟學實際上如何開展經驗檢驗及經驗工作的有效性等提出了質疑,并以實踐的多樣性主張經驗標準的多樣性;同時,實驗經濟學也代表了新古典綜合失效以來的新實踐和探索。與一些經濟學家忽略經濟學與哲學、科學史、社會學的聯系或否認科學哲學對經濟學方法論的影響相比,米洛斯基不滿經濟學方法論只探討比經濟學日常實踐稍大一點的問題,但實際上他提出的更一般的問題大多在波普爾傳統之后已經以新的“復興實踐”的名義提出,不論它提出的方式是強方法論的還是弱方法論的。從這一意義上說,米洛斯基的問題域與羅賓遜的一樣,仍未逃脫圍繞波普爾傳統的爭論引發的問題域。
二、權威定義下的經濟學方法論問題
為了使問題梳理更具說服力,現在讓我們來看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三個權威詞條定義,它們分別是:斯坦福哲學百科(SEP)、維基百科(Wiki) 和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辭典(Palgrave),均以最新版本為準,其中SEP更新于2012年,Wiki更新于2018年,Palgrave為2018年第三版。
1.SEP定義的問題域
SEP在詞條“Philosophy of Economics”中列出了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六個核心問題:①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②理由與因果;③社會科學自然主義;④經濟學中的抽象、理想化和“余者皆同”;⑤經濟學、計量經濟學中的因果關系;⑥經濟學的結構和策略:范式和研究綱領。〔8〕
2.Wiki定義的問題域
Wiki在詞條“Economic methodology”中列出了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的一般問題和具體問題:(1) 一般問題: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異同;(2) ①經濟學的定義;②根據方法界定經濟學的范圍;③經濟理論的基本原則和操作意義;④經濟學方法論個體主義與整體主義;⑤在解釋或預測現象時簡化的假設(如理性選擇、追求利潤最大化等) 所起的作用;⑥描述與實證、約定與規范以及理論中的相應應用;⑦經濟學的科學地位和領域擴展;⑧計量經濟學實踐與發展中的重要問題;⑨平衡經驗進路與哲學進路;⑩經濟學中實驗的地位作用;經濟學中數學和數理經濟學的地位作用;經濟學的文本和修辭;當代經濟學中理論、觀察、應用與方法論的關系。〔9〕
3.Palgrave定義的問題域
Palgrave在詞條“Methodology of Economics”中雖然沒有直接列出關于經濟學方法論研究包含哪些問題,但在區分當今經濟學方法論與傳統經濟學方法論的不同之處時概括了兩者關注問題的不同:(1) 傳統經濟學方法論關注問題:理論評價問題;(2) 當今經濟學方法論關注問題:理解經濟學實踐的多樣性。〔10〕
從以上權威定義關于經濟學方法論問題的闡述來看,前文關于經濟學方法論“傳統”問題的梳理在這些定義中得到不同程度體現,尤其是圍繞波普爾傳統的爭論引發的一般問題貫穿于三個定義中,所不同的是具體問題各有側重。當然,三大定義對于一般問題的表述有所不同,如Palgrave定義中理論評價問題可以看作是對范式和綱領問題的另一種表述。如果進一步梳理三大定義提出的問題,即對上述問題進行歸并、分類,我們可根據一般和具體的劃分重新整理出一個較為可行問題域。一般問題(A類) 包括:A1:經濟學的結構和策略:范式和研究綱領;A2:經濟學與自然科學和其他社會科學的異同;A3:理解經濟學實踐的多樣性。具體問題(B類) 包括:B1:實證經濟學與規范經濟學;B2:理由與因果;B3:經濟學中的抽象、理想化和“余者皆同”;B4:經濟學、計量經濟學中的因果關系;B5:在解釋或預測現象時簡化的假設(如理性選擇、追求利潤最大化等) 所起的作用;B6:計量經濟學實踐與發展中的重要問題;B7:經濟學中實驗的地位、作用;B8:經濟學中數學和數理經濟學的地位作用;B9:經濟學的文本和修辭;B10:當代經濟學中理論、觀察、應用與方法論的關系。
三、參考回歸模型的方法論問題檢驗
由于權威定義給出主要問題時需要考慮時效性、通用性,且通常會融入撰寫者本人一定的傾向性,為此,我們可參考經濟學回歸模型,將經濟學方法論的問題作為模型變量,以第一節問題梳理作為模型設定,以三大權威定義給出的問題域作為觀測樣本,并通過第二節問題劃分來估計模型,最終以較長時期內權威刊物文章的顯著問題分析作為模型檢驗。這樣既能反映經濟學方法論問題域的全貌,又能對其發展動態及沉淀問題有較好把握。
我們從《經濟學方法論》的期刊文章著手,看看實際研究中哪些問題為世界各地學者所關注,它們與上述問題相關程度如何。
1.高頻詞檢驗
經統計,《經濟學方法論》2007-2017年共有原刊論文240篇,其中不包括書評、會議綜述等,關鍵詞1200個。運用WPS表格重復項和查找功能,篩選出前后重復出現的關鍵詞(單詞或詞組),并將重復次數達5次及以上的關鍵詞與整理后的A類和B類問題進行對照,則可得其中各問題獲驗證程度如下(未得到關鍵詞佐證或較少關鍵詞佐證的則省略):
A1(7) ≥A2(4) ≥B1(2) ≥B2(2) ≥B3(2) ≥B4(2) ≥B5(2) ≥B7(2)
從比對結果可以看到,除B8和B9缺少直接支持外,其余各項獲得支持程度較為均衡,這也驗證了期刊樣本問題域較全面地反映實際研究的整體情況,或者說,對于經濟學方法論的詞條定義能較好地概括實際研究中各方面的問題。當然,這里只是簡單計數的結果,還沒有考慮高頻詞本身的重復次數不同,現在讓我們對高頻詞支持A類問題或B類問題的重復次數求和,再看看結果如何。
根據統計結果,雖然A類問題和B類問題在實際研究中均不同程度被涉及,但其中各問題的研究仍存在不均衡的現象:A3在A類問題中較為凸顯,B3、B7則在B類問題中較為凸顯。由于實驗經濟學是近年來經濟學實踐多樣化發展的一個方面,因而也可以將B7的凸顯看作是對A3的進一步凸顯。這也說明,隨著時間的推移,經濟學方法論研究在相對穩定的問題范圍內,逐漸表現出對某些問題逐漸聚焦的可能;同時,像抽象、理想化和余者皆同(B3) 等伴隨經濟學誕生就存在的問題,〔11〕則顯示出較強的生命力,在新的時代背景和語境下持續引起關注和探討。
2.全樣本檢驗
為了對A類問題和B類問題進行更全面的檢驗,現在我們對《經濟學方法論》2007-2017年期刊論文關鍵詞中除以上高頻詞以外的關鍵詞進行相關性統計。由于語義相關性很難通過系統軟件自動識別,我們依然遵循如上原則采取簡單計數的方法,對與所有問題項或A類問題、B類問題范圍內的所有問題項近乎同等相關或不相關的關鍵詞作排除處理,即僅對有識別度的、最能凸顯差異性的關鍵詞進行統計。
在剔除重復次數5次及以上的高頻詞后,樣本中的關鍵詞還剩745個。將這些關鍵詞按字母順序進行排序,并制作方便操作的工具表格進行相關性簡單計數。除B2和B4存在交叉情況外,每個關鍵詞根據語義最近原則歸入A類或B類問題中的某一項,或不歸入其中任何一項。經統計,可得出的總體結論是:高頻詞和其余關鍵詞對A類問題和B類問題的檢驗可以相互驗證。具體來看,在A類問題中,相比于A2,A1和A3是更加凸顯的問題;在B類問題中,相比于其他問題,B2、B3和B7是更加凸顯的問題。從不同樣本范圍來看,全體樣本對問題域特別是B類問題的支持更加均衡,說明經濟學方法論諸多學者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探討問題的多樣化特征明顯,也進一步驗證了問題域具有代表性;高頻詞樣本則對問題項的支持相對集中,說明經濟學方法論者探討最多的問題具有一定的收斂性,這也是隨著經濟學方法論學科發展而必然會提出的要求。
四、趨向方法論問題域的聚焦
作為交叉和分支學科,經濟學方法論從來不缺探討主題或問題,且進一步的研究必然圍繞一定的問題域而展開。通過以上分析,我們能初步看到問題聚焦的趨向,但仍需要指出,由于統計分析必然具有的技術上的和固有的局限,在經濟學方法論問題聚焦與發散的張力之間尋求簡單清晰的答案仍是難以完成的任務。
1.聚焦哪些問題?
經過一系列程序,我們從諸多問題中梳理出了最為相關的五個問題,它們分別是:(1)經濟學的結構和策略:范式和研究綱領;(2) 理解經濟學實踐的多樣性;(3) 理由與因果;(4) 經濟學中的抽象、理想化和“余者皆同”;(5) 經濟學中實驗的地位作用。它們被稱為“最”,是從得到經濟學方法論者實際研究的相關性驗證的程度上說的。現在讓我們分別看看這五個問題對于經濟學方法論來說意味著什么,它們與其他非“最”相關問題的相關性又如何?
(1) 經濟學的結構和策略:范式和研究綱領。“結構”一詞是庫恩的標志性概念,“范式”和“研究綱領”則幾乎讓人立即聯想到庫恩和拉卡托斯。的確,“經濟學的結構和策略:范式和研究綱領”這一問題深受庫恩、拉卡托斯哲學思想的影響。既然科學具有統一的結構,那么經濟學也不例外,將科學哲學運用于對經濟學整體結構的研究也就是合理的。至于經濟學中存在哪些范式和綱領,不同學者可能會給出不同的答案。例如根據庫恩,我們可以將邊際主義作為相對于古典經濟學的范式革命;如果我們把一般均衡理論作為研究綱領的“內核”,并探討經濟學中哪些構成“正面啟發”,哪些構成“反面啟發”,那么我們就是遵循拉卡托斯的進路。
以科學哲學關于科學的一般觀點投入對經濟學整體結構的分析,雖然在以“復興實踐”為旨趣的當代背景下顯得過于“宏大敘事”,但在經濟學對經濟現象的解釋和預測飽受質疑、甚至經濟學是否是一門科學都受到質疑時,探究經濟學的整體結構和策略顯得尤其重要。當然,這種探究可依賴的資源早已不再局限于庫恩和拉卡托斯,實證主義、證偽主義、建構主義、實用主義等不同進路都參與其中,形成不同范式和綱領。即使排斥宏大敘事的“復興實踐”,本身也代表了另一種范式。值得注意的是,經濟學方法論范式和綱領與“科學哲學貨架”上的范式和綱領并不總是保持同步,有時還會出現時序顛倒等現象。
(2) 理解經濟學實踐的多樣性。與探究經濟學整體結構不同,理解經濟學實踐的多樣性意味著不把經濟學放入統一的哲學框架,而是追求更為具體、可變的目標,即在“復興實踐”的名義下對經濟學多樣的實踐和過程給予關照和理解。這樣的目標無疑與傳統的理論評價和規范不同,它所依賴的資源也不再局限于哲學,而是拓展到社會學、文學、神經科學等諸多學科領域,甚至用經濟學本身來研究經濟學。在運用各種資源和方法理解經濟學實踐的同時,對這些實踐進行批判的力量則成為主要的區別和分水嶺。
經濟學實踐的多樣性直接意味著方法論的研究對象不再是傳統的經濟學理論,或主流經濟學,而是指向越來越多的“非主流”問題或模型,如對行為經濟學、實驗經濟學、時序計量經濟學方法等的關注,探討其中采用哪些特殊的方法、它與傳統經濟學研究進路的關系以及它如何是有效的等。這樣的方法論自然也很難應用于經濟學的整體實踐和歷史概括,因而也較少涉及經濟學的結構和策略。
(3) 理由與因果。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歸根結底是人的行為,而要理解人的行為就要給出各種行為的理由或其合理性。非理性的行為,長期被排除在經濟學研究范圍之外;理性的人或從個人理性出發的人,則長期作為經濟學研究的起點。如果一個人作出的行為,有很好的理由,包括外部的和內在的,他就被認為是理性的。但這種理由可能無限向外延伸,也可能求諸變幻莫測的內心世界,對此作出限定顯得不可避免。例如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某一地區居民對大豆的需求增大,必然導致該地區在可預見的時間內大豆價格的上漲,至于需求增大的理由是人們口味的變化還是其他則是另一個問題。
經濟學需要因果的解釋,這不僅對于經濟決策至關重要,而且對于它與民俗心理學等相區別也十分必要。但由于經濟學中基于因果關系的規律或“似律”并不具有如自然科學中那樣的確定性,早期經濟學家極力避免使用因果概念,就像邏輯實證主義者極力避免形而上學概念一樣。這種情況在計量經濟學中得到很大改觀,這主要得益于現代測量和統計技術的發展使得對經濟現象復雜因果關系的刻畫變得可能。但具有明顯概率特征的因果關系是否實在,抑或可作工具主義的理解,它是否具有解釋力等仍是當代哲學探討中充滿爭論的問題。
(4) 經濟學中的抽象、理想化和“余者皆同”。主流經濟學中的“經濟人”是一個追求最大化的概念,他具有完全的理性和完備的信息,足以在各種約束條件下作出最優選擇。這當然是對現實生活中人們的一種抽象和理想化,是“余者皆同”的反映。經濟學從一開始就尋求從盡量少的因果因素出發,來理解和預測人的復雜行為。甚至可以說,如果沒有對復雜現象的簡化(或極端化) 處理,也就可能沒有經濟學的誕生。與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抽象、理想化得出的結論是否仍然有效,在多大程度上有效,是擺在方法論學者面前的迫切問題。更進一步的問題也許還包括,單獨從經濟學出發,而不是從對人類行為諸多方面的理解出發而得出的結論是否仍然有效,又在多大程度上有效。
更核心的問題也許還包含在對經濟學假設的長期爭論中。我們看到,經濟學大廈建立在一些“不現實”的假設的基礎之上,這成為諸多學者批評經濟學淪為應用數學、脫離現實的主要依據。但也有一些學者認為,假設是否現實,與經濟學是否有效無關。正是在經濟學“假設之爭”中,不同學者對經濟學中的抽象、理想化和“余者皆同”的不同觀點得到了集中體現,尤其不同哲學立場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給不同時期的“假設之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5) 經濟學中實驗的地位作用。無法對經濟現象進行實驗向來是質疑經濟學成為經驗科學的有力證據,但隨著實驗經濟學、行為經濟學和計量經濟學等的發展,這種局面已得到很大改觀。實驗的方法涵蓋行為分析和心理研究、數據統計、比較與評估等來自經濟學內外諸多方法,實驗對象不僅涉及議價、拍賣等微觀市場行為,也涉及產業組織、資產市場等宏觀領域;與其他經濟學分支相比,實驗經濟學更加強調主動收集經驗數據以及理論和模型的現實影響,更加注重當前而不是歷史的經濟現象和數據。
既然實驗在經濟學中的地位如此重要,那么它又何以成為諸多學者廣泛關注和探討的問題呢?的確,這里值得推敲的問題有很多。首先,經濟學中的實驗與物理學、化學等自然科學中的實驗有何區別,是否有根本的區別?其次,經濟學中的實驗是否可復制,在多大程度上可復制?第三,如果實驗數據可重復得到,不同經濟學家對此是否會有不同的理解?第四,實驗者本身和實驗過程是否會影響實驗結果?也許還有更多具體的問題可以揭示實驗如何發揮作用及其發揮作用的限度,對這些問題的回答,都直接關乎實驗在經濟學中的地位。
2.為什么難以聚焦?
正如前文所述,找出經濟學方法論的關鍵變量或探討主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諸多經濟學方法論者長達數十年的研究很難用幾個主要問題來概括,何況相對聚焦的問題也總是處于變化發展的過程中。這種情況在近來經濟學方法論研究中尤其明顯,短暫的研究傳統和邊界逐漸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研究視域的高度發散和分化。常見的情形是,在經濟學中出現什么新的研究動向和問題,在經濟學方法論中就探討什么主題和問題。更貼近“實踐”的經濟學方法論即是對這種情形的描述,但相比于實踐的經濟學方法論者,這已經是在更大范圍和更加聚焦的方法論概括了。當然,即使經濟學方法論一直圍繞某些問題而展開,或一直以“宏大敘事”方式探討經濟學問題,要從諸多觀點和浩瀚文獻中識別出這些問題依然存在很大的制約。
另外,也許更為根本的原因是,經濟學方法論發展的前景與問題導向的關系也是不明確的。用經濟學回歸模型的概念來說,即經濟學方法論發展狀況這一因變量難以刻畫,導致作為自變量的問題域與它的回歸關系和系數難以確定。從學科發展來看,影響經濟學方法論發展的內部問題也許只是諸多因素之一,有時甚至不是主要的因素,因而即使經濟學方法論發展的量化指標得以刻畫,存在于它與問題變量之間的回歸關系也可能是十分微弱的。
3.真的需要聚焦嗎?
盡管存在這樣或那樣的局限,但問題聚焦對于經濟學方法論發展仍然具有不可忽略的作用。這不僅在于它提供了理解經濟學方法論諸多爭論的可能方式,更重要的是為探討經濟學方法論未來發展進路提供了起點。盡管經濟學方法論內部問題的聚焦和變化不一定是決定因素,但從學科發展來說這仍然可能是優先考慮的因素。我們可以說這些問題是思想市場選擇的結果,而不是原因,但它在研究中實踐后又必然成為對此進一步選擇的限制條件。無論經濟學方法論的發展如何緊跟經濟學的步伐,一定程度的問題聚焦對于學科發展乃至對于經濟現象的研究都顯得十分必要。
同時,我們需要的問題聚焦不太可能是傳統“科學哲學貨架”上的某種或幾種“產品”,我們也不太可能以統一的標準對經濟學的實踐進行方法論評價和反思,最有可能的聚焦則是面向特定經濟現象和經濟學時研究問題的聚焦,即方法論從“一對多”轉向“一對一”“多對一”“多對多”的模式。我們可以肯定地是,總體來說,正確的方法論不只一種,且它是否正確取決于我們面臨的經濟現象和經濟學研究的目的與方法。在這個意義上說,在經濟學方法論問題域上保持一定的開放性是適當的,但無論開放抑或聚焦,也都是有條件的或具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