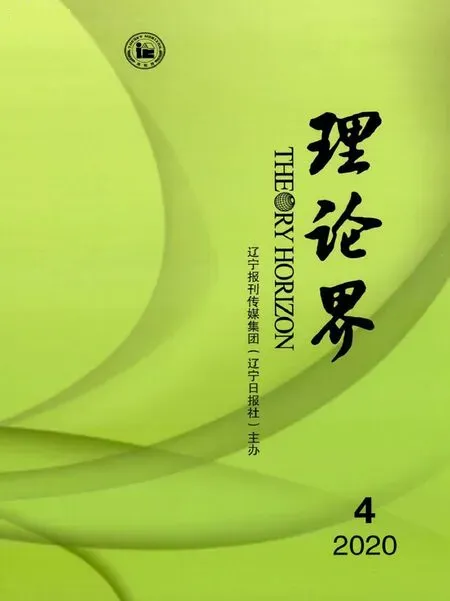論汪曾祺小說的音樂性
劉程程
叔本華說,音樂是“普遍程度最高的語言”,〔1〕他間接地肯定了音樂的多重表現意義,也說明了音樂與語言之間無法言說的曖昧。關于文學與音樂之間的聯姻關系,柯克認為“一首樂曲或一首詩或一出戲劇的整體的情感組織是很相似的”。〔2〕而談及小說與音樂之間的關系,高行健則在《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中這樣寫道:
小說一旦同音樂結合,重新迸發出來的那種表現力與感染力是音詩所難以比擬的,將賦予小說無窮變化的韻味。小說家用以標明各個章節的將不再是沒有生命的數目字,而是快板、慢板、行板,如歌如泣或一個明快的主題的變奏,寫這種小說的作家將會發掘出藝術語言中的更為微妙的感情色彩。〔3〕
這段話佐證了小說與音樂之間不可割裂的關系。同時,也帶來理解上的偏差:有人甚至以為,文學與音樂的結合是現代文學進行形式探索之時的首創。對此,筆者不以為然。中國文學史上,文學與音樂之間一直處于曖昧不清的膠著之中。戰國時期,《尚書·堯典》中便載有“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的理論。從先秦時期的《詩經》 《楚辭》,再到《漢樂府》,及至宋詞、元曲,文學有時甚至只是音樂的衍生品,人們無法生硬地將二者進行剝離。由此,小說與音樂之間的關系便無法說成是西方現代小說的首創。
汪曾祺的小說創作形式多樣,備受推崇。他深諳中國古典文學創作之道,并于西南聯大就讀期間,汲取了大量西方文學創作的精華,深受伍爾夫、契訶夫、紀徳等人創作的啟發。他敏銳地捕捉到小說與音樂之間的緊密關聯,并近乎刻意地加重筆下小說的音樂性體現。他的文字中,不只充溢著戲劇元素、繪畫因子,更加富含音樂的情致。他曾在文章中探討過語言的“聲音美”:
說小說的語言是視覺語言,不是說它沒有聲音。前已說過,人的感覺是相通的。聲音美是語言美的很重要的因素。一個有文學修養的人,對文字訓練有素的人,是會直接從字上“看”出它的聲音的。中國語言因為有“調”,即“四聲”,所以特別具有音樂性。〔4〕
以上文字可看作是汪曾祺對小說語言的獨到見解。在他看來,文字不僅能夠表達視覺意義,更應具有聽覺傳導的使命。因而他特別注重將音樂技巧嵌入到他的小說創作之中,并以雋永的文字中和著二者的差別。“音樂,也許是最接近情感的一種形式。音樂的流動性、抽象性、具體可感性,仿佛就是情感留給‘此岸’世界的一種身影,通過它我們真切把握了情感。”〔5〕“凡音者,由人也生也。人私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聲相應,故生變,變成方,謂之音。必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旄,謂之樂。”〔6〕不論古今中外,音樂都是傳遞情感的重要媒介。節奏變換、復調以及奏鳴曲式是音樂領域的重要技巧,汪曾祺在參悟了其中精髓的基礎上,將它們應用到小說創作之中,提供著有所裨益的創作經驗。他在小說與音樂這兩種看似不同,實則相通的藝術種類之間實現了融會貫通,供給著一盤盤視覺與聽覺并存的饕餮盛宴。
一、節奏的變換
節奏是音樂范疇的基本元素之一,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甚至被喻為“音樂的骨骼”。愛德華·漢斯立克這樣定義節奏:“對稱結構的協調性,這是廣義的節奏,各個部分按照節拍有規律地變換地運動著,這是狹義的節奏。”〔7〕節奏的規則或不規則的變換帶來強烈的樂感效應: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語。嘈嘈切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白居易以寥寥數筆道盡和鳴鏗鏘的節奏帶給人的強烈聽覺感受,足見音樂的節奏之美帶給聽者的震撼。作曲家們通過節奏的不斷變換,演繹出一首首蕩氣回腸的美妙樂章。汪曾祺深諳其道,他利用不斷變換的節奏為他的文本增添著跌宕起伏的韻律美。本文從“重復”“用韻”以及“流動性的張力”三個方面著手,探討汪曾祺小說的節奏之美。
1.重復
重復是作家慣常使用的創作手法之一。趙毅衡曾在文章中這樣寫道:“重復是意義世界得以建立的基石,沒有重復,人不可能形成對世界的經驗。重復是意義的符號存在方式,變異也必須靠重復才能辨認:重復與以它為基礎產生的變異,使意義能延續與拓展,成為意義世界的基本構成方式。”〔8〕中國作家對“重復”技巧的運用肇始于古代時期,古典文學中便有大部分文本注重對疊字的運用。追溯至數千年前,《文選》便載有《行行重行行》一詩,疊字“行”的使用加劇了游子離家之遠、路遠相見之難及思婦相思之苦。樂府民歌《木蘭詩》則以“唧唧復唧唧”作為小引,以機杼之聲傳達木蘭的聲聲嘆息,進而展開她替父從軍的故事。李清照則在《聲聲慢》中以“尋尋覓覓,冷冷清清,凄凄慘慘戚戚”為始,抒發著她國破家亡、形單影只的寂寥與落寞。汪曾祺參悟了中國傳統文學創作之道,他將古典文學的精華完全吸納,揉進文本的字里行間。
汪曾祺的小說,旨在通過對詞語的“疊加”使用,為小說的人物塑造及情節走向服務,增強文本的韻律感。小說《八千歲》中有這樣的文字:“……在一起時,恩恩義義;分開時,瀟瀟灑灑。”〔9〕疊字的簡潔強化了宋侉子行事果敢的性格特征,增強了人物塑造的立體感。句子的工整對仗頗似于魏晉南北朝之時盛行的駢文,卻祛除了駢文的華而不實,留下了鏗鏘有力的韻律美。汪曾祺的語言一向以簡潔準確著稱,言簡意賅卻恰到好處。“重復”的運用方便了讀者對句子的記憶,長句與短句的有機結合也成就了句子的抑揚頓挫,極大地增強了文本的可讀性。相較于當代作家莫言、閻連科、余華等人近乎拙劣的敘述語言,汪曾祺的文字不僅帶給人耳目一新的視覺享受,也提供了令人大快朵頤的聽覺盛宴。
他在意識流小說《綠貓》的首段運用了一連串的“為什么”進行反問:
——我為什么那么鈍,為什么一無所知,為什么跟一切都隔了一層,為什么不能掰開撕開所有的東西看?為什么我毫無靈感,蠢溷麻木?為什么我不是天才!〔10〕
這是一段典型的內心獨白,漫溢著主人公對自我的貶低。拋開字面意思,單就小說的語言而言,一連串的追問令讀者毫無喘息的空間,一直隨著作者的思緒游走,快節奏的敘述方式增強了文本的動感。通過對一連串“為什么”的使用,汪曾祺不動聲色地加深了句子的排比色彩,強化了小說語言的爆發力與沖擊力,為主人公自責情緒的發泄提供了渠道與出口。作者對重復的使用增強了語言的氣勢,通過文字,讀者可以輕而易舉地捕捉到主人公滿腔的憤懣、不平與自責的情緒。
2.用韻
除了對“重復”的巧妙運用外,汪曾祺也側重“用韻”。他說:“用合乎格律、押韻的、詩的語言來思維(不是想了一個散文的意思再翻譯為詩),這是我們應該向民歌手學習的。我們要學習他們,訓練自己的語感、韻律感。”〔11〕中國古典詩詞講究語言的韻律美,注意平仄韻律、對仗工整,對韻腳尤為關注。《紅樓夢》中便有例證,第三十七回,眾人初結海棠詩社,迎春要小丫頭隨口說出一字,以此限韻,小丫頭倚門而立,便說出“門”字,于是眾人決意限“門”字韻。又如第七十六回,黛玉與湘云于凹晶館聯詩,數得十三根柱子,便決意限“十三元”的韻,足見“韻”是詩詞曲賦的根基。汪曾祺對“韻”的把握增添了他小說語言的和諧之美,為讀者的聽覺帶來新鮮的審美享受,為文本增添了靈動的色彩。
1950年后,汪曾祺便長居北京。他受北京厚重的人文歷史影響頗深,創作了大量植根于北京文化的小說、散文,《云致秋行狀》是其中的典型。在這篇“京味兒小說”中,他運用地道的老北京語言,字里行間充溢著原汁原味兒的老北京風情。北京話方言特色明顯,精髓在于隱藏在其腔調中的韻律感及樂感。汪曾祺筆下的文字同樣極具節奏感:
戲班里的事,也挺復·雜,三叔二大爺,師兄,師弟,你厚·啦,我薄·啦,你鼓·啦,我憋·啦,仨一群,倆一伙,你踩和我,我擠兌你,又合·啦,又‘咧’·啦……〔12〕
加著重號的字都限“a”韻。韻腳“a”的文字的連續使用強化了句子的節奏性,讀者讀來朗朗上口。同時,老北京方言具備親切隨意、俏皮詼諧的屬性,汪曾祺對北京方言的合理運用,無形中拉近了讀者與主人公之間的距離。透過語言,小說呈現了老北京人慵懶、玩世不恭、油嘴滑舌的性格特點,讀者輕易便可捕捉到他們在日常生活中的隨意與懶散。
小說《寂寞和溫暖》中有這樣的文字:
稻子收割了,羊羔子抓了秋膘了,葡萄下了窖了。雪化了,茵陳蒿在烏黑的地里綠了,羊角蔥露了嘴了,稻田的凍土翻了,葡萄出了窖了,母羊接了春羔了,育苗了,插秧了。沈沅在這個農科所生活了快一年了。〔13〕
這段文字生動、有趣,汪曾祺將種種意象以“了”字為結尾的句子串聯起來。一連串“了”字的運用,看似是作者漫不經心的寫就,實則是他的匠心獨具——讀者讀來有詩的節奏、歌的韻味。黑格爾認為,“聲音不只是發泄情感的自然呼聲,而是情感的藝術表現。情感本身就有一種內容,而單純的聲音卻沒有內容,所以必須通過藝術的處理,才能表現一種內心生活”。〔14〕音樂的變奏帶給讀者輕松、歡快的閱讀體驗,也讓讀者透過字面感知著主人公沈沅的內心的快意及對生活的滿足。汪曾祺結合一系列生機盎然的意象,營造著春天欣欣向榮的情景以及歡快明朗的生活氛圍,宣泄著主人公不為人知的喜悅心情,與后文沈沅被打成右派后的悲慘境遇形成反差,兩相對照,強化著沈沅命運的坎坷與悲劇性。
3.流動性的張力
重復與韻律的使用為文本帶來蓬勃生機,除此之外,汪曾祺的小說同樣具有“流動性的張力”。即作者在文本中以一系列的動詞對主人公的動作進行文字意義上的再現,使得文本在具備畫面動感的同時,兼具流水一般的動態張力。徐岱的《小說形態學》一書中便提到了這一小說敘事文體特征:流動性張力。汪曾祺的小說很多情節都擁有流動性的張力,他通過對諸多動詞的連續使用,刻畫了主人公的活動畫面,在文本中形成跳躍的場景,增強了文本的流動感,因而具有“流動性的張力”這一音樂性特征。
小說《陳小手》中有文字為證:“陳小手接過來,看也不看,裝進口袋里,洗洗手,喝一杯熱茶,道一聲‘得罪’,出門上馬。”〔15〕陳小手醫德高尚,以人為本,對酬金的多少毫不在意,直接裝進口袋。洗手、喝茶、道擾、上馬,一串動作一氣呵成,整個活動場景充滿極其生動的張力與動態的視覺效應,在沖擊著讀者的視覺神經的同時,內蘊著主人公性格層面中流水般的從容豁達。汪曾祺以最簡潔的動詞還原著陳小手救人之后的一系列動作,簡潔平實、不加修飾的語言中,掩藏著汪曾祺對陳小手高潔精神的感佩。
《晚飯后的故事》開篇就有這樣的文字:
京劇導演郭慶春就著一碟豬耳朵喝了二兩酒,咬著一條頂花帶刺的黃瓜吃了半斤過了涼水的麻醬面,叼著前門煙,捏了一把芭蕉扇,坐在陽臺上的竹躺椅上乘涼。他脫了個光脊梁,露出半身白肉。〔16〕
一系列動作一呵而就,讀者可以通過主人公動作的悠閑,感知到他的愉悅自得。動感十足的文字的疊加運用使得整個畫面充斥著流動的張力與跳躍的動感。選文中,動詞的擇取畫面感強烈,兼具不可替代性,最平常卻委實最貼切。《晚飯后的故事》是典型的意識流小說,汪曾祺避繁就簡,漫無目的地講述著郭慶春意識的游離,一切皆圍繞著晚飯后主人公的“閑”展開。他以慣有的細膩為主人公營造了一個馬纓花盛放、令人熏熏然的黃昏,主人公的閑情在充滿流動性的語言中被一一呈現。汪曾祺以這些動詞的連續使用,為文本呈現著跳動的音樂性特征。正如丹納所說,“一個句子是許多力量匯合起來的一個總體”。〔17〕美感、畫面感、樂感,好的文字總是會帶給讀者不一樣的心動與享受,汪曾祺的行文特色即在于此。
二、奏鳴曲式的敘事風格
汪曾祺的小說具有顯而易見的“奏鳴曲式”敘述風格。奏鳴曲式(sonata form),由三個部分組成:
第一部分稱為“顯示部”,包括主部、連接部、副部和結束部四個部分。第二部分稱為“展開部”,絕大多數情況下是呈示部材料中矛盾沖突的繼續發展和更加劇烈的積極展開,使情感變化更為豐富。第三部分稱為“再現部”,再現的各個主題之間對比有了新的發展,樂思在經歷了劇烈沖突后形成了新的統一關系,兩個主題的調性彼此靠攏附合……由此發生材料和結構方面的變化。〔18〕
簡言之,即引子、顯示部、展開部、再現部以及尾聲五個部分。汪曾祺以奏鳴曲式的音樂曲式建構著小說的框架,展開著跌宕起伏的故事情節。
以小說《小孃孃》為例。小說伊始,汪曾祺憑借對謝家亭臺軒榭的介紹,導入故事的主人公。作為故事的小引部分,作者開始了對主人公小孃孃以及謝普天近乎素描式的介紹:漂亮大方的小嬢嬢,才華橫溢、風流倜儻的謝普天,二人年齡相仿,看似男才女貌、天作之合。接下來,汪曾祺直截了當地引出了二人之間的倫理關系:二人為嫡親姑侄關系——這也成為故事發展的焦點,是二人交往的最大障礙。
接著,在故事的第二階段,即顯示部部分,二人的關系發生了質的飛躍。因家道衰落,謝普天停學回鄉,與小嬢嬢同住在“祖堂屋”——這為二人關系的越禮提供了便利。汪曾祺借助日常瑣事細述了謝普天對小嬢嬢的關照:小到吃穿用度,大到理發保養,謝普天皆親力親為,對小嬢嬢溫柔呵護——事實上,他的行為已然違背倫理綱常,破壞了本該遵守的秩序。但在外人看來,二人的關系還未逾越倫理范疇,一切都看似合情合理。
進而,過渡到展開部部分。汪曾祺開始真正講述這個亂倫故事。主部主題可理解為是傳統的倫理綱常,小嬢嬢二人的行為是對道德倫理的大膽挑戰,二人的情感發展為副部主題。“雨還在下。一個一個藍色的閃把屋里照亮,一切都照得很清楚。炸雷不斷,好像要把天和地劈碎。”〔19〕汪曾祺有意將雷聲引入文本,作為情節發展的助力。雷鳴之下,他們的愛看似堅固,卻飽受摧殘——雷聲指代傳統道德、倫理綱常,更意味著主人公心中的道德枷鎖。面對倫理道德的拷問與譴責,徹底跨過鴻溝的二人并不勇敢,他們恐懼、不安、焦慮、忐忑、矛盾。汪曾祺直言:“他們很輕松,又很沉重。他們無法擺脫犯罪感。”〔20〕短暫的歡愉無法帶給主人公全部的滿足,種種復雜的情緒交織、糾纏、充盈在他們的內心深處,他們渴望著自我靈魂的救贖及精神枷鎖的解脫。主部主題與副部主題的交織纏繞,寫盡了主人公面臨的糾結。
之后,小說進入到再現部環節。故事發展到更為緊張的階段。隔墻有耳,小嬢嬢與謝普天的秘事為外人所知,傳聞紛紛。二人決意以“離開”規避各種閑言碎語,此時副部主題較為凸顯,他們的逃離帶給彼此的僅是片刻歡愉——讀萬卷書、行萬里路、極盡瘋狂之事。在這一環節,兩個主題互為上風,始終沒有割裂開來。私奔的二人確實擁有一段“只羨鴛鴦不羨仙”的快樂時光,然而他們始終處于“背離倫理道德”的陰影之下,二人的精神世界依舊被倫理道德的規約所束縛拘囿。小嬢嬢懷孕,本是喜事,卻頻繁做夢:
謝淑媛老是做惡夢。夢見母親打她,打她的全身。打她的臉;夢見她生了一個怪胎,樣子很可怕;夢見她從玉龍雪山失足掉了下來,一直掉,半天也不到地……每次都是大叫醒來。〔21〕
謝淑媛的噩夢源于對自我選擇的惶恐不安與矛盾糾結,恪守倫理秩序的觀念深深植根于她的靈魂深處,她始終飽受著倫理道德對她的精神折磨。他們二人的所作所為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整個家族的背叛,對整個親情圈子的否定。她時常撫摸小腹,將孩子比為“罪孽”。行文至此,故事已經接近尾聲。
尾聲部分。小嬢嬢沒能如愿順利生產,她死于難產,帶著所謂的“罪孽”離開。汪曾祺有意地將她的結局寫成悲劇,倫理道德徹底戰勝了情感。謝淑媛的死結束了二人的顛沛流離,謝普天將她的骨灰帶回家鄉,埋在桂花樹下。故事以謝普天、陳聾子的飄然遠去、不知所終為結局,是謝普天最終參悟了人生的關竅,還是他因謝淑媛的死產生了絕望的情緒,外人不得而知,但汪曾祺如此設置必然有其因果。筆者以為,小說是以倫理道德的完勝為終,再次強化了故事的主部主題。
三、復調技巧的應用
巴赫金在《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一書中,將“復調”作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要創作特征,由此提出了“復調小說”的概念。作為一種音樂范疇上的應用技巧,復調指代若干(兩條及以上) 的獨立意義的旋律聲部的結合。作為小說技巧,復調小說更多被理解為在一篇小說之中的若干(兩個或多個) 主題的統一呈現。復調小說遵循“對位法”,〔22〕米蘭·昆德拉在《小說的藝術》中概括了小說對位法的必要條件:“一、各條‘線’的平等性;二、整體的不可分性。”〔23〕汪曾祺巧妙地將“復調”應用到他的小說內部,小說《大淖記事》便是其中一例。
通常,學界將《大淖記事》的主題理解為“人性真醇的體現”以及“純愛的頌歌”。事實上,除此之外,《大淖記事》依然存在其他線索——女性自主意識的凸顯及劉號長等軍閥勢利的殘暴。《大淖記事》以作者對“大淖”的近乎詩意的書寫作為開端,引出大淖地區的風土民情——淳樸的民風成就了善良、和美、勤勞的大淖鄉民,以及主題之一的“女性的自我與獨立意識的顯現”——大淖的女性獨立、自主、勤勞,她們“像男人一樣的掙錢,走相、坐相也像男人”。〔24〕較之于男性,汪曾祺筆下的女性多了份果敢、堅毅,甚至支撐了整個家庭的重擔,男性反而成為她們的附庸與陪襯,她們的“野性”成為“自主意識顯現”的有力憑證。之后,汪曾祺正式步入“主題敘事”。
主人公巧云的出場牽引出她的不凡身世——母親在她幼年之時,因為真愛私奔(也可視為女性自主意識凸顯的有力憑證)。此為線索一。接著,汪曾祺娓娓地講述了兩個純真青年的唯美愛情,十一子英雄救美,解救巧云于危難,情竇初開的兩個人面對愛情手足無措,四目相對之間,一首關于愛情的頌歌已然開始奏響,汪曾祺所要展示的第二層線索也已完備。然而,汪曾祺卻筆鋒一轉,為兩人的愛情設置險阻——劉號長乘人之危,將巧云玷污——這是故事的轉折點,也是故事的線索三,即劉號長等人的兇悍蠻橫的顯現。巧云爹的嘆氣、姑娘、媳婦的議論皆為劉號長的流氓行徑提供佐證。而后,劉號長得知一切,聚集手下的“流氓”,“一人一根棍子,摟頭蓋臉地打他(十一子)”、〔25〕“七八根棍子風一樣、雨一樣打在小錫匠的身上”〔26〕——汪曾祺以最直接的語言講述著劉號長等人的淫威高壓。十一子面對劉號長等人的恐嚇兇殘不為所動,“不說話”、“牙咬得緊緊的”,他對愛執著而堅定,因而被打得遍體鱗傷、命懸一線。巧云聽信土方,拿尿堿救治十一子,患難與共,不惜親嘗尿堿——作者以最樸素的語言、最質樸的行為頌贊著純愛的唯美。大淖鄉民不屈從于劉號長等人的血腥暴力,為受傷的十一子送去關心與問候——這是故事的又一重線索——人性真醇的體現。故事以“大團圓”式的結局為終:劉號長被調、十一子漸愈、巧云獨立支撐起家庭。如此看來,多條線索在小說中并行不悖,互相摻雜卻彼此獨立,共同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小說結構。很難說只有哪一項是小說的最主要線索,各種線索交織纏繞,共同發聲,多種線索并存、諸多聲音兼備,使得整個小說更為完滿。借助這一音樂技巧,汪曾祺以慣常運用的結局模式完結了整個故事,刻畫著有血有肉的、具有獨立人格的人物形象,建構了他意念中真愛不滅的理想烏托邦,成為中國當代文學史上不可或缺的靚麗風景。
小說《鑒賞家》為“復調”技巧的運用又添佐證。小說中多重線索并存:A.季匋民與葉三之間的知己之交;B.葉三為人的正直、對生活本真的體悟、對審美情趣的把握以及對藝術的熱忱;C.季匋民識人知人、為人清高。汪曾祺歌詠著二人高尚的情懷,贊嘆著二人品行的高超與友誼的彌足珍貴。
小說開篇,汪曾祺便直截了當地引出故事的兩位主人公:畫家季匋民與鑒賞家葉三。鑒賞家是汪曾祺賦予葉三的“美稱”,葉三事實上并無“學院派”意義上的“鑒賞”資格。他出身寒微,靠賣水果維持生計。然而,他的生活卻別致而精彩:守著四時送果子、果子個個是好的,他深諳經商之道,對兒子的撫養絲毫不馬虎,兒子的孝順側面反映了葉三品格的高尚。兒子們勸說葉三放棄賣果子,葉三的反應異常激烈,甚至生氣,情急之下表明了送果子的初衷——為給季匋民送果子,并說:“你們也不用給我做什么壽。你們要是有孝心,把四太爺(季匋民) 送我的畫拿出去裱了,再給我打一口壽材”。〔27〕為了季匋民的畫,葉三甘心放棄安逸的生活——事實上,葉三的兒子們家境殷實,他的養老問題不足為慮,但正是對藝術的執著熱愛、對生活本真的孜孜以求,葉三始終堅持自我。進而,汪曾祺便平鋪直敘,導入季匋民,講述二人之間的交往。葉三真心贊賞季匋民的畫,并能一針見血地指出其中的不足與缺憾,發自于肺腑本心,絕非阿諛諂媚;季匋民對葉三的品評頗以為意,不以“大畫家”身份自居,對“假名士們”的高談闊論深惡痛絕——二人頗有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之感。葉三并不負季匋民所望,他對季匋民所贈之畫也是珍之惜之,視若瑰寶。二人的友誼彌足珍貴,并未隨著死亡的降臨而結束,四季八節,葉三依舊到季匋民墳上供奉鮮果。季匋民的遺作價錢上漲,葉三不為所動,不賣藏畫——這就包含雙重旨意:其一:葉三對藝術的珍視;其二:他對友誼的看重。三重線索你中有我,我中帶你,很難將三者進行區分剝離,也正因如此,構成了復調小說的審美準則。“復調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把額外的意義留給讀者。讀者需要根據上下文來判斷話中之話,還需要調動自己的想象力。”〔28〕多重線索的共同發聲為文本提供了豐富內蘊,復調小說的魅力得以顯現。
嚴格說起來,這也可以訴諸“聽覺敘事學”范疇,即聽覺想象力(auditory imagination):“所謂的聽覺想象力是對音樂和節奏的感覺。這種感覺深入到有意識的思想感情之下,使每一個詞語充滿活力:深入最原始、最徹底遺忘的底層,回歸到源頭,取回一些東西,追求起點和終點。”〔29〕最終“喚起與原始感覺有千絲萬縷聯系的想象與感動”。〔30〕文學敘事都是一種“講故事”的行為,這里的“講”就是“說”,即故事要被“說”出。而“聽”是“說”的對立面,有“說”就要有“聽”,因而不能忽略“聽覺敘事”的存在。汪曾祺的語言除了帶給讀者“賞心悅目”的視覺感受之外,同樣具有其“聽覺意義上的魅力”。
同樣是敘事,老舍筆下的文字自帶“京味兒”的光環,閱讀老舍,仿佛置身于老北京的市井街頭,感受到、觸及到以及“聽到”的是氣息濃郁的老北京“市井氣”,自有其“油滑”的特質;魯迅的文字則略顯莊重,具有“令人沉思”的特性,閱讀魯迅,是在沉痛之中思索人生及國民性優劣,沖擊讀者耳膜的則是沉痛、蒼涼以及悲哀等種種復雜;路遙的文字聽起來卻似踩在結實的黃土地上,因命運的厚重感、生存的困境是路遙文字的著力點;張愛玲的文字則別具“海上風情”,為讀者呈現的是迷離、有萬般風情的舊上海,讀者“聽到”的是時間的滄桑與回憶的雋永。而汪曾祺則不然,“他的文字,整體上顯得熱情,飽滿,像青翠欲滴的綠葉,像汁液飽滿的果實,有春水般的柔滑而純凈的細膩感”。〔31〕汪曾祺的文字有著“水一樣流動的特性”,具備“水”一樣的音樂性與日常生活性,他的語言“聽起來”生活氣息濃郁,似是與讀者在閑話家常,暢談人生經歷,于無意間拉近了讀者與作家之間的心理距離。樸實之中透著親切隨和,同時兼具音樂的節奏感,這便是汪曾祺的語言特色。“音樂話語的在場,或使小說的敘事結構本身充滿強烈的‘音樂性’,或成為指涉小說人物性別身份、階級身份、或深層性格的‘主題動機’‘固定樂思’,對小說文本的建構、生成、闡釋具有不可忽視的重要意義。從純粹的‘文學性’閱讀走向‘音樂性閱讀’,便能從另一個維度解讀這些文本,獲得意想不到的收獲。”〔32〕汪曾祺通過變換的節奏、奏鳴曲式的敘事風格以及復調技巧的應用,在小說與音樂之間實現了“會通”。正因如此,他的語言更加精妙、鏗鏘有力、樂感十足。對小說敘事的音樂性的充分把握,也為更深層次地理解汪曾祺的語言提供了一個新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