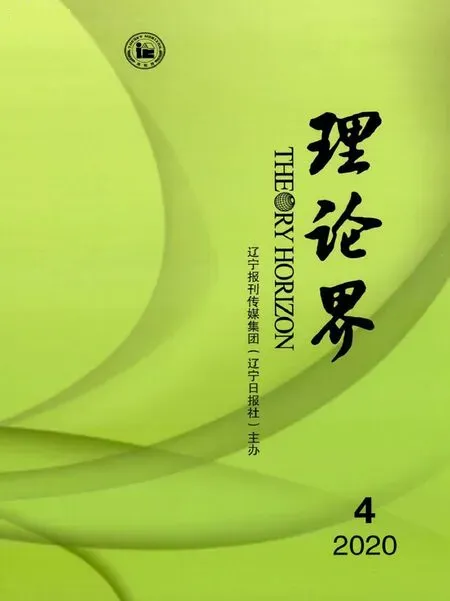哈貝馬斯的反思理論及當代性
——以《認識與興趣》為中心的討論
李錦程
《認識與興趣》 (1968) 是哈貝馬斯一部階段性的總結著作,該書提出一種認識興趣理論,具有明確的主題:一方面,批判實證主義的客觀主義知識學;另一方面,以認識論為批判理論奠定規范基礎。哈貝馬斯本人指出,《交往行為理論》的主要觀點正是在認識興趣理論的基礎上產生的。〔1〕循此路徑,學界的《認識與興趣》研究主要關注認識興趣理論的試驗性及其在哈貝馬斯思想中的承前啟后作用。
認識興趣理論的目標是為一種自我反思的批判科學奠定認識論基礎,本文嘗試把關注的核心從批判科學的認識論奠基轉回到哈貝馬斯所構建的自我反思的批判科學本身,即一種反思理論。哈貝馬斯所言的自我反思的批判科學是通過對馬克思的批判理論進行重新解讀實現的,其直接動因是實證主義的認識論批判,而采用的解釋框架則是勞動和相互作用的區分。從否定的意義來看,哈貝馬斯的反思理論混淆了兩種不同的反思概念,從而引發他的語用學轉向。本文認為,反思理論未必會隨著哈貝馬斯的語用學轉向而式微,其中隱含的兩種不同的反思概念之間的張力,對于我們理解法蘭克福學派的歷史發展和當代走向具有重要的思想意義。
一、實證主義使認識論喪失反思維度
1.實證主義的技術合理性批判
實證主義起源于19世紀30年代,是認識論的一種形式。一般來說,實證主義者賦予自然科學以首要的地位,并將其視為知識的唯一來源。20世紀早期的邏輯實證主義者認為,凡是不能通過經驗觀測證實或證偽的陳述就是無意義的,價值判斷既是如此。那么在進行科學研究時就必須避免規范性的思考,否則可能導致獨斷論。
哈貝馬斯認為,實證主義的理性形式與自然科學在當代社會中的統治地位是分不開的。隨著自然科學的飛速發展和人類文明的日益技術化,科學技術與工業管理形成一個循環的系統,并主導著工業社會的發展。理性在其中主要表現為對技術的有目的的合理性的運用,實證主義便是這樣一種對理性的技術理解的哲學反映。實證主義的理性形式改變了理性的原有內涵。理性在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中是批判的和實踐的,目的是把人類從來自內部的和外部的強制中解放出來。“在批判的理性和獨斷論之間的斗爭中,理性有自己的觀點;在解放的每一個新階段上,理性都取得巨大的勝利。”〔2〕
哈貝馬斯批判實證主義理性概念的自相矛盾。如果理性僅僅意味著價值中立的技術理性,那么實證主義對獨斷論的批判本身就是主觀的;如果理論和實踐的關系僅僅是技術的,那么實踐問題一旦不能以技術的方式提出和解決,就只能留給非理性的抉擇。實際上,實證主義的價值中立是表面的。在價值中立的旗號下,“選擇目的合理的手段建立的經濟學,即通過以技術手段為形式的、有限的預測得到證實的經濟學,是唯一得到認可的‘價值’”。〔3〕
哈貝馬斯認為,實證主義對理性的技術性理解是一種唯科學論,拋棄了認識論的反思維度。可靠知識的來源是近代哲學認識論的中心問題,但是只有到了康德提出“先天綜合判斷何以可能”問題的時候,認識論才真正意識到自身的反思維度。然而,實證主義卻否認認識的條件這個先驗邏輯問題,認識的意義完全取決于科學的成果。〔4〕實證主義使知識學替代認識論,認識著的主體不再是認識的構成要素,在某種意義上退回到了康德之前的哲學中去。
然而,實證主義的知識學取代認識論是一個歷史發生的過程,我們無法簡單地回到康德。為了克服實證主義,我們有必要回顧實證主義的史前史,理解認識論的消解過程。
2.被遺忘的反思經驗
哈貝馬斯所說的被忘卻了的反思經驗,指的是從康德到馬克思的德國思想運動。具體分為兩個階段,先是黑格爾用精神現象學的自我反思代替康德的先驗反思,接著馬克思又用社會勞動的綜合促進了黑格爾的自我反思進程。
黑格爾批判康德式的先驗反思,“人在認識之前,就應該認識認識能力。這和一個人在跳下水游泳之前,就想要先學習游泳是同樣可笑的”。〔5〕黑格爾反對本源哲學的企圖,用精神的現象學的自我反思來取代康德的先驗反思。精神現象學的自我反思把認識看成一個精神不斷自我批判、外化和展現自身的運動過程,“認識活動……成了一種把自身變為全體的環節的行動”。〔6〕對此可從兩方面理解:一方面,從精神運動的進程看,認識應該是內在地產生于現象學的反思經驗中;另一方面,從黑格爾對絕對知識的設定看,認識又無需、也不可能由此得到說明。〔7〕哈貝馬斯認為,《精神現象學》的模棱兩可之處削弱了黑格爾對康德的批判力量。黑格爾雖然指出認識應當從反思經驗中提出自身的標準,但是同一哲學的設定卻把反思和批判的認識相對化了。
然而,黑格爾的批判包含合理的成分,它把認識論所依賴的反思意識揭示為現實的結果,具有一個解體和產生的過程。馬克思繼承了黑格爾對先驗認識的批判,卻沒有接受同一哲學的設定。馬克思認識到“意識的自我反思觸及的是社會勞動的基本結構,并在社會勞動中揭示從事客觀活動的自然存在物(人) 同他周圍的客觀自然物的綜合”。〔8〕在哈貝馬斯看來,社會勞動具有綜合的意義,雖然馬克思沒有將之建構成唯物主義的認識論。社會勞動的綜合既不依賴于先驗意識,也不依賴于絕對精神的活動,而是類主體的成就。然而,類主體通過社會勞動的綜合不是絕對的,而是取決于生產力的歷史發展水平,它認識到自身是通過以往主體的生產及自己的生產產生的。
哈貝馬斯指出,馬克思將生產力的發展指認為在黑格爾那里掩蓋的反思經驗的進步機制,但是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哲學并不足以作為認識的自我反思的保證。因為馬克思是按照生產的模式理解反思的,把反思過程歸結到了工具活動的層次上。在哈貝馬斯看來,馬克思的人的科學“同自然科學一樣,把自己理解為生產知識,因而掩蓋了它必須賴以拖動自己前進的反思力量”。〔9〕
概言之,哈貝馬斯認為黑格爾和馬克思都揭示了反思經驗,但是錯過了堅持反思的正確方向,無法抵御實證主義的沖擊。伴隨實證主義的興起,認識論成了知識學,理性成了技術理性,認識論的反思維度喪失了。
二、通過轉換解釋框架恢復反思經驗
為了恢復認識論的批判維度,我們有必要回到黑格爾和馬克思所開啟的反思方向,哈貝馬斯試圖通過轉換解釋框架來做到這一點。
1.區分勞動和相互作用
在解讀馬克思著作的過程中,哈貝馬斯發現馬克思思想中存在某種矛盾性。按照生產模式理解的反思,似乎只適用于馬克思賴以批判黑格爾的哲學基礎——自我產生的類的生產。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馬克思明確指出,生產方式的科學化并不會直接導致勞動主體的解放,而只能激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矛盾。哈貝馬斯認為,馬克思在具體研究中使用的是社會交往系統概念,考慮的不僅僅是生產模式,而是包括勞動和相互作用的社會實踐。
哈貝馬斯把勞動和相互作用的區分回溯到青年黑格爾在耶拿時期(1801-1807) 寫的《精神哲學》。在《精神哲學》中,青年黑格爾把“精神”視為自我形成的媒介。“自我,作為自我意識,只有當它是精神時,……才能得到理解,而作為非同一的、認識自身的主體,是在相互聯系的基礎上借助于普遍的東西聯合在一起的。”〔10〕自我只有在與他人的相互關系中才能認識自身,青年黑格爾用戀人的關系來說明其中的倫理關系。“在愛情中,分離的東西仍然存在但不再作為分離的東西,而是作為一致的東西……彼此息息相通。”〔11〕戀愛的雙方能夠在對方身上認識到自己,然而這種主體間性不是直接的,而是先前發生的矛盾和解的結果。哈貝馬斯認為,黑格爾在此提出了一種倫理關系的辯證法,愛即非強制性的對話關系中的和解。
勞動是精神的另一個范疇,是一種能夠使欲望得到滿足的方法。然而,勞動不同于欲望的滿足,勞動的辯證法協調主客體:一方面,勞動滿足直接的欲望,這時勞動把自我當成物,把自身做成對象;另一方面,自我在勞動過程中得到經驗,能夠控制自然。勞動和相互作用的關系表現為:一方面,兩者是分立的,交往規則不依賴于工具活動,而技術規則同相互作用的交往活動也沒有關系;另一方面,兩者相互聯系,黑格爾通過提出法律規范和勞動過程之間的聯系說明這一點。“自我同一性的制度化,法律上承認的自我意識,是勞動和為獲得承認而斗爭這兩個過程的結果。”〔12〕哈貝馬斯認為,黑格爾用從外部自然和從內部自然解放出來的觀點把勞動和相互作用相連接,為反思經驗提供了一個新的解釋框架。
2.生產模式批判
以勞動和相互作用的區分作為理解類生產的坐標系,對認識類的歷史形成具有決定性意義。雖然生產力的發展有助于克服制度和意識形態壓迫,但不會自動導致社會的反思性認識。只有通過反思活動才可以擺脫意識形態的欺騙性,將社會從制度壓迫中解放出來。因此,“標志社會形成過程道路的,不是新技術,而是反思的諸階段”。〔13〕
除了勞動的綜合外,綜合必須具有第二個維度——斗爭的綜合。斗爭的綜合使兩個社會階級相結合,形成反思知識。哈貝馬斯指出,在具體的社會研究中,馬克思有可能使用了青年黑格爾的模式來說明斗爭的綜合。
馬克思把倫理的總體性理解為人們在其中進行生產的社會,倫理是制度框架,也是生產框架。〔14〕作為階級對抗運動的倫理辯證法必須同生產力的發展相適應,受到勞動系統的制約。在政治經濟學批判中,我們看到馬克思將階級對抗錨定在勞動契約制度上。這種契約制度看似自由,卻是以商品的形式把生產者的社會關系反映成了物與物的關系,從而掩蓋資本主義制度對自由的交往關系的壓制。“商品形式的奧秘不過在于:商品形式在人們面前把人們本身勞動的社會性質反映成勞動產品本身的物的性質。”〔15〕通過對商品拜物教的批判,馬克思揭露了資本主義制度的意識形態和虛假合法性。
借助勞動和相互關系的解釋框架,哈貝馬斯認為馬克思的批判意圖將得到更好的實現。生產力的發展和階級斗爭的歷史是相互交織的,雖然反思能力可能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增長,但我們無法將階級斗爭化約到生產模式中去。相反,我們必須重建階級意識的框架,并在其中分析生產的歷史,從而意識到現實生活方式的荒謬性并將之革命化。“認識著的意識只有隨著它自己把類的形成過程理解為始終以生產過程為中介的階級對抗運動,認識到自己是顯現出來的階級意識的歷史結果,并從而作為自我意識擺脫客觀假象的束縛,它才能拋棄它賴以存在的傳統形式。”〔16〕
類生產以社會勞動和階級對抗為媒介,人的科學必須再現隨著勞動系統的發展所顯現出來的意識過程,并在此過程中進行自我反思和意識形態批判,以尋求從壓迫中解放。換言之,認識論的反思活動必須以一種批判的社會科學的形式呈現出來。
三、興趣理論為批判科學奠定規范基礎
哈貝馬斯以“勞動和相互作用”模式代替馬克思的生產模式,將馬克思的社會理論揭示為反思活動的徹底形式。《認識與興趣》的主要工作,便是要從認識論的角度為這樣一種批判科學奠基。為此,哈貝馬斯把“興趣”范疇引入認識論,闡明批判科學與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在認識模式上的差異。
1.認識的興趣導向與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的客觀主義幻象
“我把興趣稱之為與人類再生產的可能性和人類自身形成的既定的基本條件,即勞動和相互作用相聯系的基本導向。”〔17〕哈貝馬斯所說的興趣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個人喜好,而是理性的興趣,具有“準先驗”的性質:一方面,興趣具有先于認識的人類學根基,決定著認識的可能方向;另一方面,興趣又只能在人類特定的社會實踐的認識活動中顯現出來。
根據興趣與不同的認識領域的特殊聯系,哈貝馬斯劃分出三種不同的興趣。技術的興趣引導經驗—分析的自然科學;實踐的興趣引導歷史—解釋的精神科學;解放的興趣引導批判的社會科學。哈貝馬斯以皮爾士對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反思和狄爾泰對精神科學的方法論反思為例,指出二者都注意到了不同科學背后的特定興趣,只是囿于客觀主義的誤解,錯失了對認識與興趣之關系的揭示。
與實證主義者不同,皮爾士注意到,研究主體是生活中的現實個體,研究對象是通過研究過程的機制確立下來的,研究的邏輯則取決于推論的程序。因此,邏輯規則的有效性問題首先需要一種先驗邏輯的回答。不過,“皮爾士只是說,如果一個從整體上說有限的研究過程是可能的,那么綜合推論事實上就必然是有效的”。〔18〕哈貝馬斯認為,皮爾斯的論證仍然局限于自然科學的客觀主義理解。哈貝馬斯指出,某些跡象表明皮爾士把研究的方法論框架理解為動物受到傷害的控制機制的歷史替代物,沿著這種思路繼續推論,認識的功能可以被理解為動物本能的行為控制的補償。那么興趣的滿足就是衡量有效控制活動的標尺,正是這種興趣決定著自然科學研究過程的先驗框架內現實的必然客體化方向。〔19〕
狄爾泰則力圖揭示精神科學不同于自然科學的方法論,將生活共同體設想為精神科學的客觀框架。生活共同體一方面由生活史中的自我形成所規定,另一方面由對話關系和相互承認所規定。哈貝馬斯將狄爾泰的方法論與皮爾士的方法論進行了對比,“在皮爾士看來,現實中遭到失敗的行為準則,應該被證實了的技術規則代替;在狄爾泰看來,不可理解的生活表現和破壞了相互期待行為的生活表現應該得到解釋”。〔20〕解釋學的方法旨在用共同的規范確保日常生活中交往行為的主體間性,這意味著解釋學受到一種實踐的認識興趣的支配。然而,狄爾泰卻想讓解釋學擺脫興趣聯系,重新陷入了客觀主義。
2.批判科學是認識與興趣的統一
興趣把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的先驗框架分別歸結為勞動和相互作用的生活聯系,使得二者的認識扎根在生活中。然而在研究過程中,自然科學家和精神科學家往往不會自發地進行自我反思,意識到認識與興趣的聯系。解放興趣引導的批判科學則不同,其特征恰恰是把引導自身的興趣納入到自我反思之中。
哈貝馬斯將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視為批判科學的例證,并將之與馬克思的社會理論相結合。心理分析是主體間的反思結構,醫生與病人之間的對話則是為了重建合理的交往關系,對扭曲交往的治療。馬克思發展了類的自我形成觀念,但馬克思未能說明這種重建類的自我形成的批判科學的性質。心理分析把統治和意識形態理解為被扭曲的交往活動,提供了一種合理的解釋框架。
根據弗洛伊德,統治制度和文化傳統壓抑本能情感,產生了病態的替代性強制。社會病癥同個人病癥一樣,采取的是扭曲的交往形式。隨著社會病癥的出現,也就產生了消除病癥的興趣,改變他們的興趣在社會系統中即表現為對解放的興趣。〔21〕反思是解放興趣的活動,它是個人意識到無意識的東西,進而對生活進行干涉。在批判的自我反思過程中,認識的過程與自我形成過程是一致的,認識和行動成為同一的活動。
在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的研究框架中,認識與興趣是分離的,只有在自我反思的批判科學中,認識與興趣才取得了統一。由于認識的興趣導向性,批判科學較之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就更為根本,后兩者也只有在與批判科學的關聯中才能得到合理的定位。至此,哈貝馬斯在認識興趣理論中完成了批判科學的基礎奠定工作。
四、反思理論的含混性引發語用學轉向
認識興趣理論是反思理論的認識論推進,并最終將反思經驗落實到自我反思的批判科學中。然而,認識興趣理論對三種科學的劃分卻使反思經驗的含混性顯現出來,反思理論內部存在不可調和的張力。
1.自我反思概念的雙重意義
哈貝馬斯的認識興趣理論遭到了麥卡錫的批評,麥卡錫一針見血地指出,存在兩種“自我反思”概念——先驗反思和批判反思,哈貝馬斯在《認識與興趣》中的論證依賴于對二者的不加區分。
具體來說,一方面,哈貝馬斯繼承康德的思路,強調對認識的可能條件的反思。在此,“自我反思”意味著對知識的主體條件進行探尋,比如皮爾斯對自然科學的先驗邏輯的追問和狄爾泰對精神科學的方法論反思;另一方面,哈貝馬斯融合弗洛伊德和馬克思的思想,強調意識形態批判的必要性。在此,“自我反思”表現為一種批判活動,它使我們意識到自我形成過程中的宰制性因素,并尋求對現狀的打破和改變,比如馬克思對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意識形態批判和弗洛伊德描述的心理分析的治療過程。
麥卡錫認為,兩種反思概念并不一樣,前一種是處理有效的知識和行動的普遍預設和條件的哲學反思;后一種關注的是一種特殊主體的特定形成史的反思,它通過從自我欺騙中解放出來,重建主體自身的自我理解。〔22〕
哈貝馬斯是運用現象學的反思經驗將兩種不同的反思含義統一起來的。作為個體和類的自我形成過程,現象學的自我反思經驗既是對知識條件的反思,又是對宰制性生活的批判。這種反思經驗同黑格爾的絕對精神運動不同,它受條件限制,“人類的形成過程取決于主觀自然以及客觀自然的有限條件:它一方面取決于相互作用的個體的個體社會化條件,另一方面又取決于交往活動同技術上可以支配(控制) 的環境的‘物質交換’條件”。〔23〕
針對哈貝馬斯的處理,阿佩爾批評哈貝馬斯簡單地把先驗反思與實踐參與等同起來。對認知有效性的理由和假設進行的商談檢驗是在一般理論反思中實現的,不能夠和馬克思的批判性實踐相混淆。〔24〕布伯納則認為,從對系統扭曲的交往的批判中,無法得出旨在引導社會條件轉化的實踐的主張,將實踐奠基在理論的先驗條件中對實踐和理論都不公。〔25〕這些批評皆在不同程度地指出,對普遍條件進行的先驗反思和對特殊形成史的批判反思,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2.哈貝馬斯的回應和理論轉向
哈貝馬斯在1973年《認識與興趣》新版后記中作出回應:“‘反思’這一詞匯的傳統意義,原出于德國唯心主義的使用,掩蓋了(混淆了) 兩個方面:即一方面壓根兒掩蓋和混淆了對主體可能具有的認識能力,即語言能力和活動能力的條件的反思;另一方面掩蓋和混淆了對無意識造成的局限性的反思,而任何一個主體在其形成過程中自身都受這些局限性的制約。”〔26〕
事實上,哈貝馬斯承認了兩種反思的區別,并凝練地將兩種反思分別命名為“批判”和“重建”。批判針對特殊的事物,旨在改變意識形態的扭曲,具有實踐后果;重建則處理普遍條件,旨在揭示匿名的規則系統,無需實踐結果來解釋。二者盡管存在緊密的聯系,卻是不同的。
批判與重建,或批判反思和先驗反思的區分將危及到認識興趣理論的有效性。一方面,先驗反思既不無技術和實踐的追求,也無解放的追求,似乎并不在三種興趣引導的認識之內;另一方面,相比先驗反思,批判反思是理性的特殊運用,無法真正實現理性和興趣的統一。
哈貝馬斯不同意先驗反思是去興趣化的,并賦予其與解放興趣一種間接的聯系。“我至少是不能想象一個嚴肅的批判社會理論竟與解放興趣之類的概念毫無內在聯系。……解放興趣絕不是一種應急的價值取向:急于擺脫苦難。……在人類科學結構中,它是根深蒂固的……這種價值取向深深地內建于人類生活的繁衍中。”〔27〕
即便如此,如麥卡錫指出的,解放的興趣仍然更傾向于一種情境性的批判。或許正是意識到認識興趣理論的內在困境,哈貝馬斯在后面的思想直接放棄了探尋批判理論之規范基礎的認識論進路,轉向了語用學。哈貝馬斯利用語言哲學的成果發展了先驗反思的普遍維度,情境性的批判漸漸淡出了他的視野。麥卡錫評價到,認識興趣理論中的康德成分得到發揮,馬克思的成分則被一種社會進化理論所取代,社會進化理論建立在交往理論的基礎上,更像歷史唯物主義的“重建”,而不是“批判”。〔28〕
五、從交往理性批判反觀反思理論
的確,哈貝馬斯后期的交往行為理論可以更好地服務于他的初衷——批判理論的規范基礎的奠基。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哈貝馬斯的反思理論失去了理論價值呢?
就批判理論之規范基礎的奠基而言,交往行為理論相較認識興趣理論的優越性是毋庸置疑的。認識興趣理論通過自我反思來確定批判理論的規范前提,仍帶有傳統意識哲學的痕跡,可能陷入其理性獨白的困境;通過語用學轉向,交往理性實現了從主體性到主體間性的理性范式轉變,不同主體間通過在理想的交往情境中的對話可以達成有效共識。
然而,交往行為理論自提出以來也遭到了不少質疑。福柯認為,交往行為理論忽視了人類交往中普遍存在的權力結構,是一種交往的烏托邦;利奧塔指責哈貝馬斯的交往合理性的元敘事是令人生疑的,蘊含著話語暴力;查爾斯·泰勒則指出,哈貝馬斯主體間的理性對話依賴于先天條件的假設,是純形式的,在現實世界中并不存在,也難以實踐。
在批判理論內部,交往行為理論也受到哈貝馬斯的同事和弟子的批判。比如維爾默批判交往行為理論的真理共識論虛構了一個理想的交往情境,仍受傳統的客觀主義真理觀的影響,在后形而上學時代并無必要;霍耐特則吸收福柯的權力分析,批判哈貝馬斯對交往行為的抽象理解,試圖通過承認斗爭概念,把哈貝馬斯的交往理論發展為包含了社會沖突的承認理論。
不管是來自外部的批判,還是來自批判理論內部的批判,這些聲音要么批判交往理性的普遍主義,要么批判交往話語的形式化和理想性特征。我們知道,交往行為理論是哈貝馬斯語用學轉向的最重要成果。如果說在認識興趣理論中,哈貝馬斯混淆了批判與重建,并且傾向把后者化約到前者之中,那么到了交往行為理論,哈貝馬斯似乎走到了另一端——把特殊的批判消融到普遍的重建之中。這樣看來,交往行為理論所遭到的批判,在哈貝馬斯在批判與重建兩種不同的反思進路之中選擇后者的時候,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
實際上,從哈貝馬斯對批判與重建的區分來看,前期有關反思經驗的理論思考是批判與重建的混合,并傾向于把重建的工作融合到批判之中。但是從交往理性批判來看,哈貝馬斯的反思理論的內在張力問題在后期思想中并沒有真正得到解決,而是掩蓋了起來。
這種批判與重建的張力,不僅表現在哈貝馬斯的前后期思想中,也表現在整個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的發展史中。在批判與重建之間,以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為代表的批判理論第一代偏重批判,他們對資本主義文明的批判是極致的,以致于阿多諾《否定辯證法》的批判走向了徹底的否定。然而如此一來,批判理論自身的合法性也成為問題。哈貝馬斯正是不滿于這種純粹的否定,把批判理論的規范基礎的構建作為自己理論思考中最為重要的工作。
交往行為理論對批判理論規范基礎的建構可以說是卓有成效的,然而也削弱了批判理論的批判鋒芒。在哈貝馬斯之后,新一代的批判理論家發現,盡管交往行為理論仍不失為對晚期資本主義的一種意識形態批判,然而卻是過于形式化和理想性的。霍耐特的承認理論使得批判理論的規范要求重新落在社會的文化沖突之中,弗蕾澤的再分配政治則進一步把社會沖突推進到經濟領域。哈貝馬斯之后的批判理論似乎存在一種超越哈貝馬斯式的重建,回到第一代的激進批判的沖動。
從批判理論的歷史發展和當代走向看,哈貝馬斯在《認識與興趣》中的反思理論便具有了特殊的意義。盡管反思理論是不成熟的,然而其蘊含的內在張力,不但構成了哈貝馬斯前后期思想的轉折點,也使批判理論中兩種不同的反思模式從隱含走向明確。歷史地看,正是在批判與重建的聯系與張力中,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得以不斷更新。
另外,反思理論的含混性蘊含著某種有待發掘的可能性。交往行為理論發展了其中重建的普遍維度,忽略了批判的特殊維度。盡管認識論進路的規范奠基并不成功,然而反思理論對從康德到馬克思的思想運動的解釋仍散發著理論魅力。哈貝馬斯之后的批判理論要求重新激發批判理論中的特殊批判功能,這種理論訴求或許不但可以從第一代批判理論,也可以從哈貝馬斯的反思理論中汲取自身發展的理論資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