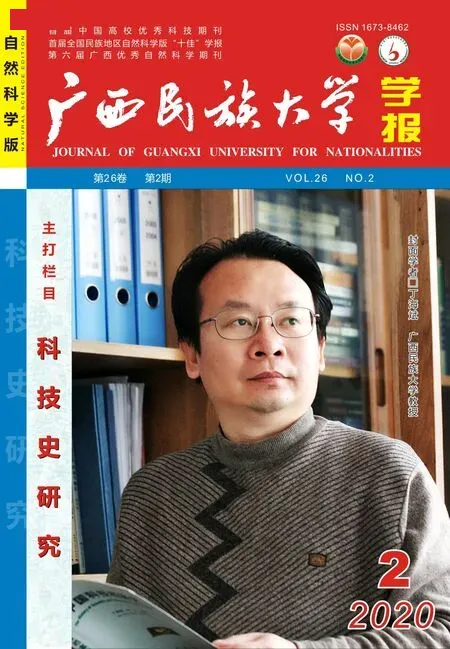跨學科的科技史家*
——丁海斌教授訪談錄
萬輔彬/問,丁海斌/答
萬輔彬(以下簡稱“萬”):海斌老師,您還記得我們是怎么相識的嗎?
丁海斌(以下簡稱“丁”):永遠難忘! 人生是由很多偶然組成的必然.如果沒有那次與您的偶然相遇,如今我們也就無法坐在一起飲茗論學.那天,您作為前輩、領導來參加科技史的學術會議,本應住單間,但您不肯搞“特殊化”,所以才有了與我這個睌輩、后生(當時我的確還很年輕)共居雙人間的特殊經歷.那天您還送我一本您的銅鼓研究方面的著作,至今記憶猶新.另外,由于會議期間和您同住一室,我們的房間陸續有學者來訪,因此我也有幸結識了不少科技史領域的專家、學者.您論學興致頗高,我們曾談起“李約瑟之問”等諸多學術話題,很是盡興.如今回首過往,真是心向往之.
萬:于是我們就成了朋友,一直相互關注對方的學術活動和成果.后來我發現您不僅在檔案學領域做出了很大成就,而且在科技史和歷史學兩個領域都有驕人的成就.
丁:獨特的學術環境、特殊的學術機緣、廣泛的個人興趣和發散性的思維方式,再加上近40年來在學術研究上從不敢懈怠,偶然間竟造就了今天我這樣一個跨學科學者.我個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向:檔案學——主要學術方向是檔案學基礎理論(檔案哲學)、檔案史(普通檔案史與科技檔案史)、檔案歷史語言學、電子檔案管理;歷史學——中國古代陪都學、沈陽地方史;科技史——科技文獻研究、“官科技”研究(可以擴展為“中國古代科技活動的社會組織形態”研究)等.其中,多數研究方向都形成了自己的理論體系.此外,我還發表過一些文化雜文.
檔案學是我的本學科,也是我學術研究的母學科.我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科技檔案管理學,是它讓我進入科技史界;因研究清代盛京檔案,我由此進入中國古代陪都研究領域.
20世紀90年代因我對檔案學基礎理論開展相關研究,從而進入文史哲的研究領域.研究檔案學基礎理論就必然研究檔案史,而從檔案史到歷史學,這具有學術上的必然性;研究科技檔案必然研究科技文獻,而科技文獻恰恰是科技史研究的基礎,所以隨著科技文獻學的建構便自然而然地進入科技史學科之中.近20年來,我與科技史界、歷史學界的交流相對多些,當然這也是各種機緣使然.
萬:您的36本著作,260多篇學術論文,橫跨檔案學、科技史和歷史學三個學科,說明您是精力充沛、成果涌流的跨學科學者.
丁:“成果涌流”不敢說,但我的確是一個努力治學的學者.努力+機緣=今天的我.當然,今天的我并不是最好的我.我經常說,最好的作品是下一部.不懈地追求學術真諦,永遠奔跑在追求學術之路上,不因種種誘惑而停下自己的腳步,這才是一個真正的學者所應具備的最重要的品質.盡管我也曾因那些誘惑而左顧右盼,但所幸并沒有停下自己的腳步.這是我人生最幸運的地方.
萬:聽說最初一些師友十分不理解,以為你是在打游擊,“打一槍換一個地方”,實際上您是抓住機遇,在幾個方向都做到了“做深做細,做大做強!”
丁:是的.具體而言,我是檔案學專業出身,又是科技哲學的博士.從1985-2020年,大約34年的時間,橫跨了幾個學科,近20年來我先后擔任過檔案學、中國古代史、中國科技史、法律史、民族學這幾個學科的導師.這些年來,我的主要研究領域和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八個方面:(1)檔案基礎理論(檔案哲學);(2)中國科技檔案史;(3)檔案歷史語言學;(4)中國古代陪都學;(5)中國古代科技文獻;(6)電子檔案管理研究;(7)中國古代科技活動社會形態研究(以“官科技”研究為主);(8)沈陽地方史.
我的思維比較活躍,在學術研究過程中一旦發現“新大陸”,我就會立馬深挖下去,在一段時間內會不遺余力,盡可能地形成一個比較完整的學術體系.在上述前5個研究方向上,學術體系都已趨于成型,有一種蔚然成林的感覺.我自己也頗感安慰,后來熟悉我的朋友慢慢也就理解了.
萬:我知道您在每個方面都寫了幾部書、數十篇文章.
丁:其余3 個方面,由于力所不逮,尚未建成體系.其中,“中國古代科技活動社會形態研究”我是想繼續做下去的,也希望更多的人參與進來,逐漸構成較成型的理論體系.
在沈陽地方史研究領域中,我參與了《沈陽通史》《沈陽文化史》《沈陽城市發展史》《沈陽工業史》等書的編寫工作.其中,與科技史關系最為密切的《沈陽工業史》三卷都是由我主持編寫的.
萬:從您的成果看,您在科技文獻學和科技文獻史方面做出的成就又好又快,讓很多以科技史為專業的人士都感到汗顏.請您談談這方面的體會.
丁:“又好又快”不敢當.正如我在前面所說,是科技檔案史的研究使我走進了科技史學科.我進入高校后,最早講授的課程是“科技檔案管理學”和“科技文件材料學”.當我開始講授這兩門課程時,驚訝地發現:當時的《科技檔案管理學》竟然沒有“史”的部分,也就是說,我們對我們的研究對象——科技檔案、科技檔案管理、科技檔案管理學的歷史幾乎一無所知.從認識論的角度看,這實在是一件巨大的缺憾.就像一個孩子是撿來的,我們既不知道他從何而來? 他的父母兄弟姐妹是誰? 也不知道他的成長過程.這個孩子站在那里,我們除了他的外貌之外,對他一無所知.這就非常尷尬! 沒有歷史,事物的完整性和清晰性就大打折扣.沒有“科技檔案史”的《科技檔案管理學》是極不完整的學科.
鑒于此,那時候我立志要解決這個問題.實話實說,科技檔案史作為檔案史里面的一個比較專門的領域,比較難.但是問題越難,最后的收獲就越多,最后的成果也越豐碩.事實上,我在科技史領域所取得的成果都來源于科技檔案史的研究,而且還遠遠沒有收獲完.
功夫不負有心人.1999年我出了一本《中國科技檔案史綱》;2007年我將其完善成為《中國科技檔案史》;到了2011年,又出了一本《中國古代科技檔案遺存及其科技文化價值研究》.這幾部書把這個體系的內容基本涵蓋了.它是我在中國檔案界的第一個具有個人特征的“標簽”,也是我進入科技史界的入門券.
萬:科技檔案史的研究對您后期的研究影響非常大,您后來又從科技檔案史發展到科技文獻史.
丁:我今年剛剛出版了《中國古典科技文獻學》,就是從科技檔案史的研究上發展而來的.此前還出版過《中國古代科技文獻史》.并且從古代科技檔案史又發展出了“官科技”和古代科技機構、科技制度方面的研究.這些方向的研究與科技檔案史的研究關系非常密切.我剛開始做科技檔案史研究的時候還很年輕,如果我現在再做的話,就不會像原來那樣做了.
萬:怎么做呢?
丁:我會把中國古代科技檔案史、中國古代科技機構史和中國古代科技制度史三方面并在一起做.我稱其為同步套裁.
萬:為什么要一起做呢?
丁:因為在研究科技檔案史的時候,一定會涉及機構的問題.如果沒有機構的話,又何來檔案之說呢?它是從機構來的,而且還一定和某些制度相互關聯.我當初在研究科技檔案史的時候,其實把科技機構的問題、科技制度的問題都密切接觸到了,所以如果現在來做的話,我會把這三個問題放在一起做.
萬: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往往是由淺入深,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由微觀到宏觀,由局部到整體.您的研究過程也印證了這一點.隨著時間的推移,研究領域逐漸擴大.
丁:確實如此.通過科技檔案史的研究,后來逐步延伸到文獻史、機構史、制度史.
萬:在科技檔案史的研究中,您對哪些部分的印象最為深刻?
丁:在科技檔案史的研究中,地圖檔案、天文檔案、醫藥檔案、工程檔案等方面都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對它們的史料挖掘最初都很艱難,都讓我印象深刻.但最深刻的還是對《周禮》的科技檔案史研究.
萬:《周禮》是一部重要的先秦史籍.您是怎樣研究這部典籍的呢?
丁:對于當時我這樣一個20多歲且絲毫沒有先秦史研究經驗的年輕人來說,是一件并不輕松的事情.幸運的是,我得到了史學前輩的指點:著名明清史專家孫文良教授指點我去看孫詒讓的《周禮正義》和鄭玄的《周禮注疏》.我在遼寧大學圖書館古舊閱覽室枯坐了整整3個月,方才啃下這兩部書及王安石《周禮新義》等《周禮》注疏與研究作品.在發表了《〈周禮〉中記載的科技檔案與科技檔案工作》一文后,還陸續發表了一二十篇論文.但是,《周禮》的相關研究還遠遠沒有結束,還有很多未解問題需要我們繼續努力去解決.
萬:我很期待您對《周禮》的進一步研究.
丁:在這里,我要批評一種學術研究的浮躁態度.有許多學者研究《周禮》,使用《周禮》的內容作為史料,但認真讀過《周禮》的學者似乎不多.在中國知網,我用《周禮》做關鍵詞進行檢索,得出文章數為926條;而使用《周禮》進行全文檢索,得出來的數字竟高達198,963.也就是說,有這么多學者在文章中提到《周禮》,難道他們都了解《周禮》是什么樣的一部書嗎? 事實上,《周禮》作為史料,被誤讀、誤用的情況極為普遍,其中也包括科技史界.
萬:能再深入地談一談您對《周禮》的研究嗎?
丁:《周禮》無疑是科技史研究中的一部重要的先秦史籍.我重點談以下幾點.
第一,《周禮》本名《周官》,它是講官制的.所以它主要與科技制度史有關,是研究先秦科技制度的重要史料,其“天、地、春、夏、秋”各篇都包含有科技制度方面的內容.佚失的《冬官·百工篇》與科技史的關系更為密切,應是主要記載手工業制度方面的內容.后人補代之以《考工記》,但其體例與《周禮·冬官·百工》并不一致,所以其缺憾是難以彌補的.
第二,不可將《周禮》所記簡單地作為西周的史實.《周禮》并不是紀實性作品,而是一種創造性作品.其中的一部分內容為西周及春秋戰國的歷史史實,也有一部分是作者自己的設計與設想.所以不能簡單地將其作為西周或春秋戰國的歷史史實,要區分歷史史實的年代——西周或春秋、戰國,也要區分史實與作者自己的設計與設想.在這個方面,我做了一點工作,通過尋找旁證的方法,基于目前的文獻和考古資料,對《周禮》中的文檔詞匯做了初步的區分,將研究成果《〈周禮〉文檔名詞再研究》一文發表在了《檔案學通訊》上.如果時間許可,我希望可以對《周禮》全書的主要內容做一個初步的考證.
萬:在中國科技史界,您的中國科技文獻研究很有影響.請問:您研究中國古典科技文獻,除了因研究科技檔案史而打下了相應的學術基礎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動機呢?
丁:我進入科技史界之后,發現科技史學科的教學活動中似乎沒有專門的科技歷史文獻學.我曾經問過一個權威的科技史研究機構:有沒有開設科技歷史文獻學的課? 怎么上的? 誰來上的? 他們回答:這門課實際上是他們機構里的一位歷史學背景的博士后在上,內容也只是一般意義上的歷史文獻學,并不是我們專業的科技歷史文獻學.后來發現即使個別高校開設了科技歷史文獻學這門課,但也缺乏專業性、系統性.實話實說,我們的科技史研究生這方面的學習和訓練很不夠.
針對這一情況,我就立志去做中國古代科技文獻的研究.把完成《中國古代科技文獻史》和《中國古典科技文獻學》作為我的學術使命.現在,我終于完成了自己的這項使命.換句話講,也算是不辱使命.
萬:能仔細談談您的中國古代科技文獻研究的基本情況嗎?
丁:目前主要成果有兩部:《中國古代科技文獻史》和《中國古典科技文獻學》.第一部書是中國古代科技文獻的通史,第二部書則是較完整且專業的中國古典科技文獻學著作.這兩部書可以搭建起中國科技歷史文獻學一個大的框架,它們可以擔負起中國古代科技史學科文獻學教材的使命.
當然,中國古典科技文獻學還有一些分門類的、細致的東西需要做.現在,我開始做數據庫方面的工作,正在和科學出版社合作.同時也感謝廣西民族大學科技史學科有這個條件能夠支持我部分經費.
另外有一件事值得一說.科技史前輩張秉倫先生曾經跟我通信探討中國古代科技文獻學的教材建設問題,當時我與張先生素未謀面,相互之間并不熟悉.張先生主動聯系我,其真誠溢于言表,實在是晚輩學者學習的榜樣.可惜我們未及深入溝通,先生即駕鶴西去,沒有達成我們之間的合作.惜哉惜哉! 愿先生天堂安好!
當然,關于中國古代科技文獻的研究,還有很多不足,還需要開展更多的深入研究.另外,中國科技史學科還需要開展《中國科技史史料學》方面的學術研究工作.當然,有《中國古典科技文獻學》作為基礎,《中國科技史史料學》的出現也就為期不遠了.
萬:在中國科技歷史文獻方面,您還有一些其他后續的想法嗎?
丁:首先,中國古代科技文獻的研究與教學要有一支專業隊伍.目前各高校這方面的專業人才還很少,應該加緊培養.我現在正在帶一些高校的中青年學者進行古代、近代科技文獻方面的研究工作,但人員較少且缺乏機制上的保障.廣西民大科技史學科如果開始加強這方面的教學工作,讓我做一點以老帶新的工作,應該會有一些成效.
萬:在考察您學術研究經歷的過程中,我發現您具有很明顯的發散性思維的特點.那么,從科技檔案史的研究中,您的發散思維起了什么樣的作用? 又取得了哪些意外的收獲?
丁:研究科技檔案史的時候,我從縱向和橫向兩個方面都發現了一些相關問題,并開始把自己的研究擴展到這些領域上.
縱向上,科技檔案是科技文獻的一部分,研究科技檔案史必然會研究科技文獻史.所以在我研究科技檔案史20年后,便又轉向中國古代科技文獻史和中國古典科技文獻學的研究工作.
橫向上,在研究中國古代科技檔案的過程中,我發現這些科技檔案主要產生于官方科技活動中,而且是中國古代科技活動的主體.于是,我又轉而進入中國古代“官科技”的研究領域(后來我更明確為“科技活動的社會組織形態史——國家科技、民間科技、宗教科技的歷史研究”).
萬:您使用中國古代“官科技”這個名詞是不是受“官文化”等名詞的啟發?
丁:是的.要想了解古代科技檔案的產生、內容、形態等問題,不清楚古代科技活動的社會形態、制度是不行的.這些科技檔案產生于當時的科技活動實踐,科技活動實踐是它們的本體.“官科技”是中國古代科技活動的重要特征.在這方面我最早的一篇文章是在1991年發表于《學術界》的《論“官科技”及其對中國古代和近代科技發展的影響》.
萬:您的中國古代“官科技”研究讓人印象深刻,能展開來說說這個問題嗎?
丁:中國古代的科技檔案主要來源于官方的科技機構.有沒有來源于民間的呢? 有,但是民間的多數不能夠保存下來,不成規模.所以我們現在所能看到的中國古代科技檔案主要是官方的,即“官科技”.
我覺得中國古代“官科技”的研究我只是起了個頭,比如說要做一個“中國‘官科技’(國家科技)發展史”,從古代、近代到當代,短時間內是無法完成的.目前,我在這個方向上的著作主要有兩部:第一部是《清代“官科技”群體的養成與結構研究》,這是我的博士論文,于2008年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第二部是今年正在出版過程中的《中國古代科技文獻官方、民間、宗教三大作者群體研究》,這個可以算是一部古代通史.上述研究還不能說已經構成了中國古代三大科技群體的研究框架.
萬:您在《學術界》發表了文章之后,似乎在“官科技”的研究方面中斷了一段時間,是從什么時候開始又重新進行了這個課題的研究呢?
丁:“官科技”的研究最初的確是我的“業余”研究.所以,在1991年《學術界》上發表《論“官科技”及其對中國古代和近代科技發展的影響》一文以后,停止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直到2004年我“帶藝投師”跟隨陳凡教授讀科技哲學博士,又開始對“官科技”接續研究.
與陳凡教授結緣大約是在2004年,我與陳凡老師等十幾位大陸學者受邀訪問臺灣高校.期間,我與陳凡教授一見如故,并因對中國科技史的共同關注而終生結緣.我原本是打算到中國人民大學讀博的,當時,我正因工作上難以脫身無法到中國人民大學讀博而苦惱(當時我已任遼寧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工作上不允許我長期離開崗位去北京讀博),而與陳教授的相遇使我得到了在沈陽讀博的機會.這是一件很幸運的事! 如果沒有讀科技哲學博士的這段經歷,我不可能在中國科技史領域走得這么遠.
在讀科技哲學博士期間及其后,我發表了幾篇關于中國古代“官科技”的文章:《李約瑟現象的“官科技”解讀》《論清代科舉與“官科技”》《清代“官科技”體系中的高層群體研究》.我的博士論文也是研究“官科技”的——《清代“官科技”群體的養成與結構研究》.也正因如此,陳凡教授更是成了我終生的良師益友.
萬:每個人在他的學術道路上都會遇到貴人指點,恩師提攜.
丁:在這里我還想談一件學術往事.1991年我的《論“官科技”及其對中國古代和近代科技發展的影響》一文的責任編輯是王光照先生.在發表我的文章之前,王先生特意寄書信于我,大氣磅礴的書法,讓我印象深刻,信中充滿了對年輕人的期許與鼓勵之情.
在我的學術生涯中,多次與一些前輩學者通信,他們表現出來的學者氣度令我終生難忘.前輩學者們的鼓勵、期許,對我的影響是巨大的,他們成為我前進的重要動力.在這里,我借這個機會,向王光照、吳寶康、王傳宇、陳智為、鄧紹興、王渝生、孫文良、張秉倫、陳凡、王雅軒、胡玉海、王海晨,還有萬老師您等前輩謹致謝忱.
萬:在“官科技”研究的問題上,您還有其他的打算或規劃嗎?
丁:從“官科技”問題出發,我將此問題擴展為“人類科技活動的社會組織形態”研究,即對“國家科技、民間科技、宗教科技”這三種科技活動的社會形態進行研究.我的中國古代“官科技”研究,實際上是這三個視角里面的一部分.“官科技”這個名詞具有中國文化的特征.如果在更大范圍內講這個問題,應該用“國家科技”這個名詞,它是指體制內的.當代中國的科技群體,主要是體制內的,少量是企業的(我將其歸到“民間科技群體”).第三部分是宗教的.當代“宗教科技”的力量弱了一些,但從歷史上看,宗教這樣一個群體在科技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們不能忽視的.按照這三大群體去研究科技史的發展,我認為是一個重要的科技史的研究視角,非常重要.就像現在我們在高校做老師,一定會受到高校的體制影響,而且影響非常大.我們要不停地填表,為什么填表呢? 因為需要對國家有個交代.國家、民間、宗教,實際上它代表的是科技體制.
科技史,本質上是人類科技活動的歷史.既然是人類科技活動的歷史,而科技活動又是一種人類的社會活動,就必然存在著人類科技活動的社會組織形態問題.既是如此,必然涉及人類科技活動在什么樣的空間中以什么樣的方式展開.這決定著人類科技活動主體的存在方式,決定著他們的工作目的、目標、方式與歸宿.這是古今中外的人類科技活動都存在著的一個問題,是一個涉及人類科技發展的根本性問題.它曾經極大地影響了世界各國在各個歷史階段的科技發展.當然,它是一個科技史的問題,也是科技哲學和科技社會學的問題.同時,它是一個歷史的問題,也是一個現實的問題.科技史界有責任對這個問題開展深入的研究.
關于以上問題的研究,我已經做了一些工作.但該問題主旨宏大,內涵極其豐富,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很多,希望得到科技史界同仁的關注!
萬:這是一個很重要的且很龐大的科研計劃,您覺得要實現它需要什么條件?
丁:我個人的時間、精力有限.將來有條件時,首先做一個“中國科技活動社會形態史”,希望能貫通古今.有條件的學者可以做一做國外的,特別是歐美的“科技活動社會形態史”.當然,除通史類研究外,一些斷代的、專題的甚至是更細致而微的研究也是重要的.
在這里,我也談談科技史學科的某些特殊性問題.科技史研究者有不同的研究類型和不同的研究思路.它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學科,這個學科的人員隊伍比較復雜,不是一種單純范式的學科.所以,以我個人的角度來說,我要談談科技史研究范式特殊性的問題.科技史研究,它有兩種不盡相同的研究范式,一種是自然科學的范式,一種是人文社會科學的范式.有一些純自然科學出身的人,他們受自然科學研究范式影響比較多,他自然而然把這種自然科學研究范式帶入到科技史的研究中來;另一部分人,比如說我,純文科出身,雖然接觸科技方面的知識比較主動一點、熱情一點,但畢竟是人文社會科學出身,所以具有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特征.從我的作品中大家可以看得很明顯,我的中國古代“官科技”研究就具有明顯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范式的特征.所以在科技史界,實際上有這么兩種不太相同的研究范式,然后他們研究的出發點、角度和方法都有一定的不同.
萬:這種不同是好事情,多元的研究角度、多樣化的研究隊伍,對學科本身的發展、完整性和研究內涵的豐富都是有好處的.我注意到最近一段時間您在歷史語言學研究方面頗有成就,并在科技歷史語言學方面已經有所涉獵,在這個方面您有什么計劃嗎?
丁:我在歷史語言學方面做了一些研究工作,發表了幾十篇文章,也有一部書計劃出版.其中涉及了一些與科技史相關的內容,如“地圖”“圖籍”等詞匯.我本人并沒有多少精力進行科技歷史語言學的研究,但有中青年學者跟我合作,以他們為主開展相關研究,如沈陽建筑大學的吳哲副教授(工程哲學博士)在工程史方面的歷史語言學研究.
我的歷史語言學研究,使用了文獻學、計量語言學、數字人文等方面的研究方法,這些研究方法在進行專業歷史語言學研究方面,具有一定的通用性,可以作為科技歷史語言學研究的借鑒.進行科技歷史語言學的研究,也是科技史研究深化的一種表現.
萬:作為一個跨學科的學者,您在跨學科研究方面有哪些感受呢?
丁:中國高校的現行體制不適合跨學科研究,因為學者早早地就被釘死在某個學科上了.學科評估、專業評估、學位點申報、項目申報、學者評價等一系列學科建設、學術評價活動都劃定了嚴格的學科界限,高校只需要“某一學科”的學者,而不是跨學科的學者.在資源分配上,也是具有很強的學科壁壘.某某學科的學者要申請其他學科的項目,是一件很難的事情.所以,如果要做一個跨學科學者,首先要少一點功利心.如果從功利出發,就不要做跨學科研究.跨學科研究是自然發生的,是純學術的,一般與功利目的無關.這是我個人的切身體會.
其實,跨學科本來是學術研究的常態.學術研究積累到了一定程度,必然是跨學科的.古今中外所有大學者幾乎都是跨學科的.試想:有哪個學科與哲學、歷史、語言、數學不無關系呢? 學科之間本就是相通的,相通是正常的,跨學科也是正常的,封閉是不正常的.但現在的學術機制把它反過來了,跨學科變成不正常的了,跨學科學者變成了稀有動物,起碼現行學術環境是不利于跨學科學術研究的.
就我個人而言,除功利性淡些之外,還有一個思維方式的問題.我做學問的方式都是從問題出發的,不把自己局限于某一學科.學術思維到哪里,我的研究就到哪里,從不考慮學科界限.但學者總是有職業的,有從事的、學習的和專業的,所以這些問題往往圍繞著自己的職業、專業展開.我本人是從檔案學專業(我的職業與我學習的第一專業)出發的,也受科技哲學(我學習的第二專業)的影響,但歸根到底是從問題出發.
在學術界,有些人學術界限觀念很強.我見過一些學者,研究遼史的要和研究金史的明確分開,研究清前史的與研究晚清史的分開.界限要分清,不分清楚就會被人笑話.我曾經也是一些人私下里講笑的對象,但現在很少有人笑話我了.因為我的幾個體系日趨成形,也得到了相關學科學者的認可,大家自然無話可說了.但這個過程是比較漫長的,你要挺過來才行.研究的問題多,自然花費的時間就多.35年過去了,我研究的幾個學科體系還在構建中,雖然說學無止境,任何研究都是沒有止境的,但多個體系的建設還是要比單一體系的建設艱難一些.我并不是一個“聰明人”,因為“聰明人”在這個功利社會中是不會做這種吃力不討好的事情的.我是一個透明的人,是一個執著的人,是一個不管別人怎么說只管做自己的事的人.現在有點做成的樣子了,就更不管別人怎么說我了.
萬:您在歷史學方面也頗有成就,特別是在中國古代陪都學和沈陽地方史研究中成就卓著,能簡要談談您是怎樣切入中國古代陪都學研究的嗎?
丁:由于地緣的關系,我早年研究過清代故宮檔案的問題.在這個過程中,我發現清代沈陽的歷史,其關鍵是它作為清朝陪都的歷史.當時我擔任遼寧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學院的重要研究方向之一是東北地方史、清史.為了帶動學院的老師們研究東北地方史和清史,也出于我個人的學術旨趣,我主動承擔了“清代陪都盛京研究”的課題.課題設立之初,我只是把它作為清代的特殊現象來對待.但深入研究之后,讓我大開眼界,發現陪都現象是中國古代長期存在的具有普遍意義的一種歷史現象.這種歷史現象,學術界此前并沒有進行認真、深入的研究,這激發了我新的研究興趣.在《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一書里,我對中國古代陪都現象做了簡單的描述,這部書成為我研究中國古代陪都學的濫觴之作.
萬:后來您在中國古代陪都學方面做了許多工作.
丁:截至目前,我在中國古代陪都學方面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一是完成了中國古代陪都研究方面的第一部斷代史——《清代陪都盛京研究》;二是完成了第一部中國古代陪都通史——《中國古代陪都史》,把中國古代陪都問題的研究大大推進了一步,具有標志性意義;三是目前我正在進行《中國古代陪都制度研究》(暫定名)的撰寫工作;四是關于主輔(首都與陪都)關系的研究,已經發表了一些論文,發現了一些有趣的歷史現象.除以上提到的著作外,這個方向上我還發表了一些重要的論文.
需要說明的是,我的中國古代陪都學的研究還涉及中國古代都城制度問題,我發現了“多京制”的問題、京都“主輔搖擺”問題.這些問題是很有趣的,值得我去繼續關注,也希望有更多的學者參加到這方面的研究工作中來.
萬:能再談談您的沈陽地方史的研究嗎?
丁:我的沈陽地方史的研究也是從《清代陪都盛京研究》這部書開始的.這部書出版后,我得到了沈陽地方史界同仁的認可,被他們“強拉”進沈陽地方史的研究工作中.后又陸續收到《沈陽文化史》《沈陽城市發展史》前輩主編的邀請,我無法拒絕,所以我又參加了這兩套書的編寫工作.后續又主持完成《沈陽工業史(三卷本)》的編寫工作.
萬:除以上研究外,您覺得您還會在哪些方面繼續進行跨學科研究呢?
丁:我思維的一個最大特點就是對新問題特別敏感,善于發現問題,我經常說我的最大缺點就是“停不下來”.
萬:這哪里是缺點,問題意識強是優點!
丁:在我當下的研究計劃里,等待完成的著作類選題大約還有20個,文章類選題更多一些.它們包括檔案學、歷史學、歷史語言學、科技史、哲學、文學等各個領域.檔案學、科技史、歷史語言學與當前的工作關系較大;哲學也是從檔案學延伸而來,目前在做的是經驗哲學,是從檔案哲學研究中擴展而來的,也是最近一兩年要做的事;文學的計劃主要是長篇小說和長篇雜文,也都有了思路,并各自有了幾萬字的初稿,但真正寫它們可能要到退休以后了.
萬:您作為一個跨學科學者,能談談您和科技史界的關系嗎?
丁:相比較而言,除了我的本學科——檔案學之外,我進入比較深的學術領域是科技史.所以關注并參加科技史的學術活動也相對多一些.當然,我的科技哲學博士的學習背景也是我加入科技史圈子的有利條件.跨學科研究者在科技史界比較多,他們的力量和他們的研究成果對科技史學科而言都是彌足珍貴的.科技史界的學術包容性強,像我這樣的跨學科科技史研究者也比較多,并沒有太多局外人的感覺.事實上,我也受到了科技史界的關注和青睞,有多次正式加入科技史專業團隊的機遇,東北大學科技史與科技哲學學科、北京科技大學科技史學科、山西大學科技史學科等國內多所高校科技史學科都曾對我青眼有加,但都因為種種原因沒有入職.像我這樣跨學科的學者,對高校學科方面的要求與眾不同.如果一個高校只有科技史學科,沒有檔案學、歷史學等相應學科,我是很難加入進去的,而廣西民族大學恰好科技史、檔案學、歷史學三者皆有,而且科技史學科、檔案學科都有很好的學術積淀,這給我入職廣西民族大學提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條件.于是,在萬老師您的邀請下,我欣然來到南寧.如今我已是廣西民族大學科技史團隊的正式成員,有一種歸屬感.
萬:在科技史學術研究上,您覺得還有什么遺憾嗎?
丁:在科技史學術研究上,我有許多遺憾.最為遺憾的是,我還沒有能夠帶一個科技史的博士和博士后,我的幾個學術研究方向都還沒有很好的學術傳承人.我希望在退休前的這些年中,能夠在檔案學、科技史、中國古代陪都學等方向上,培養出幾個好的學術傳承人來.
到目前為止,我做的與科技史有關的科技檔案史和科技文獻史要多一些.而科技制度、機構、群體、科技歷史語言學等方面,做的相對少一些.在這些領域中,我只是拓荒者之一吧,給大家開個頭.可惜的是,在科技史領域中這幾個方向上目前做的人還很少.我個人認為它們在科技史領域中的意義是重大的.
研究中國古代科技成果本身無疑是重要的,但我認為它是最基礎的,不是最重要的.那么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是中國古代的科學技術是怎么發展起來的?它為什么如此發展? 它發展的過程有什么經驗教訓?作為一種人類活動本身,它有什么樣的實踐規律? 有什么樣的活動機制? 是在一種什么樣的社會空間中活動的? 等等.只有了解了這些東西,才能最終解釋古人做了什么.希望我的工作,能為中國科技史研究的完整性盡一份綿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