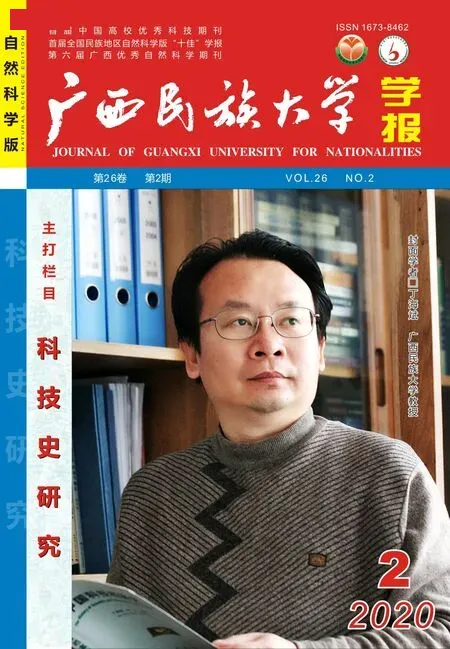基于一種改進評價方法的西部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特征研析*
韋艷玲
(柳州職業技術學院,廣西 柳州545006)
西部大開發是我國區域協調發展戰略的重要方面.西部大開發至今,西部各省份GDP、人均GDP 排名出現基本低位固化現象,與東部地區的整體差距并沒有明顯縮小,西部各省份之間經濟增長差距未明顯縮小,部分地區間差距反而擴大.例如,西藏、青海、寧夏、甘肅、貴州、新疆、云南等西部省份長期位列全國各省份GDP排名的倒數十名中,重慶經過多年快速發展從2014年才脫離了倒數十名.又如,內蒙古和新疆的人均GDP,2000年兩者分別為6502 元、7372元,2017年兩者分別為63764元、40036元,內蒙古從略微落后轉變為明顯領先.可以說,我國要全面建設小康社會,西部地區是重點難點,西部地區要加快、協調發展,盡快扭轉西部地區內部經濟發展失衡局面,對于西部地區及全國提升平均發展水平并進一步協調發展、共享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1 研究方法
區域經濟協調發展主要的研究范疇是研究區域之間的經濟關系,廣義上也包括區域內部經濟、人口、資源、環境等各子系統的關系.[1-10]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含義,一般是指區域之間的經濟活動聯系趨向緊密,各區域經濟均持續發展,區域經濟差異趨于縮小.[1-6]周文等提出一種空間計量模型進行實證;[7]王曙光等提出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ISSP 測度指標體系;[8]葉萬軍建立一種“耦合度”模型測算社會協調發展水平;[9]也有Fleisher B M 等國外學者研究了人力資本等因素對中國區域協調發展的影響,[10]等等.目前評價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無統一標準,學者覃成林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研究方面有重要影響力,[11]在該領域的研究比較深入且系統,其提出判斷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狀況評價的三個標準是區際經濟關系、區域經濟差異、區域經濟增長,并提出了相應測度的三個主要指標,即Moran's I指數、區域經濟增長水平變異系數、區域經濟增長率變異系數,[2-3]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狀況評價量化較為全面、合理,而且運用所提出的評價方法.但是,覃成林的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評價方法也存在不足之處,即計算得出Moran's I指數的值后,沒有進行顯著性檢驗.如果Moran's I指數的值在未通過顯著性檢驗的情況下,參與了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度的計算,則會導致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度計算的偏差,影響對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的正確評價.
本文在覃成林研究基礎上,采用此三指標作為本文指標,基于統計學理論,提出改進方法如下.
設S為所研究的區域總數量;i,j=1,2,…,S;x i,x j分別表示某年i區和j區的人均GDP;ˉx為人均GDP均值;W ij權重矩陣如果i區與j區相鄰則值為1,不相鄰則值為0;βt表示t年S個區域間GDP增長率的變異系數;y j為j區的GDP增長率,ˉy為S個區GDP的平均增長率.
第1步.首先計算Moran's I指數,用標準化統計量Z(I)進行空間自相關顯著性檢驗.如果通過檢驗則保留該指標,未通過檢驗則可除去該指標.通過顯著性檢驗且Moran's I指數為正數時,區域與區域之間的經濟增長可認為是正相關的,空間相關性顯著,區際經濟聯系緊密;通過顯著性檢驗且Moran's I指數為負數時,則可認為是負相關,空間差異大,區際經濟聯系微弱.
當通過顯著性檢驗時,再進行標準化數據處理,使其數值落在[0,1]之間.
Moran's I指數表達式為:

第2步.計算區域經濟增長水平變異系數.由于是反向指標,對其數值取相反數,再進行標準化數據處理,使其數值落在[0,1]之間.
區域經濟增長水平變異系數表達式為:

第3步.計算區域經濟增長率變異系數.由于是反向指標,對其數值取相反數,再進行標準化數據處理,使其數值落在[0,1]之間.
區域經濟增長率變異系數表達式為:

第4步.三個指標對于判斷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是同等重要的,故對選中的指標數據均衡賦權相加,得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度,其數值落在[0,1]之間.
2 數據計算
數據均來源于國家統計局網站、《中國統計年鑒》及各省份統計年鑒.西部大開發戰略正式實施時間始于2000年,考慮到數據的完整性、可比性,從西部大開發開始前兩年開始獲取數據,故本文采用1998-2017年共20年的相關數據以利于西部大開發前后對比.
2.1 計算Moran's I指數,并進行顯著性檢驗
計算得到1998-2017年西部Moran's I指數如表1所示.用標準化統計量Z(I)進行空間自相關顯著性檢驗,設顯著性水平=0.05,從表1的西部Moran's I指數Z值可以看出,在正態分布假設下,所有年份的西部Moran's I指數的Z值的絕對值均小于1.96,均未通過0.05水平下的顯著性檢驗.在顯著性水平=0.05情況下,可以認為不存在相關性,區域經濟的緊密性不存在正相關或負相關性,故三個指標中去掉此指標.

表1 三個主要指標數據Tab.1 The three main indicator data
2.2 計算西部經濟增長水平變異系數和西部經濟增長率變異系數
由于是反指標,對其數值取相反數,數據標準化處理后使其數值落在[0,1]之間.得到西部經濟增長水平變異系數及標準化后的數據,具體如表1和表2所示.
2.3 計算西部經濟協調發展度
由于去掉一個Moran's I指數指標,只留下其余兩個指標,故對西部經濟增長水平變異系數、西部經濟增長率變異系數兩個指標均衡賦權0.5后相加,得到1998-2017年西部經濟協調發展度時空變化如圖1所示.

表2 標準化后指標數據Tab.2 The standardized indicator data

圖1 1998-2017年西部經濟協調發展度時空變化圖Fig.1 The degree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western economy from 1998 to 2017
3 結果和特征分析
3.1 西部經濟協調發展的整體趨勢及階段性趨勢
從前文計算可以看出,1998-2017年期間,西部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整體趨勢是下降的,協調發展度降幅達36.9%,但階段性趨勢在不同時間段具有不同表現.
1998-2002年,西部大開發前后五年,西部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水平協調較高,協調發展度有小幅波動.
2002年以后有兩波明顯的下降過程:
一是2002-2005年,西部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度降幅達63.3%,主要原因是西部各省份自然條件和經濟發展水平各異,但西部大開發相應的各項政策均是典型的普惠制政策,各省份受益程度并不一致,使各省份發展的不協調加劇,體現為各省份的人均GDP增長率差異較大.如增長率最高的內蒙古人均GDP從2002年的8162元上升為2005年的16331元,增長100.1%,而增長率最低的云南人均GDP 從2002年的5366元上升為2005年的7835元,僅增長46%.
二是2007-2009年,西部地區經濟協調發展度降幅達57.2%,主要原因是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對全國及西部的區域經濟發展產生了明顯沖擊,從而引發了西部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明顯下降.[2]
2009-2012年,在出臺一系列政策的強刺激后,西部地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持續上升,協調發展度升幅達158.2%.這個變化過程也表明,中國的經濟增長潛力和應對政策促進西部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國際金融危機的不良影響,確保西部地區經濟穩健增長,穩住了經濟協調性下降的趨勢.2010年以來,深入推進西部大開發,對貧困地區援助力度進一步加大,[12]針對貴州等民族地區制定了相關支持加快發展政策,支持地方特色優勢產業,西部各省份發展程度比較均衡,如2009-2012年期間,人均GDP增長率除了最小的西藏(52.8%)外,其他省份均在60.8%到79.7%之間,保持快速平衡增長.
2012-2016年,協調發展度一直保持平穩,僅有微小的擺動和上升.這也在很大程度上表明,國家長期支持西部建設的效果已顯現,各級政府促進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的政策措施取得了實效,進一步消除了不利于西部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國際因素等影響.
2016-2017年,協調發展度下降了23.4%,西部經濟增長率變異系數為西部大開發以來的第二高值,僅次于2005年,說明西部地區經濟增長緩慢,而西部經濟增長變異系數較小,說明西部地區各省區市經濟水平差異小,總的來說,西部地區區域經濟協調發展水平有明顯下降現象.
3.2 西部的各省份之間和省份內部之間、次區域地區之間發展不平衡
首先,各省份在不同的年份中發展不一致,經濟總量小的省份一般發展較快.如西藏、貴州、云南、重慶等省份經濟增速通常超過西部地區平均增速.
其次,各省份內部經濟發展也不平衡,各地級市的人均GDP 也差距很大.比如2017年,內蒙古的鄂爾多斯人均GDP 為173046元,而興安盟人均GDP為26052元;四川的攀枝花人均GDP為92607元,而巴中僅為18163 元;廣西的防城港人均GDP 為79351元,而河池僅為20921元.這與資源是否豐富、工業基礎好壞等因素密切相關.
再次,次區域地區的經濟發展也不平衡,西南地區(西南六省份)與西北部分(西北五省份加內蒙古)的經濟總量之比由2012年的1.39∶1,上升為2013年的1.41∶1及至2015年的1.53∶1,差距有逐年擴大的趨勢.這和政策支持有一定關系,如在一些國家級經濟區域的數量上,西南地區總體上要多于西北部分.①在國家級新區方面,西南地區有4個(重慶兩江新區、貴州貴安新區、四川天府新區、云南滇中新區),西北部分僅有2個(甘肅蘭州新區、陜西西咸新區).在國家沿邊重點開發開放試驗區方面,西南地區有3個(廣西東興、云南勐臘、云南瑞麗),西北部分有2個(內蒙古二連浩特、內蒙古滿洲里).在已獲批的國家級城市群方面,西南地區有2個(成渝城市群、北部灣城市群),西北部分僅有1 個(關中城市群).西南地區還有2個國家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重慶、四川成都)、1個國家級金融綜合改革試驗區(滇桂沿邊金改區),而西北部分沒有.但是,在國家級經濟特區方面,西北部分有2個(新疆喀什、新疆霍爾果斯),而西南地區沒有.西北地區的開發和西南地區的發展并不平衡,使一些西北省份如青海、寧夏具有逐漸遠離經濟中心和邊緣化的態勢.
3.3 小結
西部大開發以來,西部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水平呈現“協調—不協調—逐步協調”的變化特征.從2000年開始,西部地區經濟協調發展水平出現了下降趨勢,從2004年開始下降加速,2004-2012年在低水平反復徘徊,2012-2016年沒有明顯變化,呈現上升中的平臺的特征,2016-2017年有明顯下降現象.總的來說,西部地區各省份經濟發展的協調度還不高,各省份內部發展也不平衡,并沒有達到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預期.
4 促進西部地區經濟協調發展的對策建議
一是堅持國家層面對西部地區的長期支持,包括給予資金、項目等優惠政策,強化政府的規劃引導和宏觀指導,以及支持引導西部地區切實融入“一帶一路”倡議、“兩橫三縱”城鎮化戰略等國家層面的發展框架,營造發展氛圍.二是加強研究制定跨省份的次級規劃,特別是對地理臨近而且經濟發展狀況類似或互補的省份,健全行政區劃和邊界的協調管理體系,在區域定位、產業布局等方面形成協調發展的向心力,引領促進科學發展.三是以產業為依托,筑牢發展基礎,不斷提高經濟發展水平,特別是注重提高落后地區的個人、企業、政府的收入水平.以工業為首要重點,持續積極承接東部等地區產業轉移,加快形成鏈條長、產能大、可持續的地方產業集群.四是建設打造不同層級、形式的發展極,強化中心城鎮、城市新區、中心城市、區域經濟帶、城市群等的集聚輻射作用.提升縣城及重要城鎮的城鎮化水平,進一步培養區域中心城鎮城市.